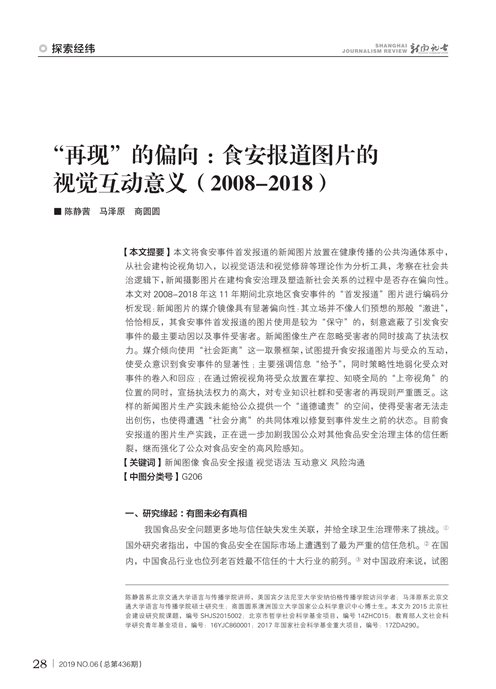“再现”的偏向:食安报道图片的视觉互动意义(2008-2018)
■陈静茜 马泽原 商圆圆
【本文提要】本文将食安事件首发报道的新闻图片放置在健康传播的公共沟通体系中,从社会建构论视角切入,以视觉语法和视觉修辞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考察在社会共治逻辑下,新闻摄影图片在建构食安治理及塑造新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偏向性。本文对2008-2018年这11年期间北京地区食安事件的“首发报道”图片进行编码分析发现:新闻图片的媒介镜像具有显著偏向性:其立场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般“激进”,恰恰相反,其食安事件首发报道的图片使用是较为“保守”的,刻意遮蔽了引发食安事件的最主要动因以及事件受害者。新闻图像生产在忽略受害者的同时拔高了执法权力。媒介倾向使用“社会距离”这一取景框架,试图提升食安报道图片与受众的互动,使受众意识到食安事件的显著性;主要强调信息“给予”,同时策略性地弱化受众对事件的卷入和回应;在通过俯视视角将受众放置在掌控、知晓全局的“上帝视角”的位置的同时,宣扬执法权力的高大,对专业知识社群和受害者的再现则严重匮乏。这样的新闻图片生产实践未能给公众提供一个“道德谴责”的空间,使得受害者无法走出创伤,也使得遭遇“社会分离”的共同体难以修复到事件发生之前的状态。目前食安报道的图片生产实践,正在进一步加剧我国公众对其他食品安全治理主体的信任断裂,继而强化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高风险感知。
【关键词】新闻图像 食品安全报道 视觉语法 互动意义 风险沟通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研究缘起:有图未必有真相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更多地与信任缺失发生关联,并给全球卫生治理带来了挑战。①国外研究者指出,中国的食品安全在国际市场上遭遇到了最为严重的信任危机。②在国内,中国食品行业也位列老百姓最不信任的十大行业的前列。③对中国政府来说,试图挽回“中国制造”的食品声誉,也成了极为重要的议题。但在2000年以后,食品安全事件在生产的各环节,多个品类中仍持续出现,不但频次有增无减,且历次事件尚未有一个积极主体出来就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和日后预防机制进行有效解答。这逐渐导致了公众对执法权力、市场主体和专业知识社群等多个路向的信任断裂。④在建构主义者的眼中,风险,并不是一个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客观统一的连续实体;相反,它是一个与过去、现在有关,并可以预测和避免“非预期未来事件”的“暂时性概念”。换言之,食品安全风险本身是流动的、被构建起来的。人们眼中的风险,并非存在于单一的时间面向中,而是与“相关联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同塑造的结果。⑤现代社会的风险不但包括“实存风险”,还包括“被建构起来的部分”。因此,风险是一种“感知”(perception);构建感知的主体,不仅包括受众本身,还包括传递信息的媒体以及其他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媒介在整个食品安全感知与沟通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对风险进行着构建。甚至有学者指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逐渐演化为“食品安全报道问题”。⑥
在食安报道的媒介中,视觉手段受到从业者的高度重视:在新闻专业社群中,“视觉呈现效果”是“好故事”的重要选择标准。⑦对学界而言,新闻摄影的突出传播效果虽已成为共识,但有关其风险建构机制的深入研究尚显不足。新闻图片直观性、形象可感性高,同时不受阅读者年龄、性别、语言和时空的限制,⑧当读者看到新闻图片时,会对这些图片的内容与形式做出反应,从而实现这些图片的语意价值。从外在表现来看,图片与文字报道最大的区别在于——新闻摄影因其“形象性”、“标记性”等特征,具有被公众自觉接受的视觉说服潜能。⑨从传播过程的本质来看,新闻图片之所以吸引受众,并带来不同的传播效果,是因为视觉传播过程本质上与口头传播或书写传播有着显著区别。视觉传播基本依靠的是直觉,是非线性的,而口头传播和书写传播是可分析的和线性的。⑩此外,通过新闻摄影所再现的事实、态度和立场,都更为隐蔽。新闻图片在发挥强大见证功能的同时,[11]也涉及国家政策的框架。[12]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图像,包括新闻摄影图像在内,都是有意设计的结果——“all photos lie”。[13]换言之,有图未必有真相。“再现的真实”(或表征真实)与“真实”应该加以区分。对于新闻业中的“视觉再现的信度”的考察尤其必要。
目前,国内外对于食品安全事件报道图像的视觉意义生成和语法关注甚少。国内已有研究大多从图片编辑策略、价值导向及符号学分析等方面针对突发事件报道(尤其是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报道)及涉及国家元首、重大政治事件等展开分析,尚未对新闻图像的偏向性和视觉再现的信度开展深入研究。既然新闻图片的建构机制与文字报道迥异,那么,新闻图片是如何开展媒介建构的?生成了何种新的互动意义和社会关系?其视觉再现的信度如何?是否存在偏向性?
二、文献回顾
1.食安“高风险感知”影响因素
基于食品的风险感知状态可细分为“风险感知过高”、“风险感知过低”及“风险感知调整”等不同状态。[14]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已对我国公众的食品安全“高风险感知”和“高度不信任”现状达成共识。已有研究指出,政府和媒体等主体对公众风险感知有着重要影响,如政府规制因素、媒体角色等,[15]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信息来源。有研究强调“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知晓程度”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认为其对化解食品安全风险有基础性作用。
新闻媒介在我国的食安风险感知中起到了何种构建作用?国外已有研究持消极态度,认为一方面媒介容易夸大食安风险;另一方面公众也乐于接受有关食品安全风险的负面信息——媒体对于食安事件的夸张报道,会引起公众的过激反应。公众对负面消息比对正面消息更为敏感和易接受,媒体对食安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可能对公众的认知产生负面影响。相对于正面消息,提供负面消息的机构或个人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当负面消息出现时,即便是尚未获得医学或科学论证,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也会大幅下降。[16]除了媒介构建之外,研究者还聚焦于公众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与风险感知有关研究,[17]但争论仍在持续。[18]公众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之外的一些其他变量,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会产生影响:如陌生性、可信性和不可预测性容易影响公众的恐慌预期,“被察觉到的食物危害事件的可怕程度”和陌生程度越大,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评价越消极,担忧越大;韩国和意大利的研究显示,消费者如果对政府的卫生检查工作、食品制造商和消费者保护机构的信任度比较低,公众的风险感知会陷入更大的恐慌中;直觉行为控制、过去行为也会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
中国公众对于本国食品安全已经形成了一种顽固的“不信任态度”,且这种态度在不断地被强化和累加。其根本原因是公众对监管部门、科学社群、市场主体的信任发生断裂,继而导致社会共治在公权力执法、知识治理、市场规训等多个维度“失灵”。[19]信任不平衡理论认为,人们在进行风险判断时,会优先接受负面信息刺激,形成对事件的不信任态度。[20]这种“不信任”使得某类食安事件出现时,公众会自发地将风险和危害延伸至整个食品领域。这种“不信任感”一旦被受众确立,或在多重刺激下(如频繁的负面报道)得到加强,那么受众将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并在日后的风险沟通中很难被改变。与此同时,受众自身的“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却很容易启用——一旦个体形成了一种明确的初始意见,它则会以一种有偏见的方式存在。当受众再次接触到事实性信息时,“情感”和非理性因素更容易发挥关键作用。[21]再者,受众在进行判断与行为决策的时候,容易忽视基本概率。[22]在食安风险交流体系中,公众处于信息流动的弱势一方,面对食品安全常识及事件时,公众存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当面对媒体报道的某一事件,或是媒体在某个时期密集报道某类事件,公众就会主观认为该事件发生概率比实际生活中高很多,并逐步将自身置于“媒体共同缔造的‘中国食品普遍不安全’”的这一“媒介化假象”[23]之下。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有很多企业或某类食品,一旦发生过很恶劣的安全问题,就很难再恢复的原因。[24]2.媒介构建的偏向性
大众媒介可以被视为整合观念和文化的框架,因此,对媒介构建行为的考察至关重要。然而,媒介构建的食安现状距离“现实”有多远?其再现的信度如何?
新闻从业者对“现实事件”的主观叙述是“存有倾向性”的。新闻报道不但拥有“性格”,而且还有意识地通过个性特征和文化符号来提高其“亲近性”。[25]同时,它还具有整合国家共同体和强化社群价值、身份认同的功能。新闻从业者们通过使用符号化和叙事,把他们所讲述的震惊事件放置在读者易理解的框架内。这样,新闻报道对受众而言就不是一连串与他们无关的事件,而是“由新闻事实构成的符号框架”。[26]Dan Berkowitz则更为精辟地指出,新闻报道实质上是一种“有关新闻故事主题、情节开展和主要人物应该是什么样的‘精神目录’”。[27]在主观加工的过程中,媒介立场和新闻从业者的偏向性也融入到新闻产品中。甘惜分指出,新闻报道是“选择”的结果,其本身具有主观倾向性。而新闻图片的使用,作为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主观构建的结果,会受到来自政党、机构、媒体及新闻从业者的影响。[28]不少西方新闻媒体明确地为自身的新闻生产活动定下基调:它们把自己看成是国家形象的把关人。[29]甚至在一些特定时刻,文化功能成为新闻生产第一要务。Barbie Zelizer考察了新闻记者在重构新闻事件时的具体实践。Glaser和Strauss则指出,即便是作为“理想型”的新闻权威,中介化话语和职业话语中都存在“策略性选择例子”的情况。[30]同样地,这种策略性选择也存在于新闻图片的使用中。例如,美国《新闻周刊》倾向使用符号化的新闻图片来展现“自己的认识”。[31]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从业者通过文字和图片来使自己成为这些议题和事件的解释权威。
对突发新闻事件的再现,记者并不总能保证及时出现在第一现场。新闻权威的塑造不仅事关语句层面,还关乎对整个故事的“修复”。读者最后看到的只是叙事者最有把握的部分——即新闻记者和媒介塑造修复后的结果。[32]例如,在肯尼迪总统被刺事件发生之时,美国记者所做的不是去卷入与事件有关的行动(因为刺杀事件发生之时新闻记者并不在现场),而是通过对这些行动的叙事来重塑自己的社群权威。新闻记者通过使用“提喻法”,即以部分代表整体的方法,来为自己的报道增值。[33]在一些突发灾难事件中,记者成为国家创伤治疗仪式的主导者。在对这些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媒介技术被认为是新闻记者得以完成共同体修复的重要工具,包括图片、电影在内的媒介技术,都起到了协助新闻记者开展事实重构的作用。[34]3.作为“社会见证”的新闻图像的运作机制
新闻图片作为一个重要角色,形塑人们的集体记忆已经有一百多年。特别是与重大灾难有关的新闻图片,在全球新闻报道中得到了高度重视。在美国新闻史上依靠图片进行成功报道的典型个案有:1937年发生在美国Hindenburg Zepplelin的爆炸案,1968年越共解放阵线间谍在西贡被处死,[35]1995年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市的大爆炸,[36]以及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等。[37]在这类新闻报道中,对受害者和见证者的再现一直以来是媒体呈现的主要面向之一。
在Kitch看来,有关灾害和危机的新闻报道,在第一阶段通过文字和视觉所传递的震惊和不敢相信,提供了有关社会分离(separation)的细节见证。[38]美国《新闻周刊》针对“9·11”事件发行了纪实照片的特刊。泽利泽指出,有关目击者的影像展现,是对亲历者的“承受见证”的再现。其在实践和空间上凝固了“承受见证”的行为,展现了这种“被迫的关注”。[39]这样的新闻图片让读者像摄影师一样卷入到可怖时刻的艰难见证中。[40]新闻媒介向受众提供了灾害场景的见证、受害者的证词和施救人员的安抚。新闻媒介使用了一定的范式来呈现各群体对灾害的哀悼。其中一幅新闻图片成为了爱国复原情感叙述中最广泛使用的元素。[41]再现“见证”的过程中,对受害者和事发现场的呈现非常必要。因为,对于事件及亲历者的见证,是重新治愈社会的关键手段。照片可以高效地帮助人们展开对事件的回忆,是记忆本身的重要印记。[42]泽利泽认为,这些“承受的见证”需要一个空间去把创伤可视化,从而去动员社会个体。这样,通过扩大的集体性,社会个体才可以走向复原。[43]在她看来,照片是具有档案性质的辅助工具,帮助人们处理“过去”的创伤。在有关创伤事件的见证作为扩大的集体的一部分被召唤出来之前,照片为个体保留了足够的空间,去对事件进行细节而具体化地存档。此外,还有多种与图片相关的仪式性实践:如对照片的展示、谈论、参观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对于创伤的事后回应去帮助个体加固与他人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照片填补了空间,使人们建立“道德谴责”成为可能,使个体得以走出创伤。通过这种形式,照片帮助个体去回归共同体,回到创伤发生之前的团结阶段。[44]对新闻图片更具体的作用机制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人们是通过“直觉”和“情感”来对图像做判断的,他们对自己所经历的视觉信息和逻辑思维做出反应,如证明、强化或推翻之前的直觉反应。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图片独有的功能在于——新闻图片可以激起和催生公众的愤怒。此外,人们的眼睛会对视觉刺激进行吸收,使得大脑对有关的图像产生感应。这样,人们就会把单个的视觉要素看成一个整体,而非看作不同部分——这与人们认识线性的文字信息不同。人们在阅读新闻报道文字的时候,是通过“叙事的逻辑”来感知故事的特定部分。例如,段落会被人们与同一故事当中的其他部分加以区分,但人们看待视觉图像的时候却不会把同一幅图中单独的视觉元素与其他部分进行区分。[45]4.健康说服与视觉再现的信度
冈瑟·克瑞斯(Gunther Kress)和范·勒文(Theo van Leeuwen)两位研究者多年来专注于视觉理论研究其理论框架受到语言学家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的功能语言学启发,在多模态话语分析中多有运用。他们将社会符号学运用于视觉图像的模态(modality)分析,从而为研究图像文本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模态被认为在建立和维系社会互动,特别是在人际元互动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视觉语法理论框架中的“模态”是镶嵌在互动的过程当中的,其定义不是关于表征(或再现,representation)多么逼真,而是有关人们如何建构和接收这些表征的信度。“视觉语法”认为视觉图像同语言一样,具有意义构建的功能:再现、构图和互动。其中图像的互动意义主要是从三个维度进行考察,即观看者与被摄物的视线接触、社会距离以及呈现出来的态度。克瑞斯和勒文提出的图像行为(image act)与语言学中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的分析框架非常类似;图像行为可以塑造新的社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图像生产者的缺位,在图像的观看过程中,文本的生产与感知发生了断裂,这使得社会关系是以“再现”,而不是以“发生”(enacted)的形式出现。[46]近几年来,勒文更新了视觉语法理论在互联网时代的适用性,认为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给视觉模态研究带来了影响:其一,是内容生产的新模式引入了新的支持手段,影响了视觉标识。二是由于颜色的使用越来越标准化,而不是像好莱坞电影和广告那类主观真实范畴使用了梦境和幻想色彩,这使得事实和虚构更难以区分,审美元素进入了新闻摄影这类事实取向的视觉范畴之中。[47]在健康传播的视觉说服领域,对视觉元素的关注较多,但对食安报道图片作用机制的研究并不多。Kiwon Seo等研究发现,[48]文字和图片组合起来形成的说服框架是通过“恐惧”来形成对受试者的说服的。“恐惧”是说服产生的中介效果。用文字和图像结合,可以降低受试者的感应抵抗(induced reactance),在配有图片的情况下,受试者所产生的恐惧水平比无图时更高。[49]健康说服发生机制研究者还发现了“图片优先效果”:即文字和图片搭配比单独使用文字更容易被记忆。根据Zillmann提出的示范理论(exemplification theory),个体观念的形成和维持是建立在抽样呈现的直接或间接经验所描述的现象基础之上的。受试者对所提供信息的记忆反应能够形塑他们的后续反馈及对信息的整体判断。[50]细化到视觉说服的人物元素方面,研究发现,让图片中的人物与受众产生联系,将印刷材料中的人物角色与受众的“相似他者”相关联,可以提高防治信息与受众的同类程度。[51]
三、研究设计及方法
本文借助“视觉语法”的框架,考察食安事件新闻图片再现的新社会关系及其再现的偏向性。已有研究发现,北京地区的食安事件报道频次高于中国的其他城市,[52]且地方性媒体在突发事件的传播中常常扮演了关键角色,[53]因此,本文选择北京市食品安全事件首发报道作为样本,并选取中国的标志性食安事件——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出现的2008年作为抽样起点。选择首发报道的原因,一是事件的后续报道一般只是零星出现:11年来北京食安事件大多数缺乏后续报道,仅有个别进入诉讼程序的事件得到了媒体的后续关注。二是首发报道在议程设置和传播效果中作用突出。
1.编码理论
基于克瑞斯和勒文的视觉语法理论,本文对食安图片的媒介构建内容和模态进行微观考察。
对图片互动意义的考察属于视觉再现模态的测量指标,主要经由三个维度:视线接触、社会距离以及态度。第一项“视线接触”指的是图像所再现的人物(represented participants)是否与观看者有视线接触,即图中再现人物通过目光指向观看者,以此建立起来的一种想象中的“接触关系”。[54]当图中再现人物的目光指向观看者、形成视线接触,即“凝视观看者”时,表明图中再现人物向观者“索取”意义,代表了一种明确态度的传达。而相反,“未凝视观看者”则仅代表信息的“给予”。
第二项“社会距离”主要根据镜头取景框架的大小来划分,可用于界定读者在图片所设置的新闻场景中的卷入程度。这类关系共有三种:人际距离(intimate/personal)、社会距离(social)和非个人距离(impersonal)。人际距离指在具备人物参与的图片中,只能看到图中再现人物膝盖及以上的部分,无法看到人物整体的形态或动作;在不具备人物参与的图片中,只能看到一个物体,或该物体的某一个部分,比如对问题食品的特写。社会距离是指图片的取景为中景,观看者能通过新闻图片看到一到三个图中再现人物的整体形象以及部分周边环境,这一取景距离可以使读者看清图中再现人物的表情以及形体动作。非个人距离则是指图片的取景为远景。例如在具备人物参与的一些新闻图片中,至少有四个及以上的参与者出现,且人物在画幅中的大小通常不超过画幅高度的一半。这种距离多用来表现开阔的场景或远处人物及空间背景。而不具备人物参与的图片,使用非个人距离时主要是对整体环境的表现。
卷入度方面:“人际距离”情况下观看者对于图中场景的卷入程度很高,与其他距离相比更能引起观看者的情绪反应;“社会距离”情况下,图片的主体(人或物)完整地出现在镜头内,并且能够看到一些周边的环境,能够使观看者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图片所呈现的场景,但相比人际距离的呈现不会引起观者太大的情绪波动;非个人距离则是指更远更大的环境,观看者会感觉到置身事外,很难对图中所再现的人和物产生情感关联,使得观者对于事件难以产生高度关注。
第三项有关“态度”的判断,克瑞斯和勒文选用了多个视角来分析图像所再现的人物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如主观性和客观性等。在主观性的图像再现中,通过分析画面的不同角度,可以分析图中再现人物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与态度。根据样本中图片的整体特点,本文选取了其中三个维度(俯视、平视、仰视)来测量样本图片试图传达的关系与态度。“平视”的正面角度带给观看者感同身受、融入其中的平等感。“俯视”的垂直角度代表着观看者的强势,同时能够对所拍摄事物一目了然。而“仰视”则代表了所再现人物处于强势地位。
2.抽样设计
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其影响之大直接推动了次年《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因此2008年被视为我国食安治理过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地区选择方面,有研究数据表明在2004-2012年间,全国被曝光食品安全事件最多的地区是山东、广东和北京,其中北京被曝光事件占15.9%,[55]国外已有研究也指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点,即食品安全发生率与城镇化程度正相关;城市食品安全系统的复杂程度和媒体报道的城市偏见有增强的趋势。[56]从区域角度来看,选择北京这一地区报道的原因在于:该地区食品安全事件比例之高值得关注,另外,北京也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典型代表。
本文对11年来北京地区食品安全首发报道的数据采集渠道为: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食品伙伴网[57]以及“掷出窗外”网站[58],分别代表执法权力、市场主体和专业知识社群三个主体。[59]数据采集、清洗后,整理出首发报道169篇,分布如下:2008年7篇、2009年10篇、2010年7篇、2011年20篇、2012年14篇、2013年17篇,2014年12篇,2015年14篇,2016年31篇,2017年23篇,2018年14篇(见图1)。随后对这些报道中所使用的新闻图片进行整理,发现有62篇首发报道中无配图,有配图的报道共使用图片236幅,最后共获得全样本236个(N=236)。首发媒体的类型方面,纸质媒体占大多数,为79%;网站占8%;电视占7%;社交媒体和环保组织分别占4%和2%。
在食安治理转型语境下,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是:食安报道图片构建的媒介镜像为何?新闻媒介通过食品安全报道的视觉图像构建了何种互动意义(社会关系)?这一构建过程出现了何种偏向性?
四、研究发现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借用图像再现的互动意义理论(representation and interaction)框架,对236个图片对象进行了分类编码及分析。首先将236幅新闻图片按照“是否具备人物参与者”进行编码,发现具备人物参与者的图片数量为109,不具备人物参与者的图片数量为127;继续对109幅具备人物参与者的图片整理后发现,除去一幅其中人物是和事件毫无关联、作为背景出现的图片外,人物可以分四类进行编码:1.执法人员;2.不法商贩/涉事人员;3.问题食品受害者;4.食品检测员。其中有17幅图片,出现两类以上人物同框的情况,因此按照人物进行数量统计,执法人员共出现37次(占比33%),不法商贩/涉事人员共出现70次(占比62%),问题食品受害者出现3次(占比2.5%),食品检测员出现3次(占比2.5%)。在不具备人物参与者的127个研究对象中,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1.报道涉及的问题食品或违法使用的添加剂;2.问题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环境;3.其他。(表1 表1见本期第35页)
下文借助图像互动意义的框架对236个研究对象进行总体分析;另外,为了考察新闻图片对食安治理不同主体的行动叙事,笔者特针对具备人物参与者的109幅图片进行了单独分析,考察四类行动主体与观看者的互动情况。
1.图像再现的聚焦环节:食品加工
食安问题存在于食品流通的各个环节,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发现,在所有236幅配图中,新闻媒体最关注的事件现场出现在食品的“生产加工环节”。通过对11年来169篇首发报道的分析,报道曝光的食安事件主要集中在“生产加工环节”。(图2 图2见本期第35页)这些问题食物大多由不具备资质的黑心作坊生产。这些作坊零散分布在偏远的村庄或郊外,商贩得以在这类隐蔽地点进行违规加工生产,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如2014年11月《法制晚报》在两个黑心作坊用“白药”浸泡豆芽的报道中,用了记者偷拍的作坊老板将豆芽从药水里捞出来的新闻图片。媒体对食品加工操作、加工环境的呈现,将这些曾经是“秘密”的信息摆在公众的面前,能够有效补充处于弱势地位的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
Hodge和Tripp将模态定义为“对内容(或文本)的感知真实”。也就是说,模态被认为是或多或少构建着真实的表征的一种属性(或属性组合)。克瑞斯和勒文强调,模态并不是关于表征事物的真伪与否,而是“传播者对表征所做的判断”和“希望受众做出的判断”,以及“受众成员实际做出的判断”的共同产物,“利用了各种可能作为情态判断基础的线索”。也就是说,模态不是关于“表征是否为真”,而是“一个给定的‘命题’(视觉的、语言的或其他方面的)表征是否逼真”。[60]在本研究的样本图片中,对人物的再现的模态远低于其他类型图片。(图3 图3见本期第36页)高模态图片中,对人物的高模态再现(49%)远低于无人物图片(69%)。中等模态的再现中,对人物的中等模态再现(36%),也低于无人物图片(44%)。样本中的新闻图片对人物进行了一定的图像处理,如调色等。部分图像呈现昏暗不明,光线不足,影像模糊等,与自然光线下的人物呈现有较大的区别。
对人物再现的场景和环境,主要集中在销售现场(37.34%)、加工现场(29.27%)和储存现场(20.18%)。在无人物图片中,再现的环境按频次高低依次为:加工现场(52.40%)、销售现场(38.30%)、安全卫生检测现场(23.18%)、储存现场(12.9%)、生产现场(4.3%)(图4 图4见本期第36页)。这与首发的文字报道描述问题存在的最主要环节基本一致,主要出现在生产加工(55%)和流通销售(25%)和餐饮消费(13%)环节。但是,对餐饮消费中出现的食品问题,样本图片中展示的很少。
2.社会距离
有针对性的媒体报道不仅能够影响公众的健康知识和态度,同时也能够影响公众的行为。[61]新闻图片取景大小体现了互动关系意义:取景体现的距离可以影响读者对待事件的“卷入”程度,继而进一步塑造读者的认知并影响其行动。在日常互动中,“距离”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图像语法所再现的距离,实质上是一种“想象的社会关系”的构建。对于“人际距离”和“社会距离”这两种距离的运用,体现了新闻媒介在试图拉近所发生的再现事件、人物与受众之间的关系;试图凸显图片中再现主体的权威性,使读者对所报道的事件产生“接近感”和“卷入感”。从读者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这一角度来看,这一图像语法的使用可以促进食安报道图片与观看者的互动,使观看者意识到食安事件的显著性。
图像语法中的社会距离这一指标系统与“权威的彰显”有直接关系。[62]图片的距离越近,越能凸显所再现人物的显著性和权威性;距离越远,再现人物所能引起观者的关注程度也越低。
样本中距离出现频次最高的是“人际距离”和“社会距离”,一共占比约94%。其中,“人际距离”[63]占比50.4%,“社会距离”[64]占比43.6%,“非人际距离”占比5.9%。将再现的行动主体类型加以交叉分析的话,样本中新闻图片对再现人物的偏向性则非常明显。“人际距离”的描绘对象主要集中在执法人员;而对违法人员的呈现,则以“社会距离”和“非人际距离”为主。这一人物再现策略所生产的互动关系,使得观看者对于执法者行动的卷入感更高,对于违法人员行动的卷入度则较低,观看者不易与自身的生活关联起来,相应地对事件带来的危害不易产生触动。
3.视线接触
受众是“卷入”还是“抽离”(detachment)与新闻图片中展现的人物与观看者是否形成视线接触也密切相关。样本图片所再现的各行动主体的人物图片统计信息见(表2 表2见本期第37页)。总体而言,图片再现的行动主体主要集中在违法人员(占比64.2%)和执法人员(占比33.9%)两大类。
如(图7 图7见本期第38页)所示,样本中的新闻图片中所展现的人物存在于观看者的“视线接触”的,仅占极少部分。产生视线接触的行动主体主要集中在执法人员这一群体。“视线接触”的分析结果迥异,在具备人物参与的研究对象中,只有4幅图片再现的人物产生了“凝视观看者”,仅占样本总数的1.7%;而“未凝视观看者”图片再现有232幅,占样本总数的98.3%。
统计结果表明,食安事件报道的新闻图片并未采取有效的方式去“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和对风险认知的思考和“回应”,没有能够邀请受众亲身去“定义”这个事件,没有试图把受众纳入食安事件牵涉的各种“关系”之中。其新闻图片生产的重点仅仅侧重“信息给予”,用于辅助新闻报道文本告诉受众食品安全事件的基本情况。换言之,食安事件首发报道图片试图展现的媒介镜像,其立场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般“激进”,恰恰相反,食安事件首发报道的图片使用甚至是较为“保守”的,没有针对目前食安治理的多个行动主体展开充分的叙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引发食安事件的最主要动因。
4.再现角度与权力关系
样本中约53.8%的图片用于描绘不具备人物在场的环境。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对违法环境的呈现。所呈现的环境大多是脏乱不堪、昏暗狭窄的违法食物生产场所或零售现场。
对违法环境的特写镜头的确有助于提升报道的可信度,适当的恐惧诉求手段运用可以帮助消费者建立对于问题食品的警惕心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媒介的担忧可能在于:恶劣的问题食品生产场景的再现,会引发消费者较强的心理不适。在本研究采集到的新闻报道的有关评论中,确实也看到了受众对此产生的消极及愤怒情绪。
2011年9月《新京报》的一篇报道曝出“蒸功夫”品牌的包子制作使用不明香精,在报道中使用了几张包子制作环境以及不明香精的新闻图片,图片中瓶装的香精以及各种调料都布满黑色污垢。(图8 图8见本期第39页)有网民评论说“看完这制作场景,老夫再也不吃外面的包子了”、“看到这个,我只想吐”、“实在是很火大!我刚要来吃饭就看到这则消息,现在哪里有胃口?”。2012年6月《京华时报》曝出有消费者在双汇火腿肠中发现死蛆,其报道配了一张蛆虫趴在火腿肠上的特写画面非常清晰。(图9 图9见本期第39页)有公众在新闻下方留言评论道:“饿死也不吃双汇,以后吃什么火腿肠都没胃口了”、“再也不吃双汇,太恶心!”。
图片再现态度方面,样本中“仰视”视角在236幅研究对象中仅有9幅,占比约3.8%;绝大多数图片选用的构图视角为“平视”和“俯视”,分别占55.5%和40.7%。
选用平视视角构图,图片生产者是“卷入”(involved)到再现的人物当中的。[65]相较于其他视角来说,平视视角能够最大程度使读者产生一种“融入”画面的感觉,对于观者获取图像的信息有一定帮助。
运用俯视视角的图片中,63.5%用于描述环境和食物等不具备人物的图片;另36.5%的俯视图片用于描述人物。在描述环境和食物的图像中选用俯视视角,旨在通过“上帝视角”让读者清楚地看到问题食品的品相、检验结果比对等现场情况;而对于有人物参与的图片来说,俯视视角会带给读者居高临下感,从而把受众摆在较高权力的位置上。
报道中的问题食品或生产加工环境主要是运用了“人际距离”以及“平视”或“俯视”的角度进行呈现,这类特写镜头的高频使用容易形成视觉冲击。已有研究认为,被察觉到的食品危害事件的可怕程度和陌生程度越大,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评价越消极,公众的担忧也越大。[66]在这样的语境下,强化观者的“卷入”程度,是提升公众对食安风险感知的有效策略。但新闻媒介的实际操作却是欲说还羞、自相矛盾。一部分虽然采用了较近的“社会距离”取景,增加了“卷入”效果,另一方却选用“斜角”而非“正面”视角,弱化了“卷入”效果。
将图片的角度与所再现人物的交叉分析后发现,样本图片对执法者和违法者的再现差异鲜明。仅有7次仰视视角全部用于描绘“执法人员”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正义形象。仰视拍摄呈现出来的人物特点是高大,可供颂扬。这类再现画面体现了执法人员在查处食品安全事件时的强势姿态,是对“执法人员”形象的宣扬。同时,也出现了6次以俯视角度来呈现执法人员的情况,但都出现在与“不法商贩/涉事人员”同框的图片中。
第三类人物是对“问题食品受害者”的再现,这在全样本中仅出现3次。事实上,从食品安全治理实践来看,受害者在所报道事件当中处于弱势地位,本应是最容易与公众这一主体发生情感和认知共鸣的,但在报道图片中却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阐释。
五、讨论 信任断裂中的食安治理表征
传统新闻业的视觉模态已经遭遇到数字技术的拷问。数字技术对传统新闻业的视觉再现,特别是“模态”的标准带来了挑战:过去,平均标准化的自然主义是模态的主要准绳,现今,这些标准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影响下,不得不被重新审视。“摄影真实”(photorealism)、“摄影真实主义”(photo-realistic)正逐渐对“真实”的定义和标准进行重构。[67]与此同时,新闻内容的跨平台传播也给受众权力带来了变化。现今,主流媒体仍然在食安报道的内容生产方面占据权威地位,但是食安报道的传播渠道已经深度嵌入到移动互联的技术网络之中。搜索引擎放大了本文消费的并行效应,用户同时得以并行地看到多种多样的文本。在本研究样本中,电视、新媒体、环保组织等成为纸质媒体之外的消息来源。同一个食安事件,受众可以通过不同的平台搜集信息。这意味着对于新闻摄影而言,用户将在未来越来越多地控制视觉模态的标识。[68]因此,对互联时代的新闻摄影的模态考察,除了从技术层面之外,还需要从社会符号学的层面去考量意义的生成。
(一)“作为文化现象”的新闻摄影及视觉修辞
从何种意义上说,一张新闻图片可以概括一场灾难、一个事件或更广阔的情况?同样地,一张新闻图片何以代表某一食安事件?
新闻摄影通过提供记者和编辑等新闻从业者一致认为有信息和思想的观点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通常而言,编辑会基于真实性原则,选择用一张或几张图片去概括新闻故事。Gibson指出,当新闻图片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时,它的问题也显现了。
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更具反思性地看待新闻图片,将他们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当作“判断的信息”。记者在选取报道角度时,都在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化学反应”。作为读者,人们总是想依赖图片去给新闻事件提供一个视觉定义——既然视觉系统的宗旨是为了理解和明晰,人们想要通过新闻图片去定义事件也实乃一种原始的心理回应机制。[69] “一张照片不是一个人,不能展示我们希望获得的有助判断的信息。它实质上是一种争夺”。[70]新闻图像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舒德森更是强调,研究者只有把新闻摄影看作是“更广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的视觉呈现”,新闻摄影作为研究对象才具有合法性。对于新闻的理解,应基于“叙事、讲述、人类利益和新闻生产中的照片及语言呈现的传统”之上来看待。[71]食安图片开展的意义书写和争夺,在中国食品安全面临的高风险感知的当下,展示的是整个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的表征集合。正是基于这一前提,我们更加强调对食安事件的新闻图片开展视觉修辞分析。
新闻摄影广泛使用了图像的隐喻和转喻的特点,来表现抽象概念、提供语境和阐释。[72]新闻图片使用的典型修辞手法是“换喻”(或转喻,metonym)。例如,一个失业的人站在一个废墟的前面,展现的是他内心的空虚(隐喻,metaphor)。一个来自非洲因为营养不良而腹部凸起的孩子,代表的是在非洲社会中饥饿的人们(换喻或转喻,metonym)。McQuire认为,所有的新闻图像都是可以交替的所有受饥荒影响的人们都可以被纳入同样的难民原型。[73]此外,“提喻法”(synecdoche)也在新闻摄影中被广泛使用。用一个事件代替所有情况,用某一个人或场景指代某一类型的情况非常普遍。
1.隐喻:食品变身工业毒品
样本中新闻图片对违法食品生产环境和问题食品的再现,展现的是一个消费社会中的“工业化生产”的隐喻,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快速进程中的道德失范和工具理性泛滥。一些生产者为了谋利,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不择手段。样本中新闻图片描述的,常常是混用的食品添加剂与工业添加剂,酸碱度超标、生蛆、腐烂、变质的食物,污秽、肮脏的容器,还有麻木和冷漠的从业者。违法生产者把食物的生产和加工纳入工业资本生产的逐利链条中,食品变成了看起来很美,吃起来有害的化学“毒品”。生产场所的再现凸显了违法食品生产者居住空间(如卧室)与生产空间的模糊边界,展现了社会投机者的无序状态,也展现了他们一味逐利的贪婪和龌龊。准备售卖给消费者的食物不加遮挡地随便放置在污水横流的地上,违法者生产的不是食物,而是毒害公众的谋利工具。
同时,对执法者的呈现的隐喻是——公职人员是食品安全的护卫者。呈现的角度刻意拉近了执法者与观看者的距离。对执法人员的呈现有刻意的烘托、放大的取向。图像生产者对食品生产加工者的态度是漠然的,呈现了违法加工者与社会总体的疏离。
此外,问题食品生产者和执法者、专业社群人员被放置到了一组关系的对立两端。一头是代表了邪恶和阴暗世界的违法食品生产者,另一头则是充满了希望、正义和秩序的执法人员。展现问题食品的图片大多颜色发灰、光照不足,或是黑白色调;彩色色调的照片中,也大多画面混浊、肮脏和清晰度较低,总体而言图片模态较低。然而,展现专业检验人员对问题食品进行检测的画面,例如对有关试剂、检验结果呈现等内容时,画面则明亮、整洁、有序。这些视觉元素召唤起观看者的潜在心理认知结构是:违法者和执法者、专业社群两类人员是对立的两个群体。问题食品加工者的世界是见不得光的荒唐、失序、恶心的疯狂世界;而执法者和专业社群人员则来自一尘不染、理性、整洁的文明世界。疯狂的世界这头,活跃着迷失心智、道德沦丧的违法者,而理性世界的那端,活动着的是受过良好教育,敬职奉公,恪守道德的职业技术人员。最为关键的是,两个世界一明一暗,有着明显的区别。
2.提喻:执法者立场的社会见证
图像生产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互动结果,往往得以生成新的社会关系。新闻摄影中的符号常常有很多的文化意涵。新闻摄影绝不仅仅是社会的“镜子”,它们提供了对世界事物的描述和召唤内容,它们是时代的符号。因此,它们提供了有关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考古的独特价值。
食安图片样本中,其显著的特点是图像生产者使用了借某一场景或某一人来指代一类新闻事件的提喻法。提喻法虽然在新闻摄影中被普遍采用,但在本样本库中,食安首发报道图片的提喻手法带有明显的“寻求见证”的意义取向。在社会事件中受到伤害或不公正遭遇的受害者,往往会通过寻求社会见证的手段,来伸张正义,恢复情感,以寻求对社群的情感和能量的修复。在样本中,新闻图片大量再现了违法生产者和销售者形象,并对违规生产食品、问题食品进行了突出的再现,用这些局部指代了食安事件的全貌。对违规生产食品的呈现,多采用“见证”的手段。另外,呈现物品的人物动作姿态:或是两手端举物证,或是进行俯视,表现问题食品加工或生产现场的脏乱无序,召唤观看者的“见证”感受。
有趣的是,这些寻求“社会见证”的图像,往往再现的是违规食品、脏乱的生产现场,极少对受害当事人的再现。究其根本,新闻图像生产者多从执法者的立场出发,而未采纳以受害者为代表的公众立场。这些社会见证,更多呈现的是执法者请求的见证。
环境展现方面,着重使用污秽的违法食品生产地点来指代问题食品的生产过程。呈现环境大多是角落、旮旯。有粗陋的毛坯平房、裸露砖墙的小作坊、污水和血水横流的违规生产房屋的局部等。让受众在见证违法生产者的低劣行为的同时,也对他们丧失的良知产生深深的反感和厌恶。
(二)对食安风险治理主体的再现
1.社会共治中的“权威”形象再现
从样本中可以看到,媒介针对食品安全事件报道的图像再现总体而言是保守而克制的,对执法人员为代表的执法力量和政府有明显的偏向;对受害者的再现则是刻意的“忽略”和“遮蔽”。新闻图片生产采用了“规避受害者”和“拔高执法权力”的再现策略。
但是,“执法权力”是不是食安治理中的唯一“权威”?在多元的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中,还有“市场主体”、“专业知识社群”、“公众”等多个主体。对于其他行动主体的再现,无疑有利于多元治理的社会共识的达成。但样本中对于“市场主体”的呈现基本只局限在“不法商贩/涉事人员”这一类别,对于食品行业组织、食品生产企业并没有给予充分关注。
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中国媒体在“事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两条腿走路时候的窘困。从媒介属性来看,被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有着特殊的指向性:“党和政府并不鼓励媒体去代表公众的意见,服务于国家的利益是中国媒介‘舆论监督’的最核心面向。”中国媒体事实上承担了提升政党的监督角色的义务。[74]下文将对“专业知识社群”和“执法权力”两个主体的再现展开讨论。
(1)专业知识社群形象的缺失
食品安全的报道离不开专业知识社群的共同行动,包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等行业评估机构及食品、药品、医学、生物、化学、营养学等有关领域的学者都是这一专业知识社群的重要组成。然而回顾11年来的样本图片,几乎看不到有关领域的学者及行业专家的身影,仅在2016年之后的首发报道图片中出现了3次检测员的身影。
中国食品安全治理实践已经开启新转向,正试图从过去政府主导的“一元主体模式”转向“多元行动主体参与的社会共治”。在这个过程中,频繁发生又未得到合理阐释的食品安全事件给公众逐渐带来了累加的创伤记忆,当新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公众容易回溯到以往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的恐慌和焦虑中。由于有关部门公共沟通的滞后和缺位,使得大众媒介成为唯一的积极叙事者角色,并为受害者寻求的“见证”提供非常有限的展示空间。
首发报道的消息来源数据也从另一个面向印证了专业知识社群在食安报道中的失语:在北京近11年来的食安首发报道中——“市民”成为最为活跃的行动主体,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媒体则是在公众爆料基础上将议题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公共注意力中的关键。[75]169篇首发报道的消息来源包括公众(市民举报)、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执法部门、专家学者以及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等五种(见图11)。其中最多的消息来源是市民举报,约占57%,而来源是食品安全领域权威的专家学者的报道仅占1%。也就是说,在报道来源方面,主要的行动者是消费者自身以及媒体。传统主流媒体在食品安全沟通机制中,是作为积极主动的主体而存在的,消息来源占比29%。
其次,从新闻报道内容来看,来自专业知识社群的专业意见和事件解读也相当匮乏。一方面,已有食品安全事件在公众认知中留下的“记忆伤痕”,若不能通过深入、专业、持续地解读和安抚,一旦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公众很容易再次强化对专业知识社群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在报道中如果缺乏来自专业知识社群的专业解读,公众的信息缺失将得不到充分回应,导致新的信任不平衡出现。当下,公众对于专家群体的认知矛盾在于:随着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日常生活中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人们更加依赖于“专家”来管理和控制风险,但他们对这些专家的信任却日益下降。[76](2)“执法权力”与政府形象的宣扬
研究发现,食安首发报道的新闻图片多是从执法者立场出发的。人物的再现比例中,对“涉事人员/不法商贩”的再现最多,其次是对“执法人员”形象的再现,对“受害者”再现最少。另外,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初期,政府在首发报道文本中却是相对失声的。只在几个重大事件的首发报道中(如“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等)出现了政府的发声和表态。在大部分事件中,首发报道中发声的行动主体主要是“市场主体”(如涉事个人或企业);工商部门或执法部门的表态一般只是程式化地表示会“依法追查或取缔”。政府有关部门的失语很容易带来公众对政府有关部门职能履行的猜测和不信任。
事实上,从实践层面上看,我国近年来已经先后从制度、组织、技术等多个层面,就构建食品安全风险防治体系做出了努力——出台了更具系统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并优化了行政机构设置(一是国务院设置了食品安全委员会,从科层权威方面增强全国食品安全治理的统一协调性;二是组建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推动风险评估技术化升级等)。但信任问题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究其原因,法学研究者吴元元指出,信任的指向和分布是由信息决定的。信任是对“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确定的一种应对机制”。对于信息对称状态或者信息优势者,信任更是没有适用的必要。因此,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中的“不信任”,主要是“处于信息弱势的公众”对其他几个“处于信息优势主体”的不信任,而这几个路向上的几类制度信任都存在严重的问题。[77]再回到对执法权力的图像语法的互动分析中来。对执法权力的呈现,有一部分为仰视的视角,这种仰视角度很容易使读者在与图像所再现人物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受压迫感,并且使执法人员展现为一种相对的强势姿态。在食品安全的维护中,执法人员的强势态度有利于彰显对于事件整治的决心。首发报道选择将执法人员建构为强势的治理角色,这对于改善目前公众对食安治理的不信任是否具有积极作用?在以往的政府独大、一元治理的行政思维下,这样的图片处理策略固然有利于强化执法权力的威严;但是,在现阶段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逻辑中,公众对于监管部门的信任已然断裂,加上政府的发声严重缺失,若媒体仍沿用以往强化执法人员的图像叙事策略,则可能起到消极作用。因为在已经出现信任断裂的食安治理中,这样缺乏信任基础地一味强调执法者的高大,并不能有效弥补公众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不信任,反而会让公众认为执法权力有“装腔作势”、“流于形式”、“缺乏务实精神”的嫌疑。
过去的“运动式执法”影响了公众对“法理型支配政治制度”的信任,这种执法形式不但不能对潜在的违规违法者形成持续有效的震慑,反而带来封闭而模糊的公众交流模式,无法及时有效地化解公众对于食品监管的焦虑与不安。另一方面,从当前的风险沟通模式来看,自上而下的信息单向流动较为常见,也是一元主义治理逻辑的体现。[78]在这样的语境下,媒体对于执法人员形象的呈现也可以进行适度地改变,比如尽量不使用仰视角度的新闻图片,以免造成读者的反感、加剧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多运用平视的视角拍摄,从视觉观感上为受众营造一种平等互动的感受。更重要的是,有效的食品安全沟通制度亟需建立,这种沟通机制应该是双向沟通,让市民可触及、可参与的。最为关键的是,行政治理逻辑的转变应该尽快落实到公共沟通制度的建立上来。
2.对受害者的遮蔽
在当前公众对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中多个主体的信任均产生断裂的情况下,国内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状况的“高风险感知”已累积到一定高位,未得到恰当阐释的事件,只能通过市场化媒体“舆论监督”的有限空间来开展公共叙事。媒体若能较为全面地展现事件现场和受害者经历,将有可能为食品安全事件带来的“社会分离”效应进行“修复”。然而,样本统计结果却与此大相径庭:现有的新闻摄影的再现策略限制了新闻图片这一有效修复工具的作用发挥。在个体和食品安全事件所产生的“社会分离”之间,公众失去了“个体处理创伤的空间”,想要回归到“更大范围的共同体”的途径被斩断,使得受害者未能通过公共平台寻回应有的“道德谴责”,受害者最终难以走出阴影。
另一方面,由于屡屡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得不到有效的制止,违法者未得到有效的惩治,反而将更多的公众反推到了广义的“受害者”阵营。
六、结论
在互联网时代,新闻媒介的结构和读者的期待让新闻图像的实质变得更加复杂:新闻图片在强化信念和提供社区认同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读者想要通过新闻图片获知有关新闻事件的情感或获得娱乐,新闻媒介也很乐意迎合。既然应该将新闻图片看作文化现象来加以对待,借用社会符号学对新闻摄影展开互动意义的分析就更具备了时代意义。
本文将食安事件首发报道的新闻图片放置在食品安全公共沟通的框架中,从建构论视角切入,以“视觉语法”和视觉修辞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考察在新的社会共治逻辑下,新闻摄影再现食安治理的互动意义和偏向性。研究发现:食安事件首发报道的图像生产较为“保守”,并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引发食安事件的最主要动因和事件的受害者。这些图像再现规避了受害者并拔高了执法权力。取景框架倾向选用“社会距离”,试图提升食安报道图片对受众的卷入程度,试图使受众意识到食安事件的显著性;其主要强调信息的“给予”,同时又悖论地弱化了受众对事件的回应。在通过俯视视角将受众放置在掌控、知晓全局的“上帝视角”的位置的同时,偏向宣扬执法权力的高大,对专业知识社群和受害者的再现则非常匮乏。这样视觉再现实践未能给公众提供一个“道德谴责”的空间,使得受害者无法走出创伤,也使得遭遇“社会分离”的社会共同体难以修复到事件发生之前的状态。目前中国媒介的食安图片生产实践正在进一步加剧我国公众对其他食品安全治理主体的信任断裂,继而强化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高风险感知,新闻媒介也逐渐丢失其作为阐释权威的地位。
综观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实践,除了治理逻辑、管理形式需要实质上的转变之外,充分发挥不同形态媒介的作用,开展多元的“复调主义”沟通,是打破目前公众对于三类主体的信任断裂问题的关键。在新的食品安全沟通制度建立起来之前,媒介仍然将发挥重要的风险建构作用。
一方面,食品安全沟通不能仅仅开展单向的信息流动或者事件通报。风险沟通要致力于建立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确定性”,避免延续以往的自上而下、模糊而封闭的“信息发布”。有效的沟通模式,应当在制度化解的基础上,以减轻或降低公众的信息不确定性,疏解公众的焦虑感为有效性的衡量指标。若不能针对经由媒体曝光的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那么公众的心理创伤并不会自行平复,相反,只会进一步地加剧和累积,在下一次食品安全事件爆发时以更加顽固的形态出现。在我国的食品安全沟通体系中,尚未出现一个活跃的行动主体来对公众由此产生的风险焦虑开展反馈和阐释,并加以心理疏导和认知引导,[79]却只是任由公众自己去寻找“事实”,自行补充有关食品安全事件的想象。这使得公众确定性的心理诉求长期不能得到满足,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于几个不同治理主体的信任断裂。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受众作为主体的异质性特点。在这个风险沟通的过程当中,受众都应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沟通对象,因此受众个人媒介素养的差别也决定了他们会如何感知和认识食品安全。从受众主体出发,其作为风险沟通中极为重要的一方,同样也应当注重媒介素养与风险素养的提升。这股由受众为主体的食品安全公众治理中的活跃个体力量,是实现目前食品安全多元共治的一个关键变量。另外,对于受众间的风险沟通,诸如社区关系和风险交流,以及初级群体当中的风险信息传递,同样应当加以关照。■
①ThompsonD. (2007). China’s Food Safety Crisis: A Challenge to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China Brief11(7).
②Liu, P. (2010). Tracing and periodizing China’s food safety regulation: A study on China’s food safety regime change.Regulation & Governance,4(2)244-260.
③鄂璠:《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小康》2015年第15期
④吴元元:《食品安全共治中的信任断裂与制度因应》《现代法学》2016年第4期
⑤Russell, L. D.& Babrow, A. S. (2011). Risk in the making: Narrativeproblematic integration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isk.?Communication Theory,21(3)239-260.
⑥黄旦、郭丽华:《媒体先锋:风险社会视野中的中国食品安全报道——以2006年“多宝鱼”事件为例》,《新闻大学》2008年第4期
⑦Berkowitz, D. (1992). Non‐routine news and newswork: Exploring a what‐a‐sto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2(1)82-94.
⑧王宁:《新闻图片大众传播中的价值导向分析》,《新闻爱好者》2016年第8期
⑨盛希贵、贺敬杰:《宣传话语的视觉“祛魅”:新媒体环境下网民对政治类新闻图片的再解读》,《国际新闻界》2014第7期
⑩Kim, Y. S.& KellyJ. D. (2007). Visual framing and the photographic coverage of the Kwangju and Tiananmen Square pro-democracy movements: A partial repl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May.
[11]Zelizer, B. (2002). Finding aids to the past: Bearing personal witness to traumatic public events.Media, Culture & Society24(5)697-714.
[12]Kim, Y. S.& KellyJ. D. (2007). Visual framing and the photographic coverage of the Kwangju and Tiananmen Square pro-democracy movements: A partial repl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May.
[13]All photos lie.(2007).images as sata.In Stanczak,G.C.Visual research methods.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Inc,pp.61-82.
[14]马颖、丁周敏、李金洲:《基于食品类别的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状态的分类方法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5]吴林海、钟颖琦、山丽杰:《公众对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的感知研究:国际文献的一个综述》,《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6]吴林海、钟颖琦、山丽杰:《公众对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的感知研究:国际文献的一个综述》,《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7]夏晓平、李秉龙:《中国城市居民户外食品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以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的调查为例》,《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第3期
[18]Mazzocchi, M.Lobb, A.Bruce Traill, W.& Cavicchi, A. (2008). Food scares and trust: a European study.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59(1)2-24.
[19]吴元元:《食品安全共治中的信任断裂与制度因应》,《现代法学》2016年第4期
[20]Slovic P.(1993).Perceived Risk,Trust,and Democracy.Risk Analysis,13(6):675-682.
[21]DruckmanJ. N.& Bolsen, T. (2011). Framingmotivated reasoningand opinions about emergent technologie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1(4)659-688.
[22]S.E.TaylorL.A.PeplauD.O.Se(2004).《社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3]胡悦:《食品风险传播的洞穴影像:网媒议程设置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4]靳明、杨波、赵敏:《食品安全事件对我国乳制品产业的冲击影响与恢复研究——以“三聚氰胺”等事件为例》,《商业经济与管理》2015年第12期
[25]Kitch, C. (2003). “ Mourning in America”: ritual, redemption, and recovery in news narrative after September 11.Journalism Studies4(2)213-224.
[26]EasonD. L. (1981). Telling stories and making sense.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15(2)125.
[27]Dan Berkowitz.(2017).Non-routine News and Newswork:exploring a what-a-story, in Dan Berkowitz.(Ed.).Social Meanings of News,Thousand Oaks, CA:Sage365pp.362–375.
[28]王宁:《新闻图片大众传播中的价值导向分析》,《新闻爱好者》2016年第8期
[29]Kitch, C. (2001).Mourning in America:ritualredemption,and recovery in news narrative after September 11’.Journalism Studies4(2)215.
[30]Zelizer, B. (1990). Achiev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hrough narrative.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7(4)366-376.
[31]Kitch, C. (2001). “ Mourning in America”: ritual, redemption, and recovery in news narrative after September 11.Journalism Studies4(2)213-224
[32]Zelizer, B. (1990). Achiev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hrough narrative.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7(4)366-376.
[33]Zelizer, B. (1990). Achiev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hrough narrative.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7(4)366-376.
[34]Zelizer, B. (1990). Achiev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hrough narrative.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7(4)366-376.
[35]Kim, Y. S.& KellyJ. D. (2007). Visual framing and the photographic coverage of the Kwangju and Tiananmen Square pro-democracy movements: A partial repl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May.
[36]Sylvester, J. L.& HuffmanS. (2002).Women Journalists at Ground Zero: Covering Crisis. Rowman & Littlefield.
[37]Kitch, C. (2003). “ Mourning in America”: ritual, redemption, and recovery in news narrative after September 11.Journalism Studies4(2)213-224.
[38]Zelizer, B. (1990). Achiev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hrough narrative.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7(4)366-376.
[39]Zelizer, B. (1998).Remembering to forget: Holocaust memory through the camera’s ey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转引自Kitch, C. (2001).Mourning in America: ritual, redemption, and recovery in news narrative after September 11’Journalism Studies4(2)213-224.
[40]Kitch, C. (2001).Mourning in America: ritual,redemptionand recovery in news narrative after September 11’.Journalism Studies4(2)213 -224.
[41]Kitch, C. (2001).Mourning in America: ritual,redemptionand recovery in news narrative after September 11’.Journalism Studies4(2)213 -224.
[42]Zelizer, B. (2002). Finding aids to the past: Bearing personal witness to traumatic public events.Media, Culture & Society24(5)697-714.
[43]Zelizer, B. (2002). Finding aids to the past: Bearing personal witness to traumatic public events.Media, Culture & Society24(5)697-714.
[44]Zelizer, B. (2002). Finding aids to the past: Bearing personal witness to traumatic public events.Media, Culture & Society24(5)697-714.
[45]Kim, Y. S.& KellyJ. D. (2007). Visual framing and the photographic coverage of the Kwangju and Tiananmen Square pro-democracy movements: A partial repl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May.
[46]Kress, G. R.& Van LeeuwenT. (1996).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Psychology Press116.
[47]Ravelli, L. J.& Van LeeuwenT. (2018). Modality in the digital age.Visual Communication17(3)280.
[48]Seo, K.DillardJ. P.& Shen, F. (2013). The effects of message framing and visual image on persuasion.Communication Quarterly61(5)564-583.
[49]Seo, K.DillardJ. P.& Shen, F. (2013). The effects of message framing and visual image on persuasion.Communication Quarterly61(5)564-583.
[50]Seo, K.DillardJ. P.& Shen, F. (2013). The effects of message framing and visual image on persuasion.Communication Quarterly61(5)564-583.
[51]KingA. J. (2015). A content analysis of visual cancer information: prevalence and use of photographs and illustrations in printed health materials.Health communication30(7)722-731.
[52]厉曙光、陈莉莉、陈波:《我国2004—2012年媒体曝光食品安全事件分析》,《中国食品学报》2014年第3期
[53]Zelizer, B. (1990). Achiev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hrough narrative.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7(4)366-376.
[54]“图像参与者”包含人物及事物,受众的凝视也可以是针对图像中的事物。本研究中的图片编码选择了重点分析具有人物出现的图片。详见Kress G R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M]. Routledge2006:118.
[55]数据源自厉曙光、陈莉莉、陈波:《我国2004—2012年媒体曝光食品安全事件分析》,《中国食品学报》2014年第3期
[56]HoltkampN.LiuP.& McGuireW. (2014). Regional patterns of food safety in China: What can we learn from media data?.China Economic Review,30459-468.
[57]食品伙伴网创立于2001年在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专业委的指导下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食品技术领域的领航网站。http://www.foodmate.net/。实际采集中,本研究主体数据来源于食品伙伴网。其一是因为地方食药监网站的舆情监测外包给了食品伙伴网,另外“掷出窗外”网站近年更新放缓。
[58]掷出窗外是一个有毒食品警告网站,由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吴恒联合34名网络志愿者创建,于2012年上线,在2012年5月份蹿红网络,引起极大反响。网上可以查询到2004年至今,全国各地的有毒有害食品记录。http://www.zccw.info/index。
[59]法学学者吴元元提出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中的几个主体分别为执法权力(以政府有关机构为代表),市场主体(食品生产企业)、专业知识(技术)社群(食品安全评估中心等专业机构、专家)及公众。详见:吴元元:《食品安全共治中的信任断裂与制度因应》,《现代法学》2016年第4期
[60]Kress, G. R.& Van LeeuwenT. (1996).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Psychology Press155.
[61]NoarS. M. (2006). A 10-year retrospective of research in health mass media campaigns: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11(1)21-42.
[62]Kress, G. R.& Van LeeuwenT. (1996).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Psychology Press126.
[63]“近人际距离”是两个人能够轻易的抓住或抱住对方的距离,再现的是人物的头部和脸部;“远人际距离”是两个人站在一起张开手臂能够互相触摸到对方手指的距离。
[64]“近社会距离”再现的是整个人物,“远社会距离”再现的整个人物和他周围的环境。
[65]Kress, G. R.& Van LeeuwenT. (1996).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Psychology Press138.
[66]Fischer, A. R.De Jong, A. E.De JongeR.Frewer, L. J.& NautaM. J. (2005). Improving food safety in the domestic environment: The need for a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Risk Analysi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5(3)503-517.
[67]Ravelli, L. J.& Van LeeuwenT. (2018). Modality in the digital age.Visual Communication17(3)285.
[68]Van LeeuwenT.& Jewitt, C. (Eds.). (2001).The handbook of visual analysis. Sage..
[69]MargolisE.& PauwelsL. (Eds.). (2011).The Sage handbook of visual research methods. Sage.
[70]MargolisE.& PauwelsL. (Eds.). (2011).The Sage handbook of visual research methods. Sage.
[71]MargolisE.& PauwelsL. (Eds.). (2011).The Sage handbook of visual research methods. Sage.
[72]MargolisE.& PauwelsL. (Eds.). (2011).The Sage handbook of visual research methods. Sage.
[73]MargolisE.& PauwelsL. (Eds.). (2011).The Sage handbook of visual research methods. Sage.
[74]Repnikova, M. (2017).Media politics in China: Improvising power under authoritaria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52.
[75]陈静茜、马泽原:《2008—2015年北京地区食品安全事件的媒介呈现及议程互动》,《新闻界》2016年第22期
[76]斯图尔特·艾伦:《媒介、风险与科学》第1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7]吴元元:《食品安全共治中的信任断裂与制度因应》,《现代法学》2016年第4期
[78]吴元元:《食品安全共治中的信任断裂与制度因应》,《现代法学》2016年第4期
[79]吴元元:《食品安全共治中的信任断裂与制度因应》,《现代法学》2016年第4期
陈静茜系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讲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访问学者;马泽原系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商圆圆系澳洲国立大学国家公众科学意识中心博士生。本文为2015北京社会建设研究院课题,编号SHJS2015002;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4ZHC0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6YJC860001;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7ZDA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