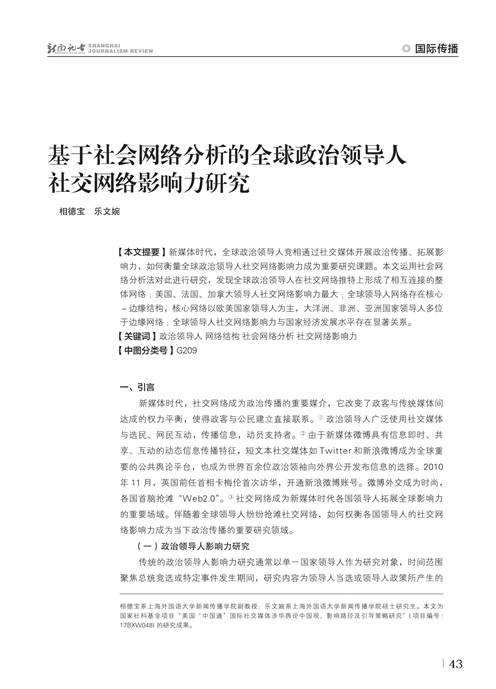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研究
■相德宝 乐文婉
【本文提要】新媒体时代,全球政治领导人竞相通过社交媒体开展政治传播、拓展影响力,如何衡量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成为重要研究课题。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全球政治领导人在社交网络推特上形成了相互连接的整体网络;美国、法国、加拿大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最大;全球领导人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核心网络以欧美国家领导人为主,大洋洲、非洲、亚洲国家领导人多位于边缘网络;全球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关系。
【关键词】政治领导人 网络结构 社会网络分析 社交网络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G209
一、引言
新媒体时代,社交网络成为政治传播的重要媒介,它改变了政客与传统媒体间达成的权力平衡,使得政客与公民建立直接联系。①政治领导人广泛使用社交媒体与选民、网民互动,传播信息,动员支持者。②由于新媒体微博具有信息即时、共享、互动的动态信息传播特征,短文本社交媒体如Twitter和新浪微博成为全球重要的公共舆论平台,也成为世界百余位政治领袖向外界公开发布信息的选择。2010年11月,英国前任首相卡梅伦首次访华,开通新浪微博账号。微博外交成为时尚,各国首脑抢滩“Web2.0”。③社交网络成为新媒体时代各国领导人拓展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场域。伴随着全球领导人纷纷抢滩社交网络,如何权衡各国领导人的社交网络影响力成为当下政治传播的重要研究领域。
(一)政治领导人影响力研究
传统的政治领导人影响力研究通常以单一国家领导人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范围聚焦总统竞选或特定事件发生期间,研究内容为领导人当选或领导人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如对于俄罗斯大选后普京影响力可持续性的分析、④对于奥巴马的东南亚政策评估、⑤对于习近平的朝鲜政策分析。⑥
国内方面,鲜少做出对全球领导人整体影响力评估的报告。国际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福布斯》、《时代》周刊等机构与媒体每年定期发布年度人物排名。《福布斯》杂志全球最具权力人物排名由《福布斯》评审团投票决定。评审团基于候选人影响到的人数、财产资源(GDP)、权力范围及用权能力对全球人物影响力进行排序。⑦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着重从知名度(awareness)、媒体关注度(news report attention rate)、信心度(confidence)、认可度(recognition)等维度对全球领导人形象进行评估。⑧
(二)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研究
2008年,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在总统竞选中充分利用社交网络平台Twitter获得连任优势,使得社交媒体与政客政治传播研究进入高潮。
一方面,社交媒体被认为是政治传播的绝佳工具。斯科格尔伯(Skogerb)提出,以Twitter和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已经被各国领导人整合为总统竞选与政治传播的重要手段,⑨巴巴萝(Barbaro)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Twitter现今已成为“政治宣传、分散政治注意力、攻击政治对手的工具”。⑩学者们还通过不同国家的案例分析得出,社交媒体为线上政治宣传、总统竞选提供了新机遇,Twitter与Facebook还使得原本政治参与度不高的公民政治参与意愿变得更加强烈。[11]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为政治领导人提供了个性展示的平台,拉近了政治领导人与选民、国民的距离,也使得政治领导人的个性研究成为当下政治传播研究的热点之一。[12]学者认为,社交媒体为政治领导人提供了半公共、半私人的自我展现平台,使领导人线下私人生活与线上媒介信息的界限变得模糊。社交媒体,诸如Facebook和Twitter,因其开放性、及时性、互动性而被越来越多的政治领导人使用。前期数据抓取过程中,本文发现2017年法国总统竞选时,两位总统候选人马克龙与勒庞均为积极的Twitter使用者,仅在第一轮与第二轮投票间的两周时间内,即2017年4月23日至5月7日间,马克龙发布了586条推文,勒庞则发布了506条,两人每日平均发文量多达39条。
目前,社交媒体与政治领导人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为具体事件中领导人的社交网络数据分析,如定性的领导人政治传播方略、形象构建、用语修辞研究及定量的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研究。定性研究结合国际关系、政治学、语言学知识分析政治领导人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文本内容,将领导人社交媒体信息归类为不同政治传播框架并对不同传播框架的传播效果进行对比研究,[13]或聚焦领导人的修辞手段与形象建设、领导力建设。[14]定量研究大多通过收集与分析某一位或某几个政党政治领导人在竞选期间的社交媒体数据,如粉丝数、点赞数、评论数、转发量等衡量领导人政治宣传、个人形象塑造的效果及领导人所发布信息的扩散路径与影响范围。[15]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全球政治领导人竞相开通社交媒体账号传播政治观点、拓展全球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如何衡量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目前对于政治领导人影响力的评估主要聚焦个人或个别国家,缺乏对全球领导人整体关系的评估;主要基于现实影响力讨论,忽略了对于社交网络影响力的研究。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进行探讨。主要研究问题为:第一,全球政治领导人在社交网络中是否形成了具有一定网络密度的网络社群;第二,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表现如何,哪些国家领导人具有较高的社交网络影响力;第三,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是否存在核心-边缘结构,处于核心网络和边缘网络的领导人具有怎样的特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国际社交媒体Twitter作为媒介研究对象。选取的主要原因是Twitter是国际社交媒体中最具影响力的网站。根据国际网站排名Alexa.com,Twitter在全球网站排名第九。同时,Twitter也是全球最大的公共舆论平台。
本文对世界197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在Twitter开设的账号进行检索,检索的原则是总统优先;如果总统在Twitter开设账号,直接选取总统账号。如果该国(地区)总统没有开设账号,则检测该国首相账号。如果首相开设账号,则直接使用该国首相账号。若该国领导人有多个账号,则选取粉丝数最多的账号。如果代表该国权力的最高领导人均未注册开通Twitter账号,则标记为无。通过检索得知,共计197个国家及地区中,111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在Twitter上开设账号;86个国家领导人尚未注册开通Twitter账号。
(二)数据抓取
本文主要研究全球领导人社交网络上相互关注的关系和结构,并对其社交媒体影响力进行评估。本文将在Twitter开设账户的111个国家领导人作为独立的行动者,利用Python程序抓取111个领导人账号的粉丝数据和关注数据,形成全球领导人相互关注的网络矩阵。之后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ORA、UCINET进行分析。
(三)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指的是社会行动者(actor)及其相互关系的集合。一个社会网络是多个节点(社会行动者)和各点之间的连线(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是分析社会网络中各种关系结构及其属性的方法,它通过建立行动者之间交往关系的模型,来描述群体关系的结构,并分析它对群体功能或群体内部个体的影响。社会网络分析采取结构分析路径,它的核心着眼点是社会行动者(或节点)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
社会网络分析不仅在方法上,而且也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式。社会网络分析成为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新的热点议题,并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全球关系领域产生广泛应用。
中心性(centrality)是对社会网络结构、关系和权力的一种描述和度量。通过社会网络中心性分析可以直接找出在整个社会网络中最具影响力的节点。中心性具有出度中心性(out degree centrality)、入度中心性(in degree centrality)、点度中心性(total-degree centrality)、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权威中心性(authority centrality)等多个指标。点度中心性是最先被提出的、概念相对简单的一个中心性度量指标。点度中心性通过测量节点的出度(out degree)和入度(in degree),直接找出网络中的中心点。出度和入度是计算特定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发生交互关系的个数。入度指的是直接指向该点的点的总数;出度指的是该点所直接指向的点的总数。点度中心性无法全面衡量节点在社会网络中的影响力。学者提出,权威中心性用于测量节点在网络中的中心性,权威中心性高的节点具有很多指向自己的连接(in-links),同时与其连接的节点同样有很多指向外部的连接(out-links)。[16]在网络中扮演权威角色的节点可从大范围节点中接收信息,且每一个节点都可以将信息传播给大范围受众。一个节点的权威中心性指数越大,则该节点在网络中所处的地位越权威,其在网络中的传播力越大,影响的社会行动者也越多。区别于点度中心性,权威中心性指标可以更好地反映节点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和信息传播能力。因此,本文选择ORA权威中心性指标作为综合衡量网络节点权威程度和影响力的指标。
三、主要研究发现
(一)全球领导人在Twitter上形成具有一定连接的社交网络,但领导人之间互动程度较低
本研究对全球政治领导人在Twitter上的关注关系进行了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发现111个网络节点中有89个处在一个紧密连接的网络中,22个网络节点游离在整个网络之外。网络中111个节点共有458条连线,双向相互连接数78条;单向连接302条。网络密度指的是一个网络的凝聚力的总体水平,是测量网络行动者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及信息交流的积极程度的重要指标。网络密度的值介于0和1之间,越接近1则代表彼此间的关系越紧密,越接近0则节点间联系越松散。结果显示,全球领导人社交网络密度为0.038,表明全球领导人在Twitter上具有一定的关联度,但连接相对松散。
网络中心势(network centralization)是衡量网络整体凝聚程度的指标,在政治领袖网络中,网络中心势数值代表着全球政治领导人关系网络在多大程度上是围绕某位领导人节点组织起来的。与网络密度相同,网络中心势取值范围也是从0到1,越接近1,则表示网络“中心化”程度高,网络权力集中;反之,则权力越分散,越难有节点起到控制整个网络的作用。全球政治领袖关系网络的中心势为0.193,数值非常低,代表着全球政治领袖社交网络中权力高度分散,很难有某位领导人对全球政治领袖网络的信息流动与互动起主导或控制作用。
根据作者之前对全球智库、大学以及媒体社会网络的研究,[17]可以看出,全球行为体间的社交网络密度数值都较低,其中连接最为紧密的全球智库,网络密度也只达0.154。全球政治领导人的社交网络密度为0.038,这意味着,相较于全球智库与大学,政治领导人间的网络联系更为松散、信息交互程度更低,领导人节点间行动相对独立;但国际政治领导人的联系紧密程度略高于全球媒体,即相对国际媒体关系网络而言,领导人间联系更为紧密(表1 表1见本期第46页)。
网络平均距离指的是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交流所需经过的连线数,又称网络特征路径长度(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网络特征路径长度是网络全局特征的一个重要指标。全球领导人网络平均路径长度(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为2.793,即平均来看,任意两位领导人节点相连需要经过2.793个节点。通过网络密度和网络平均路径长度可以发现,全球领导人在社交网络Twitter上连接较为松散,且整体网络密度并不大。
本文运用Gephi可视化功能制作了全球政治领导人Twitter社会网络结构图(图1 图1见本期第47页)。如图1所示,节点的大小代表度数的大小,节点度数越大则节点体积越大。度数是出度与入度之和,在本研究中代表政治领导人关注和被关注的次数之和。节点周边的连线数量代表领导人间所产生的关系数量。由图1可以发现,在全球政治领袖社交网络中,建立联系最多的节点为西班牙首相拉霍伊(@marianrajoy)、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modi)、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macron)、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juanmansantos)、比利时首相米歇尔(@charlesmichel)及美国总统特朗普(@realdonaldtrump)。此外,图1也显示了国际政治领导人相互关注关系中的地缘影响因素,如图1右侧相互连接的节点均为非洲领导人,图1左侧上方互联节点均为拉丁美洲国家领导人,图片正中则多为欧洲、亚洲领导人。
(二)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成为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中最具影响力的节点
权威中心性是衡量节点网络中心性的指标,权威中心度越高的节点在网络中信息传播能力与影响受众范围越大。根据对全球领导人权威中心性的计算统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全球领导人社交网络中最具影响力,排名第一(0.223);其次是法国总统马克龙(0.195);排名第三位的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0.179)。位列影响力排行前10的领导人还有墨西哥总统涅托、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印度总理莫迪、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比利时首相米歇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2 表2见本期第47页)。
从权威中心性排行表来看,全球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与所在国家发展程度[18]存在显著关系。根据对社交网络影响力排名前20位的领导人的统计,14位来自发达国家,仅有6位来自发展中国家。14个发达国家分别是美国、法国、加拿大、西班牙、英国、比利时、日本、卢森堡、立陶宛、荷兰、意大利、塞浦路斯、挪威和丹麦。 6个发展中国家分别是墨西哥、印度、哥伦比亚、阿根廷、肯尼亚和厄瓜多尔。
(三)亚洲、非洲等小国领导人游离在整个网络之外的节点最多,社交网络影响力缺失
22个游离在整个网络之外的节点主要来自亚洲、非洲的小国领导人。其中亚洲国家共计9个,非洲国家8个。亚洲国家9位领导人分别是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也门总统阿卜杜、卡塔尔埃米尔谢赫、柬埔寨首相洪森、伊拉克总统马苏姆、东帝汶总统鲁阿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和尼泊尔总统比迪娅。
非洲8位国家领导人分别是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贝宁总统帕特里斯、赞比亚总统埃德加、科摩罗总统阿扎利、塞拉利昂总统欧内斯特、突尼斯总统贝吉、佛得角总统丰塞卡、莫桑比克总统菲利佩。
另外,游离在整个网络边缘的国家中欧洲和大洋洲分别各有两个,包括欧洲的捷克总统泽曼、摩尔多瓦总统蒂莫夫蒂。大洋洲的帕劳总统雷蒙杰索、马绍尔群岛总统希尔达。北美洲1个,是海地总统若瑟莱姆。
(四)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会网络核心-边缘结构(core-periphery structure)分析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由核心地带、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带组成,同时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这种层次结构整体上没有改变,但其内部一直处于变化与重组之中,三个地带的国家不断调整变更。
社会网络分析也从模型的角度研究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core-periphery structure)。核心-边缘结构分析根据网络中节点之间联系紧密程度,将网络中的节点分为核心网络和边缘网络。处于核心网络的节点在网络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对全球领导人社会网络进行核心-边缘结构分析可以清楚把握哪些领导人处于核心地位,哪些领导人位于边缘地位。同时,有利于对处于核心网络和边缘网络的领导人特征进行挖掘。
本文利用UCINET核心-边缘结构模型对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进行分析发现,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中存在核心-边缘结构。其中23位领导人进入全球政治领导人核心网络,88位领导人处于边缘结构。
1. 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核心网络特征:欧洲领导人数量最多;美洲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连接紧密,诸多领导人成为核心节点;权威中心度越高的领导人,越趋近于网络核心。
位于核心网络的23国领导人中,9位为欧洲领导人,分别来自斯洛文尼亚、比利时、法国、立陶宛、罗马尼亚、丹麦、西班牙、乌克兰与马耳他;6位领导人来自北美洲,分别为墨西哥、巴拿马、加拿大、哥斯达黎加、美国和萨尔瓦多;4位领导人来自南美洲,即哥伦比亚、阿根廷、巴西、秘鲁;2位为亚洲领导人,分别来自日本和印度;2位来自非洲,分别为塞内加尔与肯尼亚领导人。与权威中心性排名相同,大洋洲没有国家位于核心网络。
从国家发展程度来看,位于核心网络的国家领导人中10位来自发达国家,13位来自发展中国家。13个位于核心网络的发展中国家里,有8位领导人来自美洲(包括北美洲与南美洲),美洲领导人在社交网络中相互关注、相互连接,因而在现实中位于全球政治领导人网络边缘的国家在新媒体社交网络中走向核心,成为重要节点。(表3 表3见本期第49页)
结合全球领导人权威中心度排行表来看(见表2),权威中心度与领导人是否进入核心网络具有相关性关系。直观来看,权威中心度最高的10位领导人中,9位均位于领导人核心网络。本研究还通过皮尔森相关性检测对两者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权威中心度数值与政治领导人在社交网络中所处地带间存在强正相关关系(r=.649,p<.01),即领导人的权威中心性指数越大,则其位于核心网络的可能性越大。(表4 表4见本期第49页)
在权威中心度排行前10的国家中,唯一未入围核心网络的领导人为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原因是其在网络中的出度值过低:特蕾莎·梅并未关注任何一位其他国家领导人,其权威中心性排行较高是由于其连入节点(12个)在网络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因而提高了其在网络中的权威中心性。而社交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的分区以节点在网络中联系的密度为依据,特蕾莎·梅过低的出度值导致其在网络中的联系密度较低,因而处于边缘网络。
2. 全球政治领导人边缘网络特征:大洋洲、非洲、亚洲国家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较弱,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在边缘网络节点中占比较大。
在111位开通Twitter账号的政治领导人中,88位领导人位于网络边缘结构,具体名单因篇幅原因不一一列举。全球政治领导人边缘网络具有以下特征:
从网络来看,每个大洲位于边缘网络的政治领导人人数均超过开通Twitter账号领导人的半数,边缘国家占比由高往低排序依次为大洋洲(100%)、非洲(93.1%)、亚洲(92.6%)、欧洲(71%)、南美洲(60%)、北美洲(55.5%)。大洋洲、非洲、亚洲国家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明显弱于欧洲与美洲领导人。
从国家发展程度来看,本文将位于边缘网络的国家领导人数量(第四列)与边缘网络领导人中来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数量(第五列)作出比较,得到边缘网络发展中国家占比(第六列)。数据显示,位于边缘网络的北美洲、南美洲、非洲领导人均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他大洲中,亚洲边缘网络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占比为92%,大洋洲为50%,欧洲则为22.7%。(表5 表5见本期第50页)
(五)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与所在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存在显著关系
从权威中心性排行与核心网络国家名单来看,来自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似乎在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为验证这一猜想,本研究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其国家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的权威中心性与核心-边缘分区进行对比。
如(表6 表6见本期第50页)显示,一个国家的GDP数值与其政治领导人的权威中心度呈正相关关系(r=.522p<.01),对其领导人在全球政治人社交网络分区呈弱相关关系(r=.290p<.01)。该结果与前文数据直观显示结果相符,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该国领导人的社交网络权威程度影响较大,对其领导人所处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分区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影响依然存在。
四、结论
本文对全球领导人利用社交网络Twitter进行政治传播的影响力进行研究,发现全球领导人在利用社交网络进行政治传播存在不平衡性。全球197个国家及地区领导人中,111个(56%)国家领导人在社交网络上开设账号,积极利用社交网络进行政治传播,但依然有43%的国家领导人尚未开通社交网络账号。全球政治领导人在社交网络上形成具有一定连接的整体网络,但网络密度不高(0.038)。111个开通社交网络账号的国家领导人中,22个国家领导人(19.8%)游离在整个网络之外,与其他国家领导人没有任何联系。22个国家领导人主要来自亚洲、非洲。其中亚洲领导人共计9个,非洲领导人8个。
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成为全球领导人社交网络中最具影响力的节点。特朗普推特治国,是全球领导人利用社交网络提升社交网络影响力的典范。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法国最年轻的总统,同样善用社交网络提升影响力。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位于核心网络的节点中,欧洲领导人数量最多。此外美洲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之间相互关注,形成紧密连接的子网,从而导致诸多美洲地区领导人进入核心网络。大洋洲、非洲、亚洲国家领导人在边缘网络中的节点最多。通过皮尔森相关性检测,发现全球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关系。
整体说来,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对全球领导人利用社交网络进行政治传播的影响力进行研究具有创新意义,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本文的不足在于仅对全球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相关性检测,未对其他因素如国家领导人社交网络使用行为、国家民主程度以及互联网发展程度等进行考察。未来可以对全球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与上述相关因素进行深度分析,推进该领域研究。■
①E Enli Gunn. Twitter as arena for the authentic outsider: exploring the social media campaigns of Trump and Cliton i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 32 (1),50-61.
②EnliG.S and Skogerbo, E. Personalized campaigns in party-centered politic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3). 16(5)757-774.
③子墨、胡美玲:《全球首脑抢滩“微博外交”》,《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12月17日
④林治华,赵小姝:《俄罗斯大选后普京影响力可持续性的经济学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1期
⑤葛红亮:《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回顾与评估》,《国际论坛》2017年第5期
⑥Kim, Hong Nack. China’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under the Xi Jinping leadership. North Korean Review, (2013).9(2)83-98.
⑦https://www.forbes.com/sites/davidewalt/2016/12/14/the-worlds-most-powerful-people-2016/?ss=powerful-people#70c220551b4c,检索日期:2018年4月9日。
⑧http://ash.harvard.edu/files/ash/files/survey-global-perceptions-international-leaders-world-powers_0.pdf,检索日期:2018年4月8日。
⑨Skogerb?E. ‘Everybody reads the newspaper’: local newspapers in the ‘digital age’in Local and Regional Media –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Shaping Processeseds I. Biernacka-Ligieza, L. Kocwin, Wydawnictwo MARIANowaRuda – Wrocaw, (2011). 357–373.
⑩Barbaro, M. Pithymean and powerful: How Donald Trump mastered Twitter for 2016.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2015).
[11]Castells M. Communication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the network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7). 1(1)238–266.
[12]Smith A. The Internet’s Role in Campaign 2008.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2009). http://www.pewinternet.org/2009/04/15/the-internets-role-in-campaign-2008/。检索日期:2017年5月1日。
[13]Heather K.Evans, Victoria GordovaSavannah Sipole. Twitter Style: An Analysis of How House Candidates Used Twitter in Their 2012 Campaig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2014). 47454-462;Jane Suiter.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Social Media: A Study of #mhe13 in Ireland. Irish Political Studies(2015).30(2)299-309.
[14]Jenny Madestam, Lena Lid Falkman.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 (2017). 30(3)299-311;EnliG.S. and Thumim, N. Socializing and self-representation online: exploring Facebook, Observatorio, (2012). 6(1)87-110;依再古丽·帕尔哈提:《社交媒体上的国家领导人形象建构:以普京对华微博外交为例》,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16
[15]WilliamsChristine B.and Girish J. Gulati. Communicating with Constituents in 140 Characters or Less: Twitter and the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0 Annual Meeting of the MPSA. Chicago. (2010);Linh DangXuan, Stefan StieglitzJennifer Wladarsch& Christoph Neuberger. An investigation of influentials and the role of sentiment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n twitter during election period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3). 16(5)795-825.
[16]Kleinberg, Jon M. Authoritative sources in a hyperlinked environ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DA '98 Ninth Annual ACM-SIAM Symposium on Discrete Algorithms, San FranciscoCA. Latria and Marchiori2001
[17]相德宝、张文正:《新媒体时代全球媒体传播格局与社交网络影响力研究》,《当代传播》2017年第4期;相德宝、张文正:《新媒体时代全球智库社交网络影响力探析》,《国际展望》2018年第1期
[18]IMF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名单(2017年10月号《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222–225页。
相德宝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乐文婉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中国通’国际社交媒体涉华舆论中国观、影响路径及引导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17BXW048) 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