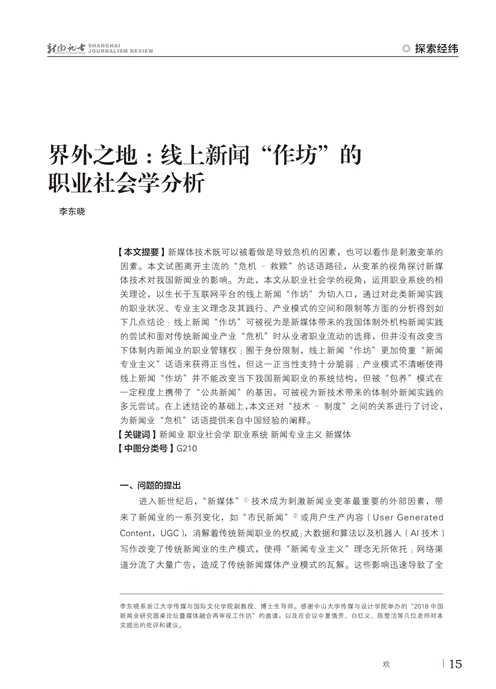界外之地:线上新闻“作坊”的职业社会学分析
■李东晓
【本文提要】新媒体技术既可以被看做是导致危机的因素,也可以看作是刺激变革的因素。本文试图离开主流的“危机–救赎”的话语路径,从变革的视角探讨新媒体技术对我国新闻业的影响。为此,本文从职业社会学的视角,运用职业系统的相关理论,以生长于互联网平台的线上新闻“作坊”为切入口,通过对此类新闻实践的职业状况、专业主义理念及其践行、产业模式的空间和限制等方面的分析得到如下几点结论:线上新闻“作坊”可被视为是新媒体带来的我国体制外机构新闻实践的尝试和面对传统新闻业产业“危机”时从业者职业流动的选择,但并没有改变当下体制内新闻业的职业管辖权;囿于身份限制,线上新闻“作坊”更加倚重“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来获得正当性,但这一正当性支持十分脆弱;产业模式不清晰使得线上新闻“作坊”并不能改变当下我国新闻职业的系统结构,但被“包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携带了“公共新闻”的基因,可被视为新技术带来的体制外新闻实践的多元尝试。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技术–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为新闻业“危机”话语提供来自中国经验的阐释。
【关键词】新闻业 职业社会学 职业系统 新闻专业主义 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G210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后,“新媒体”①技术成为刺激新闻业变革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带来了新闻业的一系列变化,如“市民新闻”②或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消解着传统新闻职业的权威;大数据和算法以及机器人(AI技术)写作改变了传统新闻业的生产模式,使得“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无所依托;网络渠道分流了大量广告,造成了传统新闻媒体产业模式的瓦解。这些影响迅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新闻业“危机”话语兴起。
在我国,“危机”也成为审视新媒体技术对新闻业影响的主要视角,对不同“危机”表现的讨论可被粗略地归纳为三个主要维度,即职业危机、专业危机及产业危机。③虽然讨论在不同维度展开,但“产业”危机成为实践者们作出因果解释、提出解决方案的支配性话语,形成了“商业主义”单一话语统合“危机”的特点。④也因此,任何传统媒体经营上的“成绩”都被作为救赎“危机”的成果受到关注。比如,根据《2017中国报业发展报告》,2017年我国报业经营整体下滑趋势已经趋缓,产业模式改革、多元经营及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财政扶持成为传统新闻媒体“解困”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党报,在外部财政扶持、政务合作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原有的“子报养母报”的情况已经发生改变。⑤在这样的“危机”话语的主导下,西方一些学者所关注和讨论的基于互联网的新闻业的“多元实践”⑥在我国没有受到关注。如美国学者泽利泽(Zelizer)所言,“危机”一词也许会遮蔽我们对新闻业处境的深入理解,因为所谓的危机并非同一的现象,而是具有地方性特征和时空差异的。⑦
全面审视我国的新闻业态,我们发现,除了上述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UGC的内容生产、新闻聚合平台以及机器人写作和算法推送等普遍的新闻业变化外,在我国的互联网平台也还有一些小规模的、非传统新闻机构的新闻实践,它们持续性地生产内容,定期推出的调查或深度报道在传统新闻业之外产生影响。比如,2018年12月25日,公众号“偶尔治愈”发布原创性调查报道《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不仅揭露了“权健”的问题,也撕开了我国保健业乱象的冰山一角,随即引发了大量的公众讨论以及相关部门对“权健”集团的调查。类似地,2018年9月4日,公众号“后窗工作室”发布了《“被反杀者”刘海龙的昆山江湖》,是对“反杀案”这一突发事件从一个独特视角的深度报道,获得了大范围的关注。这样与“偶尔治愈”和“后窗工作室”类似从事着新闻生产,但又与体制内的传统新闻机构以及“游侠式”的UGC内容生产方式不同的、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新闻实践还有不少。
这些新闻实践有如下一些特点:它们不在体制内,但是机构性质的;它们规模大小不一,但都拥有较为稳定的新闻生产团队,能定期生产和发布新闻;它们的机构性质存在差异(有些依托于互联网企业母体,有些附属于高校科研机构,有些靠公益基金支持),从业目的也不尽相同,但都是依托新媒体分发渠道,是在新媒体技术打破了传统新闻媒体渠道垄断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们不同于个人化的“市民新闻”和UGC写作,是兼具“市场化”和“新闻专业主义”要素的职业新闻活动。借鉴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德教授(Robert G.Picard)对新媒体平台的新闻手工模式(craft production mode)的界定,⑧我们将这些新闻实践统称为线上新闻“作坊”。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线上新闻“作坊”在我国语境中的存在?是否可以离开传统新闻业“危机–救赎”的路径,将其视为新媒体技术对我国新闻业带来的“多元可能”?为了遵循泽利泽所强调的“地方性特征”,我们试图从我国新闻职业的系统结构(system of profession)出发来审视这些新闻实践可能带来的影响。为此,我们将征用职业社会学(sociology of profession)⑩中职业系统(system of profession)的相关论述,主要从职业管辖权、专业主义和产业模式三个维度[11]来考察如下问题:(1)线上新闻“作坊”是否能重新生成或改变我国新闻职业的管辖权?(2)线上新闻“作坊”的新闻实践中秉持了如何的新闻理念?是否消解了新闻“专业主义”,形成了新的象征性资源?(3)线上新闻“作坊”的经营方式如何?是否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模式从而占领劳动力市场来竞争职业管辖权或改变我国新闻职业的系统结构?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希望从职业系统的角度,为当下新媒体技术之于新闻业的影响作出“技术-制度”关系维度的阐释,从而为此问题提供来自我国的经验和阐释。
二、我国新闻业的职业系统:职业社会学的视角
(一)职业系统中的职业、专业及产业
“职业”被认为是“由使用高深的知识解决特定问题的有组织的专家(experts)团体” [12]或“把某种抽象知识用于处理特定事务的具有排他性的行业群体”。[13]职业群体成员通过复杂的知识传授和训练,经由考试筛选,奉行某种道德规范或行为规范,从而获得处理某类专门的社会工作(或任务)的权威。[14]阿伯特(Abbott)从职业如何建立与工作(work)之间的关系来探讨职业的形成,[15]他认为“那种把职业和工作结合起来的社会纽带,即管辖权(jurisdiction),是职业和工作之间的合法联系,它是一种公认的权利”,“研究职业就应该研究职业与工作之间的管辖权如何形成的,如何被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结构所固着”,[16]它是一个职业系统(profession system)(系统中的各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7]阿伯特将职业系统中影响管辖权的要素分为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内部要素包括专业知识和技能、产业规模;外部要素包括工作需求(出现或者消失)、职业合法性认可、技术进步、组织变迁等。[18]艾略特·弗雷德森(Eliot Freidson)也着重职业系统要素的分析,他不仅强调不同的职业管辖权形成发挥作用的要素是不同的,还强调不同的要素在一个职业系统中起作用的力道是不同的,一些职业比较强调职业内部的自主性要素,另一些则比较强调系统外部的政治及社会结构要素。通常,国家法律的规定和国家承认是起着关键作用的外部要素。[19]对于新闻业来说,除了在各方力量作用下所形成的媒介体制,常被提及的影响因素包括科学技术、专业主义理念和产业模式。
科学技术是影响职业工作及其管辖权重要的外部因素。[20]工业化之后,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它可以消解、改变或重塑职业管辖权,[21]这一点对于新闻业来说尤为重要。“新闻业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实践,其发展与技术变革之间息息相关”,[22]这也是当下我们如此关注互联网技术对于新闻业影响的原因。
“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23]曾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职业控制形式,[24]它通过强调专业技能、提高知识门槛以及设立规范的价值标准实现对职业的控制。[25]也有学者不认同专业主义作为职业控制的阐释路径,认为专业主义所形成的价值体系对形成一个规范的职业秩序起着积极的作用。[26]埃维茨(Evetts)还强调专业主义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对专业主义的审视需要关注具体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在具体语境中探讨其价值才更有意义。[27]产业在职业系统中对保有劳动力市场的控制权起着重要作用,只有对劳动力市场有足够的控制权,才能保持对特定工作的管辖权。[28]在一个行业中,尤其是具有产业属性的行业,只有具有一定的产业效益,才具有雇佣或供养从业者的能力;反过来,职业从业者只有从职业中获得足够的,甚至是令人满意的薪资和社会地位,才会为谋求发展而贡献劳动或提供利他性服务。弗雷德森认为:行业内起支撑作用的大型企业、公司或机构,由于具有显著的产业规模,占据着行业的主体地位,成为职业管辖权的主要声称者;而行业内的小型企业或个人实践(solo practice)[29]往往因为缺乏声称职业管辖权的资源,只能与整个职业体系保持某种共生关系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专业主义”有利于行业内的各个部分,包括小型的或个人从业者,借助于已经形成的、被普遍接受的“专业主义”的价值体系来获得合法性的从业资格。[30]职业社会学的职业系统理论提供了一个不同要素相互关联的视角,为我们分析新媒体技术对我国新闻业不同层面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整合的框架。然而,在我们进入具体分析之前,还需要对我国新闻业所在的职业系统框架予以交代。
(二)我国新闻业的职业系统
如弗雷德森所言,在一个职业系统中,各个要素起作用的方式和力道是不同的。在我国,新闻职业系统的决定性要素来自新闻体制或官方认可,国家(官方)通过颁发标志着职业资格的“记者证”、组织成立职业协会、认定可以获得新闻专业教育背景的学术机构等方式形构了我国新闻业的职业系统,构筑了一个新闻业存在和运行的“鸟笼”。[31]“记者证”是新闻采访权的合法性标识。在我国,“记者证”制度规定申领记者证的人员须是在新闻机构编制内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人员。虽然,2014年10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决定在已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一类资质并符合条件的新闻网站中,按照“周密实施、分期分批、稳妥有序、可管可控”的原则核发新闻记者证,但这些新闻网站仍以传统新闻机构的网络平台为主,商业网站因不具备原创新闻采访权而不在发证之列。[32]在职业系统的论述中,职业协会(professional association)等有组织的法团实体(corporate body)是代表行业内成员讲话,与权力部门协商获得并保护其职业地位的组织。[33]在我国的新闻职业系统中,“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记协”)是我国最主要的新闻职业协会,其主管单位为“中央宣传部”,它不仅组织记者的业务交流和培训,还组织各种行业奖项的评选,这些奖项的评选对象也都是针对有官方认可的具有从业资格的从业者。
专业知识的生产部门被认为是职业系统中维护职业权威的要素,它通过使“专业知识”神秘化,培养进入职业的人才和认证(比如授予专业文凭)来建立和维系职业声望,[34]高等院校是主要的专业知识生产部门。在我国,能够承担新闻专业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高等院校,是由国家主导设立,受教育部直接管理。2013年底,中宣部、教育部又联合发出《关于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意见》,强化了从知识生产、人才培养、从业资格等一个链条上的官方权威,构成了一个具有本土特色的新闻职业系统。
在这样的职业系统中,国家通过“官方认可”将最优质的新闻资源和传播管道配备给与其社会治理关系最为密切的体制内的新闻媒体,使它们在关键内容的发布上占据竞争优势,比如,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新华社通稿成为唯一消息来源;中央级媒体获得更多报道优先权及“向下监督”的舆论空间;如果同级媒体之间发生冲突,根据不同媒体对国家政权的重要程度进行调节等。[35]当然,职业系统也是在历史地发生变化的,某些要素的变化会引起系统稳定性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国际交流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引入以及经营层面的改革使“市场”作用显现,曾是动摇我国新闻职业系统稳固性的因素。“新闻专业主义”作为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与其他话语体系(党的新闻事业、启蒙人文和市场导向的新闻)并存启发了我国新闻业多种不同的实践,[36]在改革中积累起来的构筑、阐释并正当化新闻操作“非常规”行动的象征资源具有“解放”的意义。[37]经营改革后,“市场”也成为影响中国新闻业的重要因素,使得制约我国新闻媒体的因素由单一的统治意识形态转为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力量;[38]还使得国家不再是媒介中唯一的表达主体,社会的声音可能通过市场在大众媒介中获得表达;[39]政治和市场的矛盾给媒体创造了一定的空间。[40]但由于职业系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没有发生改变,“专业主义理念”和“市场”这些影响因素只能在某些议题、某些层面和某些话语空隙中发挥作用。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强调了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要积极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新闻媒体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41]通过对新时期新闻体制、新闻理念及职业使命的界定,强化了既有的系统结构以及传统新闻机构的职业权威。
但新媒体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令人始料未及。阿伯特强调工作内容和方式的变化会是导致职业管辖权变化的直接因素。[42]对于新闻业来说,传统媒体之所以能够建立较为稳固的职业管辖权,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传统媒体拥有着渠道垄断。新媒体技术打破了原有的渠道垄断,令新闻生产和传播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线上新闻“作坊”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然而,虽然构成职业管辖权的工作与职业群体之间的纽带发生了变化,但维护职业管辖权的系统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于是,在技术和制度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是具有我国语境特征的,通过对线上新闻“作坊”的分析,我们试图发现并阐释这种张力,并从中管窥新媒体技术对我国新闻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当下难以突破的边界。[43]
三、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所关注的线上新闻“作坊”在机构性质、规模、内容定位、经营方式上均有不同,为了从不同的案例中提取一致性的脉络,本文尽可能地搜集丰富的案例进行分析。通过我们的搜索以及与业内人士的访谈,确定了如下几个较有影响力的案例,分别是:“偶尔治愈”公众号、搜狐的“后窗工作室”公众号、腾讯的“谷雨”、“故事硬核”、“ONE实验室”、南京大学的“NJU核真录”、“中国三明治”和“真实故事计划”。[44]在研究中,我们也尽量搜集不同案例的多元材料,包括机构的介绍、发布的报道或作品、公开出版的机构信息或从业者访谈、平台运营情况介绍等,这些资料均构成本文的经验材料。
此外,本文还以对从业者的访谈作为辅助材料,访谈对象包括部分本文所关注的新闻“作坊”的从业者以及传统媒体的新闻从业者。具体的访谈对象有:“偶尔治愈”主编及记者(各1名,1号被访者、2号被访者)、原“ONE实验室”写作者(1名,3号被访者)、“谷雨实验室”从业者(1名,4号被访者)、某线上原创新闻机构记者(2名,5号被访者、6号被访者)[45]、“界面新闻”记者(2名,7号被访者、8号被访者)、财新传媒记者(2名,9号被访者、10号被访者)、浙江日报记者(1名,11号被访者)、河南报业集团资深记者(1名,12号被访者)。访谈采用非结构化访谈为主,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新媒体技术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所在机构为适应新媒体技术所做的制度安排或改革;对新闻职业的认知,对新媒体非传统新闻实践活动的认知,以及在新媒体平台工作的职业阐释;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认知,工作中的践行方式;对当下新闻工作状态的描述及职业规划等。本文所有访谈集中在2018年5—10月间完成,对访谈材料的解读大多渗透在分析当中,仅在直接引用处作出标引。另外,本人在教学和科研中与大量新闻从业者有良好的联系,与他们的交流也会成为文章的经验材料,消化在文章当中。
四、体制之外,“鸟笼”之内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因素、国际化交流及“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等要素的刺激下,我国新闻实践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非常规”行动[46]或“隐藏文本”的抗争策略,[47]以解决新环境下的新闻实践与“命令型体制”[48]之间的张力。新媒体技术兴起后,产生于网络平台的线上新闻“作坊”与体制之间也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源于线上新闻“作坊”开拓了职业系统之外新的从业领地。但因这一领地只是小规模的“作坊”,并不能带来结构性的变化,因此,线上新闻“作坊”也需要遵守现有“鸟笼”内的行动规则,运用一定的实践策略来获得实践空间。这些策略包括:
(1)把握边界。“把握边界”是从业的基本要求。虽然在体制之外,线上新闻“作坊”的从业者也恪守我国新闻实践在选题、报道角度以及报道可行性等方面的边界,以确保报道和平台的“安全”。“多年的传统媒体的从业经验让我们很清楚边界在哪里,我们在实践当中有几个原则,‘红线’是肯定不碰的,有争议的尽量选择可以做的角度,在能够做的议题和领域内发挥”。(4号被访者)
(2)变换体裁。拓宽或者改变体裁可以被认为是线上新闻“作坊”的实践策略,非虚构写作就是一例。尽管有学者将非虚构写作视为新时期新闻话语范式的转型,但“非虚构”的概念来源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49]与“新闻报道”之间的交叉[50]使得“非虚构”成为扩大新闻内容来源和内容表现形式的新体裁,“‘非虚构’的提法不是新闻,可以规避一些风险,实际上,当下所谓的‘非虚构’,就是特稿嘛”。(6号被访者)
(3)身份移植。身份移植是指利用其母体机构的新闻从业资质或在垂直领域的信息服务资质,模糊身份进行新闻原创或某个专业领域的深度报道。比如,在我们考察的案例中,有个别案例是隶属于某网络平台的公众号,此平台已经获得了某类新闻信息服务(比如转载、聚合或发布)的许可,其下属的公众号便借助其母平台所拥有的某种新闻业务许可从事新闻生产。还有利用母公司在某专业领域的信息服务而致力于专门领域的新闻报道的,比如丁香园旗下的“偶尔治愈”公众号,这些都可视为是身份移植策略。
(4)随机应变。“随机应变”并不是现在才有的策略,在传统媒体的新闻实践中早有了各种式样的“临场发挥”,[51]但新媒体技术使得“随机应变”更加发扬光大,不仅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报道当中,更是运用到了平台的运营当中。比如,线上新闻“作坊”大多依托于微信公众号的技术形式,大大降低了平台创建和维护成本,如此便意味着更容易应对“突如其来”的(政策)变化。“这个号没了,就再弄一个呗”(7号被访者),“随时准备着被解散,只要愿意做,就再开一个”(8号被访者),这种可以抛却“阵地”的“随机应变”体现了新媒体技术独有的灵活性。
从这些实践策略来看,线上新闻“作坊”既没有破坏现有新闻职业系统制度安排的企图,也不具备足够的力量,他们只能在模糊的身份界定中寻求生存的空间。当然,也正是因为模糊的身份界定,反而使他们获得了一定的从业空间,“毕竟我们不是新闻机构,只有网信办一个管理部门”(4号被访者)。
不过策略与规制也是“磨合”前行的。为了应对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包括线上新闻“作坊”在内的新的实践形态,国家不断出台一些新的规制措施,以维护传统新闻职业系统的稳定性。这些措施包括: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对新媒体平台的内容生产进行监督和治理,比如,2018年,国家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成为中央直属的议事协调机构,提高了对网络信息治理的重视;强化对原创新闻从业资格的管理,体制外的新媒体平台均无获得合法进入原创新闻实践的资格;[52]通过对互联网平台的信息服务实施分类管理的方法,限制新媒体平台从业者采访权的获得等。[53]总之,由于没有官方授予的从业资格,又受到“鸟笼”的限制,虽然线上新闻“作坊”能够利用新媒体技术的便捷性发展出一些实践策略,但在当前我国新闻职业系统的制度安排下,不要说无力竞争职业管辖权,就连进入职业系统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线上新闻“作坊”必须借用其他方式获得从业的正当性。
五、倚重“专业主义”,获得正当性
克莱根(Klegon)认为:对于那些个人的、小型的从业者来说,借助于已经形成的被认同的“专业主义”价值体系,是获得正当性的策略。[54]通过对不同线上新闻“作坊”的个案考察,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策略,即其从业者特别强调并利用“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及实践技术来构筑正当性。
(1)明示“专业性”或“专业主义”价值理念。这一点在诸多案例的平台介绍,从业者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以及我们的访谈中都有体现。比如“偶尔治愈”初创者强调的“要打造医疗领域专业的深度报道平台”;“后窗工作室”在其公众号介绍中提及“专注优质内容的生产,秉承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的明示;以及利用了“非虚构”的策略,却又要通过“专业性”的强调来为“非虚构”正名的“故事硬核”等。“故事硬核”团队组建人林珊珊在一篇访谈中提到:非虚构属于新闻行业中的一个高度专业化领域,要不断地采访,才能不断地接近事实真相,“我们这里的人,多少都有点精神洁癖。” [55]在笔者的访谈中,一位被访者也强调“我们十分看重和强调专业性,这样才能有竞争力”(5号被访者)。
(2)践行“专业主义”技术。在新闻生产研究中,新闻专业主义被释义为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秉持服务“公共利益”的理念,另一个是在操作中践行专业主义的技能,包括技术上力求事实与意见分离,形式上力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等。[56]线上新闻“作坊”也通过对专业主义技术的强调来表达其实践的专业性。比如,林珊珊强调在“故事硬核”团队中专门设立了事实核查人员,“事实核查至少可以确保逐字逐句都由采访得来,每一篇非虚构作品中的全部内容都是有所凭据的”。[57]而短暂存在的“ONE实验室”也强调调查核实,“打磨出最真实的新闻故事”,在专业性上曾获得“严苛的自律和专业”的赞许。[58] “偶尔治愈”的主编在访谈中也强调“我们的稿子都是要进行调查、采访的,我们在操作流程中更强调真实、客观”,“我要求记者们必须到现场去,采访到核心的人物,保持克制、中立和客观”。(1号被访者)另有被访者在访谈中也多次强调了“专业”问题,无论是在招人、用人方面,还是对内容的生产和稿子的把关方面,专业理念和专业化的实践操作在整个团队中是极为看重的。(6号被访者)高校的新闻实践平台也是一例,利用互联网这一分发渠道,将原有学生校内的新闻实践推出校园,是一个将新闻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在现实中操练的机会,背靠着高校和新闻专业(老师和学生)的身份,在实践中,践行专业主义是获得认可的唯一办法,这一点可以从南京大学的“NJU核真录”的公号定位、选题及生产模式中体现出来。
尽管“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和操作技术为线上新闻“作坊”的新闻实践提供了可被倚重的正当性资源,但这一话语支持并不充分也不稳定。从当下我国新闻职业体系的制度安排来看,体制外的从业空间能有多大,可以走多远,都没有定数。也正是由于这样说不清楚的未来,使得线上新闻“作坊”的从业者流动特别快,正如一位被访者描述的,“这个行业的人员流动特别大,不是说收入不好,而是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要走到哪里或者能够走到哪里”。(2号被访者)这个“找不到方向”,一是指没有合法性保障,个人的职业轨迹和发展空间不明确,另一个也指线上新闻“作坊”没有形成成熟的产业模式,机构的发展路径也不明晰。
六、难“产”之业:空间与局限
职业社会学认为,产业在职业体系中起着供养从业者、对劳动力市场实施控制权的重要作用。曾几何时,供职于传统媒体是可以带来收入和社会地位双重保障的职业,[59]体面的职业地位和收入使得大批的新闻从业者创造了我国新闻业的“黄金时期”。[60]虽然学者们大多从新闻操作的空间和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界定和阐述这一“黄金期”,但不可否认的是,职业回报是支撑从业者创造“黄金期”的重要条件。
互联网技术向内容产业的介入极大地削弱了传统媒体的盈利能力,造成了传统媒体产业模式的崩塌,供养能力的减弱使得大量从业者转型离开。然而,离开传统媒体并不必然意味着离开新闻业,我们所考察的线上新闻“作坊”中便有许多传统媒体的跳槽者进入网络平台继续进行新闻生产。比如,“故事内核”、“后窗工作室”的采写团队大部分都是原传统媒体的从业者,其中以深度报道记者和特稿记者居多,“偶尔治愈”团队成员也分别来自南方报业、《凤凰周刊》及“财新传媒”等。
在笔者的访谈中,有被访者如此解释自己的“跳槽”,“主要是因为收入,现在同样是做新闻工作,但比我原来(在传统媒体)的收入高了很多”。(5号被访者)也有一位曾经在纸媒、电视台都做过深度报道的记者称“当有一天发现人们的阅读习惯已经改变了,你的读者已经不在传统媒体了,想要做新闻应该到互联网平台去谋求发展”。(9号被访者)可见,无论是更高的收入还是更适宜的空间,互联网确实为新闻从业者提供了传统媒体之外的,可以选择的从业平台,从这一点看,互联网可被视为是打破传统媒体对新闻职业劳动力垄断的解放性力量。
然而,从产业运营的角度来看,线上新闻“作坊”因为没能发展出成熟的产业模式,[61]同时又受到互联网经济模式的限制和冲击,尚没能发展成为行业内具有较大供养能力的大企业。在笔者所考察的线上新闻“作坊”的案例中,有依赖于母公司支持的,如“偶尔治愈”“后窗工作室”等;有依赖公益基金支持的,如“真实故事计划”;有与互联网企业合作的,如“故事硬核”;有依赖于志愿行为的,如各个高校的新闻实践等。大多数线上新闻“作坊”的运营仍以业界所称的“包养”模式为主。这种“包养”模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机构如何存续以及做大做强,如何为从业者提供稳定的、具有上升空间的职业回报等。虽然以“ONE实验室”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平台曾经希望通过出售版权的方式建立产业模式,但并不成功,ONE实验室也于2017年9月前后宣布解散。这些没有成熟产业模式,仍以小型团体或个人实践为主的线上新闻“作坊”,对于改变当下我国新闻职业的系统结构难有突破。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包养”模式从一定程度上又运行了一种类似于“公共新闻”的尝试。比如,“故事硬核”的林珊珊在访谈中提到,“比起在传统媒体工作时,大多记者尚不具备足够宽松的创作环境,版面和发行要求使得想要把稿件反复打磨,做到极致,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而今,“故事硬核”并不考虑太多利益诉求,在与腾讯新闻谈合作时,“我们都能看到彼此对新闻理想有种类似的执着,并没有感受到很强的利益诉求”。[62]同样地,“偶尔治愈”的主编在访谈中提到,“丁香园对我们没有营利要求,反倒让我们觉得拿着这么多资金支持,必须要做出好的内容来”(1号被访者)。“我想平台支持我们做高品质的新闻是为了树立口碑吧,这样反倒让我们可以更纯粹地去做新闻”(6号被访者)。
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提出,报纸、杂志、广播公司和新闻学院,这些新闻事业应被视为是一项非营利的活动 ……应服从于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63]虽然,“公共新闻”理念在落地实践时饱受争议,[64]但反观当下这些线上新闻“作坊”,这种被“包养”的“做新闻”的模式,“标榜着”并在一定程度上践行着新闻专业主义,反倒具有了“公共新闻”色彩,或可被视为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多元实践的尝试。
七、结论与讨论
新闻业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实践,其发展与技术变革息息相关,也因为如此,技术对新闻业影响的讨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英国新闻传播学者马丁·康博伊(Martin Conboy)和斯科特 A. 埃尔德里奇(Scott A. Eldridge II)认为,应该用“渗透”(permeation)这个概念来理解技术对新闻业的传统、实践和沟通所宣称的各个方面的入侵。[65]新媒体技术兴起后,新闻业产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有对新闻业普遍内容生产方式、职业权威及产业模式的影响,也有催生多元实践并形成对一个具体社会语境的意义。对于前者,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出了普遍性的“危机”话语;但对于后者,“多元实践”在一个具体语境中如何存在、能够产生如何的影响,需要进入一个系统结构中进行考察,本文正是希望在后一个路径上做些尝试。
因此,借用职业社会学中职业系统的相关论述,通过对我们视为“多元实践”的线上新闻“作坊”在职业化生存状况、专业主义理念和技术应用、产业模式及职业供养能力等维度的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互联网打破了传统新闻业的渠道垄断,为体制外的新闻实践提供了可能。然而,我国现有的职业系统通过授权新闻采访权和内容传播权来维护传统媒体对新闻业的职业管辖,使得线上新闻“作坊”并不具备官方认可的从事新闻生产的合法身份。一方面没有合法身份,一方面又要符合“鸟笼”内的规则要求,网络提供的技术空间与制度限制之间形成的张力使得线上新闻“作坊”只能通过多种策略来寻求生存和发展。
其次,作为“作坊”存在的新闻生产机构,在缺乏合法身份保障的情况下,更加倚重已形成的、被广泛接受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来获得认可和从业正当性,这与一些体制内媒体曾经利用“专业主义”理念来构筑象征性资源一样,新闻专业主义也成为线上新闻“作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话语资源。
最后,“作坊”仍然意味着小规模和“游击式”。在缺乏体制内资源支持以及在互联网经济本身盈利模式不清晰的情况下,线上新闻“作坊”很难形成产业规模来竞争新闻工作的职业管辖权。不过,新媒体平台毕竟为新闻从业者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从业机会,从这一点看,新媒体技术又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新闻职业系统中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成为影响当下我国新闻职业系统结构稳定性的因素。
基于上述几点结论,我们还希望就技术与新闻业及新闻职业系统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做些探讨:
首先,在任何时候,新闻业都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的存在,当我们在探讨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时,话语的指向不能离开新闻业所在的社会历史背景。从我国当下新闻职业系统的制度安排来看,体制内的新闻媒体仍然占有对新闻工作专属的管辖权,虽然互联网这一技术要素能够为体制外的新闻实践提供一定的空间,并改变了新闻生产的方式(比如“液态新闻业”[66]的提出)、为传统媒体从业者的职业困境提供职业流动的选择,但很难(大规模)改变的是体制内新闻业的专属地位。在这样的制度语境中,“危机”话语很容易被替代为传统媒体的产业“危机”,而“救赎”的路径自然是以传统媒体为中心的,进而,很难产生出“救赎”作为公共知识生产实践的新闻业(journalism)的多元话语。
其次,从改革的视角来看,如果说“市场化”、国际交流及新闻观念讨论等因素成为早期的改革动因的话,新媒体技术可被视为是当下主要的刺激因素。只是在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原则下,如果新媒体带来的变革过于剧烈,引发的变化不足以引起系统应对的话,从维护系统稳定角度加以限制是必然的。加上新媒体技术兴起本身带来的内容的混杂、“后真相”等问题,很容易将“危机”简单地归咎于技术本身,从而忽视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性或解放性的力量。
再次,互联网的兴起或许可以改变新闻业的核心工作内容,即某些“五要素”的新闻工作或许可以被市民新闻、UGC的内容,甚至机器人写作所取代,但那些需要信息核查、调查追问、还原真相的新闻工作或许会成为新闻工作更强调的主业。真如此,倒是应和了马丁·康博伊和斯科特 A. 埃尔德里奇的观点,“尽管出现了裂痕,但新闻业正处于一个好时代,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新闻业的核心职责正在得到强化”。[67]但也要看到,由于缺乏合法的从业身份、缺乏成熟的产业模式支持,“作坊”式的生产若想坚持并致力于“有价值”的新闻实践仍然比较困难。
另外,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有学者在论及我国新闻改革时提出,一些“非常规”的新闻实践活动构筑并代表了一些新的新闻观念和社会关系,已经超出了“命令型体制”的范畴,可以说是走上了超越体制的不归路。[68]而当时“超出体制”的新闻活动还只能在体制内的新闻机构中发生,如此看,线上新闻“作坊”的新闻实践至少是在体制外做出了一些尝试,只是在诸多限制下,从历史眼光看,这些尝试对于进一步改革的意义仍无法定论。
最后,新媒体技术对新闻业带来的变化是复杂而深刻的,虽然我们选择了从系统角度,在不同维度上的讨论,也难免挂一漏万或流于表面。但本文至少在“危机-救赎”这一压倒性话语之外来谈论互联网技术对我国新闻业的影响,是一种新立场和视角的尝试,也为探讨技术与新闻业变迁、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来自我国的地方性经验。■
①关于“新媒体”的界定有不同的讨论,本文意在“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的取向上来界定,即用“数字化”和“网络”这两个基本的技术特征来作为“新媒体”的分野(Manovich,2001;Jensen,2010)。转引自: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 “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年第1期
②也有被称为“公民新闻”或“民众新闻”的,主要是指个人(网民)通过网络平台参与的新闻实践活动。
③相应的研究包括:高国营&陈旭东(2006)、吴飞(2013)、胡翼青(2013)、王君超(2014)、李艳红&陈鹏(2016)、王维佳(2016)、彭增军(2017)、刘德寰&李雪莲(2017)等。另外,还包括相当多有关新闻职业边界的讨论,也蕴含在“危机”话语的背景下,并预设一种二元视角,即传统新闻机构的职业新闻人是业内人,是新闻业边界的维护者,而依托新媒体平台展开的新闻实践及实践者是业外人,是边界的破坏者,具体的研究不再列举。
④李艳红、陈鹏:《“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
⑤参见:陈国权:《2017中国报业发展报告》,《编辑之友》2018年第2期。有关党报的经营状况,与笔者在访谈中得到的信息一致,据某省级报业集团多年的从业者提及,他们报社的党报当下营利状况还比较好,但相当的资金来自于政府扶持以及各级政府所做的宣传广告。在此并无意对这种“救赎”的方式以及可持续性的效果进行评价,只是说这样对待危机的方式出发点和出路都有着我国语境中的特殊性。
⑥2009年,舒德森与小伦纳德·唐尼为应对美国新闻业危机发表的《美国新闻业的重建》的报告中曾提到,“新闻已成为单靠私营机构很难支撑的一种公共产品,应探索更多的尝试”。参见:[美]迈克尔·舒德森、黄煜:《社会学视角下的传媒研究:新闻、民主及其未来》,《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第30期。 另外,美国学者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和妮可·厄舍(Nikki Usher)所关注的新成立的数字新闻创业公司以及那些致力于提供小众新闻(niche news)的形式多样的网络新闻实践,被视为是西方新闻业救赎“危机”的一些探索。参见:Carlson, M. & UsherN. (2015). News startups as agents of innovation. Digital Journalism, 4(5)1-19. 转引自:於红梅、马特·卡尔森、妮可·厄舍:《新闻业传统的继承与革新——对10家数字媒体创业公司宣言的分析》,《新闻记者》2016年第3期。
⑦Zelizer,B.(2015). Terms of Choice: UncertaintyJournalism, and Crisis. Journal ofCommunication65(5)888-908.
⑧皮卡德(Picard)教授曾说,“新媒体出现后,传统的新闻生产正在被分解为服务模式(service production mode)和手工模式(craft production mode),其中手工模式是指新闻是由个体创业记者和强调新闻品质和个性的小型记者合作社生产”,这种合作社形式与本文关注的线上新闻“作坊”的新闻实践有诸多类似。参见:李莉、胡冯彬:《新闻业的黄昏还是黎明?——罗伯特·皮卡德谈变化中的新闻生态系统》,《新闻记者》2015年第3期
⑨尽管早已有“网络新闻”“市民新闻”这样的概念来指涉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新闻实践形态,但“网络新闻”的界定过于笼统,“市民新闻”不能包罗体制之外的,但依托于机构的新闻生产,之所以用“作坊”一词试图表达一种有组织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原创的新闻实践活动。另外,也有“网络原创新闻”的说法,但由于互联网(公司)不具备从事原创新闻生产的合法性,应某些被访者的要求,希望不进行如此的定名。
⑩也有译为“专业社会学”的,在此使用“职业社会学”的译法,更多来自于对“职业社会学”一些译著的认同。参见:[美]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11]需要说明的是,《职业系统》一书的作者阿伯特在对“职业系统”的论述中并非只论及了职业管辖权、“专业主义”(在《职业系统》一书中被翻译为“职业主义”,有关两种译法的不同,参见注释23)以及产业模式这些方面,并且,在阿伯特等人看来“专业主义”、产业模式是竞争和维持职业管辖权的策略和要素。考虑到新闻业的特殊性以及对新媒体兴起后,新闻业产生“危机”变化的三个主要方面(职业危机、“专业主义”危机和产业危机),本文则主要分析这三个维度,但并不否认还可以作出更多面向上的讨论。
[12]Carr-SaundersA. M. & Wilson, P. A.(1933). The Professions. Oxford : Clarendon Press,转引自:AbbottA. (1988).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7.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3]AbbottA. (1988).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 72.-84. 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4]AbbottA. (1988).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 72.-84. 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AbbottA. (1988).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 72.-84. 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6]AbbottA. (1988).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 72.-84. 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AbbottA. (1988).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 72.-84. 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AbbottA. (1988).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 72.-84. 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FreidsonE. (1989).Theory and the Professions. Indiana Law Journal64(3)Article 1.Available at: 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ilj/vol64/iss3/1
[20]AbbottA. (1988).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 72.-84. 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1]比如,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将支撑一切职业的专业知识变成可以通过编程被机器模拟的简化形式,取消所有可以被机器替代的工作的职业管辖权。参见:DudaR. O. & Shortliffe, E. H.( 1983). Expert Systems Research. Science220(4594)261-268.
[22]徐来、黃煜:《新闻是什么”——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模式演变与新闻学教育之思》,《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4期
[23]professionalism一词,在阿伯特等职业社会学家使用的意义本源上看,翻译为“职业主义”也许更为贴切,因为,在其职业化或职业管辖权的论述中,“职业”一词已包含了中文“专业”一词的含义的,而在阿伯特等人的论述中,“专业”一词对应的英文为“specialty”。但鉴于在新闻传播领域,“专业主义”是一个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形成共识的用法,为了不再增加混乱,继续使用“专业主义”,如无特别说明,此“专业主义”就是“professionalism”。
[24]Johnson, T. J. (1972). Professions and Power. London: Macmillan.
[25]EvettsJ. (2006). Organiz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professionalism: The legacies of Weber and Durkheim for knowledge society ( MarcuelloC. & FadosJ. L. eds.PP. 61-79). Zaragoza: Prenas Universitarias de Zaragoza.
[26]比如,涂尔干(Durkheim,1992)评估“专业主义”是一种基于职业成员(occupational membership)的道德社区(moral community)形式。休斯(Hughes,1958)认为专业主义反映了在一个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中,经济关系中信任的重要性。艾略特·弗雷德森( Freidson,2001)将专业主义作为为与市场和官僚组织之外的第三种逻辑,维护着职业的顺利发展。参见:DurkheimE. (1992).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 London: Routledge. 休斯(Hughes,1958)的论述转引自:DingwallR. & LewisP. eds.(1983).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 LawyersDoctors and Others. London: Macmillan.FreidsonE.(2001). Professionalism: The Third Logic. London: Polity.
[27]EvettsJ. (2003).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ism occupational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International Sociology18(2)395-415.
[28]FreidsonE. (1989).Theory and the Professions. Indiana Law Journal64(3)Article 1.Available at: 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ilj/vol64/iss3/1
[29]弗雷德森(Freidson)认为,起着支柱作用的大企业或部门的职业实践为付薪实践(salaried practice),在阿伯特《职业系统》的中译本中被译为“授薪实践”,而个人的、小作坊式的实践为个人实践(solo practice)。参见:FreidsonE. (1989). Theory and the ProfessionsIndiana Law Journal64(3)Available at: 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ilj/vol64/iss3/1; [美]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30]KlegonD. (1978).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An Emerging PerspectiveWork & Occupations5259-283.
[31]根据潘忠党的描述,“鸟笼”是一个比拟的说法,之所以称之为“鸟笼”既意味着(党和国家)允许一定空间的大原则的控制,同时也意味着这一控制的调整,但在另外一些学者的使用中,更强调的是“控制”,即动词的“cage”(关在笼子里)这一意涵。相关的论述可参见: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ChenH. L.& Chan, J. M. (1998). Bird-Caged Press Freedom in China(JosephY.S. Cheng ed.PP. 645-668).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新闻学研究》(台北)2009年第100期。
[32]张志安、李蔼莹:《2017年中国新闻业年度发展报告》,《新闻界》2018年第1期
[33]FreidsonE. (1989).Theory and the Professions. Indiana Law Journal64(3)Article 1.Available at: 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ilj/vol64/iss3/1
[34]KlegonD. (1978).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An Emerging PerspectiveWork & Occupations5259-283.
[35]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新闻学研究》(台北)2009年第100期
[36]潘忠党:《有限创新与媒介变迁:改革中的中国新闻业》,陶东风、周宪编,《文化研究》(第7辑)第7-2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7]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
[38]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第32页,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9]孙玮:《媒介话语空间的重构: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媒介话语的三十年变迁》,《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8年第6期
[40]参见: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于“市场”的作用,也有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何舟提出“市场化”促使我国的新闻媒体演化成了“党的公关公司”;周翼虎认为新闻业最初以市场名义打“擦边球”,获得政治声望和经济利益,但丰厚的经济利益导致同业竞争,从而保持与政府的恭顺以规避竞争风险,因此,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专业化。参见:ZhouH. (2000).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n a tug of war: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Chin-Chuan Lee ed.PP. 112-151).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新闻学研究》(台北)2009年第100期
[41]习近平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6年2月19日,参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8-08/21/c_1123299834.htm
[42]AbbottA. (1988).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 72-84. 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3]虽然“市民新闻”、UGC内容、机器人写作也是互联网带来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变化,但一来,这些变化对新闻业的影响是普遍的,不能突出我国的本土特点;二来,这些新闻生产方式消解了新闻职业和“专业主义”,似乎没有了讨论的基础;再者,从实践上看,线上新闻“作坊”更加强调深度报道,在新闻理念上更趋近于对新闻作为“公共知识”的界定,似乎与“市民新闻”、UGC内容、机器人写作在相反的路子上探索着维护“有价值”(被访者语,1号、5号被访者)新闻的尝试,而这样的新闻实践,在救赎传统新闻媒体产业危机的话语背景下,更有探讨的价值。
[44]“偶尔治愈”是“丁香园”旗下的深度报道部门,专注于医疗领域的深度报道,平台运行类似于互联网的垂直领域;“ONE实验室”是原亭东影业旗下的非虚构写作平台,代表了当下新媒体新闻实践的多样化体裁,这一点与“中国三明治”、“真实故事计划”一致,但“ONE实验室”已经解散,可以作为“失败”的案例与其它案例进行对比;搜狐的“后窗工作室”是搜狐新闻下的一个深度报道部门,致力于打造一个符合互联网传播规律的、“小而精”的深度报道平台;腾讯“谷雨”是腾讯旗下的“非虚构”创作与传播的非盈利项目,通过支持并培训写作者,所创作的作品可以在“谷雨”平台发布;“故事硬核”是“ONE实验室”解散后原班人重建的“非虚构”项目,后与腾讯“谷雨”合作并依赖腾讯的渠道发布;南京大学的“NJU核真录”是依托于新闻院校以学生团队为主的新闻实践平台(类似的还有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布谷岛”、中国人民大学的“RUC新闻坊”等),“核真录”致力于“事实核查”的理念与实践,它既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新闻样式,又代表着隶属于大学机构的,依赖于学生的志愿(或实习)劳动存续的新闻实践方式;“中国三明治”是由前南方报业记者创办的国内最早的“非虚构写作”的孵化平台,它招募写作者并提供一定的专业指导,所得作品通过“三明治”平台发布,不过如今“三明治”的定位略有变化,内容不仅局限于“非虚构领域”;“真实故事计划”由原《南方周末》深度报道记者创办,通过提供传播平台招募写作者发布“非虚构”作品,“真实故事计划”还拥有一个基本以媒体人组成的团队,对作品内容在真实性上进行核验和把关,用其创办者自己的话讲就是把原来在媒体的工作方式“平移到真实故事计划这样一个公众号或者说一个项目上面”。以上材料来源于各个项目的机构简介、笔者访谈及其他一些公开出版的文献材料,来源资料庞杂,在此略去具体出处,有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45]应被访者要求,对某些被访者隐匿其工作机构名称。
[46]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
[47]王毓莉:《驯服v.s.抗拒:中国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专业抗争策略》,《新闻学研究》(台北)2012年第110期
[48]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
[49]黄典林:《话语范式转型:非虚构新闻叙事兴起的中国语境》,《新闻记者》2018年第5期
[50]对于“非虚构”与新闻(尤其是特稿)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同的意见,在此不列举。但在业内也有相当的观点认为非虚构写作是新闻的一个分支,或者有人就认为就是新闻特稿。参见:曾润喜、王倩:《从传统特稿到非虚构写作:新媒体时代特稿的发展现状与未来》,《新闻界》2017年第2期。周逵、顾小雨:《非虚构写作的新闻实践与叙事特点》,《新闻与写作》2016第12期。相关的论述还可参见:ONE实验室解散——那些真实的新闻故事背后,http://www.sohu.com/a/199232890_317170
[51]潘忠党:《“补偿网络”: 作为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52]自2017年6月1日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令第1号)实施。根据《规定》,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申请主体应为中央及地方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中央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新闻单位,申请的受理和审核决定由国家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作出。截至2018年8月31 日,经各级网信部门审批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总计343家,1767个服务项,本文所观察的案例均不在审批之列。参见:《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许可信息》,http://www.cac.gov.cn/2018-09/10/c_1122842142.htm
[53]当下对新媒体平台的新闻信息服务许可分为“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播平台服务”三类形式,也就是说具有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平台并不一定具有新闻采访权,像腾讯、新浪、搜狐、网易等商业网站因不具备新闻采访权,其平台的从业者也就不能申领记者证,参见:张志安、李蔼莹,2018。
[54]KlegonD. (1978).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An Emerging PerspectiveWork & Occupations5259-283.
[55]杨佳琦:《“卧底深圳45天,我被一条皮带救了命”——探访故事硬核》,http://www.sohu.com/a/241093075_647752
[56]参见:GansH. J.(1979).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NY:Pantheon Books. 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李金铨:《“媒介专业主义”的悖论》,《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4期
[57]杨佳琦:《“卧底深圳45天,我被一条皮带救了命”——探访故事硬核》,http://www.sohu.com/a/241093075_647752
[58]ONE实验室解散: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挫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0930514298130588&wfr=spider&for=pc
[59]潘忠党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对当时的记者、编辑的收入及社会地位进行过细致描述。可参见: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
[60]李红涛:《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5期
[61]这里所谓的“没有发展出成熟的产业模式”是就线上新闻“作坊”的总体状况而言的,即它没能像传统媒体一样发展出“二次售卖”这样清晰的产业模式,但也不排除某些案例通过特殊方式获得资金,比如,据报道“真实故事计划”曾获得1200万元的A轮融资,或一些“非虚构”平台试图通过出售版权的方式获得盈利等。
[62]杨佳琦:《“卧底深圳45天,我被一条皮带救了命”——探访故事硬核》,http://www.sohu.com/a/241093075_647752
[63][美]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著:《富媒体 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谢岳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64]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5]於红梅、马丁·康博伊、斯科特A·埃尔德里奇:《绝处逢生的机遇:危机和新技术条件下新闻业的元话语》,《新闻记者》2015年第4期
[66]陆晔、周睿鸣:《“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7期
[67]於红梅、马丁·康博伊、斯科特A·埃尔德里奇:《绝处逢生的机遇:危机和新技术条件下新闻业的元话语》,《新闻记者》2015年第4期
[68]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
李东晓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感谢中山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举办的“2018中国新闻业研究圆桌论坛暨媒体融合再审视工作坊”的邀请,以及在会议中夏倩芳、白红义、陈楚洁等几位老师对本文提出的批评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