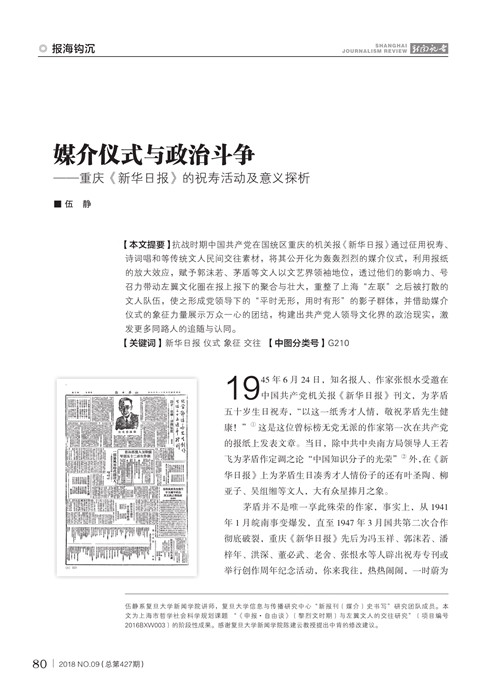媒介仪式与政治斗争
——重庆《新华日报》的祝寿活动及意义探析
■伍静
【本文提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通过征用祝寿、诗词唱和等传统文人民间交往素材,将其公开化为轰轰烈烈的媒介仪式,利用报纸的放大效应,赋予郭沫若、茅盾等文人以文艺界领袖地位,透过他们的影响力、号召力带动左翼文化圈在报上报下的聚合与壮大,重整了上海“左联”之后被打散的文人队伍,使之形成党领导下的“平时无形,用时有形”的影子群体,并借助媒介仪式的象征力量展示万众一心的团结,构建出共产党人领导文化界的政治现实,激发更多同路人的追随与认同。
【关键词】新华日报 仪式 象征 交往
【中图分类号】G210
1945年6月24日,知名报人、作家张恨水受邀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刊文,为茅盾五十岁生日祝寿,“以这一纸秀才人情,敬祝茅盾先生健康!” ①这是这位曾标榜无党无派的作家第一次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当日,除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王若飞为茅盾作定调之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②外,在《新华日报》上为茅盾生日凑秀才人情份子的还有叶圣陶、柳亚子、吴组缃等文人,大有众星捧月之象。
茅盾并不是唯一享此殊荣的作家,事实上,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直至1947年3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重庆《新华日报》先后为冯玉祥、郭沫若、潘梓年、洪深、董必武、老舍、张恨水等人辟出祝寿专刊或举行创作周年纪念活动,你来我往,热热闹闹,一时蔚为风潮。尤其是1941年郭沫若的五十寿庆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新华日报》不仅在头版社论处刊载周恩来的署名代论,③将郭沫若赞为“鲁迅的继承人”、“中国文艺界的领袖”,还增辟三、四两版特刊,专门登载董必武、邓颖超、潘梓年、沈钧儒、沈尹默等十数人的贺诗、贺词,甚至在此后长达半年之久,持续发表各类祝贺文章,其规格之高、声势之大,无出其右。据操办者阳翰笙回忆,这次“寿郭”是领导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筹划已久的“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④而南方局第二年打给党中央的报告亦称,祝寿活动已成为当时中共党组织在城市开创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工作方式。⑤
原本是文人内部私人性的祝寿往来、诗词唱和,何以被政治组织取材、征召为公开的媒介仪式?惯于以文会友的文人群体在报纸的穿针引线之下产生了何种新的交往和集结形态?政治组织如何借助媒介仪式和符号象征来构建现实、合法化自己的权威?
本文以媒介仪式为视角,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的祝寿仪式为个案,分析当时在政治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以报纸为粘合剂,联络和团结国统区文人,恢复、壮大上海“左联”之后被打散、颠沛流离的左翼文人队伍,使之形成党领导下的不是组织却胜似组织的影子群体,并借助媒介仪式的象征力量传递讯息、展示团结,孕育大众对其合法性的认同感。
“看不见领导的领导”:作为共产党人格化象征的《新华日报》
1938年创刊于武汉(十个月后转移至重庆)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公开的全国性日报。在之前的十年(1927—1937)中,共产党没有自己公开的舆论机关,在国统区几近失语,而国民党政府所掌握的报刊上则充斥着对共产党的舆论攻击与负面宣传。在此背景下,《新华日报》的出版称得上是“破天荒的大事”。⑥“这张报纸的发行,使中共在宣传上、在政治斗争上,以及在后来的发展诸方面,均有显著深刻的影响”。⑦
存在于中国政党政治高潮时期的《新华日报》是一份十分特殊的报纸:她既不同于当时处于执政地位的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也不同于欧美共产党的机关报;她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是两党关系的晴雨表,既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又无时无处不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管制和监视;她是一份被例外准许出版的公开合法报纸,但其主办者——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却并未取得合法地位,不被允许在国统区发展组织,长期处于秘密、地下状态,亦出于抗战形势的需要,有意淡化了对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等鲜明意识形态的宣传。⑧
人类学家大卫·科泽(David I. Kertzer)认为,政治通过象征来表达,所有的政治行为体都是象征的产物,从政党到政府皆是如此。⑨也正如米歇尔·沃泽(Michael Walzer)所言:“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方能热爱,必被想象才能被接受。” ⑩在这个意义上,政党组织同样并无实形,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只能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党员或象征形式被看见、被想象。抗战时期,隐没于国统区地下、对大多数人尚属神秘的共产党更是如此。《新华日报》幕后领导人、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其罕见的个人魅力,在很多亲身接触过他的党外人士眼中,成为共产党的一个化身,在党的统战工作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1]而一般民众日常能直接接触、阅读的《新华日报》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格化的一个象征,是“党在国统区的形象代表”。[12]在国统区渐趋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除了日常的宣传之外,《新华日报》事实上扮演了超乎一般党报的角色——负责掩护和发展党的秘密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代行党的领导机关职能,可谓“看不见领导的领导”(周恩来语)。[13]抗战初期,在重庆等国统区城市,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本来就少,群众基础较为薄弱。“为避免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摧残,我党在国民党区域,除掉少数做上层统一战线的党员必须公开者外,一般的党的组织及党员的面目,都力求保持秘密”。[14]而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濒于破裂,党的组织、活动方式被迫进一步垂直化、秘密化,“改为个人接头关系”,[15]支部之间和党员之间一般不发生不必要的横向联系,以至于共产党员之间互不知对方党员身份、“不知党在哪里”的情况也甚为常见。
横向的人身接触被限制,客观上反而促进了党内及党与民众之间纵向的和精神的沟通。正如托克维尔、塔尔德、安德森[16]等多位西方学者不约而同指出的:报刊为分散的、孤独的、身体上不接触的读者创造精神上的联系,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分享知识和思想,形成不在场的想象的共同体。此时的《新华日报》依托其“同时共享”的报刊特性,发挥了一枝独秀的影响:他就如同党的一位领导人,跨越中间层级,直接对党员发出指示、与群众对话,“成了代表共产党每日向国统区人民讲话的主要工具”。[17]党员万秉涛在回忆1946年重庆蜀都中学党组织的情况时提及,“这些同志间虽不发生横的联系,但通过学习讨论当时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文章报道中沟通思想,交换看法,明确了形势任务,体现了党的领导,统一了认识和行动”。[18]前“左联”作家艾芜比较了《新华日报》出版之前与之后党的领导的区别:“在上海‘左联’时期,中央搬到苏区去了,任何文件都看不到,传单也看不到,但是(抗战时期)在桂林,党的意图、指示通过《新华日报》、《群众》传达出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这是直接受到党的领导,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 [19]而当时因阅读《新华日报》而倾向共产党、成为党的同路人的读者更是不计其数,恰如齐邦媛的观察,“在报纸是唯一新闻来源的时期,他们(《新华日报》)的言论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与学生”。[20]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曾在《新华日报》创办八周年时喊出过“新华日报万岁”的口号。[21]一位读者则投书《新华日报》说:“我们虽然未曾见面,但我敢相信,我们中间已在无形中建立起一种不朽的友谊——远超过任何一种,因为我们是在同一目标之下努力着。” [22]正因着报纸的人格化,在国共政争白热化的时期,《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几乎分别成为共产党、国民党的代名词、发言人,“国共两党之间的争论多次成为两党机关报之间的论战”,[23]连报童中流行的卖报声“《新华》——《扫荡》——《中央》!”也有着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隐喻。如此一来,在什么报纸上发表文章、阅读什么报纸、接受什么报纸采访,并不被简单地看作是兴趣使然,而成为判断当事人党派倾向和身份认同的标志。以报识人、人以报分的现象在1940年代中期的重庆达到顶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张恨水起初不愿给共产党的报纸写稿,被党“争取”过来后,在《新华日报》上时有文章发表,引得陈果夫怒斥国民党宣传部,“张恨水这样有影响的作家,怎么也被《新华日报》拉去了!” [24]茅盾(沈雁冰)曾被国民党文化负责人张道藩约谈,称“沈先生一到重庆连续给《新华日报》写文章,便容易引起误会”。[25]郭沫若在回忆录中曾提及给《新华日报》题词时闹出的岔子,“‘委座’(蒋介石)表示不满意,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在有色彩的报纸上发表文字”。[26]抗战时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台湾作家王鼎钧,因害怕被揪辫子而不敢看《新华日报》。[27] “至于读者,不但没有订阅和购买《新华日报》的自由,而且一旦被发现,还要受到严重迫害,从被捕、坐监牢、关集中营,直到被杀害”。“有人认为读《新华日报》就是共产党”。[28]国民党方面还散布过这样的咒语,“说是如果还看《新华日报》,就要遭神谴,七孔流血而死云云”。[29]日本学者前田哲男的研究发现,“在重庆,很少有机关能够痛痛快快地接受该报采访,看到《新华日报》记者的名片拒绝采访,不愿意协助提供信息的现象常有发生”。[30]
“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新华日报》的“寿郭”仪式与象征意义
诗词唱和、互相祝寿历来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交往方式。报纸等现代传媒出现后,显现出其强大的交往功能,为文人的交游延展出广阔的平台,使得文人聚会、雅集的传统人际交往之上又叠加出“面觌殊悭,神交已久” [31]的新样态。蒋芷湘1870年代在《申报》主持笔政期间,就曾多次在报上组织大型的文人诗词唱和。到了1880年,在《申报》报人邹弢笔下,唱和作品经由《申报》刊登之后形成了报上与报下“一时中外诗人和者数百家” [32]的壮观局面。至于祝寿,民国时期,名人雅士互相祝寿、诗词往还的活动极为丰富,包括鲁迅都未能免俗。1930年9月17日“左联”发起了鲁迅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从日记和致友人的信中不难看出,鲁迅对此次寿辰是颇为重视的。只是囿于当时的环境,活动系秘密举行,局限于一百多人的小范围。而十一年后的1941年,“鲁迅的继承人”郭沫若的五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庆祝会在重庆《新华日报》“特刊”的加持下,则演变为一场热热闹闹的媒介仪式。
这场非同寻常的“寿郭”仪式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筹备的,并蕴藏着深刻的潜台词。据当事人、担任周恩来助手的阳瀚笙回忆,“一九四一年十月上旬的一天,郭老和我正在家里商议工作,周恩来同志来了,他兴致勃勃地提出要庆祝郭老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郭老当即谦辞。恩来同志深沉地指出:‘为你祝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33]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周恩来的署名代论《我要说的话》(标题为罕见的周恩来手书),用一系列排比句将郭沫若与鲁迅相提并论:“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当天该报还比平日增出三、四两版祝寿特刊(刊头亦为周恩来亲笔题写),登载郭沫若大幅半身照,以及潘梓年、沈尹默、沈钧儒、潘友新(苏联驻华大使)、董必武、邓颖超、绿川英子(日本反战作家)、田汉、吴克坚、徐冰、陈家康、王亚平、欧阳凡海、张西曼等十数人的贺词、贺诗,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与其他报纸只是在第二天(11月17日)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再现祝寿会的场景不同,经过特别筹划的《新华日报》是在祝寿会当天(11月16日)一早就出刊的,与重庆2000人庆祝大会及全国多地同时举行的祝寿会形成里应外合、交相辉映的态势。纪念会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由同样颇具象征意义的爱国将领冯玉祥主持,沈钧儒、老舍、米克拉舍夫斯基(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均发言称颂郭沫若的成就,周恩来作热情洋溢的压轴讲话:“……郭先生在我国文化界是一面色彩鲜艳的大旗,郭先生的旗子插到那里,我们就跟到那里!”据亲历者翁植耘回忆,“在全国规模开展这样盛大的纪念活动,这在中国是空前的”。[34]因1940年起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在重庆组织政治性的集会及演说,[35]成规模、成系列地举行祝寿(或周年纪念)仪式,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乃是借其文化、伦理外衣冲破国民党政治禁锢的一个权宜变通之计,按照另一位祝寿主角、中共南方局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的说法,“当时重庆政治空气恶劣,友好晤面不易。借祝寿集会为避禁网之一法,实则彼时我距六十尚有两年”。[36]但通过报纸将祝寿仪式公开化、政治化,并非中国共产党的首创。这可能一方面是源自苏联报纸的启发和影响,1929年12月21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曾前所未有地辟出八个版来祝贺斯大林五十寿辰,称其为列宁事业的继承人;另一方面,这种“报下”现场集会与“报上”祝寿仪式的“交汇鼓荡”,口头与印刷、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身体在场者与借助报纸在场者、实体空间和报纸营造的想象空间的“互为叠加交叉”,或许是承袭了20世纪初期中国著名革命派报纸《苏报》的遗风。“《苏报》不仅有自己特定的‘放言’方式,并且对于实际运动有建构和激发作用”。[37]客观地讲,以郭沫若当时在文学界、知识界的巨大号召力,是配得上周恩来和《新华日报》代表共产党对他的“加冕”的。事实上,早在鲁迅去世后不久,民间就有以郭沫若继承鲁迅为革命先导的呼声。[38]然而,透过征用祝寿、诗词唱和这种民间既有素材,党借助报纸的放大效应,将一份特殊的党内文件,[39]隐蔽地转换为具有合法性的公共价值,成功地营造出一种集体的欢腾,描绘出共产党引领文化界的政治现实。
郭沫若有着一贯的左翼立场和反蒋经历,是周恩来直线领导的、以无党派民主人士面貌出现的中共秘密党员,是共产党在文化领域最为具象化的展示窗口。而当时共产党尚未取得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不便公开亮明自己的旗帜进行“主义”的说教,对于多数普通民众而言,仍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形象,其精神凝聚很大程度上依赖仪式和象征及其诉诸情感的力量。通过将自身(《新华日报》)与郭沫若这一主流的象征符号挂钩,赋予其新的身份,将之“我们化”,制造普天同庆的热闹场面,党不动声色地向外界传递出“我们”(共产党人及国统区文人)是一个团结一致、亲密无间的整体的讯息,试图激发更多人的忠诚与认同,化为“我们”的一员。
仪式具有鲜明而正式和激动人心的特质,它可以给参与者以心理上的激励,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40]多次撰文参与祝寿的“自己人”叶圣陶对祝寿的目的充分会意,并热情参与其中。他认为祝寿的“意义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其给与相识不相识之友朋之振奋,实未可计量也”。[41]国民党虽也试图与声望正隆的郭沫若等流行符号攀上关系,但总显得一厢情愿和慢了半拍:“寿郭”第二天(11月17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才在《创作之寿》特稿中盛赞郭沫若的才华;[42]国民党文化工作负责人张道藩受邀出席“寿郭”仪式并第一个签名,过后却感觉滋味不对,深刻体会到共产党在文艺统战方面的用心,多年后仍耿耿于怀,“他(共产党)懂得要捧自己人,最好找敌对的一方负责人领头,才有宣传效果……” [43]
“先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新华日报》的祝寿风潮与文人群体的交往、结群
1930年代初中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军事失利,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地下党在文化大都市上海却成功地依靠被胡乔木称之为“半个党”、“党的外围组织”的“左联”等文人群体,渗透到《申报》等知名商业报刊,“撕破一角,占领一席之地”,[44]构筑起与国民党文化针锋相对的左翼文化。
抗战爆发,重庆迅速成为中国战时政治、文化中心,大批文艺界人士聚集于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统战工作来说,“左联”解体后被打散的文人队伍急需得到重新组织和整合。
茅盾是左翼文化界地位仅次于郭沫若的二号人物,长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国统区的文化工作。早在1930年代,他就和鲁迅并称为《申报·自由谈》的两大台柱子。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0月底,他曾对前“左联”成员胡风谈过这样的想法:“恢复由左翼成员组成的全国性的似组织又非组织的左翼作家网”。[45]后来的现实情况确实是:在抗战的统一旗帜下,重庆文艺界实行着一种双轨制:名义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组织受国民党政府领导,而实际上大部分文人服膺于郭沫若、茅盾等左翼文人的麾下,实现了周恩来“先划一个最大的圈子”的统战思想。正如周恩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文艺思想的领导上,是“上海工作经过全部破坏以后,所保存的唯一阵地”,“现在便发展成为全国文艺的领导力量,国民党在这方面,是瞠乎其后的”。[46]如前所述,托克维尔曾敏锐意识到,结社与报刊的发展紧密相连,“他们必须要找到一种能让他们不用见面就能彼此谈话,不用开会就能得出一致意见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报刊”。国民党政府允许《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公开出版,但不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和发展组织,相当于给予其一定的言论自由,而不给予结社、组织自由。而这本身是存在悖论的,殊不知,言论与结社实为一体两面,报刊的蓬勃发展势必带来结群、结社的实际效果。列宁的“集体的组织者”之说也有殊途同归之意,即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实则密不可分。也正如黄旦教授指出的,报刊不仅仅是静态的文字的载体和容器,它实质上也是一种动态的交往关系。报刊的公开表达、“同时共享”,必然带来结群之效,形成不同的共同体。[47]在这个意义上,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为群体的物质、精神交往所发挥的穿针引线之中介作用,不亚于20世纪初期的《苏报》,“勾连起各方活动和关系,俨然是一个新的神经中枢”。[48]现代报纸的“赋予(身份)地位”(status conferral)功能与中国文人知恩图报、聚合成群的传统心理,在《新华日报》上碰擦出惊人的火花。据说郭沫若在读了周恩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我要说的话”后十分感动,对身边的人坦言:“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句话,这一句也适于表达我和恩来同志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 [49]在《新华日报》存在的九年多时间中,郭沫若先后在该报及其姊妹刊《群众》上发表文章上百篇,而尤以1941年祝寿活动之后为多,这种数量级在报刊史上是极为少见的。郭沫若巨大的威望和影响在1945年2月22日《新华日报》二版头条发表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中得到了一次集中展现。经多方努力,郭氏亲笔起草的《时局进言》争取到312位当时文化教育领域的精英人士[50]联合签名,一致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密密麻麻的名单赫然刊登于报上,引发了“大后方抗战胜利前夜影响最为广泛的政治运动”,[51]以至于蒋介石在震怒之余大骂张道藩无能。[52]祝寿仪式的重复性、可复制性和集体性,发展出一系列符号化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确认其成员的团结。将“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老作家”(老舍语)[53]、背后有亿万读者的张恨水“争取”过来,是党的文艺统战中的又一个可圈可点的案例。同样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44年5月16日包括《新华日报》在内的重庆多家报纸组织为张恨水五十诞辰(暨创作三十年)祝寿并刊文祝贺。尽管张恨水辞谢了所有的现场聚会活动,私下里却难以对各报的贺词与评价视而不见。颇值得玩味的是,多年后他撰写回忆录叙及这次祝寿,独独提到《新华日报》总编辑潘梓年写的《精进不已》对他的“进步立场”的肯定。[54]鉴于1930年代他的作品曾被左翼作家钱杏邨(阿英)等大加挞伐为封建余孽,这就难怪他将潘梓年的评语解读为共产党和左翼方面迟来的认可,从而一解心中块垒。就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的,“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55]张恨水对左翼人士欠下的这份秀才人情,直到一年后受《新华日报》之邀为茅盾五十寿辰撰文才得以偿还,颇有投桃报李之意。事实上,过去从未在共产党的报纸发表文章的张恨水在《新华日报》上为茅盾写了什么并不重要,从贺寿文章内容看,他与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茅盾确实交集不多,但他在《新华日报》上写文章的姿态及默认加入祝寿圈子的象征、符号意义远大于实际内容。透过张恨水的例子亦可窥见,彼时报纸、名人你来我往的互动、勾连效应促使祝寿圈子如层层涟漪般渐趋扩大,左翼文艺圈自1930年代起产生的分化、裂痕到了抗战时期在党的出色“统战”下一定程度得到弥合和修补。这个圈子并无像“左联”这样的一个正式的名目,却在报纸黏合剂的作用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是组织胜似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影子群体,起了比党员直接出来活动更大的象征作用。
结语
20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始终未能在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受共产党影响和渗透的城市左翼文化相比国民党文化占据压倒性优势,这是连国民党都承认的事实。从上海到重庆,从《申报·自由谈》到《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透过新型报纸,征用符合中国文化伦理的传统人际交往素材,举行祝寿等隆重的媒介仪式,引发报上报下交相呼应,热闹非凡,为自身的权力宣展寻找到一个合法的路径,并由此领导、团结着一个“不是组织、胜似组织”,“平时无形、用时有形”的文人群体,为日后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积蓄了力量。国民党败走台湾后曾反思,文化阵地被左派占领是国民党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蒋廷黻1953年在台北所作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曾叹道,“二十年来,国民党掌握到的是军权和政权,共产党握到的是笔权,而结果,是笔权打垮了军权和政权。” [56]重庆《新华日报》的祝寿仪式及其产生的凝聚、共振效应,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已初具依靠象征进行民众动员的意识,对现代报纸功能与技巧的运用达到了相当娴熟的水平。在这里报纸既是纸面内容、意识形态的扩音器,也是纸面之外关系、网络的黏合剂。她勾连了传统与现代、秘密与公开、实体与象征,既制造现实接触,又催生文化性、心理上的反应、认同,对于我们理解党的新闻事业后来的诸多仪式化实践亦不无参考意义。■
①张恨水:《一段旅途回忆——追记在茅盾先生五十寿辰之日》,《新华日报》1945年6月24日
②王若飞:《中国文化界的光荣 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新华日报》1945年6月24日
③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④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⑤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第13页,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⑥甘惜分:《延安〈解放日报〉的遗产》,载罗以澄主编:《新闻与传播评论》2001年卷第2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⑦金达凯:《中共宣传政策与运动》第8页,(香港)近代史研究所1954年版。
⑧《新华日报》在1938年1月11日的发刊词中,丝毫没有表露出共产党机关报的意味,甚至连“本党”“共产党”的字眼都未出现,只提“抗战”,避免了对“共产党”的突显和宣传。
⑨[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第2页,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⑩转引自谢廷秋:《中国当代作家的城市想象与表达》第9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
[11]用齐邦媛的话说,“事实上,他(周恩来)本身独特的吸引力就是最好的宣传,很多人藉由他温文儒雅、充实渊博的风格认识了共产党。”见齐邦媛:《巨流河》第1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12]廖永祥口述、张家钊访问整理:《我与〈新华日报〉》,载谭继和主编:《青史留真 第一辑》第1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3]马识途:《马识途文集·盛世二言》第222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1937-1943.5 18》第320页,中国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
[15]《南方局关于文化运动工作向中央的报告(1942年)》,载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第14页,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16]分别见[法]托克维尔:《托克维尔文集:论美国的民主(下)》第137页,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第214、235页,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6页,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7]廖永祥执笔、重庆市《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四川省《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编:《新华日报史新编》第35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18]中共重庆市江北区委、沙坪坝区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蜀都中学党史资料汇编》第78页,内部发行1987年版
[19]艾芜:《艾芜全集(第14卷)》第369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20]齐邦媛:《巨流河》第1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21]方仲伯:《忆李公朴》,载《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1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22]吴玉英等编:《〈新华日报〉的回忆》第4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3]爱泼斯坦:《爱泼斯坦作品集:人民之战》第122页,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
[24]张伍:《忆父亲张恨水先生》第21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5]转引自钟桂松:《茅盾与张道藩的一段往事》,载褚钰泉主编:《悦读MOOK 第二十八卷》第60页,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
[26]郭沫若:《郭沫若选集 第2卷》第21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7]王鼎钧曾说,“什么报都看,唯有中共办的《新华日报》,我不敢看”。见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 关山夺路》第5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28]分别见熊复:《熊复文集》第三卷第285页,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苍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苍溪文史资料》第5辑第26页,内部发行1992年版
[29]林默涵:《浪花》第50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30][日]前田哲男:《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 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第70页,王希亮译,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31]意思是,虽然很少谋面,但通过报纸神交了很长时间。见《无题恭和香词人韵》,《申报》(上海版)1873年4月25日
[32]转引自凌硕为:《新闻传播与近代小说之转型》第7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第21辑第88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4月
[34]翁植耘编著:《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 忆解放前重庆的文化活动》第21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35]《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1940)》,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二编 政治 5》第1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6]编纂组:《董必武年谱》第4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37]黄旦:《报纸革命:1903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6期
[38]例如上海的民间报纸《文汇报》曾称,“中国唯一的可敬的斗士鲁迅先生死后,有许多人们,都在祈求另一个人来作他们的前导,而郭沫若先生,该是最可希望的一人。”见仲琦:《漫写郭沫若》,《文汇报》1938年2月7日。
[39]1938年,党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内部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见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40]李路曲:《比较政治学解析》第21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41]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24卷第249-25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42]原文是“以澎湃横溢的才气,在文艺理论、小说、诗歌、历史碑铭、甲骨文各方面获得极大的成功,在全世界作家当中,郭沫若先生是个奇迹”。见《创作之寿 郭沫若五十生辰文化界集会庆祝》,《中央日报》1941年11月17日
[43]张道藩口述、赵友培执笔:《文坛先进张道藩》第218页,台北重光文艺出版社1975年版
[44]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回忆录 十六 》,《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8期
[45]胡风:《胡风全集》第36卷第1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4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1937-1943.5 1》第332页,中国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
[47]黄旦:《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往——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学术月刊》2012年11月
[48]黄旦:《报纸革命:1903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第6期
[49]翁植耘编著:《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 忆解放前重庆的文化活动》第38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50]这个名单囊括了大后方文艺界、教育界的绝大多数精英人士,如沈钧儒、邓初民、张申府、茅盾、胡风、柳亚子、沙千里、夏衍、陶行知、曹禺、邵荃麟、老舍、巴金、冰心、顾颉刚、徐悲鸿、白杨、宋云彬、马思聪、陈望道、周谷城、马宗融……。
[51]散木:《1944年重庆〈对时局的进言〉事件》,载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 总第27辑》第60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2]蒋介石骂张道藩,“为什么文化界一些重要人物都被共产党拉了过去”。见廖静文:《徐悲鸿传》第38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
[53]《新编老舍文集》第四卷第113页,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9年版
[54]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24卷 总第69-71辑》第29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
[55]费孝通:《乡土中国》第9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56]转引自古远清:《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第551-552页,武汉出版社年2006年版
伍静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研究团队成员。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申报·自由谈》(黎烈文时期)与左翼文人的交往研究”(项目编号2016BXW00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陈建云教授提出中肯的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