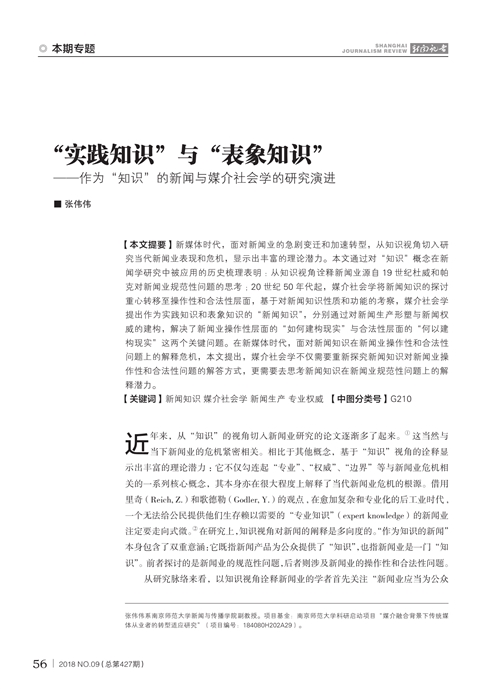“实践知识”与“表象知识”
——作为“知识”的新闻与媒介社会学的研究演进
■张伟伟
【本文提要】新媒体时代,面对新闻业的急剧变迁和加速转型,从知识视角切入研究当代新闻业表现和危机,显示出丰富的理论潜力。本文通过对“知识”概念在新闻学研究中被应用的历史梳理表明:从知识视角诠释新闻业源自19世纪杜威和帕克对新闻业规范性问题的思考;20世纪50年代起,媒介社会学将新闻知识的探讨重心转移至操作性和合法性层面,基于对新闻知识性质和功能的考察,媒介社会学提出作为实践知识和表象知识的“新闻知识”,分别通过对新闻生产形塑与新闻权威的建构,解决了新闻业操作性层面的“如何建构现实”与合法性层面的“何以建构现实”这两个关键问题。在新媒体时代,面对新闻知识在新闻业操作性和合法性问题上的解释危机,本文提出,媒介社会学不仅需要重新探究新闻知识对新闻业操作性和合法性问题的解答方式,更需要去思考新闻知识在新闻业规范性问题上的解释潜力。
【关键词】新闻知识 媒介社会学 新闻生产 专业权威
【中图分类号】G210
近年来,从“知识”的视角切入新闻业研究的论文逐渐多了起来。①这当然与当下新闻业的危机紧密相关。相比于其他概念,基于“知识”视角的诠释显示出丰富的理论潜力:它不仅勾连起“专业”、“权威”、“边界”等与新闻业危机相关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其本身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代新闻业危机的根源。借用里奇(Reich, Z.)和歌德勒(GodlerY.)的观点在愈加复杂和专业化的后工业时代一个无法给公民提供他们生存赖以需要的“专业知识”(expert knowledge)的新闻业注定要走向式微。②在研究上,知识视角对新闻的阐释是多向度的。“作为知识的新闻”本身包含了双重意涵:它既指新闻产品为公众提供了“知识”,也指新闻业是一门“知识”。前者探讨的是新闻业的规范性问题,后者则涉及新闻业的操作性和合法性问题。
从研究脉络来看,以知识视角诠释新闻业的学者首先关注“新闻业应当为公众提供何种知识”这一规范性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杜威筹办《思想新闻》时所提出的“组织化知识”新闻观,以及随后帕克修正杜威时所提出的“熟识知识”新闻观。在杜威和帕克之后,从知识视角探讨新闻业的研究将关注重心从规范性问题转移到操作性和合法性问题上。媒介社会学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这一深受建构主义哲学影响的研究取径,基于对“新闻知识”性质和功能的梳理和分析,对新闻业作为现实建构者的操作方式和合法地位进行了解释。在本文中,研究者将首先介绍“表象知识”和“实践知识”两种作为分析性工具的知识观,并在此基础上梳理杜威和帕克关于新闻知识的前媒介社会学叙述,展示两位学者因不同知识观的影响形成关于新闻业规范性问题的不同看法。随后,研究者梳理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社会学对新闻知识的研究演进,揭示出该取径是如何建构新闻知识作为表象和实践的两种知识属性,与新闻业操作性和合法性问题的关联性。最后,研究者针对新媒体时代新闻业的危机,阐述媒介社会学再次从知识视角来诠释新闻业操作性、合法性乃至规范性问题的意义和潜力。
一、“表象知识”与“实践知识”:分析知识的两种概念工具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以“范式的转换”来阐述人类认识论的发展。③西方社会关于知识的认识,同许多重要而又基础的概念一样,也历经了几种范式的转换。在17世纪启蒙运动以前,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知识观曾分别成为社会中诠释知识的主导范式。伴随着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哲学抬头,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学者为知识概念带来了全新的诠释。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二元主义影响下,理性主义学者提出了一种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即认为世界是由两种存在形态构成,一种是物体(things),一种是思想(thoughts)。前者是观察者观察的对象,后者是观察者对观察对象的理性抽象,而“知识”就是对客观世界,尤其是对客观世界规律的重现。由于理性主义所提出的知识,本质上是以抽象的形式再现客观世界的规律,这种知识被称为表象知识(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④
从属性来看,“表象知识”是人通过大脑的反思产生的知识,是思维和分析的结果,是强意识的、抽象的、可以言明的系统知识,具有普遍意义,不以环境文化等具体地方性要素为转移。表象性知识不是来自具体的情景,不以具体地域和文化的经历为基础,而是来自理性人对世界的客观观察、抽象思维和真实再现。典型的表象知识包括物理公式、数学定理、化学元素表等等。⑤
从认知过程来看,理性主义的表象知识观体现出一种对纯粹客观性的孜孜追求。理性主义对知识的起源、知识的陈述、知识的辩护,以及认识的过程有着严谨客观的规定。在《谈谈方法》中,笛卡尔提出四条著名的认识规则:(1)凡是我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作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晰分明地呈现在我的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2)将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序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善解决;(3)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4)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⑥笛卡尔之后,从斯宾诺沙到莱布尼茨,一批理性主义学者围绕知识所建构的理论化客观化乃至程序化的论述,使其知识观与宗教神学、形而上学的知识观相比,呈现出显著的“科学”特征。这种“科学”特征,以及这种特征折射出的对理性人性的崇尚,十分契合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反教会解放思想的社会心理。因此,“表象知识”一经提出就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学界分析知识的主导性概念工具。其他哲学流派提出的关于知识的种种诠释,要么本身是“表象知识”的派生概念,如多元主义的“集合性知识”;⑦要么在理性主义的压制下难以受到学界的重视,如神秘主义的知识论等。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主义摒弃主观、客观至上的知识论主张,开始遭遇到诸如“休谟问题”、“康德问题”等的挑战和质疑。⑨理性主义在知识客观性问题上的解释困境,促使一些学者转而开始寻求新的哲学范式来建构新的知识观。在一系列挑战理性主义知识观的阐述中,实践主义知识观开始浮现,逐步发展成为与理性主义分庭抗礼、诠释知识的另一主导范式。
实践主义知识观的代表性人物是迈克尔·波兰尼。在1958年出版的《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中,波兰尼提出应当用“个人知识”取代“表象知识”来诠释人类社会的知识。在波兰尼看来,理性主义所提出的“纯粹客观”的知识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个人参与的”,“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必然包含着个人系数”。⑩显然,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观,与理性主义孜孜追求的超越个体、绝对客观、普遍存在的知识观立场争锋相对。波兰尼进一步提出“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概念,作为支持“个人知识”的理据。根据波兰尼的解释,理性主义所提出的表象知识是一种显性知识,而人类知识还包括那些无法言说的“缄默知识”,它是人类非语言智力活动的结晶,“我们所认识的多于我们所能言说的(we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11]应当说,在波兰尼之前,近现代许多哲学家在对知识进行探讨时,曾或多或少地觉察和论述这种内在的、非言述性的知识。例如,美国心理学家威廉姆·詹姆斯曾对知识进行二元分类,提出“熟知知识”的概念。[12]但是直至波兰尼在《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中提出“缄默知识”的概念,人们才真正开始对知识的缄默维度进行直接关注。波兰尼的知识论,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对理性主义知识论种种批判反思的集合。在波兰尼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格式塔心理学、现象学、发生认识论和存在主义等哲学流派的影响。[13]在波兰尼的个体知识观中,“实践”取代理性主义崇尚的“理性”成为获取知识的途径。以波兰尼为代表的实践主义学者指出,理性主义主客二分法的认知模式必须被打破,因为科学家从来都不是在语言、理论或研究中去表征世界,而是干预性地介入世界,“知识”就是在主体动态介入客体的可见过程中涌现出来。[14]波兰尼之后的实践主义学者在“缄默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的概念。[15]从认知过程来看,作为“表象知识”的对立面,“实践知识”是行动者的经验积累,是行动者长期实践的自然沉淀。由于行动者的行动只能在具体场景中发生,因此实践知识是地方性的、在行动者的具体实践中自下而上产生的,而不是如表象知识那样自上而下、由人脑通过抽象思维产生。[16]实践主义学者呼吁摆脱长期秉持的理性思维定势,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探索以地方性、弱意识性、缄默性等为主要特征的“实践知识”,因为这是当代人类社会主导行动逻辑的根本机制。[17]正如“表象知识”提出后因契合彼时崇尚科学的社会心理而受到普遍认可,“实践知识”获得广泛接受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19世纪中期以来,现代西方哲学中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长期受理性主义漠视的直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渐成为哲学家关注的焦点。[18]在此背景下,在认识论层面,带有浓厚非理性主义色彩的“实践知识”,作为对理性主义纯粹客观知识观的修正,很快就发展成为与“表象知识”并置的分析知识的概念性工具。步入21世纪之后,“表象知识”和“实践知识”——这两种由理性主义与实践主义基于不同认识观而建构的知识论范式,在各自不断的更新和发展中,逐渐成为学界诠释知识的一种共识性二元分类。[19]
二、“新闻知识”的前媒介社会学叙述:杜威、帕克与新闻业的规范性问题
追本溯源,杜威、帕克等人1892年筹办《思想新闻》时所提出的新闻观大约是最早对新闻进行的知识化诠释。[20]这两位学者从知识的角度,对新闻的性质和功能进行思考,就新闻业应该为公众提供何种知识这一规范性问题分别给予了两种不同的答案。
在杜威一生漫长而丰富的事业中,筹办《思想新闻》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但在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等传播史研究的学者看来,这段插曲至关重要,它直白地反映了杜威的新闻思想,即将新闻视为“一种组织化知识”,以作“调和或舒缓社会分化之弊的本源手段”。[21]这既是詹姆斯·凯瑞建构“李普曼-杜威之争(Lippmann-Dewey Debate)”的叙事基础,[22]也是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思想起点。[23]《思想新闻》筹办于美国进步时代前夜,报纸是彼时最为兴盛的大众媒体。时任密西根大学哲学系主任的杜威出于对报业现状的不满,在与来自纽约的“流浪记者”富兰克林·福特相遇后,雄心勃勃地提出创办《思想新闻》的宣言。根据杜威的阐述,《思想新闻》提供的是作为“组织化知识”的新闻,它不是“有消息而无思想”,而是与“原理联系起来”,以哲学的洞察和科学般的精准报道事件的发展趋势,成为调节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整合和民主政治的有效手段。[24]很显然,杜威对新闻知识的诠释是以理性主义表象知识为基础。换而言之,杜威认为“新闻知识”也应当如科学知识一样,是一种反映客观世界规律的“表象知识”。
然而,杜威很快就意识到他这一新闻理念过于浪漫和理想,因为“没有方法,也没有时间”,将“社会科学”、“有效的新闻采集”以及“巧妙的文字表达”三者完美地结合,来生产他所希望的作为“组织化知识”的新闻。作为结果,杜威不得不在出版前期,宣布《思想新闻》的夭折。[25]参与筹办《思想新闻》的另一重要人物罗伯特·帕克,当时还只是位刚从大学毕业、在底特律开始记者生涯的边缘角色。虽然,帕克在筹办《思想新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但这段经历,尤其是杜威从知识角度诠释新闻的观点,对帕克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过了近五十年之后,帕克于1940年写下了《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知识社会学里的一个章节》(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一文,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新闻知识观。帕克认为杜威作为“组织化知识”的新闻知识观充满乌托邦色彩。彼时,“实践知识”的概念尚未提出,帕克借用心理学家詹姆斯“熟识知识”(acquaintance knowledge)的概念,提出新闻“不是物理科学那样的系统性知识”,而是仅仅作为一种变动的、短暂的、孤立的事件的“熟识知识”。[26]帕克认为作为“熟识知识”的新闻在内容上虽然很接近杜威批评的“有消息无思想”,但他并不觉得这样的新闻无法完成杜威所期待的民主功能。帕克指出新闻作为“熟识知识”,它的价值在于能够激发读者的复述、对话和讨论,乃至形成民主不可或缺的公共意见:
个体看到新闻的第一个典型反映是向他人复述。复述带来对话,进一步引起评论,甚至带来讨论。……讨论一旦开始,由于人们对事件的理解不同,讨论就不再是新闻,而是新闻所引发的话题。讨论所激发的意见和情感的冲突通常终止于某种共识或集体意见——我们通常称为公共意见。公共意见赖以形成的,就是对当前事件(如新闻)的解读。[27]不难看出,与杜威期待新闻业为公众提供的“组织化知识”与能够反映客观世界规律的“表象知识”不同,帕克寄望新闻业所提供的“熟识知识”是基于社会行动者行为活动的“实践知识”。杜威和帕克各自根据对新闻知识本性的不同理解,为新闻业的规范性问题提供了两种不同答案。不过,杜威和帕克对新闻知识的诉求却是相同的,他们一致认为新闻业应当为公众提供能够促进社会民主的公共知识。应当说,杜威和帕克藉由知识概念诠释的新闻民主观,成为大众媒体时代讨论新闻业规范性问题的思想起点。后来的学者尽管没有再像杜威和帕克那样从知识视角展开对新闻业规范性问题的论述,但在思想上他们延续了杜威和帕克的新闻民主观理念。[28]
三、“新闻知识”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新闻业的操作性和合法性问题
杜威和帕克之后,从知识视角诠释新闻业的研究陷入沉寂。究其原因,或许因为在规范性层面,杜威和帕克从表象知识和实践知识两种知识属性出发所提出的“组织化知识”与“熟识知识”,对“新闻业应当为公众提供何种知识”这一问题的回答已经足够充分。因此直至20世纪50年代,媒介社会学(media sociology)对新闻知识的关注从规范性层面转移至操作性和合法性层面,从知识视角诠释新闻业的研究才开始重新复苏。
作为一种深受建构主义哲学影响的研究取径,媒介社会学起步于大众媒体蓬勃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媒介社会学认为媒介组织所拥有的特定生产逻辑和媒介组织外部各种社会因素构成了新闻的“社会性”,因此应当将新闻生产当作社会过程来考察。在研究维度上,媒介社会学为检视新闻生产的过程及其与社会的勾连提供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维度。其中,政治经济学属于宏观维度,该视角侧重考察传媒组织新闻生产过程与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的关联性。新闻生产社会学(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属于中观维度,这种视角侧重将媒介作为社会组织进行分析,深入研究新闻媒体基本的运作过程。而文化研究属于微观维度,该视角侧重考察文化传统和象征表达系统对新闻行业的渗透和影响。[29]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媒介社会学针对新闻业的操作性问题——“如何建构现实”,以及合法性问题——“何以建构现实”,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对新闻知识的性质和功能进行考察,从知识视角为新闻业的操作性和合法性问题做出解答。与新闻业规范性问题的知识化诠释主要来自杜威和帕克的贡献不同,一批媒介社会学取径的学者投身于新闻业操作性和合法性问题的知识化诠释中。这些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显示知识视角对新闻业问题的解释潜能的同时,也使得媒介社会学当之无愧地成为新闻知识研究的集大成者。
(一)新闻业如何“建构现实”?——新闻室“实践知识”的考察
从时间上来看,媒介社会学是从中观的新闻生产社会学视角展开研究的。“新闻室观察研究”是该取径的研究起点。在媒介社会学之前,学界对“新闻知识”的探讨基本停留在杜威和帕克所关注的规范层面,即媒体应当为公众提供怎样的“新闻知识”,以促进社会民主的发展。而媒介社会学的“新闻室观察研究”则将关注的重心从规范层面转移到了实践层面,该研究主要通过民族志的方法,“对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以及新闻制作过程做出深入的、概念性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描述和分析,并指出新闻内容如何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各种存在因素的影响”。[30]用建构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媒介社会学关注新闻业向公众提供的知识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以盖伊·塔奇曼(1978)、赫伯特·甘斯(1979)、马克·费什曼(1980)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现,“实践知识”在新闻生产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就某种程度而言,媒体及其从业者就是在一整套实践知识规训下开展新闻生产。[31]按照内容的不同,新闻生产可以分解为发现、选择和报道三个阶段。[32]媒介社会学学者提出,无论进行哪一个阶段的工作,新闻工作者必须首先掌握“新闻常规”这一实践知识。[33]所谓“新闻常规”,就是“新闻工作者在工作时采用的一套模式、惯例以及重复的行为或型态”。[34]新闻常规存在的原因是由于媒介组织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运用有限的人力资源去完成新闻的生产,因此需要常规化新闻生产过程以获得控制、提高效率。常规在传媒组织和个人的互动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对于传媒组织来说,常规是一套控制机制,以促使新闻工作者达到组织的预期目标。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常规是他们“工作时所依循的脉络”,他们“在常规中执行任务,也透过常规完成他们的工作”。[35]然而尽管新闻常规如此重要,但作为一种实践知识,它不仅高度情境化和非系统,而且也“难以言说(inarticulate)”。[36]媒介社会学者们指出,新闻工作者很难指望通过公开的学习一蹴而就地掌握常规,而只能通过不断的实践来把握它。例如,马克·费什曼指出,新闻媒体建立“条线系统(beat system)”来收集新闻线索,即预先设定的采访条线(beat),如政府条线、教育条线、医疗条线等,根据采访条线配置相应的跑线记者蹲守,从而捕获第一手线索。但是,不仅不同媒体的条线系统存在差异,媒体内部也会因情境的变化对条线系统进行调整。[37]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跑线记者对某条采访条线知识(如医疗条线上的医学知识)的获得主要依靠长期实践的积累。[38]因此,新闻工作者对条线系统这一实践知识的学习、掌握和运用,完全是一个动态和变化的过程。
“新闻判断(news judgment)”是另一个对新闻内容发挥重要影响的实践知识。经过多年的发展,新闻行业内部已经建构起一套共享的价值观。换言之,新闻判断的标准已经比较固定,如新闻工作者主要依据重要性(importance)、趣味性(interest)、争议性(controversy)、异常性(the unusual)、时效性(timeliness)以及接近性(proximity)这六个要素来进行新闻选择。但是,这一看似固定化的标准,并不能排除新闻工作者的个体价值观。新闻选择仍然深受新闻工作者个体的影响。[39]面对同样的新闻判断标准,不同经历的新闻工作者很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同一个新闻工作者在不同的时期也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作为一种实践知识,“新闻判断”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一种“惯习(habitus)”,它的实现效果取决于新闻工作者的“临场发挥(improvisation)”。[40]事实上,不仅是新闻判断,所有形塑新闻生产的“知识”,都与新闻工作者的实践行为紧密相连,深受新闻工作者具体实践的影响。所以,同一媒体内部的新闻工作者即便接受了相同的关于新闻生产的知识培训,他们的新闻业务表现也可能大相径庭。因为这些指导新闻生产的“知识”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phronesis)”,它是新闻工作者日积月累的经历形成的“新闻直觉(news sense)”,这种“新闻直觉”帮助他们在纷繁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采取行动。[41](二)“建构现实”的新闻业何以合法?——“新闻专业知识”的考察
电视媒体带来了大众传播的发展高潮。电视直播通过媒介事件让人们看到大众媒体制造大规模共识成为可能。[42]作为社会中建构现实最集中的象征力量,大众媒体毫无争议地享有公众的高度信任,以及对公共信息的排他性管辖。[43]大众媒体的强大影响力引发媒介社会学者对新闻业合法性问题的思考。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一批媒介社会学者使用宏观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和微观的文化研究视角来探讨“新闻专业知识(journalistic expertise)”。他们试图在揭示这些专业知识性质的基础上,诠释这些专业知识如何帮助新闻工作者获得在公共生活中与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等同的合法性地位。[44]与“新闻室观察研究”所发现的以新闻常规为代表的实践知识不同,尽管“新闻专业知识”包含实践要素,但从知识属性来看,“新闻专业知识”显然是可以言明、具有普遍性的系统知识。本质上,“新闻专业知识”是媒体管理者、新闻教育者以及政府官员等基于对新闻行业的观察和思考,自上而下为新闻从业者设计的一套表象知识体系。“新闻专业知识”通过学校教育、评奖机制、行业性组织共同体等途径进入新闻工作者的视野,作为他们从业前的必需储备,在帮助他们建立起行业性的壁垒、阻止其他非专业者进入新闻行业的同时,赋予了他们作为现实建构者的合法性地位。[45]在新闻专业知识中,“客观性”毫无疑问处于统领地位。作为一种表象知识,“客观性原则”自20世纪以来逐渐在世界新闻事业中占据主导位置,成为新闻界公认的标准,乃至新闻业的核心特征——很多时候,学者用“客观新闻学”来概括新闻学的本质。[46]基于客观性的重要性,它很自然地成为媒介社会学者最为关注,研究也最为深入的一种新闻专业知识。
媒介社会学学者首先指出,“客观性”从出现直至被新闻工作者奉为圭臬,体现出鲜明的理性选择的意味。根据舒德森的历史考据,19世纪40年代电报技术的出现和美联社的成立直接催生了客观性原则。但是,如同科学领域许多表象知识在被提出之初都不容于时代那样,“客观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新闻界所抛弃。在黄色新闻风行的19世纪,“故事模式”是新闻界的主流报道模式,“讲好故事”比“报道新闻”更重要,因为它更有利于发行。“客观性”于20世纪重回新闻工作者视野,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乃至“信仰”。在舒德森看来,客观性是新闻工作者面对社会批评和不信任的一种理性选择:“新闻从业者之所以如此信奉客观性,一方面是因为想要这样做、必须这样做;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大众深深怀疑和无所适从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一种逃避。” [47]如果接受舒德森的观点,把新闻工作者对客观性的信仰视为他们利益权衡的使然,那么显然这种理性选择给予新闻工作者极大的“利益”。舒德森之后的媒介社会学者将客观性为新闻工作者带来的“利益”论述得更为直白。甘斯、苏梅克和里斯等人均指出,客观性为新闻工作者提供一种自我保护,在截稿时间的压力下,新闻工作者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证明他们所报道的新闻故事是“真相”(truth),而客观性可以让新闻工作者避开新闻报道所隐含的价值观及其带来的其他后果,从而抵御外界的攻击性批评。
然而客观性在新闻领域能够成为世界通行的形而上学的绝对标准,它为新闻业所提供的“利益”远不止于此。哈克特与赵月枝从宏观政治经济学视角对电视媒体客观性报道的考察,揭示出客观性在新闻业合法地享有对公共信息垄断性管辖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一种通过视觉传达信息的媒体,电视比广播和报纸享受到更多由“客观性”带来的裨益。通过摄像机的实景效果,电视营造了一种透明幻象,观众似乎直接看到未经人为操纵的外在世界。这种“目击的真相”让观众形成一种“自然的错觉”,对媒体报道的新闻内容深信不疑,由此产生对新闻业建构“真实世界”的认可与期待。哈克特与赵月枝为此深感忧虑,因为客观性遮蔽了新闻媒体和政治权力之间的亲密关系,它实际上十分有利于政治家介入媒体进而影响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判断。哈克特与赵月枝强调,客观性成为新闻业“一个不会死的上帝(a god who won’t die)”,有着宏观的政经因素影响:新闻业需要客观性来获得建构现实的合法性,而政治家需要作为现实定义者的新闻业来实现意识形态霸权。[48]另一些媒介社会学者从微观的文化视角去勾连“客观性”与新闻工作者职业合法性关系的研究,展示出客观性对构筑和维系新闻边界的重要价值。里斯对客观性内涵的挖掘表明,客观性作为一种表象知识,它在抽象理论层面为新闻业确立了与其他行业相区隔的“特质”。客观性建立在一种理性主义的假设之上,即“事实能够抽离价值或观点独立存在,而新闻工作者能够作为中立的传送者将事实报道给读者”。在实际的执行层面,“客观性”被具化为“准确(accuracy)”、“平衡(balance)”以及“公平(fairness)”等操作手法,这些手法帮助新闻工作者将自身与非专业者区分开来,建构起新闻业的专业边界,捍卫自身对建构现实的合法垄断。[49]里斯的观点在Bishop、Lewis等人随后关于新闻边界的研究中被进一步验证。[50]以客观性为代表的新闻专业知识是可以言明的表象知识。同样采用微观的文化研究视角,泽利泽基于对电视记者话语的分析,揭示出新闻专业知识“可以言明”的表象特征对新闻工作者建构职业话语进而确立职业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在泽利泽看来,新闻专业知识的“可以言明”,是新闻工作者进行职业话语建构的基础,通过特定的叙事和修辞技巧,作为“阐释共同体”的新闻工作者们将自身诠释为公共事件最权威的叙述者,在此之上,他们进一步建构新闻业作为现实定义者的合法性。[51]显然,在泽利泽那里,新闻业的合法性地位是由话语建构出来的。这种非常彻底的建构主义论述,体现出泽利泽对新闻专业知识表象特征的深刻体察、理解与演绎。
(三)小结:表象知识、实践知识与新闻业的三重问题
在大众媒体兴盛的年代,作为“建构现实”的新闻业,它为公众提供了信息、价值和逻辑,这构成了公众的“知识”,极少有公众去质疑新闻业。诞生于斯时代,深受建构主义哲学影响的媒介社会学,从知识视角对“新闻业如何建构现实”以及“新闻业何以建构现实”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围绕新闻生产进行的中观视角的考察显示,在操作性问题上,“建构现实”的新闻业依赖实践知识来实现新闻生产;围绕客观性等新闻专业知识进行的宏观和微观考察则表明,在合法性问题上,新闻业“建构现实”的特权通过表象知识来获得。如果用建构主义的话语进行简单概括,那么就是媒介社会学对新闻知识的研究演进发现,实践知识和表象知识分别通过对新闻生产的形塑和新闻权威的建构,解答了新闻业的操作性和合法性问题。
如果从研究成果来看,媒介社会学从知识视角对新闻业操作性和合法性问题进行诠释的研究,催生出一批经典的新闻学研究著作,如《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做新闻》、《什么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等。与之相比,杜威和帕克关于新闻知识的前媒介社会学叙述似乎显得十分单薄。然而从研究意义来看,杜威和帕克对新闻业规范性问题的知识化诠释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关于新闻知识的前媒介社会学叙述,着力所解决的规范性问题是新闻业的根本问题。凯瑞曾这样论述服务公众之于新闻业的重要性:
目前为止,新闻业是有根基的,它的根基就是公共。目前为止,新闻有一个主顾,这个主顾是公众。[52]因此,正是杜威和帕克运用“表象知识”和“实践知识”两种知识概念分析工具,从“新闻知识”的视角对新闻业、公众和公共生活三者的关系做出解答之后,媒介社会学对新闻业操作性问题和合法性问题的知识化诠释才有价值。“表象知识”和“实践知识”对新闻业规范性问题的解答,既是探讨新闻业操作性问题和合法性问题的前提,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回答新闻业这两个基础性问题的答案。基于此,“知识”与新闻业三重问题的对应关系可以如图1所示。学者关于新闻知识的研究脉络表明,“表象知识”和“实践知识”首先共同对新闻业的规范性问题做出解答。在此基础上,“实践知识”对新闻业的规范性问题、“表象知识”对新闻业的合法性问题再分别做出解答。培根曾言“知识就是力量”。学者关于“新闻知识”的研究,或许可以谓之“知识就是答案”。
四、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知识”危机与媒介社会学的再出发
步入新媒体时代,新闻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带来一批学者对新闻知识的重新关注与反思。在这些学者看来,当前新闻业的危机实质上就是新闻知识的危机。[53]那些在大众媒体时代被媒介社会学诠释为“答案”的“新闻知识”,显然已经难以回答新媒体时代新闻业的操作性和合法性问题。
新媒介技术为新闻业带来了新兴的新闻生产方式。算法新闻、数据新闻、机器新闻写作、沉浸式报道,这些新技术驱动下的新闻生产创新带来了崭新的新闻实践,也亟待提炼和总结新的实践知识来指导这个全新的新闻生产过程。新媒介技术为个人发布提供了平台,曾经作为信息接收者的受众,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信息,他们开始主动参与、创作以及分享,变为公共信息的生产者、批评者和传播者。新闻业面临愈来愈多的竞争者,但表象的专业知识对新闻权威的建构却在不断式微。在当下这样一个后真相时代,曾经作为信仰的客观性也面临让位,因为“客观事实的陈述,往往不如诉诸情感和煽动信仰容易影响民意”。[54]如果说,在大众媒体时代,媒介社会学曾经成功地从宏观的政治经济学、中观的新闻生产社会学和微观的文化研究视角,探究出解答新闻业操作性和合法性问题的“新闻知识”。那么,在新媒体时代,面临危机的新闻业需要媒介社会学再出发,重新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去寻找“新闻业如何建构现实”与“新闻业何以建构现实”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面对新闻生产因技术而不断发生变迁,“新闻室观察研究”如何围绕新兴的新闻实践,提炼出经得起经验证实和逻辑证明的“实践知识”?面对新闻专业权威的衰落和新闻边界的日益模糊,政治经济学研究如何去批判和修正以客观性为代表的既有新闻专业知识?文化研究又如何捕获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专业知识话语建构上的创新?这些都是新媒体时代媒介社会学者研究“新闻知识”的关键问题。
然而,在这些关键问题之外,媒介社会学者或许应当首先思考一种被学界忽视许久的“新闻知识”——“新闻业应该为公众提供何种知识”。“新闻知识”的研究缘自19世纪杜威和帕克对新闻业、公众和公共生活三者关系的思考。在新媒体盛行的21世纪,“作为知识的新闻”显然应当拥有不同于报纸发达的19世纪和电视主导的20世纪的“释义”。那么,当代新闻业应当为公众提供怎样的知识以促进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民主发展?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是解决目前新闻业操作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前提。■
①例如Boyer,D.(2010).Digital expertise in online journalism (and anthropology).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83(1)73-79.;Reich,Z.(2012).Journalism as bipolar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22339-358.
②Reich, Z. & Godler, Y.(2016). The disruption of journalistic expertise. Rethinking Journalism Again: Societal role and public relevance in a digital age(Chris Peters & Marcel Broersma ed.PP.64-80).UK : Routledge
③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
④Jackson, P. T. (2008). Foregrounding ontology: dualismmonism, and IR theo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34(01)129-153.
⑤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⑥笛卡尔:《谈谈方法》第6页,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1版
⑦张东荪:《知识与文化》第1页,岳麓书社2011版
⑧张东荪:《认识论》第4-5页,商务印书馆2011版
⑨PopperK.(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Hutchinson. 石中英.《波兰尼的知识理论及其教育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20卷第2期
⑩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版
[11]石中英:《波兰尼的知识理论及其教育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20卷第2期
[12]ParkE. R.(1940).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45(5)669-686.
[13]李白鹤:《默会维度上认识理想的重建:波兰尼默会认识论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14]NordmannA.(2006). Collapses of distance: Epistemic strateg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science. Danish Yearbook Philosophy, 41(7).; 蔡仲.《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实践唯物论”—〈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评述》,《科学与社会》2013年第1期
[15]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实践知识”和“缄默知识”是可以相互替换的概念。参见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16]Pouliot, V. (2008).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62(02)257-288.
[17]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18]李白鹤:《默会维度上认识理想的重建:波兰尼默会认识论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19]Pouliot, V. (2008).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62(02)257-288.
[20]孙藜:《作为“有机知识”的新闻:杜威和“夭折”的〈思想新闻〉》,《现代传播》2014年第2期;王金礼.《作为知识的新闻:杜威、帕克与“夭折”的〈思想新闻〉》,《学术研究》2015年第3期
[21]孙藜:《作为“有机知识”的新闻:杜威和“夭折”的〈思想新闻〉》,《现代传播》2014年第2期
[22]SchudsonM.(2008). The“Lippmann-Dewey Debate”and the Invention of Walter Lippmann as an Anti-Democrat 1986-1996,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1-20.
[23]王金礼:《作为知识的新闻:杜威、帕克与“夭折”的〈思想新闻〉》,《学术研究》2015年第3期
[24]孙有中:《美国精神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第15-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王金礼:《作为知识的新闻:杜威、帕克与“夭折”的〈思想新闻〉》,《学术研究》2015年第3期
[25]孙藜:《作为“有机知识”的新闻:杜威和“夭折”的〈思想新闻〉》,《现代传播》2014年第2期
[26]ParkE. R.(1940).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45(5)669-686.
[27]ParkE. R.(1940).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45(5)669-686.
[28]例如McCheseny, W. R. (2000). Rich media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New York, NY: New Press.;Baker, E. C. (2002). Mediamarketsand democrac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等
[29]SchudsonM. (1989).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Media Culture Society11(3),263-282.
[30]李立峰:《序[什么在决定新闻]:新闻室观察研究的经典之作》;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1]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Fishman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Gans,J.H.(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32]McManus, J. (1992). Serving the public and serving the market: A conflict of interest?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7(4)196-208.
[33]Tuchman,G. (1977). The exception proves the rule: The study of routine news practice. In P. M. Hirsch, P. V. Miller & F.G. Kline (Ed.)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everly HillsCA: Sage Publications.
[34]Shoemaker, J. P. & ReeseD. (1996).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Publishers USA.
[35]刘蕙苓:《探索广告主导向新闻:置入性行销对电视新闻常规与记者专业性的影响》,政治大学新闻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36]Cohen, D.M.& Bacdayan, P.(1994).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re stored as procedural memory: Evidences from a laboratory study. Organization Science5(4)554–568.
[37]Fishman, 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38]Reich,Z. & Godler, Y.(2016). The disruption of journalistic expertise. In G. Peters. & M. Broersma.(eds.). Rethinking Journalism Again: Societal role and public relevance in a digital age(pp.65-80). New York, NY: Routledge.
[39]Shoemaker, J. P. & ReeseD. (1996).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Publishers USA.
[40]Narsh, C.(2014). Research degree in journalism: What is an exegesis? Pacific Journalism Reviews20(1)76-98.
[41]丁立群:《亚里斯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道德与文明》2012年第5期。Narsh, C.(2014). Research degree in journalism: What is an exegesis? Pacific Journalism Reviews20(1)76-98.
[42]Dayan, D. & Katz, E.(1994).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3]李立峰:《范式订定事件与事件常规化:以YouTube为例分析香港报章与新媒体的关系》,邱林川、陈韬文编:《新媒体事件研究》第161-18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4]AndersonC. (2008). Journalism: Expertiseauthorityand power in democratic life. In D. Hesmondhalgh & J. Toynbee (Eds.)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pp. 248- 64). New York,NY: Routledge.
[45]罗文辉:《新闻人员的专业性:意涵界定与量表建构》,《新闻研究集刊》1995年第2期
[46]郭镇之:《客观新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47]SchudsonM. (1981).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48]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原书Hackett, A.R.& Zhao, Y. (1998).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CA: Garamond Press.)
[49]Reese, S. D. (1990). The news paradigm and the ideology of Objectivity: A socialist at Wall Street Journal.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7390–409.
[50]BishopR. (1999). From behind the walls: Boundary work by news organizations in their coverage of Princess Diana’s deat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23(1)90-112.;Lewis, S.(2012). The tens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ntrol and open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and its boundary.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5(6)836-866.
[51]Zelizer, B. (1992)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the Media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2]Carey, W. J. (1987). The press and public discourse. Center Magazine, 20(2)5.
[53]Reich,Z. & Godler, Y.(2016). The disruption of journalistic expertise. In G. Peters. & M. Broersma.(eds.). Rethinking Journalism Again: Societal role and public relevance in a digital age(pp.65-80). New York, NY: Routledge.
[54]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
张伟伟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项目基金:南京师范大学科研启动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从业者的转型适应研究”(项目编号:184080H202A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