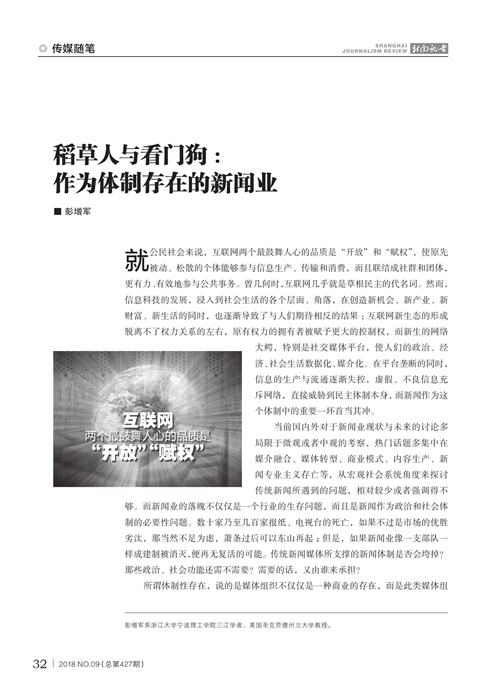稻草人与看门狗:作为体制存在的新闻业
■彭增军
就公民社会来说,互联网两个最鼓舞人心的品质是“开放”和“赋权”,使原先被动、松散的个体能够参与信息生产、传输和消费,而且联结成社群和团体,更有力、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曾几何时,互联网几乎就是草根民主的代名词。然而,信息科技的发展,浸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角落,在创造新机会、新产业、新财富、新生活的同时,也逐渐导致了与人们期待相反的结果:互联网新生态的形成脱离不了权力关系的左右,原有权力的拥有者被赋予更大的控制权,而新生的网络大鳄,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使人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数据化、媒介化。在平台垄断的同时,信息的生产与流通逐渐失控,虚假、不良信息充斥网络,直接威胁到民主体制本身, 而新闻作为这个体制中的重要一环首当其冲。
当前国内外对于新闻业现状与未来的讨论多局限于微观或者中观的考察,热门话题多集中在媒介融合、媒体转型、商业模式、内容生产、新闻专业主义存亡等,从宏观社会系统角度来探讨传统新闻所遇到的问题,相对较少或者强调得不够。而新闻业的落魄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生存问题,而且是新闻作为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必要性问题。数十家乃至几百家报纸、电视台的死亡,如果不过是市场的优胜劣汰,那当然不足为虑,萧条过后可以东山再起;但是,如果新闻业像一支部队一样成建制被消灭,便再无复活的可能。传统新闻媒体所支撑的新闻体制是否会垮掉?那些政治、社会功能还需不需要?需要的话,又由谁来承担?
所谓体制性存在,说的是媒体组织不仅仅是一种商业的存在,而是此类媒体组织的使命和功能,其所作所为,乃是一种制度和体制安排,是社会政治机制的一部分,用英文说,就是journalism as institution。 Institution ,词典里对应的中文词是机构,然而,institution不仅仅是机构,它不但包括实体组织,而且包括实体组织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为社会所认同的一系列价值理念、伦理、行为规范、管理机制等等。体制意味着成规模成建制,体制意味着享受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一系列的体制性特权、优惠和便利,承担议程设置、公共舆论、信息验证、权力监督等道义和社会责任,而不是简单的信息收集和传播。
机构(institution)和组织(organization)不同。机构是为满足社会基本需求而设立或者形成的组织,发挥重要的公共功能,是经常性的存在。所有的机构当然开始都是组织,但只有一小部分组织成为机构。而如果一个机构的重要性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转而成为基本、广泛的必需,就成为体制。人人都可以建立一个组织,但却不能建立一个机构,更谈不上建立一个体制。
当然,体制化同时意味着新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新闻人依托专业组织,从事有报酬的全日制的工作,是一个共同体;新闻人的所作所为是职业组织行为,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业余热情和爱好。
新闻专业主义也并不依赖民主体制才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在专制社会依然还会有非常专业的新闻。但是,民主社会却有赖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而且是体制性存在。
崩塌的体制
那么作为体制的新闻业状况如何呢?有关传统新闻业的不景气已经不用多讲了,一句话,体制性崩塌。
首先从实体来讲,世界范围内,传统媒体几乎天天都在倒闭。就美国来说,在过去20多年里,关张的报纸有600多家,剩下的也大多是苟延残喘。从业人员,过去的15年间减少了将近一半。例如,《洛杉矶时报》从1100多人减少到不到600,《巴尔的摩太阳报》从400人减少到150。印第安那州第二大城市韦恩堡(Fort Wayne)的一家报纸,一年前停出纸版,只留下8个采编人员,最近居然又开掉了7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
体制性崩塌还反映到新闻教育上。目前美国大学新闻学院的招生状况不妙,数量和质量全面下滑,即使选了新闻传播专业的,更多的是学公关、广告和媒体制作,学新闻的学生寥寥无几。
体制崩塌还有其他表现:比如说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与认同度降到历史最低。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公众信任传统媒体的只有32%。而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久前攻击新闻媒体是人民公敌时,竟然有30%多的共和党民众,12%的民主党民众,支持认同特朗普的攻击,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人同意授权给总统来关掉或者制裁“坏”媒体。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大跌眼镜了,要知道美国是一个有着宪法第一修正案,以新闻出版自由为体制之本的国家。
也许有人会说,不是还有几家旗帜性的新闻媒体,比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情况还不错吗?首先,几家有起色的媒体虽然网络付费订户有所上升,但实际上的财务状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如果细分利润的来源,可以发现新闻这个渠道收获并不多;其次,美国的政治体制首先是基于地方和社区自治的,即使联邦政府的选举也是基层的普选,所以更重要的是地方报纸。试问《华尔街日报》会关心到一个小城镇的居民收入吗?《纽约时报》会去报道一个人口不到三万的小城市的市长选举吗?而这些中小城市的报纸几乎所剩无几,出现了所谓的“新闻沙漠”。哈贝马斯说过:公共领域有赖于一个规范化的、自我约束的新闻体系的存在。这些地方媒体的消失,损失的不仅仅是一家报纸和电视台,而是独立、原创的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和公共参与的必要知识。
“维新”与“改良”:体制还是非体制
对于传统新闻体制的塌陷,学界和业界的学者、专家基于立场和认识不同而观点不同。坚持天不变道也不变,过去才是美好的,必须看着报纸才能喝咖啡的,算是“守旧派”,更极端一些的算是“顽固派”,现在基本上已不多见。
激进的,欢呼新媒体的胜利,庶民的胜利,认为传统媒体或者该死,或者虽然不该死,但新桃换旧符,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把这一派笼统地归纳一下,可以称作“维新派”。
“维新派”主张彻底抛开体制,代表人物既包括硅谷新贵,也包括对于旧体制失望的学者。“维新派”大多认同麦克卢汉的理论,相信技术决定一切,也必然会解决一切问题。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查维斯(Jarvis)的言论比较有代表性,他在一篇博客中说:“我希望对新闻单位的老总们说这样的一段话:你们玩砸了!而今做什么都晚了。你们最该做的就是别挡道,让路给那些互联网的原生代,他们才懂得新经济、新社会。他们要重塑新闻,重新开始。”
同激进的“维新派”不同的另一批人认为,虽然随着媒介生态的改变,新闻媒体应该与时俱进,但是新闻媒体的根本使命没有改变。这些人可以姑且叫做“改良派”。
“维新派”观点的主要依据之一是人们虽然不看传统媒体,但并不等于人们不在网络上获取新闻。这个论点听起来有理,但却是个容易误导人的迷思。是的,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由于移动互联的发展,全球范围,每个人平均每天的媒介消费达到了7个半小时,而在发达地区,比如北美,则是10个小时还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所谓的媒介消费并不代表新闻或者信息的消费,甚至都不是内容消费,只是过去一些非媒介行为成了媒介消费,比如社交和购物。消费的质量更是堪忧,许多是无意义的消费,比如有调查表明:59%的链接没有打开就转发了,而真正打开的,55%的人只看了不到15秒。
同这个迷思相关的论点是:新媒体可以取代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而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针对“谁在报道新闻”进行了一项专门研究,具体的方法是挑选美国的一个中型城市——巴尔的摩,跟踪一周内六个重要话题的新闻报道。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新闻是由传统媒体生产的,特别是地方报纸。80%的新闻都是重复或者再包装,而在原创的20%中,95%来自传统媒体。虽然获取信息的渠道看起来非常多,实际上许多博客、网络杂志和在线新闻机构所做的只是洗稿或者炒冷饭而已。
“稻草人”和“看门狗”需要体制豢养
舒德森的名著《为什么民主需要一个不可爱的新闻界》,从规范理论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新闻界的不可或缺。美国学者舒尔在《大局:为什么民主需要卓越的新闻》(The Big Picture: Why Democracy Needs Journalistic Excellence) 中也讲到:“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商业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公共利益两套马车并驾齐驱的时代,前者崇尚的是差别,后者要求的是公平。如果不发生车祸,就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而不应该仅仅讨论商业模式。”普利策在1904年就开始强调新闻的公共服务功能,强调新闻是为了公众,为了社区,不是为了个人。他在捐款给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新闻学院时说:“新闻学院,照我看来,不但不应该是商业的,而且应该是反商业的。”
无论何种媒介环境,新闻传统意义上的三大功能:启蒙大众,监督权力和提供论坛依然是其根本。2009年,美国奈特民主社会信息需求委员会(Knight Commission on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Communities in a Democracy)在一份报告中直截了当地说:“新闻,对于社区的健康犹如纯净的空气,安全的街道,好的学校和公共卫生。”2011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社会需要新闻媒体提供八类至关重要的信息,包括紧急状况及险情,医疗卫生,教育, 环境, 公共事务以及官员和候选人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至关重要但平淡枯燥,商业价值不大。而这些信息需要系统地、经常地提供,不可偏废,不可时有时无。对于权力和利益集团,则需要全天候的监控,而这些都要求新闻体制性地存在。比方说,医院不应当是商业组织,而应该是机构和体制,如果医院是商业组织,那医院的宗旨就成了赚钱而不是救死扶伤。作为体制存在,消防队、警察局无所事事才是理想状态。同理,新闻业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尤其它的警示监督功能,即一般所说的“稻草人”和“看门狗”,存在的本身就是意义。“稻草人”效应,顾名思义是新闻媒体的存在本身即有警示威慑作用;“看门狗”更进一步,就是一旦有事,会真的去嗅、去挖、去咬。这些需要强大的组织力量, 而非个人力所能及。
“新闻沙漠”的后果
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民主真的需要一个新闻界,比如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帕布肯(Popkin)就对所谓新闻在政治中的作用不以为然,认为所谓新闻的作用更多的是新闻界自我神圣化,即使真的需要,从历史上看新闻媒体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正如“维新派”所坚持的,即使传统的报纸电视消亡了,也完全用不着担心,因为新媒体、社交媒体完全可以取而代之。
真的如此吗?我们不妨搁置一下争论,来看看活生生的现实。
美国南加州洛杉矶近郊有一座小城,名叫贝尔(Bell),人口不到4万,人均年收入不到3万美元,六分之一人口在贫困线以下。
上世纪90年代末,贝尔小城聘请了一位市政经理(city manager),这个所谓的市政经理是由市政委员会聘请来管理城市事务的专业人士,也可以说是这个城市的CEO,因为选举出来的市长和市政委员会并不一定懂城市管理。开始的年薪7万多美元,这已经不低了,美国平均家庭年收入也就三四万。
贝尔原有一家报纸叫《贝尔实业邮报》,创刊于1924年,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互联网的冲击,难以为继。这家小报倒了几次手,在市新领导班子上任不久便倒闭了。
随后的十多年里,市政府的一干人马,为自己开出了天价的薪水。经理的固定年薪从7万升至80万,加上各种福利,年收入超过150万,美国总统的年薪也不过40万美元,而小城警察局长的年薪达到了40多万,是洛杉矶这个600万人口的警察局长的两倍。2010年,《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偶然得到爆料:贝尔小城的市政经理拿着全美最高的城市经理年薪,前去调查,贪腐的盖子终于被揭开,结果,包括市长在内的7位市领导被控侵吞公款,最高的判了12年。而《洛杉矶时报》由此获得了2010年度的普利策公共服务奖。
虽然我们不能说当地报纸的倒闭导致了贪腐行为的发生,至少可以说新闻的沙漠给这帮蛀虫提供了便利和侥幸,竟然能持续十多年而安然无恙。要说起来,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是没有听到一些议论,据称有好事、胆大者前去问询,结果被当权者弄了份假工资单搪塞过去。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地的报纸还活着呢?这家报纸的一位前记者说得好:“这正是为什么城市需要一个报纸做市民的看家狗,这是脸书发个牢骚贴或者写一个马后炮的博客万难胜任的。”人人都是记者又怎么样?当时贝尔市政府的网页不是非常及时地发布会议议程和会议纪要吗?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上了一天班,还要带孩子,忙家务,谁会有空有兴趣去关注政府的网站发布了什么?即使看了数据报表,又如何去验证真实性、准确性?即使是记者,也需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才能够破译官僚们有意来欺骗人民的数据和报表。
而类似贝尔这样的小城镇在美国有几百几千个,失去了当地的报纸,成了新闻的沙漠,这是人人即使24小时抱着手机刷屏都弥补不了的。
在加州旧金山硅谷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小城叫东帕里阿尔托(East Palo Alto),往南不到5英里就是谷歌总部,距离苹果总部也就不到13英里,毗邻的还有脸书总部、惠普总部,还紧挨着硅谷的神经中枢斯坦福大学。然而,这样一个3万多人的城市,由于没有自己的新闻媒体,也难逃新闻沙漠的命运,别说日常事务,就是市长选举,也不见一个字的新闻报道。
数字时代,社会被逐步媒介化,照理更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专业的体制性的新闻机构来提供公共服务,而实际上,新闻业正在遭遇体制性崩塌。当然,这不等于说报纸不能死掉,但是,全社会都应该充分认识到新闻业作为体制性存在的重要性,避免新闻的碎片化和沙漠化。正如舒德森在刚刚出版的《为什么民主依然需要一个不可爱的新闻界》中再次强调的那样:新闻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体制性的质疑机构,是民主得以存在的基石。■
彭增军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