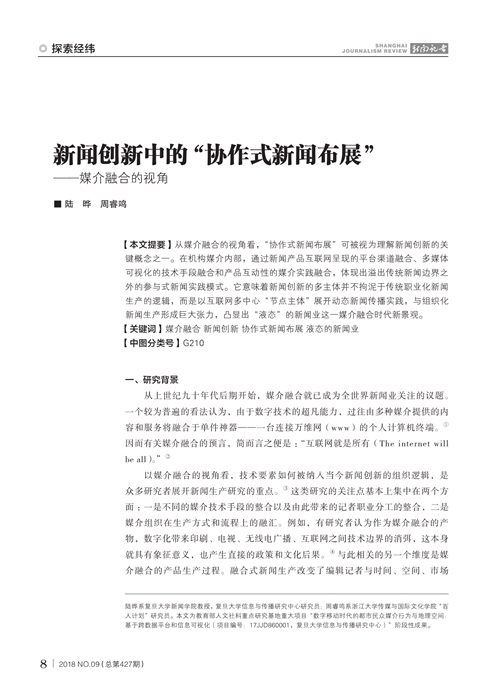新闻创新中的“协作式新闻布展”
——媒介融合的视角
■陆晔 周睿鸣
【本文提要】从媒介融合的视角看,“协作式新闻布展”可被视为理解新闻创新的关键概念之一。在机构媒介内部,通过新闻产品互联网呈现的平台渠道融合、多媒体可视化的技术手段融合和产品互动性的媒介实践融合,体现出溢出传统新闻边界之外的参与式新闻实践模式。它意味着新闻创新的多主体并不拘泥于传统职业化新闻生产的逻辑,而是以互联网多中心“节点主体” 展开动态新闻传播实践,与组织化新闻生产形成巨大张力,凸显出“液态”的新闻业这一媒介融合时代新景观。
【关键词】媒介融合 新闻创新 协作式新闻布展 液态的新闻业
【中图分类号】G210
一、研究背景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媒介融合就已成为全世界新闻业关注的议题。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由于数字技术的超凡能力,过往由多种媒介提供的内容和服务将融合于单件神器——一台连接万维网(www)的个人计算机终端。①因而有关媒介融合的预言,简而言之便是:“互联网就是所有(The internet will be all)。” ②
以媒介融合的视角看,技术要素如何被纳入当今新闻创新的组织逻辑,是众多研究者展开新闻生产研究的重点。③这类研究的关注点基本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的媒介技术手段的整合以及由此带来的记者职业分工的整合,二是媒介组织在生产方式和流程上的融汇。例如,有研究者认为作为媒介融合的产物,数字化带来印刷、电视、无线电广播、互联网之间技术边界的消弭,这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也产生直接的政策和文化后果。④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维度是媒介融合的产品生产过程。融合式新闻生产改变了编辑记者与时间、空间、市场压力这些传统的新闻生产相关要素的关系:在1970年代的美国,全国电视联播网每天一次晚间新闻节目,大多数的报纸,包括日报和晚报,在每天凌晨或下午出报,因此编辑部每天的工作常规都是以24小时为单位来处理突发新闻;数字时代的24小时电视新闻频道和互联网新闻网站消弭了新闻常规周期的传统时间边界,取而代之的是飘忽不定的“新闻旋风”;而且,新闻内容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与新传播技术的特质甚至多媒体公司的组织架构发生了关联——也就是说,一家媒介机构会为多个新闻平台生产更具弹性的新闻产品,新闻编辑部越来越变成集电视/视频演播室、互联网制作设施、广播/音频设备、图形工作站以及上百台电脑终端于一体的技术空间——有研究者将此称为“新”新闻编辑部(New Newsroom),⑤而且,产出的产品被笼统地划归为“内容”这个可以涵盖任何故事、影像或其他类别的知识产权类型,而不再是社会公共生活中具有特殊文化含义的“新闻”。⑥这类研究一直延续至今。
传统上,新闻从业者往往认为新闻采编这一编辑部主导的内容生产活动是以职业新闻人为核心的,⑦持这种看法者在当今信息与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革命的浪潮中依然不在少数。研究发现,新闻从业者对技术,尤其对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普遍持积极态度,⑧但往往将技术作为新的工具整合到新闻编辑部原有的工作流程当中。尽管新技术的采纳推动了新闻编辑部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原有的组织文化和内容生产逻辑,从如何接近消息来源到如何吸引受众,都依然在按部就班地发挥作用,即便是那些创新程度较高的媒介组织内部也是如此。⑨研究者的焦点也往往落在数字时代如何提高新闻生产的效率和生产力;数字技术普遍介入的新闻生产图景当中新闻从业者如何成为更灵活的生产者,以便一次性满足多种媒介需要;编辑记者如何重新学习新技能以适应跨媒介平台的技术要求;如何维护技术变革时代新闻业的职业声誉,⑩不一而足。
然而,以这样的思路讨论新闻创新(journalistic innovation),只是停留在媒介融合的最表层。且不说传媒行业在外部与其他传统行业的融合如电视、电信、互联网的三重融合,就像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天空卫视在英国和美国提供的视频观看、语音通话、宽带服务,已对消费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1]即便单单局限在媒介组织内部,与快速变幻的融合实践相比,这类将技术融合视为工具的阐释也是远远不够的。就像Boczkowski和Ferris从1994年开始在欧洲一家媒介公司进行的长达十年的田野研究所显示的,媒介融合并不简单地如通常认为的那样导致产品同质化,相反,这家公司的数字内容从生产环节的边缘逐步变成带动整个生产过程运作的轴心,与原有的印刷和广播内容生产逐渐整合成一个生产系统。但这样的生产系统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它还同时推动了传统内容和数字内容产品的进一步细分,因此在技术密集的当代媒介环境中开发新的概念资源,以期深入理解技术融合和跨界实践的新动态就显得极为重要。[12]
二、协作式新闻布展:理解新闻创新的关键概念之一
所谓新闻创新(journalistic innovation),特指“发生在新闻领域的,由新闻实践的主体采纳、实行和扩散新观念的行为,包括由一连串这样的行为构成的过程”。[13]鉴于新闻业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于新闻创新的界定,不仅关涉在新闻生产和报道形式上采用的新路径,也关涉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对新闻报道的高品质和新闻业高道德标准的承诺。[14]在实践领域,新闻创新包含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两个层面,其核心是关乎“什么是新闻”、“如何报道新闻”等一系列职业价值观的认知拓展,甚至是全新理念的产生和践行。[15]因此,新闻创新可以理解为新技术条件下的新闻业重构——既是从行业层面对新闻生产过程、新闻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盈利模式等的调适,也是从新闻体裁、叙事风格/模式层面对新闻故事讲述技巧的调整。[16]新闻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它是新闻实践中的创新,也是社会创新的形态之一,体现出媒介与社会网络中相互依存的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变化。[17]关于新闻创新的主体,有研究者认为应包括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或曰公众)两方,因为他们都生成新闻内容,其创新实践至少有赖于以下四个维度:(1)创造、分发、呈现高质量新闻内容,(2)让公众参与到一个互动的新闻话语当中,(3)采纳针对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优化的新方法进行新闻报道,(4)面向数字移动环境开发新的管理和组织策略。[18]也有学者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思路:除了由在媒介组织中工作的人——职业记者、技术人员、商业营销人员,有时也包括虽来自媒介组织之外但按照组织逻辑整合进来的社会力量如“公民记者”——构成的行动者(actors),和传统意义上的受众(audiences)——也即公众,他们多种多样、活跃于不同的平台、经由不同的技术整合,虽处于媒介制作与发行的接收端,也通过创造和生成内容贡献于媒介(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他们早已超越了依旧按传统媒介思路命名的“公民记者”,已然成为新闻生成的重要主体[19]),还引入了第三个新闻创新的主体:行动元(actants,这一中译来自符号语言学研究领域),它包括“所有非人类的技术”(all nonhuman technologies),如算法、应用程序、网络、界面或接口、内容管理系统和其他介入媒体工作的物质对象,这些技术可能在媒介机构内部或外部发挥作用,有时也会跨越机构的界限。[20]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sm)、算法、开源软件运动、机器人写稿、虚拟现实VR等技术驱动的新闻实践,以及这类实践对全社会有关新闻乃至知识生产的认识论的影响和改变,也倍受关注。[21]事实核查(Fact-checking)则被看成是在新技术和社交媒体推动的商业竞争压力下,在公众和社会政治系统关系不断改变的现实中,人们寻求新闻真相的创新行为,以及这一新闻创新背后有关新闻规范性的传统价值立场。[22]这些讨论可视为全世界职业媒体机构共同面临“新闻业危机”[23]的应对,其中一些预设似乎仍暗含组织化新闻生产目标和逻辑的天然合理性。然而,越来越多的新闻传播实践行为和基于这些实践行为的经验研究,展示出新闻传播的现实情境对组织化新闻生产一整套规范性理念和实践策略的偏离、挑战、溢出甚至背道而驰。组织化新闻生产控制逻辑转移和生产过程透明化[24]只是表象,新技术更深远的影响和新闻传播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组织化新闻生产规范之外——互联网用户对新闻的发现、分享、评论,使得新闻不再是刊出(publish),而是公开(publicize),这样的“协作式新闻布展(或译作策展) (collaborative news curation)” [25],意味着新闻创新的多主体并不拘泥于传统职业化新闻生产的逻辑,而是以互联网多中心“节点主体”[26]展开动态新闻传播实践,与组织化新闻生产形成巨大张力,凸显出“液态”的新闻业[27]这一媒介融合时代新景观。
如果将协作式新闻布展视为以技术驱动的媒介融合在当下产生的新的新闻传播实践,有两种理解路径。其一是沿用出自会展行业的“布展”或“策展”,它强调通过对展品陈列的设计、编排、主题架构来达成对单个展品内涵价值的超越,这更接近互联网新闻生成的规范性理解。最初在新闻领域,布展被用来强调新闻的专业筛选和视觉化呈现,着眼记者编辑对不同新闻来源信息进行的阅读、选择、排除、组织和集中呈现;近期有研究者将这一概念用作描摹职业新闻从业者在自媒体时代的众说纷纭中成为澄清事实、论证说理的主持者,都是这种规范性理解的表现。[28]其二是从会展行业的理解扩展到eScience领域,布展意指通过数据创造者、提供者、存档者、消费者共同参与的标注、评价、选择、转换数据的行为,令数据增值、广泛共享和再利用,这更接近互联网新闻生成的液态现实,尤其是当下中国移动互联网新闻实践活动的液态现实。倘若在这个意义上吸纳digital curation包含的特质,布展可概括节点主体在新闻生成各环节的即时互动,与“把关”不同,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参与式新闻实践模式,一个意义生产与再生产动态交织的模式。2018年5月3日,人物杂志微信公众号《奥数天才坠落之后》发布后,报道的主人公随即在知乎贴出了自己的回应《奥数天才坠落之后——在脚踏实地处》对稿件提出质疑并被多个公众号转发,之后又有多个公众号对这一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个人公众号“霍老爷”(ddz_223)5月7日的推送《奥数天才坠落:我从不相信任何一个中国记者》,这些文章都有大量观点多元的评论,多个文本连同众多评论不断叠加甚至相互质疑、冲突,构成新闻内容的多个面向,也体现出这一新闻生成的复杂路径,正是媒介融合背景下协作式新闻布展的典型特征。
三、协作式新闻布展的媒介融合实践:几个相关融媒体产品案例
基于作者对上海几家主流媒体的长期观察,本研究以相关案例进行协作式新闻布展的媒介融合实践讨论。作者进行调研和参与式观察的媒体包括:
2014年1月上线的《解放日报》新媒体产品上观新闻(http://www.shobserver.com/home);
创办于2014年7月、被认为是国内第一个直接切入移动互联网的媒体整体融合转型产品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2016年7月上线的上海广播电视台SMG融媒体中心核心产品看看新闻(http://www.kankanews.com),和2016年底《人民日报》首批推出的中央厨房17个融媒体工作室之一的大江东工作室。
其中上观新闻、澎湃、看看新闻都以Web网页、移动客户端、社交媒体作为新闻发布平台,呈现方式包括文字、图片、影像;上观有图文直播和视频直播频道,看看新闻以传统电视之所长开设24小时直播流“上海这一刻”、“魔都眼”(图1-1 图1-1见本期第12页);上观和澎湃都有互动板块“互动”和“问吧”(图2-1、图2-2 图2-1、图2-2见本期第12页),看看新闻则专设“报料”频道(图1-2 图1-2见本期第12页),而且,为方便用户在社交平台分享内容,看看新闻设置了视频的一键截屏和默认静音模式;大江东的内容则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的不同平台上发布。
此外,作者于2017年5月、8月、11月和2018年2月,在相关资深媒体人当中展开了多次焦点小组和深度访谈。此后,在本文修改过程中,作者继续在阿基米德、今日头条、快手、新浪微博、腾讯新闻、新华网未来实验室展开调研,以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媒介融合的理解。所有调研和访谈资料均以直接引语在本文中呈现,篇幅所限不再逐一单独标注。
1.产品实例一:新闻产品的互联网呈现——平台渠道融合
在上述几家主流新闻机构的媒介融合实践中,最基础、最表层的融合方式是平台渠道的融合,这类融合目前主要体现在新闻编辑部将自己的产品根据不同需要在多个平台渠道上发布,以期抵达更多用户。
以看看新闻为例,2017年点击量最高的新闻,在其自己的客户端KNews上,全网数据排名前三的是一条时政新闻和两条社会新闻,分别为:8月30日14:50《王毅回应印度撤军:希望印度充分吸取教训 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4月29日10:16《台情侣困喜马拉雅47天1死 曾约定谁先死就吃其肉活下去》、5月21日20:17《华人小女孩坐码头边亲近海狮 忽然被咬住裙子拖下水》,点击量分别是422万、395万和350万。而看看新闻通过重新剪辑发布在视频创作分享APP秒拍上的内容,点击量前三名都是社会新闻:《相识25年,梅西终于给了她一个完美“世纪婚礼”》、《老白的警犬养老院:全年无休,7年花费上百万》、《14年博弈后上海“最牛钉子户”终搬离,解开心结迎接新生活》,点击量分别是2567万、2489万和2080万。因平台不同而产生如此巨大的点击量之间的差距,对传统电视时代“酒香不怕巷子深”和互联网发展初期“内容为王”的行业信心,不能不说是某种冲击。
平台渠道的融合也意味着新闻产品可能“自发”通过互联网节点形成爆发式、多点对多点的网状传播。2017年上海两会期间,上观依托融媒体工作室搭建起一个项目制的临时性跨部门平台,由政情、财经频道、视觉和编辑中心不同部门采编人员合作,制作短视频《上海24小时:你和这座城市的每一刻》,在3分半的时长里,结合视频和数据,呈现凌晨到深夜24小时不同场景、不同人群,讲述新时代的上海故事、上海精神。5月7日发布,经由包括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视频网站、社交媒体多渠道转载和转发,累积、叠加产生社会影响(图4 图4见本期第13页)。
当然,平台渠道的融合还体现在媒介机构通过集纳其他平台渠道的内容来增加自己新闻产品的丰富性。上观2018年3月26日发布短视频《外婆包的青团还是那个味道,你知道步骤是怎样的吗?》,方言旁白配字幕,是非常适合清明节的应景之作。这段点击量近万的视频并非上观原创,而是出自“艺美乡村”一个由上海市建设用地和土地整理事务中心2016年1月创建微信公众号、2017年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注册的品牌。该视频2018年3月22日首发,阅读量不到3000、点赞数不到50。但上观并非直接转载艺美乡村,而是转自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实名认证的政务平台上海发布。这条3月23日被上海发布转发并加盖水印的视频,在其拥有超过600万粉丝的上海发布秒拍平台上,观看总量近100万次(图5 图5见本期第13页)。这其中同样包含平台与内容影响力关系的全新暗示。
尽管不同渠道、不同新闻产品形态内容之间很难直接类比,但这些实例显示,那些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的点击量,其巨大差异提示我们,不同平台渠道的特质本身对新闻产品内容形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多个平台渠道触达用户的路径和效果也不尽相同。上述这些过往新闻生产议题之外的考量,作为多方向、多维度、多节点相互推动的协作式新闻布展的一种常态,已对当下的融合新闻生产,产生了直接和直观的影响。
2.产品实例二:多媒体可视化产品——技术手段融合
在融合新闻的讨论中,对技术手段融合的关注由来已久,文字、声音、图像的融合已成常态。当下,技术手段的融合主要以多媒体可视化新闻产品的形态呈现。以澎湃为例,目前澎湃约600名员工,其中采编团队约400人,技术团队约200人。作为国内唯一一家由报纸全员转型而来的互联网新闻机构,澎湃自诩是融合转型的先行者,强调以全媒体为核心的新闻生产流程再造,所谓“每一个编辑记者都要具备全媒体生产能力、每一个内容产品都要考虑全媒体呈现方式”,除了文字,视频音频(和直播)、动画、H5、VR等可视化表达都有所涉猎,尤其综合绘画、摄影、视频、音频、文字开发多媒体连环画的可视化H5新闻产品,已日趋成熟。2016年9月15日,福建宁德市庄里村村支书周炳耀因在台风中保护村民生命财产而牺牲,年仅45岁,牺牲这天正是中秋节。按照中宣部部署,澎湃制作H5《致敬|好人耀仔:一位宁德村支书的45岁人生》(图6 图6见本期第14页),宣传周炳耀先进事迹,10月17日上线,48小时点击量达280万,总点击量高达2000万,除高点击量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外,这一H5作品还获得了2017年世界新闻视觉设计协会(Society for News Design,简称SND)优秀设计奖。
2018年澎湃又获SND两个优秀设计奖,其一是动画类优秀奖《字源奇说|水墨创意动画〈鸟〉,几个字带来的却是万千伤害》,其二是交互图表类优秀奖《68年风雨录:台风来去之间》。《字源奇说|水墨创意动画〈鸟〉》(图7 图7见本期第15页)2017年3月31日上线,是澎湃为4月1日“国际爱鸟日”的专门创作,主创团队包括创意、绘画、建模、动画渲染、合成、调色等多个技术工种;2017年7月28日台风“纳沙”和“海棠”在24小时内先后登陆福建福清,两者登陆时间和空间距离如此短,历史罕见。澎湃在7月31日上线《68年风雨录》(图8 图8见本期第15页),用交互网页展现1949至2016年中国台风的相关数据,封面动态交互根据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资料中心的数据集(tcdata.typhoon.gov.cn),使用mapbox的API绘制地图,用p5.js将台风坐标点采用Web Mercator投影方式映射到地图上,气象局的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每6小时记录一个点,包含该位置的经纬度、台风强度、气压、风速等数据,经过筛选后直观展示出68年来台风的路径和数量,随后展示了近年来因为带来巨大灾害而被除名的台风案例,以及68年间不同省份被热带气旋和超强台风袭击的次数等等,数据分析师和平面设计师是其中重要的团队成员。由此可见,以多媒体可视化为核心的技术手段融合,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技术团队、创意团队在新闻编辑部的重要性,而且,高度技术性的影像表达进一步凸显了新闻从业者作为一种类似巴西哲学家威廉·弗卢塞尔探讨摄影师和摄影机关系时所讨论的特殊角色,即人置身在装置中、与之密切联系,人在其中既非常量也非变量,而是人和装置融为一体,[29]这样一种展开协作式新闻布展的复杂角色。
3.产品实例三:互动产品——媒介实践融合
在机构媒介的融媒体产品中,还有一类互动产品,这类产品从内容和形态上都溢出了传统新闻的边界。它们往往跟新闻热点或新闻事件相关,但呈现为互动游戏,具有强烈的社交化娱乐属性。
就像《人民日报》客户端为八一建军节开发的H5产品《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7月29日晚推出,截至8月2日17时,“军装照”H5的浏览次数累计达8.2亿,独立访客累计1.27亿,一分钟访问人数峰值高达41万。“做新闻的终于把自己做成了新闻”,[30] “还不仅仅是传播,更包括参与、互动,从小孩一直到老人,从海内到海外,这说明主流媒体、机构媒体今天和社会大众、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和纽带,比五年前要紧密得多”。
与《人民日报》“军装照”类似,2017年4月19日,上观新闻在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结束之际,推出互动H5《测一测你是〈人民的名义〉中的谁》,总浏览量超过600万;2017年10月上观为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制作的互动H5《解放日报·上马英雄榜》,整合了1996年至2017年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的全部参赛者成绩,参赛者只要输入姓名和参赛年份,不仅能查询成绩,更可上传一张自己的马拉松参赛照片,生成带《解放日报》报头的个人专属解放日报头版报道(图9 图9见本期第16页),并一键分享微信朋友圈。这个获得10万+点击量的H5互动产品,用户IP显示来自40多个国家。
看看新闻2017新年推出互动H5“跳一跳”小游戏《遇见2017》;2017年9月为配合洋山港四期建设全球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全自动化码头的宣传推出的互动H5“抓娃娃”游戏《来,和世界冠军比赛“抓娃娃”》;201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推出的互动H5智力问答游戏《两会必答题》,点击量分别是15万、39万、7.5万。
这些溢出传统新闻边界的互动产品,体现出公众媒介实践形态的融合。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在于,多位资深新闻从业者在调研中提到,当下在新闻活动中“社交性、互动性成为用户的第一需求”。例如,互联网音频平台阿基米德将自身定位为“一个能够提供服务的社交音频平台”,“传统广播电台的节目,通过阿基米德分发到微博、微信,分发到哔哩哔哩、蜻蜓等其他平台”,社交性被认为是体现“移动互联网+广播”这一全新传播模式特征的重要属性。正如媒介文化学者亨利·詹金斯所言:媒介融合不只是技术的变迁,“融合改变了现有的技术、产业、市场、内容风格以及受众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融合改变了媒体业的运营以及媒体消费者对待新闻和娱乐的逻辑”——不仅跨媒介跨行业,融合也“发生在同一设备、同一行业、同一公司、消费者头脑中”。[31]
四、讨论:协作式新闻布展的移动社交性成为媒介融合的核心
上述文献梳理和案例分析,展示了媒介融合视角下新闻创新实践带来的种种变化,以及协作式新闻布展在其中的特征和意义。新闻相关的社会场景正在发生巨变,移动社交则是这一巨变的风暴中心。正如一些欧美媒介学者提供的实证研究结论显示的那样,“新的移动界面不仅改变了我们如何筛选和访问新闻,也改变了我们如何进行沟通和塑造社交空间”,[32] “社交媒体意味着人们花费大量时间来观察(监视)其他人在做什么,人们共享情绪、注意力,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媒介产品的社交元素,而不是内容本身”,[33]因此“适应新媒体平台需要的不仅仅是重新利用现有媒体产品”。[34]在我们走访的多位资深新闻从业者看来,“与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相关的传统新闻概念,包括社会共识、分化与凝聚、阶层之间的理解或信息互通等因素,正在消散”,“融合新闻颠覆了过往传统媒介的结构化新闻及其仪式化场景,什么零碎、随意的内容都可以成为新闻”。在公众一方,“用户不在乎媒体生产的是否是纯粹的新闻产品(即遵守传统的新闻专业流程、有专业壁垒的新闻),用户需要的是娱乐、信息、态度及理解”;在机构媒介一方,“新闻处理方法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变得很高。从某条新闻被披露到其传播路径,都具有极高的偶然性,有些爆款新闻(即使内容会被认为很糟糕)似乎没有规律可言,无法复制”。
面对这一巨变,与新闻内容生成、传递相关的新兴互联网企业,均表现出强烈的技术驱动取向。在调研中,今日头条和快手都反复强调自身的定位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快手用户的增长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和WiFi流量变得便宜直接相关,快手用户跟人口分布大致接近,用户最多的地方是北上广深,北京2000万人口,每天有300万人打开快手。快手简单、平等、普惠的理念是建立在人工智能基础上的。”“字节跳动公司除主产品今日头条之外,还有抖音、西瓜视频、火山视频、悟空问答、激萌、抖音海外版Tik Tok等,在移动社交领域占有不同的市场,目的都是以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开发回馈社会。如头条寻人以地图位置精准推送寻人信息,截至2018年7月已帮助6000多家庭找到失散的亲人;神经网络模型在反谣言上的应用也取得良好进展。”可以说,正是这些技术创新,激发了各类极具移动互联网特征的新型节点式融合传播,构造了协作式新闻布展的社会场景。
事实上,协作式新闻布展的“内外无别”已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融合新闻生产的常态。以非虚构写作著称的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不仅着眼于互联网平台的融合叙事,而且通过谷雨计划与传统媒体机构和高校合作、签约工作室(如非虚构写作工作室故事硬核、可视化工作室数可视等)、签约作者(如纪录片导演范俭),“连接外部生态”,以期通过其“公共性、专业性、实验性,成为中国最好的公共媒体”。阿基米德团队认为,“今天讨论内容的传播速度,跟分享有极大的关系。分享就会涉及标题,会涉及内容的关联,也会涉及针对不同人群的呈现”,因此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必须建立在技术能力基础上,“阿基米德共83个人,技术团队超过40人,没有任何外包,一个是音视频的处理能力,目前主攻对音频的自动解构,包括自动标签、自动分类、自动摘要、自动拆分短音频等等;再就是数据处理能力和后台开发能力”,其关注焦点在于,移动互联网时代“人和社群已经不再是独立的生活的点,每个人身处其中同时连接人和物,我们可以成为连接城市的重要节点吗?”新华网融媒体未来研究院认为,当今“媒体的优势是广泛连接的优势”,籍此,基于“重新连接”的协作式新闻布展,理应成为理解媒介融合的关键概念。
由此可见,协作式新闻布展提示我们,随着技术的变革,公众渐次作为显在的社会力量参与新闻实践;职业控制与开放参与之间虽蕴含张力,但新闻从业者与公众的理性协作无疑会活跃、拓展、丰富我们的公共生活。从技术和组织的维度看,这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业变迁的普遍趋势。但就中国经验而言,我们发现,当媒介融合与社会转型相交织,协作式新闻布展这一参照系在实践中展现出了某种复杂性。
中国缺乏社会制度环境的一致性。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各路社会力量间构筑的权力关系不断调整,至今仍然变动不居。这种未曾停歇的调整既为社会制度建设制造了多面的想象空间,让当代人在绵延千年的社会-历史传统和近现代不断革命的巨大投影之下闪转腾挪、累积改革的宝贵增量,又将社会制度建设带入某种未曾预料的复杂局面。就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传媒改革而言,权力、资本、职业三者之间并未形成某种相互拱卫的结构(或出现稳定不可逆的趋势)。国家能力的提升、社会-历史传统的召唤,以及这种召唤之下对资本的臣服与合谋,使得职业力量被有效规训,话语空间被日益挤压。随着媒介融合进入新闻场域的不只是技术,还有个体意识萌发而尚欠反思自觉的公众。他们的价值观不再定于一尊,却难以时时秉持理性、科学、自主、协商的精神,就关键公共议题取得“最大公约数”、达成共识。他们时而从权力和资本的合围中醒来,时而不自知地重陷于消费主义、民粹主义等数字洪流之中。多重亚文化的盛行既是他们实现自我意义生产、彰显公民主体性的信号,又是他们娱乐至死、戏谑其间的标志。面对技术渗透其间的数字网络场景,以及这一场景中权力、资本、职业、公众不断博弈的新型权力关系,新闻创新必然要在制度环境变迁中产生某些特定的在地后果。
新闻创新镶嵌于中国社会转型之中。媒介融合不是自外于中国传媒改革的全新叙事,而是处在中国传媒改革的延长线上。两者指向同一主题:新闻实践就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权力关系调适。换句话说,新闻创新仍是探索中国社会制度建设的一环。同过去一样,新闻实践主体必须在推拉创新活动的社会力量之间往复游走。有所不同的是,在不断重构的制度环境中,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使得后者的逻辑不再局限于权力、资本、职业统摄的封闭场域,而是被导入到节点互联的网络之中。所谓新闻创新特定的在地后果便是,权力关系的调适溢出了尚未坚实的新闻场域,跨越了新闻业仍待固化的职业边界。数字网络空间中,新闻实践主体由新闻机构泛化为任何栖身网络节点的组织与个人,尚未成型的新闻从业者职业共同体日益消散。“液态”的新闻业在此形成,社会也出现了液态特征。
可以看到,新闻创新的在地后果是数字化、网络化传播技术变革前后两种调适逻辑的张力。对新闻从业者来说,以技术工具继续促进权力、资本、职业三重力量的调适,推动新闻实践走向专业,回归新闻本位,这是媒介融合的题中之意。然而,在一个不稳定的制度环境中,技术不单是工具,不单是促进新闻业自我改造的强大动能,它还是塑造社会景观、重构传播模式、颠覆权力关系的场景性诱因。循着中国传媒改革的惯性,依赖“上下合作”、“临场发挥”等策略及其组成的某套“转型”策略开展的媒介融合,将不可避免地同正在形成的网络-液态社会逻辑相冲撞。因此,我们需要把媒介融合和新闻创新置于正在浮现的新型社会逻辑和权力关系中思考,才能更好地回答当前一些似是而非容易引发误解的问题。
无论如何,围绕协作式新闻布展而展开的媒介融合不仅是新闻创新的迭代性实践,更是一种全新的力量,它正在重新界定有关“什么是新闻”的社会共识,重塑新闻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并推动作为全社会文明健康的公共生活重要基础的新闻文化的进一步拓展。[35]■
①BoczkowskiP. J. & Ferris, J. A. (2005). Multiple MediaConvergent Processesand Divergent Products: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n Digital Media Production at a European Firm.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597: 32-47.
②OwenB. (1999). The Internet challenge to television.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 16.
③MitchelsteinE. & Boczkowski. P. J. (2009). Between Tradition and Change: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on Online News Production. Journalism, 10 (5): 562–586. DomingoD. & Paterson, C. (eds.)(2011). Making Online News: Newsroom Ethnographies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Internet Journalism (2nd ed). New York: Peter Lang. Steensen, S. (2011). Online Journalism and the Promises of New Technology: A Critical Review and Look Ahead. Journalism Studies12 (3): 311–327. Singer, J. B.DomingoD.Heinonen, A.HermidaA.PaulussenS.Quandt, T.ReichZ. & Vujnovic. B. (2011).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Guarding Open Gates at Online Newspapers.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④BoczkowskiP. J. & Ferris, J. A. (2005). Multiple MediaConvergent Processesand Divergent Products: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n Digital Media Production at a European Firm.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597: 32-47.
⑤KlinenbergE. (2005). Convergence: News Production in a Digital Ag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97: 48-64. ?
⑥Auletta, K. (2003). Backstory: Inside the Business of News. Penguin Press HC.
⑦AndersonC. W. (2013). Towards a Sociology of Computational and Algorithmic Journalism. New Media & Society15 (7): 1005–1021.
⑧Arceneaux, N. & WeissA. (2010). Seems stupid until you try it: press coverage of Twitter2006–9. New Media & Society12(8): 1262–1279.
⑨English, P. (2016). Twitter’s diffusion in sports journalism: Role models, laggards and followers of the social media innovation. New Media & Society18(3): 484–501.
⑩KlinenbergE. (2005). Convergence: News Production in a Digital Ag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97: 48-64.
[11]ThanassoulisJ. (2011). Is Multimedia Convergence to be Welcomed?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59(2): 225-253
[12]BoczkowskiP. J. & Ferris, J. A. (2005). Multiple MediaConvergent Processesand Divergent Products: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n Digital Media Production at a European Firm.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597: 32-47.
[13]王辰瑶:《新闻创新:不确定的救赎》,《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5日
[14]PavlikJ. V. (2013). Innovation and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1(2): 181-193.
[15]Quinn, S. (2005). Convergence’s fundamental question. Journalism Studies6(1): 29-38. GynnildA. (2014). Journalism innovation leads to innovation journalism: The impact of computational exploration on changing mindsets. Journalism, 15(6): 713–730. Boczkowski, P. J. (2016). Digitizing the News: Innovations in Online Newspaper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白红义:《从技术创新到新闻创新:重塑新闻业的探索性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16]周睿鸣:《“转型”:新闻创新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对〈澎湃新闻〉的案例研究》,2017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7]WestlundO. & and LewisS. C. (2014). Agents of Media Innovations: Actors, Actantsand Audiences. 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1(2): 10-35. BrunsA. (2014). Media InnovationsUser InnovationsSocietal Innovations. 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1(1): 13-27.
[18]PavlikJ. V. (2013). Innovation and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1(2): 181-193.
[19]谢静:《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4期
[20]WestlundO. & and LewisS. C. (2014). Agents of Media Innovations: Actors, Actantsand Audiences. 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1(2): 10-35. LewisS. C. & Westlund, O. (2015). Actors, ActantsAudiencesand Activities in Cross-Media News Work. Digital Journalism, 3(1): 19-37.
[21]CoddingtonM. (2015) Clarifying Journalism’s Quantitative Turn. Digital Journalism, 3(3): 331-348.
[22]GravesL.NyhanB. & ReiflerJ. (2016). Understanding Innovations in Journalistic Practice: A Field Experiment Examining Motivations for Fact-Check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6: 102–138.
[23]LuengoM. (2014). Constructing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15(5): 576-585. AlexanderJ. C. (2015).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Cultural power.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8(1): 9-31. ZelizerB. (2015). Terms of choice: Uncertaintyjournalism, and cri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5: 888-908.
[24]Deuze, M. (2005). What i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 Journalism, 6(4)442-464. Singer, J. B. (2007). Contested Autonomy: Professional and popular claims on journalistic norms. Journalism Studies8(1): 79-95.
[25]Bruns, A.(2001). GatekeepingGatewatching, Real-Time Feedback: New Challenges for Journalism. Brazilian Journalism Research, 7(11): 117-136. 陆晔、周睿鸣:《新闻生产转向“策展”模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7日
[26]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2015年第12期
[27]陆晔、周睿鸣:《“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7期
[28]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
[29]威廉·弗卢塞尔:《摄影哲学的思考》,毛卫东、丁君君译,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7年版
[30]人民网评:《爆款“军装照”,举国同怀军队情结》,取自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803/c1003-29448362.html。
[31]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32]BowdK. (2016). Social media and news media: Building new publics or fragmenting audiences??In GriffithsM & BarbourK. (Ed.) Making PublicsMaking Places. University of Adelaide Press.
[33]Schroeder, R. (2018). Media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 UCL Press. ?
[34]WolfC. & SchnauberA. (2015). News Consumption in the Mobile Era. Digital Journalism, 3(5): 759-776.
[35]Carlson, M. & UsherN. (2016). News Startups as Agents of Innovation. Digital Journalism, 4(5): 563-581.
陆晔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周睿鸣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移动时代的都市民众媒介行为与地理空间:基于跨数据平台和信息可视化(项目编号:17JJD860001,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