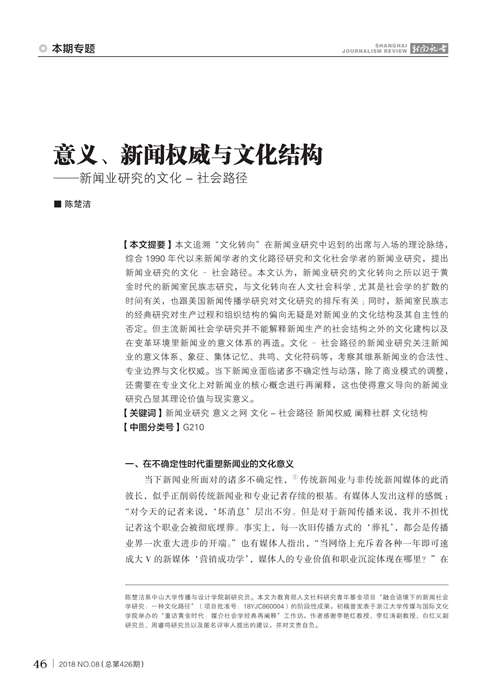意义、新闻权威与文化结构
——新闻业研究的文化-社会路径
■陈楚洁
【本文提要】本文追溯“文化转向”在新闻业研究中迟到的出席与入场的理论脉络,综合1990年代以来新闻学者的文化路径研究和文化社会学者的新闻业研究,提出新闻业研究的文化–社会路径。本文认为,新闻业研究的文化转向之所以迟于黄金时代的新闻室民族志研究,与文化转向在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扩散的时间有关,也跟美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对文化研究的排斥有关;同时,新闻室民族志的经典研究对生产过程和组织结构的偏向无疑是对新闻业的文化结构及其自主性的否定。但主流新闻社会学研究并不能解释新闻生产的社会结构之外的文化建构以及在变革环境里新闻业的意义体系的再造。文化–社会路径的新闻业研究关注新闻业的意义体系、象征、集体记忆、共鸣、文化符码等,考察其维系新闻业的合法性、专业边界与文化权威。当下新闻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与动荡,除了商业模式的调整,还需要在专业文化上对新闻业的核心概念进行再阐释,这也使得意义导向的新闻业研究凸显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闻业研究 意义之网 文化-社会路径 新闻权威 阐释社群 文化结构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在不确定性时代重塑新闻业的文化意义
当下新闻业所面对的诸多不确定性,①传统新闻业与非传统新闻媒体的此消彼长,似乎正削弱传统新闻业和专业记者存续的根基。有媒体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对今天的记者来说,‘坏消息’层出不穷。但是对于新闻传播来说,我并不担忧记者这个职业会被彻底埋葬。事实上,每一次旧传播方式的‘葬礼’,都会是传播业界一次重大进步的开端。”也有媒体人指出,“当网络上充斥着各种一年即可速成大V的新媒体‘营销成功学’,媒体人的专业价值和职业沉淀体现在哪里?”在新旧杂糅的不确定性时代里,新闻业与记者正面临重塑自身合法性与文化权威的挑战,而如何应对众多的不确定性,基本上围绕着退场、呼吁和忠诚等表现。②潘忠党指出,在当下的“新闻危机”话语中,“最直接侵害新闻业的很可能是新闻界(包括学界和业界)自己对其行业的犬儒式解构,因为它不是建构式的反思,而是新闻界的自暴自弃;它不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下进一步阐述理念、规范和追求,而是消解新闻业在社会运作中应有和可能有的公信力;它不是阐述新闻业如何作为一个重要主体参与并引导社会协调对话,而是以无奈为由放弃这一社会责任”。③可以说,今天的媒体从业者,正面临着职业意义混沌的时期。当新闻专业主义被批判和嘲讽,当严肃新闻业抵不过信息搬运工和“10万+”的社交媒体鸡汤,记者和其他内容生产者参与新闻业的意义是什么?当新闻业的存在令人感到忧虑,新闻权威受到非新闻业的质疑和挑战,新闻业的文化体系又如何能够重新树立自己的合法性?媒体社会学研究中的组织分析与政治经济分析似乎并未告诉我们如何去应对这些文化意义上的困惑。
1989年,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曾将有关新闻社会学的研究概括为三种路径,即社会组织路径、政治经济学路径、文化路径或人类学路径。④如他所说,新闻社会学领域的主流和经典文献,主要出自新闻的社会组织研究路径;而文化路径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流派。在舒德森的评述中,文化路径的分析受到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影响,提出记者、新闻机构及其互动关联方处于一个既定的象征体系内,而新闻正是他们在这一象征体系内互动的结果。⑤如果说社会–组织视角的研究将新闻的建构视为人际关系的产物,那么,文化视角的分析则聚焦新闻生产中“事实”与符号(symbols)的关系,强调文化传统和象征体系对新闻生产的约束,而不管经济组织的结构或职业常规的特征为何。舒德森还指出,记者在新闻工作中不仅仅是为了跟新闻线索和同行维持或修复关系,也是为了维护他们在受众眼中的文化形象。⑥如果说舒德森的这一总结是专门针对新闻社会学研究,那么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早在1975年已提出“传播学的文化路径”(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的主张。⑦当凯瑞提出这一主张时,新闻社会学研究的“黄金时代”正打开帷幕,但却并未在兴盛于1970–1980年代的媒介社会学的黄金时代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可以说,文化路径的新闻社会学研究,在这个“黄金时代”中缺席了。迟至1990年代初,以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基于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报道总统之躯:肯尼迪刺杀案,传媒与集体记忆的塑造》⑧的出版为标志,一种文化视角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才得以系统性地出场。这从丹尼尔·伯克维茨(Daniel Berkowitz)在1997年主编了《新闻的社会意义》,⑨而后于2010年再主编《新闻的文化意义》⑩亦可见一斑。这背后的社会语境与知识脉络是什么?文化路径的新闻业研究,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意识的转向?有哪些学者代表了这一路径的研究方向?在一个新闻业急剧变化的时代,提倡文化路径的新闻业研究有什么意义?本文将从这些问题出发,探究新闻业研究的文化路径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及其表现,并联系新闻业的现状作进一步的讨论。
写作本文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在当下传媒业面临急剧不确定性的时代语境下,占据主流的理论和实践强调了新闻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驱动下的“量化转向”(quantitative turn),[11]或者强调商业模式重构、技术中心主义,认为技术将裹挟整个新闻业的发展前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重构新闻业商业模式,掌握先进传播技术,就能够解决新闻业面临的困境?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要返璞归真,追寻新闻业、记者存在的意义以及其如何重塑意义的非技术性的问题?其二,既有的新闻社会学研究的谱系,其主体为组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相应地,文化社会学路径的分析处于非主流。新近出版的两本反思新闻业经典研究的著作Remaking the News [12]和Rethinking Journalism Again [13],在对媒介社会学经典研究的反思与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闻业研究的新问题与新视角,但他们都主要聚焦在技术、物质、经济因素,对文化的因素依然少人问津。加深对文化社会学路径的新闻生产研究,应当能够丰富我们对处于流动状态下的新闻业的理解。
二、“文化转向”在新闻社会学中的迟到与入场
(一)“文化转向”及其对社会学的影响
“文化转向”这一概念、现象首先来自西方史学中的新文化史研究。新文化史从符号学、象征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吸收了相关的理论预设、核心概念与方法路径,注重探究符号、仪式、文化的意义,寻求对存在(being)而不是成为(becoming)的理解,提供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具体语境下人类行为的状态。新文化史研究“所注重的是生活于此时此地特殊环境之中的人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将研究聚焦于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世界,用叙事史学的方式展开深描,将读者带入一个个不同的微观世界”。[14]为了区别以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史,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作为主编将198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文化史会议上报告的论文合集成《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一书出版,首次将这种史学流派统称为“新文化史”,“文化转向”也被正式命名。[15]而影响史学研究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的重要思想家,不能不提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16](Clifford Geertz)。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影响,吉尔茨也认为人是悬挂于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webs of significance)上的动物,而“意义之网”不断生产着人的行为风格,也就是说,人与其所处的文化相互形构。韦伯认为,与自然科学家不同的是,社会学家们研究的不是无生之物,而是要分析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activity)。人类的活动产生社会关系,而这些活动还受到一种不见于自然现象的性质即意义(meaning)的影响,研究人类社会活动的意义,意味着要进入具体的社会脉络去阐释人们如何证明社会活动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以及人们诉诸何种价值、期望或理想作为行动的动机。总而言之,一种社会关系或活动,是各种不同的意义之组合。[17]吉尔茨提出,文化是内在于人的意义体系,人类学家所从事的民族志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18]在《文化的阐释》一书中,吉尔茨这样定义文化:“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内嵌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19]吉尔茨对文化的定义,对阐释路径的提倡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革新,对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20]与吉尔茨同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新文化史学家罗伯特·丹东(Robert Darnton)就指出,新文化史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关注符号、象征体系、仪式等议题,是受到了吉尔茨所提倡的学术思想的影响。[21]在新文化史家看来,文化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因素,文化既不是社会或经济的产物,也不是脱离社会诸因素而独立发展,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22]在新文化史之后,西方社会学研究也于1980年代末开启了文化转向并于1990年代形成潮流。社会学的文化转向除了受到“文化转向”的推动,还源于社会学者们对社会学鼻祖之一——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晚期思想——关于意识、信仰体系、仪式、象征、团结等进行了再挖掘。[23]1972年,斯蒂芬·卢克(Steven Luke)发表了关于涂尔干的全景式传记——《爱弥尔·涂尔干:他的生活与著作》(Emile Durkheim: His Life and Work)之后,涂尔干系的学者们对这位社会学大师的生平和思想的转变有了全局性的新理解。1982年,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在《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二卷)》中展示了涂尔干晚期作品中对宗教生活的新取态的转向(亦即文化转向),指出涂尔干对社会科学的理论遗产可以从根本上被重构;1988年,亚历山大编辑的《涂尔干社会学:文化研究》出版。总之,进入1980年代,社会科学家们认识到涂尔干学术思想中的文化转向的潮流开始形成,到了1990年代则加速汇聚,诸如意识、象征主义、再现、道德、团结等概念开始与关于话语、差异、结构和意义的讨论如影相随。[24]总而言之,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可以归为两大类别:文化作为对象(culture as object)和文化作为路径(culture as approach)。前者是将文化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一种研究范围、内容的扩展;而后者则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从政治经济学、组织分析、结构分析转向话语、仪式、象征元素的分析,所关注的就是意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25]在这里,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后者。
(二)“传播学的文化路径”以及文化研究与新闻业研究的背离
如上所述,美国社会学领域真正开启“文化转向”的繁荣景象要到1990年代,已然晚于新闻社会学研究的“黄金时代”,而象征人类学、符号学、语言学的发展也并未触及新闻社会学研究。尽管1970–1980年代的新闻社会学被概括为“新闻室民族志”,[26]但研究者们并未真正将民族志中吉尔茨式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理念以及附诸其中的文化意义渗入对新闻生产的研究。在英美两国经典的新闻社会学著作中,例如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Deciding What’s News(1978),盖耶·塔克曼(Gaye Tuchman)的Making News(1978),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的Putting Reality Together(1978),文化路径的分析都难觅踪影。可以说,对社会结构、组织常规、资源分配、社会控制的聚焦遮蔽了新闻业的文化面向。民族志只是媒介社会学者们获取新闻生产经验数据的一种方法,不是内嵌于研究中的理论思维。
不过,在1973年,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研究转向已确认了吉尔茨的阐释路径对他的深刻影响。随着《文化的阐释》在这一年的出版,凯瑞的研究项目产生了鲜明的文化转向。在翌年,凯瑞拟就了数篇学术随笔(essays),[27]构成了“作为文化的传播”这一理念的核心,使“传播学的文化路径”这一主张呼之欲出,而这种文化路径无疑是将吉尔茨式的人类学范式移植到传播学研究中。[28]在1960年代的美国知识界,对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社会科学主流的反抗主要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阐释主义的影响。左派学者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而政治上温和的学者则走向了由吉尔茨引领的阐释主义路径研究。[29]凯瑞借此提出传播学的文化路径主张,也是出于对主导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实证主义范式的不满。[30]凯瑞认为,在主流的传播学研究中,文化主要是被当作一种环境或一种背景,而不是作为一种关键的、活生生的活动场所。[31]不过,不同于英国伯明翰学派基于阶级文化问题而将文化研究当作一种参与社会的政治工程(political project),[32]凯瑞所提出的美国式的“文化路径”这一术语是出于命名上的方便,并且所借用的思想资源是美国实用主义和芝加哥社会学派。[33]凯瑞本人不中意“文化科学”这一当时对应于自然科学的名词,所以就将诸多学科中区别于实证主义的研究都归入“文化路径”名下,如“乔伊·古斯菲尔德、杰·詹森、欧文·戈夫曼、托马斯·库恩,符号互动论和芝加哥社会学派,肯尼斯·伯克、勒斯莉·菲尔德以及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小群体,还有马歇尔·麦克卢汉、哈罗德·因尼斯,再加上那些愿意与反对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而汇聚成群的马克思主义学者”。[34]凯瑞的主张对新闻业研究的重要影响在于他提醒应将新闻当作一种文化形式,也就是视为一种意义制造的实践,那么,新闻业的历史就不仅仅是制度或技术、经济安排的历史,而是更为丰富与多元。[35]尽管如此,传播学的文化路径研究仍然只是传播学主旋律中的一声异响,在他的学生和他所在的伊利诺伊大学之外,凯瑞的影响都是有限的。[36]同时,发生于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各种社会运动冲击着由白人中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新闻业的权威。然而,社会上的批评并没有改变新闻业的主流报道的结构与价值观,新闻业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记者的社会角色也没有产生相应的改变。[37]一方面,这是新闻业的价值观的持久性所致;另一方面,新闻社会学研究也没有深入地从文化意义的重塑层面去理解新闻业面临的变迁。而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是民族志所提倡的阐释路径关注的是人的行动的主观意义以及驱动行动的意义体系的自主性,这与组织研究关注结构对记者能动性的限制无疑是存在矛盾的。于是,对媒体组织结构限制性的聚焦也就忽略了支撑新闻业和记者职业行为的文化意义的关注。
1988年,凯瑞编辑出版了《媒体、神话与叙事:电视与新闻》(Media, Mythsand Narratives: Television and the Press)一书,提出“要严肃地对待文化”。该书作者囊括了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迈克尔·舒德森、罗杰·希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还有文化人类学家伊丽莎白·伯德(Elizabeth Bird)等,他们从文化视角考察了电视的文化意义、媒体仪式、新闻业的文化边界、记者的新闻权威等议题。[38]尽管如此,文化路径的研究在媒体社会学中依然并不活跃。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认为,新闻业的文化分析在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中之所以难成大器,是由于很少有学者愿意自我认同为“文化研究学者”,[39]从而使得这一学派难以在美国主流新闻传播学界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英美文化研究学者也从早期对新闻生产的关注逐渐转移到对通俗文化、另类文化、亚文化等关系霸权、身份认同、文化抵抗的文化现象的分析,新闻业仅仅成为文化研究的背景或论证的素材;同时,构成新闻业研究核心的事实、真相与现实等概念,在文化研究学者那里只是被当作社会主导阶级塑造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从而使文化研究的批判性与新闻业研究的核心格格不入。[40]对文化研究学者来说,将文化研究置于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学科体系之内只会压缩文化研究的多元化空间、跨学科性以及批判性,最终使文化研究过度妥协地用传播学的学科形象来重塑自身,导致文化研究淹没于传播学的模式之下,使其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种替代性范式而非一种严肃的挑战。[41]最终,发端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与新闻业研究愈走愈远。
(三)文化共鸣与集体记忆研究的介入
不过,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交接期,随着西方新社会运动(如环保运动、反核抗争等)的频发,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社会抗争中的文化因素,[42]也考察大众媒体与新社会运动的互动中的“框架共鸣”(frame resonance)等议题。[43]文化视角也开始被吸纳进入媒体社会学的分析之中。比如,舒德森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文化要素在媒体生产、媒体与公众互动中产生影响,则媒体产品或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产品需要满足以下情形:可索引性(retrievability)、修辞力量(rhetorical force)、共鸣(resonance)、制度存续能力(institutional retention)和鼓励决心(resolution)。[44]舒德森指出的共鸣因素也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呼应。威廉姆·甘姆森(William Gamson)和安德烈·莫迪利亚尼(Andre Modigliani)对媒体话语的建构主义分析指出,媒体话语具有其自身的文化逻辑,而不是被动地反映公众舆论,同时,媒体通过提供一套阐释话语包或框架使公众能够挪用去建构其对公共事务的理解,公众不再是被动的,媒体也不是对公众情感毫无感知。[45]詹姆斯·艾特玛(James Ettema)的研究也指出,新闻对社会特别事件的报道所采取的框架,并非都依赖于组织常规的社会建构,而是往往诉诸与读者间的文化共鸣(cultural resonance),既凸显事件的重要性,也使事件报道具有仪式和神话色彩,使读者接受记者的叙事是真实可靠且重要的。[46]而1998年时,詹姆斯·艾特玛和西奥多·格拉瑟(Theodore Glasser)对美国调查记者的研究就采纳了吉尔茨式的民族志“深描”方法,以移情的视角尽可能地从受访记者的角度来呈现他们从事调查报道的故事以及其中蕴含的意指结构(structures of signification)。他们关注的是作为一个群体的调查记者,而不是以新闻编辑室为中心的组织分析。通过深度访谈,他们集中考察调查记者在客观性与道德卷入之间的悖论(paradox)及其化解之路,指出调查报道记者在揭露社会问题时所采用的各种叙事策略(如客观化、再现、核查、合理化)往往赋予了报道文本以道德意义,从而将调查报道看作一种道德话语的手艺(craft as moral discourse)。[47]这些阐释性研究,无疑都提供了不同于新闻社会学经典的视野和洞见。
文化视角进入媒介社会学的另一种方式,是研究媒体与集体记忆的互动。在这方面,芭比·泽利泽对肯尼迪刺杀案与美国新闻界所建构的集体记忆的分析[48]和舒德森对水门事件的集体记忆的研究[49]堪称代表。泽利泽并不仅仅看新闻生产的结构限制、组织常规、信源关系,而是考察新闻记者如何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再阐释和集体记忆的塑造来建立其文化权威。新闻业的集体记忆为记者社群生产了关于他们所报道的历史事件的共享知识和信仰,而塑造集体记忆的方式也构成了建立新闻权威的一部分。关于新闻业的集体记忆研究往往都与新闻权威密切相关,不管是对典范型的新闻偶像的纪念还是对有影响力的媒体机构的纪念,都在通过新闻业的历史来重塑新闻业的当下形象,这在专业特征分析和组织分析中是难以顾及的层面。
三、文化路径的新闻业研究:从社会建构到文化意义
兴盛于1970-1980年代的新闻社会学经典,总体上聚焦的是新闻生产中的社会结构、组织常规与记者相对弱势的能动性。尽管新闻社会学经典关注了记者的价值观,但记者参与新闻工作的意义赋予维度则未被考察。进入1990年代之后,从文化视角来考察新闻业,至少有来自新闻学研究和文化社会学研究两个领域的学者日渐形成丰富的文献。下文将分别就两个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和关键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形成一个整合的理论框架。
(一)新闻业的文化分析:阐释社群、新闻权威与文化建构
系统性地提出从文化视角分析新闻业的代表当推新闻学者芭比·泽利泽,其研究可以概括为记者的阐释社群与文化权威研究。泽利泽将新闻业的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定义为“通过文化的棱镜来策略性地和明确地审视新闻业的连接基础(articulated foundations)和新闻实践,而在其他学科视野下,它们会被视为理所应当(而遭到忽视)”。[50]文化在这里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它指的是一种促使群体成员从合乎惯例的角度去理解事情,并以合乎共识的方式付诸行动的现象。其二,新闻本身被理解为文化现象,并与卷入新闻生产的个人和群体所认可的文化息息相关。它没有把视角落在新闻组织上,而是落在记者身上,从他们的视角去考察作为阐释社群的一员的意义,以及记者如何再现身份认同等问题。[51]泽利泽之所以使用文化分析这一名词,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区别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可以看出,新闻业的文化分析并不与文化研究重叠,尽管二者有部分共享的议题和旨趣。泽利泽指出,透过文化视角去研究新闻业,源自多种学术理念的推动,包括文化社会学、哲学的建构主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符号转向、语言学中的民族志转向、文化史、美国实用主义、涂尔干理论中的象征团结、文化批评以及英美文化研究等等。[52]她将文化路径的新闻业研究追溯到以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为代表的芝加哥社会学思想,指出帕克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开展的关于新闻的研究中,就提出了将记者视为一个集体知识生产者的群体成员的观点,而新闻也具有文化同化、塑造认同的力量。[53]与泽利泽异曲同工的是,文化社会学者罗纳多·雅各布斯(Ronald Jacobs)也认为,文化路径的媒体研究应当追寻芝加哥社会学尤其是帕克的理论传统,如关注新闻的文学形式与小说的文化结构之间的互动与互文性,以及新闻业与时代的文化需求的互相呼应。而繁荣于1970年代的新闻室民族志研究,在雅各布斯看来,则对媒体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不感兴趣,聚焦点放在了新闻工作者和试图影响新闻框架的推销者(promoter)上,[54]从而窄化了媒体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与发展的前景。
如果说凯瑞提倡“传播学的文化路径”是出于对实证主义主流范式的不满,那么泽利泽提出,新闻业的文化分析则是在制度分析和组织分析主导下的新闻社会学之外寻求补充。她认为,纠结于新闻业是否满足专业的要求以及是否符合民主监督者的规范认知,都窄化了新闻业在变动的实践中的丰富意涵,指出与其从效果来审视新闻业,不如从新闻如何运作的种种形式,例如表演、叙事、仪式、阐释社群等来切入。[55]泽利泽借鉴文学理论提出了“记者作为阐释社群”的概念,将记者社群与其他阐释社群对公共事件的发言权的竞争作为切入点,从记者社群所表达的共享话语和集体阐释去透析新闻业的文化意义。[56]简而言之,只有文化分析才能将新闻记者与非新闻记者、主流的新闻业与非主流的新闻业、传统与新兴实践、正当的与非正当的行动者之间的交互影响纳入同一个框架内,而不必顾此失彼。
新闻业的文化分析考察的是记者借以理解其专业的文化符号体系(cultural symbol system),哪些语境因素在影响新闻实践,以及不同的新闻形式的区分边界是如何被建构的。与那些试图建构新闻业具有普适、统一的文化的研究不同,泽利泽认为新闻业的文化分析通常不预设新闻业内部存在统一性,而是存在差异、区别、矛盾乃至冲突,不同的文化工具也被记者用于解释哪些对于新闻业而言是重要的、正确的和受青睐的。[57]因此,新闻业的文化分析是取决于具体语境、时间和空间的,而非无差别和静态的。进而言之,文化分析保持着对变动中的新闻业的定义、边界、传统和实践的考察,以此审视新闻业如何在常规情境以及危机情境下被落到实处。[58]文化分析学者不再仅仅将新闻看作记者的职业行为编码或者记者与编辑的组织分工的产物,而是视其为“一种复杂的、多维度的意义格构”(lattice)。[59]新闻业研究所探索的也就是记者在维系其作为社会现实发言人的文化权威时所凭借的意义结构、符号与象征体系、意识形态、仪式和传统。首先,文化分析认为一种关于新闻业的文化赋予(cultural given)使记者与非记者能够汇聚;其次,使新闻业独立于其他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变量也可以当作连接差异的桥梁,从而“使新闻业构成一个离散的、常常自相矛盾的驱动力的整体”;其三,文化分析不仅仅将记者看作信息的传送者,也将其视为文化生产者,通过媒体产品的倾向来表达他们对好与坏、道德与非道德、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分。[60]总之,文化分析聚焦于新闻业内外部的形象差异所存在的张力,同时采取一种动态并依据具体情境和历史环境而变化的视角来审视新闻传统、常规与实践。
泽利泽认为,当新闻业面临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动荡影响之时,通过文化构念去思考新闻业便显得尤有价值。区别于组织和制度视角,文化视角考察的内容之一是制度性的新闻实践、常规和传统对记者个体以及群体之间具有什么意义,既通过记者自身的眼光来审视新闻业,追寻作为阐释社群之一部分对记者的意义,也考察记者的自我呈现。[61]可以说,泽利泽的研究拓宽了新闻社会学的视野,她所提出的“记者作为阐释社群”、新闻(文化)权威等概念,无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与泽利泽重点关注记者的阐释社群与文化权威相比,还有文化路径的学者提出新闻业研究应从关注过程到关注意义,从考察新闻的社会建构到新闻的文化建构,丹尼尔·伯克维茨堪称其中代表。事实上,伯克维茨等人前期关于新闻失范现象、新闻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集体记忆的研究,[62]与泽利泽等人的研究存在诸多交叉之处。伯克维茨指出,文化视角的新闻业研究重点要解决的是通过新闻的讲述去理解新闻职业文化以及生产新闻的社会。在这一视角下,记者被当作这样一群人:“他们在一个新闻编辑室、媒体机构及社会的文化之下生活与工作;他们将新闻机构所生产的文本视为一种体现了核心价值与意义的文化的产品”。[63]伯克维茨认为,新闻业研究在过去的数十年来经历了三种视角,即从新闻(news)的选择的视角逐渐转向社会学组织(sociological organization)视角,再转向新闻业的文化维度(cultural perspective),简而言之,新闻业研究的焦点从“做新闻”的过程、限制和结构转移到“做新闻”作为一种职业对卷入其中的记者的意义。[64]伯克维茨和刘正稼认为,新闻室民族志研究的关键发现可以概括为“新闻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news),关注的是生产过程,而文化路径的新闻业研究则可以概括为“新闻的社会文化建构”(the social-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s),关注的是意义的生产。[65]他们认为,文化路径的新闻社会学研究,重点是探讨新闻生产中记者如何整合共享的意义,即如何通过关于新闻业的神话叙事、集体记忆和表意符号(ideograph)去建构新闻业的意义。[66]在泽利泽和伯克维茨的指导、影响下,以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瑟斯·刘易斯(Seth Lewis)等为代表的新生代学者对新闻业边界(boundaries of journalism)、新闻权威(journalistic authority)的研究,[67]构成了新闻业的文化分析的新起点。他们的关注点放在了新闻业在新的媒体生态系统下如何面对挑战,自我调整,重构边界与再造权威之上。对新闻业而言,以往不被视为新闻业的合法成员、元素或实践的形式都可能日益被接受为正当的新闻形式,由此便会不断重新定义新闻、记者和新闻业的边界及文化权威。记者对新闻权威的宣称亦非一劳永逸,而是受到来自新闻业内部与外部的竞争和挑战,需要不断地进行协商、重申乃至调整。在他们的研究中,新闻权威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客体,而是处于一种演变之中,也不是以新闻业为中心,而是处于一种关系性(relational)的网络之中,展现了新闻业在与不同的行动者的具体互动中所形成的新闻权威的具体形态。[68]卡尔森等人对新的媒体行动者、受众和媒体生态的关注,对新闻权威研究进行了丰富和拓展。比如,在泽利泽的研究中阙如的公众批评在社交媒体环境下获得了重视,这是因为新闻机构和记者对新闻权威的声称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公众的频繁、直接、日常化的媒体批评(mundane media criticism),[69]卡尔森沿袭泽利泽的阐释社群概念,提出元新闻话语分析,从而将公众、其他媒体行动者都纳入分析范畴内。[70]就其关于新闻业的公共讨论而言,基于社交媒体的日常媒体批评构成了元新闻话语的一部分,这尤其在主流媒体、记者出现差错、伦理缺陷甚至被揭露造假丑闻时,尤为明显,并且比起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体批评更具有破坏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伯克维茨对文化路径的新闻业研究之所以兴起的归因,在某种程度上过于偏向方法和时间成本的考虑,不乏对这一理论取向的庸俗化考虑。在他看来,文化路径的新闻业研究是文本(更多是狭义上的新闻文本而不是民族志意义上的文本)导向的,这样既可以节省数据收集的时间,也可以应付学术考核体制的要求。[71]但我们应当指出,文化路径的新闻业研究并不必然排斥对新闻生产过程、常规的分析,生产过程与常规在民族志的深描中也可以当作一种文本;并且,民族志的深描法不应当因为时间投入过长原因就被抛弃。重要的是以文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受组织研究浸润已久的那些理论、概念和视角。比如,新闻常规在新的媒体环境下,是否因应新闻职业文化的调整而改变?其改变的背后,体现了一个社会中关于新闻定义的何种意义体系?
(二)文化社会学的强范式:新闻业的文化结构与恒久符码
文化社会学者也对新闻业的文化意义进行了研究,这以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Alexander)、罗纳多·雅各布斯(Ronald Jacobs)等学者以及他们的学生为代表。他们从新闻业、文化与公共领域的关系着眼,[72]分析新闻业的文化结构(cultural structure)与二元符码(binary codes),指出新闻业的文化结构和二元符码框架了记者和市民社会对新闻业的理解与阐释。就理论渊源而言,亚历山大的文化社会学主张综合了符号学、人类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涂尔干晚期的文化思想等。诚然,在转向文化社会学研究之前,他归属于新功能主义者。[73]随着新文化史家提出文化转向和象征人类学的影响日益深入,他开始意识到文化社会学的意义。在一篇学术访谈中,亚历山大表示:“在1970年代,我仔细阅读了克利福德·吉尔茨的《文化的阐释》、埃米尔·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玛丽·道格拉斯的《纯洁与危险》,以及维克多·特纳的著作,但是,我并未足够重视它们。我不认为我真正理解了这些观点的反响,直到1980年代早期我开始认真阅读和讲授符号学,例如罗兰·巴特、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马歇尔·萨林斯,以及其他一些作者的作品”。亚历山大指出,“当1980年代中期我开始做文化社会学研究时,我承认自己感到相当孤立,不仅在美国之外的主流社会学是这样,而且英国文化研究和欧陆批判性解释工作亦复如此”。[74]如亚历山大所言,他的文化社会学理念取道于吉尔茨将社会看作活生生的文本的思想,认为社会像文本一样包含自身的解释,[75]而文化社会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有三项,即阐释社会生活的文本型态,强调文化结构相对于社会结构的自主性,并努力厘清文化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与伯明翰学派开启的文化研究和“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不同,亚历山大等学者提出的强范式(strong program)的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强调文化作为自变量以内在的方式塑造了世界的文本,具有自主性而非依赖于社会结构,认为人的行为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包含在情感和意义之中,而非完全按照工具理性行动。[76]在这一范式下,其分析着重于“文化作为文本”的意义,提出任何非亲历的社会现实都是文本的作为。譬如,人们对大屠杀受难者所表现出的悲痛、哀悼是由媒体报道塑造的,而非人们亲历大屠杀场景的结果。[77]相应的,新闻业和记者也就不仅仅是信息的搬运工、加工者或传递者,而是社会文化的建构者。
具体到文化社会学路径的新闻业研究,亚历山大等人认为,文化社会学主张新闻应被视作对现实的阐释而不仅仅是信息,新闻不是告知而是阐释。[78]亚历山大认为,新闻室民族志研究在1980年代之后衰落,由于文化社会学的介入在近年来获得明显的复兴。[79]区别于传统新闻室民族志和布迪厄的场域分析,文化社会学的关注点在于媒体、文化和公共领域的关系,并且,他们以交往性(communicative)和表意性(expressive)而不是工具的或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待媒体,关注记者如何以新闻话语阐释新闻业,包括有关新闻业在民主生活中的使命、新闻组织和记者的责任,以及主流新闻理念可能产生缺陷的方式。[80]罗纳多·雅各布斯则提出,“黄金时代”的新闻社会学研究往往并不聚焦文化和公共领域,也不认为媒体话语有何独特之处,在他看来,对组织约束与工作常规的强调导致社会学者没有将媒体与广泛的公共生活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化约主义的媒体社会学:一切新闻选择都被简化为组织的选择。而要让媒体社会学复兴,就必须将公共领域、公众的问题纳入研究范畴,而不能仅着眼于媒体组织的一亩三分地。[81]在强范式的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社会文化现象往往重复体现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文化符码,[82]例如洁净vs.风险,善vs.恶,正确vs.错误等,而公共话语中关于新闻业发生的危机事件、反常现象或丑闻也常常在文化符码中被建构和阐释。循着这一思路,伊丽莎白·布里斯(Elizabeth Breese)在其关于美国新闻业危机话语的研究中发现,每当出现一种新的技术或一种新的新闻实践方式,新闻界总会将新来者描述为具有威胁的“局外者”,并将新闻业的衰落和危机描述为新的、令人震惊的和前所未有的问题。她认为,美国新闻界的危机话语秉承了一种文化定义的模式,并依赖那些二元对立、叙事和转喻(trope)去描述和评估新闻业所发生的事件与变迁。从长时段而言,新闻业的危机话语内嵌于长期主导新闻业的意义体系(亦即由客观vs.主观、公正vs.倡导、体面vs.煽情等构成的二元对立符码)之内,也是由这一意义体系所生产的。[83]2016年,亚历山大等人编著了《新闻业危机再商榷》一书,指出业界和学界关于新闻业危机的讨论聚焦在技术和经济层面,而没有看到新闻业的深层文化结构仍然活跃,新闻的形式或许会改变,但新闻业的文化力量将赋予其新的制作和传播的实践、模式和方式。他们认为,新闻业的文化力量拒绝技术和经济决定论,并且有助于促成个体和集体的能动性,历史上的媒体技术变革也导致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在传媒业中形成,但这一过程不是单向的,如果传统新闻业在适应新的媒体技术和形态,那么非传统新闻业的媒体实践也在向专业新闻业靠拢。[84]因此,他们提出,传媒业的危机应当被理解为有文化依据(the culturally informed)的新组织形式的重构,而不是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在此过程中,文化符码不仅仅促发关于技术和经济变革带来的焦虑,还提供管控这些变革的路径,从而使得新闻业的民主实践能够在新的形式中得到维系而不是破坏。[85]诚然,文化社会学预设的新闻业文化的自主性不是天然给定的或者确定无疑的,而是需要记者社群和市民社会的共同争取,它既是公众对新闻业在一个社会中的角色和价值的期待,也可能随着政治共识和社会语境的变化而调整,无论如何它不是绝缘于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正如公共领域的独立性常常受到来自市场、国家、道德、宗教组织的倾轧,新闻业的自主性也常受到威胁,常因边界被僭越而令人忧虑不已。” [86]而依据于文化符码的一系列新闻话语的表达,实际上也起到划定边界的效果,让记者得以保护他们减少技术革新与商业动荡带来的冲击,保持他们对新闻工作的合法控制权。[87]总之,新闻业的文化结构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公众对民主的需要如同对新闻业的需要,新闻界既不能对新闻业的文化意义过度浪漫,也不能感到无奈而放弃对它的争取。
(三)一个整合路径:新闻业研究的文化-社会路径
作为对以上两种相互关联、同中有异的文化路径的新闻业研究的总结,本文就代表性学者、聚焦点、出现年代、理论资源、关键概念、研究方法、研究焦点、文化与新闻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归类(表1 表1见本期第57页)。
需要指出,这里的归类不代表着两者是截然分隔的,实际上它们具有诸多共通之处。其一,他们都拒绝仅将新闻业界定为信息的生产活动,而是一项意义导向的工作,具有公共的文化意义,阐释则是意义建构的关键机制。记者的报道以及他们围绕报道而产生的元新闻话语,应当被当作意义建构的表现。其二,它们对主流新闻业与新兴的新闻实践形式之间的互动的关注,对新闻业危机话语的分析,对新闻业边界的历时态考察,显示出这两个取向的学者具有共享的研究议题。其三,新闻权威、专业边界、阐释社群等关键概念在两者的流通也表明了融合文化社会学概念与文化路径的新闻业研究的潜力。
当然,两者也存在差异。第一,坚持文化分析的新闻学者是以新闻业和记者社群为中心,而亚历山大和雅各布斯等文化社会学者则更多地从整个社会的文化语境来考察新闻业如何通过与公众的互动来确立其在民主、公共领域的角色与意义。可以说,新闻学者的文化路径首先是从新闻业出发,而文化社会学者的分析则基于新闻业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第二,文化社会学者的分析强调新闻业的文化结构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认为其文化结构具有独立于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力量。也就是说,新闻业文化是一种自变量而不是因变量。而在新闻学者的文化分析中,更常见的是将文化既当作一种限定记者和新闻业行动空间的结构,也突出记者作为阐释社群对这一文化资源的挪用和塑造,文化与新闻业处于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
基于对它们的整合,本文提出“新闻业研究的文化–社会路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注重新闻业的文化建构取向,但不能仅仅注重文化取向而忽略了新闻业与社会结构的交互影响,社会结构如何影响新闻业的文化意义建构,新闻业所处的社会结构又如何体现了意义结构,也需要纳入进来考量。譬如,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影响下,新闻业的文化意义可能是存在差异的,而新闻阐释社群所使用的新闻话语也可能是不同的;同时,在变化的社会结构之下,我们也能够发现,新闻业的某些文化价值又是恒久的。
四、迈向意义导向的新闻业研究
在“黄金时代”的新闻社会学经典之后,新闻学界对新闻社会学研究的反思也紧跟媒介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然而,现有的理论反思或修正在很大程度上仍纠结于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88]无论是强调结构的限制,还是提出行动者的能动性,或者以结构化理论进行综合的尝试,都还是在原有的框架内探索。一言以蔽之,社会组织路径的新闻社会学关注的是媒介生产的过程以及“生产者-结构”的二元对立或博弈,而不是新闻生产者在参与新闻业的过程中所编织、体验的“意义之网”。不可否认,来自技术的冲击、裹挟,来自竞争领域的挑战、颠覆,来自权力与资本的约制,来自公众的日常化批评,都不断在削弱这个时代作为记者的意义支撑。既有的意义体系能够让传统和新兴的新闻从业者确立安身立命之所吗?在一个充满多元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时代语境下,如何重塑新闻业的意义?这些问题难以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组织分析中得到答案。在不确定性的时代能够烛照新闻业的前景的,应当是侧重意义分析与阐释的文化路径的理念。本文聚焦并整合新闻业的文化分析和文化社会学的新闻研究,不代表着要否定主流的新闻社会学研究,而是在传统研究路径之外提供新的思路。新闻业研究是紧扣新闻业发展和变化的语境的,当新闻业的生态体系以及关于新闻、记者和新闻实践的定义都在经历调整之时,新闻业研究理当跳出传统的框架。
提倡文化-社会路径的新闻业研究,首先是基于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的理论成果的吸收,从而对新闻业的研究提出新的视角,观照在主流的新闻社会学研究中较少被关注的面向-意义体系。遵循吉尔茨的观念,意义在这里应当被当作包含认识、情感、道德在内的一般性思考,而象征/符号则是传递意义的载体。在新闻业中,这包括新闻的集体记忆、媒介聚像、新闻职业典范的意义建构、新闻业实践的范式更新与修补等现象。
其次,也是基于对变化的新闻业的生态环境、文化权威的动态把握,无论是重新界定新闻、记者和新闻实践,还是调和技术变革、经济动荡、组织重构和文化力量的关系,都需要从意义的层面去理解新闻业的新形态。具体而言,文化–社会路径的新闻业研究考察的是不同的内容生产者在元传播[89]的过程中的意义生产以及完成之后的阐释与反思,亦即一个生产意义、维持意义和修补意义的长期过程,而非仅仅关注他们在内容生产中受到结构的制约。我们可能提出如下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从事新闻职业或广泛意义上的元传播活动具有什么意义?新闻业内在的文化结构是怎样影响元新闻话语的形成的?专业记者如何与非专业新闻生产者、传播者互动,既维护新闻业的边界和文化权威,又在元传播的意义上塑造新闻业的公共性?在新闻业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建构一个共享的意义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什么样的冲突与调适?不同类型的内容生产者之间的差异又是如何在二元对立的文化符码中被阐释的?这些问题都有待新闻学者对变化语境下的新闻记者和广泛意义上的内容生产者的日常意义体系进行移情的理解和阐释。
其三,需要指出的是,新闻业的意义体系应当是多层次的,而非一个宽泛、单一的所指,并且,新闻业的意义体系应该是与公众共享的,而不是独白、自说自话或顾影自怜的。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划分:在职业层面上,新闻业的意义体系对记者而言意味着什么?如何在职业层面建立新闻工作的正当性?在“新闻业—公众”关系的层面上,开放的新闻生产对记者和非记者的意义分别是什么?意义的建构如何与新闻业的边界和新闻权威产生关联?在“新闻业—技术”关系的层面上,技术创新如何被新闻业的意义结构所吸纳?技术的社会结构又如何与新闻业的文化结构形成互动?
最后,文化–社会路径的新闻业研究还应在新闻业面临不确定性以及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的质疑,假新闻甚嚣尘上的“后真相”语境里,通过对新闻业的核心——事实、真相、真实等概念的再阐释,去重塑、维系新闻业的意义体系。归根结底,我们所要聚焦探讨的问题是新闻业的社会意义、文化价值、正当性的当代重构。■
①Zelizer, B. (2015). Terms of Choice: UncertaintyJournalism, and Cri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5(5): 888-908.
②DavidsonR.& Meyers, O. (2016).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Exit, Voice and Loyalty among Journalists. Journalism Studies17(5): 590-607.
③潘忠党:《在“后真相”喧嚣下新闻业的坚持》,《新闻记者》2018年第5期
④SchudsonM. (1989).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MediaCulture & Society11: 263–282。2005年时,舒德森又将政治经济学路径一分为二,即新闻生产的政治语境研究和新闻生产的经济组织路径,从而提出新闻社会学的四种研究路径之说,参见SchudsonM. (2005). Four Approaches to the Sociology of News.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4th edn.) (pp. 172-197). London: Hodder Arnold.
⑤SchudsonM. (1989).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MediaCulture & Society11: 275。不过,在2005年的修改版中,舒德森删掉了对文化路径不足以称之为一个流派的判断。
⑥SchudsonM. (2005). Four Approaches to the Sociology of News.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4th edn.) (pp. 172-197). London: Hodder Arnold, p. 174187190.
⑦Carey, J. (2008[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⑧Zelizer, B. (1992).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the Media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⑨Berkowitz, D. (Ed.) (1997). Social Meanings of News: A Text-Reader. Thousand Oaks: Sage.
⑩Berkowitz, D. (Ed.) (2011). Cultural Meanings of News: A Text-Reader. Thousand Oaks: Sage.
[11]CoddingtonM. (2015). Clarifying Journalism’s Quantitative Turn: A Typology for Evaluating Data Journalism, Computa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 Digital Journalism, 3(3)331-348.
[12]BoczkowskiP.J. & Anderson, C. W. (Eds.) (2017). Remaking the News: Essays o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Scholarship in the Digital Age. 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
[13]PetersC.& Broersma, M. (Eds.) (2017). Rethinking Journalism Again: Societal Role and Public Relevance in a Digital Age. Oxford: Routledge.
[14]姜进:《总序》第3页,载[美]林·亨特编,姜进译《新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HuntL. (Ed.) (1989).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 Los Angeles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6]中文亦有格尔茨、吉尔兹等不同翻译。
[17]简惠美等译:《导论三:韦伯的学术》,载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译:《学术与政治》第73–7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GeertzC. (2017[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p. 5.
[19]GeertzC. (2017[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p. 95.
[20]Clark, S. (2011). Thick DescriptionThin History: Did Historians always Understand Clifford Geertz? In Jefferey C. AlexanderPhilip Smith & Matthew Norton (Eds.)Interpreting Clifford Geertz: Cultural Investig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 105-12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1]Darnton, R. (2017). Foreword: Anthropology, Historyand Clifford Geertz. In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pp. vii-ix). New York: Basic Books.
[22]陈恒:《卷首语》,载陈恒、耿相新编《新史学》(第四辑)第1页,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23]Alexander, J.C. (Ed.) (1988). Durkheimian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Cambridge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Smith, P. & AlexanderJ. (2005). Introduction: The New Durkhei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 Philip Smith (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urkheim (pp. 1-37). Cambridge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 10-13.
[25]ReedI. (2006). Culture as Object and Approach in Sociology. In Isaac Reed & Jeffrey Alexander (Eds.)Meaning and Method: 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Sociology (pp.1-14). Boulder &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26]见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Thousand Oaks: Sage, p. 64.
[27]如 CareyJ.& Kreiling, A. L. (1974). Popular Culture and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Notes toward an Accommodation. In J. G. Blumler & E. Katz (Eds.)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pp. 225–248). Beverly Hill, CA.: Sage; CareyJ. (1974). 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ism History1(1): 3-5; CareyJ. (1975).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2): 173-191.
[28]PooleyJ. (2016). James W. Carey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utation at the University’s Margins. New York: Perter Lang, p. 77.
[29]PooleyJ. (2007). Daniel CzitromJames W. Careyand the Chicago School.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24(5): 469-472.
[30]Carey, J. & GrossbergL. (2006). From New England to Illinois: The Invention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In Jeremy Packer & Craig Robertson (Eds.)Thinking with James Carey: Essays on Communications, Transportation, History (pp. 11-28). New York: Peter Lang, pp. 20-21.
[31]SterneJ. (2009). James Carey and Resistance to Cultural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Cultural Studies23(2): 283-286.
[32]HallS. (1990).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The Humanities as Social Technology, 53: 11-23; Hall, S. (2016). Cultural Studies 1983: A Theoretical Histor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p. 7; Hall, S. (2005[1980]).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 In Stuart Hall, et al.(Eds.)CultureMedia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2–79 (pp. 2-35).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33]Hay, J. (2009). Undressing the Death Sceneand other Puzzling Communication about Culture that James Carey Bequeathed Me. Cultural Studies23(2): 187-214; Pooley, J. (2016). James W. Carey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utation at the University’s Margins. New York: Perter Lang.
[34]Carey, J. & GrossbergL. (2006). From New England to Illinois: The Invention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In Jeremy Packer & Craig Robertson (Eds.)Thinking with James Carey: Essays on Communications, Transportation, History (pp. 11-28). New York: Peter Lang, p. 21.
[35]Carey, J. (1997). Afterward: The Culture in Question. In Eve S. Munson & Catherine A. Warren (Eds.)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pp. 308-339). Minne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 331.
[36]这一点获益于作者与李金铨教授的探讨。
[37]Eason, D. (1986). On Journalist Authority: The Janet Cooke Scandal.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3: 429-447.
[38]见Carey, J. (Ed.)(1988). MediaMythsand Narratives: Television and the Press. Newbury Park, CA.: Sage.
[39]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Thousand Oaks: Sage, p. 190.
[40]Zelizer, B. (2004). When FactsTruthand Reality are God-terms: On Journalism’s Uneasy Place in Cultural Studies.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1(1): 100–119.
[41]Grossberg, L. (1993). Can Cultural Studies Find True Happiness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3(4): 89-97.
[42]JohnstonH.& KlandermansB. (1995). The Cul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Hank Johnston & Bert Klandermans (Eds.)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pp. 3-24). Minneapolis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43]SnowD.A.& BenfordR.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 197–217.
[44]SchudsonM. (1989). How Culture Works: Perspectives from Media Studies on the Efficacy of Symbols. Theory and Society18: 153-180.
[45]GamsonW. A.&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5: 1–37.
[46]EttemaJ. (2005). Crafting Cultural Resonance: Imaginative Power in Everyday Journalism. Journalism, 6(2): 131–152.
[47]EttemaJ.& GlasserT. (1998). Custodians of Conscienc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Public Virt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8]Zelizer, B. (1992).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the Media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 10.
[49]SchudsonM. (1992). 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 How We Remember, Forget, and Reconstruct the Past. New York: Basic Books.
[50]Zelizer, B. (2005). The Culture of Journalism.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 198-214). London: Hodder Arnold, p. 200.
[51]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Thousand Oaks: Sage, p. 176.
[52]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Thousand Oaks: Sage, pp. 178-179; ZelizerB. (2005). The Culture of Journalism.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4th edn.) (pp. 198-214). London: Hodder Arnold.
[53]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Thousand Oaks: Sage; ZelizerB. (2005). The Culture of Journalism.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4th edn.) (pp. 198-214). London: Hodder Arnold.
[54]JacobsR. (2009). Culturethe Public Sphere, and Media Sociology: A Search for a Classical Founder in the Work of Robert Park.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40(3): 149–166.
[55]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Thousand Oaks: Sage, p. 8.
[56]Zelizer, B. (1992).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the Media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elizerB. (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0(3): 219-237.
[57]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Thousand Oaks: Sage.
[58]Zelizer, B. (2005). The Culture of Journalism.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4th edn.) (pp. 198-214). London: Hodder Arnold, p. 211.
[59]Zelizer, B. (2005). The Culture of Journalism.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4th edn.) (pp. 198-214). London: Hodder Arnold.
[60]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Thousand Oaks: Sage; ZelizerB. (2005). The Culture of Journalism.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4th edn.) (pp. 198-214). London: Hodder Arnold.
[61]Zelizer, B. (2005). The Culture of Journalism.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4th edn.) (pp. 198-214). London: Hodder Arnold, pp. 200-201.
[62]如Berkowitz, D. (2000). Doing Double Duty: Paradigm Repair and the Princess Diana What-a-story. Journalism, 1(2): 125–143; BerkowitzD. (2010). The Ironic Hero of Virginia Tech: Healing Trauma through Mythical Narrative and Collective Memory. Journalism, 11(6): 643–659; BerkowitzD.& GutscheR. E. (2012). Drawing Lines in the Journalistic Sand: Jon StewartEdward R. Murrow, and Memory of News Gone by.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9(4): 643–656等。
[63]Berkowitz, D. (2011) (Ed.). Cultural Meanings of News: A Text-Reader. Thousand Oaks: Sage, p. xii.
[64]Berkowitz, D. (2011) (Ed.). Cultural Meanings of News: A Text-Reader. Thousand Oaks: Sage; BerkowitzD.& LiuZ. (2014). The Social-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s: From Doing Work to Making Meanings. In Robert S. Fortner & P. Mark Fackler (Eds.)The Handbook of Media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ume 1 (pp. 302-313). Oxford: Wiley Blackwell.
[65]Berkowitz, D.& LiuZ. (2014). The Social-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s: From Doing Work to Making Meanings. In Robert S. Fortner & P. Mark Fackler (Eds.)The Handbook of Media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ume 1 (pp. 302-313). Oxford: Wiley Blackwell; BerkowitzD.& LiuZ. (2016). Studying News Production: From Process to Meanings. In Chris Paterson, David LeeAnamik Saha, & Anna Zoellner (Eds.)Advancing Media Production Research: Shifting SitesMethodsand Politics (pp. 68-78). HampshireUK: Palgrave Macmillan.
[66]Berkowitz, D.& LiuZ. (2014). The Social-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s: From Doing Work to Making Meanings. In Robert S. Fortner & P. Mark Fackler (Eds.)The Handbook of Media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ume 1 (pp. 302-313). Oxford: Wiley Blackwell.
[67]Carlson, M.& LewisS. (2015).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arlsonM. (2018). Journalistic Authority: Legitimating News in the Digital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68]Carlson, M. (2017). Journalistic Authority: Legitimating News in the Digital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69]Carlson, M. (2016). Embedding LinksEmbedded Meanings: Social Media Commentary and News Sharing as Mundane Media Criticism. Journalism Studies17(7): 915-924; FenglerS. (2012). From Media Self?regulation to ‘Crowd?criticism’: Media Accountability in the Digital Age.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9): 175-189.
[70]Carlson, M. (2017). Establishing the Bundaries of Journalism’s Public Mandate. In Chris Peters & Marcel Broersma (Eds.)Rethinking Journalism again: Societal Role and Public Relevance in a Digital Age (pp. 49-63).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71]Berkowitz, D.& LiuZ. (2014). The Social-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s: From Doing Work to Making Meanings. In Robert S. Fortner & P. Mark Fackler (Eds.)The Handbook of Media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ume 1 (pp. 302-313). Oxford: Wiley Blackwell.
[72]Alexander, J.C.& SmithP. (1993). The Discourse of American Civil Society: A New Proposal fo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Society22(2): 151-207; Jacobs, R.N. (1996). Civil Society and Crisis: CultureDiscourseand the Rodney King Beat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01(5): 1238-1272; AlexanderJ.C. (2006). The Civil Sp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cobs, R.N.& Wild, N.M. (2013). A Cultural Sociology of The Daily Show and The Colbert Re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1(1): 69–95.
[73]新功能主义是1980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学界兴起的一股力图综合当代最新研究成果以重新建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传统的流派或理论取向。亚历山大正是“新功能主义”这一术语的命名者。新功能主义接纳学术界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评,提出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也提出注重分析文化和人的行动的意义性质,但它并不是为结构功能主义辩护,而是试图去超越它。参见苏国勋:《新功能主义: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的一种新的综合视角》,《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8期;林聚任:《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与社会学理论传统重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74]Cordero, R.Carballo, F.& Ossandón, J. (2008). Performing Cultural Sociology: A Conversation with Jeffrey Alexande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1(4)p. 535.
[75]周怡:《强范式与弱范式: 文化社会学的双视角——解读J .C .亚历山大的文化观》,《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194-214页。
[76]周宪:《主持人语》,载周宪、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2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77]Alexander, J.C. (2003).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8]Alexander, J.C. (2015).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Cultural Power.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8(1): 9–31.
[79]Alexander, J.C.Jacobs, R.N.& SmithP. (2012). Introduction: Cultural Sociology Today. In Jeffrey C. AlexanderRonald N. Jacobs & Philip Smith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ultural Sociology (pp. 3-2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0]Alexander, J.C. (2016). Introduction: Journalism, Democratic Cultureand Creative Reconstruction. In Jeffrey C. AlexanderElizabeth Breese, & Maria Luengo (Eds.)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Democratic CultureProfessional CodesDigital Future (pp. 1-28). Cambridge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eese, E. (2012). Interpreting the News: A Cultural Sociology of Journalistic Discour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Luengo, M. (2016). When Codes Collide: Journalists Push Back against Digital Desecration. In Jeffrey C. AlexanderElizabeth Breese, & Maria Luengo (Eds.)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Democratic CultureProfessional CodesDigital Future (pp. 119-134). Cambridge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1]JacobsR. (2009). Culturethe Public Sphere, and Media Sociology: A Search for a Classical Founder in the Work of Robert Park.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40(3)p. 150.
[82]Alexander, J.& SmithP. (2003). The Strong Program in Cultural Sociology: Elements of a Structural Hermeneutics. In Jeffrey Alexander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pp. 11-2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3]BreeseE. (2012). Interpreting the News: A Cultural Sociology of Journalistic Discour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84]Alexander, J. C.Breese, E.& Luengo, M. (Eds.) (2016).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Democratic CultureProfessional CodesDigital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5]Alexander, J.C. (2015).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Cultural Power.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8(1): 9–31.
[86]Alexander, J.C. (2015).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Cultural Power.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8(1): 9–31.
[87]OstertagS. (2016). Expressions of Right and Wrong: The Emergence of a Cultural Structure of Journalism. In Jeffrey C. AlexanderElizabeth Breese, & Maria Luengo (Eds.)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Democratic CultureProfessional CodesDigital Future (pp. 264-281). Cambridge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8]Usher, N. (2013). Marketplace Public Radio and News Routines Reconsidered: Between Structures and Agents. Journalism, 14(6): 807-822.
[89]潘忠党:《新闻变迁的核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7日
陈楚洁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融合语境下的新闻社会学研究:一种文化路径”(项目批准号:18YJC860004)的阶段性成果,初稿曾发表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举办的“重访黄金时代:媒介社会学经典再阐释”工作坊,作者感谢李艳红教授、李红涛副教授、白红义副研究员、周睿鸣研究员以及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建议,并对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