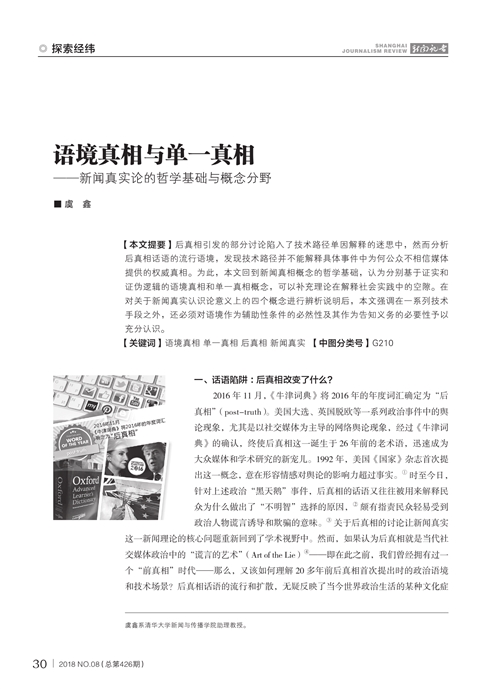语境真相与单一真相
——新闻真实论的哲学基础与概念分野
■虞鑫
【本文提要】后真相引发的部分讨论陷入了技术路径单因解释的迷思中,然而分析后真相话语的流行语境,发现技术路径并不能解释具体事件中为何公众不相信媒体提供的权威真相。为此,本文回到新闻真相概念的哲学基础,认为分别基于证实和证伪逻辑的语境真相和单一真相概念,可以补充理论在解释社会实践中的空隙。在对关于新闻真实认识论意义上的四个概念进行辨析说明后,本文强调在一系列技术手段之外,还必须对语境作为辅助性条件的必然性及其作为告知义务的必要性予以充分认识。
【关键词】语境真相 单一真相 后真相 新闻真实
【中图分类号】G210
一、话语陷阱:后真相改变了什么?
2016年11月,《牛津词典》将2016年的年度词汇确定为“后真相”(post-truth)。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的舆论现象,尤其是以社交媒体为主导的网络舆论现象,经过《牛津词典》的确认,终使后真相这一诞生于26年前的老术语,迅速成为大众媒体和学术研究的新宠儿。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意在形容情感对舆论的影响力超过事实。①时至今日,针对上述政治“黑天鹅”事件,后真相的话语又往往被用来解释民众为什么做出了“不明智”选择的原因,②颇有指责民众轻易受到政治人物谎言诱导和欺骗的意味。③关于后真相的讨论让新闻真实这一新闻理论的核心问题重新回到了学术视野中。然而,如果认为后真相就是当代社交媒体政治中的“谎言的艺术”(Art of the Lie)④——即在此之前,我们曾经拥有过一个“前真相”时代——那么,又该如何理解20多年前后真相首次提出时的政治语境和技术场景?后真相话语的流行和扩散,无疑反映了当今世界政治生活的某种文化症候:如何表述,又如何归因?谁在使用,又对谁言说?因此,要想透彻剖析后真相话语的流与变,我们不妨先从学界对后真相形成原因的讨论开始,对其如何被表述和归因的路径进行考察。
(一)后真相的技术路径解释
总的来说,技术因素及其形塑的媒介环境和社会结构,构成了对后真相形成原因的主流解释。
首先,技术赋权了个体的信息生产效能,消解了机构生产者的专业约束。缺乏社会意义的噪音、无法确证但挑动情绪的流言,甚至具有主观恶意和欺骗性的谎言,充斥舆论空间。⑤社交媒体充分激发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和主观欲望,客观事实和现代理性被立场、情感、信仰所取代,⑥事实和观点边界模糊,观点和个人体验凌驾于事实之上。在被虚假甚至编造的新闻、未经证实的流言和煽情的个人经历所挤占的公共舆论里,认知更新导致的信息生产速度远赶不上技术更新导致的信息扩散速度,真相也就被不断发酵的舆论甩在了身后,真实和新鲜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⑦
其次,信息技术不仅重构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方式,也改造了人际关系的结构。社交媒体一方面卓有成效地完成了相同背景、相同观点、相同兴趣个体的组织聚合;另一方面也因本能的利益驱动,通过个性推荐、定制推送等算法机制将业已隔离的网络社群进一步割裂。⑧价值观念、群体文化成为信息扩散的内在动力,而伴随事实逐渐式微的同构过程则是雄辩的进一步正当化。以至于有学者将后真相时代类比为数字时代的景观社会,认为社会的分化和不信任扩散,根本就是现有技术场景下后真相的本质属性。⑨
最后,来自认知心理学和行为实验的结果也揭示,个体认知的局限性以及社会救济手段的无效性,似乎也无法预见社会能动性对技术主导下的后真相突围的可能性。选择性接触、选择性认知、选择性信任等一系列心理机制,构成了在固定意识形态下忽视事实的基本逻辑——即使是作为补救措施的事实核查新闻也同样如此。⑩在分析美国超过2000个网民的30天真实浏览数据后会发现,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人读过至少一篇事实核查报道,甚至没有一个人在读过某条假新闻后,阅读了关于此条假新闻的事实核查文章。[11]这类被称作“持续影响效应”(continued-influence effect)的心理机制认为,受众往往相信那些错误但传播广泛的信息,而对之后的修正信息视而不见或无意识地忽视。[12]而且,如果这种修正挑战了受众的价值观,那么对原先错误信息的信任反而会更加强烈。[13]概括来说,技术解释路径认为技术因素对信息生产过程的重塑,构成了后真相形成的基础——信息技术赋予了个体表达的权利,然而由于缺乏专业媒体的伦理和社会责任约束,个人表达的扩张模糊了事实与观点的边界,降低了公共舆论逼近真相程度。在此基础上,技术阻碍而不是促进了不同网络社群间的连接机会,进一步强化了非事实因素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体心理机制的局限性也解释了那些针对技术困境的补救方式,效果非常有限。上述这些具有深厚理论传统和确切实证数据的结论,确实对结构化理解后真相时代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技术赋权个体表达”这一技术解释框架中的基本判断,却仍然无法解释为何在信息技术远未普及的20世纪90年代,就已有人洞察并提出了后真相的概念——彼时的新闻和信息,大多由专业化的新闻机构所生产。那么,一个显见的问题便是:现在的后真相时代和曾经所谓的“前真相”时代,区别在哪里?
(二)后真相话语的言说对象
虽然在数量和规模上,近两年关于“后真相”的讨论远远多于过去二十多年的总和,这可能可以解释成是因为技术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后真相讨论规模的时间差别,仅仅是讨论规模的差别,而并非现象本身规模的差别——也就是说,近年来关于后真相讨论的突然流行,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就必然存在一个“前真相”时代。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后真相的讨论并不是重要的,甚至后真相的现象也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
事实上,关于新闻真相与新闻生产之间的关系,新闻社会学早期研究的一个重要判断,可谓一针见血:专业机构新闻常规的核心不是关于“新闻的选择性”(selectivity of news),而是“新闻的创造性”(creation of news);新闻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14]当然,新闻虽然是创造出来的,但也不能是编造出来的,新闻实际上是由被挑选的事实加上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unspoken assumption)所组合而成的——比如在西方语境下,工人阶级往往具有冲突性和破坏性,而中产阶级则是理性的、冷静的[15]——或许,自古以来真相就是有前提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即使是专业新闻生产的年代里,真相也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而确定,相对于后真相的那个所谓“前真相”时代,同样不是完全的真实——甚至可以说,两者在新闻真实的范畴内区别并不如人们想象得大。
因此,与其说技术是后真相的形成原因,倒不如说技术是为了解释后真相的一个结果。人们——其实主要是媒体和知识精英——之所以感受到一个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是由于长期的社会分化和族群撕裂所导致的前提的动摇——原本被文化精英牢牢掌握并反复再生产的前提的动摇。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真相话语的本质就是“后共识”,即“当一个社会失去对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共识,观念传达与接受之间就会短路”,人们就只会也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来对不同的事实进行选择和判断。[16]回到后真相话语的流行语境,美国大选、英国脱欧无疑是导火索。在这些所谓的“黑天鹅”事件中,媒体精英和知识分子发现,他们发表的那些权威、客观、可信的事实真相不再被民众认可和接受,而特朗普阵营发表的大量虚假、主观、信口雌黄的“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反而引发了民众的共鸣和狂欢。[17]于是,一场本来应该关于不同前提的社会争辩,在话语上慢慢变成了真相对假新闻的严厉审判,并且掀起了倡导严格地进行事实查验,呼吁民众关注专业媒体,主动屏蔽社交媒体假新闻的运动,来作为解决后真相困境的良方。
如果要透过“谁在使用,又对谁言说”的角度切入探讨后真相话语的文化症候,那么结论或许更有启发性。刘建明认为,后真相话语是由西方知识精英创造出来的,用于解释当代社会民众对于真相的不在乎和所谓共情的热衷。通过知识精英(对民众)的批判,似乎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进入后真相时代是一种必然,强调“阐释”而非“真相”是时代的趋势。后真相的核心不是真相的有无和重要与否,而是“竭力把假象视为真相,歪曲和限制人们对事物真相的追求”。[18]总的来说,后真相话语的陷阱在于制造并强调了“真相/事实”和“情绪/雄辩”之间的对立关系,[19]而缺乏对何为真相的深刻反思。技术虽然并非导致后真相的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对传播关系的重构,将“真相在哪里”的问题摆在了公众面前。后真相所引发的其实不是客观事实的表述是否具有瑕疵,其真问题在于引领我们重新反思新闻真相是如何与另类事实彼此共存的。[20]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在冲破后真相的技术迷思之后,回过头来重新思考一下新闻真相的本来面目。
二、新闻真相:哲学基础与概念分野
(一)哲学基础:从证实与证伪说起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但是新闻真实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总体而言,新闻真实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新闻报道与事实真相的关系问题,即前者是否能够与后者相符合,[21]进而又延伸区分为本质真实/现象真实、宏观真实/微观真实、整体真实/具体真实等概念的讨论。[22]由于新闻真实是关于主体如何反映、再现现实世界的一种认识活动,因此对新闻真实的认识论讨论也是其重要方面。
一般认为,新闻的客观性是新闻真实的认识论原则,然而关于新闻客观性的批评和质疑却又在这一观念诞生的初始就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对于客观性的批评,主要来源于客观事实的复杂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环境要素和新闻生产环节的制约性,这些都导致了认知的片面性、碎片化和动态性。[23]这无疑加深了对新闻真实是否可能的忧虑。
从逻辑学的角度讲,新闻真实本身就是具有认识论意义的概念,新闻真实的使命是实现存在论意义上的事实真相。[24]沿着这一理路,王亦高引入逻辑上的证实和证伪概念对新闻真实进行了讨论,他认为证实的报道实际上是“各个论证环节必须100%齐备才行”,这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因此也很难是“科学的报道”。相反,新闻报道如果能够通过不断证伪,捕捉确凿的事实,即可逐渐达到新闻真实。[25]诚然,证伪概念的引入对于讨论新闻真实的认识论路径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意义。但是,如果同样回到哲学层面深入分析,则会发现证实和证伪在托马斯·库恩所谓的范式意义上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前提假定。[26]在本体论层面,证实和证伪的逻辑在对于社会现实的属性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前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社会现实是由社会中人的思想和实践所构建出来的,不同语境和条件下社会现实的呈现形态和因果关系是多元而相对的;后者则认为社会现实是自然存在的,不受人的思想和实践所影响,是具有普遍性的单一且绝对的现实。在这一基础之上,两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观念,比如“人”的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归纳还是演绎的思维、价值相关或是价值中立等。
在新闻真实的情境中,新闻真相和社会现实具有一致性,新闻真实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与再现。这种一致性不仅表现在理论讨论的争鸣上,也表现在新闻实践的趋势中。近年来,借鉴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闻实践形态逐渐发展出了定性取向的民族志新闻和定量取向的精确新闻两个新兴形态,[27]而这恰好也分别对应了对于新闻真相证实和证伪的两种逻辑。可以说,如果认同新闻真相的“单一现实”属性,那么基于量化数据、遵循证伪逻辑的精确新闻是对长期以来以“讲故事”(story telling)作为呈现真相的新闻实践的反省和补偿,这自然是一类值得称道的尝试。
然而在现实的新闻实践中,我们看到的主流形态仍然是定性的信源采访、内容组织、故事叙述,那么即使暂且不深究其背后“多元现实”的本体论哲学基础,我们是否也应该破除这种新闻真相情境中的新闻真实神话,或者说谦虚地纳入民族志对于语境化和多元性的反思,以求恢复新闻叙述中“被遮蔽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让新闻释放更多平等的意义”。[28]因此,单纯捕捉某些“确凿的事实”来对新闻真实进行证伪,并不是哲学意义上证伪的逻辑。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可证伪性”是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划分标准,但在他的论述中也明确指出,“单个反例证伪”只是怀疑一个命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诉诸其他的在主体间可相互检验的、可复制的事实”,才成为证伪的充分条件。[29](二)概念分野:单一真相与语境真相
而在关于波普尔证伪逻辑的讨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如果命题具有辅助假说集,严格的证伪也不可能,这被称为“迪昂-奎因(Duhem-Quine)命题”。尤其在社会现象的观察中,复杂的社会辅助条件和限定前提假说,使得证伪在实践中成为不可能。[30]可以说,这些社会现实中的辅助假说集就是真相存在的语境。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新闻报道的哲学基础是证实的逻辑,那么就必然要在承认多元现实——新闻真相的相对性——的本体论前提下,强调开展民族志和人类学的语境化反思的重要性。这种根植于一定社会语境的新闻真相,本文将其称之为“语境真相”。
与此同时,是否仍然存在或者需要寻找确定存在的“单一真相”呢?正如波普尔所说,证伪的充分条件在于主体间相互检验的、可复制的事实,这在认识论意义上指的正是“语境真相”,“迪昂-奎因命题”虽然提出了证伪在实践中的不可能,但在逻辑上则是可行的。因此,本文认为在逻辑和形式上保留基于证伪逻辑的单一真相概念仍具有必要性。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证伪和证实分别基于单一现实和多元现实假说,本体论意义上不能同时存在。但是,社会现实究竟是单一现实还是多元现实,这仍然是人类试图要回答的一个终极问题。因而,本文采取认识论上的折中主义原则,认为没有必要将社会现实本体论的争议绝对化,并将其作为一切讨论的前提——这本身也不符合人类认识世界的规律。
类似语境真相的讨论也在当下的学界和业界中有所涉及。近期,美国新闻界正在展开一场辩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新闻是否不应仅满足于关注那些特定情境下的客观事实,而且要根据短期的社会需要来判断究竟什么是真相。[31]上述观点看上去似乎离经叛道:真相怎么可以判断呢?但是,如果考虑语境真相概念中的价值相关性,对客观事实进行价值判断就显得不可避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要获得一个没有争议的单一真相,那么前提条件则必然是社会存在唯一的价值判断。而所谓后真相时代,一方面是技术打破了原本精英垄断的真相呈现权力,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说与社会价值共识的破裂和社会群体的分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寻找新闻真相的本来面目,必须艰难地承认新闻真相本身并没有那么简单或客观。某种意义上说,新闻真相就是建构真相的新闻生产过程,它的目标不是客观地呈现,而是获得社会的信任。作为“与媒体自身的经济、政治诉求相关”的权力机制,[32]新闻生产领域遭遇的后真相挑战,与其说是“假新闻泛滥”、“民粹谣言的流行”,不如说是将原来隐藏在主流媒体真相垄断权背后的信任危机赤裸裸地摆到了公众面前。
2016年以来关于后真相的讨论和反思,往往与假新闻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仿佛只要消除那些主要产生并流传于社交媒体之上的虚假信息,我们就能够重新回到真相时代了。然而,无论从对后真相的话语陷阱分析,还是对新闻真相的哲学辨析和概念分类,我们都不难发现真相这一概念并非简单等同于真新闻或真事实。基于证实/证伪逻辑的语境真相/单一真相的概念框架,丰富了我们对认识论意义上新闻真实的理解,以下本文将对这两个概念以及相关的“事实假象”和“单一假象”概念进行详细的界定和辨析。
三、关于新闻真实的四个认识论概念
沃德(Claire Wardle)按照信息内容是否是事实和生产主体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将假新闻区分为欺骗性信息(dis-information)、误解性信息(mis-information)和误导性信息(mal-information)三类。[33]其中,欺骗性信息基于虚假信息,且有主观恶意;误解性信息基于虚假信息,但无主观恶意;误导性信息基于真实信息,但有主观恶意。杨保军则从更加普遍和概括的层面提出,作为认识论意义上的新闻真实可以分为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而现象真实则有真相真实和假象真实之分,真相因为与本质之间具有同一性,所以真相就是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统一;相对应的,假象真实并不必然就是假新闻,“假象本身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并不是想象物、虚构物”,只是假象真实与本质真实并不一定一致[34]——在这一框架中,没有主观恶意的真实信息,也不一定就是“真相”。
假象真实概念的提出,敏锐地捕捉到了新闻失实现象的复杂性,新闻失实不仅包括没有事实根据的虚假新闻,也包括具有事实根据但与本质真实不一致的现象再现方式。然而,对于什么是与本质真实相一致的“真相真实”,既有的理论框架并未详尽阐述。本质真实反映了本体论层面唯一的真实存在,而真相真实作为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论概念,则可以通过证伪与证实两条路径进行理解和分类,本文认为可以将其区分为“单一真相”和“语境真相”。语境真相,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限制条件下,所呈现出的真相状态。结合假象真实的相关讨论,按照新闻现象与本质真实的符合程度进行分类,那么新闻真实在认识论上就具有四种类型:单一的真相、语境的真相、真相假象相混合但具有事实性存在的假象、单一的假象(表2 表2见本期第35页)。
首先,从哲学基础上来看,“相”与“象”属于对社会现实不同层次的话语表达。“象”是对社会现实客体的呈现,一般不涉及客体间的关系构建,比如基于事实的事实假象即指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而基于非事实的单一假象则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主观塑造;“相”则不仅包括客体的呈现,也包括了逻辑关系的构建。正如上文所述,如果采纳认识论上的折中主义观点,单一真相和语境真相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单一真相是对社会现实的无限逼近,而语境真相则是在一定的“辅助性假说”条件下对社会现象的有机再现,人们期待通过对语境真相的不断发掘,进而逐渐抵达单一真相。实践上来看,完全反映社会现实的单一真相几乎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将不同语境下的真相有机整合,才能逐渐扩大和纠正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知,这也正是“语境真相”概念提出的价值所在。
其次,与本质真实、现象真实的对应关系。单一真相和单一假象是认识论意义上新闻真实的两个极端:单一真相即是完全的真相真实,是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的统一,单一假象是欺骗性信息、误解性信息等不可信信息的组合,它和本质真实一定不一致,属于非真实的范畴。语境真相和事实假象则介于两者之间,本文所称的事实假象等同于假象真实,虽然基于事实性存在,但不一定与本质真实相一致。语境真相则是部分的真相真实,它虽然也与本质真实不一定一致,但是相比于事实假象,语境真相完成了对客体间关系的构建,是相对来说更加逼近完全真相真实的认识论概念。语境真相在经过多元新闻传播主体相互补充、对话协商、通力合作,进而达到“有机真实”,[35]就是一种更加接近本质真实的状态——新闻不是绝对的真或假,很多时候“更真”是一种常态。[36]最后,从信息的容量、来源、组合、框架等角度观察,基于事实性存在的单一真相、语境真相、事实假象都是可信和权威的,相应的单一假象则是来自模糊信源的不可信信息。其中,单一真相由于唯一性——即超越了社会现实中的“辅助性假说”,它必然是包含了“全部的”的可信信息。而语境真相,则是由“全面的”可信信息组成。如何理解此处“全面”的含义?本文认为,此处的“全面”指的即是能够满足该语境真相所处社会语境所要求的可信信息的容量——这正好体现了证实逻辑的要求,即真相的呈现是否具有该语境下的典型性。从操作层面的信息框架来看,事实假象和单一假象由于未涉及关系构建,因而没有框架;单一真相由于反映了完全的真相,因而理应不存在人为影响设置的框架;语境真相是唯一具有某类具体框架的,这类框架完成了对事实的某类组合,继而试图符合所处的社会语境。在新闻实践中,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关于某个具体议题的新闻报道,即使全部基于能够通过事实核查的真实信息,也同样能构建出两个完全相反的故事(语境真相)。[37]
四、结语:后真相之后是什么?
后真相的话语流行虽然具有技术路径解释的偏向性,但是不可否认客观上促进了公共知识对真相的反思。后真相之后是什么?一方面自然是要解决技术赋权导致的虚假信息——即认识论意义上的单一假象的泛滥问题,这方面目前已经讨论较多,比如通过算法技术和人工智能对海量信息进行事实分辨,同时通过用户数据分析来寻找使公众愿意接受准确信息的机制和策略。[38]但是另一方面,语境真相概念的提出,也在操作和实践层面提醒我们,在呈现社会事实的同时,新闻生产的主体也需要同时提供所处的社会语境和价值判断标准。既然新闻记者只能提供“置于某类框架下的现实”,[39]那么对公众进行语境的告知义务,则应当成为新闻传播的伦理要求。
当然,在自媒体等非专业化新闻生产的场景下,新闻传播的伦理要求则显得不具有可行性。那么,对于公众媒介素养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应当成为一条必需的路径。实践已经证明通过关于事实核查的专业知识培训,受众对事实信息的分辨能力就会显著提升,效果远远优于专业和学历的影响,[40]而提升受众关于新闻生产前台和后台的知识认知,那么他们对于信源评价、背景知识、事实核查等方面的信息则会更加关注。[41]总而言之,如果将后真相仅仅归咎于社交媒体导致的假新闻泛滥,解决方案也只局限于对假新闻的纠偏,而不对新闻真实的真正内涵进行全面反思,进而发现语境作为辅助性条件的必然性以及作为告知义务的必要性,那么后真相或许就只能成为漫漫历史中的昙花一现,当代政治和传播活动的真问题也将继续被遮蔽。■
①史安斌、杨云康:《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9期
②Worrall P. 2016. Fact heck: do we really send ?350m a week to Brussels? Channel 4 News. 19 April. Retrieved fro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708115949/http://blogs.channel4.com/factcheck/factcheck-send-350m-week-brussels/22804
③The New Republic. 2016. Donald Trump is not a liar. Retrieved from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24803/donald-trump-not-liar
④The Economist. 2016. Post-truth Politics: Art of the Lie. Retrieved from 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706525-politicians-have-always-lied-does-it-matter-if-they-leave-truth-behind-entirely-art.
⑤Gu L.Kropotov V. & Yarochkin F. (2017). The fake news machine: How propagandists abuse the Internet and manipulate the public. Retrieved from https://documents.trendmicro.com/assets/white_papers/wp-fake-news-machine-how-propagandists-abuse-the-internet.pdf
⑥吴晓明:《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⑦陆学莉:《反转新闻的叙事框架和传播影响》,《新闻记者》2016年第10期
⑧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
⑨Mihailidis P. & Viotty S. (2017). Spreadable spectacle in digital culture: Civic expression, fake news, and the role of media literacies in “post-fact” socie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61(4)441-454.
⑩虞鑫、陈昌凤:《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生产逻辑与效果困境》,《新闻大学》2016年第4期
[11]Guess A.Nyhan B. & Reifler J. (2018). Selective exposure to misinform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onsumption of fake news during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Retrieved from http://www.dartmouth.edu/~nyhan/fake-news-2016.pdf
[12]Lewandowsky S.Ecker U.K.H.Seifert C.Schwarz N. & Cook J. (2012). Misinformation and its correction: Continued influence and successful debias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13(3)106-131.
[13]Nyhan B. & Reifler.J. (2010). 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 Political Behavior, 32(2)303-330.
[14]李红涛:《黄金年代的“十字路路口”:〈生产新闻〉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崛起》,《中国传媒报告》2013年第4期
[15]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1980). Bad New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6]汪行福:《“后真相”本质上是后共识》,《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17]史安斌、周迦昕:《“川普”奇观与美国政治新闻的困境》,《青年记者》2016年第4期
[18]刘建明:《“后真相”论的执迷与幻觉》,《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12期
[19]刘擎:《共享视角的瓦解与后真相政治的困境》,《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20]Lewandowsky S.Ecker U.K.H. & Cook J. (2017). Beyond mis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and coping with the post-truth era.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6(4)353-369.
[21]杨保军:《如何理解新闻真实论中所讲的“符合”》,《国际新闻界》2008第5期
[22]郑保卫:《对新闻真实理论中两组概念的解读》,《新闻战线》2007年第6期
[23]杨保军:《新闻真实需要回到“再现真实”》,《新闻记者》2016年第9期
[24]杨保军:《事实·真相·真实——对新闻真实论中三个关键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新闻记者》2008年第6期
[25]王亦高:《试论新闻报道中的“证伪”》,《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2期
[26]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75-83页,傅大为、程树德等译,台湾允晨文化1985年版
[27]黄淑敏:《新闻报道在借鉴社会科学方法中应把握的原则》,《新闻爱好者》2015年第4期
[28]孙起:《瞬间现象与田野传统:民族志新闻的意义与前提》,《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7期
[29]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第73-74页,查汝强、邱仁宗译,沈阳出版社1999年版
[30]张杨:《证伪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吗?》,《社会学研究》2007第3期
[31]McNair B. (2017). After objectivity? Schudson’s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in the era of post-factuality. Journalism Studies18(10)1318-1333.
[32]王辉:《瞬间与无限:新闻真实的两种理解方式》,《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2期
[33] Wardle C. & Derakhshan H. (2017). Information disorder: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making. Retrieved from https://firstdraftnews.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PREMS-162317-GBR-2018-Report-de%CC%81sinformation-1.pdf?x69924
[34]杨保军:《简论新闻的真相真实与假象真实》,《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
[35]杨保军:《新媒介环境下新闻真实论视野中的几个新问题》,《新闻记者》2014年第10期
[36]操瑞青:《作为假设的“新闻真实”:新闻报道的“知识合法性”建构》,《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5期
[37]Boussalis C. & Coan T.G. (2016). Text-mining the signals of climate change doubt.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3689-100.
[38]Albright J. (2017). Welcome to the era of fake new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5(2)87-89.
[39]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的真实面孔——如何在“后真相”时代寻找“真新闻”》,《新闻记者》2017年第5期
[40]Wineburg S. and McGrew S. (2017). Lateral reading: Reading less and learning more when evaluating digital information. Stanford History Education Group Working Paper No. 2017-A1 . Retrieved from https://ssrn.com/abstract=3048994
[41]Himma-Kadakas M. (2017). Alternative facts and fake news entering journalistic content production cycle. Cosmopolitan Civil Societ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9(2)25-40.
虞鑫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