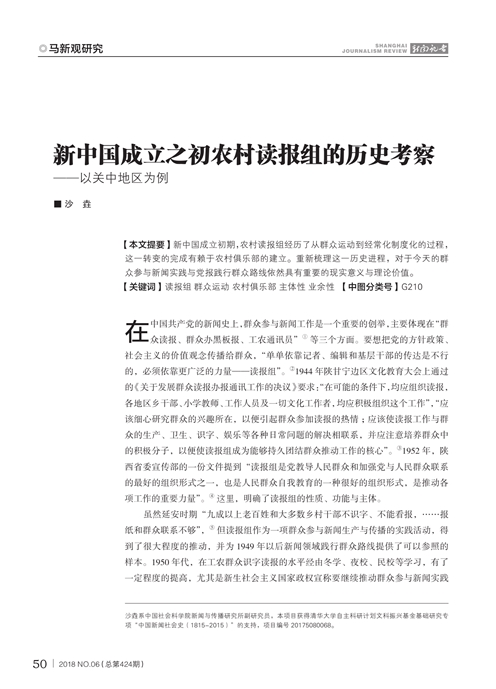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读报组的历史考察
——以关中地区为例
■沙垚
【本文提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读报组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到经常化制度化的过程,这一转变的完成有赖于农村俱乐部的建立。重新梳理这一历史进程,对于今天的群众参与新闻实践与党报践行群众路线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关键词】读报组 群众运动 农村俱乐部 主体性 业余性
【中图分类号】G210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上,群众参与新闻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创举,主要体现在“群众读报、群众办黑板报、工农通讯员” ①等三个方面。要想把党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传播给群众,“单单依靠记者、编辑和基层干部的传达是不行的,必须依靠更广泛的力量——读报组”。②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通讯工作的决议》要求:“在可能的条件下,均应组织读报,各地区乡干部、小学教师、工作人员及一切文化工作者,均应积极组织这个工作”,“应该细心研究群众的兴趣所在,以便引起群众参加读报的热情;应该使读报工作与群众的生产、卫生、识字、娱乐等各种日常问题的解决相联系,并应注意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以便使读报组成为能够持久团结群众推动工作的核心”。③1952年,陕西省委宣传部的一份文件提到“读报组是党教导人民群众和加强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之一,也是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是推动各项工作的重要力量”。④这里,明确了读报组的性质、功能与主体。
虽然延安时期“九成以上老百姓和大多数乡村干部不识字、不能看报,……报纸和群众联系不够”,⑤但读报组作为一项群众参与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实践活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动,并为1949年以后新闻领域践行群众路线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样本。1950年代,在工农群众识字读报的水平经由冬学、夜校、民校等学习,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尤其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宣称要继续推动群众参与新闻实践的大背景下,读报组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新面貌?从中我们又能提炼出哪些经验与特征,用于指导今天的新闻生产与实践?
聚焦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读报组,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依据历史档案,同时辅以深度访谈。笔者分别于2012年8月赴西安市档案馆、2013年1月赴陕西省档案馆、2013年8月赴渭南市档案馆查询档案,由此获得大量的一手资料、田野笔记和档案资料。为了更为清晰地还原彼时的群众参与新闻实践,笔者还开展了一些访谈,以便建构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中农村读报组活动的全面认知。
一、1950年代初读报组的建立
陕西省的农村读报组是从1950年7月开始建立的,截至1952年6月底,据陕西省委宣传部不完全统计,全省已经建立起7.559万多个读报组。参加的人数已达142.63万多名,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0%以上。⑥这些读报组对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都起到了巨大而积极的作用。“读报组的兴旺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基层社会生机勃勃,组织化程度很高”。⑦那么,它们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读报组是哪些人在读,又为什么愿意读?答案是“农村知识分子和识字农民”。⑧根据1952年对渭南专区蓝田县六区二乡、宝鸡专区宝鸡县鸡峰区五乡和咸阳专区淳化县铁王区秦家河乡的调查,这三个乡每村均有3-4个知识分子或识字农民。⑨这个数字在1950年代初的关中农村是较为普遍的。要把这些人动员起来,加强思想教育,“使他们认识读报工作是一项光荣任务,能够任劳任怨、不计报酬,踏实负责地工作”。⑩同时,物色一些成分好、热情积极的知识分子加以培养,培养的办法,一是吸收他们参加速成识字师资训练及积极分子训练班,二是由完、普小教员巡回指导,就地培养。以这种方式不断扩大读报员的队伍。
读报就需要有报纸,1950年代初农村百废待兴,订报的钱从哪里来?初期各地多半是读报组的组员们平均摊派,这种方法不可持续,必然会有人不愿意,进而导致报费收不起来,有不少读报组也就因此解散了。但同时,各级宣传部门又三令五申,一遍遍号召动员建立读报组,怎么办?实践中,人民群众探索出如下解决办法:(1)各村制定增产计划,将增产的粮食拿出一部分订报;(2)有荒山的地区,全体村民一起去开垦一块荒地,将所生产的粮食拿出来订报;(3)全村集体搞副业生产一次,如卖柴、贩炭、割麦、打场等,或抽一个人去搞几次副业生产,其他村民予以辅工,将生产所得利润或工资,拿来订报;(4)每个组多喂一只鸡,将鸡蛋卖的钱订报。[11]无论是垦荒、卖柴、贩炭,还是养鸡都属于临时性的措施,对个人的热情与积极性依赖程度较高。但不管怎样,在1952年的时代背景下,它们确实解决了订报费的问题。
可是,偏远地区怎么办?有些农村交通不便,邮局直接寄不到。一般来说,只能送到县里,县里又经过区、乡两级政府转给农村读报组,有时转得遗失了,有时压下几十天还转不到。时间长了转一次就是厚厚一沓,群众又一下没时间看完,于是就觉得“不如买个书本本方便”,不愿意订报了。一些读报组也就因此解散了,还有的流于形式,不能经常读报。为此,一些县区由宣传部牵头,积极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如兴平县委宣传部与邮局协同在全县建立了3个大邮圈19个发行站和11个代办所,开通邮路,使报纸能迅速直接送到群众手里,1952年全县已经有70个乡能够看到当日的报纸。再比如周至县组织农村通讯网,从区到乡直至村都建立了报纸宣传站,由群众选出传讯员转送,传讯员所花费的劳力,用记工算账的办法,由全体组员帮助他生产或代他参加公共劳动等来补偿,这样,该县45个乡就有28个乡能看到当天的报纸,路较远的17个乡也可以看到前一天的报纸。[12]还有某些山区农村,人口分散、地区辽阔,有些村庄只住两三户人家,村与村距离很远,要把几个村的人合起来组织一个读报组,事实上办不到,若一个村单设一个组,又没有识字的人。对此,陕西省宣传部要求:首先,凡是到这些地区去工作的干部,都必须随身带报纸,人到哪儿,报到哪儿,见了群众就念就讲;其次,先在有识字人的村庄建立读报组,先找到识字的人,经过宣传教育取得本人同意,教给他读报的方法,然后把村里的人组织起来成为一组;最后,选择有积极性的读报组长或读报员,划分区域,分工负责,定期抽空到没有识字人的村子读报,即“流动读报员”。[13]
二、以群众运动的思路组建读报组
“群众运动是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非常规政治手段,具有常规行政手段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可以帮助党和国家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实现乡村治理”。[14]群众运动的策略和模式,一般认为包括:“启蒙与唤醒,以政治号召争取群众”;“组织及组织化生活,构筑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物质基础”;“实际运作中前紧后松,存在矫枉过正的动机”,[15]等等。爬梳史料可以发现,1950年代初关中农村读报组主要是按照群众运动的思路进行的。
成立读报组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宣传部门。1950年起,陕西省宣传部一面责成各级党委宣传部大力建立读报组,一面搞试点,在华县结合土地改革大量发展读报组,两三个月中即建立起650多个组。“国家的在场”与“党政干部的大力支持”是读报组得以普遍建立的重要原因。哪里的党政干部重视和推动此项工作,哪里的读报组就能得到迅速发展。如临潼县的干部重视,1952年全县已有读报组1433个,2.8万多人参加读报,占10岁以上人口的62%。平均每个自然村有4个组。[16]不仅如此,村、社干部的重视和支持也很重要,因为读报员没有行政权,安排读报时间和召集农民听报等,都必须通过干部,只靠读报员自己很难召集起来。
如果说政治的推动和干部的支持是农村读报组成立的前提,那么广泛发动群众参与读报活动便是关键,这里的“群众”包括两类群体,读报员和听报农民。
激励机制是发动读报员的主要措施。既包括物质上的,比如通过发动群众适当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给工作成绩好、受到群众欢迎的读报员以适当的物质奖励。还包括精神上的,比如1952年七一节,由省委宣传部、省人民政府文教厅、陕西日报社联名奖励了4个模范读报单位和15名模范工作者和读报员,起到了“奖励模范,树立旗帜”的作用。总之,通过团结教育、培养辅导和激励机制,确实有效地推动了农村读报组的发展。比如淳化县秦家河乡白堡村到1952年9月,就组织了读报组36个,听众约700余人,发展宣传员47名并伴有黑板报30块,广播筒15个。[17]更重要的工作是让农民广泛参与。除了上级宣传部门和党政领导的动员之外,“社会大讨论”是另一个有效方式。比如《陕西日报》1951年7月组织各地农民以读报组的方式发起了“雷昌恩发家走的哪条路?”的讨论,以此为依托,仅长安、富平等五个县即有5000多个读报组参加了讨论。估计全省参加讨论的,约有两万多个组。群众来信说,他们“思想上对读报组的重要性有了明确的认识,懂得了建立与巩固读报组的方法”,“深深感觉参加模范读报组的好处”,并都表示“下定决心把读报组工作搞好”。[18]群众运动过程中常见的“政治主导”、“组织推动”、“激励动员”、“社会大讨论”等思路和措施在这里均可见到。不仅如此,1950年代初农村读报组实践还呈现出一拥而上、前紧后松、流于形式等特点。
由于各级宣传部门缺乏经验,也未能及时动员,很多农村地区的干部、群众对读报组缺乏了解,读报组发展得很慢,1950年初全省才1900多个读报组。至1950年底,宣传部门采取了上述措施,找到了读报员,获得了地方党政干部的支持,进行了广泛的组织动员,到1951年七一,新增2.02万多个读报组,到1952年6月底,又新增5.55万多个,达7.559万多个读报组。[19]但由于发展过快,各地将建立读报组视作政治任务去完成,比如佛坪县三分之二的读报组流于形式,不能经常读报。[20]宝鸡鸡峰区五乡把35岁以上的人都编入读报组,每组有六七十人之多。读报时哄哄一堂,你说他笑,[21]收效甚微。还有些地方读完之后就算完事,不进行讨论,所学的知识不用在生产上。因此到1952年8月中旬,省委在各地委宣传部长和报社社长联席会上确定,下半年起,读报组的工作任务调整为“整顿,使不巩固的能够巩固起来,并在巩固的基础上逐渐提高。到明年(1953年)春季,再根据整顿情况,来确定新的发展计划”。[22]当读报组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更多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一)在形式与内容层面,主要是自上而下地宣传党的政策与意识形态,文件里不断强调要结合农村实际,这也恰恰说明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结合村情民情;换言之,读报内容是外来的,与农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没有更多的互动,甚至连读报这一宣传的形式都是新的,农民一下子能不能接受和喜爱?(二)虽然群众被动员起来了,成立了很多读报组,也探索了解决经费的途径,但是动员之后怎么办?并没有确立一个长效机制保障读报组的运行。换言之,在1950年代初,农村读报组并没有深度嵌入社会结构,而是以群众性运动的形式漂浮于社会结构之上。(三)团结和培养一批农民知识分子,既识字又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服务意识,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各地均未有意识地采取各种办法对农村识字的农民加以培养” [23]的现象大有存在。
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人民群众。对政党或国家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不能被群众理解和支持,不能深入人心,将很难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更罔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对农民群众来说,他们感受到了新的文化和新的气象,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生活的逐步改善,他们对文化娱乐、科学知识和思想教育都表达出了更高的诉求。无疑,读报组是一个可以深入农村,让群众参与,教育群众,并实现群众自我教育的有效方式。只是,读报组活动的经常性如何保证?
三、农村俱乐部:读报组的经常化与制度化
一份关于农村读报组的调查报告提到要“使读报工作做到经常化制度化”,[24]如何做到?这需要从1950年代中期的农村俱乐部说起。
1955年4月陕西省召开了第一届文化行政会议,要求各地农村文化馆、站逐步把主要力量转向组织和辅导俱乐部工作。[25]因为农村合作化事业迅速发展,给农村文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要“大力发展农村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综合性的组织——俱乐部”。[26]1956年,西安市计划建立农村俱乐部564个,咸阳市18个,咸阳县323个,鄠县321个,长安县768个,铜川县270个,渭南专区7382个,宝鸡专区7235个。[27]事实上,截至1957年1月,陕西省83个县、市,建立了1.3211万个农村俱乐部。[28]什么是农村俱乐部?《关于发展和提高农村俱乐部的初步意见》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农村俱乐部是在合作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进步的、高级的农村业余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是党和政府在农村开展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重要阵地,是鼓舞农民生产热情、推动中心工作的有力工具,是活跃农民文化生活,以健康的文化休息代替不正当娱乐的良好场所。由于它是群众自己办的,而且是包括各种文化艺术形式的综合的组织,所以最受群众欢迎,也能够充分发挥劳动人民在文化艺术上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同时,它能够紧密地结合生产,为群众服务,也便于政府和文化部门进行思想指导和业务辅导。” [29]俱乐部不是临时的群众活动小组,而是伴随在农村合作化过程中产生的综合性的文化常设机构。成立俱乐部是纳入县、区、乡的“文化工作规划”和“合作化全面规划”的,是“农村干部经常的领导工作之一”,要“经社管委员会批准,报乡人民委员会备案”。[30]俱乐部设立文艺宣传股,包括创编工作、幻灯放映、业余剧团、收音广播、黑板报、读报组等;社会教育股,包括图书室、民校、识字组、讲座会等;科技推广股,包括农业科学技术和卫生的普及宣传,推广自然改造经验等;体育活动股,包括军事体操、各种球类运动等。同时还要求“分设各股”要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不能大而全。[31]俱乐部在农业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通过选举组成俱乐部委员会,统一领导俱乐部活动,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委员4人(委员人选中有村主任、两个农业社主任、团支部书记、村社文教委员、村妇女主任)。每股设正副组长各1人,各项具体工作都有1-3人负责。显然,读报组是农村俱乐部的一个常态化与制度化的内设机构。自1955年起,读报组被纳入国家文化体制,成为最基层的开展业务的活动单位。
因此,可以认为农村俱乐部的建立是农村读报组从群众运动走向制度化的关键一步。
农村俱乐部是“农村业余文化活动的一种综合形式,把农村各种单一性的、分散的文化艺术活动,联合起来便于进行辅导和统一领导”。[32]换言之,农村俱乐部是农村文化资源的总动员,为农村文化和新闻宣传活动搭建了一个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趋势:第一,读报组不再孤军奋战,它有很多合作伙伴,比如秧歌、戏剧、快板、说书、广播、板报、幻灯、讲座等等,这里既有农村传统的文化形态,农村的风俗习惯和民间文化被尊重了,也有报刊、广播、幻灯、电影等新的媒体形态,两者通力合作,有机融合,共同服务于农民的生产生活与社会主义建设。第二,读报组已经抵达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维度,成为一种仪式。读报活动能结合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配合农村中心工作,读报与入社结合起来,通过读报的方式团结社外群众,让社外群众对合作社产生感情,并向往社内群众的文化生活,从而更接近和积极要求入社;反过来,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社壮大了,也就更能保障读报组的经常性运转。同时,也更注重根据群众不同年龄、性别和兴趣来组织读报内容,采取“一读二讲三讨论”的方法,让听报群众更好地领会文章精神、学到知识,同时注意坚持业余原则,读报不耽误生产。
每个大队、生产队都会订阅报纸,一般来说大队的报纸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生产队订阅省一级的《陕西日报》、《陕西农民报》和《陕西科技报》。报纸直接送到大队长和生产队长家中,队长看完之后放在办公室,让普通社员阅览。但社员一般不会主动去阅读报纸,经常到生产队办公室看报的人是固定的一小批积极分子。……到了晚上,还要读报政治学习。开队会一般是隔几天或者十几天,要把贫农代表叫上,他代表贫下中农的意见,和现在的人大代表很像。开会时,生产队长要召集全队人一起学习,大家自己带上小板凳,主要学习报纸社论。队长常常去公社开会,开完会回来就在生产队的会议上传达上级精神,主要形式是队长宣读。[33]大跃进的时候,村里安装了几个喇叭,水井房一个,生产队两间办公室的门外空场上一个,还有其他公共场所一个。在每天早晨起床以及吃饭的时候,大喇叭就响了,转播收音机的新闻和文艺节目。[34]由此可以看出,读报活动已经融入生产队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去了,即便没有读报员,读报也会由生产队长完成,且作为政治学习的日常仪式。而且,读报不仅有现场宣读、讲解的方式,还会通过村里的大喇叭、收音广播等方式进行传播。通过夜晚开会读报和早晨广播报新闻,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图景勾勒尽显。在1956年前后,关中农村读报组用实践探索出一条从群众运动到制度化、常态化的运行模式,将读报组纳入国家文化体制,成为合作化运动进程中文化领域的标准配置,有固定的组长和机构设置,如此,读报组开展活动就有了制度保障。同时,读报不是可有可无的临时活动,而是定期举行的日常仪式,其内容也与农村彼时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有时甚至能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推动社会发展。
某种程度上,1950年代中期农村俱乐部和读报组的实践对群众运动的成果“难以制度化、常规化,只能以接连不断的新运动来维系,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解的矛盾” [35]这一重要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四、余论:读报组的当代意义
在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史中,“读报组”留下了浓重的一笔。“重新梳理和思考读报组的发展历程,对于思考在社会急剧转型、各种矛盾交织的今天,党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36]从新闻史的角度,可以梳理出1950年代农村读报组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到制度化常态化的转变;在理论层面,则对今天媒介中心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路径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思考。
首先,常态化不仅需要制度的保障,更需要人的主体性。读报组实践启发我们乡村媒介活动当以群众为主体,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社会建设,不仅能践行群众路线,而且能化解社会矛盾,还能激发潜藏在社会深处的正能量和价值感。
比如,1950年代长安县东祝村读报员常常把报纸带到田间,利用休息时间阅读,还把破屋子改造成了图书室,4个识字青年义务担任管理员,建成“屋顶广播”,每周二、四、六晚上轮流播讲国内外大事和村里的生产情况,还有黑板报、漫画,每周一期……[37]如果没有一定的主体性觉悟,仅仅靠群众运动式的动员,是很难做到的。青年读报员不是照本宣科地读报,而是有情感、有温度,以问题为导向,读报方式讲究灵活多样,他们“避免平铺直叙地念文件,结合讲解,视内容篇幅的不同,采取边读边讲,先读后讲,对篇幅过长的只讲大意,不读全文。讲解时结合实际,有鼓动气氛,启发群众共鸣。当群众在听讲中纷纷议论时,就顺势引导讨论,不必勉强再读下去,对尚未读到的精神,则结合讨论进行补叙”。[38]比如,在读秋收秋播相关的文章时,刘家岭大队的读报员就引导群众逐项排查各项准备工作,引发群众热烈讨论,他们发现大队在种子、库房、牲畜、场地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队长听到这些意见,当晚就召开队委会,落实各项工作。
广播有广播员、报纸有读报员、电影有放映员,他们的身份都是农民。他们以人为媒介,把内部的、外部的故事内容和传统的、现代的媒介形态都整合起来,嵌入农村社会结构之中,共同服务于1950年代的农村社会转型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很难想象,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没有这样一支“指挥自如、训练有素、且能广泛深入民间的群众性宣教队伍,那么各项政策的上传下达还能否进行得如此顺利”。[39]通过俱乐部和读报组,在1950年代的农村新闻传播与文化实践中,农民获得了与其政治经济身份相匹配的文化身份,以文化主体的身份登上了社会和历史舞台,在这里农民自己“创造了一个可供自我认同的崭新的农民主体形象”。[40]以史为鉴我们也可以反思,当代媒介抵达乡村社会,是否还有这样的深度,是否还有这样的结构性互动,是否还能够调动起群众广泛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其次,读报组践行的是一种群众广泛参与的、业余的新闻生产模式,这与新闻专业主义截然不同。读报组实践中,人是业余的,读报员不是记者、编辑,甚至连通讯员都不是,而且识字水平比较有限,主要是热情和信念支撑他们完成这项工作,而不是专业主义,他们的主业是农业生产劳动;读报的时间、地点也都是临时的,他们经常是在田间地头,利用农民劳作的休息时间读报,有的地方规定,读报只能占劳动休息时间的三分之一;或者是在晚上政治学习和生产大会之前,群众陆陆续续到来,但尚未到齐的空隙中读报……
但正是这种业余的方式推动了社会转型发展和行业制度的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这启发我们思考:专业主义的发展路径是不是人类社会或文化发展的唯一路径,是否存在另外的可能性?业余,因其不是主业,就不会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保证了文化传播活动的相对纯粹性,以及区别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独立性;业余,挑战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日益分野,以及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缺乏交流沟通的现实的社会结构,重返马克思“生产者联盟”或“劳动者联盟”。至少在1950年代,读报组建立了农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于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沟通机制。也在某种程度实现了马克思所期望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41]在这里猎人、渔夫、牧人和谈判者、诗人的身份是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实现统一的。如同在读报组,很难说一个人是读报员、通讯员,亦或是农民,因为其身份是多重的,又是统一的。
所以,业余性在某种程度上重启了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白领、中产阶级与工人、农民相联结、并进而有机统一的进程,成为一个模糊的中间地带,传播即联结,可赋予日益僵化的社会结构更多的“可沟通性”。■
①李文:《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黑板报》,《新闻知识》2008年第3期
②李文、王兆屹:《看延安〈群众〉周报如何贴近群众——一段不该遗忘的党报传统》,《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4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168-169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④《两年来建立读报组的基本情况及经验》,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81
⑤李卓然:《文教大会上李卓然同志总结报告边区报纸成为群众事业》,《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0日
⑥《两年来建立读报组的基本情况及经验》,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81
⑦李海波:《新闻公共性、专业性与有机性——以“民主之春”、延安时期新闻实践为例》,《新闻大学》2017年第4期
⑧《关于农民文化政治学习的情况与会议意见》,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81
⑨《关于农民文化政治学习的情况与会议意见》,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81
⑩《西乡县板桥公社刘家岭大队建立读报组的调查报告》,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232,永久,案卷号444
[11]《两年来建立读报组的基本情况及经验》,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81
[12]《两年来建立读报组的基本情况及经验》,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81
[13]《两年来建立读报组的基本情况及经验》,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81
[14]李里峰:《群众运动与乡村治理——1945-1976年中国基层社会的一个解释框架》,《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5]叶青:《论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运动模式的运作》,《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6]《两年来建立读报组的基本情况及经验》,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81
[17]《关于农民文化政治学习的情况与会议意见》,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81
[18]《两年来建立读报组的基本情况及经验》,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81
[19]《两年来建立读报组的基本情况及经验》,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81
[20]《两年来建立读报组的基本情况及经验》,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81
[21]《关于农民文化政治学习的情况与会议意见》,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81
[22]《两年来建立读报组的基本情况及经验》,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81
[23]《关于农民文化政治学习的情况与会议意见》,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81
[24]《西堡障大队是怎样开展订报活动和队队建立读报组的》,渭南市档案馆,全宗号J001,长期,案卷号1073
[25]《加强对农村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领导,大力发展农村俱乐部》,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232,永久,案卷号8
[26]《陕西省1956年至1957年农村文化工作计划》,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232,永久,案卷号17
[27]《陕西省1956年至1957年农村文化工作计划》,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232,永久,案卷号17
[28]《1956年工作总结和1957年文化工作计划》,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232,永久,案卷号45
[29]《关于发展和提高农村俱乐部的初步意见》,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232,永久,案卷号17
[30]《关于发展和提高农村俱乐部的初步意见》,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232,永久,案卷号1.
[31]《关于发展和提高农村俱乐部的初步意见》,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232,永久,案卷号17
[32]《关于发展和提高农村俱乐部的初步意见》,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232,永久,案卷号17
[33]访谈:颜生文,2008年7月27日。颜生文,曾长期担任吕塬大队书记,刘塬生产队隶属吕塬大队。
[34]访谈:刘兴文,2008年7月27日。刘兴文,刘塬生产队业余剧团艺人,为1950年代识字农民青年。
[35]李里峰:《群众运动与乡村治理——1945-1976年中国基层社会的一个解释框架》,《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36]王晓梅:《建国初党报领导下的“读报组”发展探析——以建国初〈解放日报〉“读报组”发展为基本脉络》,《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6期
[37]《长安县东祝村农村俱乐部是怎样办起来的》,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232,永久,案卷号8
[38]《西乡县板桥公社刘家岭大队建立读报组的调查报告》,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232,永久,案卷号444
[39]张炼红:《历练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革考论》第3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0]倪伟:《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释读》,载罗小茗主编:《制造“国民”:1950-10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第26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沙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本项目获得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振兴基金基础研究专项“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15)”的支持,项目编号2017508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