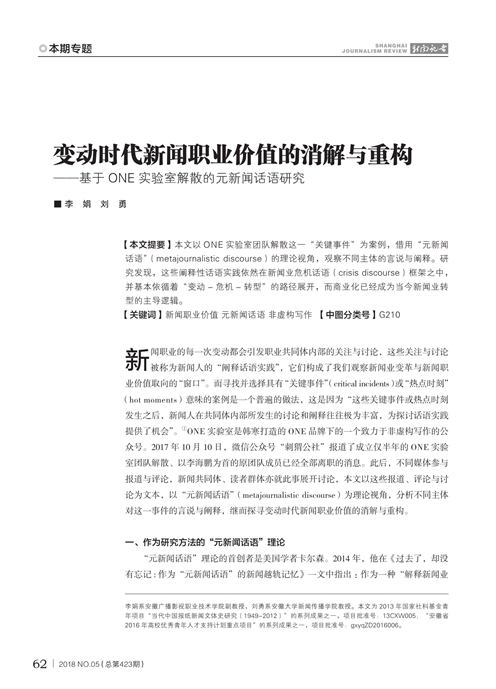变动时代新闻职业价值的消解与重构
——基于ONE实验室解散的元新闻话语研究
■李娟 刘勇
【本文提要】本文以ONE实验室团队解散这一“关键事件”为案例,借用“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的理论视角,观察不同主体的言说与阐释。研究发现,这些阐释性话语实践依然在新闻业危机话语(crisis discourse)框架之中,并基本依循着“变动-危机-转型”的路径展开,而商业化已经成为当今新闻业转型的主导逻辑。
【关键词】新闻职业价值 元新闻话语 非虚构写作
【中图分类号】G210
新闻职业的每一次变动都会引发职业共同体内部的关注与讨论,这些关注与讨论被称为新闻人的“阐释话语实践”,它们构成了我们观察新闻业变革与新闻职业价值取向的“窗口”。而寻找并选择具有“关键事件”(critical incidents)或“热点时刻”(hot moments)意味的案例是一个普遍的做法,这是因为“这些关键事件或热点时刻发生之后,新闻人在共同体内部所发生的讨论和阐释往往极为丰富,为探讨话语实践提供了机会”。①ONE实验室是韩寒打造的ONE品牌下的一个致力于非虚构写作的公众号。2017年10月10日,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报道了成立仅半年的ONE实验室团队解散、以李海鹏为首的原团队成员已经全部离职的消息。此后,不同媒体参与报道与评论,新闻共同体、读者群体亦就此事展开讨论,本文以这些报道、评论与讨论为文本,以“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为理论视角,分析不同主体对这一事件的言说与阐释,继而探寻变动时代新闻职业价值的消解与重构。
一、作为研究方法的“元新闻话语”理论
“元新闻话语”理论的首创者是美国学者卡尔森。2014年,他在《过去了,却没有忘记:作为“元新闻话语”的新闻越轨记忆》一文中指出:作为一种“解释新闻业变动意义的理论”,“元新闻话语”在两个维度上界定了新闻业:其一是“寻求建立对可接受实践与行为边界的控制”;其二是“寻求对新闻权威的控制”。有鉴于此,“‘元新闻话语’应该被视为定义新闻业变动的一种永久的阐释性实践”。②2016年,卡尔森再度撰文《元新闻话语与新闻业的意义:定义控制、边界工作与合法性》,将“元新闻话语”视为“一个综合研究行动者如何协商记者作为新闻事件合法记录者的文化权威的分析概念”,继而全面阐释了“元新闻话语”理论。他首先将新闻业视为一种“依赖语境、通过社会关系进行生产”的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元新闻话语”就是“对新闻文本、生产这些文本的实践和接受这些文本的条件所展开的公共表达”,它将“行动者(actors)、实践场所/受众(sites/audiences)、主题(topic)”三个要素连接到“建构定义、设定工作边界和判定新闻业合法性的过程之中”。藉此,“新闻业内外各种行动者展开竞争,建构、重申甚至挑战新闻实践的边界与极限”。③换言之,“元新闻话语”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透镜(conceptual lens)”,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不同行动者对于新闻业的含蓄断言和明确争论”。④有鉴于此,除了新闻越轨、媒介记忆、初创新闻公司宣言之外,近年来,西方学术界还运用“元新闻话语”理论在超链接、⑤接近权⑥等方面展开研究。
国内研究者引入美国学者芭比·泽利泽“阐释的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⑦概念,将记者视为“阐释的共同体”——记者不仅通过新闻报道中的叙事,而且通过对其新闻实践活动的叙事来建构职业权威。2014年以来,这类研究逐渐增多,研究者往往会寻找某一“关键事件”或“热点时刻”,通过观察新闻人围绕某一具体报道个案、个体职业经验以及新闻业的公共话题所进行的“自我言说”(譬如集体记忆叙事、新闻人离职或逝世的纪念话语、知名媒体新年献词叙事话语、新闻专业主义阐释话语等),来反观新闻职业权威与新闻职业价值的建构。⑧受此启发,本文亦从这个角度来使用“元新闻话语”,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当下中国的社会脉络中,新闻业如何建构关于自身的话语,又是如何被其他社会实体进行建构的,以及这种建构将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 ⑨
二、作为内容生产者转型标杆的ONE实验室
ONE实验室解散之所以能够成为“关键事件”并引发广泛讨论,是因为其“特稿作者–内容–影视”的运作模式,从一开始就在国内非虚构内容产业确立了标杆地位。
一方面,ONE实验室拥有一支优秀的特稿写作团队。除了“最会写特稿的两个男人”李海鹏和林天宏外,ONE实验室还集结了数十位国内非虚构写作领域的一流作者,他们都有在《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南方人物周刊》、《人物》、《时尚先生》等专业媒体的从业经历,都有为其带来专业名声的代表作。譬如,《少年杀母事件》与《黑帮教父的最后敌人》的作者林珊珊、《太平洋大逃杀》与《生死巴丹吉林》的作者杜强、《大兴安岭杀人事件》的作者魏玲、《北京零点后》的作者王天挺等。由此,这一组合亦被业界称为“特稿梦之队”。林天宏就曾自信满满地说:“在生产真实故事的领域,如果ONE实验室这帮人说在国内排第二,恐怕也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吧。” ⑩
另一方面,ONE实验室拥有一套专业的采编标准和变现模式。“信仰手艺,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是ONE实验室的公开标识。除了采访、写作与编辑的标准更加专业与严苛外,ONE实验室还是国内首个设立事实核查岗位的媒体,其发布的所有作品均经过事实核查。“ONE实验室的每一个稿子都有讨论小组。在小组里,事实核查员、记者和编辑会一起讨论稿件的选题、走向和角度等问题”。[11]由此,专业化的精耕细作,成为ONE实验室的一个重要标签。此外,与影视对接的变现模式,也使ONE实验室在业内独树一帜。李海鹏将这个变现模式归纳为一个简单的公式:(IP+原著作者+演员+宣发)×故事。[12]上述优势不仅使ONE实验室被建构为新闻界的一个“神话”,也令时时处于“变动–危机–转型”话语框架中的传统新闻人看到了希望。“非虚构写作”从2010年开始崛起,此后伴随多篇作品的影视改编权被高价出售,大量新媒体非虚构写作平台被搭建,传统“特稿”被更名,“非虚构写作”遂被看作新闻人转型、创业的新契机。李海鹏在ONE实验室上线当天发布了一条“宣言式”微博:“希望我们是最职业的,成绩最好的,信仰手艺的,不忘记责任的,在一片灰暗中闪光的。” [13] “最职业”、“信仰”、“手艺”、“责任”、“闪光”等关键词,既是对ONE实验室职业化定位的宣示,也是对其职业权威的话语建构。对于传统内容生产者而言,这更是对新闻职业价值与新闻人尊严的召唤。从这个意义上说,ONE实验室重申了内容生产的价值,寄托了新闻从业者的诸多希望与期待,比如新媒体转型、内容创业乃至新闻职业价值的重估等等。因此,ONE实验室解散的消息甫一爆出,就成了新闻界的“热点时刻”,为新闻职业共同体、社会公众均提供了一个“集体言说”的机会,各方据此所进行的讨论与分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照新闻业变动、新闻人转型的重要机会。
三、不同主体对ONE实验室解散事件的言说与阐释
面对ONE实验室的解散,结合既有的报道、评论以及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各方的回应与阐释,我们将叙事主体分为三种:ONE实验室成员、同行、读者。
(一)ONE实验室成员
一般而言,团队解散、媒体停摆,当事媒体都要发表声明,作出解释,恰如报纸停刊,往往都会在最后一期制作“告别特刊”。但是在本次事件中,ONE实验室并未作出任何说明,其微信公号发布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太平洋大逃杀〉之后,ONE实验室作品〈生死巴丹吉林〉也将改编成电影了》,之后遂停留在2017年7月20日再无更新。倒是ONE实验室的三位核心成员发表的“告别话语”,呈现出较大的张力。已有不少研究者将离职记者的话语实践视为一种“告别叙事”(goodbye narratives),从中探察记者在离职之时对其所处媒体、职业、时代的认知与阐释。Spaulding认为,“怀旧”是“告别叙事”中的主要内容与基调。[14]白红义则发现《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停刊时,两报员工的“告别叙事”涉及个人、组织及行业不同层面,从而“将新闻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勾连起来”。[15]2017年10月10日,“刺猬公社”率先发布《ONE实验室解散,“特稿梦之队”集体离职》,在其报道中援引接近ONE实验室人士的观点,“之所以项目中止,应该跟非虚构写作的产出效率低、变现困难有关”。由此促发ONE实验室三位核心成员先后发表了同中有异的“告别叙事”。[16]林天宏首先在朋友圈确认了ONE实验室的解散,他表示“公司的业务一切正常”,同时他已接棒李海鹏,“与他的工作交接一切顺利”。这一回应虽然正式且直接,但完全没有交代实验室解散的原因。此后,他再度发文,提出五点看法:
1.单纯的非虚构写作(我甚至从来不觉得有非虚构写作产业这个概念)一定是不具备商业变现模式的,起码短期内看不到。2.我从来不否认非虚构写作在剧作故事创作中的力量,但仅仅有这个一定是不够的。某些时候非虚构写作和编剧是两个行当。3.非虚构写作的商业价值必须也只有进入影视开发环节,尊重市场方向,尊重行业规律,尊重专业编剧,与专业编剧合作,取长补短,互相配合,才可以发挥出这群人最大的作用。4.至于要有大机构包养之类的观点,不在讨论范围。所谓资本急功近利等等,也不在讨论范围。你拿人家投资的时候怎么不说呢?5.非虚构写作者进入影视圈子要放下身段虚心学习,大多数人刚进来时都是带着某些虚幻的想象,这怎么行?
不难看出,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从业者和ONE实验室的首席内容官,林天宏的“告别叙事”充满了反思意味,其背后则凸显了商业逻辑对于新闻职业价值的解构:一方面,他变相交代了ONE实验室解散的真正原因是传统特稿作者对影视行业的“水土不服”;另一方面,他丝毫没有提及新闻职业的意义、价值与特质,相反,他强调的是非虚构写作者(传统新闻业者)首先要接受影视行业专业编剧的“规训”,要“放下身段虚心学习”,要放弃传统新闻人的“某些虚幻的想象”。何为“虚幻的想象”?尽管林天宏没有解释,但因循他商业逻辑的表达,很难不让人将这种“想象”与新闻职业固有的价值相勾连。
李海鹏也在朋友圈发布了他的“告别叙事”,第一句话即开宗明义,“这大概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了,因为我要离职,ONE实验室也随之解散”。接着,他又点名表扬并感谢了ONE实验室的8位作者(并标注了他们的代表作)和1位事实核查员,声称他们是“他共事过的最优秀的同事”,继而交代他和团队成员的归宿,“大多数人会作为一个整体继续从事非虚构相关工作”,他自己则要“呆在书房读书学习写东西”。秉持他一贯的写作风格,李海鹏用一种拉家常的方式,不露痕迹地表达了对自己以及写作的信心——“跟看到这条的家里人特别说一句:不用担心,现在的世道怪,写东西很赚钱的。毕业22年,做过10份工作之后,我希望写出自己喜欢的作品,也作为一个虚荣的人向大家真正地介绍自己。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大家加油,天下事犹未晚也”。与ONE上线之时发布的微博明显不同,李海鹏的“告别叙事”不仅没有强调新闻职业的光荣与梦想、价值与责任,相反,在他的叙述中,新闻业、特稿、非虚构写作等职业化概念都被置换为“写东西”——这样一个被消解了新闻职业色彩的普通化表达。
与前两者相比,ONE实验室前负责人林珊珊的“告别叙事”强调的则是一种“纪念话语”,凸显了林珊珊对于非虚构写作的坚守:“ONE实验室是未完成的梦想,也是非常美好的回忆。非虚构故事自有巨大的魅力和价值,小伙伴们还会在一起,还会继续写,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人进入这个行业。”她还在朋友圈发的文中设计了一个精巧的结尾,既展示对ONE实验室的眷念,也暗示非虚构写作的美好前景——“在这学期去清华新传学院代一门高级采写课,就有不少同学对非虚构充满热情——也有同学问我:老师,你知道一个叫ONE实验室的机构吗?何止知道呢,这段单纯进取的时光,会成为永久的财富”。与此同时,林珊珊也在后续的采访中表示原班团队会成立新工作室,继续做非虚构故事,“方式是和一些内容平台合作”,只是不再对“非虚构作品影视改编”要求那么迫切了”。[17]林珊珊的“告别叙事”除了表达出对于她在ONE实验室“进取”时光的眷念之外,还特别将她在“高校讲授高级采写课”与“继续从事非虚构写作”相勾连,话语中透露出新闻一线从业者对于新闻职业意义与价值的坚守。
(二)同行
ONE实验室的解散势必在媒体行业内部引发震动,新闻业关注此类议题的方式无外乎两种,其一是通过集中报道扩大影响,实现议题的扩散与聚焦;其二是经由报刊、自媒体平台发布评论与专业评析,呈现观点碰撞,寻求专业共识。我们在梳理资料时发现,业内对于本次事件的报道与评论基本集中在新闻网站以及微信、微博等泛媒体平台,讨论与分析的重点也逐渐由“原因剖析”转向“意义阐释”,由“非虚构写作”转向“新闻业转型”。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ONE实验室何以解散?
对于ONE实验室解散的原因分析,构成了泛媒体平台报道、同行评论的重点。首发媒体“刺猬公社”在报道中明确指出:“生产特稿所需要的大量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成本都显得尤为奢侈。除了制作成本过高,如何将特稿内容变现则是另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18]此后,证券时报网的《韩寒“ONE实验室”团队解散:“慢内容”终究无法突破“快资本”》、微信公号“创业邦”发布的《ONE实验室解散,“慢创作”与“赚快钱”的悖论》、钛媒体的《资本等不了好故事 韩寒旗下ONE实验室解散李海鹏离职》等报道,也纷纷将报道聚焦非虚构作品生产的长周期、高成本与资本的快速盈利诉求之间的矛盾,这些亦构成了众多叙事者的归因判断。“刺猬公社”创始人叶铁桥进一步将关注点集中到非虚构产业与时代的矛盾上,他指出,这是一个“快速消费型奢侈品衰落的时代”,因为“品质和情怀,没法很好地与商业兼容”,所以,“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门不划算的生意”。[19]资深媒体人朱学东在朋友圈发文则更加言简意赅:“就一点,资本追求的是效率。” [20]第二,非虚构写作的特质与边界何在?
在探究ONE实验室解散的因果关联时,非虚构写作的特质与边界自然首当其冲。但最初,几乎所有的讨论都把“非虚构写作”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加以使用,而各自表述却又往往在“文体形态”、“写作姿态”、“文学潮流”三种维度之间混用。伴随讨论的深入,许多同行开始追问这个概念使用的逻辑前提,即“究竟什么是非虚构写作?其专业边界在哪里?”对此,《南方周末》前记者、资深媒体人叶伟明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他提出的三个问题却切中肯綮:“1.为什么是非虚构写作,而不是其他创作类型,在当下受到追捧?2.当我们谈“非虚构写作的商业模式”时,我们在谈什么?这门生意,创作者和资本所期待的边界是否一致?3.如果你正在创作,并为此痛苦(物质精神皆可),是什么让你坚持?” [21]第一个问题涉及对新闻业变动的反思,尤其是对非虚构写作独特性的探寻;第二个问题实质是对非虚构写作商业变现模式的质疑;第三个问题则暗含对新闻人职业价值的追问,由此引发了同行的广泛关注。“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从定义和操作两个层面做出解答,他认为,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基于事实素材的写作就是非虚构写作”,包含“特稿新闻式写作、传记、纪实文学”多种文体形态。从操作标准看,非虚构作品首先必须呈现的是一个“真实故事”;其次,这个故事要能够“成立”,即具有逻辑自洽性;最后,作品要“线条清晰,语言简洁。所有的观点、情绪表达包括形容词、副词、连词,能删就删”。[22]有学者从历史维度梳理非虚构写作的中国路径,继而指出其文体特质,“作为一种交叉文体,‘非虚构写作’始终是在新闻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博弈中寻求平衡”。[23]第三,传统媒体人职业转型与内容创业何以可能?
ONE的离场究竟是一个个案,还是非虚构写作整体性失败的先兆?非虚构写作的商业模式在哪里?传统媒体人职业转型与内容创业何以可能?这三个相辅相成的问题构成了业界讨论的又一个重点。对此,同行的观点明显分为两派,一派认为ONE实验室的解散说明非虚构写作的商业模式不可行,因为写作是一回事,拍影视剧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鸿沟”。因此,“想进行批量IP生产进军影视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会,是一个乌托邦”。[24]更有人全然否定了非虚构写作的商业化及至媒体人内容创业的合法性,认为其实质只是“顶端的非虚构写作者得了名和(不知可怜到多少的)利,再去给后来者造梦。赚的还是有志于非虚构写作的后来者的钱——这是贩卖梦想,或者,又何尝不是写作传销”。[25]另一派则以“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为代表。他在ONE解散当天就连发两条微博,一条认为业内的报道与分析,“看似祝福特稿梦之队,却唱衰了整个行当”,另一条则表达了对于内容创业的信心,“希望一切都好,我们擦亮眼睛,能找到一条路”。[26]雷磊在之后的访谈中,明确表示“这条路”就是“非虚构的商业之路”,在他看来,只要非虚构行业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作者做到写作探索就好了,写更好的文章”,还有一些人可以做一些商业化运作,“去探索非虚构内容的商业价值”,这样,不仅写作者可以“获得更多经济利益上的回报”,还会“有更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来写,有更多的作品出来”。[27]与之类似,还有论者认为,“无数内容生产者转型和创业最大的门槛”就是“仅仅把内容作为丈量商业世界的标尺”。因此,对于内容创业来说,“内容只是子弹。没有商业模式这杆枪,子弹也没有用武之地”。[28]此外,在同行的叙事中也会零星地出现诸如“情怀”、“理想主义”等涉及新闻职业价值的表达。比如,资深媒体人罗昌平的评论充满了“隐喻”——“少了一个观看这世间善恶的窗户!那窗台蝶雀花藤拥簇,还曾架着精致典雅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资深媒体人石扉客则言简意赅地评价:“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想还是原来的新闻理想,但现实却不再是曾经的现实。对于媒体人转型的这个现实困境,资深媒体人孙旭阳认为,传统媒体人才转型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区分在旧有的评判标准下的好稿子与自媒体时代的好产品之间究竟存在哪些区别”,而更为重要的是,“对文字品质的执念、济世的情怀,与商业原本很难兼容”。钛媒体(TMTpost)创始人、总编辑赵何娟则在结合自身职业经历与观察之后,指出:“这些年经历下来,我还是最喜欢老财经财新的传统,他们的积淀最深,每个记者都应该以成为深度记者为目标,每个记者都应该有权利有责任写深度。内容,从来都是细水长流的事业。”什么是老财经财新的传统?何为深度记者?这些表达背后也凸显出新闻业的传统价值与记者的专业化特质。
(三)读者
社会化媒体时代,读者成为用户,其参与讨论、发表观点也变得简单而直接,藉此与专业新闻人形成一个“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通过公共表达来形塑理解与实践,继而更好地把握新闻业的变动。[29]ONE实验室解散后,网络空间弥漫着各种夹杂悲观、纠结、惋惜、期待、祝福的复杂情绪。网友“以琛的”写道:“ONE实验室解散了,恍恍惚惚有个错觉,仿佛是一个时代落下的感觉。” [30]网友“荒野上的风声与病九”则在悲观中透出些许敬佩之情——“ONE实验室解散了。新闻的一角塌了。它用它的死亡告诉我,理想的失败。但同时它也用它的死亡告诉我,它曾拼命抗争过。” [31]网友“归于平静bolan西”则更多是带着某种惋惜的困惑:“ONE实验室解散了,一群精英也没能抵住金钱压力吗?” [32]还有网友为ONE的解散鸣不平,“认真的写作者依然是被低估的,太多并不太认真或怀揣其他目的的人将写作当成了活计或捷径”。[33]而当林珊珊表示她和她的团队会继续从事非虚构写作时,ONE实验室300多人的读者群则被“会一直等你们”的话语刷屏。[34]“知乎”也辟出问答专区“如何评价韩寒ONE实验室团队解散”和评论专区“韩寒旗下ONE实验室解散,非虚构写作的商业模式在哪里”,结果分别有43个回答和19条评论,其中很多分析都具有专业性。网友“贝勒王”的“原因阐释”与许多专业人士的观点几无区别:“从链接文章看,非虚构故事IP化是海市蜃楼,因为非虚构故事不具备完整的IP价值,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任何人都可以把它改编成小说、戏剧等,而且很容易在创作中规避法律问题。” [35]此外,还有网友借用两种经典理论进行深度阐释——面向市场的写作,其追求的都是“群选经典”;追求严肃目的的写作,追求的都是“专业经典”。一般来说,“资本并不在意内容的正确性,只在意内容的关联性”,这恰恰契合于“群选经典”。有鉴于此,ONE实验室的做法实质是用适合“专业经典”的规则在“群选经典”的场域中参与竞争,“自然是落于下风的”。[36]对于非虚构未来,网友“四面楚戈”则结合其特质做出预测:“正因为有直抵人心的魅力和忠实记录和精细描摹现实的特质,所以,非虚构写作的价值不在当下,而在将来”。[37]与职业新闻人的阐释性实践相比,读者关于ONE的言说反而出现了大量诸如“理想”、“价值”、“意义”等表述,他们对于新闻业的传统价值以及新闻的职业理想都表现出较高的认同度和心理期待,对于ONE解散的原因、非虚构写作的前景等专业话题的回答与讨论,也表现出较高的专业水准。可能的原因在于,作为新闻行业奢侈品的特稿等非虚构作品,其读者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和知识水平,因为,相较于碎片化的表达,一篇非虚构作品往往长达上万字,如果没有一定的欣赏水平和兴趣,读者是不可能愿意阅读的。
四、变动时代新闻职业价值的消解与重构
卡尔森指出,“元新闻话语提供了一个视角,将相互竞争的行动者、他们说话的场所和所谈论的受众以及所讨论的话题联系起来”。[38]基于此,本文集中探讨了不同主体对于ONE实验室解散这一“关键事件”所进行的话语阐释。我们发现,这些阐释性话语实践依然在新闻业危机话语(crisis discourse)框架中,基本依循着“变动–危机–转型”的路径展开,而商业化已经成为当今新闻业转型的主导逻辑,继而影响着变动时代新闻职业价值的消解与重构。
一方面,ONE实验室的“特稿作者–内容–影视”的闭环生产模式实质就是一种商业导向的新闻生产模式,其核心目的是变现。因此,当ONE实验室解散之后,林天宏的“反思话语”的前提是“非虚构写作的商业价值必须也只有进入影视开发环节”,从根本上消解了新闻职业的既有价值;李海鹏的“告别叙事”则是基于“现在的世道怪,写东西很赚钱”的逻辑展开,同时,他将新闻报道置换为“写东西”,消解了新闻职业的独特性。
与此同时,新闻同行阐释的主导性话语中不断凸显的关键词集中在生意、变现、交易、爆款产品等商业语汇上,“让人意外的是,人们对ONE实验室失败的探讨,都集中在‘变现失败’,很少有人去梳理整个团队的创作或者作品,人们更关心的,永远都是变现、变现、变现。人们吵闹着IP时代,吵闹着变现模式,更多是一种焦虑和浮躁的表现”。[39]其实质依然是商业逻辑,背后隐含着对传统新闻职业价值的消解。甚至有业者将ONE的解散、非虚构变现困难的原因归结为“从业者本身职业性匮乏”,这里的“职业性”并非基于新闻专业主义框架,而“应该是通过商业模式推导自己的生产模式”。[40]这种观点凸显了商业逻辑对于新闻职业价值的解构。
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变动时代,新媒介技术带来传统新闻业的生存危机,新闻人的职业认同与身份认同双双被打破,加剧了传统新闻人的失落与焦虑,诚如《正午故事》主笔郭玉洁在其非虚构作品中描述的那样:“互联网之后,原有的商业模式失效了。机构媒体衰败、破产,必须向市场证明自己有理由活下去。一夜之间,部门之间的壁垒被打破,每一个内容生产者都必须学习做生意。离开了机构,人们急于建立个人名声,让粉丝围绕在自己的名字周围。” [41]于是,当《太平洋大逃杀》被乐视影业以百万价格买入,这样一个被李海鹏称为“内容带来利润的小小创举”,立刻让生存空间日趋逼仄的传统媒体人找到了一根化解传统媒体危机、新闻人转型的“救命稻草”——非虚构写作。作品能够变现,不仅说明非虚构写作具有经济价值,也证明了新闻人的存在价值乃至内容创业的合理性,由此新闻职业的传统价值逐渐消解,专业主义离场,商业主义统合新闻职业价值,其结果必然是“商业主义构成了当下中国新闻业者在面对数字化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挑战时所形构的话语的核心”。[42]另一方面,在新闻职业价值的认同层面,作为“阐释的共同体”的新闻从业者内部业已产生分化。尽管商业逻辑已经成为媒体转型的主导逻辑,但依然有从业者表现出对于传统职业价值的坚守。ONE实验室负责人林珊珊不仅在“纪念叙事”中明确表达了这个逻辑,还用实际行动践行新闻职业的价值。2018年,林珊珊团队重新组建了“深入硬核,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的“故事硬核”工作室,该工作室加盟腾讯谷雨,并与其达成共识——“双方的合作当然是因为都还信仰媒体的公共价值,而且我们都认为即使是在影响表达更加强势的当下,优质的文本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魅力”。[43]这种分化也体现在参与讨论的同行中。《南方周末》前记者方可成在其朋友圈发文指出,“真实、精致、责任感、好手艺,这些都是当下的病态商业环境中无人买单的。所以要么走非营利之路,不要妄图按照商业逻辑的游戏规则生产最好的内容;要么深刻改造商业环境,让短视和狭隘的资本愿意承认和支持更长远的品牌和社会价值”。[44]知名媒体人杨瑞春也提醒林珊珊们根本不用去想非虚构的商业化问题,因为“优质的特稿自有其价值,当稿件完成度足够好影响力足够大,就已经足够圆满。如果碰巧有IP变现可以喜悦一下,但那已经是衍生价值,为这个驱动则会乱了心性”。[45]这些讨论都涉及对于新闻职业价值的复归与重估。
应该看到,“元新闻话语”为我们审视变动中的新闻业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尤其在新媒介技术崛起,媒体业态与传播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元新闻话语不仅是一个意义和实践系统,还是一个开放的、各种话语在场而交织的论坛”。[46]有鉴于此,正是新闻从业者和非新闻从业者的共同参与才促成了“元新闻话语”的生成,而新闻业的意义、价值及其社会角色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以重构。■
①白红义:《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6期
②Carlson.Matt.(2014).GONEBUT NOT FORGOTTEN: Memories of journalistic deviance as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Journalism Studies.15(1).33-47.
③Carlson.Matt.(2016).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 nitional Control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Communication Theory.26(4).349-368.
④Carlson,M. & UsherN.(2016).News startups as agents of innovation: For-profit digital news startup manifestos as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Digital Journalism,4(5)563-581.
⑤MaeyerJ.D.& Holton,A.E.(2016).Why linking matters: A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ism,17(6)776-794.
⑥Patrick.F.&Ross.T.(2018).AccessDeconstructed: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Photojournalism’s Shift Away From Geophysical Acc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42(2)121–137.
⑦Zelizer. B. (1993).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0(3)219-237.
⑧这类研究代表性成果逐年增多,大体包括:李红涛、黄顺铭:《谋道亦谋食:〈南方传媒研究〉与实践性新闻专业主义》,《当代传播》2014年第4期;白红义:《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6期;丁方舟、韦路:《社会化媒体时代中国新闻人的职业困境——基于2010-2014年“记者节”新闻人微博职业话语变迁的考察》,《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郭恩强:《多元阐释的“话语社群”:〈大公报〉与当代中国新闻界集体记忆——以2002年〈大公报〉百年纪念活动为讨论中心》,《新闻大学》2014年第3期;陈楚杰:《媒体记忆中的边界区分,职业怀旧与文化权威——以央视原台长逝世的纪念话语为例》,《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2期;白红义:《新闻范式的危机与调适——基于纪许光微博反腐事件的讨论》,《现代传播》2015年第6期;陆晔、周睿鸣:《“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7期;李艳红、陈鹏:《“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立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李红涛:《“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5期;张志安、张震:《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职业权威的话语建构——基于48家媒体2016年新年献词的话语研究》,《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等。
⑨白红义:《“正在消失的报纸”:基于两起停刊事件的元新闻话语研究——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为例》,《新闻记者》2017年第4期
⑩晓通:《ONE实验室解散,“特稿梦之队”集体离职》,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2017年10月10日
[11]腾讯全媒派:《专访“真相看护者”:在中国做一名事实核查员是怎样的体验?》,http://news.qq.com/original/dujiabianyi/shishihechayuan.html
[12]苏建勋:《资本等不了好故事韩寒旗下ONE实验室解散李海鹏离职》,钛媒体,2017年10月11日
[13]新浪微博“李海鹏”,2017年1月5日
[14]Spaulding,S.(2016).The poetics of goodbye:Change and nostalgia in goodbye narratives penned by ex-Baltimore Sun employees. Journalism,17(2)208-226.
[15]白红义:《“正在消失的报纸”:基于两起停刊事件的元新闻话语研究——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为例》,《新闻记者》2017年第4期
[16]本部分对于三位微信朋友圈的引文皆引自石灿:《李海鹏辞职有树,林天宏接任,泛媒体圈激辩ONE实验室解散》(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2017年10月11日)的文中微信截图。
[17]克里斯唐:《韩寒“ONE实验室”团队解散,这还是非虚构写作者的最好时代吗?》,http://36kr.com/
[18]晓通:《ONE实验室解散,“特稿梦之队”集体离职》,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2017年10月10日
[19]叶铁桥:《越深度,越奢侈,所以“ONE实验室”解散了》,《青年记者》2017年10月(下)
[20]石灿:《李海鹏辞职有树,林天宏接任,泛媒体圈激辩ONE实验室解散》,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2017年10月11日
[21]叶伟民:《韩寒旗下“ONE实验室”解散,非虚构写作的商业模式在哪里?》,微信公号“叶伟民写作参考”,2017年10月12日
[22]张迪:《“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我们的优势只有一条,就是要靠自己生存》,https://mp.weixin.qq.com/s/HzE7hWbm_el38lbupc4pmQ
[23]刘勇:《新闻与文学的交响与变奏——基于对“非虚构写作”的历时性考察》,《现代传播》2017年第8期
[24]张丰:《变现,变现,连韩寒都失败了,写字的人还能发财吗》,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intouchtoday/n4043.html
[25]一萌:《韩寒不需要李海鹏》,微信公号格致余论,2017年10月19日
[26]新浪微博“雷磊ak”,2017年10月10日
[27]张迪:《“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我们的优势只有一条,就是要靠自己生存》,https://mp.weixin.qq.com/s/HzE7hWbm_el38lbupc4pmQ
[28]叁师傅:《ONE实验室解散,新世相再升级,也给做内容的手艺人提了个醒》,https://mp.weixin.qq.com,2017-10-11
[29]Carlson.Matt.(2016).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 nitional Control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Communication Theory.26(4).349-368.
[30]新浪微博“以琛的”,2017年10月11日
[31]新浪微博“荒野上的风声与病九”,2017年11月21日
[32]新浪微博“归于平静bolan西”,2017年10月10日
[33]新浪微博“丁天D小姐”,2017年10月11日
[34]罗立璇:《别着急,非虚构好着呢》,https://baijia.baidu.com/s?id=1581034978398783469&wfr=pc&fr=app_list
[35]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6488034/answer/242739243
[36]https://zhuanlan.zhihu.com/p/30040753
[37]晓通:《ONE实验室解散,“特稿梦之队”集体离职》,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2017年10月10日
[38]Carlson.Matt.(2016).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 nitional Control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Communication Theory.26(4).349-368.
[39]张丰:《变现,变现,连韩寒都失败了,写字的人还能发财吗》,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intouchtoday/n4043.html
[40]罗立璇:《别着急,非虚构好着呢》,https://baijia.baidu.com/s?id=1581034978398783469&wfr=pc&fr=app_list
[41]郭玉洁:《众声》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42]李艳红、陈鹏:《“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立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
[43]晓通:《ONE实验室涅槃重生,原班人马携“故事硬核”重出江湖》,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2018年2月5日
[44]方可成朋友圈截图,石灿:《李海鹏辞职有树,林天宏接任,泛媒体圈激辩ONE实验室解散》,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2017年10月11日
[45]晓通:《ONE实验室涅槃重生,原班人马携“故事硬核”重出江湖》,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2018年2月5日
[46]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
李娟系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刘勇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史研究(1949-2012)”的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3CXW005;“安徽省2016年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的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gxyqZD2016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