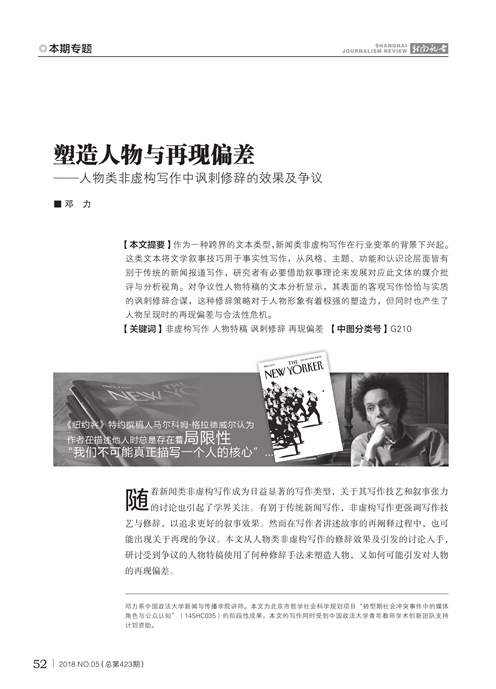塑造人物与再现偏差
——人物类非虚构写作中讽刺修辞的效果及争议
■邓力
【本文提要】作为一种跨界的文本类型,新闻类非虚构写作在行业变革的背景下兴起。这类文本将文学叙事技巧用于事实性写作,从风格、主题、功能和认识论层面皆有别于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研究者有必要借助叙事理论来发展对应此文体的媒介批评与分析视角。对争议性人物特稿的文本分析显示,其表面的客观写作恰恰与实质的讽刺修辞合谋,这种修辞策略对于人物形象有着极强的塑造力,但同时也产生了人物呈现时的再现偏差与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非虚构写作 人物特稿 讽刺修辞 再现偏差
【中图分类号】G210
随着新闻类非虚构写作成为日益显著的写作类型,关于其写作技艺和叙事张力的讨论也引起了学界关注。有别于传统新闻写作,非虚构写作更强调写作技艺与修辞,以追求更好的叙事效果。然而在写作者讲述故事的再阐释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关于再现的争议。本文从人物类非虚构写作的修辞效果及引发的讨论入手,研讨受到争议的人物特稿使用了何种修辞手法来塑造人物,又如何可能引发对人物的再现偏差。
一、文献综述
1.跨界的文本:非虚构写作与新闻写作的渊源
当下新闻业的生产形式与文本形态日益多元,追求快速发布信息的短新闻与讲述故事的叙事新闻日渐分野,“非虚构写作”也成为新闻生产关注的“新”方向,但其实两者早有渊源。“新新闻写作”代表人物汤姆·沃尔夫就曾总结在对现实事件的写作中如何向现实主义小说家学习技巧,来为作品添加情感力量。①首届普利策奖特稿写作获奖记者约翰·富兰克林也将特稿定义为“一种非虚构的短故事形式”。②因此尽管非虚构写作还包括历史、传记等其他题材,它与新闻写作的关系仍显得更为密切。
从与新闻写作的关系来看,非虚构写作来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文学新闻”或“新新闻”,③这类写作挑战了当时新闻业传统的报道方式,更因其现实题材与立场表达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④
非虚构与虚构写作文本的相互影响也是研究者关注的话题。“新新闻”出现伊始大多借用虚构写作手法,突破了事实性新闻写作的传统,由此引发关于新闻与文学关系的探讨,以及对事实与虚构边界的讨论。⑤而数十年后,新闻的形态伴随技术更新发生了极大变化,新闻业叙事手法的丰富和多元程度加深,相关讨论开始从新闻写作对虚构技艺的借鉴,转移到讨论如何发展属于新闻业自身的调查及叙事方法,⑥甚至有观点认为,还应该看到新闻写作对虚构写作产生了反向的影响。⑦
上世纪八十年代,普利策特稿写作奖的获奖作品被译介到中国,让经历过报告文学风潮的新闻从业者看到另一种“使新闻真正成为‘作品’”的写作方式。⑧伴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媒体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开始出现一批特稿写作的尝试者,他们往往是新闻机构“特稿部”或“深度报道组”的记者,被认为最早开始了“非虚构写作的新闻实践”。⑨如果说早期的“特稿”还隶属于组织化的专业新闻生产,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与影业等方面资本的介入,非虚构写作不再为传统新闻媒体所垄断,不断有新兴的非虚构作品平台出现,⑩但若辨别这一写作社群中活跃且有持续生产力的作者,仍可发现不少前新闻人的身影。这类写作者将建立个人职业身份的话语重心转移为对写作技巧的强调,而弱化了更具机构属性和规训作用的组织化新闻报道原则。与此同时,以往用来评价传统新闻写作的规范标准,也不再完全适用于新闻类非虚构作品。
2.新闻类非虚构写作的叙事特征与评价框架
无论以新新闻、文学新闻、叙事新闻,还是特稿来为其命名,新闻类的非虚构写作与传统新闻报道的区分,不仅在于其风格、主题、功能有异,更在于其认识论的不同。[11]其一,非虚构写作往往借鉴虚构的技法,以提升叙事的效力。其中故事化的叙事结构,和常见于虚构写作中的描摹场景、对话、细节、视角等叙事方法,[12]并不能被传统新闻写作类型的信息化、呈现式或解释性报道等模式所完全涵盖。[13]其二,关于写作材料,传统新闻写作所处理的材料通常是由消息源提供并经确认的事实和以直接引语形式呈现的意见;[14]而新闻类非虚构写作除了要处理这些材料之外,还需处理的核心材料是大量的关于人物或事件的叙述。其三,从写作功能来看,较之常规新闻,新闻类非虚构写作的传播目的不仅是告知信息(informing),而且是展演故事(performing),通过生动讲述种种人物及其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及经济问题,将生活世界与社会议题进行关联。[15]其四,从认识论来看,传统新闻写作所处理的事实是可描述的、可分类的、易于处理的,事实与观察者的意识过程无关,是客观外在的存在;[16]而新闻类非虚构的写作者并不掩饰其主观性,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理解与阐释来为写作对象所叙述的经验赋予意义,因此作者的意识过程成为一种中介化的主观性(mediating subjectivity)贯穿在整个故事的讲述中。[17]既然两种文本有以上区分,用于衡量传统新闻写作的准确性或可验证性等评判标准,对于新闻类非虚构来说虽仍属必要,但已不再足够。研究者曾有过讨论,除了客观性原则下的写作程序与规范,还有何种应然性框架可用来评价不同于“客观新闻”写作的“新新闻”。[18]Mitchell运用话语分析来构建文学新闻的核心伦理准则,他认为写作者既要在处理采访对象的信息时做到公正(fairness),又要如实地(faithfullness)为读者提供准确与详尽的文本。[19]一方面,新闻类非虚构写作的消息源不是被观察、总结、分类的对象,而是阐释与了解的主体,[20]写作者不得不思考描述或暴露他人生活的方法及其后果;[21]另一方面,写作者还需要考虑如何尽可能地以读者能理解的方式来呈现现实,如何避免对真相的故意操纵。[22]这样,写作者需要同时处理他与写作对象和与读者之间的两份契约。
3.塑造人物:人物类特稿写作的叙事张力与再现偏差
建立起作者和书写对象之间的信任,写出让读者产生对人物的某种领悟或理解的故事,是非虚构写作追求的理想状态。然而在写作者为他人叙述的经验赋予意义的再阐释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对人物再现的争议,这在人物特稿中最为突出。
人物特稿是典型的以叙事性见长的新闻类非虚构写作,写作者认为“成功的人物特写包含了叙事新闻所有的必要的元素”。[23]与常规新闻相比,人物特稿更为关注生活世界中的细节,能够从具体的人物出发来展开某个抽象的社会议题。这也使得人物特稿成为一种以小见大的个案式写作文本。在中国,人物特稿曾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出现,但当下的写作者则试图“把背后的金光去掉”,并将其归类为非虚构写作。[24]对人的呈现是复杂的,人物特稿所“描画”和“记录”的对象,更多的是一般新闻很少处理也难以处理的“观念”和“意义”,[25]写作是为了“记录人在生活里寻觅意义和目的时的行为、动机、感情、信仰、态度、不满、希望、恐惧、成就和渴望”。[26]为了在文本中处理“意义”并塑造人物,写作者需要“发掘人物的复杂性,并通过一系列事情来展示它”。[27]人物特稿中需要处理的核心材料首先是写作对象自己的叙述(narratives),其次来自外围采访的材料也是为了从其他角度补充这些叙述。从定义上看,叙述是一种特定的话语形式,它是一种对过去经验的塑造与排序,也是一种回溯性的意义生成,一段叙述传播的是叙述者的观点、情感、想法与阐释。[28]而非虚构写作者绝不简单搬运写作对象的叙述,而是以一种自我参与(involved)的方式,理解并重述这些经验。然而当写作者用自己的视角来重构另一个人的叙述时,即使是基于事实的叙事,也可能会生成不同的意义与阐释。
当写作者需要处理的核心材料是他人的叙述时,对他人经验的描述便带来重塑的风险。关于如何讲好故事与塑造人物的写作技艺讨论,总是伴随着另一种不确定与自省的话语。《纽约客》特约撰稿人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认为,作者在描述他人时总是存在着局限性,“我们不可能真正描写一个人的核心”,“人们比我们对他们的特写呈现出来的更为复杂”。[29]国内特稿作者也谈到,写作人物并赋予意义的过程是“把别人的一生浓缩和重新组合的过程”,需要承担起“重构故事的风险”。[30]写作者认识到了叙述他人故事时所拥有的强大的再描述力量:“作为一名记者,我的权力要比我故事中出现的人要大得多”。[31]人物特稿写作者的反思虽然鲜活具体,但囿于篇幅及其言说视角,仍未能系统性地明晰非虚构写作中的叙事张力,以及写作者和书写对象之间叙述与被叙述的关系。对写作关系的讨论,同样出现在使用叙事方法的定性研究者的反思中。[32]和人物特稿作者一样,这类研究者同样需要和研究对象所叙述的经验、观点、情感打交道,也有着相似的写作宗旨,要写出关于写作对象的准确、真实、相互信任的文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定性研究者对于其研究主旨——“如何最好地描述并阐释他人的或其他文化中的经验”——曾提出“再现的危机”(a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这一重要反省。[33]类似的,人物特稿写作在描述并阐释他人的经验的同时,也需要面对可能出现的“再现偏差”及其带来的后果。尤其当新闻类非虚构写作面对更广泛的受众,且写作的人物足够复杂或充满争议时,写作者的采访过程与文本作品更可能成为公众讨论的对象。当“再现偏差”引发了媒介批评时,作者已不能只在自省的框架内谈论其作品的叙事张力,还必须对公开的评价作出回应。
对于研究者而言,虽然人物特稿的叙事效果及再现争议引发了学术关注,但新闻学研究仍较少以类型写作的分析视角入手来考察此问题,[34]也鲜有通过文本分析来探讨叙事性新闻文本的话语实践及其评价标准。而随着新闻业转型中非虚构写作的再次兴起,对于这样一种将文学叙事技巧用于事实性写作、处理意义多过描述事实、强调个人化写作技艺的新闻写作类型,研究者也有必要借助叙事理论与文本分析方法,建构一种有别于传统新闻写作的文本评价方法或规范标准。[35]
二、研究问题与样本选取
关于文学新闻写作准则和伦理的探讨,其对象一般既包括对文本作为言说行为的准则,也包括对文本生产过程中报道行为的准则。[36]本文仅关注人物特稿这类典型的新闻类非虚构写作的文本层面,讨论如何从其文本特征及其所引发的争议出发,发展出有助于媒介批评与讨论的评价视角。具体而言,本研究从引发争议的人物特稿入手,来看这类文本所使用的修辞或写作方法中,有哪些因素导致写作对象或读者所认为的“再现偏差”的出现。文本分析将从两个层面回答研究问题:第一,在写作层面,文本使用了哪些叙事手法来发挥塑造人物的效力,实现了何种修辞效果?第二,关于文本呈现的结果,这些修辞方式又如何导致“再现偏差”的出现?
从研究问题出发,本文的案例选取遵循立意抽样(purposive sampling)原则。本文并不试图一一列举各种人物写作中的各类再现偏差,而是仅从文本修辞这一分析维度切入,来看人物特稿的事实化写作中存在何种修辞,可能导致再现偏差的出现。在选取案例时,第一个标准是人物特稿中的人物塑造或叙事修辞是否存在争议,即是否引发了关于人物呈现的业内讨论、媒介批评及读者评论;第二个标准是其争议是否来自叙事层面,即文本的人物呈现、修辞或写作方法被认为出现了偏差。因此,这种样本选择排除了一类人物特稿,即正面的人物报道、吹捧性传记或娱乐化报道,所选取的人物特稿可能本身就以有争议性的复杂人物作为报道对象。同时,本文只从文本写作的修辞及其后果这个层面来讨论人物特稿的写作,尽管有某些人物特稿争议度高,但因其偏差来自其采访与事实搜集过程的不足,而并非修辞层面,也最终未选取其作为回答本文研究问题的案例。另外,在选样时还排除了存在故意造假和编造事实的文章,但未排除因未经多方消息源核实而出现少量事实性信息失实情况的文章。
按照这样的选取样本标准,本文选择两篇近年来引发争议的人物特稿,一篇是《人物》杂志于2013年2月刊载的《厉害女士》,描写对象是河南省兰考县长年收养弃婴的中年女性袁厉害,她的数名收养子女当时刚刚经历了火灾;另一篇是《智族GQ》杂志于2016年刊载的《耶鲁村官秦玥飞:权力的局外人》(后简称《耶鲁村官》),描写对象是一名从耶鲁毕业后选择在农村做基层村官的年轻男性。这两篇人物特稿在发表之后,不仅引起业内人士如记者同行和新闻学者的多方探讨,更是引发对该人物或该报道感兴趣的读者作出评论和探讨,且记者有所回应,形成了媒介批评与从业者公共答辩之互动过程。除了两篇特稿本身,其引发的讨论和争议文本,也构成本研究文本分析的对象。这些讨论的文章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发表于与新闻业务相关期刊上的文章,作者除了学界人士,还有业界人士,甚至同题采访的记者;另一类则是新媒体平台上的讨论,除了公众号文章外,还包括在知识社区型内容平台如“知乎”上的相关讨论,在关于两篇特稿的提问下有着数百条回答,这些也都构成文本分析的材料。
三、对争议性人物特稿的文本分析:人物塑造与再现偏差
两篇人物特稿的写作对象皆为较为复杂的新闻人物,虽然两篇稿件的新闻故事、人物特征、写作风格不尽相同,但都在讲述故事和塑造人物时使用了讽刺修辞作为最主要的叙事方式。在对新闻作品的文本分析中,研究者们发现当客观写作或事实性写作是新闻叙事的必需修辞时,讽刺修辞也可同时通过铺陈事实和直接引语而得以成立,达到将客观性变形为讽刺性的效果(the ironic transfiguration of objectivity)。[37]通过这种转换,写作者可以在事实性写作的要求下塑造人物、讲述故事,甚至表露对报道对象的道德立场或主观评价。[38]本文选取的两个文本,都遵循事实性写作原则来铺陈细节或使用引语,但同时达到了通过讽刺修辞来塑造人物的叙事效果,也由此引发了关于人物再现偏差的争议与媒介批评。
从修辞分析来看,形成讽刺的修辞需要以下三个形式要件:第一,讽刺由双层意义组成,即被描述者的叙述与写作者的叙述;第二,这两者间要存在冲突和矛盾,一种是“所说的和所指的相互矛盾”,构成语言讽刺(verbal irony),另一种是“当事人的想法和观察者认知存在矛盾”,构成情境讽刺(situational irony);第三,被讽刺的当事人对自己成为讽刺修辞的对象是不自知的。[39]这两篇特稿的叙事满足了这些形式要件,既通过描述言行冲突来塑造人物形象,也通过重述情境来讲述故事,最终实现了讽刺修辞的效果,但同时也带来人物呈现时的再现偏差与合法性危机。研究发现分为这三部分展开:
1.重塑形象:通过语言讽刺来解构人物言说
当一个重要的新闻人物同时吸引多家媒体报道时,人物特稿记者的写作会更追求故事的讲述,以及对人物的刻画与塑造。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与叙事和修辞有关,即作为非虚构写作,人物特稿如何能够在符合事实性写作原则的同时,还能实现塑造人物、讲好故事的修辞效果?同题写作给了我们在比较中评估文本修辞效果的机会,《厉害女士》这篇以当时的热点人物袁厉害为主角的人物特稿,相较于其他报道,其“独家”事实的补充(虽然部分事实的准确性后被质疑)、其选取与呈现事实的方式,在与同题稿件的对比之下形成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叙事。这种叙事效果首先来自一种对比冲突,从文章开篇第二段始,记者便直接铺陈了一组以“此前(如何)”与“事实(如何)”开头的对比段落,其中因对比而生成的叙事张力显而易见:
经过《人物》记者7天的实地观察和调查,我们得到许多与此前描述互相矛盾甚至完全相反的事实:
在此前宣传中,袁厉害对她收养的100多个孩子一视同仁,关怀备至,视若己出。
事实是,这些年,袁厉害的孩子以残疾程度和相貌,被她分为几等。“头等”孩子得以享受最好的照顾,而最需要照顾的下等孩子,一度同垃圾、苍蝇、大小便挤在一起艰难求生。
这样的对比段落一共连续重复了五次。这些段落中的文本首先呈现出新闻写作的惯例,如使用直接引语,提供经过核实的事实。然而此时,引语与事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使人物的话语与行为之间形成了矛盾:矛盾一方是此前“宣传”、“舆论”中的袁厉害形象和她“对外承认”、“宣称”的经济状况等话语,另一方则是记者以“事实是”的表述来呈现的与这些话语截然相反的行为。显然,写作者使用被描述者的话作为材料来塑造人物形象时,并非简单使用被描述者的“引语”来对其境况作解释,而是让被描述者的行为和语言形成对比,在这种对立中,人物的行为恰恰被自己曾说过的话解构了。通过这种对立,这篇人物稿件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叙事,重新塑造出一个与此前媒体报道中的“兰考好人”截然相反的形象。
《耶鲁村官秦玥飞》一文使用了同样的修辞手法。当秦玥飞为村里拉来筹款建设水渠时,却遇到有人停工要钱的情况。对于此事的处理,他最后实际上妥协单独给钱了事,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其以“嘘寒问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又兼顾了人情,又维持了一种议事原则”。
当写作者如此将人物的行为与语言并置之后,便呈现出“说一套,做一套”的矛盾,在修辞上构成一种较为直接的“语言讽刺”。[40]这种语言讽刺修辞在新闻报道中并不鲜见,比如调查性报道在描写负面角色如官员时常用的一种手段,就是“让他们被自己说过的话作茧自缚”。[41]调查报道常常通过修辞与叙事来建构出“受害者”与“恶人”这一对典型的人物角色,在塑造“恶人”角色时,就常通过言行冲突所形成的语言讽刺来解构本人说出的话。写作者通过“语言与行为的并置”来创造冲突,营造出一种通过事实来“揭开面纱”的意味。[42]而这两篇人物特稿,也使用了与调查报道同样的语言讽刺修辞来解构人物的言说,重新塑造出一个在同题报道中未被呈现的人物形象。
2.重述经验:通过情境讽刺来形成故事冲突
写作者并不总是“按照人对自己的理解来描画他们”。[43]对于人物及其所处境况,书写对象的自我叙事与书写者的叙事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与张力,这便在整体层面构成故事冲突的另一种讽刺修辞,即情境讽刺。[44]相较于语言讽刺,情境讽刺的写作更为复杂,通常通过对人物及境况的描摹,呈现出其内在的自我矛盾、虚假或荒谬。
此时,被描写者所陈述的话语即“引语”的使用,是在为书写者的叙述意图服务,而且书写者也并不避讳在文中以第一人称直接发表意见。《耶鲁村官秦玥飞》接近文末处便出现了作者以第一人称视角与当事人关于稿件中人物形象的直接对话。从对话中可以看出,双方对于人物及其所处境况有着截然不同的描述:
我把这次报道的初稿给秦玥飞看。他指责我写了篇负面报道,他认为他的创业计划以后会对社会有贡献,而我黑了他和他合作方的形象,我不该去毁掉一项会对社会有贡献的工作。“Five years of hard work. Do I deserve this ?(五年的辛劳。我就该得到这种结果吗?)”他一直觉得他是个“audacious person(一个果敢的人)”,押上自己的青春。
我告诉他我需要记录的是真实的情况。他说没有什么真不真的,所有媒体宣传都是政治化的。他介意我记下他说的“fuck”。他问我,会有人把钱捐给一个满口脏话的人吗。他的另一些高频词是“接地气”、“正能量”。
这是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他做的任何项目都要调动别人的资源,得到别人的通过。他有的只是时间,嘴皮子,一段名校学历,一个通报给全国的荣誉称号。他倚赖别人的好感才能行事,他也觉得他善于让别人喜欢他。他总想保证,即使是最不开明的群体,也不能挑出他形象上的毛病。他不能得罪任何人。“中国太复杂,我们玩不起。”
尽管难以下定论,但成功的人物特写不仅需要对人物的个性、外在作出描述,还需要对他们的动机作出解释。[45]上文虽然以人物为主角,但主题更多涉及意义和观念,所描写的人物及其处境也充满了复杂的细节和线索。上述引文中,作者与当事人都在阐释主人公及其行为的意义,但显而易见双方产生了巨大分岐。村官秦玥飞描述了他在基层政治中的实践、理想与困难,也讨论了个人的野心与挫折感之后,认为自己是“一个果敢的人”,而记者则在文章开篇就以“一无所有的村外人”来定义他,并在文末再一次提起。
讽刺修辞正是当“更高层次的意义与低层次的意义产生反差时”才成立的。[46]两相对比,写作者的看法显然占据了更高的位置,叙述者显得有更多察觉,有先见之明或事后总结的能力。在其比照下,新闻主角所宣称的信念、希望和信心显得并不能成立,此时一种更深的讽刺感便产生了,而关于人物的故事冲突也得以形成。
此外,除了当事人和写作者之间意义的冲突,讽刺修辞的另一个形式要件,是被描述的叙述主体呈现为一种“无知却自信”(confident unawareness)的状态,他全然不知自己的想法会在另一个层面即读者与作者作为观察者的视角下站不住脚。而仅仅是无知并不会让他成为讽刺的对象,无知的同时还自信,更显得傲慢狂妄,行文中便产生其需要责罚的暗示。[47]《耶鲁村官》一文就使用了这样一种微妙的呈现方式。在写作者的叙事中,新闻主角在回溯其经历及其所面临复杂环境时,显得自以为高明,但其自我叙述却不断出现含混与自相矛盾的情况。如此,被呈现为“无知却自信”的主人公,便成为讽刺修辞的对象和受害者。新闻主角在阅读完稿件后对作者的“指责”,实为一种抗议,是他看到文本中对自己的经验与叙述的再现之后,意识到自己成为讽刺修辞的受害者。
3.修辞效果的另一面:文本的再现偏差与合法性危机
事实性写作使得新闻叙事的讽刺修辞有着比其他文类更为具体的对象。文学作品的讽刺主题更具普适性,如“希望皆是虚妄”,而新闻写作往往只针对一个具体的叙事对象来展现讽刺,如“原本确定的事实并非真相”。[48]事实性写作原则也使得非虚构写作无法像创意写作那样,以最为精湛优雅的行文来完成叙事,但对于具体的写作对象而言,仍可让讽刺修辞发挥效力。这种叙事效力使得新闻文本也可以像戏剧一样建构出鲜明的人物角色,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人物呈现时的再现偏差与写作的合法性危机。
从功能角度来讨论讽刺修辞的传播效果,可发现它可以通过对人物和情境的再描述,起到揭示和纠正的作用。经由详尽调查比证的调查性报道使用讽刺修辞,是为了揭露造成不公平或不合理现象的“恶人”,并对事件中的“受害者”给予声援。同时,讽刺修辞还发挥着纠正的功能,而且当对意义的再次建构一旦完成,读者便不会再次去破坏已被纠正过的意义。[49]这也意味着写作者通过“纠正”原本关于人物的叙述,使用讽刺修辞来重新塑造出人物形象之后,读者的印象便再难颠覆。
有着如此强大的叙事效力,讽刺修辞也可能对文本的叙事合法性产生同样强大的反冲力。以事实性材料来实现讽刺效果的前提是事实的准确性,避免失实仍然是非虚构写作的底线。当文本试图用“事实”来再描述或再定义一个人时,如果事实被证有误或未经多方消息源核实,则变成了空留修辞形式、并未揭露实质的策略性讽刺修辞。《厉害女士》这篇稿件之所以会引发争议,其中一个原因即是其事实出处受到普遍质疑,新闻界同行对该文本的判断是缺少了新闻报道的必要规范,如未充分获取多方证据,未形成关键证据链条;[50]连普通读者也认为其“预设立场,主观痕迹明显,行文表述不严谨、前后矛盾,采访信源明显偏少、可信度差”。[51]当所用事实未经全面证实时,文章开篇却反复“用‘事实上’这三个字来代替证据”,[52]这时对人物言行不一的语言讽刺修辞,便失去了原有的叙事效力,反过来让文本出现了极大的合法性危机。
这篇人物特稿还引发了关于文本类型的讨论,业界人士认为该文“是调查报道的方向,却错穿了一件特稿的外衣”,[53]或“以人物特稿的方式,去操作了一个调查性报道的题材”。[54]这种文本的“错位”,实际上指的是作者在面对一个复杂有争议的采访对象时,使用了调查报道常用的塑造“恶人”形象的修辞。如果仅观《厉害女士》一文,袁厉害“兰考好人”的形象已然被解构,读者本应很难再去推翻这个被解构后重塑的“厉害女士”的印象。但这位处于媒体焦点的新闻人物偏偏存在着多种版本的“真相”,在多元信息的参照下,这篇文章试图以讽刺来塑造人物的强大修辞力量反过来让文本形成了严重的再现偏差。
人物特稿的写作者还可能落入臧否人物的陷阱。当讽刺修辞成为塑造人物的主要方法时,当事人的叙述往往成为被解构的言说,他们对个体经验的阐述也成为与写作者叙述形成反差的“低层次的意义”。这样,写作者以他人的叙述与经验为材料,成为文本的阐释权威。然而这种全知的再描述视角也成为媒介评论的焦点。对《耶鲁村官》一文的媒介批评认为,文章“多处浓墨重彩地对细节加以过度诠释”,对人物的“刻画确实有失公允”,更对作者“是否有资格驾驭特稿”产生了质疑。[55]更有熟悉写作对象的读者反对写作者将主人公定义为“权力的局外人”,他们在新媒体平台上讲述自己眼中秦玥飞的形象和故事来作为对比,并提出文章对主人公所处环境的呈现也有问题,比如对农村人形象的脸谱化处理与俯视视角等。[56]可见,即使讽刺是一种有效的塑造人物的修辞手法,但在人物特稿的实际运用中,也有可能因为其他方面的疏忽或不足而导致文本的合法性危机。
四、结语
小说家可以进入到人物的自省之中,甚至窥破人物的潜意识,他可以在写作中直接谈论他的人物,也可能安排我们听到人物的自言自语。[57]正因如此,虚构人物的各个方面都可被写作者设计得非常清楚可知,“而我们生活中的真人虽说并非个个都是不解之谜,但也是很难理解的”。[58]这即是人物类非虚构写作的难点所在,写作者需要理解复杂的人物,依照事实和引语材料来重述人物经验,但他们不自我标榜为客观报道者,而自认是故事讲述者。将现实材料加工写作成为有着曲折情节和丰满人物形象的报道,成为这些写作者的追求。他们允许自己的主观性呈现在叙事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对比和铺陈事实的手法,让被描述的人物暴露其处境与信念,让普通读者在叙事中也能读出讽刺的意味和结论。
本文分析的两篇人物特稿在事实性写作的同时,都使用了讽刺修辞来呈现冲突、讲述故事,这种修辞对于人物形象有着极强的塑造力,但也引发了关于文本再现偏差的争议。出现再现偏差争议的原因,来自文本传播的各个环节:文本写作时表面的客观写作与实质的讽刺修辞合谋,形成对人物形象的权威刻画;而文本生产一旦完成开始传播,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若出现了关于人物的其他形象或描述方式,便可能引发同行或受众对该文本的批评或争议。本文着重在文本修辞的范围内分析人物特稿写作如何引发对人物的再现偏差,但若更全面地探讨再现偏差这一传播现象,还需对文本写作、传播渠道、文本接收与反馈平台进行考察。尤其是在新媒体平台增多之后,读者往往通过对文本的协商式阅读或对抗式阅读,形成并公开表达出对文本再现偏差的观感。
在信息多元的传播环境下,人物类非虚构写作除了准确性或可验证性的要求之外,还需满足不同于传统新闻写作的规范标准或写作伦理。从业者曾提出过伦理层面的自省:“叙事作者需要如履薄冰,以确保能够同时对当事人和读者做到伦理的诚实”。[59]要将伦理的诚实落实为文本的合法性,还需认识到非虚构写作者不只是描述他人的经验,还要对于通过自己的感知而书写出的他人经验负责任,[60]因此更需要思考如何处理写作者与受访者之间视角不同的问题。写作者若要对写作关系作出进一步的反省,不妨借助叙事研究者的建议,[61]在叙述他人经验时,在双方主体之间保留一种自省式的差异,更多考虑文本是否公允地呈现写作对象的声音,让写作对象的经验以一种更具支持性或互动性的叙事方式被诠释出来。■
①Wolfe, T. (1975). Part one: The new journalism. In T. Wolfe & E. Johnson (Eds.)The New Journalism (pp. 15–68). London: Pan Books.
②FranklinJ.(1994). Writing for Story: Craft Secrets of Dramatic Nonfiction: New York: Plume.
③BishopW. & StarkeyD. (2006). Keywords in Creative Writing.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④Forde, K. (2014). The Fire Next Time in the civil sphere: Literary journalism and justice in America 1963. Journalism, 15(5): 573-588.
⑤BramanS. (1985).The “facts” of El Salvador according to objective and new journalis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9(2): 75-96.
⑥[16]BoyntonR. (2005). The New New Journalism: Conversations with America’s Best Nonfiction Writers on Their Craf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⑦Underwood, D. (2013). The undeclared war between journalism and fiction: Journalists as genre benders in literary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⑧朱强:《译后记》,戴维·福尔肯弗里克主编:《头版:〈纽约时报〉内部解密与新闻业的未来》第191-194页,赵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⑨周逵、顾小雨:《非虚构写作的新闻实践与叙事特点》,《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12期
⑩曾润喜、王倩:《从传统特稿到非虚构写作: 新媒体时代特稿的发展现状与未来》,《新闻界》2017年第2期
[11]Connery, T. (Ed.). (1992). A Sourcebook of American Literary Journalism: Representative Writers in an Emerging Genre. New York: Greenwood.
[12]沃尔夫:《故事的情感内核》,马克·克雷默、温迪·考尔主编:《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第193-200页,王宇光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13][18][35]Aucoin, J. (2001). Epistemic responsibility and narrative theory: The literary journalism of RyszardKapuscinski. Journalism, 2(1): 5–21.
[14]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5]BaymG. (2017). Journalism and the hybrid condition: Long-form television drama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news and narrative. Journalism, 18(1): 11-26.
[17]Harbers, F. &BroersmaM. (2014). Between engagement and ironic ambiguity: Mediating subjectivity in narrative journalism. Journalism, 15(5): 639–654.
[19]MitchellP. (2014). The ethics of speech and thought representation in literary journalism.Journalism15(5): 533-547.
[20]SofferO. (2009). The competing ideals of objectivity and dialogue in American journalism.Journalism10(4): 473–491.
[21]HarringtonW. (2007). Towards an ethical code for narrative journalism. In M. Kramer & L. McCall (Eds.)Telling True Stories (pp. 170–172). New York: Plume.
[22][36]GreenbergS. & WheelwrightJ. (2014). Literary journalism: Ethics in three dimensions. Journalism, 15(5): 511-516,第512页
[23][45]巴纳金斯基:《人物特写》,马克·克雷默、温迪·考尔主编:《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第98-102页,王宇光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24]卫毅:《人物特稿就是去掉报告文学背后的金光》,周逵主编:《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第55-8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5]莱曼:《将故事和观念融合》,马克·克雷默、温迪·考尔主编:《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第153-157页,王宇光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26][43]Harrington, W. (Ed.). (1997). Intimate Journalism: The Art and Craft of Reporting Everyday Life, Thousand Oaks, CA: Sage.
[27]纳尔逊:《塑造人物》,马克·克雷默、温迪·考尔主编:《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第171-174页,王宇光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28][32]ChaseS. (2005). Narrative inquiry: Multiple lenses, approaches, voices. In N. K. Denzin& Y. S. Lincoln (Eds.)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pp. 651-679). Thousand Oaks, CA: Sage.
[29]格拉德威尔:《人物特写的局限》,马克·克雷默、温迪·考尔主编:《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第106-108页,王宇光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30]林珊珊:《人人都会讲故事》,周逵主编:《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第223-24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1]凯瑟林·博:《真相与后果》,马克·克雷默、温迪·考尔主编:《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第224-226页,王宇光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33]Lincoln, Y. &DenzinN. (2000). The seventh moment: Out of the past. In N. Denzin& Y. Lincoln (Eds.)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1047-1065).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34]BuozisM. & Creech, B. (2017). Reading news as narrative: A genre approach to journalism studies. Journalism StudiesArticle first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62017https://doi.org/10.1080/1461670X.2017.1279030.
[37][42]Ettema, J. &Glasser, T. (1994). The irony in – and of – journalism: a case study in the moral language of liberal democracy.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4(2): 5–28,第22页
Forde, K. (2014). The Fire Next Time in the civil sphere: Literary journalism and justice in America 1963. Journalism, 15(5): 573-588.
[38]SongY. & LeeC. C. (2015). The strategic ritual of irony: post-Tiananmen China as seen through the ‘Personalized Journalism’ of elite US correspondents. MediaCulture & Society37(8)1176-1192.
[39][40][44][46][47][48]Muecke, D. (1969).The Compass of Irony.London: Methuen Publishing,P82、23、30、24.
[41]EttemaJ. &Glasser, T. (1988). Narrative form and moral force: the realization of innocence and guilt throug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8(3): 8–26.
[49]Booth, W. (1974). A Rhetoric of Irony. 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0][53]叶铁桥:《缺乏阅历的报道者选错了报道手法》,《新闻界》2013年第6期
[51]见知乎网站关于《厉害女士》一文的讨论: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764556
[52]杨江:《从〈厉害女士〉一文看媒体立场预设》,《新闻记者》2013年第3期
[54]张志安:《批评性人物报道的操作策略——简析人物杂志〈厉害女士〉报道》,《新闻记者》2013年第3期
[55]远浪:《耶鲁村官特稿风波:技艺的大师,伦理的局外人?》,2016年10月3日发布于“北窗”微信公众号:lightthere
[56]见知乎网站关于《耶鲁村官秦玥飞:权力的局外人》一文的讨论: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020051
[57]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第78页,冯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58]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第437页,周铁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59]沃尔特.哈林顿:《叙事记者的伦理守则》,马克·克雷默、温迪·考尔主编:《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第217-219页,王宇光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60]HarringtonW. (2003). What journalism can offer ethnography.Qualitative Inquiry9(1): 90-104.
[61]Chase, S. (2005). Narrative inquiry: Multiple lenses, approaches, voices. In N. K.Denzin& Y. S. Lincoln (Eds.)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pp. 651-679). Thousand Oaks, CA: Sage; 周佩霞、马杰伟:《视觉政治及道德伦理:纪录片〈麦收〉引起的争议》,《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总第9期
邓力系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本文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转型期社会冲突事件中的媒体角色与公众认知”(14SHC035)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写作同时受到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