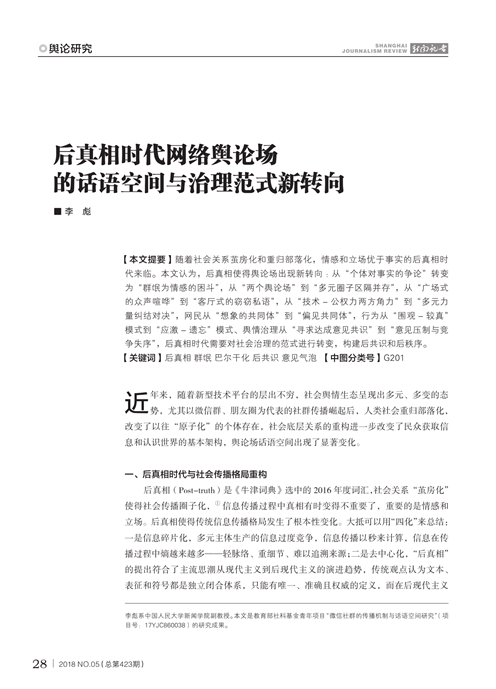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与治理范式新转向
■李彪
【本文提要】随着社会关系茧房化和重归部落化,情感和立场优于事实的后真相时代来临。本文认为,后真相使得舆论场出现新转向:从“个体对事实的争论”转变为“群氓为情感的困斗”,从“两个舆论场”到“多元圈子区隔并存”,从“广场式的众声喧哗”到“客厅式的窃窃私语”,从“技术-公权力两方角力”到“多元力量纠结对决”,网民从“想象的共同体”到“偏见共同体”,行为从“围观-较真”模式到“应激-遗忘”模式、舆情治理从“寻求达成意见共识”到“意见压制与竞争失序”,后真相时代需要对社会治理的范式进行转变,构建后共识和后秩序。
【关键词】后真相 群氓 巴尔干化 后共识 意见气泡
【中图分类号】G201
近年来,随着新型技术平台的层出不穷,社会舆情生态呈现出多元、多变的态势,尤其以微信群、朋友圈为代表的社群传播崛起后,人类社会重归部落化,改变了以往“原子化”的个体存在,社会底层关系的重构进一步改变了民众获取信息和认识世界的基本架构,舆论场话语空间出现了显著变化。
一、后真相时代与社会传播格局重构
后真相(Post-truth)是《牛津词典》选中的2016年度词汇,社会关系“茧房化”使得社会传播圈子化,①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有时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立场。后真相使得传统信息传播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抵可以用“四化”来总结:一是信息碎片化,多元主体生产的信息过度竞争,信息传播以秒来计算,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熵越来越多——轻脉络、重细节、难以追溯来源;二是去中心化,“后真相”的提出符合了主流思潮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演进趋势,传统观点认为文本、表征和符号都是独立闭合体系,只能有唯一、准确且权威的定义,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文本、表征和符号都是开放的动态系统,对任何事物哪怕是“真相”所做的阐释都可以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在具体的实践中,全球化并未朝向整合方向发展;三是部落化,后真相时代民众为追求情感共鸣必然需要“抱团取暖”,人类在网络空间重新数字部落化;四是偶像化,“谁说的”比“说什么”更重要,用“谁说的”来决定是否相信,有“我支持的人所说的就是真的”心态。
可以说,社群是后真相时代的硬件,信息的圈子化传播造成了立场先行的后真相时代来临;情感是后真相时代的软件,情感使得网民抛弃对事实真相的追索,转为情感宣泄和寻求归属感,而这两个要素恰恰是舆情演变的新趋向。舆情已经从以往单纯的信息流动的事实传播1.0时代,转变为以情感传导和关系嵌套的复合传播2.0时代。某种意义上说,后真相时代就是舆情2.0传播的底色和历史坐标,舆情研究范式也从以往的单向度的信息维度转化为“信息-情感-关系-行为”的多元维度。
二、舆情2.0:后真相时代舆论场的话语空间新转向
根据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观点,社会舆论场作为社会元场域的一个子场域,必然受到大的媒介、政治和文化环境等元场域的影响,②后真相时代使得舆论场在话语空间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向,进入了舆情2.0时代。
(一)舆情本体:从“个体对事实的争论”转为“群氓为情感的困斗”
真相时代,民众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大抵追求的是事实真相,通过围观-倒逼形成话语权力压制来获得真相,但在后真相时代,事实真相经过“七嘴八舌”无数次地再阐释甚至是故意扭曲与篡改,其本身不再是事实真相的核心,而是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从大的元场域来说,“后真相”其实是社会分化和社会焦虑下的产物,每当出现医患、师生和警民矛盾等事件时,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其实不完全是就事论事,而是基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体验“迁移”于此,把之前的感受“代入”,进行简单的情绪宣泄,从对事实的争论转变为情感的困斗。正如2018年初刷屏朋友圈的《如何写出阅读量100W+的微信爆款文章?》中咪蒙总结的那样:“大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众不是想看你怎么表达你自己,而是想看你怎么表达我。要体察到人性的痛点,表达大众的情感共鸣。” ③咪蒙的文章很大程度上都是放大情感,引发共鸣,对于其粉丝网民而言,在他们看到这些带有激烈观念或情感的观点时,内心一定是有共鸣而深信不疑的,不再理会这些观点或情感实际上是矛盾的,更不管论证推理的逻辑是否经得住推敲。这些单纯而强烈情感的力量比现象背后复杂多维的社会现实更富有传播的魔力,传播中需要的是这些符合情感信念的事实而不是事实真相本身。
(二)场域结构:从“两个舆论场”到“网络社群巴尔干化”
长期以来,“两个舆论场”一直是官方与学界解释当下舆论场结构的重要概念,即一个是以大众媒体主导的“官方舆论场”,一个是互联网中的“草根舆论场”,这种提法既承认了舆论场的对立分化又为观察舆论场提供了简单有效的视角。但随着社交网络时代来临,不同的网民开始基于血缘、地缘、学缘、业缘和趣缘等形成独立的圈子,以往铁板一块的草根舆论场进一步圈子化,相较于高高在上的主流媒体,网民们更愿意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寻求精神慰藉,获取归属感。换言之,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Echo Chamber)效应和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效应使得一个个圈子的“内壁加厚”,圈子和圈子沟通与对话的难度在逐步加大——圈子内部的人抱怨其他圈子的人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圈子,希望与其他圈子交往,但又以固有的偏见打量着外部世界,如日益刻板印象化的医患关系、师生关系和警民关系等。以往“两个舆论场”非此即彼的结构格局被一个个分散到不同社交网络平台的多元“圈子”所取代,这些圈子类似于打地鼠游戏中的一个个“地洞”,表面是开着口,期待与其他圈子沟通但实际上却是隔着厚厚的“内壁”,进而加剧了社会群体的撕裂,分裂成有特定利益的不同子群,即网络社群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愈发明显。
另外,圈子内部的表达并非是理性平等的对话,由于圈子是基于熟人网络的转移,把线下的社会资本带入线上的虚拟圈子中,很容易形成与线下熟人网络一样的话语权力结构。另外,圈子内部也存在话语权的争夺,为了能在圈子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很多成员表现特别偏激。正如《乌合之众》中所表述的,任何时代的领袖(包括意见领袖),都是特别偏激的,偏激的观点才具有煽动性,话语表达必须简单粗暴,情绪明确,爱憎分明的人更容易在圈子内部得到拥护,产生虚妄的成就感,激发其他成员表达更加偏激的观点,最终形成了只诉诸情感不诉诸理性、抱团对抗的“不加思考”行为模式。
(三)话语表达机制:从“广场式的众声喧哗”到“客厅式的窃窃私语”
微博时代话语表达更像是在大的广场上大家一起叽叽喳喳各抒己见,这中间可能会存在小圈子,但所有人的声音如果想去听的话都可以听到。随着社群传播时代来临,本应在网络公共领域开展的正常讨论,越来越转向隐匿化、完全封闭的小圈子,更像躲在自家的客厅里“窃窃私语”。由于圈子内成员大抵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信息大多经过了“立场过滤”,与之相左的信息逐渐消弭,“意见茧房”形成。这种表达机制是符合人类最初始的群体组织的。社会学中有经典的150定律,由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该定律是根据猿猴的智力与社交网络推断出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50人。会客厅式的话语表达使得圈子内部的归属感更为强烈,因为熟人网络情感支持的正效应,具有情绪放大和制造虚拟社会环境进而形成虚拟社会认同的作用,很容易形成意见一致的“意见气候”,因此作为数字部落的成员,很容易使得人们失去彼此辩论的机会和勇气。在圈子内部制造的“数字泡沫”中,就很容易情绪化,甚至极端化,形成群体极化现象,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利的。
(四)权力主体:从“技术-公权力两方角力”到“多元力量纠结对决”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的舆情发展,基本上是技术在推动着舆情生态演变,从晚报、副刊的兴起,到都市报的蓬勃发展,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风起云涌,BBS、贴吧、SNS和现在微博、微信、微视频及新闻客户端多元格局,背后的逻辑线就是技术演进使得话语权被不断释放。微博使得民众人人具有“麦克风”,有了公开表达的权利;微信使得民众人人都有“圈子”,获得了社群归属感。政治力量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对技术进行了一定的规制,两者的不断角力是舆情1.0时代的显著特点。
近年来互联网寡头格局形成,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三家技术新贵开始介入话语表达平台,越来越具有“超国家”的能力。资本对舆论生态的干扰最典型的体现是2016年赵薇执意在其导演的电影中与“台独”艺人戴立忍合作引起网民愤怒,之后资本的力量在微博上删除反对言论,强压舆论。在一些公共事件中,部分商业资本通过话题排序、关键词过滤、网页删除等手段对舆论进行隐性控制,并且每次公共事件都最终成就若干个微信营销大号,很多热点舆论背后往往是“带血的10万+”。如杨改兰事件中在朋友圈刷屏的“盛世蝼蚁”,就是一个财经公众号“格隆”为营销而进行的炒作。
2017年,境外敌对势力从幕后到前台,在国内公共热点事件中移花接木炮制虚假新闻和网络谣言,混淆视听,扰乱舆论生态。如泸州太伏事件中流传最广的视频是由法轮功组织的新唐人电视台移花接木炮制出来的;北京红黄蓝事件爆料人“Reginababy_lsy”的微博注册地是美国,并且在这个事件中一幅含沙射影污蔑“老虎团”的漫画也被大肆传播,作者郭某某是一名由国内逃往美国的法轮功分子……近年来,境外反华势力大力开发网络虚拟机器人,进行机器自动发帖,编造大量政治谣言企图由境外向境内倒灌,这些行径扰乱了本已错综复杂的国内舆论生态。这意味着,社会舆论生态的权力主体已经由1.0时代的技术-政治两元力量向2.0时代的技术-政治-资本-境外势力多方角力的战场。
(五)网民主体:从“想象的共同体”到“偏见共同体”与“行动共同体”
“想象的共同体”由本尼迪克特·安德尔森提出,他认为印刷资本主义是民族主义建构的关键,是凝聚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必要技术手段。印刷品等为读者提供了“虚拟的共时性”,并使他们经由这种共时性而产生共同体想象,仿佛他们仅仅操持同种语言便息息相关似的。④现代传播手段从印刷术跃进到网络技术时代,新的传播手段依然遵循“提供虚拟共时性——凝聚共同体想象”的路径,只是不再仅仅局限于民族主义,不同阶层的网民在互联网这个大平台被凝聚,形成了全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在舆情1.0时代,一旦发生了社会公共事件,民众在平台上各抒己见,最终改善线下社会公共治理,尤其是以孙志刚案为标志,网民开始作为独立的话语表达主体登上社会舆论场,“天下网民是一家”、网民是弱势族群成为这一时期“想象的共同体”。
后真相时代,“立场”已赤裸裸地压制“事实”,虽然在历史上不乏一时被“立场”所蒙蔽的时期,但过去人们还是会承认“事实”比“立场”更加神圣,如今一些谎言、谣言之所以能够“披着真相的外衣”在新媒体上大行其道,绝不是因为谎言已经被指鹿为马为“事实”,而是因为人们认为虚假信息中蕴含的“立场”比“事实”更加重要。在大众媒体祛魅的时代,谎言和“事实”此起彼伏,人们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第一反应往往是相信自己的感觉,跟着感觉走,之后一旦出现了与自己直觉相悖的证据,人们就会倾向于选择性忽视,不以达成意见共识为目的,只是追求情绪宣泄。拥有共同偏见的人聚合在一起,“想象的共同体”被窄化了,形成一个个“偏见的共同体”,如陕西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中,民众下意识地将对医生群体存在的偏见进行了集中放大。
偏见的共同体在虚拟认同的刺激下又转化为行动的共同体,如李小璐留宿事件中,PG One的粉丝自发捐款购买热搜词,抹黑抨击其偶像的紫光阁杂志公号;北京大兴火灾后,一些人组织起来为相关人员提供住宿和工作机会等等,这些都从偏见的共同体转化为行动的共同体。
(六)网民行为模式:从“围观-较真”模式到“应激-遗忘”模式
在真相时代,一旦发生舆情事件,民众会自发地在网络上进行围观,“围观改变中国”,在网民的凝视之下,社会事件得以解决。这是一种“围观-较真”行为模式,如持续三年之久的正龙拍虎事件,最终以周正龙被抓、官方道歉为结局。
后真相时代,情感太多,事实已经不够用了。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壁垒更加坚实,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池塘,都像是自己池塘边的青蛙,信息理解变短变浅,偏见与偏见的人交锋,只是情绪的冲撞。人们只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立即反应,然后遗忘。面对舆情事件的发生,一个个的小圈子成员开始探出脑袋来关注,这是一种下意识的看热闹行为,是一种应激机制,但只诉诸情感发泄不关注事实真相,不加思考地与当事人同悲同喜,情感付出廉价,但不再像以前那么较真,只是“逢场作戏”地关注自己圈子内部的“小确幸”(小而确定的幸福)。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近年来舆情事件反而让人感觉少了,其实客观上并没有少,只是人们是用一种全新的“应激-遗忘”行为模式来对待这些事件罢了。
(七)舆情治理:从“寻求达成意见共识”到“意见压制与竞争失序”
真相时代的舆情治理,公权力部门无论是积极回应还是消极应对,最终都以达成意见共识为目的,并且在客观上促进了公共治理的改善。如孙志刚案之后政府宣布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这一时期网络议题的管理最终往往伴随着公共政策的改善。
后真相时代,由于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KOL)的退场、转场而被削弱,以往官方-意见领袖-民众的二级意见流动模式转变为官-民直面模式,缺少意见领袖的缓冲,在公共危机事件面前官民直接面对,再加上刻板成见效应,很容易引发舆情波动。公权力部门想不明白:以往“屡试不爽”的舆情应对方式怎么失灵了——发了情况通报、解释了真相为什么还是没有人相信?这是因为民众从寥寥几句的情况通报中看不出自己想要表达或者被慰藉的情感,事实真相在公权力部门与民众之间的互相撕扯下已经支离破碎,公权力机关需要民众“静下来不要闹事”,而民众觉得自己的立场与情感没人关注,事实真相已经不重要了,“解惑”不如“解气”来得更真实。
个别部门领导虽然在意网络舆情,但在实际运作中对舆情报告的写作要求“定制化生产”——在立场预设的前提下为其提供舆情报告,构建了不实的意见环境,再加上个别政府部门也没什么经验来进行社会对话,疏解情绪淤积,后真相时代的舆情处理不再是以达成各方意见共识为目的,而是以达成一元意见为目的;处理舆情事件也不再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消除负面信息成为下意识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网民感觉到烂尾新闻有始无终,意见竞争以简单的意见压制而告终,事件处理以多输为结局。无论是雷洋事件的删帖处理还是北京红黄蓝事件中的“硬盘背锅”,这些事件并没有足以使得各方意见达成共识,只是通过简单的优势意见压制而告终,意见竞争呈现失序状态。
三、从后真相到后共识和后秩序:网络社会治理范式的新转向
后真相时代“事实”的唯一解释性被消解,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事实的“塑造”,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对“事实”的解释权还给了每个人。另外,后真相的确带来了非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非理性都是不好的,在莫斯科维奇看来,“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反倒没有多大用处,它既不能带来音乐,也不能带来美术”。⑤勒庞也认为,民众的非理性才是历史前进的深层动因,“尽管理性永远存在,但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就像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这些东西”。⑥但问题是后真相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将泛滥的情感宣泄进行有效引导,发挥非理性的最大价值,实现社会新型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解后真相的是后共识。后共识并非是对事实真相本体的共识,而是对说真相者和真相表达方式的共识,要实现后共识必须重构舆情1.0时代的社会治理范式,构建后真相时代的舆情治理“后秩序”。
(一)思维范式转变:用“意见博弈的正和思维”来代替“零和斗争思维”
“后真相”带来了社会分化、焦虑和撕裂,但并不是必然会发生,即使发生,其烈度也可以以缓和的形式出现,处理的方式不能硬碰硬,更不能劈头盖脸地单向度打击别人,偏执化地维护自己。后真相时代柔性思维更为重要,因为情感相比事实就是柔性的。舆情管理不能总想着剥夺别人发言的权利而令自己的声音更大来压制反对声音,这是一种零和斗争思维,最终往往造成多输的结局。2017年底之所以舆情热点事件不断,主要的原因一是上半年的舆情势能被压制,二是公权力强力介入公共话语讨论。代替零和思维的是正和思维,该思维认为博弈中的双方利益都将增加,至少一方利益增加、另一方利益不受损害。由此出发,就会把如何促进意见共识和对话放在首位,会通过合作(甚至妥协)来博弈。正和思维其实也是一种增量思维,在通过正和思维创造增量的同时,要注意增量分配适度向相对弱势的意见群体倾斜,以矫正当前社群意见过于分散的状态。正和思维有利于正向对冲情绪宣泄泛滥的现实,增加社会意见竞争的柔性。同时要不断对当前舆情治理思维和方向进行反思,不走极端,以此寻求意见的和合之道和情绪宣泄的引导之法。
(二)治理路径选择:破除社群的“回声室”、“意见气泡”负效应,建构重叠共识
社交网络时代,社会的组成单元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网民个体,而是一个个抱团的社群,舆情治理客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往针对个体形成的舆情应对模式从根本上失去了效力。只要是圈子就会存在回声室效应——信息被圈子壁垒不停地重复反弹,以至于无论该信息是否是真的,圈子内的每一个人都最终会相信,并且圈子外部的任何信息,都很难在这个圈子中传播或者不会到达圈子中——“回声室”使得圈子内部产生“意见泡沫”,不同圈子之间又各说各话,“信者愈信”,⑦很容易出现观点极化和同质化。要改变这种极端现象,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打破回声室,让圈子里的人看到更大的世界,“让装睡的人没法睡得好”,让数字部落里松动的人慢慢走出去,主要路径是将各个圈子的共识进行显性化,进而重叠共识;二是凝聚各数字部落,解除“部落”中的身份枷锁及“偶像必定是对的”等偶像化误解,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构建对话平台,放大优势意见,寻找最大公约数,建构最大共识。
(三)话语空间重构:警惕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合谋”
圈子是后真相的底层框架,情感是后真相的纽带,这恰恰与网络民粹主义异曲同工。莫斯科维奇认为:“人类这种东西不能承受太多的真相。群体所能承受的就更少。一旦人们被聚集在一起,并融为一个群体,他们就失去了各自的鉴别力……他们理解的唯一语言是那种绕过理性,直接向灵魂讲述的语言,这种语言所描述的现实比实际的情况既不更好,也不更坏。” ⑧在他看来,人们在民粹主义的运动中,不仅失去了鉴别力,而且丧失了理性。情感逻辑是驱使网民行动的逻辑,很容易让从众的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或义愤填膺,从而失去判断力,在狂热的围观之下以庸俗正义之名集体作恶。因此,必须需要警惕后真相与民粹主义的“合谋”。
“随着平民意识的觉醒,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裂痕的加大,平民大众不再将自身的权利诉求于精英与政客,并开始走向政治前台”。⑨民众的崛起已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重要政治现象。因此,必须将民粹表达与精英话语之间的冲突限定在现有政治秩序的轨道之内发泄与平息,这才是未来舆情治理要义所在。
(四)底层技术支撑:技术的“锅”技术来背,互联网具有耗散结构属性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技术的发展是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是在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状态下演进的,具有耗散结构特性。以往的技术都是在人类原有操作系统上的一个个“应用”,好比APP之于苹果系统,而互联网改变的是社会结构底层的人际关系,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不是简单地嵌入而是重构和彻底格式化原有的社会系统。同时互联网作为一种新技术也具有自平衡属性,有研究者对技术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算法技术让资本和技术“合谋”,通过“贪嗔痴”的推送模式帮着人们做决定,人人都成为被投喂的Feed怪兽。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技术带来了“后真相”,后真相带来的一切问题也可以由技术本身来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
当前舆情研究还多停留在1.0时代,即只考虑信息的流动,而忽略背后的“情绪”和“关系”,舆情发生后好比泼出去的水,往何处流具有随机性,但背后不变的是社会情绪和传播关系网。上帝在打开社交网络技术这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大数据、情感计算和机器学习等技术之门,2018年初火起来的区块链技术、数字对象体系架构(Digital Object Architecture,DOA)技术等,都有助于从底层彻底解决目前舆情研究失灵的问题,将虚拟社群在底层技术框架下留下的“蛛丝马迹”进行机器学习研判,在此基础上辅以情感计算等模型,可以准确地研判社会情绪走向和痛点,改变舆情研究重信息轻情绪、重描述轻研判的现状。
结语:从“威权精英”到“庸众社会”
后真相时代,全球信息传播平面化、圈子化带来了对于事件真相认识的方式、方法的重大转变。如果说20世纪是威权政治时代,那么21世纪则是庸众社会。庸众是个中性词,即平民社会,一定程度上特朗普的当选就是庸众社会形成的标志,以希拉里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精英因忽略了“庸众”而最终尝到了苦头。网络公共领域是现代性社会的重要表征,它不是单纯的“意见束”,不是各种意见的简单重合,而是在传统社会中嵌入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各种意见在其中不是压制而是对话与沟通,达到正和有序竞争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有序运行,否则只要“庸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网络空间的意见波澜总会此起彼伏。■
①李彪:《社会舆情生态的新特点及网络社会治理对策研究》,《新闻记者》2017年第6期
②[法]布尔迪厄等:《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2页,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③《如何写出阅读量100W+的微信爆款文章?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603/02/43812370_659438085.shtml
④⑧[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167页,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
⑤[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第5辑)》第32页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⑥[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6页,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⑦董晨宇、孔庆超:《后真相时代:当公众重归幻影》,《公关世界》2016年23期
⑨龚群:《后真相时代与民粹主义问题——兼与吴晓明先生唱和》,《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
李彪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本文是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微信社群的传播机制与话语空间研究”(项目号:17YJC86003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