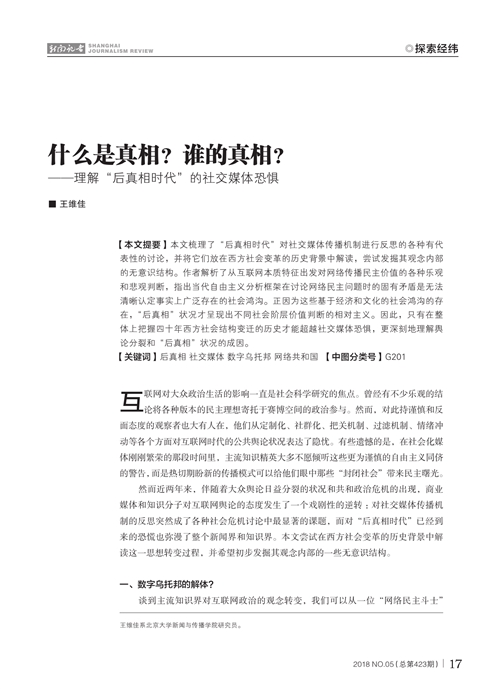什么是真相?谁的真相?
——理解“后真相时代”的社交媒体恐惧
■王维佳
【本文提要】本文梳理了“后真相时代”对社交媒体传播机制进行反思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讨论,并将它们放在西方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中解读,尝试发掘其观念内部的无意识结构。作者解析了从互联网本质特征出发对网络传播民主价值的各种乐观和悲观判断,指出当代自由主义分析框架在讨论网络民主问题时的固有矛盾是无法清晰认定事实上广泛存在的社会鸿沟。正因为这些基于经济和文化的社会鸿沟的存在,“后真相”状况才呈现出不同社会阶层价值判断的相对主义。因此,只有在整体上把握四十年西方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才能超越社交媒体恐惧,更深刻地理解舆论分裂和“后真相”状况的成因。
【关键词】后真相 社交媒体 数字乌托邦 网络共和国
【中图分类号】G201
互联网对大众政治生活的影响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曾经有不少乐观的结论将各种版本的民主理想寄托于赛博空间的政治参与。然而,对此持谨慎和反面态度的观察者也大有人在,他们从定制化、社群化、把关机制、过滤机制、情绪冲动等各个方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公共舆论状况表达了隐忧。有些遗憾的是,在社会化媒体刚刚繁荣的那段时间里,主流知识精英大多不愿倾听这些更为谨慎的自由主义同侪的警告,而是热切期盼新的传播模式可以给他们眼中那些“封闭社会”带来民主曙光。
然而近两年来,伴随着大众舆论日益分裂的状况和共和政治危机的出现,商业媒体和知识分子对互联网舆论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逆转:对社交媒体传播机制的反思突然成了各种社会危机讨论中最显著的课题,而对“后真相时代”已经到来的恐慌也弥漫了整个新闻界和知识界。本文尝试在西方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中解读这一思想转变过程,并希望初步发掘其观念内部的一些无意识结构。
一、数字乌托邦的解体?
谈到主流知识界对互联网政治的观念转变,我们可以从一位“网络民主斗士”的经历中体会这一过程:瓦伊尔·高尼姆(Wael Ghonim)来自埃及,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网络行动主义的传奇人物。在那场常常被称作“推特革命”或“脸书革命”的北非政治动荡中,他成功地利用社交媒体激发起了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也由此成为全球主流舆论推崇的英雄人物。
作为开罗美利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谷歌集团的工程师、穆罕默德·巴拉迪的铁杆支持者和独裁政府曾经的阶下囚,高尼姆身上所具备的政治潜质非同一般。他既生活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又分享着“全球市民社会”的价值共识,并自愿在“封闭的专制社会”中将之付诸实践——所有这些社会标签和价值标签集合在一起,使他成为西方民主建制派眼中最受欢迎的那类自由战士,也成为国际主流舆论垄断埃及革命解释权的一个重要声音。2011年,《时代》杂志将高尼姆选入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人士(“Time 100”);世界经济论坛也将他选为全球青年领袖,一系列荣誉纷至沓来。
2012年,高尼姆将他在埃及政治运动中的网络动员经验集纳成一本专著——《革命2.0:人民的力量胜过当权者》。①在此书中,这位网络时代的英雄分享了当时最为积极的政治愿景:社交媒体的繁荣将带动草根革命,推动民主参与,推翻独裁统治并最终构建理想的市民社会。《纽约时报》的书评大胆预言:“此书将成为未来不断强化的无边界数字运动的试金石,这些运动将持续瓦解权力体系,无论它是企业集团还是国家政权”。②然而,不过三五年时间,被网络民意持续瓦解的“权力体系”竟成了民主建制派自身。伴随着极端组织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扩散、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出人意料”的结果,各种右翼政党和社会运动借力新媒体手段的广泛兴起,以及欧美社会中按照教育程度高低和地域差别形成的意见对抗……与全球化理念相伴而生的自由民主体系正在被拖入困境,社会舆论日益分裂的局面已经带来了无法回避的共和危机。此时,在民主建制派眼中,数字乌托邦的美好愿景已经支离破碎,一场对社交媒体的恐慌开始在主流媒体和知识精英中蔓延。
这一观念转变集中体现在高尼姆的最新言论中(此时他已是哈佛大学的智库研究员)。在2016年的TED演讲中,高尼姆开场的第一句话是:“我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要解放一个社会,你所需要的只是互联网,然而,我错了!” ③
二、要解放社会,先解放互联网?
高尼姆的TED演讲似乎是代表所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后真相时代”做出的忏悔。他总结了当下社交媒体引发社会分裂的几个主要原因:缺少核查机制的谣言传播、缺少多样观点的回音壁效应、缺少辩论程序的极端表达、缺少慎思明辨的情绪冲动,以及缺少对话意识的自我展示。这些缺陷促使高尼姆重新思考互联网的民主价值,并提出重新“设计”社交媒体,以便让自由主义的各种论辩原则更好地呈现在网络空间,正如他最后的总结:“要解放社会,先解放互联网。” ④2017年秋,在网络舆论状况最令知识精英感到迷茫的那段时间里,高尼姆又与人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集中阐述他“解放互联网”的方案,即让社交媒体平台摒弃以商业利益为驱动的算法,并保证算法输出的透明化。他们建议,平台企业应该开发一个基于公共利益原则的数据接口,将必要的公共信息、广告信息和审查信息向社会公开。⑤工程师出身的高尼姆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提供的方案虽然在技术上不难实现,却是在向信息传播业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基本市场规则进行挑战。且不论公共利益信息的界定有多困难,这种外部审查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商业情报问题、数据所有权问题、个人隐私问题等等都早已是市场社会无法撼动的法权根基。我们很难想象在不挑战信息传播业市场属性和公司化运行模式的前提下,高尼姆这套要求提高透明度的方案有任何付诸实践的可行性。在社会舆论重压之下,承诺进行内部机制调整恐怕已经是脸书、推特这些上市企业能够做到的极限了。或者可以说,马克·扎克伯格们已经是在本着政治责任,而不是法律义务来进行内容、算法和广告模式的自我审查了。那么问题来了,高尼姆这类进步自由主义者们有意识、有胆量更进一步去挑战整个信息传播业的资本主义体系吗?
如果说高尼姆的方案是从平台运行的“后台”解决问题,那么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尝试从信息发布的“前台”解决问题。“事实核查新闻”就是这类努力中最典型的代表。根据杜克记者实验室(Duke Reporters’ Lab)2018年的最新统计,在短短四年间,伴随着对网络信息乱象的恐慌,全球事实核查网站的数量上升了239%,从44家一跃增加到149家。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开始加入阻遏网络谣言的队伍,努力防止虚假信息干扰大众的政治判断。这些捍卫真相的工作固然十分可敬,但是面对庞大复杂的网络信息,也着实显得势单力薄。更重要的是,在共和危机愈演愈烈的前提下,谣言的举证并不能从根本上消弭社会分歧。正如《经济学人》那篇著名的封面文章《谎言的艺术》所说,“后真相”之所以为“后”,是因为真实与否已经降低到了次要位置,不同的人群只选择相信符合他们各自偏好的信息。⑦
三、走向数字化独裁?
从高尼姆“重新设计”社交媒体的倡议到新闻记者们可敬的“事实核查”努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是一个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的消极过程,而似乎是一个从乌托邦到“更高级的”乌托邦的执迷不悟的过程。相比这些建设性的讨论和积极的行动主义,很多更具学理性的分析由于触及互联网政治一些深层问题而做出了比较悲观的判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已经再版两次的《网络共和国》⑧和帕里泽(Eli Pariser)的《过滤气泡》,⑨两位作者都认为基于使用者个人选择的网络传播通过无限的信息过滤破坏了公共生活本该具有的文化多样性,而且使得媒体传播的大众涵化功能严重退化,推动了社会意见极化和共和政治的危机。马修·辛德曼(Matthew Hindman)的《数字民主的迷思》一书则是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证明网络信息的每一个层次都遵循着赢家通吃的模式,赛博舆论场本身的结构性局限导致了公共讨论的多元性被严重抑制。⑩这些著作的很多经验材料都来源于社交媒体繁荣之前的网络传播状况,由此可见,要“解放互联网”并不是改变平台算法和盈利模式那么简单。
虽然以上的分析总体倾向悲观,但他们至少还是假定网络空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而随着2018年《卫报》等媒体对剑桥分析公司大规模操控网络舆论的曝光,外部权力肆意介入传播过程并操控网民态度的事实几乎淹没了所有对社交媒体的积极期盼。8000多万脸书用户的数据被非法获取并导入大数据模型分析,进而根据分析结果投放相应信息以控制人们的情感和行为。[11]这个听上去像反乌托邦小说一样的新闻故事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后真相”状况的恐慌。结合前些年各种新闻报道中盛传的俄罗斯网络水军故事,特别是圣彼得堡的互联网研究中心(Internet Research Agency)在脸书、推特等平台上开设大量虚假账户扰乱欧美舆论场的事件,[12]社交媒体平台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了孕育各种政治阴谋和民意操控的温床。对此,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惊呼可能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社会精英的恐慌:“过去两年的历史渐渐清楚表明,社交网络对民主制度的威胁比独裁统治更加严重!” [13]在现代化的历程中,知识分子们表达出对一种传播工具或传播技术的恐慌情绪并不是罕见的思想史现象,它与那些崇拜新媒体、新技术的乌托邦观念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通过强调传播工具本身的特性来假定并解释它们引发的社会关系变化。正如弗格森这类建制派知识分子将长期复杂经济状况下形成的社会危机完全转嫁给社交媒体和邪恶的外部力量。与其说这是知识分子判断力的羸弱,不如说是他们对深层社会矛盾的无意识回避。
在此,我们重新强调一下“后真相”概念的本意或许会获得些许启发。与“网络谣言”、“虚假信息”和“宣传操控”等话题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后真相”并不强调信息准确与否的重要性,而是强调舆论分裂和极化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他们更愿意接受的信息,并将其当做“真相”。可见,问题的关键症结不在于传播过程之中,而在于传播过程开始之前的情绪和立场。
四、言论自由的社会边界
为了探析社交媒体恐惧的深层意识结构,我们需要先脱离对互联网问题的直接讨论,而把时间倒回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看看现代言论自由学说的精神原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 S. Mill)这位“自由主义之圣”曾经审慎地评价过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民主状况的观察。他指出,托克维尔的美式政治平权不适用于英国,原因在于两国的阶级分布有差异:与美国社会财富分布比较平均的状况不同,[14]当时的英国存在数量庞大的劳动阶级。在密尔看来,在民主政体中,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劳动者掌权的可能性,他们既没有以财产为基础的理性决断能力,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育,不可能恰当地行使权力;其二是“多数人的暴政”,或者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自由的窒息。密尔认为,这种危险在美国已经体现出来,它最终将导致社会的僵化。[15]密尔,在以赛亚·柏林笔下是“自由的最热心斗士”,[16]他凝结在《论自由》一书中对言论自由的经典阐述几乎是研习大众舆论问题的必读著作。而以上对英美两国民主道路的比较恰恰与《论自由》发表于同一年(1859年)。从中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的先贤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言论自由和“民主”的实现是以排斥性条件为前提的,隐藏在《论自由》的普遍价值表述背后的是对自由主体边界毫不含糊的清醒判断。这等于说,在社会存在阶级分化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一个共享的言论自由机制和一套被普遍认定的“真相”。
回到150年后的互联网传播时代,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显然已经很难容纳这种狡黠的辩证要素。在互联网传播繁荣的初期,知识分子们构造了一个几乎脱离社会经济属性的“网民”概念,在理念上天真地取消了言论自由权利的社会边界。这种思想状况给当下民主建制派的窘境埋下了隐患。其尴尬之处在于,当密尔的暴民论成为禁忌时,知识分子们虽然可能在内心里对“民粹”万般诅咒,在公共讨论中却只能将问题归罪于社交媒体的运行机制;归罪于俄罗斯政府的蓄意侵犯;归罪于公关公司利欲熏心的舆论操纵。久而久之,“后真相”倒好似真成了个纯粹的传播学问题。
即使是谈到网络传播中的主体,当代自由主义者也很难像密尔一样清晰地调用阶级概念,这恐怕是二十世纪历史带给他们的病灶。由此,唯一的断案方式就是划出一条理性和非理性的抽象边界,并指出社交媒体的特性纵容了网民情绪化的表达,带来了理性辩论的失败。这样,他们再次回避了社会文化分裂的根源问题,或者沉醉于“解放互联网”的各种技术方案,或者寻求疏导情绪冲动的方法。近些年来,在主流的传播学和心理学中,有关网民情绪的研究一时汗牛充栋,应该就是这种思路的反映。
五、什么是真相,谁的真相?
“我爱那些念书不多的人!”特朗普在2016年内华达州竞选集会上的一句激情表白成了很多媒体的报道标题。当年的选举结果表明,那些“念书不多的人”也爱特朗普。受教育程度成为这次美国大选中划分选民阵营的一个显著标准。[17]在英国脱欧选举中,这一指标上产生的分化更加明显。[18]如果将学历高低简单地等同于理性判断的能力高低,那就忽视了受教育水平所展现的丰富社会经济含义。
如果我们把特朗普支持者、英国脱欧派和其他欧洲国家右翼政党的票仓地域分布与选民受教育程度的指标叠加起来,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在1970年代晚期开始被全球化建制派经济政策所抛弃的“铁锈地带”的劳工大众构成了当下西方社会最为强大的反全球化、反建制派的力量,也由此成就了新的政治风潮和文化传播领域的“后真相”状况。
他们曾经是福利社会民主生活的中坚力量和自信自足的中产阶级,如今却成为信息社会中常常被主流媒体奚落的人群,成为知识精英眼中被网络“过滤气泡”和社交媒体回音壁包裹的无知大众。在经受了四十年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边缘化待遇之后,这些“非理性”的人们终于利用新的传播方式,以不可阻挡的态势发出了另类的声音。他们的公共表达也许是情绪化的、偏听偏信的,但是在这些情感和偏见的背后则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残酷的历史进程。在其中,我们见证了欧美社会金融业、信息科技、服务业的快速兴起,也见证了传统工会文化的衰落,见证了新富阶层和全球化建制派创造的各种政治正确,见证了曾经的民主主体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双重衰落。
终究还是有很多知识分子不满足于将社会分裂的危机简单归结为社交媒体的问题。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A. R. Hochschild)的杰作《本土的陌生人》走访了大量社会中下层右翼白人家庭,作者尝试着放弃所有知识精英惯有的偏见,为我们描述了这个人群的遭遇和情感,深入地探寻了西方社会分裂的历史成因。[19]越南裔美国作家林丁(Linh Dinh)花费了大量时间,走过了大量旅途,穿越美国那些陌生的贫困社区。他用善意的热情和诚恳记录了那些社会边缘群体耸人听闻的,或者十分荒谬的社会经历,让美国那些经常被遗忘的公民们发出声音,成就了一部感人的专著《美国末日的明信片》。[20]正是通过这些生动的叙述和那些具备宏观视野的社会研究,我们才得以看到比碎片化事实更加真切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与“真相”相对的不仅是“谣言”和“盲从”,而且是无数的人们的生活、情感、价值汇聚成的“历史”。
对于某些西方民主建制派来说,强调当下民众对“真相”的守护固然重要,但是最好不要健忘以往自己篡改“真相”的丑行,否则只会暴露道德表象下赤裸的相对主义。我由此想起整整十年前一个不应被忘记的时刻,2008年的4月19日,柏林、伦敦、巴黎、洛杉矶等世界主要城市的华人举办集会,向全世界发出“支持北京奥运,反对西方媒体片面报道”的声音。“做人不要CNN”,在一片红旗招展的背景中,我依稀记得那响亮的口号。如今,面对“后真相”时代的种种恐慌,人们最终要问:“什么是真相,谁的真相?”■
①GhonimWael. Revolution 2.0: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is greater than the people in power: A memoir.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2.
②VargasJose Antonio. “Spring awakening: How an Egyptian revolution began on Facebook.” The New York Times 17(2012).
③④GhonimWael. Let’s design social media that drives real change. TED lecture. https://www.ted.com/talks/wael_ghonim_let_s_design_social_media_that_drives_real_change#t-7214.
⑤GhonimWael. & Rashbass, Jake. Transparency: What’s Gone Wrong with Social Media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https://medium.com/@ghonim/transparency-whats-gone-wrong-with-social-media-and-what-can-we-do-about-it-e1cdc8e6b085.
⑥Stencel, Mark. & GriffinRiley. Fact-checking triples over four years. February 222018.https://reporterslab.org/fact-checking-triples-over-four-years/.
⑦Art of the lie - Post-truth politics. The EconomistSeptember 102016.
⑧SunsteinCass R. # 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
⑨Pariser, Eli.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Penguin UK, 2011.
⑩Hindman, Matthew. The myth of digital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11]CadwalladrCarole and Graham-HarrisonEmma. Revealed: 50 million Facebook profiles harvested for Cambridge Analytica in major data breach. The Guardian. Mar. 7. 2018.
[12]参见《纽约时报》和《纽约时报杂志》的两篇报道:
MacFarquhar, Neil. The Russian Troll Factory: Zombies and a Breakneck Pace.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82018.
ChenAdrian. The Agency.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22015.
[13]FergusonNiall. Social networks are creating a global crisis of democracy. The Global and Mail. Jan. 192018.
[14]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考察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在那一时期,美国是一个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国家,西进运动使得土地的占有更加平均,“小业主”成为美国社会的基本政治力量。这一社会状况催生了以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命名的“杰克逊时代”,正是在这一时代,美国先于很多欧洲国家将选举权扩大到所有白人男性。
[15]MillJohn Stuart. M. de Tocqueville on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2. John W. Parker and son1859.
[16]以赛亚·柏林著:《自由论》第4页,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17]Gould, Skye. and Harrington, Rebecca. 7 charts show who propelled Trump to victory. Business Insider.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exit-polls-who-voted-for-trump-clinton-2016-11.
[18]BallJames. Here’s Who Voted For Brexit, And Who Didn’t. Buzzfeed News. https://www.buzzfeed.com/jamesball/heres-who-voted-for-brexit-and-who-didnt?utm_term=.ip6opYgmm#.frr1R7400.
[19]HochschildArlie Russell.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The New Press. 2018.
[20]DinhLinh. Postcards from the End of America. Seven Stories Press2017.
王维佳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