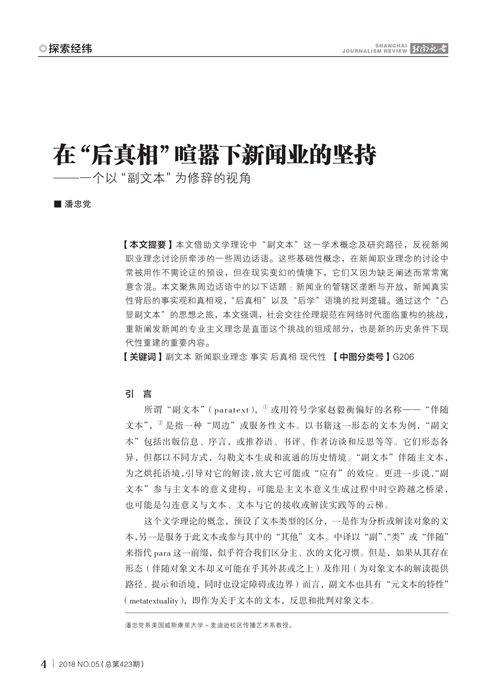在“后真相”喧嚣下新闻业的坚持
——一个以“副文本”为修辞的视角
■潘忠党
【本文提要】本文借助文学理论中“副文本”这一学术概念及研究路径,反视新闻职业理念讨论所牵涉的一些周边话语。这些基础性概念,在新闻职业理念的讨论中常被用作不需论证的预设,但在现实变幻的情境下,它们又因为缺乏阐述而常常寓意含混。本文聚焦周边话语中的以下话题:新闻业的管辖区垄断与开放,新闻真实性背后的事实观和真相观,“后真相”以及“后学”语境的批判逻辑。通过这个“凸显副文本”的思想之旅,本文强调,社会交往伦理规范在网络时代面临重构的挑战,重新阐发新闻的专业主义理念是直面这个挑战的组成部分,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性重建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副文本 新闻职业理念 事实 后真相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206
引言
所谓“副文本”(paratext),①或用符号学家赵毅衡偏好的名称——“伴随文本”,②是指一种“周边”或服务性文本。以书籍这一形态的文本为例,“副文本”包括出版信息、序言,或推荐语、书评、作者访谈和反思等等。它们形态各异,但都以不同方式,勾勒文本生成和流通的历史情境。“副文本”伴随主文本,为之烘托语境,引导对它的解读,放大它可能或“应有”的效应。更进一步说,“副文本”参与主文本的意义建构,可能是主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时空跨越之桥梁,也可能是勾连意义与文本、文本与它的接收或解读实践等的云梯。
这个文学理论的概念,预设了文本类型的区分,一是作为分析或解读对象的文本,另一是服务于此文本或参与其中的“其他”文本。中译以“副”、“类”或“伴随”来指代para这一前缀,似乎符合我们区分主、次的文化习惯。但是,如果从其存在形态(伴随对象文本却又可能在乎其外甚或之上)及作用(为对象文本的解读提供路径、提示和语境,同时也设定障碍或边界)而言,副文本也具有“元文本的特性”(metatextuality),即作为关于文本的文本,反思和批判对象文本。
在这一理解中,分析对象是某种形态的文本,它处于和其他文本的关联当中。因此,“副文本”的概念体现了凸显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视角。③这一分析路径,也有将对象静态化的趋向,将文本看作犹如绘画艺术中被描摹之静物。其实,任一对象文本不仅处于和其他文本相互关联的网络之中,而且这网络也在生成和变异的动态当中。有时,这一关系网络如何被建构更需关注。在此视角下,我们不仅分析作为物件(artifact)的文本,更可考察以文本为有机构成的社会实践,或称“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④用霍尔(Stuart Hall)的语汇,这种分析关注编码和解码这两个文化社会的动态,探寻其中牵涉哪些表意资源,又形成了哪些文本间的关系。⑤
“副文本”这个概念因此提供了一个学术论述的修辞手段,我们可借用它所指向的路径,审视在新闻职业理念的讨论中的一些预设理念。这些理念游弋于“周边”或“伴随话语”之中,虽为必要的预设,却不常被置于新闻职业理念讨论的前台。尽管如此,作为理论的基础设施之一部分,它们却烘托或支撑着各种关于新闻职业理念的话语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预设的理念,无论是否正式登场,都是新闻职业理念言说的参与者,不仅构筑其内涵,而且成就其形态。
“副文本”这个修辞手段,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展开学术反思的路径,即客体化我们论说新闻职业理念的话语过程,既反思我们的论述实践,更在其中揣摩我们所处的学术场域中各种“他治的”(heteronomous)力量。⑥这样的话语操作,也反转了文本之间的关系,把“副文本”的关注置于论说的前台,形成凸显“副调”的文本时刻。
这样的周边议题有很多,本文聚焦其中三个:
新闻业是否在走向消亡?新闻真实性是否有可论证的学理基础?事实作为社会公共生活的基础是否已被“后真相”的时代病兆所颠覆?
这些都曾“不是问题”,安憩于“众所周知”的预设当中。但在今天,新闻业面临危机,使得它们都成为问题,直接挑战20世纪以来首先形成于欧美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并因此形成了“边缘”成为话语重构之中心的局面,讨论它们的“副文本”也因此走上前台。
一、开放而非无序:作为“主义”的新闻业
新闻业(Journalism)的危机,对新闻职业的历史存在及其现实可能提出了质疑。进一步的问题是:以专业主义的职业理念所规范的新闻业是否为仅限于世界一隅的历史偶然?它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可能?我不长于新闻史,无力对此展开原创的研究,只能依赖已有文献,借助同行学者的研究成果。⑦以此为基础,我们所探究的不是“新闻业是否为专业”或在多大程度上如何可能“专业化”,因为那是预设历史目的论的问题,而是探讨新闻从业者群体如何作业,如何表述自己在其中践行的理念,如何运用专业主义的职业理念来建构这些话语实践,如何以这样的话语实践服务公众、建构职业群体的认同。⑧
这一取向沿袭了新闻生产社会学的传统,糅合了文化社会学、话语分析等理论元素,是一个社会建构主义的取向。⑨在此视角下,新闻从业者群体通过其话语实践,表达自己的职业理念,并以之建构自己的群体和职业。这种实践一是为实现其职业垄断,以之获取经济效益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回报;二是为形成“阐释的共同体”,以之巩固职业群体的认同,建构群体内外的区隔。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维系并正当化职业垄断新闻操作的结构安排。
但是今天,新闻业正面临危机。⑩这个与新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相伴随的危机是全方位的: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垄断正被打破,职业人士的话语实践不再能维系职业与非职业人士之间的区隔,新闻业所依赖的传统媒体正面临市场转型的挑战,维系新闻业的经营模式日益式微,新闻从业者作为职业群体日渐萎缩。不仅如此,新闻这种话语和叙事形态或文化形式正被消解于“后真相”的喧嚣之中。那么,我们所知的新闻业是否在走向消亡?由职业人士所维系的新闻业是否可能并且应当通过“坚持新闻专业主义”而被“拯救”?“后真相”这一形态的传播是否预告了真相出局这一历史的必然?[11]这个问题首先牵涉到“新闻”和“新闻业”这两个人们熟悉但却指代漂移的基本概念。我们提出的界定是:“作为文本的新闻(news)是可验证(verifiable)事实的呈现;作为活动的新闻是观察、记录、查核、传递事实并建构意义的社会和文化实践”。[12]后者指的就是新闻业(journalism),它是一个由历史地形成的体制和伦理规范所结构和制约的行业。美国历史学家尼龙(John Nerone)因此说:“新闻业是规训媒体之新闻呈现的主义”。[13]这个看法与英国学者查勒比(Jean Chalaby)的观点基本吻合。[14]查勒比以对英国报业的历史分析为基础,认为新闻业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话语实践”,它成型于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的英美社会情境。Journalism以-ism为后缀的名词,有“主义”之含义,指代的当然不仅是作为活动的实践,更是这些活动所体现的共同趋势;它由一些付诸实践的规范所构成;它有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基础,即服务于市场和代议制民主的新闻实践场域(journalistic field),在其中,信息生产以市场为依托,以产业化生产为模式,以事实采集和挖掘为内容,以规范这些活动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可简单地概括为新闻从业者与新闻源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而展开。带有-ism这一后缀的“新闻业”,如查勒比所说,是将这些元素编码其中的“话语类型”(discursive genre);更宏观一些,新闻实践场域和其他场域之间有着互构的关系,新闻业是按现代性符码所建构的“话语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15]美国学者通过分析美国的历史经验,描绘了大致类似的历史轨迹。[16]不过,在他们的分析中,一个更为凸显的聚焦点是新闻业与美国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熟悉李普曼-杜威争论的人都知道,现代新闻业在美国的成型,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主改革之一部分,其中包括“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造成垄断资本力量的突起,科学发展导致科学主义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大众社会成长带来的多元诉求,学者、政治家、社会改造活动家们共同打造了“进步主义运动”等。但是,正如哈林(Daniel Hallin)所指出的,新闻业这一镌刻了现代性符码的话语形构蕴含着内在张力。到了20世纪中期,经过罗斯福新政和冷战而聚集的政治共识陷于坍塌,该共识所得以维系的既有话语秩序遭受挑战,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体现当时新技术的电视媒体。整合电视广播新技术的资本运作生成了高度商业化的经营模式,不仅萎缩了传统新闻业在媒体的分量,而且进一步促发了新闻实践规范的解构,包括据实报道、客观公正、排除报道者的主体性等。[17]将视线转回大洋此岸,一个相关的命题是现代新闻业在中国的历史根基。虽然我缺乏发掘和分析第一手史料的条件,但阅读新闻史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兴起也是现代性建构这一历史进程之一部分,它还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西学东渐是其中重要的活力来源,而与美国的交流——包括经由日本的中转——尤其突出。这当中不乏美国资本和文化势力向中国的战略性扩张和渗透,也不缺少中国学界和业界在其求知和变革欲望的驱动下,为救国于危难而展开的主动邀约和吸纳。当然,这个现代新闻业的建构过程中更有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底色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的传统。[18]这些历史研究成果显示,规训新闻业的信念,如致力于服务公众和报道事实等,并非全是舶来品,也不为某一意识形态体系所独有,更不是来自西方的洪水猛兽;同样地,在当下,面对新信息技术及其相应的社会基础设施和交往结构的重建,中外新闻业也面临类似的危机,虽然中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情景。
所谓“危机”,即某种失序的危险;新闻业的危机,也即上述现代性所编码的话语形构面临消解。哈林在网络媒体形成气候之前,就已经看到了个中端倪。[19]而这二十多年的变化,更是将这“失序”活生生地展现于我们眼前:新闻业当下的危机,正在挑战新闻界对“事实性信息搜集、表述和传递”的职业垄断,也即是在“液化”按现代性编码的话语形构,[20]甚至在消解“新闻”这个以搜集和呈现事实性信息为基本特性的话语类型。但这同时也蕴含了突破结构、开拓空间、展开创新的趋势,其中蕴含的建构工作给新闻界提出了挑战,即遵循何种价值观以充分地收获新信息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可供性(affordances)?
正是延此逻辑,我们认为,职业新闻业并非在走向消亡,而是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实践空间,即参与建构公共生活所必需的交往模式,实践并阐述它的建构所要遵循的交往伦理和规范。也就是说,新闻从业者对于从业的伦理和规范之理解,需要走出如何维系职业垄断的命题范畴。[21]对此,本文不需再多展开,只引述两条文献作为进一步的佐证。
第一条即是哈林1994年的论文,它常被引作批判“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论据。确实,在此文中,哈林宣布了“美国新闻业高度现代主义的消亡”,但他没有宣布新闻活动的消亡,也没有宣布专业主义话语的消亡(或必然被历史所抛弃),而是说,美国新闻界通常所理解的以超然和无价值立场为特征的新闻专业主义规范体系无以维系,政治共识坍塌后公共领域的虚空需要有立场和追求的新闻业来填充。他据此提议,第一,新闻界不能仅以政治权威与公众之间的中介自居,而是要以如何拓展民众的政治讨论为框架来重新设想自己的角色;第二,与其摆出自己超脱党派政治的专家姿态,不若开放自己活动的“后台”,重新进入市民社会,成为民众当中的对话者之一,也让公众了解新闻从业者的发声逻辑。据此逻辑,新闻专业主义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它的形态正在演变,而且必须改变,其路径即是开放,也即重构职业的边界,开拓职业与非职业、专家与民众交织、互动的之间(in-between)区域。[22]第二条文献是美国政治学家德泽(Albert Dzur)关于民主的专业主义(democratic professionalism)的论述。[23]他认为,以专业主义为职业操守和伦理规范是民主运作有序深化的利器,因此,以这样的规范所构成的专业如何发挥作用,是民主理论必须特别关注的议题。在日益多元的社会,民主运作需要商议、协调,以及以此为途径的相互认可与包容;它还需要“职责分享”(task-sharing),即各群体、角色和部门分享公众自主的决策责任。专业及其遵循职业伦理和规范的运作,正是社会构成的各元(群体、部门、领域等)之间必需的中介,而这中介作用的发挥,又有赖于“民主的尊重”(democratic deference),也即全社会对各民主机构(包括媒体)和规则(包括新闻制作)等在各自领域内的应有权威保持基本的信任和尊重。按照德泽的逻辑,新闻界任重道远,新闻业大有可为。新闻业由新闻界主动、积极参与的重构,当是当代社会有序开放、深化民主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
说白了,在当下的“新闻危机”话语中,最直接侵害新闻业的很可能是新闻界(包括学界和业界)自己对其行业的犬儒式解构,因为它不是建构式的反思,而是新闻界的自暴自弃;它不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下进一步阐述理念、规范和追求,而是消解新闻业在社会运作中应有和可能有的公信力;它不是阐述新闻业如何作为一个重要主体参与并引导社会协调对话,而是以无奈为由放弃这一社会责任。
二、多元主义而非相对主义
新闻必须真实,这似乎毋庸置疑。但是,它究竟意味着什么?通常,业界遵循的专业规范强调事实性(factuality)、客体性(objectivity)和真相(truth)。对这些观念的强调,似乎意味着罔顾社会的多元、现实的多重社会建构,并因此而忽视多种真相并存、角逐和碰撞这一现实。坚持经验主义的事实观,似乎即是在固守一个陈旧的、已被“事实的社会建构”成为常识的今天所抛弃了的事实观和真相观。
的确,“客观性”是个备受诟病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这其中不乏对“客观性”这个外来词的简单化理解。在我看来,objectivity翻译为“客体性”更好,因为它指代新闻以及其他认识世界的经验主义路径都必需的一个基本预设——即认识的对象是外在于认识主体的客体。因此,经验知识的获取,必须遵循接近这客体的实践步骤和规则;经验知识的呈现,也因此必须包含对这步骤和规则的陈述。而自我宣称专业主义规范的新闻业之所以具有其生产新闻的文化权威,皆因这些步骤和规则已经成为业内的工作“常规”。新闻的客体性原则备受争议,是因为在市场和权力作用下的新闻生产场域中,这些工作“常规”不可能是实现客体性原则的理想途径,而是会成为意识形态的基础设施之一。[24]但是,新闻实践在不断创新当中,是活生生的,它们总是在挑战对客体性原则形而上的教条化界定;这样持续不断的挑战,同时也是在确认客体性原则在新闻知识生产场域的核心处位。[25]即便是激烈批判这一原则、认为它被资本主义真相体制所劫持的左翼学者们也有人认为,“在许多方面,客观性、独立性和公共利益继续成为媒体批评甚至是来自左翼的批评的用词”。[26]在李良荣看来,“新闻要求真实、全面、客观、公正,这是任何社会的常识。真实的反面是假,全面的反面是片面,客观的反面是主观,公正的反面是偏见。谁也不会说我的报道是假的、主观的,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因此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能够被社会接受”。[27]据此,新闻专业规范中包含了这么一个哲学常识:作为“以事实为基础的话语实践”,[28]新闻业与其他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s)一样,预设了主-客体之分,并以认知客体为基本趋向。也就是说,第一,在一般情况下,所谓“经验的真相”(empirical truths)外在并可知;第二,我们可能而且应当尽力以探寻此真相为追求,坚持并改进展开这探寻所应遵循的规范、程序和方法。[29]这个哲学观点,与“新闻是社会地建构的再现”(representation)这一描述性的理论概括毫不矛盾,因为,其中的“建构”和“再现”,同样预设了主-客体之分。与在规范理论层面论述新闻业不同,[30]这一“社会建构”的论断重在描述主、客二者之间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关系,呈现它们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多样展开,以及规范性原则在实践中的有缺陷状态。但正是将新闻生产的过程客体化,并以此展开经验的考察,才使得我们发现其中社会建构的机制;也正是将社会发生客体化,对之展开观察和核查,才有了新闻活动,也即新闻学的研究对象。
这绝不是说,新闻业所面对的复杂社会现象中只有一个绝对真理,只有一种真相,事实不言自明。恰恰相反,既然预设了主-客体之分,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直面这样一个经验的现实:在复杂的人类社会活动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多元、多样、多变、互动的,并非是决定性地对应的。不同的现象、情境、视角、解读路径等,都会助成不同的事实认识和真相体验。多元主义(pluralism)因此不仅是自由主义的价值伦理体系,而且是以社会条件、生存状况、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多元为现实基础的知识论原理和方法论趋向(orientation)。
这里可简要列举若干人们熟知的论述,以呈现这一趋向在多种知识建构情境下的不同表现:
第一,就科学知识的积累而言,“观察”并不能充分检验理论假设,亦不构成辨析理论之优劣的充分基础,因为任何观察都有“理论的负荷性”(theory-ladenness),[31]这使之无法成为“外在”于理论的“公正”裁判。一个理论“范式”不仅逻辑地推导出观察的方法和程序,而且通过这些方法和程序,形成经验的“事实”或“数据”。[32]因此,理论与证据有相依关系,以经验观察来检验理论是与不确定性共存的过程,不同范式呈现了不同的外在现实。
第二,社会现象由具有文化意义也即浸润了人的主观建构的事件所构成,我们因此需要观察和理解具体的个人如何体察自己特定的情境,运用其信念和认知,形成意愿并采取行动。这是展开“具体现实的经验科学”的路径。[33]更进一步,文化是特定环境中的人群所共同编织的意义网络,储存着社会的共享知识,[34]理解一个文化需要进入其意义网络而展开解读。[35]对新闻业的社会建构主义研究,广义地说,即是这个阐释路径下的一个领域。[36]第三,语言不具有指代客体现实的确定性,这是20世纪初开始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中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一转向深刻影响了各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形成其他一些类似的概括,如“符号学的转向”(semiotic turn)、“话语的转向”(discursive turn),以及在民主理论中的“商议的转向”(deliberative turn)和公共政策领域的“争辩的转向”(argumentative turn)。虽然具体用词不同,发生的学科领域不同,具体的理论内容不同,但它们都强调了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历史偶发性和流动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再现(representation)或意指(signification)是现实的社会建构并且版本多样。但同时,这些论述也表明,不同取向和表达所形成的“现实”,相互之间既可能相互冲突,也可能相互应答(engage)。[37]第四,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引发了所谓“信息方式”的革命,使得信息的记载符码失去了任何“指代”的要素,[38]而且拓展出物质现实的新维度(如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或是具有物质体验之可供性甚至是具有外在于人类主体的物质性的新型现实。[39]因此,主-客体相互渗透,而非泾渭分明。
对这些不同学科的文献,我个人了解有深浅不同,对于第四类即技术哲学的论述,因为自己偏好经验研究之故,了解得比较肤浅。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做出如下的归纳:这些来自多个学科、针对不同命题、采用不同路径的论点都告诉我们:
(1)人们建构他们据以展开行动的“现实”和“真相”,在这个意义上,“现实”或“真相”是结果而非起因。
(2)不同的意义体系(即具体的文化和/或生活世界)下有不同的“现实”和“真相”,它们并不可完全通约(但不是完全不可通约!),亦不可简单地以优劣排序。
(3)任何“现实”和“真相”都是特定“真相体制”(regime of truth)[40]下的建构,其“事实性”高度不确定。
这些观点构成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多元主义趋向。但是,它们没有也不可能取消主-客体之分以及趋向客体这一认知的基本态势。更进一步说,它们没有而且也无法消解这样一个必要的可能,即不同的“现实”和“真相”(更准确地说是指认现实和真相的各种“宣称”)可以而且应当相互比较;在话语场域的竞争中,我们可以对它们做出效度(即事实性程度和解释力)高下的评判。当然,这个过程在历史情境的制约下发生,由此得出的评判也因之而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和暂时性。多元主义不可等同为相对主义,或作为支持相对主义的论据;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对经验的真相做出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最可接受从而可共享的评判,以此展开人的社会性,实行有序治理。[41]这绝不是说,这样的评判没有高度不确定性,也不是说获取、查核、验证事实以做出这样的评判不牵涉复杂的政治争斗和意识形态冲突;而是说,人们之间的不同不足以排除他们之间的相同,历史、文化和情境的独特不足以消弭普遍性特征。
因此,“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准则”、“事实性”、“可验证的事实”等词汇更准确地表达了“客体性”的内涵。[42]这些表述其实包含了对美国新闻业追求“平衡”、“中立”等的实践方式的批判,因为,认识论的相对主义(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不是“客体性”的理解模式,恰恰相反,“客体性”要求通过事实核查和验证而坚持维护真相的明确立场。如美国新闻学者德拉姆所言,[43]认识论的相对主义以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了新闻业应有的社会解放功能。这种排除新闻从业者个人选择和判断的对客体性的界定,不仅没有描述新闻从业者的实际工作活动,而且制造了一个相对主义的陷阱:不同视角、不同观点、不同认知模式等都具有知识和道义上的对等性。这其实是以客体性之名,行相对主义之实。
在利益群体通过煽动情绪、粉饰谎言、放大恐惧、放逐真相等手段操纵公共空间的所谓“后真相”时代,[44]我们格外需要警醒自己,不要沉醉于相对主义的绚丽气泡之中。
三、“后”作为前缀颠覆了什么?
但“事实”或“真相”是否可能?刨根究底地追求它是否有意义?“后真相”概念似乎在给予一个否定的答复。
在最初宣告“后真相时代”的畅销书中,美国社会评论家基斯(Ralph Keyes)用这个概念概括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各种文化病灶:诚信下降,撒谎变得日常,语言操纵和形象管理成为艺术,叙事胜过事实等。他认定,后现代主义学者们的“社会(或话语)建构论”、“文化相对论”、“解构权力”等种种学术话语,在溢出象牙塔,转为流行话语后,侵蚀事实、祛魅真相,营造了一个“后真相”得以成为现象的话语氛围。[45] “后真相”被《牛津词典》册封为2016年度的热词之后,英国哲学家巴基尼在其通俗哲学读本《真相简史》中,也有类似分析。[46]简言之(这当然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失真”),“后真相”是“后现代”的一部分,是指在后现代状态下,以解构普适原则为诉求而出现的“伦理的阴阳魔界”(ethical twilight zone)。[47]此处的“后现代”,更明确地说,指的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状况,即多样、多元和流动等特性的凸显,挑战了忽略这多样性和条件性的主导知识和话语趋势(包括标准化、普适化和宏大叙事),也令我们经此而获得多重现实的体验,包括多元和流动的主体和认同。[48]也就是说,我们在此指的是与“现代性”相对照的所谓“后现代性”。与之不尽相同,“后现代主义”则是有很多分支、学派构成的思潮,[49]它以解构、颠覆西方主流的知识体制和以之编码的社会结构与秩序为基本取向。
以“后”作为前缀的理论意义(包括社会伦理和审美价值),首先在于解构,用哈维(David Harvey)的话说,后现代主义“起自并应对了现代主义”。[50]那么,“后真相”解构了什么?作为形容词,它描述性地概括了特定社会和文化状况,在现代主义的视域下,它们是社会和文化的病灶。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正面的认识论理解是,“后真相”是对挑战现代性的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概括,它解构的是作为现代性之一部分的“真相体制”(regime of truth)。[51]这即是权力体系。福柯认为,权力之维系,不仅在于它可抑制我们,向我们说“不”,更在于它可生成现实。[52]他指出:
真相并不外在于权力,亦不缺少权力……真相绝非对自由精神的奖赏,或者面壁清修的醒悟,也非那些自我解放的成功者们才有的特权。真相是此世之物,它在各种形态的制约下孕育而生,并使权力之效用不可避免。每个社会皆有其真相体制,也即真相的“总体政治”,其构成是:各种接受并建造真实的话语;使人得以辨别真伪的机制和事例,以及它们获得核准的手段;在真相获取过程中衡量并赋授价值的技术和程序;还有那些承担着直言真相职责的人的社会地位(p.131)。[53]福柯进一步强调,他所批判的“真相体制”不仅“属于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而且是“资本主义形塑和发展的条件”(p.133),因此,批判的知识分子应当在“真相体制的层面发挥其(批判)作用”。在另一篇文章中,福柯更进一步认为权力将人客体化,即在生产和表意的关系之中界定主体(subject)。[54]据此,他宣称,他的学术研究主题并非权力而是主体,更准确地说,是揭示人被生产为主体的历史方式(p.778)。
值得一提的是,福柯的这两篇文字都是典型的“副文本”,这不仅因为“真相与权力”是访谈记录,后一篇“主体与权力”是他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论文集所写的后记。在这些文本时刻,福柯反视自己的历史论著,为它们的解读提供线索和路径。我们在此引述这两篇文字,是因为它们在“后学”的论述当中比较彻底地消解了实证主义的“事实”和“真相”观:世间万物,包括人作为社会行动的主体,皆为特定权力体系下的建构(包括宣称和运作)。既如此,那么如何可能有脱离权力的“事实”和“真相”?那样的宣称本身岂不就是权力运作之策略,甚至是权力本身?
但是,福柯真的消解了事实和真相吗?确实,如福柯所言,[55]首先,每个社会有自己独特的“真相体制”,它与该“社会的结构和命运攸关”;其次,“‘为了真相’的斗争是存在的,至少‘围绕真相’的斗争是存在的”(p.132)。但是,在他试图表达精确而且清晰的时刻,我们就会发现,福柯不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谈“真相”。他说:“我并非用‘真相’指代‘被发现而且获得接受的各种真相之集合’,而是那些‘各种判断真伪、赋予真相以权力的影响力所遵循的规则之集合’”(p.132)。也就是说,福柯是在论述关于真相的宣称,认为它们是权力体系的产物;或者说,他认为生产并运行对真相的宣称,是权力的话语形态的运作。我们千万不能因这“副文本”的表述不精确,而忽略掉这样一个重要区别:福柯论述的是“真相”话语的生产和运作,而非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相。
社会权力以两种形态运作,一是强制,一是话语。[56]这似乎已不是什么新观点。福柯的洞见在于向我们揭示,这后者往往以再生、再阐述“科学性”、“事实性”和“真相”等形态出现,并将自己物化于包括教育和学术机构在内的“真相体制”当中。
但是,毫厘之差可致千里之谬。如果我们不细究福柯使用“真相”这个词的具体指代,我们可能就会以为他消解了“事实”和“真相”,或是消解了确认“事实”和“真相”是具有哲学和现实意义的人类追求。类似地,一旦人们将库恩在“范式转换”论述中关于“不可通约性” [57]——缺乏可比的测量和衡量标准——的论点引出科学哲学的范畴,以论证文化和其他意义体系之间的不可比性,就难以避免荒谬:难道二战后形成的《日内瓦公约》不是在不同文化、语言和政治体制下的人们形成的规范人道主义的“公约”吗?假如人们根据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们(这个标签是否适合福柯,他自己是否如此自我界定,需在另外的场合讨论)的论述而认为,因为科学研究无法在特定“真相体制”的政治经济关系之外展开,所以构成科学知识的定律(不完全等于科学的话语!)都有“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偶发性”(contingency),那就难怪要遭到如艾伦·索卡(Allen Sokal)等科学家们的嘲讽和戏谑。[58]很难想象,去掉主-客体之分、趋向客体的认识路径,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现实具有外在和可知性这一本体论预设,自然科学家们如何可能论证其学科、学术活动的正当性?当然,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即便在自然科学界,不同学科类型之间(如物理、化学、生物等),研究对象的基本单元不同,其运作方式亦不同。但这些不同,真就足以取消现实的外在性吗?真的就意味着,宣称不需要事实的制约、知识不需要经验观察的检验吗?在社会建构、语言和/或技术决定论的话语中,对“事实”和“真相”的解构,往往以“不同”(如视角、立场、体验等)作为论辩的基础,但吊诡的是,这种论辩的风格往往是以本质主义的决定论来论证其号称去本质论的观点,即现实没有客观存在是本质,它之被建构是本质!而且,运用欧美等国家/文化的理论家们来否定现实的外在性、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等,本身就蕴含了逻辑矛盾:这一话语的运作本身已经预设了跨文化、超越具体情境的外在性和通约性。
并非各色建构主义者们都否定主-客体之区分、否定客体外在于主体的现实性。至少,我自认为是现实主义的社会和话语建构主义者,但我决不否定客体性。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否定客体性,在我看来,多少有以我为尊、以人类为尊(anthropocentrism)的倾向。当代认知心理学认为,至少在个体认知的层面,这一倾向导致“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的认知偏误(cognitive fallacy);在社会交往层面,作为一种依赖“直觉系统”的认知路径,它往往——即便人们普遍地用心良苦、心底无私——成为交流的障碍、社会政治意识两极化的机制。[59]
四、“有话好好说”
至此,我们把话题引向了“有话好好说”这个日常伦理。这是一个难以引发争议却又极难实现的日常伦理,徐贲教授把它诗意而又理性地表述为“明亮的对话”,[60]意在强调以敞亮、清晰、恰当的方式文明说理。
我与徐教授一致,并进一步认为,这其中的重要基础,是认可现实主义认识论(realist epistemology)的基本原理:现实的外在性、事实的可知性、认知的可相互理解,[61]以及践行它们的交往准则:尊重事实,呈现事实,以事实推导结论。以事实界定真相,这既为明亮的对话之基础,又只可能在如此对话中得以呈现。所谓“后真相”状态,如刘擎所言,是对我们长期信奉的“公共交往规范——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真相面前人人平等”等的挑战,使得它们“都不再是自明正当的,也不再能够有效地应对公共意见的分歧”。[62]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针对“后真相”的各种喧嚣,我们需要将重新建构新闻专业主义定位在建设以“明亮的对话”为内容的公共生活这个基本点上。
确定这个立足点涉及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展开“明亮的对话”的难点在哪里?第二,新闻业在其中有何独特的价值,以至我们需要重构“专业主义”的规范?
第一个问题在其设问中已预设了“明亮的对话”之可能及其正当。在整合以“交往”为重心的当代社会理论、民主理论和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可将问题表述为建构何种“元传播的范本”,[63]即在一个媒介化的多元社会,不同层面和范畴的社会交往应各自遵循什么伦理规范,相互应如何整合,以求最大限度地体现民主和理性原则,并以之维系社会的动态和谐。本文批判地审视“后真相”这个概念,不在于它概括了这个伦理规范层面的无序状态,而在于它可被轻易地用来否定交往规范中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原理。
换个方式看,“后真相状态”的蔓延得益于现代性的高度发达:个体化的趋向、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价值的凸显,以及实现它们的技术(包括个人技术的普及等)。[64]在此生存条件下,我们不仅沉浸于海量的信息、多元的视角,而且自由发言、随时发声,并因此可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至少理论上如此——参与公共生活。“后真相”一词从负面概括了这一“高度现代性”的趋势,表达出其中对我们参与公共生活的消解:我们不同程度地着急,不仅急于发言,而且急于上火,为情绪所左右;我们不同程度地过于自信,以自我中心的“天真的实在主义”(naive realism)为倾向,[65]坚信自己认知的现实性和公正性,推断他人的错误和偏见;我们不同程度地急于表达,而且不善聆听,因为,说比听更容易获得存在感;我们不同程度地犬儒或易于陷入犬儒,并以之否定事实、真相和真诚,回避追求事实和真相之旅的艰难;我们也会不同程度地崇尚权威,将事实和真相等同于权力的下达。正是针对这些倾向,我们呼吁建设“明亮的对话”所得以展开的交往规范、规则和程序。
显然,展开“明亮的对话”需要事实,需要真相,也需要对话之所。我们需要共享事实性信息,共享用以判断事实真伪的基本逻辑,需要认可展开这判断所需要的程序,我们也因此需要社会分工体系中继续有处理共享社会知识的职业生产者、扩散者和修正者,新闻界即是其中无法替代的一员,这就是新闻业的独特价值之所在。以“明亮的对话”为基本元素的公共生活,需要具有能动性的公众作为主体,而这样的公众也只有在这对话过程中形成。新闻业的救赎来自于它可能为这一公共生活提供的独特价值,它由如下三方面构成:
第一,新闻业可提供比其他各类社会群体采用各种其他方式所能提供的相对更为——不仅实在地如此,而且被广泛地认为如此——充分、精确、可信、适用的信息,也即是为不同视角下的意见阐发者们提供他们共同倚赖的事实陈述。也就是说,新闻业以自己努力维系的公信力,以其搜集、查核、传递事实并以此接近和呈现真相的专业技能,成为“明亮的对话”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和服务者。
第二,新闻业的独特价值还来自于它作为一个开放的论坛,不仅促成、传递不同观点和意见的表达,以及它们相互间的交流,而且彰显、阐发展开这表达与交流所遵循的准则和规范,并因此成为令“对话”更为“明亮”的推动者和示范者。
第三,新闻业传达公众舆论,作为开放而且理性的能动者,在社会的“真相体制”中不可或缺。
新闻业的使命就是活跃公共生活中的“明亮的对话”,并以此在“人人可为记者”的网络媒体时代获得自救。不可否认,新闻业要有可持续的经营模式,但以广告经营和资本运营为核心的资源整合并非唯一可行的模式;新的业态呼唤经营模式的创新,同样重要的是,新闻业服务公众的使命也呼唤多种类型的媒体运作模式。[66]在这方面,我自知提不出可即时付之于行的方案,因为我身不在业界,缺乏一线的体验,况且,此等谋划也非所有学者都必须担当的使命。我相信,真正的创新必来自于身处一线、有志有识的从业者。
这些是相当“冬烘”的观点,讨论它们也需要一个“有话好好说”的知识生产场域。为此,我们需要以认知的自主,警惕对于客体现实或真相的单方面宣称。但是,如果我们蔑视客体,否定它决断我们认知的正当性,那么,我们就难免解构所有认知的问题,将之转换为政治的问题。我们对自由的追求,要求我们去除常识的遮蔽,但是,如果我们抛弃了人的社会性和人与人之间可能相互理解的基础——用现象学的社会学语汇,即共享的社会知识存储(social stock of knowledge)以及社会现实的客体性,[67]那么,我们就消解了人类主体性的可能。既要破除常识的束缚,又要避免践踏常识,这当是人类所追寻的“心智成熟”。
这一点首先由康德在230多年前那篇题为《什么是启蒙》的短文中得到论述。[68]康德在其中将“启蒙”界定为人类获取心智之成熟,以理性之途径实现认知自主的历史过程。如福柯所言,[69]虽然康德的论述有内在的矛盾,但它将追求真相与自由直接相联,勾勒了被概称为“现代性”的基本态势(attitude)或社会思潮(ethos),并在历史和批判地反思这一相交之点提出了“何为我们?”这个问题。[70]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批判地审视作为历史现象的现代性逻辑,指出它将局部的历史经验普适化,将人类获取认知自主的路径归置在由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和历史目的论组成的宏大叙事之下,并以此客体化人之主体。[71]但是,摆脱这个历史枷锁之路并非是取消事实、否定真相。我们需要的是历史的分析,这是一条“不懈地批判我们自身”的路径。[72]如此看来,我们不应把“后”这一前缀当作历史时代或社会状态断裂的标记,而是将“后现代”和“后真相”当作一种类型的表述,它们概括了“现代性”和“真相”的历史性,揭示了这历史性中所蕴含的权力运作。我们可以此为进路,提醒自己,真相没有呈现其真面目的完美渠道,谨慎而且缜密地核查与验证事实,是相对更难被权力所劫持的途径。因此,我们需要将寻求、核查、鉴定事实和真相的过程,置于公共讨论之中,使它成为开放而透明的公共参与的过程。
籍此,我们可以如此总结本文对新闻业的职业理念的周边审视: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针对的仍是现代性的问题,其核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如何重构交往的伦理规范,以求在“明亮的对话”中,展开提升人类心智成熟的新一轮历史实践。■
①Gérard Genette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by J. E. Lewin). 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②赵毅衡:《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中文也有“类文本”的译法。赵毅衡运用“伴随文本”概念,涵盖更广;他吸纳了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观点,并试图以之容纳各种不同类型的周边性文本。
③对于文本之间的关系,热奈特区分intertextualtranstextual, artchitectualmetatextualhypotextual等类别,界定甚至阐述这些类别及各自的理论意义,都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在此只为指出,第一,任何单个文本都悬浮于与其它文本关连的网络之中;第二,人对任一文本的接触都在这关系网络之被启动或关注的一隅而发生。
④参见Norma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2.
⑤Stuart Hall,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 Willis (Eds.)Culturemedia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2-79 (pp. 128-138). London: Hutchinson, 1980.
⑥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London: Polity Press1993.
⑦这么选择也因为我们拒绝这样一种历史本质论,即以特定视角建构某一历史叙事,然后宣称某一类型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特定性,再以此全盘否认作为现实可能和分析路径的新闻专业主义。我们认为,历史能丰富我们对当下的分析,也能充实我们的理论阐述,但是历史从来不是既定事实,当下也不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我们对于历史偶然性(historical contingency)和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理解不能简约为历史决定论。
⑧见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中国台北)2002年第71期;Zhongdang Pan & Ye Lu, “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in C. C. Lee (Ed.)Chinese mediaglobal context (pp. 215-236)London: Routledge2003.
⑨夏德森和安德森也划分了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制度(或行政)的取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考察新闻从业人员群体的专业化程度;另一是文化史的取向,考察新闻从业者展开工作并在其中维系其管辖权的活动和表达。归拢在后一取向下的有夏德森、翟丽泽(Barbie Zelizer)等,其理论源头可被追溯到韦伯和阿伯特(Albert Abbott)。“文化史”这个名称显然涵盖不当,但这么两个取向的区分还是有助于我们梳理和组织文献。这一段参考的文献包括:Andrew Abbott,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Michael Schudson & Chris Anderson, “Objectivity, professionalismand truth seeking in journalism,” in K. Wahl-Jorgensen & T. Hanitzsch (Eds.)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pp. 88-100)New York: Routledge2009; Barbie Zelizer“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0(3)219-2371993; Jingrong Tong, “Journalistic legitimacy revisited” Digital Journalism, DOI: 10.1080/21670811.2017.1360785.
⑩Jeffrey C. Alexander“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Cultural power”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8(1)9-312015.
[11]这是澳大利亚政治学者John Keane在最近一系列演讲中探讨的论点。见“Reflections on post-truth: Lecture at WZ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l9XkoSOE。
[12]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
[13]John Nerone, “The journalism tradition” in W. F. Eadie (Ed.)21st Century Communication: A Reference Handbook (pp. 31-38)Beverly HillsCA: Sage, 2009.
[14]Jean ChalabyThe invention of journ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1998.
[15]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R. Young (Ed.)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pp. 51-78)Boston, MA: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81.
[16]如注13引用的John Nerone,2009;以及Michael Schudson, “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Journalism, 2(2)149-1702001。
[17]Daniel C. Hallin, We keep America on top of the world: Television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Routledge1994. 同时参见注9引用的Schudson & Anderson, 2009。
[18]关于西学东渐和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兴起可参考的文献包括:林牧茵:《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版;宁树藩:《“怀念汪英宾教授——兼论他的〈中国报刊的兴起〉》,《新闻大学》1997年春季号;张咏、李金铨:《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载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第281-30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明亮:《中国新闻界与“世界报界大会”的姻缘》,2018年1月3日取自人民网-传媒频道: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4110/189065/13592712.html;Timothy B. Weston, “China,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and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er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acific Affairs83(2)327-3472010。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底色与我国现代新闻理念的文献,可参考: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中华书局2007年版。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与现代新闻理念的关联,参见: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1998年版;李良荣、沈莉:《“五性一统”原则新探》,《新闻大学》1995年冬季号。此外,虽然我们此处无法展开详尽论述,但需要指出,我们曾区分关于新闻业的四个话语体系,参见注8引用的Pan & Lu,2003;Chin-chuan Lee“The concep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ts: Ideological convergence and contestation,” in H. D. Burgh (Ed.)Making journalists (107-126)London: Routledge2005。林芬也在她的分析中,辨认了中国的入世、关心民众疾苦这个士大夫传统,见Fen J. Lin“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or individual’s deed? The literati tradition in the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z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175-1972010。美国政治学者哈斯德以自主(independence)和倡导(advocacy)的程度为基本维度,区分了四种在中国经验地可见的关于新闻业角色的职业规范和实践类型。见Jonathan Hassid, “Four models of the fourth estate: A typ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journalists.” The China Quarterly208813-8322011。
[19]见注17所引的Hallin1994。
[20]陆晔、周睿鸣:《“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7期
[21]见注12
[22]见注17所引的Hallin1994,以及注9所引的Schudson & Anderson, 2009。
[23]Albert W. Dzur, Democratic professionalism: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dentity, and practice,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8.
[24]Herbert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80;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Gaye Tuchman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 Free Press1978.
[25]刘洋:《新闻场域和客观性争锋:一个理解网络时代新闻业危机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4期
[26]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第189页,沈荟、周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7]李良荣:《新闻机构与平台的新闻专业主义不能丢》。微信公众号网易新闻学院we_know_media,2017年6月20日
[28]见注14
[29]翻阅一本包括了韦伯对于“客体性”的论述的科学哲学读本,从洋洋大观的48章、785页中,我们看到关于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等领域各种话题的不同论述,其中有实证主义立场的表述,也有建构主义立场的表述,此处提到的这两点却是各家大致都认可的基本观点。见Michael Martin & Lee C. McIntyre (Eds.)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1994.
[30]如Jay G. Blumler & Stephen Cushion“Normative perspectives on journalism studies: Stock-taking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ism, 15(3)259-2722014.
[31]Norwood R. Hanson, Perception and discovery: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tific inquirySan FranciscoCA: FreemanCooper & Company1969.
[32]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2nd Ed.)Chicago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33]Max Weber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by E. A. Shils & H. A. Finch)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49. 引语来自第72页。
[34]Peter Berger &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1966.
[35]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1973.
[36]见注24所引的Tuchman, 1978。
[37]这方面的文献很多,可参考注4所引的Fairclough1992; Cristina Lafont, The linguistic turn in hermeneutic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José Medina)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 2002; John S. Dryzek, 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of deliberative governanc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Ju?rgen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nslated by William Rehg)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1998.
[38]Mark Poster,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CambridgeUK: Policy Press1990.
[39]Luciano FloridiThe 4th revolution: How the infosphere is reshaping human reali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40]Michel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C. Gordon (Ed.)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pp. 109-133)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80.
[41]James Bohman, “Realiz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s a mode of inquiry: Pragmatism, social factsand normative theory,” 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18(1)23-432004.
[42]见注12
[43]Meenakshi Gigi Durham, “On the relevance of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to the practice of journalism: The case for ‘strong objectivity’” Communication Theory, 8(2)117-1401998.
[44]Julian BagginiA short history of truth: Consolations for a post-truth worldLondon: Carmelite House2017.
[45]Ralph KeyesThe post-truth era: Dishonesty and deception in contemporary lif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2004.
[46]见注44
[47]见注45
[48]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M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1.
[49]Walter Truett Anderson, “Introduction: What’s going on here?” in W. T. Anderson (Ed.)The truth about the truth: De-confus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postmodern world (pp. 1-11)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95.
[50]注48所引Harvey1991第7页。
[51]见注40所引Foucault1980。在此需要说明两点。第一,虽然指出了以“后”为前缀的各种概念相互间有某种逻辑相通之处,我们既无力也在本文无篇幅来扫描各种“后学”(post-isms),而只是以直接关系“后真相”的“真相体制”概念入手展开分析。第二,在中文表达中,“真理”和“真相”在哲学意义上有重要区分,我们清楚这一点,但反映并受限于我们自己的经验主义趋向,我们回避在形而上学的层面探讨“真理”,而只谈由承接经验观察限定的“真相”。我们与此同时也规避了——在基本价值基础上也拒绝——所谓“绝对真理”或真理的单一普适。简单地说,我们不需要“真理”这个概念来讨论“真相”。关于不同语境下的“truth”,参见注44所引Baggini,2017。
[52]需要特别指出,福柯讨论“真相体制”的语境是法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类型和角色的转换。在他看来,以伏尔泰为代表的“通识型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s)已经被以专门性知识和相关技术为立身之本的“专门型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s)所取代。前者以其道德感召为文化权威,常以“天才作家”的身份出现,而后者则以其专门知识,在国家和资本使然的场域,提供维系民生的谋划,并获取局部形态的权力。
[53]见注40
[54]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Critical Inquiry8(4)777-7951982.
[55]这段的引语都来自注40所引的Foucault1980。
[56]Bruce LincolnDiscour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myth, ritual, and classification (2nd Ed.)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57]见注32
[58]针对“后学”的词藻堆砌、指代不明的学风和论述逻辑,美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向后学重镇Social Text递交了一篇恶搞的所谓“论文”,居然通过盲审而发表。文章发表后,他公布了真相。物理学家Steven Weinberg在他的科学和文化哲学散文集中讨论了此事。见Facing up: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inberg,2001pp. 138-161。
[59]相关文献很多,可参考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1; Edward B. Royzman & Kimberly Wright Cassidy“I know, you know”: Epistemic egocentrism in children and adult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7(1)38-652003; Carl R. Sunstein & Reid Hastie, Four failures of deliberating groups, Public Law & Legal Theory Working Paper No. 215.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2008.
[60]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61]Ilkka Niiniluoto, Critical scientific realism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62]刘擎:《共享视角的瓦解与后真相政治的困境》,《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63]见注12所引潘忠党、陆晔,2017。上文提到的“语言学转向”本身以及它所引发的跨越不同学科的人文、社会理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围绕“交往”——以信息传递和/或意义建构为基本元素的社会行动和关系建构——而发生的行动与社会动态,譬如言说、话语、商议、呈现和再现、文化及其生产,等等。我们如此提及,只为道明文本之间这部分的网络式连接。
[64]德国学者克洛茨以四个“元过程”来概括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全球化、个人化、商业化和媒介化。我们在此提及的是个人化和媒介化,但同时需要指出其它两个“元过程”已经蕴含其中。见Friedrich KrotzThe meta-process of “mediatization as a conceptual fram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3(3)256-260。
[65]Gordon B. MoskowitzSocial cognition.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2005.
[66]James Curran, “Mediations of democracy”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 (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4th Ed.) (pp. 122-149)London: Hodder Arnold Publication2005.
[67]见注34所引Berger & Luckmann, 1966。
[68]Immanuel Kant, “What is enlightenment?” (Trans. by J. Schmidt)in J. Schmidt (Ed.)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pp. 48-64).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69]Michel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 Rabinow (Ed.)The Foucault reader (pp. 32-50)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84. 这部分的论述集中在第38-39页。
[70]见注54所引Foucault1982第785页。
[71]见注54所引Foucault,1982。
[72]见注70所引Foucault1984第43页。
潘忠党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