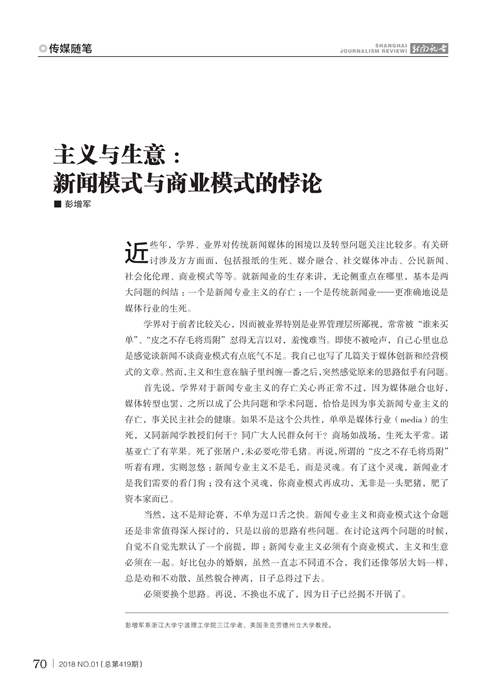主义与生意:新闻模式与商业模式的悖论
■彭增军
近些年,学界、业界对传统新闻媒体的困境以及转型问题关注比较多。有关研讨涉及方方面面,包括报纸的生死、媒介融合、社交媒体冲击、公民新闻、社会化伦理、商业模式等等。就新闻业的生存来讲,无论侧重点在哪里,基本是两大问题的纠结:一个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存亡;一个是传统新闻业——更准确地说是媒体行业的生死。
学界对于前者比较关心,因而被业界特别是业界管理层所鄙视,常常被“谁来买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怼得无言以对,羞愧难当。即使不被呛声,自己心里也总是感觉谈新闻不谈商业模式有点底气不足。我自己也写了几篇关于媒体创新和经营模式的文章。然而,主义和生意在脑子里纠缠一番之后,突然感觉原来的思路似乎有问题。
首先说,学界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存亡关心再正常不过,因为媒体融合也好,媒体转型也罢,之所以成了公共问题和学术问题,恰恰是因为事关新闻专业主义的存亡,事关民主社会的健康。如果不是这个公共性,单单是媒体行业(media)的生死,又同新闻学教授们何干?同广大人民群众何干?商场如战场,生死太平常。诺基亚亡了有苹果。死了张屠户,未必要吃带毛猪。再说,所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听着有理,实则忽悠:新闻专业主义不是毛,而是灵魂。有了这个灵魂,新闻业才是我们需要的看门狗;没有这个灵魂,你商业模式再成功,无非是一头肥猪,肥了资本家而已。
当然,这不是辩论赛,不单为逞口舌之快。新闻专业主义和商业模式这个命题还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只是以前的思路有些问题。在讨论这两个问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先默认了一个前提,即:新闻专业主义必须有个商业模式,主义和生意必须在一起。好比包办的婚姻,虽然一直志不同道不合,我们还像邻居大妈一样,总是劝和不劝散,虽然貌合神离,日子总得过下去。
必须要换个思路。再说,不换也不成了,因为日子已经揭不开锅了。
这个思路也许不那么清晰,但作为起点,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首先,新闻专业主义该不该、能不能是商品?如果不是商品,何以要有商业模式?既然新闻模式和媒体商业模式压根儿就和谐不了,为什么非要吊死在商业模式这棵树上?
也许有人会说,从历史上看,这两者虽然不和谐,不是也曾经有过辉煌吗?不是还有普利策吗?这个没错。但是,细想一下就可以发现,新闻从来都没能够自给自足,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商品,所谓的商业模式其实是媒体业而不是新闻业的商业模式。即使把原来新闻依附于媒体的模式叫商业模式,那现在已经破产,无法持续。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媒体危机正好给了一个新闻和商业模式分道扬镳的机遇。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为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发展寻找一个生存模式?抑或可以有个真正的新闻商业模式也未可知。虽然历史上没有,现在没有,将来还看不到。
新闻的核心
世界上的事情说不清楚的根本原因大概有两点,一为定义,二为测量。定义决定认知,测量决定验证。因而,这里谈新闻也有必要从定义说起,界定一下我们所谈的新闻是什么。首先,我们这里要定义的是journalism,而不是news。虽然说journalism是做news的,但有news不一定就是journalism——抱歉,这里不得已用英文来区分一下,因为如果用中文来讲这个意思,恐怕更成绕口令了。
新闻(journalism)不等于媒体(media),因而新闻模式不等于媒体模式。再而,我们也不是来复习教科书上对journalism的定义,诸如新闻(journalism)是“关于新闻(news)报道、评论、分析的原则和技巧”。我们需要狠抓头皮琢磨的是:这个journalism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的核心和界限在哪里?只要是有关news的生产、传播就是journalism吗?娱乐新闻是journalism吗?体育新闻是journalism吗?文章、马伊琍“周一见”和“且行且珍惜”是journalism吗?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吃瓜群众上传发布一张现场照片是journalism吗?它同一个报社记者发一张同样的照片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深究起来却特别有意思。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过这么一件事:美国有个非常有名的先锋派画家汉斯·汉克(Hans Haacke),擅长以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来解释和批判政治社会现实。1971年,汉克应邀到美国现代艺术的最高殿堂之一古根海姆美术馆举行个展。就在距开幕不到六周的时候,个展被美术馆馆长麦瑟尔(Thomas Messer)叫停,理由是其中三幅作品不是艺术,而是新闻(journalism)。
这三件被馆长称为新闻作品的是什么呢?有两件是纽约曼哈顿贫民住宅区的正面黑白照片,外加公开的资料:住宅编号、业主信息、交易记录、市值、按揭情况等等,题目为:《截至1971年5月1日夏普斯基家族曼哈顿房地产持有:真实时间的社会系统》。第三件作品更绝,是要参观者参与填写的调查问卷,包括性别、年龄等项。
个展的发起人和策展人是立体主义画派和当代艺术的权威福莱(Edward F. Fry)。福莱极力推崇此组作品,说是“改变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也改变人们对于现代艺术的认识”。福莱当然对馆长贬艺术为新闻的做法不以为然,据理力争,结果被炒了鱿鱼。福莱虽然是个大牛,但再没有在美国各大艺术博物馆找到工作,而是转到大学教书,混得风生水起——这不是在讽刺学界好混,只是想说业界和学界江湖不同。
插句题外话:汉斯·汉克一件题名为:《新闻:RSS新闻订阅,纸张,打印机,尺寸不一1969/2008》(Hans Haacke, News, RSS News feed, paper and printervarious dimensions, 1969/2008)也非常有名,同新闻关系更近一些,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那我们的问题来了:馆长说汉克的三幅作品不是艺术而是新闻,那我们觉得呢?它们是新闻吗?如果不是,那新闻是什么?
这个定义还真不好下。首先,从理念层次看,新闻应该是特定理念比如公共服务、民主看门狗等主导下的新闻的采集和呈现行为等等;其次,我们可以说新闻是一系列操作规范,比如验证、准确、客观、平衡、多信源等等。这两方面的讨论多了去了,但并没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那么,再来看结果,因为无论理念还是操作规范,其落脚点肯定是内容。而媒体的内容非常庞杂,也很难为新闻确勾画出一个清晰的边界,何况新媒介环境中,特别是受众加入到内容生产以后,即使有认同的传统边界也正在被重新协商和认定。
那么,让我们再简化一下,不去定边界,而是去看看媒体内容里同新闻的理念和价值观最吻合的。同新闻的政治和社会角色最相配的那部分内容是什么。照著名学者琼斯(Alex Jones)的话说,这块东西是新闻的“铁核心”。①这个核心不是名人,不是体育不是漫画,不是拼字游戏,不是广告,不是周末度假,去哪玩、去哪吃,不是菜谱,不是宠物,不是房产投资、化妆减肥。这个核心就是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的事实报道,这个核心的核心便是深度和解释性报道,用通俗的话讲,就是硬新闻或者严肃新闻。
这块核心应该是最重要、也是最没有争议的journalism吧。以这个核心为基础的新闻模式是什么呢?可以简单概括为三大功能,即“启蒙民众、监督权力、提供论坛”,也就是报道和解释事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至关重要的新闻,是新闻的灵魂。
以上这个说法应该没有大毛病,可我想说的重点不是这个,而是这个核心功能和核心内容——硬新闻和严肃新闻——往往是枯燥的、最不吸引受众的,也恰恰是最花钱、叫好不叫座的。说白了一句话,严肃新闻从来就不是商品,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许更不是。
所以说,新闻模式同商业模式原本就是志不同道不合的两条道上跑的车。
新闻从来不是买卖
首先来说,新闻不是商品,因此也不是买卖。既然我们常说新闻是民主的保证,是第四权力,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那凭什么是商品呢?其他权力机关和公共服务是商品吗?法院有商业模式吗?反过来讲,既然是公共利益,作为私企的媒体组织为什么需要背着抱着这个新闻宝贝却得不到补偿呢?媒体组织为什么不能在商言商呢?无论你怎样站在社会责任公共利益等道德制高点去谴责,其关系也是拧巴的。媒体是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抱怨来抱怨去,成了怨妇,唱“琵琶行”解决不了问题。
新闻的模式以上面的定义,就是以公共服务为宗旨的严肃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在这个模式里,事件本身只是素材,要经过一系列专业的提炼才能成为新闻。新闻的模式细分可以有几种,比如有欧洲的更文学化、政治化、个人化、知识化的模式和美国的客观、平衡、事实性报道的模式,但归根结底是公共服务模式。比较无奈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新闻模式同商业模式捆绑在了一起,或者商业模式借着新闻这个壳上市了。在英国尚有BBC电视系统的公共模式,在美国就完全成了商业模式。
然而,新闻模式同商业模式是两套逻辑、两套话语体系。新闻模式里,公共服务是其出发点和目标。新闻服务对象——或者希望服务的对象是公民,成功的标志是讲政治、负责任的合格公民。而商业模式是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正如韩林和马西尼(Hanlin、Mancini,2004)所说:“其目的是利润,通过消息娱乐吸引个体的消费者,然后再把消费者的注意力卖给广告商”。②
这种基本生态从19世纪30年代现代大众新闻开始就一直没有改变。无人否认商业成功的重要性,《华盛顿邮报》前老板格林汉姆(Katharine Graham)曾说过,新闻专业主义的最大保证就是经济实力。但是说破了天,媒体作为盈利组织,首先是是企业,民主的公益毕竟是第二位的。两者有时候貌似可以调和,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是冲突的,这个应该说是制度设计的缺陷。韩林和马西尼说,美国的模式——即新闻模式和商业模式捆绑的模式——提出的目标很少能够完成,而且常常同新闻业的现实不符。③
也许有人反驳说,那历史上新闻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不是出现了许多典范吗?这话没错,可问题的症结不是说历史上有没有专业主义,而是这个新闻专业主义是否养活过自己。
新闻从一开始就不是商品。在美国,最早的新闻报纸是印刷厂的副产品,犹如现在的复印店随便印份传单之类。到后来,新闻纸成为党派和富有阶层供养的政治宣传品,是政治斗争的工具。1833年,《纽约太阳报》创刊,进入便士新闻时期,一份报纸卖一分钱,媒体犹如今天的社交媒体,开始走入大众,而在此之前,一份报纸要卖六分钱。六分钱同一分钱今天来看差别不大,但是在1833年,一头牛才卖12美金,17美分可以买一磅咖啡。六分钱一份的报纸自然把平民排除在外了。
教科书上说便士报开创了报纸的商业模式,但是,我们可以算算账:一分钱一份是根本是收不回成本的。这个模式实质是把受众变成了商品,卖给广告商。在这里特别容易引起误会的是,便士报创立的是媒介(media)的商业模式,而不是journalism的商业模式。有一句话一针见血: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闻产业;新闻人误以为自己在做新闻,实际上是在做广告。这好比过去江湖上卖跌打丸的,武功杂技表演不是商品,是撑场子,卖的不是艺,卖的是药。1896年,奥克斯(Adolph Ochs)买下了《纽约时报》,提出了新闻的理想模式:“平衡报道,不骄不馁,不偏不倚,百家争鸣,理智讨论,独重事实,不媚受众。”然而,这个冠冕堂皇的模式在现实中却很难实施,因为在其商业模式中,必须“媚众”,没有受众,广告商不会给钱。
美国媒体经济学家汉密尔顿(Hamilton)在《适合销售的新闻》一书中④深入分析了市场如何将信息转化为新闻的过程,强调市场对内容的决定作用。在这个商业模式里,新闻并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读者的消遣,而记者是为了工作,老板为了赚钱。媒介经济的商品属性,决定其根本是供需关系,消费者的愿望驱动媒体的消费。
汉密尔顿总结说,决定新闻的不是什么新闻学的“五个W”,而是关乎经济利益的“五个W”:
1.谁在乎(Who cares)。
2.他们为此想付出什么(What they want to pay for)。
3.媒体和广告商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人(Where can media and advertisers find them)。
4.什么时候提供这些新闻才是有利可图的(When providing these news can be profitable)。
5.为什么这个可以赚钱(Why it's profitable)。
从历史上看,新闻模式也是让渡给商业模式的。在便士新闻之后近150年的时间里,这个商业模式左右新闻内容。严肃新闻内容不到15%,85%是娱乐,而娱乐是最能赚钱的。什么最娱乐?暴力和色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批判了三五十年,媒体暴力和色情变本加厉。
15%同85%这样的比例还可以这样解读:做15%的那部分新闻人是由娱乐新闻来养着的,或者换个说法:新闻人的工资基本是由从来都不看也不欣赏自己的那部分受众养着的。
决定媒体生产的从来都是底线,是市场供需。曾经有编辑抱怨说:我们少报或者多报消息实际上没有读者关心,但是如果今天的漫画没有了,或者填字游戏没有了,马上就有人抗议。
但是,如果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于受众的话,我们就又错了,所谓的读者是上帝是天大的误导,因为广告商才是。我们以为报纸的衰落是因为读者跑了,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广告跑了。传统媒体被广告抛弃。一方面广告有了新欢——新媒体;再一方面是广告业不用借助媒体这个中介而独立做生意,可以直接深入到读者的屏幕。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新闻模式和商业模式在历史上可以凑合的话,那么,为什么媒体不可以利用自己的经验和资源,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继续这个模式?新闻模式和商业模式继续搭伙过日子,虽然不理想,但有总胜于无。可严重的问题是:就是这样凑合的日子也没得过了。为什么以前的模式不灵了呢?原因有多种,比如媒介生态的改变、垄断被打破等等,但最根本的是盈利单位由过去的整个报纸变成了单篇的文章。以前的内容打包配送,严肃新闻可以被搭配出去。而现在的社交媒体时代,受众消费转发的是一篇文章、一个视频或者一张图片,打包批发变成了单个打赏。
有了大数据,饿死总编辑
媒体内容的盈利单位改变以后,以往的新闻和商业搭伙的模式不再现实,新闻模式和商业模式之间的冲突更加突出,困局近乎无解。在很大程度上,媒体融合、媒体转型的过程就是对新闻(journalism)的排斥挤压过程。
道理很简单:媒体日子好过的时候,都是“底线”第一位,现在连“底线”都失守,自身难保,怎么可能考虑新闻这个二线、外围?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是盈利。现在所谓“吸引受众(engagement)新闻”的实质是市场说了算,报什么不报什么,是由受众即时监测数据来决定的。哪条新闻最受欢迎,哪条转发率最高,读者都是什么人,一切都在屏幕上一目了然,哪还用得着总编辑来开什么编前会?更多的读者依据的是算法的推送而不是编辑的选择。根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的的调查,⑤54%的受众更倾向于通过算法的推送比如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等获取新闻,只有44%倾向于依靠新闻编辑和记者,例如报社通讯社网站和email。而且35岁以下的人中,前者的数字为64%,后者只有34%。可谓有了大数据,饿死总编辑。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地方报纸不再设总编辑职位。
而这种几乎完全由市场说了算的商业模式已经确定新闻的娱乐化和小报化不可避免,而整个新闻生产和流通的网络化更为此创造了条件。波兹曼(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说过这样的意思:当只有报纸的时候,信息是有用的、相关的,是可以行动的;当新闻不相关,可以随时随地消费,产生距离时,新闻就成了娱乐。
从目前媒体融合和转型的路径和方向来看,其结果多半会是:商业未必成功,而新闻专业主义必然流离失所。
近年来,由于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崩盘,许多媒体从原来的印钞机(30%的利润率)变成了负资产,而媒介融合和媒体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在这种情况下,风投基金看准了机会,前来抄底。当然,这对于濒临破产的媒体来说,有了金主毕竟不是坏事,也许,资金注入以后,可以争取到一个喘息调整的机会,等度过难关以后再说。问题是,如果一个报社被风投所控制,会考虑新闻专业主义吗?
有这样一个故事:河边有一只折翅的蚂蜂,央求青蛙把它背过河。青蛙说,你可千万别咬我。蚂蜂自然信誓旦旦,可刚踏上岸,蚂蜂立刻就是一口。青蛙很愤怒:你为神马咬我?蚂蜂一撇嘴:不是我要咬你,是我的本能要咬你。风投资本的本性是什么?是投机,是利润。
因此,过去十年,风投资金的进入非但没有减轻商业压力,反而加剧了传统新闻的崩溃。因为这些资本新贵同以前的家族出版和专业报业集团不同,这些金主同新闻媒体没有感情联系也没有价值认同,对于他们来说,一家报纸同一个养猪场没有区别,挣钱就养着,不挣钱就杀掉喝血吃肉。
有人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传统媒体经营那么多年,就是没有盈利,还有品牌。问题是,当媒体内容的盈利单位为单篇文章,而受众又零碎化时,品牌的影响力被无情消解。牛津路透新闻研究所跟踪了2000位用户,发现大多数人能记得什么路径得到的消息,比如朋友分享、应用推送、什么平台等,而能够记住文章原创和出处的还不到半数。⑥
当然,也不是说一点希望没有。这个希望不在别处,就在公众的觉醒,能够认识到新闻的问题不是通过商业模式可以解决的,其公共服务需要公众埋单。公众的觉醒与回归也许需要经过更长的时间、更多的教训。可喜的是,现在已经有一些积极的苗头。对于社交媒体,人们从最初的狂热逐渐过渡到冷静。牛津大学路透研究所的统计,只有24%的人认为社交媒体能够分清虚构和事实,相比之下,40%的人对传统媒体更有信心。传统媒体特别是报纸的付费订户有可观的增长,29%的年轻人愿意付费的原因是赞助专业新闻。
得州大学的齐湘教授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会出现“拉面效应”。⑦所谓“拉面效应”,是说大众一开始可能会喜欢廉价或者免费产品,比如拉面,一旦人们有了钱,或者吃腻了,还是会去消费有营养的牛排。皮尤中心2004和2008年的调查数据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线上新闻的消费明显减少,似乎佐证了这一现象。
然而,无论传统媒体的未来如何,都必须抛弃原来的思路,新闻特别是核心新闻,从来也不是商品,更不是买卖,媒体商业模式和新闻的生存模式是两个问题,该公共的归公共,该商业的归商业。如果不厘清这个关键问题,依然把新闻模式等同媒体的商业模式,那无论媒体转型成功与否,新闻专业主义都无可救赎。■
①Jones, A. Losing the new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②HallinD. & ManciniP. Comparing media systems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 252。
③Halilin & Mancinip. 206.
④Hamilton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sell: How the market transforms information into news.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⑤Journalism Digital News Report 2017Reuters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⑥Journalism Digital News Report 2017.
⑦ChyiH. I. (2015).?Trial and error: U.S. newspapers’ digital struggles toward inferiority。Media Markets Monographs,?14。Schoo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Navarra?Spain. ISBN: 978-84-8081-444-7.
彭增军/彭增军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