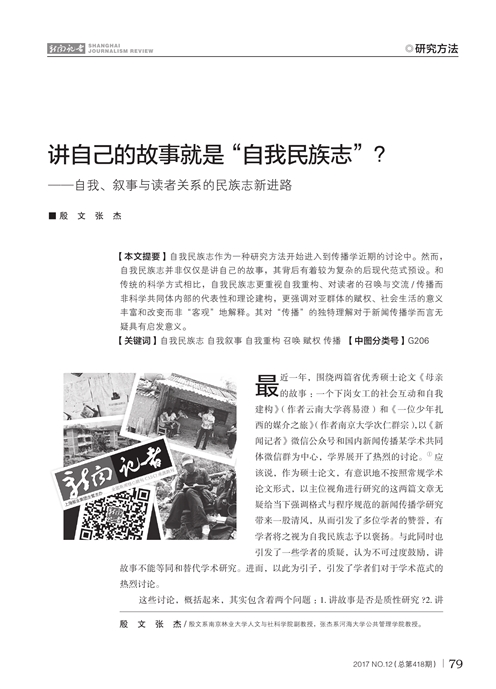讲自己的故事就是“自我民族志”?
——自我、叙事与读者关系的民族志新进路
■殷文 张杰
【本文提要】自我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开始进入到传播学近期的讨论中。然而,自我民族志并非仅仅是讲自己的故事,其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后现代范式预设。和传统的科学方式相比,自我民族志更重视自我重构、对读者的召唤与交流/传播而非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代表性和理论建构,更强调对亚群体的赋权、社会生活的意义丰富和改变而非“客观”地解释。其对“传播”的独特理解对于新闻传播学而言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自我民族志 自我叙事 自我重构 召唤 赋权 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最近一年,围绕两篇省优秀硕士论文《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作者云南大学蒋易澄)和《一位少年扎西的媒介之旅》(作者南京大学次仁群宗),以《新闻记者》微信公众号和国内新闻传播某学术共同体微信群为中心,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①应该说,作为硕士论文,有意识地不按照常规学术论文形式,以主位视角进行研究的这两篇文章无疑给当下强调格式与程序规范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带来一股清风,从而引发了多位学者的赞誉,有学者将之视为自我民族志予以褒扬。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不可过度鼓励,讲故事不能等同和替代学术研究。进而,以此为引子,引发了学者们对于学术范式的热烈讨论。
这些讨论,概括起来,其实包含着两个问题:1.讲故事是否是质性研究?2.讲自己的故事是否是自我民族志?
应该说,民族志大都以讲故事的形式出现,然而这两篇论文引起讨论的地方在于:1.似乎缺乏明确的理论关怀与建构。民族志的故事,即使是“深描”,最后也会有理论意义的讨论。2.研究的客观性如何保障。一般意义的民族志均采用客观化的观察方法,即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投入-抽离,时刻保持对自身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能给研究带来的影响的反思性。即使近年来兴起的叙述民族志或主体民族志,采用主体间性和视域融合的认识论,通过让案主联合发声的方法来展开报告,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展现研究者自身位置的局限性和呈现客观性背后的主观性。②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这两篇文章似乎并没有明显的理论讨论,故事讲完了,给学术带来的价值是什么?特别是后一篇论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写作方式,作为研究者又是叙事者,这个故事是主位取向的,但如何保证资料的真实性?这是一个真故事吗?
随着讨论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作者论文在网上的部分公开,关于该论文是否具有学术意义的质疑开始下降。在进一步的学术讨论中,学者们迅速越出对这两篇论文本身质量的讨论,关注这场讨论背后所折射出的学界知识生产的路径问题。有学者将这篇文章与民族志,特别是自我民族志联系起来,认为带有理论关怀,反映了传播学界一直相对忽视的诠释范式,③反对将科学研究的程序:提出问题-搜集证据-解决问题即实证研究的方法作为判断该文质量的标准。④
这次讨论无疑体现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界对于学术规范的自觉,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但是,从目前的讨论来看,正如已有的两篇研究文献的主题,大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此展开量化与质化、形式规范还是问题优先等当下传播学界研究取向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持质化立场的研究者倾向于将这两篇文献贴上“民族志”和“叙事”的标签,然后借此来讨论质化与量化的分野。这种讨论在学科范式的丰富和厘清上当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将这两篇文献简单视同于叙事研究,特别是将第二篇文献简单视为自我民族志的一种创作尝试,可能会让年轻学子特别是硕士研究生们引发对于自我民族志和叙事研究的一些“误读”,从而激发硕士研究生们的简单模仿,这反而会混淆了自我民族志的传播。有鉴于此,本研究拟对该论文及其引起的“争议”从叙事和自我民族志的角度予以初步分析和厘清,这对于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共识和知识传播而言,也是有益的。
一、讲故事与叙事
讲故事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技巧。历史学、文学、人类学都很注重文章的可读性,史学大家史景迁更是以讲故事著称,人类学的民族志报告也是可读性颇强。然而,现代学术规范强调学术创新,随着实证主义成为现代学术的主流范式,修辞上也呈现出文献回顾-问题提出-资料搜集-资料挖掘-得出结论或建构模型这样的科研“八股”,从而使得如果仅仅是单纯的“讲故事”而没有学术问题的提出-分析-解释-建构流程,就丧失了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称之为论文的合法性。这两篇硕士论文一开始引起的争议也是集中在此。
那么,这两篇硕士论文是不是叙事研究呢?许多叙事研究者将叙事看作故事(story)的同义词。⑤但是与故事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叙事(narrative)不仅包括事件与情节,还包括解释。叙事是对一系列事件进行组织并予以解释,包括赋予故事中的角色以能动性以及对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行推论和解释。⑥Polkinghorne将叙事界定为通过故事形式来表达的某种组织图式,它同时包括创造故事的过程,故事的认知图式及故事的结果。⑦叙事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它把叙事者的经验组织成为具有时间性和富有意义的情节(plot),从而让事件得以连贯一致,通过情节,叙事将事实上复杂的、模糊的经验事件改编为具有一致性的故事。⑧
透过上述的定义可见,叙事研究虽然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现,但却有着作者自身的理论自觉嵌入其中,是对人类经验和知识的讲述、组织和解释,只不过一切都是含而不露。叙事研究不仅仅是日常生活意义的讲故事,更是一套后现代理论话语,它采用了讲故事的形式,但背后蕴藏着一套后现代的学术理念。
因而,叙事研究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是在后现代背景下针对现代主义强调实证和科学提出的一套替代性方案。在这套方案中,讲故事被赋予了拥抱日常生活,抛弃现代社会理论宏大叙事的理论任务。“故事或自我假说决定我们如何塑造生命经验。我们并非通过生命故事存活,而是故事塑造、组成并‘拥抱’着我们的生活。” ⑨
叙事意义的讲故事强调人们并非依据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所宣称的科学性(认识社会的普遍客观知识和规律)来认识世界和生活,而是通过自己头脑中的先在概念来认识世界。这些概念来自人们过去的主观经验和情境,并构成了人们当下的行动与生活指南。而这些故事或者说是叙事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还体现在自我认同的建构方面。“在对其他人描述我的处境、做我自己是什么感觉时——我检视了自己的状况,并试图找到我的核心特质——当我的描述带出了某种结构时,我可以直言,这是来自我对自身处境的已然存在的想法”。⑩
这种对普遍性客观科学叙事的反思自然引发了对差异和意义多元的重视,叙事研究的背后隐藏着对“科学”叙事权力的反思和否定。“真理之路朝向大众,朝向简明易懂的科学之路,并且与特殊性、情境性、具体性息息相关”。[11]因而,叙事研究更重视个人与社区的所谓“地方知识”而非专家知识。这种对地方知识重视的背后其实是对生活意义,对个人叙事所建构的自我的重视。因此,叙事研究虽然采用了讲故事的形式,但是不能仅仅将之视为日常生活或者文学、史学意义的讲故事,它有着一整套的理论预设。讲故事是为了更好地展示地方知识和具体自我的多元视角,从而让社会科学对于生活世界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有更完整的理解。其间,时间的序列性、情节和自我的反思性成为叙事关注的重心。[12]从叙事的目的性和组织性而言,这两篇硕士论文采用了讲故事的形式或者说叙事的形式,但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叙事组织、解释和自我呈现的理论自觉。严格来说,是采用了讲故事形式的科学研究(探讨或验证规律)而非叙事研究。
二、讲自己的故事与自我民族志
对第二篇硕士论文的讨论中还牵扯到近来人类学中的一种新体裁:自我民族志。不少讨论者将这篇论文视为自我民族志的某种努力。当然,从形式上来说,这篇硕士论文采用了讲自己的故事的形式来展开分析。那么,讲自己的故事是不是就是自我民族志呢?
自我民族志是近年来“反思”民族志或者说后现代民族志的一种民族志的新取向。它采用自我叙事的形式,着力于作者自身的危机经历和生活重构。一般来说,采用自我民族志的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癌症病人,失亲者,肥胖病患者等。这类群体往往很难被研究者进入和真正理解,在传统的民族志研究中,处于失语者的状态。因而,自我民族志的兴起,通过对特殊群体命运与生活的聚焦、反思和交流,对于改善公众对这些群体的理解,进而改变社会生活而言,无疑具有赋权的积极意义,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第二波:建构性后现代主义。
表面看来,自我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是一体的,与传统的民族志构成了明显的区别。“从自己的个人生活开始,关注自己的情感、思绪和情绪。” [13]但其实面对的是民族志的老问题:研究者对于田野和研究对象的进入与退出的方法问题。自我民族志强调的是对于特殊群体,自我作为群体成员理解“地方知识”的独特优势,以及将这种地方知识传播给外群体的能力和技巧。更重要的是,自我民族志是通过叙事的手法,来重新建立起自我的时间连续性,从过去指向未来,从而对于自我的重构提供新的资源。
这就意味着,讲自己的故事并不是自我民族志的目标,通过对自我故事的重现选择来完成自我认同的建构,完成对未来的我的新的理解和期许,才是自我民族志采用主位叙事的意图所在。因此,自我民族志在书写手段和书写目标上其实是一种自我叙事(self-narrative),[14]个体除非把它和自己的过去、现在连接起来,否则是难以理解的。自我叙事其实是一个将不同生涯部分的自我片段整合成有说服力的整体故事的过程。[15]与自我叙事的目标相契合,艾利丝将自我民族志定义为一种自传体裁的写作和研究方法。它显示了意识的多层次性,将个体与文化连接起来。自我民族志采用一种先外后内的观察方法,研究者会先透过民族志的广角镜聚焦于外在于个体经历的社会与文化面向,然后,由外而内看,揭示出一个通过文化与社会持续产生的脆弱的自我,但自我民族志拒绝一种文化的解释。[16]如果说艾丽斯强调的是自我民族志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重构从而实现对自我的诊疗功能,那么,博克钠则强调自我民族志的“传播”功能。他认为自我民族志是一种召唤叙事(evocative narratives),其目的是表达和讨论,而非传统的社会科学所强调的代表性。[17]因此,通过自我叙事表达,使外群体的人能够对自我和内群体的经历产生共情和理解,构成了自我民族志的另外一个目标和旨趣。
综上所述,自我重构与召唤读者加入,这才是自我民族志的两大任务。
自我民族志对于多元社会中的沟通与理解非常重要,邓金将自我民族志视为是民族志和韦伯以来的解释社会学的当下发展。“个人视角对于确定社会生活隐藏着什么问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分析社会问题是如何形成的来说,同样是非常重要的”。[18]对于叙事所强调的地方知识和生活意义而言,自我民族志无疑具有独特的理解优势。“只有你能写出自己的经历,没有谁可以代替你,与此同时,就你的经历而言,也没有谁能够写得比你好,你所写的任何东西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 [19]自我民族志对于运用格尔茨的深描方法而言,无疑具有独特的优势。深描的核心任务就是将研究对象经验中起支撑作用的意义揭示出来,它不仅是描述,同时是一种解释,通过解释,让读者真正领会地方知识和经验。因此,深描是去理解研究对象的观点并予以主位意义的解释,这是解释的黑匣子。[20]而这个黑匣子对于自我民族志而言,却是其最大的优势。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生活的理解构成了其深描的基础,这种自我叙事的深度理解和深度解释往往是作为外来者的其他研究者无法做到的,特别是当研究者身处某种特殊群体之中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这篇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特殊的,被其他群体很难深度理解的群体,作者采用自我民族志的方法是适当的。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使用自我民族志的方法自觉是相对缺乏的。对于运用自我叙事,通过叙事重组来重新审视自我、构建新的自我评价和对未来自我的重建方面,从目前该文的框架和介绍来看,是相对不足的,而通过叙事的技巧运用,从而达到开放这种地方经验,召唤读者聆听、理解、交流独特群体生活的主动意识和技巧也是不足的。而这恰恰如前所述,是自我民族志的两个中心任务。可见,讲自己的故事,如果不能做到自我的重组,通过回顾过去建构当下和未来;如果不能通过这种自我叙事来邀请读者参与理解和交流,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自我民族志。
三、如何评价自我民族志
艾利丝的自我民族志即使在质性研究内部也引起了争议。焦点之一就是如何衡量自我民族志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如何评价一项自我民族志的研究质量?艾利丝认为:“采用那种称为‘系统的社会学内省’和‘情感召唤’的方法来试图理解自己的生命历程。然后,我把它写成一个故事。通过探究一种特别的生活,我希望了解一种生活方式。” [21]由此可见,自我民族志的评价标准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特别是持客观主义立场的质性研究,它并不将理论建构视为主要的研究目标和评价标准,而将开放式的邀请、交流/传播与对话视为评价自我民族志是否成功的最主要标志。
这种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标准的转向与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兴起后对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的正统共识的冲击有关。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客观的,可以依照某种可操作的、可复制的流程去获得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识,而是开始反思这种正统共识本身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权力地位,需要采用新的研究方式来对这种权力宣称予以反思。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建构一种新型关系:合作性关系而非宰制性关系。[22]而恰恰通过自我民族志,传统的研究者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分离被打破了。[23]正是这种对自我民族志中潜在的作者-读者、专家-研究对象新型关系——交流而非单向的真理宣称的追求,使得自我民族志固然有着对理论的追求(只是这种理论追求更多的是通过叙事技巧来表达,是含而不露的),但更重视读者的参与与对话。在自我民族志的阅读中,相较于传统的质性研究报告或专著,读者彻底地转换了角色。他们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变为共同参与者。读者对自我民族志期冀的是被告诉和复述,而非理论化和条理化;渴望为进一步讨论提供素材,而不是提出确定性的结论;渴望丰富多彩的细节性描绘,而不是对有关事实干巴巴的摘要性描写。[24]也就是说,传统的民族志和质性研究评价的标准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专业标准,而自我民族志的评价标准除了原有的专业标准以外,更强调的是沟通标准。前者重视的是成果的学术共同体评价,后者重视的是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与传播效果。
也正因为自我民族志重视与读者新型关系的建构,重视文本本身的邀请和对话意蕴,自然引起了对其叙事真实性的批评。其中最有力的批评就是认为自我民族志或者说自我叙事是一个“自我的浪漫建构”,它不能成为社会科学的一分子。[25]叙事必须用来进行严肃的社会分析,才能成为社会科学。[26]这种批评包括两个层面:1.自我民族志或者说自我叙事很难保证叙事的真实性。2.自我民族志没有明确的理论建构和理论讨论。
然而,针对第一个层面,对于后现代主义而言,叙事既是讲述生活,同时本身就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办法抽离叙事去谈客观性的问题。在叙事意义的层面上,也无法评价哪个叙事是更“真实”的,除非是对于准确性有要求的具体的细节性的历史学研究。针对第二个层面,自我民族志当然流派很多,代表性的艾利丝还是强调社会学的内省和理论自觉的,但是对于自我民族志而言,最主要的还不是学术的理论建构或者理论讨论,而是要通过叙事形成自我的一致感使得过去、现在和将来能够连成一体。“无论我们是否有意去追寻,一致性对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27]叙事是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因而,对于自我民族志而言,重要的不是去问我的故事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我的过去,而是我的故事会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故事会把我形塑成什么样的人?它能给我的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可能性?[28]这种对自我的“诊疗”以及由此产生的读者的移情和交流、对话,在自我民族志看来,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自我民族志而言,事实与价值之间不存在着截然的界限,因而两个层面的批评在自我民族志看来都是原有的实证主义范式下的发问,而自我民族志正是要打破这种研究者权威的迷思。既然在实际的田野和质性研究中,是无法避免观察者影响的,那么自我民族志会发问,为什么不直接承认这种影响并将观察者作为研究的中心呢?社会科学不应该仅仅只有朝着客观的科学的路径,而是要沿着人文与解释的传统,朝着让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有意义、更有道德和伦理的实践之路去迈进。
因而,对于自我民族志而言,代表性、理论建构这些实证主义的研究规范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自我民族志作为一种叙事文本对作者-读者关系的改造,从科学共同体内的研究转向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传播实践,以及这种沟通对于作者和更大范围的社会公众能够产生的伦理实践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民族志的评价标准是沟通而非科学,对于真实性的评价也来自读者而非学术共同体内部。叙事需要唤起读者的共鸣,使他们认为叙事是真实的,故事是黏合剂,它联结读者与作者,沟通他们的生活,发掘出各自生活的连续性与相似性。[29]当然,故事本身必须是实际发生过的而非虚构的,这是自我民族志对于叙事真实性的底线。
那么,自我民族志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文本,它与非虚构小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事实上,自我叙事本身就要求有一定的解释而非单纯地讲自己的故事。“自我叙事是讲述自己的经历,并对其做出解释。自我叙事可以同时处理过去、现在与将来。”这种解释事实上是具有理论意义的,因此,邓津强调,解释者必须是见多识广的读者,他要熟悉解释理论的总体概况,并能在自己解释故事时灵活运用。[30]而对于自我民族志而言,这种对自我经历的解释更需要具有学理的意蕴,体现在艾利丝所说的社会学的内省上面。自我民族志的目的是通过故事来揭示应该如何使得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因此,自我民族志是一种伦理实践,是理论自觉下的伦理实践。这就回到了社会学创建初期的道德关怀,社会学是一门道德科学,其目标是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因此,故事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意义沟通的手段与桥梁,而故事的意义则来自社会科学家们自身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框架,自我民族志是要将故事与分析框架融为一体的。[31]叙事作为一种资料的重组方式,这种重组本身就蕴含了不同的理论选择和理论表达,辅之以必要的分析,就构成了带有一定学术意蕴的自我民族志。因此,自我民族志,特别是艾利丝的自我民族志,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和知识出发,通过自我叙事,来开放邀请,鼓励读者来思考、对话那些影响和框定人们日常生活与生命事件的文化模式与社会结构,并通过对话来展示人们如何可能逾越这些限制人行动与日常生活的文化与社会结构。可见,自我民族志是要让社会学知识向学术界以外的读者开放,要让社会学变得对普通人具有亲和力与影响力。
因此,自我民族志依然是带有学术追求的自我叙事,只不过它跳出了传统的学术共同体内部,而更追求与社会其他成员的沟通和影响,追求社会学和人类学自身应该具有的伦理意蕴。这也就意味着,自我民族志是一种开放社会学学科边界,让社会学知识成为公众讨论平台进而改变现实生活的公共社会学的学术努力。
自我民族志的信度和效度并不来自量化分析的代表性,类似于质化研究所强调的理论的推论能力或者说概括力。但是自我民族志强调的是故事的可沟通能力。故事的概括性不仅仅是体现在一般质性研究所遵循的同行认可的理论代表性,更体现在读者对故事的共鸣、反思和交流。因此,就如同质性研究的“代表性”不是量化意义的代表性,自我民族志作为一种重视沟通的新型民族志,其对理论的理解和对“代表性”的理解也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民族志。
四、自我民族志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启示
自我民族志走出了传统民族志的藩篱,将“传播”视为民族志最重要的目标。其“传播”观主要强调两点:
1.传播是自我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在遵循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采用叙事技巧,让读者产生移情效应,理解和交流才能成为可能。因此,自我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自我叙事,需要采用写作技巧和自我暴露,需要展现自我的脆弱时刻和所思所想,人生的艰难抉择,这既是自我反思、诊疗,从而达到自我重建的需要,同时也是通过主位视角的情感表达,召唤读者、满足读者更好地移情的需要。
2.传播是对亚群体的赋权。自我民族志的目标不仅仅为了科学共同体的解释,也是为了实现更好的社会生活,赋权是自我民族志传播的核心功能。自我民族志的传播有着三重赋权目的。首先,自我民族志通过对自我艰难时刻的回顾,通过叙事来展现自我重构的过程,从而达到自我疗治、自我赋权的效果。其次,对身属亚群体的群体赋权。通过对自我重构经历的展示和交流,从而召唤读者对亚群体产生移情,丰富社会公众对于亚群体的认知,对于亚群体的命运和经历进行反思、讨论和交流,进而改变读者对亚群体的刻板印象,改善亚群体的社会状况,实现对亚群体的赋权。最后,通过自我民族志的传播:自我与读者的交流,让自我、具有相似经历的亚群体成员获得实践知识,改善自我和他人的命运,并实现更大范围的公众讨论,从而有了改变公共政策,在宏观层面实现对亚群体赋权的可能。
因而,自我民族志的传播观因对自我与读者沟通关系的重视和对社会生活改善的伦理关怀,使得其与新闻传播学之间具有天然的家族亲和性,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其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前景可期。在一定程度上,新闻传播学长期存在的业界和学界之间的隔阂,在自我民族志的传播视角下,其问题域可能会发生改变,无须继续纠结新闻传播学的业务性和理论解释性何者更为重要、优先的问题,而改为如何通过自我民族志的学术研究、让新闻报道更具有自我疗治和开放交流、实现对亚群体赋权的目标,从而出现学界和业界合力的可能。■
注释:
①这场讨论以《新闻记者》微信公众号2016年7月14日推送《获评省级优秀硕士论文,看看人家写点啥?》介绍云南大学蒋易澄的硕士论文为开端,从2016年8月17日发文《谁说省优论文一定很枯涩?这篇省优论文让人不忍释卷》介绍南京大学次仁群宗:开始进入高潮,学者以新闻记者微信公众号为平台,各抒己见。学者们对这两篇论文的相关讨论详见《新闻记者》官方微信公众号2016年7月15日《郭建斌:“记叙文”也能获评优秀硕士论文?大咖告诉你为什么》、2016年8月18日《朱丽丽:一场学术与生命的遇见:“记叙文”获省优秀论文释疑》、8月19日《一篇获奖论文引发的讨论》、8月22日《学术创新还是缺少规范?一篇“讲故事”的论文获奖引起的讨论(续)》、8月25日《郭建斌:对硕士论文〈一位少年扎西的媒介之旅〉的看法——兼谈学术评价的学术化》,8月30日发文《优秀硕士论文作者也有话说:我是为了被压抑话语权的母亲而写》、《优秀硕士论文作者也有话说:我为什么会写一篇“研究自己”的论文》介绍了两位当事人对于自己论文的看法。
②关于叙述民族志,参见巴巴拉·泰德洛克:《民族志和民族志描述》,载于邓津、林肯主编:《定性研究》第二卷《策略与艺术》,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3-494页。关于主体民族志,详见朱炳祥:《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王铭铭:《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③朱丽丽:《学术的环流:叙事、地方知识与主体性》,《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
④胡菡菡:《“反学科”的传播学:告别“范式”想象回归研究问题》《新闻记者》2017年第1期
⑤PolkinghorneD. E.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human science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⑥MurrayM.:《叙说心理学》,见J. A. Smith主編l:《质性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实务指南》,台北远流出版社2006年版
⑦PolkinghorneD. E.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human sciences. Albany, 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13.
⑧PolkinghorneD. E.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human sciences. Albany, 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18-19.
⑨white,michael(1995)re-authoring lives:interviews and essays.Adelaide:Dulwich Centre Publication.转引自Martin Payne著,曾立芳译:《叙事疗法》第20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
⑩SchotterJohn(1985). Social accountability and self-specification’in K.J.Gergen and K.E.Davis(ed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erson.New York:Springer Verlag.
[11]GeertzClifford(1973)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
[12]Clandinin,D.J&ConnellyF.M:《叙说研究:质性研究中的经验与故事》,蔡敏玲、余晓雯译,台北心理出版社2003年版
[13][16][17][22][24][28][29][31]艾利丝、博克钠著,风笑天等译:《作为主体的研究者:自我的民族志、个体叙事、自反性》,邓金、林肯编:《定性研究第三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第782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GergenK. J.& Gergen, M. M. (1988). Narrative and the self as relationship.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1pp17-56.
[15]CrossleyM. L著,朱仪羚等译:《叙事心理与研究:自我、创伤与意义的建构》,涛石文化2004年版
[18][19][30]邓金著,周勇译:《解释互动论》第38、39、71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0]OrtnerSherry B.(1997)Thick resistance:Death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agency in Himalayan mountaineering.In Ortner,Sherry B.(Ed)The fate of “culture”:Geertz and beyond[Special issue].Representations,59p158.
[21]艾利丝、博克钠著,风笑天等译:《作为主体的研究者:自我的民族志、个体叙事、自反性》,邓金、林肯编:《定性研究第三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第782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3]Jackson,M.(1989)Paths toward a clearing:Radical empiricism and ethnographic inqui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艾利丝、博克钠著,风笑天等译:《作为主体的研究者:自我的民族志、个体叙事、自反性》,邓金、林肯编:《定性研究第三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第791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5]AtkinsonP.(1997)Narrative turn in a blind alle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7pp325-344pp338-339
[26][27]Carr,D.(1986).Timenarrative ,and history.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97.
殷文 张杰/殷文系南京林业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副教授,张杰系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