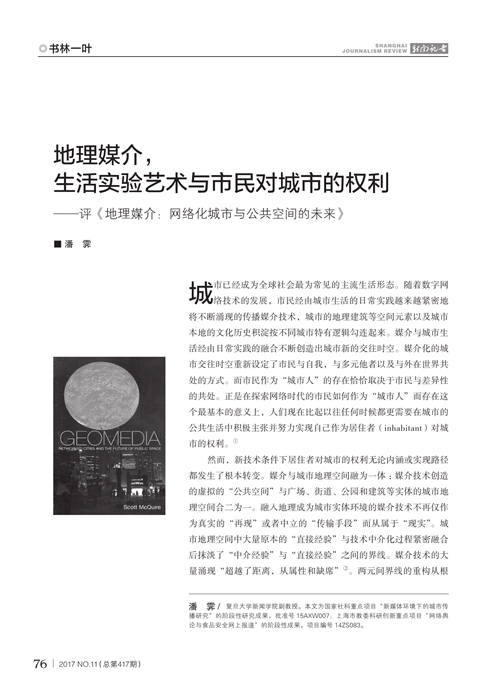地理媒介,生活实验艺术与市民对城市的权利
——评《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
■潘霁
城市已经成为全球社会最为常见的主流生活形态。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市民经由城市生活的日常实践越来越紧密地将不断涌现的传播媒介技术,城市的地理建筑等空间元素以及城市本地的文化历史积淀按不同城市特有逻辑勾连起来。媒介与城市生活经由日常实践的融合不断创造出城市新的交往时空。媒介化的城市交往时空重新设定了市民与自我,与多元他者以及与外在世界共处的方式。而市民作为“城市人”的存在恰恰取决于市民与差异性的共处。正是在探索网络时代的市民如何作为“城市人”而存在这个最基本的意义上,人们现在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中积极主张并努力实现自己作为居住者(inhabitant)对城市的权利。①
然而,新技术条件下居住者对城市的权利无论内涵或实现路径都发生了根本转变。媒介与城市地理空间融为一体:媒介技术创造的虚拟的“公共空间”与广场、街道、公园和建筑等实体的城市地理空间合二为一。融入地理成为城市实体环境的媒介技术不再仅作为真实的“再现”或者中立的“传输手段”而从属于“现实”。城市地理空间中大量原本的“直接经验”与技术中介化过程紧密融合后抹淡了“中介经验”与“直接经验”之间的界线。媒介技术的大量涌现“超越了距离,从属性和缺席” ②。两元间界线的重构从根基上颠覆了经典传播研究背后的“再现论”预设。在新的媒介条件(即新的城市)中,以在场—缺席或中介—直接等两元对立结构为基础的媒介理论应怎样从技术环境变化出发重建自身根基?市民对城市的权利面临着怎样的机遇?数字技术与城市地理的融合过程涌现出哪些悖论?我们在新的条件下如何讨论媒介和城市的关系?传播技术的发展如何才可以为市民实现对城市的权利开辟新的可能?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近推出城市传播译丛第一部,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斯考特·麦奎尔(Scott McQuire)所著《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以下简称《地理媒介》)。该书从“地理媒介”概念入手,整合多学科资源对传播学理论作了彻底的反思重构,从理论上激发读者对传统媒体研究背后的“再现论”范式作创造性批判。作者阐明了数字媒介在促进城市公共生活方面的种种悖论,并通过在不同城市空间的现场实验探索了地理媒介支持的交往在“重造公共空间”方面的可能性。问题与多重可能性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城市传播研究的关键。③对问题—可能性的整体叙事和分析充分体现了麦奎尔教授理论上的创新和对城市公共生活的应然立场。本文从麦奎尔对媒体与城市关系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对技术可能性的讨论和整书结构等侧面入手,希望对此书的意义和局限有较为中肯的评述。
问题:媒介与城市公共生活的堕落
麦奎尔教授《地理媒介》全书提问的基点是,作者体察到媒介技术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剧变给城市公共生活及媒介研究带来了新的问题。问题的提出本身彰显了作者基于对在场—缺席两元对立结构的反思,重新理解媒介技术和即时性的理论意图;阐明了作者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智慧城市”理念及其背后技术观念的深刻批判;而发问方式也预示了问题答案对于城市公共生活的未来所具有的指向性意义。
数字网络媒介与城市地理元素全面的深度融合将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转化为“地理媒介(geomedia)”。④“地理媒介”深刻改变了城市和媒介的结合及两者对于公共生活的意义。诸多新的城市交往实践迅速涌现。技术与技术实践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城市文明理解技术的速度。技术与(技术)文明在发展速度上的失调导致城市公共生活的全面堕落和现代文明的退化⑤。这种堕落和退化表现在个体与城市生活整体的生命力之间的关系。从个人角度,Jonathan Crary指出:⑥“(在数字网络环境中)个人的物化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个人不得不为自己更好地参与数字环境或响应数字化的速度而重新认识自我。”自我在数字媒体环境中的“物化”在城市中创造出诸多碎片式的差异,并“打开”了更多炫人耳目的新奇体验。城市中被传播技术(程序算法)“黑匣子”驱动的喧嚣忙碌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繁忙纷乱的城市网络矩阵中,个人即兴的破坏性创造和人与人之间“心有灵犀”的偶遇却愈发难觅。市民个人存在的意义或湮灭在日常每个离散时刻的繁忙乏味,无迹可寻。与碌碌无为如影随形的是城市市民个人生活激情和创造活力的衰退。除此以外,城市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间传统边界急速地重构也产生双重后果:诸多原隐于城市“后台”的交往实践获得了“可见性”,而城市对“缺席”的象征性“召唤”也发生了转变。这种变化将大量“新奇诡异”的体验带入市民生活:既可激发市民实验性的探索精神,也带来了存在意义上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焦虑。⑦城市乏味的喧嚣和无处躲避的“焦虑”笼罩了个人日常生活——个人的堕落和生命的退化迫在眉睫。
从城市整体看,作为城市精神生命力源泉的玩乐精神(play)和公共参与过程在超工业化逻辑支配下也发生了关键转变。按斯蒂格勒⑧所言,这种转变令城市生活所有方面都有可能被作为经济生产的基本元素重新安排。这种安排秩序中,城市本地的历史文化符号、数字网络媒介技术和城市地理空间的意义都缩减为被资本权力利用以提高监测控制效率,增加信息传输精准程度的手段和工具。想象媒介技术和规划城市生活的方式也多被精确度、覆盖面、速度和效率等概念主导:空白、模糊和迟延成了媒介技术和城市规划要克服的障碍。遵循数字网络时代超工业主义(super industrialism)的逻辑,7天24小时全面无遗漏的实时监测,完整到每个细节的规划设计,基于理性计算预测规避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对市民主体自发性的无视,成了城市规划实践背后常见的理念和意识形态。⑨一旦这种工业化的技术安排被奉为理所当然,人与技术、人与他者、市民与城市间原本存在的诸多其他可能性皆被遮蔽起来,城市的生命力因此枯竭。在城市本身遭到破坏的同时,如何面对城市社会的激增的复杂性和不断涌现的差异性却变得愈发举足轻重。⑩
麦奎尔教授指出,目前甚为流行的“智慧城市”话语即超工业化实践的代表。以“智慧城市”为典型的城市规划话语实践了关于控制城市的幻想,却忽视了城市生活本身具有的复杂性。智慧城市能通过多种数字网络不断地提供城市中人财物流动的数据。[11]对城市生活主要方面实时全面的数据化带来不间断的全面追踪,不断增强的监测管控,以及对未来更强大的预测能力。为此目的,智慧城市规划需利用数字网络技术管理规训并刻意消除城市公共生活中的不完整性、不确定性和市民生活实践中自发的主体性——那些成了“智慧城市”想象中给管理者造成不便的“噪音”。“智慧城市”建设背后的观念压制了关于城市未来可选项的有益对话。雷姆·库哈斯[12]认为智慧城市观念的流行恰恰表征了对现代城市想象的贫乏。萨森认为,智慧城市的计划过多将数字技术用作增强中心控制和管理的工具。[13]城市变得越“智慧”,生活其中的市民却可能对自己越不满,并丧失对集体未来的信仰。麦奎尔教授在书中更是认为,市民对自我的不满和信仰的丧失反过来又加剧从众心理,形成了城市公共生活不断堕落的恶性循环。而全书提问的出发点就是:“地理媒介”作为新的媒介形态能否有效地打破这种可能带来城市公共生活全面堕落和文明退化的恶性循环。全球网络化时代,无论是提出问题或对问题的回答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人类集体的未来。
可能性:地理媒介带来的其他选择
针对(或说循着)提出的问题,麦奎尔用多琳·马西看待城市的框架来观察媒介技术给城市带来的变化。马西在《城市世界》一书中指出“城市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城市这种模糊性,这种可能性与问题并存的状态会一直贯穿本书”。稍加改动,媒体技术可能性与问题并存的暧昧同样也贯穿了麦奎尔的《地理媒体》。数字网络技术或可招致的堕落可能仍需由技术来救赎。远程通讯技术一方面被学者视为对现代民主的重大威胁,同时也被视为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民主和平的唯一可能。[14]麦奎尔教授就是从这个立场出发强调了“媒介”转变为“地理媒介”的过程给城市公共生活带来的多重可能性,并在书中大声疾呼“数字媒体的传播潜力在目前被极大地浪费了”。
数字网络媒体传播方面的潜力集中表现为地理媒介在重造城市公共空间方面的多重可能性。公共空间是城市中不同个人有限在场之间进行彼此显露的所在。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认为,健康有益的城市公共空间需在市民个人隐私的安全边界和松散的社会接触间达成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的持续能促进公共信任的形成。[15]而媒体技术迅速以各种新形态(如大屏幕,墙面灯光秀等)嵌入城市已有的地理空间,在由逻辑算法关联起来的地点间重新安置了非具身性的碎片化主体。这种嵌入和安置将媒介技术原本对交往的时空设置叠加糅合到广场、公园、步道等那些本就设定市民聚散流动的时空安排之上。这种叠加混杂是生成性的。地理与媒介的“联姻”改变了城市公共空间中公共交往的形态;创造出身体“集体在场”的新城市体验,也重新划定了个人边界和松散接触间的平衡点。作为后果,公共与私密,中介互动与当面交往,生人与熟人等城市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范畴随之发生了松动。
与技术(反)乌托邦观点不同,麦奎尔从这种松动敏感地意识到城市公共空间除了被商业和政治裹挟外,还能成为市民培养和试验新型社会交往技能的场所。地理媒介为市民在城市公共空间中以实验精神积极探索体验新的社会互动形态创造了可能。但仅具备媒介技术条件并不足以实现可能。麦奎尔教授强调为了培育市民的实验精神,网络化的城市公共空间需充分“留白”。与“智慧城市”的设计理念不同,城市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要对不完整性,市民的自发性和不确定性的涌现作有意的保留和鼓励。按萨森所说,城市要在充分认可“不完整性”本身的价值后,利用设计规划鼓励居民通过本土实践来将信息传播技术城市化。这种对“不完整性”的保留能有效地包容市民日常交往中的实验性创造,并推动差异化行动主体在参与式公共空间中尝试多样化的合作共处。麦奎尔教授认为,这种对实验精神的包容可以在网络化城市公共空间中培养市民与“地理媒介”技术相匹配的社会技能。不断获取和实践更新的社会交往技能是人们作为“网络化市民”存在,并实现自己对城市权利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麦奎尔教授的研究不止步于理论,更实际实施了包括城市广场大屏幕互动,光柱墙面投影和大屏幕跨国舞蹈教学等多场城市公共空间的数字艺术实验。实验从理论上支持了探索性艺术实践对市民探索精神和社会技能培育的促进作用。艺术实践的实验性具身(embodiment)方法通常探讨政治和商业力量鲜有涉足的互动维度:这为城市交往摆脱政治或资本逻辑提供了沃土。开放的艺术实践将城市生活所有交往关系作为审美对象加以重新审视。[16]媒体技术、具身行动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体验——打开城市生活的审美维度同时推动了“成为公共”的过程。经由市民的艺术实践,城市本身成了始终“有待完成”的艺术作品。城市中的社会关系和权力权威不再仅仅依据植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生活形态。权力与社会关系更直接地被转化为具有时间性的“传播”过程。在探索习得新的交往技能过程中,市民们创造出新的关联,打开原本被封闭的通路,并将现实中孤立的不同层次重又连接起来,化为城市创造力和生命力新的源泉。恢复城市生活的生命力和激情重又成为可能。对此,麦奎尔教授描绘在松散但充满各种激进不完整性的城市时空中,市民作为生活艺术家栖息其中(inhabit)积极地实践更为圆满和充满激情的生活。城市生活实践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那些让人激动的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为人们驱散现代城市喧嚣繁忙过后的绝望平庸和无趣提供了不断更新的可能。
《地理媒介》全书架构与可能性的实现
从问题入手到通过实证研究凸显技术和城市“交集”中涌现出的多种可能,麦奎尔教授所著《地理媒介》一书就如何看待城市与媒介,如何看待数字媒介的暧昧性以及通过什么途径恢复市民与城市之间的多重可能性等议题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全书既分析阐明了城市传播在数字媒体时代的变化,更着力通过“地理媒介”的概念颠覆了经典传播理论的预设“再现”理论。这种颠覆体现了作者的尖锐的问题意识,对现有媒介研究理论脉络的深切把握和对技术复杂性的高度敏感。作为从城市新媒体入手反思传播理论和传播研究的新媒体专著,本书为传播学理论的范式创新指明了发展方向。
就整书架构看,《地理媒介》首先解析了从“媒介”到“地理媒介”的转变过程;分析了“地理媒介”的传播特点;以及这种转变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意义。然后作者开章明义,强调突出了市民对城市的权利;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变迁和智慧城市话语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解。在建构起全书理论分析的框架后,《地理媒介》具体分析了不同的实证案例。第二章“谷歌城市”通过谷歌街道考察城市数字平台的意义。作者将“谷歌街道”视为城市形象中介化的新形态,将其重要性与谷歌整体的商业策略联系起来加以观察。通过将智慧城市的广义逻辑与谷歌街道联系起来,作者提出数字存档新的操作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前人们如何利用社会实践和政治想象来重新定义城市本身。第三章“参与式公共空间”提出人们或可倒转那些利用大规模监视手段的媒体实践。章节开门见山地提出需对当下关于“公共参与”的话语修辞进行批判性分析。该章聚焦公共空间中的数字艺术实践,探索数字网络环境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公共交往形态。通过回顾艺术实践中“情境”观念的发展历史,并将其与当代艺术的“社会转型”关联,作者试图深入理解公共媒体艺术如何促进了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挪用”。第四章“城市屏幕和城市媒介事件”则集中考察了当下城市公共空间中借由公共大屏幕技术产生的社会交往。通过对公共空间中不同类型大屏幕的实证研究,作者提出“城市媒介事件”模型。结合第二代城市大屏幕在特定情境中的集体互动实践,作者指出类似实践有潜力创造出新的公民参与模式,并提供独特的跨国沟通经验。整书收尾“重构公共空间”一章致力于总结前文个案分析对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的理论意义。作者强调地理媒介和城市公共空间的纽带在当下已成为重新理解媒体技术的关键。通过基于地理媒介技术的城市公共交往,市民或能更好地认识在当面即时的社会关系中被技术中介化的多重时间性;更确实地接受城市高度的差异性和不断提速的流动性;并以不同方式掌握网络城市中与他者合作共处的社会技能。
从全书的架构看,未来的研究似乎应该在技术的多重可能性得到学理脉络和实证实验的双重支持之后,更进一步探究在特定的城市文化环境中,在彼此迥异的政治经济架构中如何将城市生活转变成艺术探索的实践领域。麦奎尔教授有次与本文作者聊天时曾无意提起本书研究过程中安排任何一次大屏幕实验,尤其是在异质文化中安排这样大规模的数字媒介艺术实验都是困难重重的妥协过程。接下来的问题是从理念上将日常生活艺术实验化同时,如何克服现实城市环境中的种种阻碍,以便将数字艺术的社会实验日常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构成了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我们是否能够认识到麦奎尔教授全书缘起的问题意识——更重要的是读者多大程度上能将《地理媒介》中对城市以及对媒介理论传统范式的深刻反思在日常媒介实践,城市规划和各类公共交往中加以践行决定了城市和市民在未来的集体命运。■
①LefebvreHenri. (1996). “The right to the city”in Kofman & E. Lebas(eds.)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②④McQuire, Scott.(2016). Geomedia: Networked City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③多琳·马西、约翰·艾伦:《城市世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⑤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⑥Crary, J. (2013). 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 of Sleep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⑦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⑧StieglerBernard(2011). The Decadence of Industrial Democracies. Vol.1: Disbelief and Discredittrans. D.Ross and S. Arnold, Cambridge: Polity.
⑨TownsendA. (2013). Smart Cities: Big data, civic hackers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Utopia, New York: Norton.
⑩LefebvreHenri. (1996). “The right to the city”in Kofman & E. Lebas(eds.)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pp. 129.
[11]Batty, M.Axhausen, K.W.GiannottiF.PozdnoukhovA.BazzaniA.WachowiczM.Ouzounis,G.& PortugaliY. (2012). “Smart cities of the future”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Special Topics, 214481-518.
[12]KoolhaasRem. (2014). ‘My thoughts on the smart city’Talk given at the High Level Group meeting on Smart Cities, Brussels, 24 Sept. 2014Transcript at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2010-2014/kroes/en/content/my-thoughts-on-smart-city-rem-koolhaas.
[13]SassenS. (2011). The global street: Making the politicalGlobalization8(5)573-9.
[14]StieglerBernard(2010). Telecracy against democracyCultural Politics, 6(2)171-80.
[15]雅各布斯、简:《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Randon House Trade Publishing(1961)
[16]Bourriaud, N. (2002). Relational Aesthetics, trans. S. PleasanceF.Woods with M. Copeland, Dijon: Les presses du reel.
潘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城市传播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批准号15AXW007;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网络舆论与食品安全网上报道”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S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