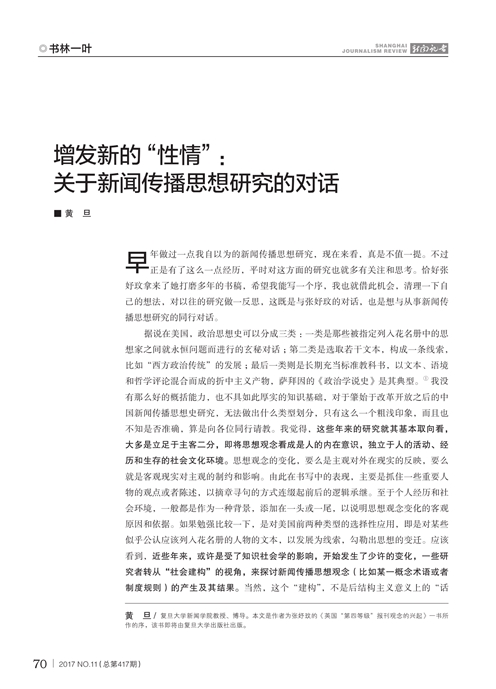增发新的“性情”:关于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对话
■黄旦
早年做过一点我自以为的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现在来看,真是不值一提。不过正是有了这么一点经历,平时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就多有关注和思考。恰好张妤玟拿来了她打磨多年的书稿,希望我能写一个序,我也就借此机会,清理一下自己的想法,对以往的研究做一反思,这既是与张妤玟的对话,也是想与从事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同行对话。
据说在美国,政治思想史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那些被指定列入花名册中的思想家之间就永恒问题而进行的玄秘对话;第二类是选取若干文本,构成一条线索,比如“西方政治传统”的发展;最后一类则是长期充当标准教科书,以文本、语境和哲学评论混合而成的折中主义产物,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是其典型。①我没有那么好的概括能力,也不具如此厚实的知识基础,对于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无法做出什么类型划分,只有这么一个粗浅印象,而且也不知是否准确,算是向各位同行请教。我觉得,这些年来的研究就其基本取向看,大多是立足于主客二分,即将思想观念看成是人的内在意识,独立于人的活动、经历和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思想观念的变化,要么是主观对外在现实的反映,要么就是客观现实对主观的制约和影响。由此在书写中的表现,主要是抓住一些重要人物的观点或者陈述,以摘章寻句的方式连缀起前后的逻辑承继。至于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一般都是作为一种背景,添加在一头或一尾,以说明思想观念变化的客观原因和依据。如果勉强比较一下,是对美国前两种类型的选择性应用,即是对某些似乎公认应该列入花名册的人物的文本,以发展为线索,勾勒出思想的变迁。应该看到,近些年来,或许是受了知识社会学的影响,开始发生了少许的变化,一些研究者转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探讨新闻传播思想观念(比如某一概念术语或者制度规则)的产生及其结果。当然,这个“建构”,不是后结构主义意义上的“话语实践”或“话语建构”,而是现代社会学范畴内行动者的行动及其意向。依照一位社会学者的通俗解释,这种研究的特点是“主张各种社会现象(结构、组织、制度、事件等)本质上都不过是人们意向行动(或符号互动)的产物而已,社会世界是一个‘意义世界’”,只有“理解和掌握建构这些现象的行动者在建构它们时赋予其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才能“确切地把握社会现象”。②简而言之,人们是积极主动地通过意义建构和分享,从而确认了自己所生存的现实实在,并确定和协调各自的行动。比如在关于中国报刊历史上的“职业主义”或者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研究方面,大致就是遵循这样的路子。我自己所写的那篇有关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影子,相信同行们对之是早有所感觉的。
这样的印象要是还基本成立的话,在张妤玟这本书中所呈现的,则与之都有相类,但又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她的问题意识很明确,若化约成一句话,即英国的“第四等级”——这一对全世界新闻业及其实践有重大影响的报刊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依我所见,这其中最有兴味也是激起张妤玟最大好奇的,就是它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并且是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这一类似“如何是可能”的提问方式,使得作者不是把注意力死死盯在概念本身,而是敞开了眼光,打量与之相关的各种要素,并且从报刊与政治关系的理论预设出发,从当时英国的政治哲学、宪政革新、大众政治和报刊实践的相互纠缠中来展示其复杂之面相。作者不是把思想观念和社会、政治等因素分开,依此分析各自的决定和被决定或者作用与反作用,而是力图将各种层面的因素糅合在一起,呈现出一个纵横交错、复杂多面的“第四等级”。按她自己的表述,采纳的是一种“历史深描”,“通过描述英国报刊在其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揭示过去和现在塑造与影响报刊的各种力量,以还其本来的、多样的历史面目”。这就使得思想观念的研究,与曼海姆式的“知识社会学”有了交通,和人类学路数有所合流,同时也具有了话语分析的味道,“从社会中的知识因素转向知识中的社会因素”。③这样的一种努力,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不可否认,这也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在这样的思路中,政治、社会、文化、报刊活动等等不再是各自离散,甚至也不再是作为一种点缀式的背景因素,而是造就“第四等级”观念所不可缺少的力量,这就必然要求作者除了熟悉报刊实践历史本身之外,还需要对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均有比较全面和透彻的了解与把握。张妤玟无疑是为此坐了很长时间的冷板凳,并且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的。别的不说,只要看一下书后所附的征引过的文献,对此就应该有深刻印象。也正是因此,她对自己的论题有过深思熟虑,书的视野、气象和格局都显得很大气,书中展开的面虽宽但主要脉络始终清晰,问题焦点突出又不使人觉得单一,涉及的人物、头绪多且纷繁,叙述起来却是丝毫不乱多有分寸。
以历史深描来做“第四等级”,一定程度上就与剑桥学派发生了关联。比如斯金纳就说过:“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我强调文本的语言行动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我研究概念变化不在于关注使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来表达这些概念的‘意义’,而是通过追问运用这些概念能做什么和考察它们相互关系以及更宽广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④一眼即可看出,这种说法与张妤玟在书中的声称以及全书的铺陈,是非常相像的。张妤玟是在英国亚伯大学念的历史学硕士,博士毕业后又在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系访学半年,主要就是修改博士论文,也就是现在要出版的这本书。若受到英伦风格的浸染而有所偏好,也不过是近朱者赤的又一佐证。无论其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应该都不令人意外。
之所以要提到张妤玟研究路数的来历,是因为她的这种写法,与我最近脑中所盘旋的如何重新认识新闻实践发生了碰撞。如前所述,以往的这方面研究,不管属于提到的哪一种,其思想和实践活动都是分离的,并都具有实在论的倾向。做新闻传播研究的,对“符号互动论”应该不陌生。“符号互动论”的一个独出心裁之处,就是认为“心灵”(心智)是在互动的社会过程中产生和存在,米德明确强调,“社会过程在时间上和逻辑上都先于从它之中产生的有自我意识的个体”。他还说,“心与身的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它存在于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共同体的一员而在行为中组织起来的自我与作为一个物理东西而存在的肉体有机体之间”。这无疑是说,心灵的问题是与身体相关,人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一互动社会过程中去的,所谓的“主我”和“客我”,正是这样发生关系的。⑤既然“心灵”存在于社会互动过程中,就不可能离开这一过程来讨论新闻传播思想,即便仍然还是以“实在论”为基点。新近在一本书里读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中的一个流行词,并形成了当代思想的“实践转向”。出于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的研究问题,研究者们对“实践”的理解及其研究是五彩缤纷难定一尊,不过据说在两个要点上有最低限度的共识:第一,他们都认可实践是“具身的、是以物质为中介的各种系列的人类活动”。第二,他们都坚持“一种独特的社会本体论:社会是围绕着共有的实践理解而被集中组织起来的一个具身化的、与物质交织在一起的实践领域”。⑥要是对之稍加概括,主要就是四个关键点:具身化,即实践与人的身体及其感知不可分离,“人类活动的形式是与人体的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指“机能和活动,而且包括身体体验、外表呈现,甚至还包括身体结构”;物质为中介或与物质交织,这就是说,实践不是习以为常的主体作用于客体,相反,是与各种物质构造,乃至于非人类实体互为构成;共有的理解,说明实践离不开解释和讨论,理解(思想观念)既不在实践之内也不在实践之外,就是实践的一部分。“具有技能的身体要求实践理论关注心灵和活动、个体或是和社会的共同交会点”;实践为本体,社会就存在于共同的实践并在实践中成其所是,并没有一个先在的定型了的结构。⑦由此倒想起布迪厄说过的一段话:“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又在行动者之内。……帕斯卡尔的那句格言:世界包容了我,但我能理解它,这恰恰只是因为它包容了我。”在行动者和社会世界之间,是“一种真正本体论意义上的契合”。⑧
这里不是具体讨论实践或新闻实践的合适场合,关于此,需要有专文来阐释。不过即就以上浮光掠影式的一瞥,亦足以起到警醒的作用,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习以为常的思想和行动两分,主观与客观两立。“具有技能的身体要求实践理论关注心灵和活动、个体或是和社会的共同交会点”,若真是如此,一直以来我们是如何理解新闻实践的呢?我们又该从何处发现思想,如何切入并处理所谓的新闻传播思想研究呢?当然,我没有九九归一,“自古华山一条路”的意思,学术从来不能也不可能是在一棵树上吊死,“横看成岭侧成峰”才有繁荣之象。问题的关键是,恰恰是目前绝大部分的中国报刊史或新闻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始终悬挂在一棵树上荡荡悠悠,始终要抽离出独自存在的纯思想和纯现实、纯意识和纯行动,从中做着反映与被反映,指导与被指导,制约与被制约的因果验证或推演,不能拓展出一个新的视野,而“实践理论”,就有可能在这方面为我们打开思路。
举一例子,凡是研究新记《大公报》者,“四不主义”都是无法绕开的话题。然而,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是把“四不主义”视之为该报的宗旨,并作为一种规则,贯彻其实践始终,并由此确立其办报范式。顺着这样的逻辑,文本上的“四不主义”就代表着“四不主义”本身,它的内容是透明的而且必定是人人皆明,研究唯一要做的,就是验证它在实践中的状况及其效果,最后的结论要么是做到了或者是没有做到,要么是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够好。倘若是从“心灵和活动、个体或是和社会的共同交会”的“实践理论”出发,或许就可以将“四不主义”理解为一种规范而不是规则。因为用规则(包括共有的信念或概念图式)来看待“实践”,是以语言和实践分开为基准,然后把实践解释为就是被表达在语言中的那种特殊信念或者概念图式,于是,语言或文字的含义,就指代了实践本身,从而与实际的作为有了比对的可能,两者以一种因果的关联互为作用:或者与之相符,或者与之不合。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将“四不主义”视为一种规则而是规范,那么,它就不是一个预存的作为解释对象的客观事实,而是一种共有实践理解的意向性观念,它存在于人们的讨论解释或从事某事的实践过程之中,⑨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新闻实践的构成部分。套用哈贝马斯的分类,这就是一种规范调节行为的“交往实践”。⑩这意味着,作为实践的“四不主义”,不仅是与各种不同因素发生关联,而且其是被如何理解如何体现,也必定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除此之外,不存在一个清晰而又固定不变的“四不主义”。因此,从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角度,关注的应该是“四不主义”在实践中的构成性、多样性、复杂性乃至暧昧性,这样,就会大大拓展研究的空间和问题,就会把新记《大公报》放到所有的社会和物质网络关系中进行考察,而不再只是举擎着纸面上那几条规定做“镜子”,比照来比照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照完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如果张妤玟不是把“第四等级”仅仅作为一个概念,从不同的情境中展示其多样来源和面目,而且还适当注意其“共有的实践理论”那一面,把“第四等级”概念化为一个在实践中被使用、把握、回应而且不断导入回归的“第四等级”意向,全书的各个部分,也就是其“多个面目”之间就会生发出凝为一体的活力,不同层面的实践有了一个贯通的渠道,最后的结论也会因此步出归纳而走向理论抽象。
与“历史深描”相关,张妤玟将“历史还原”确立为孜孜追求的目标,“将这一观念还原到其当初所形成时的语境与社会环境中去,探讨它产生的深层历史原由,并考察它的意涵随社会历史变迁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得以产生的原因。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本书希望能够为读者认识报刊、政治与社会间的关系提供多元的视角”。这一部分是全书最为精彩的,我也是饶有兴趣地从中了解到当年英国的状况,并受到多多的启发,由此猛然明白戈登·伍德为什么说,“怎么强调18世纪英国人对他们闻名于世的自由道德自豪程度都不为过”,而且这同样是美国——这个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对于宗主国所抱有的自豪感。[11]我相信,当然是带有武断性,张妤玟的这种想法仍然可以追溯到斯金纳所代表的剑桥学派。斯金纳自称在研究取向上是跨文本跨语境,他和他人所编辑的一套思想史研究著作丛书的冠名就是“语境中思想”。[12]斯金纳之所以如此重视“语境”,一方面是他接受了柯林武德的影响,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概念,相反,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人那里,同一个概念有着不同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是他对那种舍去语境仅仅以某一观念为单元结构的思想史研究现象的一种反拨,比如像洛夫乔伊那样,“观念史考察的就是各个单元观念出现、孕育、发展和组合进入各种思想系统的过程”。[13]“复原”着重的是特殊,就是格尓兹说的“地方性知识”之意。这有利于解说酝酿某一现象或者观念生成的“生态”,有助于知其所以然,避免望文生义,以生南橘北枳之误。翻看一下目前新闻传播研究,此种现象屡见不鲜,生拉硬扯,胡乱凑合,研究者还洋洋自得,连学术没有入流都不自知。因此,“复原”对于今天的新闻传播研究仍然是一个需要加强的基本功。然而,暂且不说是否真的存在一个确定不移可以“复原”的实景,即便在“复原”的脉络上,如此“复原”之后又如何呢?“地方性知识”莫非只能是一种“知识”?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注重语境是正确的,但不能将思想史家的任务化约为对语境的反映,思想史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研究,“思想史家所能够合理承担的任务远不止于斯金纳有时所表述的那样,仅仅只是去还原研究对象的观点和意图”。[14]我以为,这不仅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特殊”与“一般”的问题,更是与历史学者自身的定位和所理解的职责使命有关。历史研究,不能局限于知识性挖掘,不能只是为展示前人的荣光,也不是为了批判前人的失误乃至“原罪”,而是让人从中领悟到自己的生存和处境,以便反思和回答现实情境中的问题。由此,有两点必须慎重对待:第一,历史对于特殊性的重视,使得地方文化和经验的重要性成为关注的对象,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但研究问题的解决,不能仅停留在文化和地方的层面,否则就容易不知不觉走入相对主义。我之前说过,在新闻传播领域,有一个现象更值得警惕,不少研究者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情有独钟,似乎只要有了这样一个通俗的常识性表达,一切都在不言中。这只会导致孤立和隔绝,而不可能生长出新东西。从元地理学角度来看,这属于“环境决定论”一脉,即“不同人类群体间的社会和文化差异可以最终归因于他们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据地理学者之见,“环境决定论”是变相的微妙的且大多数人无力辨识的“种族主义”变体,因此也更为危险。[15]第二,历史是一种陈述,海德格尔说,“陈述是有所传达有所规定的展示”,它“是根据已经在领会中展开的东西和寻视所揭示的东西进行展示的”。[16]领会中展开和寻视所揭示,显然不只是熟读材料摆弄材料复原材料,而是从中领会到了会心的东西,寻视到刺激内心的亮光。这一切,是研究者自身阅历、对社会现象的体察与理论问题混合交杂辨析搏斗的豁然所悟。所以余英时先生说,“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17]一个研究,如果连自己都没有“领会”,提不出一个有分量的问题,又怎么可能打动别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海德格尔这个存在主义的表达无碍于我们在历史学中的运用,那么,治史者由外而内,审视一下自己的“心智品质”,从而厘清自己在事与叙之间的位置,生发出米尔斯式的“想象力”,而不是整天把心思和精力主要花在用什么招数上,刻意回避研究什么、解决什么的难题,而转换为如何研究,似乎路径方法自身就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我感觉得出来,张妤玟对自己的论题不仅有自己的理解和体验,而且还蕴含着内心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人们的思考和想象。如果说美中不足,在于视野尚不够宽广,比如“第四等级”与英国的政治文化以及宪政政治实践有关,这固然不假,但要是能进一步打开,放眼全球关系,尤其是从报刊实践和理念的层面对之先有一个基本定位,处在一个何样的关键点,这个研究的价值会更加得以突出。记得威廉·詹姆斯说过,实用主义作为一个方法,让哲学的“性情”有了巨大的变化。[18]中国的报刊史和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急迫需要研究者们对学术有新的理解,以不同的方式改变旧“性情”,增发新“性情”。只要不懈坚持,必定就有效果。为此,我对张妤玟们寄予厚望。
吃了多年的学术饭,我越来越感到,学术研究不但是存在于对话之中,而且一定是在对话中潜行,学术就是借助对话的自我修炼和感悟。治学者是通过与书籍、研究对象和同道的对话,才能使自己避免拘泥一端,得以不断丰富乃至丰满。学术思考同时也是研究者与人类生存现实境况的对话,不断回味和领悟人生,“世事洞明皆学问”,藉此感受学术研究的严肃以及学术追求永无止境的乐趣。对话是学术的生命,也是一个学者不断进取的动力。一个真正的学者总是与自己的研究共同进化。麦克卢汉说得好,洞见是与各种形态生命的一次接触,而这,一定借助于对话式的相互作用才是可能的。[19]谢谢张妤玟的书,给了我这些诸多的刺激,为我提供了一个与同行畅所欲言的机会。作为一个序已经够长了,就到此为止,但对话不会因此而终止,我相信。■
①彭刚:《历史地理解思想——对斯金纳有关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的考察》,载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第125-159页,引见129页,广州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谢立中:《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第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上卷)第2页,陈志宏、王琬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④转引自李宏图:《笔为利剑: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载昆廷·斯金纳、博·斯特拉思主编:《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中文版序言第4、5页,彭利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166页以及166页注①,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⑥⑦西奥多·夏兹金:《导论》,西奥多·夏兹金、卡琳·诺尔·塞蒂纳、埃克·冯·萨维尼:《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第3-4页,柯文、石诚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⑧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72页,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⑨参见约瑟夫·劳斯:《实践的两种概念》,载西奥多·夏兹金、卡琳·诺尔·塞蒂纳、埃克·冯·萨维尼主编:《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第216-227页,柯文、石诚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⑩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第10-17页,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第28页,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2][13][14]彭刚:《历史地理解思想——对斯金纳有关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的考察》,载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第144页、第128页、第156、141页,广州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马丁·W.刘易士、卡伦·E.魏根:《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第24-25页,杨瑾、林航、周云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91页,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三联书店1987年版
[17]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载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第78-94页,引见第9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8]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载约翰·杜威等著,田永胜、谢志斌、李绍猛、曹荣湘、周春水、欧阳梦云、陈亚军、游冠辉、杨玉成、崔人元主编:《实用主义》第45-180页,引见第6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19]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序言》,载哈罗德·英尼斯:《传播的偏向》第2页,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黄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本文是作者为张妤玟的《英国“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兴起》一书所作的序,该书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