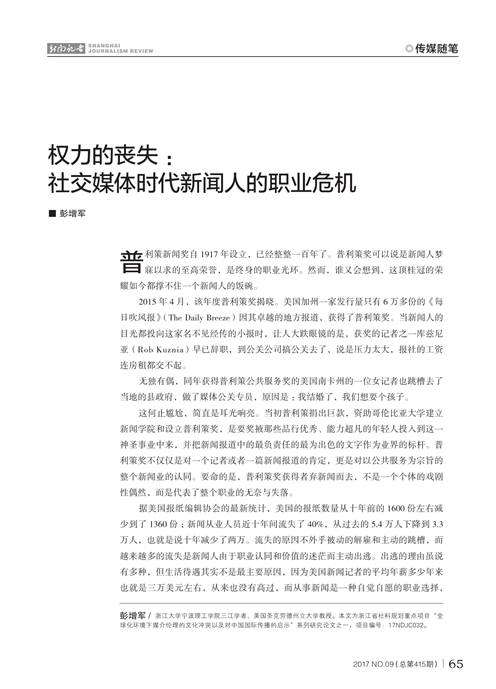权力的丧失: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人的职业危机
■彭增军
普利策新闻奖自1917年设立,已经整整一百年了。普利策奖可以说是新闻人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是终身的职业光环。然而,谁又会想到,这顶桂冠的荣耀如今都撑不住一个新闻人的饭碗。
2015年4月,该年度普利策奖揭晓。美国加州一家发行量只有6万多份的《每日吹风报》(The Daily Breeze)因其卓越的地方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当新闻人的目光都投向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报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获奖的记者之一库兹尼亚(Rob Kuznia)早已辞职,到公关公司搞公关去了,说是压力太大,报社的工资连房租都交不起。
无独有偶,同年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的美国南卡州的一位女记者也跳槽去了当地的县政府,做了媒体公关专员,原因是:我结婚了,我们想要个孩子。
这何止尴尬,简直是耳光响亮。当初普利策捐出巨款,资助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新闻学院和设立普利策奖,是要奖掖那些品行优秀、能力超凡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一神圣事业中来,并把新闻报道中的最负责任的最为出色的文字作为业界的标杆。普利策奖不仅仅是对一个记者或者一篇新闻报道的肯定,更是对以公共服务为宗旨的整个新闻业的认同。要命的是,普利策奖获得者弃新闻而去,不是一个个体的戏剧性偶然,而是代表了整个职业的无奈与失落。
据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最新统计,美国的报纸数量从十年前的1600份左右减少到了1360份;新闻从业人员近十年间流失了40%,从过去的5.4万人下降到3.3万人,也就是说十年减少了两万。流失的原因不外乎被动的解雇和主动的跳槽,而越来越多的流失是新闻人由于职业认同和价值的迷茫而主动出逃。出逃的理由虽说有多种,但生活待遇其实不是最主要原因,因为美国新闻记者的平均年薪多少年来也就是三万美元左右,从来也没有高过,而从事新闻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职业选择,大多数人选择新闻作为职业首先不是因为钱。新闻人摈弃新闻业的根本原因是职业认同、成就感等全方位的困惑与失落。根据近年的调查,在美国200个职业排名中,报社记者连续三年倒数第一。电视记者相对“风光”一些,倒数第二。新闻人的职业排名还不如管道工。
有关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对新闻业的冲击,学界业界已经讨论太多。讨论的重点多在规范理论层面的新闻专业主义,应用层面上的媒体融合、媒体转型、盈利模式等,对新闻职业的讨论也基本在业务层面,比如全媒体报道、大数据新闻等。笔者曾在《新闻记者》(2016年第10期)的一篇文章中叩问“记者何为?”重点探讨的也是记者在新媒体时代的角色。其实,更紧迫、更严重的问题不是记者何为,而是记者何用。在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业作为一个行业(industry)是否已经过时?与此相连,目前的新闻的业余化或者说非职业化趋向,是否意味着新闻作为一个职业的消失?当人人都可以是新闻人的时候,那以新闻为职业的新闻人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或许比新闻机构和行业的成败更为关键。人们总是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我们不妨反问一句:如果没有新闻人这些毛,要媒体商业公司这些皮囊——无论如何膘肥体壮,又有何用?
没有新闻人的新闻业?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点来看,大众媒体是工业化的产物,具备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即通过资本占有生产资料,控制和垄断生产和市场,成为产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由工业化过渡到后工业化时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媒体生态的改变,产业重新定位,进而引发职业界限的消解和社会关系的重构。
后工业化新闻生产这一观点首先是由美国学者希尔斯(Doc Searls)在2001年提出的,指的是新闻不再必须围绕生产工具、生产资料来组织生产,职业和职场可以分离,而工业化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工作必须在工厂,办公必须在办公室。后工业化新闻生产的另外一大特征是生产成本和传播成本大幅减少,大众新闻可以是大众平台的小众生产,也就是美国著名新媒体学者詹金斯教授(Jenkins)强调的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或者是社会学家卡斯特(Castells)所说的自我大众传播时代(self-mass communication)。
所谓产业,所谓职业,定义可以有许多,关键词不外乎界限和垄断、领地和门槛。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这个产业的界限和领地已经被全方位突破。社交媒体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几乎是颠覆性的。根据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如今60%的人是从脸书和其他社交平台来获取新闻的,而脸书等社交平台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媒体组织,更不是一个新闻机构。当新闻业被新媒体公司如谷歌、脸书、推特等占领和控制后,还存在一个所谓的新闻业吗?至少可以这样说:传统新闻业已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新闻产业正在重构,而新闻职业也在重新定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闻人对职业价值和意义产生了怀疑和困惑,身份认同以及自我认同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形势不可谓不严峻,虽然有理由认为最严酷的考验还没有到来。新闻不仅失去了受众,失去了信任,失去了市场,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自我认同,失去了方向。
在某种程度上,新闻人遭遇了公众和媒体机构的双重背叛。
首先是公众的不信任和冷漠。在水门事件后的1972年,高达72%的美国人对于新闻界有信心,到了1991年,降到了55%。而现如今,只有不到32%的对媒体有信心。而在中青年人群中,只有可怜的26%。
新闻人对公众也丧失了信心:人民群众是不可靠的。BuzzFeeds新闻网在一项调查中发现:李鬼打败了李逵——彻头彻尾的假新闻在脸书中的关注度超过了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头条新闻。尤为令人失望的是:2016年美国大选的最后三个月的关键时段,虚假新闻传播热度更是超过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这些假新闻往往骇人听闻,假得不能再假,然而,无论主流媒体如何揭露、证伪,人们还是照信照传不误。人们一方面不相信主流媒体,另一方面却相信虚假新闻,实在是分裂得无人能懂。
还有什么比你所服务的公众的冷漠更令人沮丧的事情吗?笔者认识一位美国地方报纸的总编辑,从实习生开始做起,工作了四十多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去年年底退休的时候,包了一家餐厅办告别会。消息发了,请柬也送了,原以为至少要来200来人,还发愁地方小不小,饭菜够不够,结果只来了不到50位,丰盛的自助餐剩下大半。普利策评论奖获得者、《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卡尔(David Carl)曾感慨道:公众总是不停抱怨新闻界不接地气,可谁又关心自己家乡的报纸的裁员,甚至注意到了报纸版面的减少?
如果说公众的不信任和冷漠还可以忍受的话,那自己所服务的媒体组织的背叛则是更大的打击。行业不景气是从二十多年前开始的,其间一线的编辑和记者就一直被压缩和裁减。各大媒体集团在行业整合的过程中,为了在华尔街的业绩好看,纷纷“抛弃”新闻业务,单是在2014年8月份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里,美国三大主要新闻集团,甘乃特(Gannet),论坛(Tribune)和斯科瑞普斯(E.W. Scripps),不约而同地将报纸业务剥离。一些新闻媒体开始用对待市场销售人员那样根据点击率来付记者编辑薪酬。新入职的记者试用期满,不是根据业务水平来而是浏览量来决定去留。
在这样的生态中,新闻人的生存空间被一步步挤压,权力也在一步步消解。
权力的丧失
笼统地讲,当前新闻业有两大危机:一个是经济危机,关乎新闻业作为一个行业的生存与发展;另一个是职业危机,即新闻作为一个职业的社会认同,一句话,新闻人的专业性和社会价值体现在哪里?
新闻业的经济危机不同于一般所说的经济危机,危机的原因不是供需矛盾,而是供需关系的转换,说白了就是产业地位受到挑战,旧的商业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局。
相对来说,对于公众和社会来讲,新闻的职业危机也许更为紧要,因为从根本上讲,我们关心媒体机构的生死,不是在乎它的生意好坏,而是因为它提供了公共服务的平台和资源,着眼点在人而不是机构。
职业意味着社会认同你的某种专业知识和技能且愿意为这种服务埋单。从某种程度上讲,职业说白了是一种界限,是一种控制权,这种权力来源于公众的信任。密苏里新闻学院首任院长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在为世界新闻记者协会所撰写的《记者守则》中直截了当地宣称: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本是公众信任。这种公众信任带来的不仅仅是权利(rights)更是一种权力(power)。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逊(Terence Johnson)在一本《职业与权力》(Professions and Power)的著作中详细分析了职业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某个行业的职业化过程就是一种权力关系的构建过程,社会产品的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通过职业化来界定同消费者的社会界限和距离,而这种权力关系,界限和距离的产生和维持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和条件。
因此,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革命,核心是对权力关系的破坏和重构。卡斯特认为,技术进步本质上“是权力关系的形成过程”。
那么,新闻职业权力的丧失,或者说得委婉一点,权力的消解都有哪些呢?
首先,从整体来讲,新闻的公共性让位于商业性,导致新闻人主导权的丧失。这个有种种具体的表现,比如新闻编辑部的公司化管理,从记者与编辑主导变为商业经理主导。记者和编辑不但要对新闻的生产负责还要为销售负责,新闻人直接成为生产线上的盈利单位,新闻人服务的不是公众而是老板。
第二,新闻人编辑权的丧失。编辑权是新闻人的核心权力,而现在,我的稿子我做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首先,编辑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专制”走向“分享”。把关人的权力让渡给了受众,每天看流量看受众的反应,哗众取宠成为手段甚至目标,雅俗共赏的结果是俗的胜利。
与此同时,记者的编辑权逐步让渡于技术与算法。大数据和算法的制定和控制者是技术人员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人,这也是新闻人失落的一个大的方面。当然还有炒得很热的机器人写稿。一个编辑完全控制不了人们读什么,指导阅读的决定力量往往是朋友圈。编辑权的丧失意味着新闻人对自己的职业和专业不能负责,却又常常得为这个行业的错误担责。
第三,职业地位的丧失。先不讲什么无冕之王,以及政治、社会地位,就是在新闻组织内部,新闻人的主体地位也在不断被消解。比如美国最大的报业集团甘乃特集团经过数次的整合,许多报社编辑部不再设总编辑一职,由代表公司利益的发行人独霸天下,销售、广告和经营部门同编辑部平起平坐。这对于新闻和经营水火不容的职业理念来说,简直是大逆不道,甚至是耻辱。
第四,新闻人丧失了职业上升通道。媒体整合的结果,是横向的技术化,而不是纵向的专业化。新闻人被要求无节制地横向拓展,而纵向则很难有上升的空间。传统上,新闻人根据资历可以升迁到管理层,而现今的公司化管理架构很难有新闻人的上升空间。以往的新闻人经过专业积累,最终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而现在所谓的全媒体记者疲于奔命,做跨平台、全媒体报道,很难有专业的积累。
这些权力和权利的丧失,极大影响到新闻人的职业身份认同。职业身份认同听起来似乎是个形而上的问题,其实体现在日常琐碎的业务操作中。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同样适用于新闻生产,有什么样的新闻编辑部,有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就必定会有什么样的记者和编辑。传播学家凯瑞(James Carey)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闻人生存在一个操作的世界里,这些行为规范不仅仅创造产品和服务,同时也创造了记者本身,记者在行为中成型和定性。简单一句话,干什么决定是什么。
职业认同与职业操作的错位
新闻人是个理想和价值观支撑的职业,然而,现在的新闻人的职业认同与职业操作错位严重。价值观和职业伦理告诉自己什么是应该做的,而实际工作中却不得不去做自己不认同的事情。
美国《纽约》(New York)杂志最近发布的有关新闻人职业认同的调查发现,新闻人的职业认同与职业操作的错位非常普遍。
首先,受访者普遍认为新闻业最大的问题是商业模式的溃败。而第二大问题,则是由于商业模式的崩溃,而一味去迎合受众。超过75%的受访者说时刻感到市场的压力,45%的人说自己不得不通过哗众取宠来迎合受众。从无冕之王、把关人堕落成自己所不屑的取悦者(entertainer),极大地伤害了职业自尊。
让人感叹的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新闻人的价值理念没有动摇。75%的受访者坚定认为新闻必须坚持客观性,超过86%的受访者表示应该告诉读者他们应该或者需要知道的,不管他们有没有兴趣。但是,可悲的是,他们同时认为,目前已经没有平台和机会去实践这些理念。
当问到职业的困惑和压力都来自哪里时,41%的受访者说是老板,紧随其后有37%对自我非常不满,只有不到18%认为压力来自受众。绝大多数记者认为每天做的工作已经远离新闻专业主义,认为自己的工作丧失了职业尊严和意义。一位受访者说道:“每天早上编前会上,通常先汇报一通前一天的数据,其次才谈新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数字比新闻重要。”
如此种种职业权力的消解,职业认同的丧失,对于一个以公共服务为宗旨,以独立、客观等理念为灵魂的职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对民主社会的政治健康极为有害。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写道:“一个有力的、无私的,训练有素,明辨善恶,并且勇以行之的新闻界,才能保持新闻业的公共品质。失去这个公共品质,所谓民治不过是个骗局和笑话。一个玩世不恭的或者唯唯诺诺的新闻界必然会造就同它一样卑劣的民众”。
当然,职业的迷茫和危机,带来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恐怕还有待于整个社会的变革,因为这不仅仅是新闻的问题。以往我们在关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比较多地关注了机构兴衰,而忽视了在这场大变革中新闻人的命运。没有优秀的职业新闻人,恐怕很难有高质量的专业主义的新闻。而新闻人的认同危机、职业危机,关乎新闻的未来,更关乎社会的未来。正因为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参与到新闻的生产和传播中来,才更应该强调新闻的专业性和职业性。新闻人需要解决的,是如何重新认识和确立自己的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找回职业存在的价值和权力。■
彭增军/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全球化环境下媒介伦理的文化冲突以及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启示”系列研究论文之一,项目编号:17NDJC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