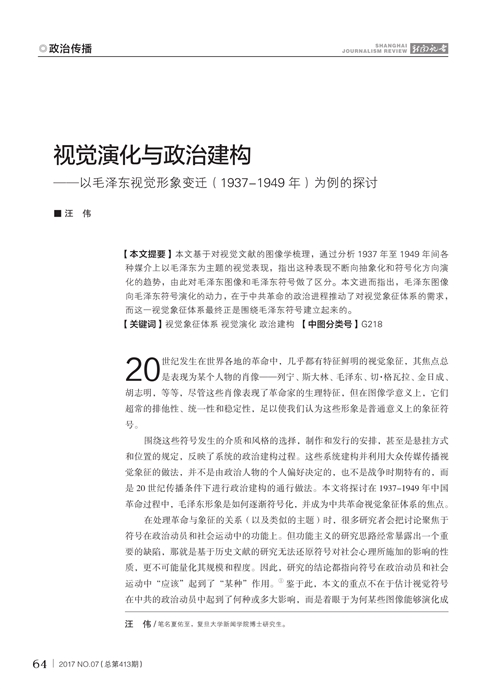视觉演化与政治建构
——以毛泽东视觉形象变迁(1937-1949年)为例的探讨
■ 汪伟
【本文提要】本文基于对视觉文献的图像学梳理,通过分析1937年至1949年间各种媒介上以毛泽东为主题的视觉表现,指出这种表现不断向抽象化和符号化方向演化的趋势,由此对毛泽东图像和毛泽东符号做了区分。本文进而指出,毛泽东图像向毛泽东符号演化的动力,在于中共革命的政治进程推动了对视觉象征体系的需求,而这一视觉象征体系最终正是围绕毛泽东符号建立起来的。
【关键词】视觉象征体系 视觉演化 政治建构 【中图分类号】G218
20世纪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革命中,几乎都有特征鲜明的视觉象征,其焦点总是表现为某个人物的肖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切·格瓦拉、金日成、胡志明,等等,尽管这些肖像表现了革命家的生理特征,但在图像学意义上,它们超常的排他性、统一性和稳定性,足以使我们认为这些形象是普通意义上的象征符号。
围绕这些符号发生的介质和风格的选择,制作和发行的安排,甚至是悬挂方式和位置的规定,反映了系统的政治建构过程。这些系统建构并利用大众传媒传播视觉象征的做法,并不是由政治人物的个人偏好决定的,也不是战争时期特有的,而是20世纪传播条件下进行政治建构的通行做法。本文将探讨在1937-1949年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形象是如何逐渐符号化,并成为中共革命视觉象征体系的焦点。
在处理革命与象征的关系(以及类似的主题)时,很多研究者会把讨论聚焦于符号在政治动员和社会运动中的功能上。但功能主义的研究思路经常暴露出一个重要的缺陷,那就是基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无法还原符号对社会心理所施加的影响的性质,更不可能量化其规模和程度。因此,研究的结论都指向符号在政治动员和社会运动中“应该”起到了“某种”作用。①鉴于此,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估计视觉符号在中共的政治动员中起到了何种或多大影响,而是着眼于为何某些图像能够演化成抽象的象征符号,而其他图像未能发生这种演化,这些由具象演化而来的象征符号在不同情境中发挥的功能,以及它们何以最终占据了视觉象征体系的焦点位置。
合作与操控:“正式”风格的建构
在毛泽东形象传播的历史上,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访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是一个分水岭。斯诺是最早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通过斯诺的相机和笔,毛泽东的名字和形象第一次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毛的经历和对中国革命的观点才为外界所知。尽管毛泽东后来多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但再没有哪次采访的详细和坦率程度,能够与1936年斯诺对他的采访相比。这次采访后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②一书,在西方和中国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斯诺在采访和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权力秩序中还没有达到后来的高度,这本书对斯诺和毛泽东,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③
在1936年的采访中,斯诺为毛泽东拍了好几张照片,一张戴八角军帽的毛泽东半身肖像(图1 图1见本期第65页)流传最广,后来还被用于《东方红》布景,更加广为人知。
通过和图2做比较,能够更清晰地说明图1的风格。在Red Star Over China首版中,图2是书中第一张插图。从照片上的阴影长度看,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可能是在中午。刺眼的阳光直射在毛泽东的脸上,他不舒服地皱起了眉头。和图1一样,这张照片上的毛泽东形象消瘦,不同的是他没有戴军帽,而是露出潦草的分头。从着装和背景看,可以判定图1和图2是同时拍摄的。
对斯诺那个时代的新闻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来说,照片既是采访的物证,也是一种有力的媒介,它能够补充和扩展文字的表现力,令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④但和人们一般的认识不同,作为一种物证,照片其实称不上客观,拍摄者的个人偏好、被拍摄者对相机的熟悉程度和他们对自我形象的期待、编辑部的口味、市场兴趣、印刷技术乃至新闻审查机制,都会投射到拍摄过程中,影响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对拍摄时机的判断和对拍摄手法的选择,最终也会影响照片的视觉效果。
既然拍照同时受到各种动机的驱动,而对拍摄时机和手法的安排、对照片的挑选和修改如此容易,照相术可以很便利地被用于操控受众对现实的感知。裴宜理提出“文化操控”这一概念,是指人们通过改写、扭曲或重塑象征符号的历史含义来谋利。⑤正如裴宜理和其他人通过很多实例证明的那样,删改政治人物的照片,往往都是出于明确的政治目的。⑥
和修改已经完成拍摄的底片不同,拍摄过程中的操控更复杂。根据斯诺夫人的回忆,图1中毛泽东头上的帽子并不是毛泽东自己的,而是斯诺摘下自己的帽子,将它戴到毛泽东头上,目的是拍摄一张“很神气的、‘半官方的’像”,因为拍照时毛泽东“穿着随便,又光着头,看起来太不正式”。⑦
大量照片上毛泽东都戴着帽子,包括斯诺为他戴上的那种八角形红军帽。这些照片并没有像图1那样广泛流行。所以,关键并不在于帽子,而在于斯诺和毛泽东为拍摄这张照片进行的合作,以及他们的合作对照片风格和用途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体现在图1和(图2 图2见本期第65页)的差异上。图2略带仰视视角,由于来自头顶强烈的光线,毛泽东非常不舒服地皱着眉头。刺眼的光线不仅会改变表情,也会让人身体紧张,因为被拍摄者需要忍耐不适,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某个姿态不变。这让毛泽东的脖子和下垂的双臂尤其显得僵硬,进而暗示出他整个身体的绷紧状态。这个问题在图1里同样存在。但随着拍摄角度改变,被拍摄者的身体不适和精神紧张对画面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减轻。同样,图2上披散的头发、轮廓被破坏的右耳、无意识张开的嘴巴和敞开的衣领——这些快照中很容易出现的细节,在图1中都不存在。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图1中的形象较之图2显然更为矜持和庄重,更像是一幅“正式”的肖像。
“正式”一词可以有多个含义。它意味着制作这类肖像是为了严肃的用途,并符合公认的风格,换言之,正式照片意味着动机、自我认知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斯诺想为毛泽东拍摄一张“正式”甚至“官方”风格的照片,以展示一个年轻的红军领导人冷静而有魄力的形象,而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斯诺到访,为此做了精心准备,⑧负责接待斯诺的毛泽东也配合斯诺的各种要求,数次与他长谈,罕见地向斯诺讲述了个人经历。毛泽东有充分的理由接受斯诺的建议,拍摄符合需要的照片。拍照时毛泽东并没有戴帽子,于是斯诺取下自己头上的帽子,将它戴在毛泽东头上。斯诺这样做唯一的原因是这顶帽子和它上面的红星,能够清楚地显示毛泽东的身份。这会让他的照片有更明确的指向。
当斯诺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戴到毛泽东头上,并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拍摄就变成了一种表演。毛泽东的表情很不自然,使图1充满了紧张情绪和戏剧感。这种紧张情绪和戏剧感有效地克制了毛泽东给斯诺的真实印象:散漫、随便、不拘小节,眼神涣散,肩膀总是塌下来,和周恩来等人形成鲜明的对照。⑨
斯诺从陕北回到北平,为他长期供稿的英文媒体提供西北之行的独家报道。这些报道最终结集为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并于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碍于图1的版权已经高价售给亨利·卢斯的《生活》(Life)杂志,不能用作英文版书籍插图,他转而将其提供给了中文译者。斯诺的朋友和学生曾将他的部分报道翻译并编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出版。图1是书中第一幅插图,⑩位于“译者序言”之后,全书正文之前。像一份标准档案那样,照片下还附有斯诺写的图片说明。此书出版在Red Star Over China之前,虽然没有Red Star Over China的经典译本《西行漫记》那样的影响力,却是毛泽东得到的第一本斯诺著作。[11]1938年2月《西行漫记》出版时,同样选择了图1作为毛泽东的肖像插图。
斯诺的报道和照片提供了一幅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更系统、焦点更明晰的图景,也即早在1936年,毛泽东已经是中共和红军无可争议的领袖和象征。图1这张照片显然位于这一图景的中心。斯诺著作的中文译本对毛泽东照片的挑选和编辑,更加强化了这种印象。
在某种程度上,传播效果是传播意图的实现。图1和其他毛泽东照片的区别,表现在它具有一种稀缺的正式风格。一幅正式风格的肖像,意味着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对观看者的反应有明确的期待,并为消除可能的歧义而共同努力。皮埃尔·布尔迪厄指出,“肖像照实现了自我形象的客观化”,为此人们不惜采取“近乎立正姿态的不自然的僵硬姿势”,“即使这意味着要以牺牲‘自然性’为代价”。[12]布尔迪厄没有指出的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合作才是这种风格形成的关键。
复制与传播:从毛泽东图像到毛泽东符号
在政治视觉象征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首要问题是传播谁的形象,其次才是传播什么样的形象。肖像照片首先是个人特征信息的载体,其次才是一种独特的视觉形式。作为政治人物个人特征的载体,一张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密切合作,并且因其“正式”的风格而在被拍摄者的自我期待与社会期待间取得均衡的肖像照片,可能会得到更多传播机会。但是,这种社会审美的偏好能否在传播过程中得到实现,则主要取决于风格以外的政治和经济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政治进程对象征体系的需求程度、构建方式和对视觉焦点的选择,以及社会环境是否具备传播图像所必需的技术、设备和材料,是否有活跃的出版活动。
对象征体系的构建,包含着对视觉元素的选择,给定符号特定的政治意涵,依据某个标准对不同元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其目的是形成一个由多个符号构成同时有明确焦点的完整的意义网络。视觉焦点的选择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必要的时候可以以一个单一符号指称整个中共革命的观念和实践。一旦选定视觉焦点,整个象征体系的构建,必然围绕这个单一符号来进行,复制和传播资源都将向这一符号倾斜。选择焦点意味着政治秩序对象征体系的确认。正如政治秩序的构建一样,对视觉焦点的确认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和逐渐的确认。
中共各根据地都极重视宣传工作,但说到视觉传播的意识、能力和实际影响,绝无其他出版物能与晋察冀根据地比肩。因为靠近中国物资集散的铁路命脉津浦线,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有“解放区”最完备的照相制版技术和设备,因此得以从1942年开始出版《晋察冀画报》。这本画报由于大量发表摄影作品,在解放区堪称绝无仅有。1945年后,晋察冀画报社还出版过多种画册、摄影丛书和8开单页的《晋察冀画刊》。这些刊物的总发行量达到了几十万份。晋察冀画报社还为其他根据地培养摄影、制版和印刷人才。到国共内战期间,其他中共根据地出版的以刊登照片为主的画报,也大多受到《晋察冀画报》的影响。
《晋察冀画报》刊载过很多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袖人物的照片和美术作品。但在杂志创刊之初,并没有赋予毛泽东形象额外突出的位置。特别是在其“创刊特大号”(1942年7月)中,尽管封二位置是一幅题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画作,但在这期杂志中占据绝对视觉焦点的却是无处不在的聂荣臻形象:聂荣臻的题词、照片、画像出现了数十次之多,其中一张聂荣臻戎装肖像照占据整整一页位置,一篇长达13页的文章报道聂荣臻的生平(题为《晋察冀根据地舵师聂荣臻——模范敌后根据地及其创造者的生平》,作者署名“萧斯”,为邓拓笔名),杂志还刊出一个完整的图片故事《将军与孤女》。
杂志创刊号在篇幅分配、视觉设计和报道语言上对聂荣臻的功绩所做的强调,使他的地位不但凌驾于晋察冀根据地其他军政领导人之上,也让杂志封二对毛泽东形象的展示和歌颂黯然失色。
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根据地以外,晋察冀根据地是中共在日军后方创建的最大一块敌后根据地。聂荣臻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经营居功厥伟,但以如此密集和高强度的视觉形式赞颂聂荣臻,并将他置于其他军政干部之上,仍显得异乎寻常。[13]这期杂志在晋察冀根据地和延安激起了什么样的反响,现在无从得知。但意味深长的是,在此后出版的《晋察冀画报》中,聂荣臻形象急剧减少。第二期杂志还刊出了两幅聂荣臻照片,但从第三期开始,这位晋察冀根据地创始人的形象就很少再出现在杂志上,更不要说占据重要的位置了。
而对毛泽东形象的处理,第四期杂志(1943年9月)是一个转折点。占据内文第1页位置的是毛泽东肖像照片,下署“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第2页为毛泽东简历,接下来是朱德肖像和简历,同样占据两页篇幅,第5页和第6页为跨页,刊出9位八路军将领照片,依次是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和聂荣臻的副手萧克。这9位八路军将领照片的跨页版面安排规定了读者的视角。随着杂志展开,排列整齐的肖像占据了整整两页纸,形成了沉闷和封闭的视觉印象。肖像大小、先后顺序和与照片同时刊出的文字说明,传达了一种秩序感。这种视觉秩序与当时中共党内的政治秩序是严格对应的,与创刊号对聂荣臻形象的突出处理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随着整风运动展开,延安正兴起将毛泽东置于其他中共领导人之上进行歌颂的风气,其方式与《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对聂荣臻所做的宣传非常相似。在这种气氛下,《晋察冀画报》从第五期(1944年3月)开始,固定在杂志扉页刊登毛泽东照片(只有第七期例外)。尤其是该刊第九、十期合刊(1945年12月),处理毛泽东形象的手法,让人想起1942年的创刊号中对聂荣臻形象的处理:杂志不但在首页刊出毛泽东的肖像照片,还在第47页刊出雕塑家王朝闻所塑毛泽东头像照片,第48页刊出带插图的报道《毛主席与劳动英雄的会见》(作者莫璞),插图为铅笔画,约占半页篇幅。这种高密度和多样式的图像组合,让毛泽东成为整本杂志的视觉焦点。
抗日战争后期和内战初期,困扰中共宣传出版机构的物资供应和制版、印刷条件有所改善,各地创办了大量画报,如《冀辽热画报》《东北画报》《华北画报》《中原画报》《天津画报》《人民画报》《华东画报》等。在画报显著位置刊登毛泽东肖像,已经成为惯例。尽管朱德和其他高级军政领导人的照片也非常常见,但这些画报的视觉语言已经将毛泽东置于无可争议的中心位置。
出版《毛泽东文集》的做法,在“延安整风”后蔚然成风,而引领风潮的仍然是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根据地。1944年7月,晋察冀日报社编选的5卷本《毛泽东选集》出版,1947年又以晋察冀中央局的名义,增补出版了6卷本和续编。印制《毛泽东选集》调用了最好的技术人员、设备和纸张,装帧方面也体现了编选者的良苦用心,扉页均有毛泽东肖像。各根据地群起仿效。到1948年底前,各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至少有21种。
内战后期,特别是1948年之后,中共控制下的城市越来越多,物资和技术限制进一步缓解,图像出版越发兴盛。包含有毛泽东形象——特别是肖像照片和肖像画——的出版物数量持续增多,而与这个数量增加的趋势相反,毛泽东形象在传播中趋于统一。少数具有正式风格的毛泽东肖像照片被反复复制,相对其他毛泽东形象获得了明显的传播优势。
晋察冀画报社1945年在张家口印制的《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近影集》,是已知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的毛泽东个人影集,共发行5000册。画册收集13张照片,主要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生活照和各种迎来送往场合的合影,但其良苦用心却主要表现在画册中依次出现的三张肖像上(图3、图4 图3、图4见本期第69页)。这些肖像照片都曾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得到了广泛复制和传播。
在这个复制品数量增加和原型减少的过程中,毛泽东形象逐渐变得稳定而清晰,表现出明显的统一性和排他性。将毛泽东形象标准化的努力与当时的政治进程有关:到延安整风后期,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获得了空前崇高的地位,他的形象也逐渐变成革命的象征符号。以图3和图4为例,无论是年轻的工作人员捧着自己亲手放大的毛泽东肖像,[14]或在展示自制照相设备时以效果良好的领袖照片为证,[15]这些“关于照片的照片”都说明,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形象已经具有革命符号和神圣物品的性质,而它们正好具备正式乃至标准的风格,自然绝非偶然。
照片的风格越“正式”,被摹写的机会越多,因为它们不但符合人们对领袖人物形象的期待,也是构建一种完整和高度集中的视觉象征体系的内在要求使然。在延安时代,摄影师就知道,很少有人能让毛泽东坐下来,在精心布置的光线条件下,拍摄一张肖像——即使这张肖像将被用于“正式”乃至“官方”用途。[16]这使得复制品进一步向少数照片上的毛泽东形象集中。
作为中共革命的象征,符号化的毛泽东形象在国共内战期间广泛地出现在政治动员仪式、公共空间、家庭生活和建筑装饰等场景之中。而维护毛泽东形象统一性和排他性的努力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强化。进入1949年后,毛泽东著作和形象出版开始受到强力约束。尽管中共当时还没有形成后来完全自上而下、更为严格和集中的领袖形象传播机制,但旨在对毛泽东形象实施统一管理的尝试,一开始就是通过强制性的法令来实施的。特别随着中国共产党军队向南方的大城市推进,接管上海这样的图像出版、印刷、发行和消费中心后,控制领袖画像的模本、印刷和发行,成了军事接管时期一项引人注目的政策。私人贩售毛泽东画像的现象屡见不鲜,反映出接管初期的上海对中共革命的视觉符号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的第一份指令即与此有关。这份文件明确指出,“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照片画像及用毛主席与朱总司令照片所做的各种形式徽章,除指令专门机关外,任何人不得私自印本或制造……违反上述规定者,一律不准发行与贩卖,否则以违法论处”。[17]显然,专营政策的目的不是限制毛泽东形象本身的传播,而是限制那些在官方看来不符合标准的毛泽东形象传播。
象征与情境:视觉焦点的政治功能
在政治象征的语义结构中,有两类常见图像。叙事类图像可以用于建构历史观念,[18]而肖像画通常是无背景、无纵深和无情节的,因此必须置于特定环境之中,才能理解其功能。
以毛泽东画像为例,其主要用途之一是在政治集会上悬挂。由于集会规模与对集会进程的有效控制是一对矛盾,所以,画像在集会中发挥的功能,首先是提供一个笼罩全场的高视点,使被参与者始终有被注视的感觉,尽管这种注视是象征性的。来自画像的象征性注视在大型集会上尤其必要,因为集会场地越大,参与者越多,主席台(也是观礼台、演讲席)距离后排和边缘参与者的距离越远,参与者与集会主旨和进程保持同步的难度就越高,演讲者或观礼者的交流实际上被广阔的空间所切断。由于画像的存在,分散在集会不同位置的参与者拥有一个共同的视觉焦点,象征性注视迫使参与者的视觉注意力保持在画像和主席台附近。
在一些更为复杂的场景中,肖像画的在场,为现实和象征提供了一个可见的连接点。1944年,《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延安“七大”礼堂的招待室里听毛泽东阐述中共政策时,发现侃侃而谈的毛泽东与背后墙上悬挂的斯大林画像形成了强烈的互文关系:
我一眼看到毛先生背后的油画上,史丹林委员长倚着桌子,伸着右手,摊着掌心,眉飞色舞地面对着我们,似乎在雄辩,又似乎在向我们说教。[19]这段文字传递的视觉经验,与罗工柳的油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做整风报告》(1951年)的视觉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图5 图5见本期第70页)。在油画中,马克思、列宁的画像构成了毛泽东演讲的背景。这些“画中画”的巨大尺幅足有毛泽东一半高,他们和站立于台上的毛泽东形成了一极,与观众相对。油画阶梯状下降的构图,引导观众的视线从左上角向右下角延伸,强化了“领袖-大众”的二元结构。“画中画”位于这一结构的源头位置。构图和明暗对比(主席台最亮),不但规制了人们的视线,也规制了对油画主题的想象:它们乃是对真理的线性传承所做的隐喻。如果观众假定自己置身台下(正如画家希望的那样),和画中的观众一样仰头听讲,他们将同时受到演讲者和画像的逼视。
美术史家巫鸿分析过“画中有画”的结构,以及“画中画”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图3、图4和图5尽管有着不同的介质和风格,却有完全相似的结构和心理动机。正如巫鸿指出的那样,“画中有画”的图像结构在象征与现实之间构建了多重隐喻关系,而“画中画”往往是对全画主题的说明。[20]如果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社会看作一幅风俗画,对赵超构这样外来访客而言,延安无处不在的毛泽东符号:画像、雕塑、徽章,就是点明主题的“画中画”。它们构成了延安社会的基本视觉经验。
延安作为一个符号空间的特征,反映了中共在政治生活中寻找视觉焦点的努力。1937年以来,延安的符号领域经历了一个逐渐聚焦的过程:随着政治进程的推进和政治运动的展开,中共的权力构架在调整后趋于稳定,新的符号被创造出来,大量美术作品都描述新延安的城市布局:桥儿沟天主教堂、杨家岭大礼堂、延河两岸的风光以及宝塔、新市场,这些空间成为视觉艺术常见的表现对象,作为新延安的标志性景观,完成了对“革命圣地”的影像建构。
而“革命圣地”的视觉焦点,最终就落到了毛泽东符号上。1945年,在延安杨家岭专门建造的大礼堂中,召开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确立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政治秩序也集中而强烈地投射在“七大”会场的视觉设计中。
当会议代表鱼贯进入“七大”礼堂时,他们的视线将被两侧墙壁上的红旗和标语引导到会场正面;在那里,主席台与普通代表座席相对,整个主席台被旗帜、标语、徽章、画像所包围。主席台后方墙壁高悬着毛泽东和朱德的侧面浮雕像,雕像上挂着条幅,以秀丽的楷体手书“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横幅上再饰以超大弧形匾额,以无个性的宋体字书写着“七大”的口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在“七大”会场里,标语上“毛泽东”的名字、侧面浮雕像和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本人,牢牢占据着视觉焦点。它们响应着大会的主题,即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着重阐述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道路”。新党章将毛泽东推上了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并列的共产主义伟人的位置。
至此,毛泽东在中共权力格局中的位置,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他的视觉形象以及有个人风格特征的语言和艺术,已经成为中共和中共革命的象征。毛泽东符号牢牢占据了革命象征体系的焦点,“正式”的风格也逐渐过渡成为“标准”的风格。
1949年10月1日,一幅6米高、4.6米宽的巨幅毛泽东画像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成了中国革命当仁不让的视觉焦点。画像重新定义了天安门,将其从古老的皇宫入口变为俯瞰街道和广场的检阅台,从天安门前经过的人群则仰望画像,在虚拟的注视中感受到个体与革命、群众与领袖的关联。从那时起,不定期更新的“标准像”模板向全国发行,由指定的生产和发行机构复制传播,使得毛泽东标准像进入到公共机构、企业和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普通家庭之中。尽管标准像仍然带有毛泽东的个人特征,但这种特征已经极尽简化、抽象和美化之能事。正如邓小平等人反复强调过的那样,“毛泽东思想”并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中共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象征。毛泽东的标准像也并非毛泽东的肖像,而是中共革命的视觉象征。
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出现毛泽东标准像的空间,都是对“城楼-毛泽东像-广场”这三位一体的符号空间的模仿。无论在哪里,毛泽东标准像总是处于水平视线之上。它定义了空间,迫使人们抬头仰望,从中体验到敬畏之情。当中共以文化手段为重新叙述党史而努力时,它出现在《东方红》的舞台布景上,俯瞰演员和观众,正如油画《开国大典》在毛泽东周围开辟出无限广阔的空间一样,以符号定义空间的策略,也最终定义了官方的历史叙事。
在此后数十年中,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建筑不断扩宽、延展、改建,但画像这一视觉焦点从未发生变化,画像上投射出来的象征性视线约束着整个广场,它自身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秩序不断延续的象征。
讨论和结语
以上讨论已经揭明毛泽东图像和毛泽东符号的区别,以及具体的毛泽东图像向抽象的毛泽东符号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图像学意义上的视觉演化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政治建构两个方面。
在毛泽东形象的传播中,摄影起到了原始记录(documentary)和视觉原型(archetype)的作用。那些具备正式风格的肖像照,因为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合作,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歧义,这种风格的形象也正符合人们通常对领袖人物形象的心理期待,所以更容易被传播。在本文讨论的案例中,具有这类风格的肖像照片极其稀缺,进一步增加了少数照片的传播机会,而其他媒介对这类照片的复制、摹写和改动,使得毛泽东形象逐渐抽象化和符号化。
本文业已指出,围绕毛泽东符号的政治建构,取决于政治进程对象征体系的需求。这一需求推动了对视觉符号的选择,对符号意义的确认以及对各个符号重要性的排序。在整风运动后期,毛泽东符号被置于中共革命象征体系的焦点位置,对毛泽东符号的传播方式和强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并导致了标准像—— 一种更抽象、应用更广泛、垄断性更强的毛泽东符号的出现。这一符号主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文化。它不但定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间、仪式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还定义了主流的历史叙事,成为中共政治延续性的象征。■
①Peter Kenez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9-1929)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P118P215
②Red Star over China汉译版本甚多,译名不一,且英文版和中文版使用插图不同,为便于论述,本文所引英文书名处,均指该书英文初版。
③从那之后,毛泽东和斯诺之间形成了一条特殊的纽带。因为这种纽带的存在,1939年、1959-1960年、1965年及1970年,斯诺又曾四度访问毛泽东。
④1936年,亨利·卢斯买下《生活》杂志(Life),将其改造成刊登照片为主的新闻周刊。第一期杂志于1936年11月23日出版。仅在一个多月之后,1937年2月1日出版的《生活》杂志就发表了斯诺关于延安之行长达5页的报道。报道发表时,图1位于文章最前面,占据半页大小。正是因为对照片的大胆使用,《生活》迅速成为美国发行最广和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之一。
⑤裴宜理:《安源》第11页、190-191页,闫小骏译,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⑥夏佑至:《干掉摄影师》第4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⑦洛伊斯·惠勒·斯诺:《埃德加·斯诺和中国》(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演说),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第331页,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
⑧准备工作包括征集和编辑一本长征回忆录。斯诺拿到这本回忆录的副本时,发现包括100多名长征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作者中既有高级将领,也有普通士兵。这份材料构成了斯诺著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⑨Edgar Snow: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New York: Random HouseP167
⑩书中共收入34张照片、10首歌曲和一幅长征地图。
[11]1937年5月,斯诺的朋友王福时陪同斯诺的妻子尼姆·威尔斯抵达延安时,随身带了一筐样书,并将其中一本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写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中引用自己与斯诺的谈话,即来自此书。
[12]皮埃尔·布尔迪厄:《摄影的社会定义》,见罗岗、顾铮编:《视觉文化读本》第5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聂荣臻完全了解杂志的内容。实际上,他不但亲自审定过所有稿件,还指示将照片文字说明译成英文。见顾棣编著:《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上)第3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4]顾棣日记,1944年12月21日,见顾棣编著:《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上)第82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5]顾棣编著:《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上)第15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6]陈石林、曾璜:《标准照后:访陈石林》,《中国摄影家》,2007年第12期
[17]见《上海市军管会关于出版和照片的几项规定》,1949年5月28日,见上海档案馆编:《上海解放》第370页,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
[18]1949年之后出现过大量这类图像,如古元的木刻《毛主席在延安》(1951)、石鲁的壁画《转战陕北》(1959年)和王式廓的油画《转战陕北》(1970)
[19]赵超构:《延安一月》第61页,新民报馆1946年版
[20]巫鸿:《重屏》第16-17页,文丹译,黄小峰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汪伟/笔名夏佑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