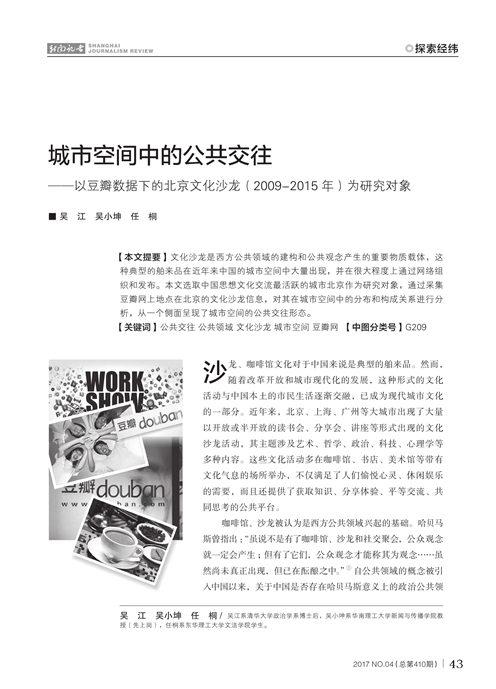城市空间中的公共交往
——以豆瓣数据下的北京文化沙龙(2009-2015年)为研究对象
■吴江 吴小坤 任桐
【本文提要】文化沙龙是西方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公共观念产生的重要物质载体,这种典型的舶来品在近年来中国的城市空间中大量出现,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网络组织和发布。本文选取中国思想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城市北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采集豆瓣网上地点在北京的文化沙龙信息,对其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和构成关系进行分析,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城市空间的公共交往形态。
【关键词】公共交往 公共领域 文化沙龙 城市空间 豆瓣网
【中图分类号】G209
沙龙、咖啡馆文化对于中国来说是典型的舶来品。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这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与中国本土的市民生活逐渐交融,已成为现代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出现了大量以开放或半开放的读书会、分享会、讲座等形式出现的文化沙龙活动,其主题涉及艺术、哲学、政治、科技、心理学等多种内容。这些文化活动多在咖啡馆、书店、美术馆等带有文化气息的场所举办,不仅满足了人们愉悦心灵、休闲娱乐的需要,而且还提供了获取知识、分享体验、平等交流、共同思考的公共平台。
咖啡馆、沙龙被认为是西方公共领域兴起的基础。哈贝马斯曾指出:“虽说不是有了咖啡馆、沙龙和社交聚会,公众观念就一定会产生;但有了它们,公众观念才能称其为观念……虽然尚未真正出现,但已在酝酿之中。” ①自公共领域的概念被引入中国以来,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政治公共领域或文学公共领域,备受争议。必须指出的是,受制于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语境,公共领域理论对中国的现实并不具备尽然的解释力。尽管如此,中国大城市中文化沙龙的持续发展及其背后的文化商品化动力,却表现出与西方公共领域产生的文化商品化内核相一致的特征。
基于此,我们选择北京作为考察地点,尝试发现在网络与现实并生的传播环境下,城市空间中的公共交往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又将朝向怎样的方向发展。将北京作为样本是因为这是中国思想文化交流最为活跃的城市,从2009至2015 年,仅在北京就已举办了上万场次文化沙龙。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的文化沙龙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性;而对北京文化沙龙的数据描绘,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城市空间中的公共交往,从而在一个具体的领域中了解非官方的传播机制在知识重构的社会治理中的可能作用。
一、熟人、书店、互联网:文化沙龙的“圈子”变迁
在现有的资料中,很难找到完整、系统地记录互联网时代以前中国文化沙龙的资料,但从历史访谈、回忆录和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到不少文化沙龙的轮廓。
资料显示,新中国第一批沙龙活动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②活动通常都以一个“精神领袖”为中心,以熟人之间的小“圈子”为基础,参与者多为知青、高干子弟,以及一般知识分子和文艺爱好者。但由于此类活动在当时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色彩和政治性特点,几乎无一例外地保持相对封闭和“地下”状态,以至产生了“地下上流社会”③的提法。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沙龙中包括聚餐、唱歌、出游等“戏码”,但阅读和文艺创作无疑始终居于核心,其中不乏对时事的热烈探讨。当时,在沙龙参与者中间影响甚大且广受传阅的读物,多为“黄皮书”“灰皮书”,即从特殊渠道获取的原本专供高级领导干部和研究机构阅读的文艺类和政治类书籍及其手抄本,以及其他参与者的文艺作品。正是通过书籍交换(俗称“跑书”④)等参与者的个人行为,不同的沙龙联结在了一起。
20世纪80年代曾被认为是“沙龙的黄金时代”。⑤这一时期,期刊成为公共空间最为重要的信息载体之一,围绕文艺期刊的写作、编辑和挑选,作者、编辑和读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⑥高校同样是文化沙龙的主阵地,相关活动既包括普及度和开放度较高的读书会、舞会等活动,也包括围绕学术著作和教科书的编撰、西方学术作品的译介而形成的专业化讨论群体。相关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公共表达空间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主流政治理念与民间诉求的同构性、知识分子艺术家身份的叠加性,以及文学繁荣与读者成熟的同步性。⑦
20世纪90年代,由于文学私人化程度加深,以及作家去知识分子化⑧等的影响,文化沙龙活动处于相对停滞期。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万圣书店、风入松书店和国林风书店为代表的民营书店⑨在一定意义上承担起了市民社会“凝结核”的作用,这促使书店成为沙龙活动的主战场,不仅是读者自发聚集和交流的场所,而且书店还主动组织讨论会、读书会等活动。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文化沙龙活动有所增加,并且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是活动形式由地下/半地下转为公开化,“神秘”“危险”“躲躲闪闪”的特征淡化;二是参与者结构由封闭的“圈子”转向开放,即由先前建立在既有“小圈子”、熟人关系和共有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参与者结构,转向参与者的陌生化、身份多元化和非专业化。沙龙活动的发展得益于文化市场的繁荣、人们既有文化兴趣的延续和增长,活动和运作模式的成熟化,咖啡馆和书店等物质载体的增加等因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互联网为活动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工具:一方面,QQ、论坛、豆瓣等起到了纯粹传播信息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们在维系线上社群、发起线上活动的同时,也催生了线下活动的需求。基于这样的转变,本文将网络空间中的文化沙龙所呈现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呈现特征、主题分布和内容范畴等加以分析,并进一步讨论其背后的公共性要素。
二、数据来源及采集方法
本研究所用数据抓取自豆瓣网的豆瓣同城栏目(http://beijing.douban.com/),在该栏目中,各活动主办方通过豆瓣小站来发布活动信息。本研究选取豆瓣网主要是由于该网站的核心用户对图书、影音等文化产品的关注度高,并可以通过关注友邻、发豆邮、加入小组和小站进行分享和讨论,从而构成特定空间中的公共讨论。由于豆瓣网鲜明的文化定位,很多文化沙龙主办方都选择在该网站上发布信息,并且使用搜索引擎的检验结果显示,豆瓣同城是很多文化沙龙的唯一发布渠道。还有一些主办方,虽然在豆瓣以外设有官网,但是官网上记录的举办活动情况甚至不如其在豆瓣小站上的记录完整。因此,豆瓣同城是观察城市文化沙龙较好的数据来源。
笔者使用Python对豆瓣同城数据进行了抓取(抓取时间为2016年1月),抓取内容包括沙龙类别、举办地点、收费情况、活动简介等,时间跨度设定为2009年1月至2015年12月。经过筛选后共得到在北京举办的共12550场文化沙龙活动信息。具体操作如下:(1)为挑选出主要在北京举办活动的小站,笔者首先抓取了“北京活跃的主办方”一栏中的小站列表,然后又获取了类型为“讲座”的北京主办方列表,并去除列表中将主要功能定位为网上售票、组织户外运动等的主办方。(2)在沙龙类别的设定上,按照普遍性的分类,沙龙包括电影沙龙(集体观影活动)、桌游沙龙、戏剧沙龙(集体观看戏剧或排练戏剧的活动)、英语沙龙(即英语角活动)等多种类别。基于本研究的主旨,我们仅选取分析围绕某些主题展开公开讨论交流的活动。(3)去除列表中将主要功能定位为网上售票、组织户外运动等的主办方。在抓取信息时,聚餐、卡拉OK、招募义工、问卷调查等不属于文化沙龙的活动被自动过滤。
三、文化外衣、经济主体与精英内核:城市文化沙龙的基本构成与呈现形态
(一)城市空间中不均衡分布的文化沙龙
从豆瓣所呈现的时间分布来看,2009至2015年,北京文化沙龙增数显著,从2009年的461场,增加到2013年的2643场;2014年开始下降为2324场,2015年为1550场。沙龙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同样不均匀(表1 表1见本期第45页)。从2009年至2015年(可在区级水平确认活动地点的沙龙数量=12542),高达5786场(46.1%)是在朝阳区举办的,遥遥领先于排在后两位的城区的活动场次(海淀区3377场,东城区2317场)。而在顺义区、大兴区等地区举办的活动数量却很少。
这一方面是由于北京文化区域的分布集中度较明显,另一方面也与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将历年区县沙龙场次与上年地区生产总值进行关联性分析,结果显示了关联的显著性(表2 表2见本期第46页)。
各个区域举办沙龙的密集程度从另一方面表明,沙龙分布在城市中心地带,并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状况(图1 图1见本期第46页)。在北京市五环路以外,举办活动的场所及活动场次非常少。在五环路以内的范围中,西南部地区虽然也有一些活动举办地,但这些地点相对分散,且活动频率较低。相反,在五环路内的西北部、中东部和东北部等地区,不但活动场所较多,而且活动频次也较高,这些地区多为高校周边地区(如中关村、五道口),商圈(如南锣鼓巷、蓝色港湾)、写字楼密集地区(如呼家楼)或文化创意产业密集地区(如798艺术区)。
由此可见,城市文化沙龙的活跃程度与城市经济紧密相关。这种经济差异同样也能解释近十年来沙龙活动的数量相较以往大幅增加的景象。具体来看,经济发展对文化沙龙的影响主要由于以下原因:(1)最为明显的是,当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提升时,人们的文化消费水平也会提升,从而能够积累更多知识,接受更多文艺熏陶,培养更敏感和丰富的性情,因而参与文化沙龙的意愿也就更高;(2)在朝阳区、东城区和海淀区的部分区域,高校较为集中,也是青年群体经常活跃的地区;(3) 经济水平高的地区,人们消费水平更高,因而就会出现更多咖啡馆、独立书店,以及营利或半营利性质的文化体验场所为沙龙活动的举办提供了条件。(4)经济发达地区有着更多繁华商圈,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朝阳区和东城区的文化创意产业相当发达,这既是路径依赖(即,以往文创产业主体的偶然落地和逐渐聚合),也是北京市或城区层面城市功能定位及相关文化产业政策激励和支持的结果。⑩
(二)区域特征与文化沙龙的类型分布关联
上述分析显示,文化沙龙的分布与城市空间中的经济条件、文化机构分布等有着较为明显的关联。表3的数据显示,朝阳、海淀、东城、西城四个区域中的文化沙龙占北京2009年至2015年文化沙龙的98.5%,而其他区域的文化沙龙总和仅占到1.5%。很显然,北京的文化沙龙在地理分布上显现出极化的现象。
在这些不均衡分布的文化沙龙里,对居于核心的四个区域的沙龙类型加以统计,可以发现:朝阳区的美术设计、星座占卜、音乐戏剧、政治和经济等类型的沙龙占比较大;海淀区在工作学习技能提升、科普、阅读、政治、生态环保方面占比较大;东城区在美食、传统文化、生态环保等方面较为显著;西城区的传统文化、美食和阅读类型沙龙较多。由此可见,无论是数量上还是与公共问题的接近性方面,朝阳和海淀都是最为集中的地区。而在这两个地区中,由于海淀区的高校集中,以学生为主要参与群体的工作学习技能提升类、阅读类、科普类沙龙也最多。而政治类话题在这两个区域中比重相当,也说明了北京城市文化沙龙与城市空间的特性具有内在的关联。
比较周围其他12个区的文化沙龙,可以发现在沙龙的外围区域,生态环保、星座占卜、心理学等类型占比相对要高一些,而经济、政治、科普、音乐戏剧等类型的沙龙则在十位数以下。这也再次说明文化沙龙与城市空间的布局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样的呈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共讨论的分布情况,但并不意味着在核心区域之外就没有公共讨论。
当今的文化沙龙与近现代西方话语中的公共空间都强调身体的在场性。在通信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人们相互结识并参与讨论的最高效方式便是以直接在场的方式参与活动。在当代社会,网络技术已经充分满足了沟通需求,在此情况下,但是人们仍然选择来到活动现场。最为明显的原因在于,主办方为盈利目的增加顾客数量,因而选择能够带动购买行为的线下活动。其次,普通人能够与名人面对面互动,是实体活动相对于线上互动的又一优势。再次,一些活动的吸引人之处就在于能够满足人们现场参与的需求,如体验茶道、学习书法、制作手工艺品等,这些优势是线上活动不具备的。
(三)建立在文化商品化基础上的开放式参与活动
与社交媒体所提供的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平等参与的公共空间不同,线下的文化沙龙弥补了网络交流所不具备的主体在场性。近代以来,西方公共领域理论强调政治性的公众参与,对抗性表达和批判精神是其灵魂。尽管互联网空间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但隐匿身份却让很多不具备这种精神的人也敢于发言,换句话说,网络表达是身体在场的公共领域的一种缺失形式。
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中,很难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词语的对应物找到合适的位置,所以我们难以回答“当今中国的文化沙龙与公共领域之间是否有着本质相似性”这样的问题。然而,可以看到的是,文化沙龙与西方社会理论中的“公共领域”一样,建立在文化的商品化基础上。
营利性机构是当前文化沙龙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从2009年至2015年,共有443个组织作为主办方举办过文化沙龙。其中,以公立机构、公益组织的名义或在公立机构中产生的主办方有37个,约占9.1%,包括日本文化中心、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北京同志中心等。这些机构组织的活动占数据集中全部活动的16.7%;其余活动中,除少量活动由公益机构举办后,大部分为营利性机构举办的活动。超过半数(52.4%)的活动设置了嘉宾/主讲人/点评人或类似的组织角色。
商品化主要体现在主办机构的性质上,但对参与者来说,以开放式的参与模式为主。有52.8%的活动没有要求参与者提前报名,以随时可加入的方式保障文化沙龙的整体开放性。尽管不少活动由营利性机构组织承办,但其中高达70.5%的活动不要求参与者支付任何费用;也仅有约11.8%的活动标明需支付从1元到30元不等的费用,并且其中一部分是以场地费或最低消费的名义收取的,而活动本身无需缴纳费用。尽管如此,我们也注意到收费的文化沙龙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表4 表4见本期第48页),这意味着原本相对于文化消费的公共空间正在不断成为消费的一部分。
(四)精英文化的主题延续:科学、阅读与知识分享
不管是否存在咖啡馆文化传统,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其文化沙龙与咖啡馆形成有趣的关联。在我们所采集的数据中,有4.3%的沙龙活动是在咖啡馆或书店等与咖啡馆形成一体化经营的场合中进行的。而整体数据中又有高达40.8%的活动是与阅读联系在一起的,形式包括读书会、朗读会、读编交流会,甚至图书首发会等。其中,以政治为话题的沙龙中,有63.7%是围绕着阅读行为进行的。
咖啡馆、沙龙在西方现代文明史上被认为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种源自英法的公共领域文化传统,奠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内核。书籍和阅读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这带来了文化沙龙的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参与沙龙的人必须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11]其次,活动具有一定稳定性,例如,不少沙龙活动都是以读书会、读书俱乐部的形式出现的,活动参与者在固定的场所内就阅读内容进行讨论,甚至可能按照条例组织自己的委员会。[12]人们一方面把私人阅读体验带到公共讨论中,另一方面又用公共讨论来丰富和检验自身体验。
在如北京这样的城市中,文化沙龙的要求除了阅读分享之外,还朝向对品味和对各艺术领域专业知识的要求延伸。从主题分布来看,科普类沙龙最多(15.0%),其次是美术设计类(14.0%),其后的主题包括传统文化(13.4%)、心理学(12.0%)、政治类(7.7%),以及美食健康、兴趣分享等(表5 表5见本期第49页)。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过程显示,咖啡馆时常是公众讨论科学,以及科学家开设物理学、解剖学、天文学等课程的场所。[13] 这种在科学领袖倡导下的精英讨论,成就了近代西方的自我教化和科学启蒙。本研究采集的数据也显示,在北京的科学类沙龙中,普及科学知识、新技术产品推广等为主要内容。与科普主题的沙龙一样,上述主题分类中,美术设计、传统文化、心理学、政治类、环保类等沙龙都以主讲+讨论的方式展开。沙龙也成为知识分子与公众互动、扩大影响力的平台。历史和现实均显示,文化沙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满足人们参与愿望的替代物。而在城市咖啡馆中举行的去政治化主题的沙龙活动,及其所蕴含的分享聚会或商业活动特征,使其政治敏感性大为降低。
四、结论与不足
当代中国是否具有政治公共领域或至少是文化公共领域?首先,公共领域存在的前提是其自身与私人领域共同存在且泾渭分明。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未给公共领域留下多少空间。另外,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使中国发展出了黑格尔意义上的、拥有独立性的市民社会,这仍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公共领域的主要作用是对充满特殊利益的市民社会进行调节;因此,如果市民社会根本不存在的话,公共领域也并无存在价值。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本文通过对北京城市空间中文化沙龙的分析,尝试回应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即中国的公共领域会采取何种载体,城市空间中的公共交往以何种形态出现?基于豆瓣数据的城市文化沙龙分布及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典型城市空间中的公共交往形态。可以发现,以北京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的文化沙龙与近代西方公共领域的实体形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主要体现在城市空间所营造的文化公共性方面:
1.文化沙龙与西方公共领域都建立在文化的商品化基础之上
在公共领域所依托的咖啡馆和沙龙活动中,通常需要将文化产品作为凝聚众人参与的核心。如哈贝马斯所言,公共空间只有以文学艺术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为基础的才能增加文艺作品的世俗性和可理解性。[14]对当代中国城市文化来说,产品的提供者通常都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对此类机构来说,扩大自身影响力,增加销售额的目的是其组织沙龙活动的主要动机。
2.文化沙龙和西方近现代公共空间本质上都具有身份非限制性和平等性
西方近现代公共空间本质上的批判性以其较高水平上的开放性为必要条件。尽管教育和财产是进入公共领域的隐性标准,但原则上人们参与文化沙龙等活动时都是平等的。咖啡馆在西方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中提供了一个平等、开放的平台,使人们有机会讨论国家大事,结识陌生人,[15]这种平台甚至还在历史事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16]北京城市文化沙龙的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为城市公民提供了同样的开放平台,尽管很多沙龙采用了意见领袖的模式,但并未对沙龙活动中交流的平等性造成影响。
3.文化沙龙与公共领域建构所形成的讨论议题具有相似性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公共领域发挥着“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 [17]的作用。尽管从表面上看,以文学、艺术、旅游、心灵体验和日常生活为主要议题的文学公共领域似乎与制度抗争并无关联,但共同“反对政治领域中的专制主义”,[18]参与者恰恰是通过围绕这些看似与政治无关的展开讨论从而完成政治批判的。从北京的文化沙龙议题分布来看,政治性的议题占比并不高,且呈下降趋势。然而,这种“去政治化”的文化沙龙议题是否意味着公共领域的缺失?国家能力和行动领域的扩张,是否意味着公共批评空间的更多限制?这些仍是值得更深入探讨的问题。
21世纪的头十年,借助于互联网的宣传功能,北京地区沙龙活动得以蓬勃发展。2013年之后沙龙数量的下降,除了微信兴起后带动的发布平台转移和分流,以及经济发展放缓所带来的影响之外,我们更需要关注其活跃度下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尤其是政治和公共讨论类的文化沙龙数量的下降,以及商业性沙龙的增长。这似乎意味着原本相对于文化消费的公共空间不断成为消费的一部分,成为盈利的工具。
本文从一个有限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城市文化沙龙的分布和特征,并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作为参照,探讨其城市空间中的公共交往形态。使用的数据为豆瓣同城采集到的文化沙龙信息,并依照标签对其进行了归类。尽管通过这样的做法,我们从上述几个方面对这些文化沙龙信息进行了总体性的描述,但出于主题集中性的考虑,本文对信息发布的具体话语内容未做分析。此外,本文仅考察了北京一个城市的文化沙龙现象,若要较为全面地描述中国城市文化沙龙的特性,还需要考察更多的城市,比较并发现它们的异同。这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空间。
此外,尽管我们做了可能的尝试,但本文所做的分析和探讨,并不足以回答中国是否可能发展出市民社会的某种形态?这样具有长期争议性的问题。也难以判断文化沙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促进交流和批判的功能。当代中国的文化沙龙在思想观念和消费文化的双重冲击下,很难发现其对中国公众思想多元化的实质性贡献,也没有看到相互冲突的思想体系因沙龙活动而形成某种共识的现象。而要解释这些困惑,则要进一步观察和探讨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抱有消费休闲的心态而非交流批判的心态,主办者和知识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放弃提高大众品位的理想而屈尊俯就等等。■
①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王晓珏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41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②③参见杨健:《1966-1976的地下文学》,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电子版(http://www.bxwx.org/text/92/92317.html),“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李坚持、黎利地下沙龙”。
④参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第6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⑤陈丹青访谈(视频):http://chuangxin.umiwi.com/2011/0905/35144.shtml,2016年1月10日
⑥作为80年代现代诗歌运动的象征的《今天》就是此类刊物的代表。
⑦⑧参见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
⑨张小劲:《市民社会与国家知识治理制度的重构——非官方传播机制的生长及其作用》,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市民社会与治理”研究报告,1999年
⑩除了给予相关政策激励外,公共部门还能通过更为直接的方式支持文化活动。例如,朝阳区文化馆是由朝阳区文化委员会所领导的下属事业单位,文化馆及其筹建的相关机构是区内文化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11][12][14][17][18]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王晓珏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2、35、40、41、55、83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3]郭宏安:“法国大革命与文人”,《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22日
[15][16]艾利斯著,孟丽、陈广兴译:《咖啡馆的文化史》第55、62、66、24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吴江 吴小坤 任桐/吴江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吴小坤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先上岗),任桐系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