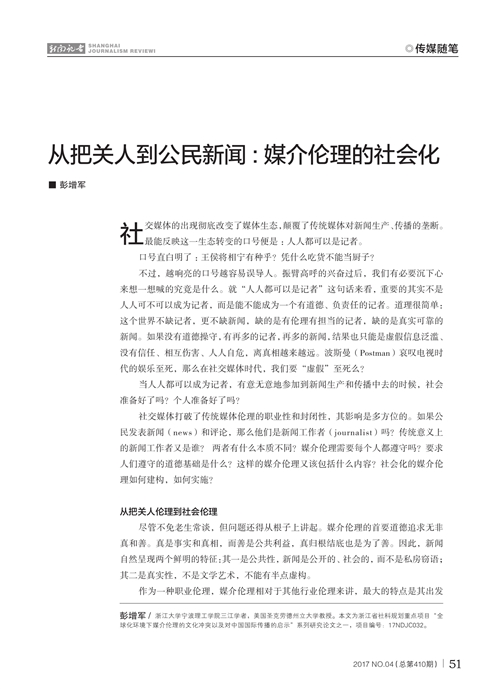从把关人到公民新闻:媒介伦理的社会化
■彭增军
社交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媒体生态,颠覆了传统媒体对新闻生产、传播的垄断。最能反映这一生态转变的口号便是:人人都可以是记者。
口号直白明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凭什么吃货不能当厨子?
不过,越响亮的口号越容易误导人。振臂高呼的兴奋过后,我们有必要沉下心来想一想喊的究竟是什么。就“人人都可以是记者”这句话来看, 重要的其实不是人人可不可以成为记者,而是能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负责任的记者。道理很简单:这个世界不缺记者,更不缺新闻,缺的是有伦理有担当的记者,缺的是真实可靠的新闻。如果没有道德操守,有再多的记者,再多的新闻,结果也只能是虚假信息泛滥、没有信任、相互伤害、人人自危,离真相越来越远。波斯曼(Postman)哀叹电视时代的娱乐至死,那么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要“虚假”至死么?
当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有意无意地参加到新闻生产和传播中去的时候,社会准备好了吗?个人准备好了吗?
社交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伦理的职业性和封闭性,其影响是多方位的。如果公民发表新闻(news)和评论,那么他们是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吗?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工作者又是谁? 两者有什么本质不同?媒介伦理需要每个人都遵守吗?要求人们遵守的道德基础是什么?这样的媒介伦理又该包括什么内容?社会化的媒介伦理如何建构,如何实施?
从把关人伦理到社会伦理
尽管不免老生常谈,但问题还得从根子上讲起。媒介伦理的首要道德追求无非真和善。真是事实和真相,而善是公共利益,真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善。因此,新闻自然呈现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公共性,新闻是公开的、社会的,而不是私房窃语;其二是真实性,不是文学艺术,不能有半点虚构。
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媒介伦理相对于其他行业伦理来讲,最大的特点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公共利益。一个律师可以说为自己的雇主服务,一个医生可以说为自己的病人服务,但一个新闻工作者却不能说为自己的广告商或者订户服务。美国传播学家凯瑞(James Carey)如此强调新闻媒体的公共性:
新闻的公共性是上帝一般神圣的字眼,归根结底,没有这个字眼,一切都是扯淡。如果说新闻有所依托,那这个依托无疑是公众;如果说新闻有个雇主,那个雇主只能是公众。新闻界以公众的名义取得正当性。它存在的意义,至少在口头上,就是提供公众新闻。它是公众的喉舌,维护公众的知情权,为公众服务。公众是图腾。
新闻由于其公共性质,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认同。而媒体公共性的保证和约束不是别的,正是伦理。
传统媒介伦理是在新闻媒体作为把关人的前提下构建的。公民新闻动摇了媒体把关人的地位,影响了传统媒体的新闻定义权和新闻生产规范权,削弱了传统媒体控制新闻的能力。有观点认为,公民新闻的出现实际上宣告了专业新闻的结束,公民新闻完全可以取代传统媒体。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新闻是否能够取代传统媒体,而是公民新闻的公共性在哪里?如何体现?有什么样的道德理由要求其必须为公共利益服务?它的公共性又如何得到法律的承认和社会的认同?
传统新闻是系统的体制内的职业行为。新闻记者和编辑从事新闻生产大多是自主选择,对伦理的遵守有自律和他律的约束。而公民新闻则比较复杂。对于多数人来说,参与公民新闻不是主动的选择,而往往是偶然的客串,比方说正好在新闻现场,成了围观群众或者新闻当事人。对于这样的公民新闻,该提出怎样的道德伦理要求?一个人发帖子可不可以只为自己爽一把而不考虑公共利益?为什么要客观?为什么要核实?为什么要平衡报道?
这样的发问当然有道理,有些问题还不一定有确切的答案。但是,有意栽花也好,无意插柳也好,只要参与了新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其行为就不再局限于个人,而是要产生社会影响。新闻作为言论和表达自由的主要形式是一种权利,但伴随权利的是义务和责任。新闻作为一种力量,随时可能对社会和个人造成伤害。也许有业余的新闻,但没有业余的伤害。
网络社会,几乎所有的传播行为都已经社会化,进入到公共领域,而伦理问题的社会化就更为突出。比如说隐私,就呈现了越来越明显的社会性和非自主性,无论你自己如何小心翼翼地守身如玉也避免不了。因为在你的个人信息里,不但有你个人的隐私,更包含了太多别人的隐私,比如你的微信朋友圈和QQ好友。如果你通过微信或者QQ登录其他网站和服务,必然就带去了自己和好友的信息,一不小心就出卖朋友,株连“九族”。社交网站比如脸书就是靠出卖用户的信息给广告商来盈利的。据最新测算,一个美国或加拿大的脸书用户的价值大约为5.85美元。
“裸奔时代”没有隐私。因此,每一次传播行为,都是社会化的操作,有社会化的影响,因此需要社会化的媒介伦理。
也许有人会说,新闻传播业进入了虚拟现实的后专业主义时代,机器人都开始写稿了,还弹什么伦理的老调。但是,不可忘记的是,无论多么虚拟的现实,多么智能的机器,后面永远都有个肉体。机器也许改变了做事的方式,但是改变不了责任,人类永远是道德的行为人。
从互联网的普及,再到社交媒体的兴盛,至少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无论业界还是学界似乎都忽略了公民在社会化传播中的道德伦理责任。尽管各种骇人听闻的道德伦理问题层出不穷,但都止步于就事论事,而没有把媒体伦理的社会化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来讨论,更谈不上构建。
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犹如洪水泛滥,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受到冲击,伦理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支离破碎,但是,即使破碎成一个个孤岛,至少也可以给传统媒体人提供伦理坐标。而公民新闻直接就泡在了洪水里,迷失者有之,浑水摸鱼者更有之,网络成了一个丛林社会。比如在网络上随便一搜都可以搜到介绍自杀方法方式的网站或者信息。某个自杀网站居然有这样的口号:“消灭自己,拯救地球。”并劝说人们自杀的时候干得漂亮些:“自杀是个难事,极其容易犯菜鸟错误。所以,你需要深入研究,精心准备。”
有的专业新闻网站为公民新闻提供平台,也出了诸多伦理问题。例如,2014年5月26日, 美国有线新闻网的iReport发布了一条流星将要撞击地球的新闻,煞有介事地宣称:“如果天文学家对了的话,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将在不到30年内消失。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曼哈顿大小的流星正在撞向地球,具体碰撞时间是2041年3月35日。”尽管这是一个恶作剧新闻——发布者还特别卖了个破绽——3月35日,依然在30个小时内,有25万的浏览量和2.3万的转发量。
如果上面的恶作剧没有造成直接后果的话,另外一些假新闻则会造成社会动荡和个人损失,比如2008年,有人在CNN网站上发布苹果老总乔布斯死亡的假消息,结果引起股市动荡。
网络色情暴力图片更是比比皆是。2013年中国传媒大学女大学生被男子当街杀害,路过的网友拍到了浑身是血的受害人照片,被人传到了网上,还被许多网络大V 和专业媒体机构盲目转发了。大家当然也不会忘记2017年大年初二宁波雅戈尔动物园老虎吃人事件。有现场目击者录下了老虎攻击闯入者的视频,在网络和朋友圈大量转发。也许有人辩解说,这些照片和视频尽管有些血腥,但发布出来有助于弄清真相和解决问题。但是,真相不一定非要用血腥和暴力才能呈现吧。
相对职业记者,大多数公民新闻的参与者没有接受过基本的新闻训练,更没有受过任何媒介伦理的教育,因此出现问题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
有不少人对于媒介伦理的社会化有不同的认识,认为伦理原本就应该是行业的伦理守则,不应该放大到社会,应该包容和鼓励言论自由,观念市场本身会优胜劣汰。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社会也不总是理性的。 另外,新的传播手段可以使恶的危害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以前的公共领域,传播的影响限于介质能够达到的范围。而在新媒体时代, 一个人在网络上出口成“脏”,骂的可不是一条街,而是整个地球村。
社会媒体伦理的构建
传统媒体伦理架构是单向的,局限于新闻媒体的伦理操守,很少涉及公众的责任和伦理。这在社交媒体之前,问题不是太大。这就好比交通规则,如果只有职业司机才能上路,那只讨论职业司机的伦理守则也就够了。然而,在今天的媒体生态中,人人都买得起车,人人都可以开车上路,仅仅有行业性的职业伦理是远远不够的。媒介社会化和民主化的后果是模糊了职业新闻人与普通人的界限,人们的身份不再是单一的,而更可能同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美国著名媒介伦理学者瓦尔德(Stephen Ward)在谈到新的媒介伦理时强调:“新的媒介伦理必须是开放的,不仅仅是职业的伦理,必须是社会的媒介伦理。”
但这样的社会媒介伦理应该如何构建?包括什么样的内容?谁来制定?如何实施?这一系列问题解决起来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然,首先能够想到的途径是借助传统的媒介伦理比如借鉴影响较大的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伦理守则。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粗略说有四大原则:第一是追求并报道真相;第二为减少伤害;第三是独立;第四是担当。在这四条基本原则中,除了第二条比较明确,其它三条作为对公民新闻的要求,都极有可能引起争议。职业记者守则第一条要求“追求并报道真相”,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追求真相,二是有料必须爆。但是,如果我只是一个现场目击者,发了一张现场图片,我发了我拍到的,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相?再说,凭什么我必须报道我知道的?至于第三条的独立和第四条的担当就更不靠谱了,我只是一个打酱油的,独什么立?担什么当?
当然,照搬原有的职业伦理体系是不行的,但原有的职业伦理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讨论问题的框架和抓手,就一些紧迫问题开展社会性的对话,以求达到一定的共识。比如可以在一些自媒体组织中尝试。不少自媒体的大V都曾供职于传统媒体,本身就对媒介伦理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和体验,相对比较容易达成可行的伦理守则。比如美国著名博主布兰德(Rebecca Blood)就提出了六项博客伦理原则,受到不少自媒体人认同。这六条原则避免了空洞的说教,平易近人,切实可行:
1.只发布你认为真实的事实。如果只是臆断,请如实指出。
2.如果所提到的内容网上有,请提供链接。让读者去判断你引述的准确性。
3.公开纠错。
4.像定稿一样写每一篇博客。你可以补充,但一经发布,不要随意改写。
5.声明存在的利益冲突。
6.标出有问题或者有倾向性的新闻源。
相对于具体的伦理守则,更难解决的是社会化媒介伦理所依据的道德哲学基础。大家都知道,传统媒介伦理的道德哲学基础主要是功利主义的,即以公共利益这一目的和结果来评判新闻操作的正当性。 但是,功利主义的一大问题是对结果评判的相对性,因为什么是公共利益,何时何地的公共利益都不是绝对的。况且还有由谁来评判的问题。在传统的媒介伦理中都比较棘手,在社交媒体和公民新闻中就更难操作往往会成为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借口和说辞。康德的理性伦理作为绝对的戒律,比较僵化,在实践中往往陷入矛盾。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社会化的伦理应该更多依赖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因为康德是规范性的律条,是从外部强加的,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是由里及外的,品德高尚的人自然不会作恶。这有点像王阳明的心学,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无非说这个东西应该从内心做起,通过经验使德行逐渐内在化。
当然,社会化的媒介伦理不能只靠几个德行高尚的人,社会化媒介责任取决于全社会的共识和大多数人的媒介素养。就眼下的社会现实来看,这几乎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别说道德共识,就连基本事实都无法认同。
那么,社会媒介伦理的建设究竟有没有希望,从何说起,又跟谁说起呢?面对这样的难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上个世纪20年代发生的,关于媒体、民主与社会的李普曼(Lippmann)和杜威(Dewey)之争。
李普曼显然对民众没有信心,认为普通民众达不到民主社会的要求,民主理论要求公民知情,至少对选举出来的领导者有所认识和了解,所谓知情参与。这在古希腊的公民社会,甚至在美国大革命时期的波士顿的市政厅是可能的,但是在工业化以后的现代社会,在媒介时代,世界变得如此复杂,如此超过人们的社会经验,普通的民众已经力所不能及。李普曼认为普通老百姓生活在一个他们无法完全理解的世界,“公众不但反应迟钝,而且非常容易走神,只有出现戏剧性冲突才会缓过神来”。因此,李普曼推崇精英统治,普通人只要听令,见贤思齐就是了。
杜威基本认同李普曼关于媒介化社会太过复杂,超出一般人理解能力的判断。但是,他总结的原因不同,给出的药方也不同。杜威认为,这不是民主的失败,而是民主的考验,一个主动参与的、明智的民众并非不可能,解决的途径是启蒙,包括通过学校教育和新闻界的启蒙,让民众成长、自我发现、自我实现。
那么,今天媒介伦理社会化的药方应该是李普曼和杜威的结合。一方面,我们需要调整改进已有的媒介伦理,坚守原则,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坚持社会伦理重构过程的开放性,鼓励全民的广泛参与。在教育上,可以考虑作为媒介素养的一个重点内容,像哲学、科学一样,成为大学甚至中小学的必修课,只有这样,才能从象牙塔走向社会,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不断总结,逐步形成一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媒介伦理。■
彭增军/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全球化环境下媒介伦理的文化冲突以及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启示”系列研究论文之一,项目编号:17NDJC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