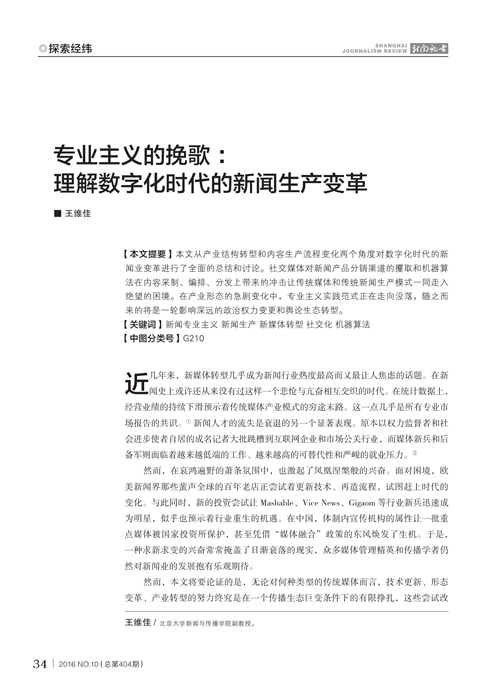专业主义的挽歌:理解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生产变革
■王维佳
【本文提要】本文从产业结构转型和内容生产流程变化两个角度对数字化时代的新闻业变革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讨论。社交媒体对新闻产品分销渠道的攫取和机器算法在内容采制、编排、分发上带来的冲击让传统媒体和传统新闻生产模式一同走入绝望的困境。在产业形态的急剧变化中,专业主义实践范式正在走向没落,随之而来的将是一轮影响深远的政治权力变更和舆论生态转型。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生产 新媒体转型 社交化机器算法
【中图分类号】G210
近几年来,新媒体转型几乎成为新闻行业热度最高而又最让人焦虑的话题。在新闻史上或许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悲怆与亢奋相互交织的时代。在统计数据上,经营业绩的持续下滑预示着传统媒体产业模式的穷途末路。这一点几乎是所有专业市场报告的共识。①新闻人才的流失是衰退的另一个显著表现。原本以权力监督者和社会进步使者自居的成名记者大批跳槽到互联网企业和市场公关行业,而媒体新兵和后备军则面临着越来越低端的工作、越来越高的可替代性和严峻的就业压力。②
然而,在哀鸿遍野的萧条氛围中,也激起了凤凰涅槃般的兴奋。面对困境,欧美新闻界那些蜚声全球的百年老店正尝试着更新技术、再造流程,试图赶上时代的变化。与此同时,新的投资尝试让Mashable、Vice News、Gigaom等行业新兵迅速成为明星,似乎也预示着行业重生的机遇。在中国,体制内宣传机构的属性让一批重点媒体被国家投资所保护,甚至凭借“媒体融合”政策的东风焕发了生机。于是,一种求新求变的兴奋常常掩盖了日渐衰落的现实,众多媒体管理精英和传播学者仍然对新闻业的发展抱有乐观期待。
然而,本文将要论证的是,无论对何种类型的传统媒体而言,技术更新、形态变革、产业转型的努力终究是在一个传播生态巨变条件下的有限挣扎,这些尝试改变不了一个越发清晰的现实,即新闻内容生产和从事新闻内容生产的知识分子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正日益边缘化。这不仅是一轮来势汹涌的资本转移和人才迁徙,更是一轮影响深远的政治权力变更和舆论生态转型。一百多年来,在商业媒体市场中发展成型的新闻专业主义范式和社会责任理念正在走向终结。而这些重要的政治影响很少在传播研究中被全面地讨论。
一、新闻生产的后工业化转型
在阐述新闻业的变革时,人们通常习惯于将其概括为“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在某种程度上,这类阐述符合变化的表面现象,也适合服务于媒体组织的改革目标。但是将新闻业的变化理解为一种线性进化过程,或者将“新媒体化”作为拯救新闻业的思路,实际上都是带着旧思维看待新变化,无法把握问题的本质。当下新闻业的变革,不是发生在行业内部由旧到新的转换,而是整个行业组织结构的功能拆分、权力转移和性质变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资本的创造性破坏提供了可能,原本纵向整合的“采制-编排-出版”的专业化新闻生产流程分崩离析,新闻传播领域正在被一种后工业化的文化生产模式所占领。
以下一些现象层面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解读这场变革:
首先,“社交化”如今已经成为传播和获取新闻信息的一个主导性趋势。根据皮尤中心2016年的调查,美国大多数成年人(62%)都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③而在“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中,Facebook已经远远领先其他媒体成为获取政治新闻的第一源头(高达61%)。④除了Facebook,当然还有微信、Twitter、Whatsapp、Instagram等众多“超级应用”,这些传播领域的新贵不仅逐渐代替了报纸、广播、电视,甚至让前移动时代的互联网信息门户也沦为了日趋没落的“传统媒体”。
“社交化”的趋势首先意味着传统新闻机构失去了直接面向市场分销产品的权力。几家主要的社交媒体集团正在垄断信息传播渠道。这种新的分工等于将传统新闻机构挤压到产业价值链的下游,变得处处被动。与此同时,“社交化”还改变了新闻商品的最终形态。以往,专业新闻编辑可以在众多单个新闻故事的基础上构筑一套意义系统、设置一套公共议程。而在社交媒体的时代,碎片化的新闻代替了一份报纸、一套节目和一个首页,并通过不透明的过滤和排序规则成为日常新闻消费的主要对象,这导致传统新闻机构丧失了重要的议程主导权。
对新闻商品进行整体设计和分销的权力是传统媒体获得广告收入的有力保障,而社交化传播在拆分信息内容的同时剥夺了产品分销渠道,因此,传统新闻机构的广告流失就成为一种必然而致命的后果。无论如何,离开了广告,付费墙和版权交易是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传统媒体产业的。更何况这两项收入的稳定性本身就不容乐观。在这个意义上,“社交化”的趋势不仅意味着“平台”代替了“门户”,更意味着“内容采制、内容编排、内容传送、广告营收”四位一体的“福特式”新闻生产机制正在分崩离析。如果用零售业的经济结构做一个类比,那么后工业化的新闻产业就像是前店后厂的商品市场中突然崛起了一个沃尔玛式的超级分销商。由于这种巨无霸的“平台型企业”可以一站式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借此集中几乎所有的客源流量,因此众多下游生产商只能按照它所规定的标准、模式来提供商品,并根据需要改造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流程。
信息分销终端和议程设置实体的功能被社交媒体夺取后,留给传统媒体的只剩下产业下游的内容生产部分。然而,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专业内容生产的严重贬值。如今,一个街边路人可以拍摄巴黎恐袭和纽约警察暴力执法的震撼画面并广为传播,一个普通难民可以用手机实时报道欧洲边境人群迁徙的动态实况。在这样的时代,专业新闻采编业务只能沦为高投入低产出的没落行当和处处迎合社交媒体传播逻辑的下游供货商。Facebook们正在把传统媒体逼入绝境。原本高贵的新闻人现在唯一的渴求就是能从社交平台上给他们的网站导入一些流量,但即使这点空间也正在被Instant Articles、Apple News、微信公号或者Twitter Moments这些巨无霸的新产品所吞噬。在这些超级应用所提供的“工位”里,传统大报和个人账号平起平坐,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权威和尊严。
其次,在“社交化”趋势的推动下,用“机器算法”(Algorithm)来代替人工编辑如今已经成为新闻业的新趋势。这一变化是新闻传播后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从实质来看,网络爬虫技术和大规模用户行为数据的记录、分析能力是“机器算法”的核心工具。爬虫技术让数字化媒体摆脱了低端的内容生产,而自动化的数据分析和推送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又大大提高了内容传播和广告投放的精确性。更重要的是,利用数字化技术,以往媒体机构的信息服务、受众调查、注意力贩卖三项业务能够无缝衔接、合为一体。这种工作效率让传统新闻生产模式望尘莫及。
随着“算法”这项利器越来越成熟,“新闻聚合类媒体”(News Aggregator)应运而生并迅速繁荣。以Buzzfeed、今日头条等科技企业为代表的这类媒体不再像传统新闻机构那样耗费大量知识劳力来采制新闻,而是在互联网上自动抓取内容(辅以版权交易),再运用计算手段和少量的人工进行分类编排,并根据用户的社会特征和使用习惯进行个性化推送。
从本质上看,传统新闻机构和聚合类媒体都是内容供应商,他们都依赖于社交平台这些虚拟的渠道供应商来实现产品的消费。而大量资本之所以选择迁徙到聚合类媒体的原因是他们更彻底地摈弃了“传统”,更彻底地采用了信息技术来代替知识劳动,从而把商业传播的工具性和获利本质推到了极致。当然,与那些当年在市场浪潮中崛起的小报一样,这种眼球经济的工具性是以反精英主义和“受众自主选择”的面目出现的。
随着Buzzfeed、Flipboard和今日头条等公司的强势崛起,传统大报不得不在新闻生产流程上被动模仿这些新型媒体。此时,正是这些新闻业老贵族们从前所珍视的专业标准和精英气质拖了他们的后腿。这大概就是很多行业专家所谓的“缺乏互联网基因”吧。
对于传统新闻业来说,更糟糕的故事还在后面。大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不会为了某项单一功能而发展。除了自动化的信息搜集和分类推送,“机器人写新闻”也从神话变成了现实。Narrative Science这类科技公司的快速发展,暗示着人工智能广泛进入知识生产领域已是指日可待。
当后工业化的进程在新闻领域开启的时候,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到这一潮流反价值的一面。在资本创造性破坏的颠覆力量之下,任何工业时代的“传统因素”都只剩下一点伦理和政治上的争辩空间,丧失了所有现实经济的合理性。新闻业的变革,改变的不仅是盈利模式和生产流程,也在改变着社会的权力结构。在这些变化的过程中,新闻人,这个秉持专业主义标准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在历史上扮演了现代进步倡导者和社会责任承担者角色的群体,正在丧失公共议题的发言权和议题主导权。
二、竞次传播:新闻编辑室的变化
在《纽约时报》2014年那份引起业界轰动的“内部创新报告”中,倡导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团队是这样教育报社采编人员的:⑤
记者的身份让我们更倾向于以内容好坏而非传播策略优劣来评价竞争对手。然而BuzzFeedHuffington Post 和 USA Today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列清单、花边新闻、智力问答和体育报道。他们的成功来源于精心设计的社交渠道、搜索方式和社群建构等工具和策略。他们甚至常常忽视内容质量。
“常常忽视内容质量”的行业新秀代表着新闻业的未来,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报道水准上的传统记者则迫切需要转变思维!《纽约时报》的老板小苏兹伯格让自己“80后”的儿子带队,对美国新闻界进行了历时半年的调研和访谈,并得出了这样的革命性观点。整个报告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求采编团队从重视新闻本身,更多地转向扩大受众点击率和转发量的数字化传播手段,由此需要那些“落伍守旧”的新闻编辑室人员“亦步亦趋地与报社经营业务领域的读者开发部门合作”。⑥
由此可见,“社交化”和“机器算法”等新变化不仅剥离了传统新闻机构的编排和传播功能,也在改造着新闻内容生产的核心逻辑。如今,新闻编辑部的工作重心正在更彻底地从“如何报道”转向“如何传播”。任何一个长期观察新闻业变化的人都很难否认,“GOING VIRAL!”(病毒传播),如今几乎已经成为包括主流大报编辑室在内众多新闻人念兹在兹的核心追求,而“Audience Development”(受众拓展)也已经是新闻行业最热门、最时髦的词汇。为此,原本设置大众议程、引领社会风气的新闻记者开始放下尊严,主动迎合大众品味和社交媒体的需要。借用社会经济领域的名词,新媒体传播中的工程师文化已经开启了一种“竞次现象”(racing to the bottom)。无论是新生的新闻聚合应用还是大报的新闻编辑室,都在抛弃传统的专业伦理标准,把追求“10万+”“100万+”作为内容采编的核心目标。这不仅是一项避免被淘汰的生存竞赛,也是一种在新闻界广为弥漫的流行风尚。
新目标一旦确定,新闻的生产流程和工作方式就必然被改造。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受众互动工作组”(Audience Engagement Team)以及类似的新部门在众多主流媒体的新闻编辑部中被广泛地设立。目前,这种岗位的人才需求已经渐渐超过传统编辑记者。他们的工作通常包括挖掘受众数据以制定有效的社交媒体策略、观察新闻故事的传播趋势并调整编辑方针、管理受众评论内容等等。总之,就是建立一种24小时的实时反馈机制,以新闻内容的接受情况和传播效果来指导新闻编辑的策略和方向。为了适应这种新的人才需求,美国众多名校的新闻院系都跟风建设了计算新闻或数据新闻的课程和学位项目。
比“受众互动工作组”更具工程色彩的,是新闻机构中越来越强大的数据分析研究团队。如今,无论是传统新闻机构还是聚合类媒体,所有依赖于社交网络的内容提供商都在数据挖掘和开发上下足了功夫。以往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理论物理学博士或统计学博士会进入报社编辑部与记者们一起工作。而现在,这已经是一种流行现象。《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道琼斯新闻、《赫芬顿邮报》、Mashable等各种类型的新闻服务机构都不约而同地设立了“首席数据科学家”的岗位。在“病毒传播”的诉求愈发强烈的背景下,首席数据科学家会不会最终行使总编辑的职能,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数据分析方面走在前沿的是聚合类媒体。以BuzzFeed为例,他们的研究团队开发了监控和优化网络扩散过程的工具。这个被称为Pound(Process for Optimizing and Understanding Network Diffusion)的系统可以对任何一则新闻信息在所有主流社交媒体上的扩散过程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此帮助编辑判断不同情况下何种内容具备病毒传播的潜质。类似的工具在很多新闻机构中都得到了应用。通过这些实时的传播效果统计,数据科学家们可以指导新闻记者如何发掘选题,甚至如何拟定标题、如何措辞、如何选择图片等等。
将数据分析的自动化工程手段引入新闻编辑流程,这个趋势的本质是消除传播效果反馈的间接性和延时性。对受众点击、转发、评论的实时监控和分析能够以最高效率促使编辑室调整内容策略。在传统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信息技术,受众调查相对不那么精确,也不那么及时。然而,正是效果反馈的相对低效率在客观上缓解了新闻工作的市场压力,给编辑室提供了一些自主空间。在这种条件下,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才有可能在商业化传播中保留一席之地,使知识分子们完成对公共议程和大众品味的引导。可惜,在冷酷而高效的数据新闻时代,这种“精英气质”显然已经失去了立足空间。
价值和责任感的衰落很快就体现在日常的内容制作过程中。对于编辑记者来说,新闻产品的“形式感”“体验性”“可视化”“互动性”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在受众互动组加入之后,编辑室内讨论最多的已经不是新闻的选题价值和采写质量,而是什么样的内容和形态更容易引发受众的点击和转发。如今,很多新闻机构甚至要求记者在报告选题的时候同时报告作品的呈现方式和预期传播效果。简洁的信息列表被认为是不错的手段,大量图片的使用更是被提倡,而游戏、问答等带有互动性的手段也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原来记者们所追求的是发表那些有社会效益和舆论影响力的作品,而当下他们则专注于怎么样使用一个H5软件制作出“10万+”的帖子。为了批量生产病毒传播作品,主流大报和通讯社争相建设“中央厨房”全媒体报道平台,并将它作为新闻机构应对新媒体环境主动创新的核心成果。在新闻界这股风气的带动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VR、AR、无人机等新的表现手段在这个行当中会如此受到追捧。仿佛忽然之间,越来越多充满社会责任感的编辑记者变成了时髦的技术控。
当我们忽视产业结构变化而专注于业务领域的实践时,很容易将新闻编辑室的这些变革看作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技术进步和业务创新。实际上,当前新闻业的主流观念也确实如此。一种颠覆传统的强烈快感伴随着让人眼花缭乱的新工具、新名词,在新闻界四处弥漫。在这种状况中,抽离视线的反思是很困难的。然而,一旦我们看清了新闻产业后工业化转型的实质过程,就很难再将编辑室的改革看作是主动的创新和进步。在权力流散的过程中,所有新闻内容生产者的选择都是被动的,如果用专业的伦理标准和现代价值来衡量,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些改革称作一种逐渐堕落的“竞次传播”的现象。
三、专业主义的挽歌
在技术升级和媒体融合成为主流话题的当代新闻界,很少有人顾及职业群体及其实践理念的变化。然而,正是这些新闻业变革中常常被忽视的软性因素将对未来社会的舆论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专业主义的命运,理应成为我们思考媒体转型问题的一个落脚点。
将近两百年前,伴随着各种争议和鄙夷,面向大众市场的商业媒体开始出现并逐渐繁荣。从那时起,新闻记者们就迫切希望向公众展示他们的自主性、专业性和进步性,以此塑造职业荣誉感,提升行业门槛,从而稳定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而媒体机构则需要获得良好的社会信誉和权威性,以此得到公众的授权和持续的消费。因此,传媒业的大亨们一直乐于提倡记者的专业主义理念,并愿意维持记者一定的自主空间,即便这些做法在短期内会减少获利的手段,降低获利的效率。经过长时间的实践磨合,新闻记者的专业主义理念和新闻产业的增殖逻辑之间一直维持着微妙而默契的平衡。
在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中,这一切都显得十分自然,十分合理,以至于人们常常忽视其存在的各种历史条件。当历史条件变化时,平衡自然会被打破。
在专业主义诞生的19世纪晚期,欧美新闻产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而几家报业集团主导新闻市场的寡头垄断局面将竞争的激烈程度维持在可控范围内。这个时代的媒体垄断,是纵向整合的全产业链垄断,媒体集团对产品的最终形态有着相对自主的决定权,保持着一定的权威性,而并不完全服膺于大众市场。寡头垄断的局面让同一行业中几个主要商业实体间更容易构建共同的伦理规范和市场规则。此时,维持专业的权威性和占领更多的广告市场基本是正相关的关系。这个新闻产业的黄金年代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它让媒体机构有足够的主动空间来容纳新闻人的知识分子气质和社会责任诉求。
然而到了当前的数字化时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击碎了行业的壁垒,成本高昂的全产业链运营成为历史。平台型企业通过垄断内容产品分销权,将专业媒体机构打入产业价值链的下游,从而有可能以极低的成本在传播形式和内容上掌握主动、设置规范;与此同时,他们通过投资和兼并将一些内容生产业务纳入自己的版图,通过集团内部的交叉补贴解除新闻生产的短期盈利压力,以此培植有舆论影响力的媒体,为企业的长期目标服务。在这个时代,资本控制的集中性、隐蔽性和内容生产的分散化、小型化是一个显著趋势。传统新闻机构落入内容生产市场的汪洋大海。极端激烈的竞争局面让市场主导成为唯一的选择,没有哪个内容生产商能够容忍专业主义标准所需要的成本和耐心。
除了产业结构方面的影响,在社交化和数字化的变革中,以往新闻机构所忌惮的社会道德约束和媒体监管机制正在失效,这也是专业主义面临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下,媒体机构的行为很容易得到观察和监控:从记者的采访,到编辑部的结构和工作流程,再到出版发行和广告运营,每一个环节都在社会生产和交换的“前台”完成。
然而在数字化时代,不仅内容生产主体的数量无限增多,而且内容传播的整个流程几乎都被转换成一套不透明的后台程序。大数据化与机器算法与其说是用科学来代替人工,不如说是用隐蔽来代替公开。这种信息传播“后台化”的趋势与网络信息发布主体的匿名性结合在一起,使得对新闻内容进行审查和问责的成本变得极为高昂,而传播危险、偏颇、媚俗信息的成本则变得极为低廉。不仅如此,垄断了产品分销权的平台型企业还常常以自己不是内容生产主体为理由规避传播过程中的责任和风险,这给传统的媒体规制手段带来了更多尴尬和困难。
前面讲到,传统媒体机构之所以能够主动地维护专业伦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需要建立商业媒体的政治合法性,以此获得社会赋权,运营传播产业。如今,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带来了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低的广告收益,还带来了社会道德约束和公共审查的失效。在这样的传播生态中,新闻机构恐怕再没有条件、也没有理由继续维持各种传统的伦理和责任。当理想、尊严的保障和经济安全的保障一道消失,大批离职的新闻记者已经用行动唱响了专业主义的挽歌。
当然,除了产业结构方面的条件,政治气候和政策导向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闻人群体专业共识的形成。在专业主义诞生地美国,19世纪晚期的进步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时期的广泛政治共识都是影响新闻记者思想观念和实践范式的外在环境。正如丹尼尔·哈林(Daniel C. Hallin)所言,“广泛的社会共识曾经让新闻记者感受到他们可以成为精英政治体系中的一员,与此同时还保有中立和独立的品质”。⑦自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进程开启以来,这种经济安全条件下才有的从容和优雅就开始面临威胁。到了今天这个疯狂的网络经济时代,现代价值在新闻业中恐怕已经没有立足的空间了。如果像哈林所言,新政自由主义时代的新闻业是“高度现代性”的,那么当下的新闻业可能正在进入一个“高度后现代性”的时代。
在挑剔的批评者眼中,专业主义可能只是商业媒体赤裸裸市场关系的遮羞布。的确,与那些对专业主义持简单赞扬态度的观念保持距离是有益的——专业新闻记者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很多进步性的作用,但是都市职业阶层的历史处境和商业新闻生产者的功能属性还是限制了他们呈现社会问题的立场与视野,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只能是维系资本主义法权制度的建制派。然而,作为传统新闻生产中的把关中枢,这个职业知识群体和他们秉持的专业标准一旦被抽离出信息传播的过程,必然会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正如专业主义的诞生映射出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巨变一样,专业主义的衰退也意味着一个新的传播生态和政治环境的出现,它绝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忽视的问题。
随着传统新闻业实践范式的消逝,新媒体时代的很多社会政治特征都开始浮现。例如,由于缺少了职业记者群体这个社会冲突的减压阀和调停者,我们已经在近年来的网络舆论中发现了极端化和民粹化的趋势;在权威信息源趋向弱势、信息传播隐蔽性逐渐增加的背景下,舆论安全和社会动员都成为棘手的治理问题;缺少了专业知识精英的把关,信息的无限过滤和个人定制可能正在带来公共知识的衰退等等,无论学者们的价值判断如何,新闻专业主义在信息传播领域的退场都将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值得深入讨论的现实问题。■
注释:
①在传统媒体经营业绩下滑方面,有两个统计数据可以参考:麦肯锡公司的调查显示,从2011年到2014年,全球印刷媒体的年收入以3.6%的速度跌落,累计降低收入220亿美元。参见: McKinsey & Company. Global Media Report 2015:Global Industry Overview. P.21. www.mckinsey.com/client_service/media_and_entertainment.皮尤中心的统计发现,美国2015年纸媒的经营业绩出现了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双双迫近10%的明显下降。在美国经济回暖的背景下,传统新闻业却出现了近五年最惨重的衰退。参见:http://www.journalism.org/2016/06/15/state-of-the-news-media-2016/. 在中国,都市报的经营状况是新闻业市场化的风向标。这个十余年前风光无限的朝阳产业如今却常常被冠以“断崖”、“坍塌”、“崩溃”等骇人的形容词。
②据统计,在美国,仅2014年一年,传统新闻从业者的数量就缩减了十分之一,与20年前相比已经减少了近四成。随着媒体并购和裁员的消息不断传出,这一趋势将加速发展。参见:MICHAEL BARTHEL. Newspapers: Fact Sheet. http://www.journalism.org/2016/06/15/newspapers-fact-sheet/. 在中国新闻圈,记者跳槽、转行的消息也是不绝于耳。社交平台领英(LinkedIn)对中国媒体从业者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5年中,媒体从业者年均跳槽率增长达到4.5%,人员流失在2015年达到峰值,跳槽率高达13.45%。在跳槽的媒体人中,21%的人选择了流向互联网等高科技行业,而专业服务类公司(如公关公司、广告公司等)则以18%的占比紧随其后。参见,任晓宁,“媒体人跳槽都去哪儿了? 互联网等高科技行业最受青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16年7月19日。
③Pew Research Centre. News Us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2016. http://www.journalism.org/2016/05/26/news-use-across-social-media-platforms-2016/
④Pew Research Centre. Facebook Top Source for Political News AmongMillennials. http://www.journalism.org/2015/06/01/facebook-top-source-for-political-news-among-millennials/
⑤A.G. Sulzberger. etc. “The New York Times Innovation Report”. 2014.3. p.24.
⑥Ibid. p.4.
⑦Daniel C. Hallin. “The Passing of the “High Modernism” of American Journal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2. 42(3): 17.
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