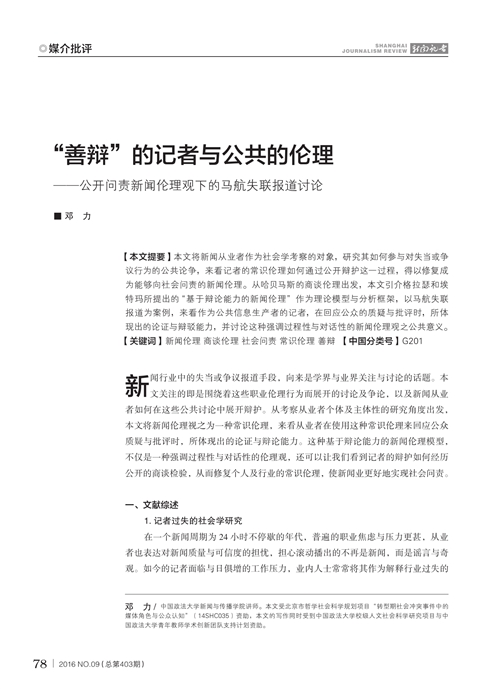“善辩”的记者与公共的伦理
——公开问责新闻伦理观下的马航失联报道讨论
■邓力
【本文提要】本文将新闻从业者作为社会学考察的对象,研究其如何参与对失当或争议行为的公共论争,来看记者的常识伦理如何通过公开辩护这一过程,得以修复成为能够向社会问责的新闻伦理。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出发,本文引介格拉瑟和埃特玛所提出的“基于辩论能力的新闻伦理”作为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以马航失联报道为案例,来看作为公共信息生产者的记者,在回应公众的质疑与批评时,所体现出的论证与辩驳能力,并讨论这种强调过程性与对话性的新闻伦理观之公共意义。
【关键词】新闻伦理 商谈伦理 社会问责 常识伦理 善辩
【中国分类号】G201
新闻行业中的失当或争议报道手段,向来是学界与业界关注与讨论的话题。本文关注的即是围绕着这些职业伦理行为而展开的讨论及争论,以及新闻从业者如何在这些公共讨论中展开辩护。从考察从业者个体及主体性的研究角度出发,本文将新闻伦理视之为一种常识伦理,来看从业者在使用这种常识伦理来回应公众质疑与批评时,所体现出的论证与辩论能力。这种基于辩论能力的新闻伦理模型,不仅是一种强调过程性与对话性的伦理观,还可以让我们看到记者的辩护如何经历公开的商谈检验,从而修复个人及行业的常识伦理,使新闻业更好地实现社会问责。
一、文献综述
1.记者过失的社会学研究
在一个新闻周期为24小时不停歇的年代,普遍的职业焦虑与压力更甚,从业者也表达对新闻质量与可信度的担忧,担心滚动播出的不再是新闻,而是谣言与奇观。如今的记者面临与日俱增的工作压力,业内人士常常将其作为解释行业过失的原因,例如《纽约时报》杰森·布莱尔的自传《我在〈纽约时报〉的日子》便如是说。①同时新媒体的出现令全球新闻产业都面临急速变迁,新闻行业的变化与对生产新闻速度的要求,使得记者行业出现了一种“去技术化(de-skilling)”的现象,即节约劳动力的新技术、对记者多种技能要求出现,而团队工作越来越少。②如此不尽如人意的工作环境对于新闻业的标准是否会有所威胁?压力与焦虑是否会导致更多失误,而这些失误又会如何影响当下的新闻工作?
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一个应首先回答的理论问题是如何理解行业中的错误。社会学家贝克认为,一种职业当中之所以存在违背伦理的行为,更多来自这种职业的社会结构而非成员的人性缺陷。③在一项针对律师行业的研究中,休斯提出“劳动的道德分工”(moral division of labor)的说法,他认为一种职业的系统运转,需要那些所谓的“坏分子”完成某些工作。④这些研究结论提醒我们,对于一些职业而言,违背伦理的错误行为已经根深蒂固,成为其日常运作的一部分。这种将错误视作新闻工作中“正常”的一部分的结论,无疑出自功能主义理论取向。而媒体行业从业者亦有如此观点,他们认为一些错误是为了完成工作而不可避免的,一些错误行为成为了可以接受的行为。⑤类似的现象曾出现在犯罪研究中,当某些社区的成员觉得越轨现象广为存在,此时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效力降低,何为可被接受行为标准发生变化,道德标准降低,学者将其概念化为“道德腐蚀”或“降低越轨底线”(defining deviancy down)。⑥
具体以新闻业中的失误为研究对象,一种研究取向是从新闻组织角度出发,来看错误行为是否以及如何被处理,在何种程度上被媒介组织容忍或允许。比如长久以来,媒介组织就使用新闻更正(news correction)的办法,以示对错误负责。⑦在当今的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更正的意义更为复杂——新闻从业者可以更为快速地处理错误,而新闻受众自发进行公共的新闻核实。⑧有研究者对媒介组织的新闻更正做内容分析,伴随现代媒介组织的发展,标准化与正式化的新闻更正成为了新闻业中的常规之一,各国的新闻更正文本也反映出不同国家与社会中媒介体制的差异。⑨这些研究更多强调的是媒介组织机构如何处理错误(比如除了内容分析外,对从业者的深访也以采编部门负责人为主,而非犯错记者本人),这种考察角度,是从新闻业的社会学研究取向出发,将记者作为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一员。
为探索新闻业中失误的意义,媒介学者迪金森提出另一种研究角度,倡导应重新将新闻学研究的重心放到记者个体及其主体性上来。有别于新闻业的社会学研究,迪金森提出了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学研究(sociology of journalists),试图在全球新闻产业都面临急速变迁时,为传媒行业的社会学考察再次注入生命力。⑩以从业者为研究中心,这一理论取向认为记者不仅仅是新闻常规与新闻风俗的遵循者,而是一群社会行动者,他们的社会行动不能够完全由媒介学者给出的新闻工作的社会学面向如应然性职业准则、机构束缚、同僚压力等概念所完全解释,而应将其视作一种独特的职业类型,他们的劳动形态也是独特的、不断变化的,他们的日常新闻判断也不仅仅是受到各种政治经济、组织、消息源、管制等因素影响之后的结果。
因此,在考察失误行为时,研究者的重点不应止于分析新闻工作如何受到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而应观察个体记者差异及其改造的可能性,展示对记者主体足够细致和足够接近的考察。迪金森认为,那些记者“犯错”的例子提醒我们,在研究他们的新闻实践时,可以将其理解成为一种行业雇员的社会行为,而这种行业的劳动状态随着工作状况压力俱增而日益严峻。对新闻实践中错误的研究,需要了解错误如何发生、在何种环境下发生。在他的理论取向之下,应探讨的相关研究问题包括:这些犯错记者的实践行为如何被其他记者评价,这些行为是否以及如何被处理,而这些行为在何种程度上被其媒介组织容忍或允许?记者如何习得工作常规,按照上级和同事可接受的方式做新闻,如何被监督,错误对其职业有可能造成哪些影响?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更强调对更为寻常(甚至在某些新闻生产语境下成为常规)的过失现象作出社会学解释。这样考察职业过失,可以看到记者是如何在内外部的规制与伦理准则之下行动的,同样,也可以提供一种关于记者社会化,如何实现其工作角色的实证研究思路。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能让我们更明晰错误如何发生、在何种环境下发生,还揭示未来可能发生错误的频率;而避免仅仅通过研究得出将错误视作新闻工作中“正常”的一部分的结论。[11]这种研究思路,也是新闻学研究近来越来越强调记者主体性而不是新闻生产结构性的一种趋势的体现。
2.新闻伦理作为一种常识伦理
如何在新闻从业者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内,从记者个体及其主体性出发来研究媒介失误?有研究者提议应关注新闻伦理的日常实践层面,而不要止步于静态的应然准则层面。[12]以从业者为研究对象,我们对新闻伦理的理解似乎不再应该仅限于那些需要遵循的抽象准则,与其对伦理或非伦理的新闻实践进行区分,不如讨论如何实践伦理。从实践的层面出发,西奥多·格拉瑟和詹姆斯·埃特玛将新闻伦理视为记者的日常道德实践与反思,是一种“常识伦理(common sense ethics)”。[13]从常识入手,可以回答新闻业的原则性伦理价值从何而来,以及这些原则性伦理价值与局部实践之间有何种关系的问题。
在新闻业这一现代职业当中,常识是日常知识的主要来源,受常识影响的从业者,一般不会考虑逻辑上存在的不同安排有哪些,而是依靠一些“惯用选择”或习以为常的方式来下判断。因此,常识为行动提供的是合适的“引导”,而非合理的“思考”。葛兰西称常识一般停留在保守的实然层面上,其特征是“狭隘的、无批判力的、不连贯完整且矛盾重重的”。[14]虽然常识缺乏严谨与理性,但我们不能由此将其全然抛弃,因“我们的道德判断最为直接地依赖着日常直觉”。[15]根据伽达默尔的常识理论,常识之所以产生,来自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的经验,并往往由共同体之结构与目标所决定。常识代表了一种共享的判断,所以常识中的道德因素,既是个人的道德判断,也是一种总是心怀他人的判断。[16]新闻从业者心怀职业共同体或社会共同体的道德常识,即是累积其伦理知识的来源。伽达默尔认为常识并非一种“正式能力或智识才能”,从常识到知识的转化,来自具体的个人行为情境。因为无从判断下个情境,便不可能抽象地知晓对错,而只有在遭遇某种情境的过程中,才得以获知哪种做法是正确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以及不断重复的类似过程中,人们培养了道德反思与自我认知的能力,发展并完善思考,使得常识中的实践智慧开始接近于一种知识形态。“伦理来自于,但不止于常识”,作为典型的常识伦理,新闻业的伦理知识并非某种可提前预知、可传授或可获取(acquire)的客观技能或知识,而是一种情境化的知识。[17]那么从实践的维度来思考从业者的职业失误时,研究应该关注的是,当具体特殊情境发生时,从业者是否拥有并有能力去应用伦理知识来应对,并通过这些过程,发展出道德反思与自我认知的能力。
3.新闻伦理的公共面向
有研究者就以从业者为研究对象,通过记者访谈,来讨论有伦理争议的个案,研究发现即使某些错误被常规化与合理化,从业者能够体现出伦理自觉与反思能力。[18]上文已说过,记者需要经历一个运用常识判断对错并加以反思的过程来发展伦理知识,然而这一反思过程并非个人自省,更多是社会性的,从业者心怀的共同体也要超出职业共同体的狭窄范畴。
实际上,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伦理规约在“负责”(Be Accountable)这一条下的五条要求就涉及了职业共同体之外的公众。新闻记者应该:(1)澄清和解释新闻报道,就新闻界的行为邀请公众对话;(2)鼓励公众说出他们对新闻媒体的不满;(3)承认错误,并迅速纠正;(4)揭露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不道德行为;(5)同样遵守对他人提出的高要求。[19]学界也越来越强调新闻伦理的公共面向:有研究者强调新闻伦理的目标是接受社会问责,即要判断从业者的行为是否符合伦理,必须与公众对话,经得起社会公议;[20]技术发展与公众期待让新闻业必须与公众的媒介批评对话;[21]新媒体的出现也令新闻伦理需要超越封闭的职业伦理,成为关照公众的具有开放性与对话性的伦理。[22]在诸多定义中,格拉瑟和埃特玛提出一种最为激进与民主的伦理概念,认为伦理的讨论不应只存在于专家或机构之中,甚至也应超出从业者用来抵御外在压力的专业伦理规范,要将伦理讨论置放入更大的共同体当中。他们认为,新闻业中的伦理规范及其应用话语,虽然常常谈及“公众”或“公众利益”,却鲜少有公众参与到某个规范的确立、应用与修订当中,公众的利益也只有在与新闻行业相同时才被提及。[23]舒德森曾说,从新闻业的本质上看,它缺少面对公众质询的机制,没有像其他机构那样必须受到公众评议或管制性公共政策的约束;换言之,记者即使有着对工作的反思,也不会经历以落实到行业政策为目标的规训式检验。[24]詹姆斯·凯瑞也曾说美国传媒界缺少一种“持续成体系的有智识水平的媒介批评”。[25]即使有高质量的媒介批评,它们也常以专著或期刊文章的形式出现,无法让记者参与进来,去讨论新闻室中的规范及其日常的应用。而媒体人对自身所面临的矛盾处境或解决办法的思考总结,也只能以独白形式发表,而仍然缺少对于媒介批评进行反思并回应的公共争论的锻炼。高质量的媒介批评与从业者公共答辩不仅少见,其互动更是稀缺,这种描述对于中国传媒界而言同样准确。为改变这种现状,让其他机构或个人的观点进入到新闻业伦理规范的讨论,让记者对工作的反思得到公共检验,格拉瑟和埃特玛提出了一种基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discourse ethics)的新闻伦理概念。
4.基于商谈伦理的新闻伦理观:辩论对常识伦理的修复
此前提到常识是伦理知识的基础,但究竟如何从实践中提炼出原则?哈贝马斯提出应该在公共开放的讨论中使常识得以修复(rehabilitation),商谈伦理则不仅是审视常识,也是重建常识的机会,令常识除了有用,也可进行辩驳(defensible)。公开辩护“为那些必须要自己解决所面对的道德实践问题的人们提供空间”,辩护并非独白式或个人化的,而是社会性与对话性的。[26]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倡议一种“论争的合作过程”,这个过程有助于“信息、理性与相关词汇的交流与评价”。商谈伦理强调一个要经过审议而取得理性共识的过程,与传统伦理理论依靠的是与涉及对错的假设探讨或个人沉思不同,它对“理性(reason)”和“合理性(rationality)”的定义,不再停留在个人层面,而是强调其社会特性。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新闻伦理,则将争议与分歧视为一种机会,能让受到媒介行为影响的所有人参与到公共讨论中来,而记者则承担起公开坦率回应的职责。新闻业的伦理或道德准则的有效性,就必须通过公共开放的商谈检验(discursive test)。只有如此,才能够将新闻业实践与新闻业原则结合起来,使新闻业的运作经受一个真正的公共论证的过程,这即是格拉瑟和埃特玛所提出的“符合伦理即向社会负责”(being-ethical-means-being-accountable)的新闻伦理观。[27]在确定了道德实践理性的本质上是交流性的、主体间性的之后,在商谈伦理的框架下,格拉瑟和埃特玛提出以善辩(eloquence)这一概念来取代权威:重要的不再是谁说,而是说了什么、说得怎样。在相关道德规范所需经历的商谈检验中,说话者不论身份如何,起作用的只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更佳论证的力量”。更佳论证通过辩论与讨论得以生发,在回应他人的论断、反击、建议或反对的过程中,其结果不在于赢得争论这一比赛,而在于最终获得相关人士的最为广泛的赞同。新闻从业者能够做到向社会负责,意味着当公众对于其行为的合理性不依不饶时,能够面对质询,公开呈现其所作所为并解释原因。此时,伦理便基于一种沟通的能力,这种沟通能够彰显出行为背后的判断,以及判断背后的原则;由此,新闻伦理也就基于记者与最值得回应的媒介批评之间相抗衡的善辩能力。[28]格拉瑟和埃特玛的研究中,就访谈了若干知名调查报道记者,访谈的问题涉及两个与消息源有关的日常性的实践原则,一个是能否秘密录音,一个是能否在采访时隐藏记者身份。相较于不能捏造事实、不能抄袭等非常明确的是非选择,这两个伦理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记者对这些话题并未形成一个伦理层面的确定态度,因此被问到的时候,他们并不能提供一个准备好的公认道理,而会动用常识性伦理。多数受访者的伦理思考虽然合理却不甚连贯,这种情况下,受访者展现出不同的辩护能力。某位记者选择了一种立场之后,却在访问者追问时,无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立场。而另一位记者体现出较强辩护能力,正是因为他曾经在公开讨论中接触并回应过相关问题。这位记者回想起自己对于秘密录音的看法曾经发生过转变,是在一场调查记者与编辑的讨论会上,“与同行交谈,遇到了不同观点,想了想对方是否正确”;除了同行意见,他/她对伦理问题的观点,也来自“与其他职业者的交流,来自读者、邻里的反馈”。[29]这两位记者的访谈材料正说明了新闻业伦理作为常识伦理的实践性:伦理教育并非来自对伦理规则的机械学习,而是开展辩论,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使原本可能存在种种缺陷的常识得以修复。
善辩不仅仅是从业者的一种能力,而且是从新闻实践中提炼出原则的机会。作为从业者,他们对公众的辩论即使到最后不一定能达成共识,但这一过程本身仍有助于那些有反思性的记者,从而提高新闻业的水准。作为研究者也是如此,与其用伦理手册上的条条框框来对从业者的行为下判断,不如去考察从业者在涉及新闻伦理的事件中表现出的辩论能力,分析媒体人如何回应公众质疑与批评,同样也是在鼓励媒介在公共讨论与公共生活中扮演应有的角色。
5.新闻伦理规范的商谈检验
格拉瑟和埃特玛所提出的“符合伦理即向社会负责”的新闻伦理模型,一方面是强调从业者实践与公共辩护能力的伦理理论,另一方面也可成为用来衡量从业者表现的分析工具,来考察相关事件中的讨论或辩护是否满足商谈伦理概念所提出的要求。
首先,商谈伦理强调“论辩的合作过程”,那就意味着讨论要满足两个本质特征:一个是“准入”(access),即辩论的开放、自由。开放意味着只要是受到了相关规范或原则影响的人即可参加。这里的自由包括消极自由——没有强迫或宰制的外来压力;也包括积极自由——人们受益于由于交流而创造的更好的沟通机会与条件。另一个是“论辩”(argumentation),它提倡一个真诚对话的观点交换而非策略性的目标导向(比如实现影响力、服从或控制)。在商谈伦理的原则下,个人并非寻求自身利益,而是寻求共同利益。争论以共识或妥协为目的,是理性、公平、合理的处理方式,争论使参与者得以采取哈贝马斯所称之“互惠视角”(reciprocal perspective taking),或达成伽达默尔所称之“同情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从而实现社会团结与社会协作。[30]以上两项是实现商谈伦理的论辩形式的要求,而对论辩内容同样有两个方面的衡量。两位学者将关于规范的讨论分成两种论述形式,即“证立性论述”(discourse of justification)与“适用性论述”(discourse of application)。[31]关于规范的证立性论述涉及普遍原则的有效性,而适用性论述则涉及这一规范运用于某个特定判断时是否恰当。这两种论述往往相继出现,当证立性论述结束之时,适用性论述便开始了。而这一对论述之间的转换,也暗示着“抽象原则”与“具体情境”的难以分离:抽象原则难以独立于具体情境而存在;而在应用抽象原则时,个案也并非归属于原则,而是对规范的进一步解读。
这一对论述形式即可作为分析工具来使用,仍用以上记者访谈的例子来说明:在讨论能否接受秘密录音时,有记者使用了“事实准确性”原则,这一规范是通过新闻业中长期的讨论所确立起来的证立性论述;但在秘密录音的具体情境的讨论中,记者对此规范的适用性论述却显得欠缺辩驳力。因为此时,这一规范并不完全适用于秘密录音的伦理情境中。所以普遍来讲,当某一规范在此行业被更牢固地证立清楚时,或某一规范更适用于某情境时,辩护者便能够更为善辩地论证自己对于某争议性操作手法的看法。如此,这两种论述形式,即是商谈理论所包含的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及适宜性这两方面的考察,便构成了判断记者论辩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
二、案例选择:采访马航遇难者家属的合理性辩论
本文以新闻从业者对马航失联报道中采访受难者家属这一争议报道手段的讨论作为考察内容。选择此事件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马航事件构成了一个对从业者的记忆与反思程度较为深刻的热点事件。新闻业中热点事件(hot moment)的意义,不仅在于事件本身的不普通,导致事件及相关报道造成很大影响,甚至能造成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而对于记者群体而言,热点事件也会影响他们的职业行为标准,并有利于其职业发展。[32]一项对记者如何记忆的研究表明,对于记者个体而言,所谓的热点事件对于不同媒体的记者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不同的影响。[33]本文选择马航事件这一国际重大事件的报道作为案例探讨,因为这是不少媒体记者能够参与到国际突发事件报道的少有机会。
选择这一事件的另一原因是,该事件报道周期较长,关心此事的人们对中国记者与国际同行的报道表现作出比较与评判,引起了新闻业界与公众对报道争议手法的讨论。马航失联事件的报道过程,甚至本身也成为了新闻内容,比如2014年3月19日《法制晚报》便有题为《〈纽约时报〉记者批露马航事件报道幕后故事》的报道。在这种情况下,记者的采访行为、采访中的争议与失当行为,都被公众聚焦,并引发了新媒体平台上的讨论。其中,因为灾难事件的属性,采访家属问题,便成为此次事件所代表的灾难事件的典型争议点。
由于以上原因,马航事件的公共讨论便为本研究提供了可使用的研究材料。首先这一事件要求记者在公开平台进行回应,而且这些回应不仅仅是抽象地谈论业内或同行的常规做法,而是要为自己所作出的报道行为进行解释与辩护。其次,不少亲自参与报道的记者作出长文反思,与报道手记等个人反思的独白式文章不同,这些文本更多意义上是在与同行及公众对话,关心此事或受影响的人也可从互联网上获取,因此可被看作是面向公众的文本。这些来自不同从业者的文本提供了较为恰当的素材,能够让我们看到叙述与辩护,以及其中体现出的思考过程与辩护能力。这种有着较长周期反思过程的新闻事件,较之一般事件,更会调动记者对自身职业规范进行一次重新建构。
参与马航失联报道的记者当中,不少人都面对了公众及同行提出的是否应该采访遇难者家属的质疑。汹涌而来的质疑一大部分出现在互联网,新媒体平台让新闻生产过程对公众而言更为透明,公众所认为的“失当”或争议行为也更易受到批评,记者便被迫将自己的伦理思考公之于众。本文的研究材料即来自网络众议与同行讨论过后,从业者如何回应。具体而言,本文分析《南方传媒研究》上三位记者论述是否应该采访遇难者家属这一议题的三篇文章,[34]这些文章长短不同,却是每一位记者在采访或观察此新闻事件过后,经历了质疑,并与同行或网友辩论之后,写成的较为完整的文字回应。实际上文中某些内容在正式发表之前,便已由作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并引发讨论,所以这些文字中不仅有对自己采访报道经历的叙述与辩护,也有在比较所听到的不同意见或质疑之后,在反思与总结之后所形成的论述,因此呈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提出主张再加之论辩的过程,成为本文理论框架下较为合适的分析材料。与格拉瑟和埃特玛对于调查记者的访谈类似,本文重在展示如何运用前述所提出的理论分析模型,对从业者较为典型的论辩过程与论辩能力作出分析。
三、案例分析:回应公开质疑的商谈检验
从业者A的报道《第84号乘客》即以其中一名马航失联乘客为新闻主角,这篇报道也成为该记者所在媒体微信公号史上当时传播率最高的稿件,但“在某些批评者眼里,《第84号乘客》没有任何价值,他们追问的是记者为何不去彻查并报道事故原因”。这一质疑并非直接批评其报道行为失当,而是提出采访家属是对媒体资源的浪费,她的回应是“作为人物记者”应当更多“记录人”,所以需要“把新闻人物放到背景中去理解”。其采访过程还有个插曲,另一家媒体记者指认她“在不告知采访的情况下采访了画家的同事,违背职业规范”,虽然后来证明是误解,但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的感受是“猜疑、谜团、谣言与混乱”,也体会到整个事件过程中的媒体普遍所受到的指责:“先是谴责媒体骚扰家属,终于发展到对中国媒体在国际竞争中完败的不屑、指责和叹息。”对于“骚扰家属”这一普遍的指责,A并未在文中直面回应,而是一一叙述自己的采访过程与手段。作为人物记者,采访受难者家属对于她而言并非失当行为,采访家属是“记录人”的必然选择。但她仍然为采访家属行为中的失当与否划定了界线,间接承认了“不告知采访意图”或“刺激家属情绪”是失当的行为:
“我承诺不贸然采访,以免刺激家属情绪。感谢他们的信任,我跟随两天,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也采访了画家的另一位朋友,但观察到其家人情绪很糟糕,我并未提问,只在稿件中呈现了一小段观察。我想这应是采访家属时可以把握的界限。”
A并未对于采访家属是否是失当行为作出更多辩解,而是叙述自己的采访过程及细节,以证明她采访家属的行为在“界限”之内。然而,另外两名记者的讨论便不是如此,双方从各自观点出发,对此议题背后的新闻规范作进一步的阐述,作出激烈的辩论,体现出本文所使用的“符合伦理即向社会问责”新闻伦理模型所考察的辩论能力。
对于灾难事件报道该不该采访当事人和家属,从业者B明确表示“可以采”。他认为在公众知情权的让渡之下,媒体应发挥资讯散布功能(disseminator)和解释与调查功能(interpretive)的功能,这二者都是早已在新闻业界得到证立的原则,即一套较为稳固的“证立性论述”;而灾难报道中的媒体既然要实现这样的社会功能,便应当最为快速和深入地报道更多信息:
“以最快的速度来揭示信息,尽可能地挖掘隐情,是媒体的天职,也是公众知情权的天然组成部分。采写固然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但决无任何理由反对媒体去现场,更无任何理由反对媒体报道灾难内容。”
“新闻是一个很残酷的行业,媒体能做什么,不能解决什么,边界从来都很清晰。按照传播规律,遵循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规则,尽可能快和深入地突破报道更多的信息,就是媒体该做的。”
B所提出媒体应当传播资讯与调查解释的证立性论述,在新闻业已被牢固证立,但对其论辩的考察,还需要看他就这两个行业规范是否适用在采访遇难者家属的伦理情境中的“适用性论述”。这里,B提出一个说法,媒体应当及时传播的信息当中包括了“遇难者家属的悲伤”,受难者家属和灾难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都是媒体进行传播与调查的对象:
“空难事件,出发和到达机场,与空难现场一样,乃至于遇难者生前空间一样,都是敬业记者应该抵达的广义现场。当事人的眼泪,家属的痛苦,和灾难过程、灾难原因等一样,本身就是灾难的组成部分。遇难者家属的悲伤,是命运的无常,也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共同悲伤,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部分,更是追问事件原因与责任最具道义力量的拷问。”
由于B曾经将自己的观点发布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并广为传播,便引发了从业者C在文章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驳斥。C的论述并未质疑其证立性论述,而是从B的适用性论述入手,提出其不恰当之处:
“家属齐聚的首都国际机场及之后的丽都酒店,是否属于‘灾难现场’?显然不是。或者说,两处最多属于见证或感受灾难的现场。在这里,你问不到‘客机如何失踪’,只能问到‘令尊是如何失联的’。17天来的事实证明,失联者家属获取信息的渠道,远远不如媒体。”
“话又说回来,媒体当时派人去守家属倒也无可厚非,从采编流程来说,属于常规动作,只是没必要以‘灾难现场’这种说辞来赋予合理性。”
C并未提出媒体采访受难者家属是失当行为,但他并不同意B以“这种说辞来赋予合理性”,更准确地说,他不认为B所提出的媒体职责适用于采访受难者家属这一伦理情境。从商谈检验的要求来看,C的批评指出了B的适用性论述是薄弱的。他认为B的证立论述“基于受众知情权的媒体报道权”适用到采访受难者家属这个情境中是不合适的,因为公共事件的信息与受难者家属的信息性质不同;
“当事人的眼泪,家属的痛苦如果归属公众知情权范畴的话,那么这项权利又从何而来呢?”
“B没有明确定义‘揭示信息,挖掘隐情’中‘信息’和‘隐情’的具体所指。但我认为,他将灾难过程和原因,与当事人及家属的痛苦眼泪并列,并不恰当。”
除了对不同意见作出辩驳,C还总结了整场讨论中存在两种证立论述的辩论,即“媒体应及时报道事实(基于受众知情权的媒体报道权)” VS “媒体不应侵犯不幸者的隐私权”。他用小标题“正确 VS 正确”来概括,因为这两种证立论述都是广为接受的准则。这种情况在辩论中并不鲜见,而在商谈伦理的框架下来看待这种伦理辩论,要做的并非去分析其中哪一套更为“正确”,而是看实践者如何论述,在运用自己所支持的原则时更为“适宜”。对于整场讨论而言,还可以考察其能否实现商谈伦理的目标:参与者以共识或妥协为目的,由于交流而创造更好的沟通机会与条件。关于整场马航失联报道讨论是否实现了理想的商谈,C的判断是否定的:
“在这场讨论中,我发现存在一个常见的逻辑错误,那就是以‘正确VS正确’,正方宣示媒体的报道权(牵带公众的知情权),反方则主张乘客家属的隐私权,痛斥媒体侵入这些不幸者的生活。双方大部分时间都在各说各话、鸡同鸭讲,权利和道德大词满天飞,形同一场失败的演讲比赛。”
在针对相左观点的辩论与对整场讨论的评价来看,C的长文都体现出较高的辩论能力。回到C对能否采访家属的论述,他虽然不指认这是失当行为,但个人反对这种操作方式,认为采访时的人际互动一定会再次伤害受难者家属。他曾经的一次采访经历令其反思,自述“越来越怀疑当晚我赖以自我开脱的理由”:
“我不认为媒体和公众可以向乘客家属行使所谓知情权,这既荒诞又残忍。正如我认为,任书婷老人那晚完全有权不接受我的采访。”
虽然不少从业者可能都经历过相似的指责或自我的反思,但不一定都作出过公开的论述与辩护,与不同意见较量,吸收来自公众的反馈。从这位从业者对自身采访经历如何影响其观点形成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常识的新闻伦理的特点:从业者从新闻实践中提炼出原则,在公开辩论中回应同行与公众,在反思和回应过程中形成观点。
四、结语
本研究属于迪金森所提倡的对新闻记者这一职业人群的社会学研究,重在从记者主体性出发分析其行业实践。记者因其扮演公共信息的生产者的角色,其过失行为可能最需要公开辩解。本文考察记者采访过程中的过失和争议行为,具体分析记者如何为自己的受争议行为作出辩护。以格拉瑟和埃特玛所提出的基于辩论能力的新闻伦理模型为理论框架,本研究关注记者如何动用“常识伦理”来实践日常的道德判断,也考察新闻业中原则性的伦理价值如何通过公开讨论的商谈检验,使得新闻业得以向社会问责。如案例所示,记者个人公开为自己辩护的过程可以成为一种“伦理教育”,使得原本可能存在缺陷的个人化的常识性道德判断,得以修复成为能够向社会负责的新闻伦理。
在中国新闻业的语境中,既定的伦理原则往往并未被普遍共享或严格执行,高质量的媒体批评与可互动的回应平台缺失,记者的失误或争议行为往往被众人斥责或直接“定性”后受到公开处罚,由于新闻事件往往周期短,这几乎成为周而复始的现象。马航事件的不同在于广大公众的关注,他们即使不是直接相关者,却也表现出对其中新闻操作行为合理性的不依不饶的追问,他们通过新媒体渠道提出公开质询,要求新闻从业者解释原因,而周期较长的新闻事件也允许记者有足够长的时间反思、辩护并成文。虽然这些文章最终通过行业期刊公开发布,但我们也可思考互联网的出现是否使讨论环境更符合商谈伦理的形式要求。对比以前较为封闭的新闻生产过程,互联网使得公众对记者行为的评价更易实现,即使这种强迫从业者面对公众的回应,有时成为工作中要处理的一种负担,但也为新闻行业提供了一种行政处理之外的公共讨论空间。
新闻业没有面对公众质询的规训式检验,但通过回应质疑的商谈检验,可能会实现高质量的媒体批评与从业者的公共答辩之间的更优互动,也督促从业者提炼个人反思,参与公众对话,经过公共论辩的锻炼之后,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实践职业准则。这也正是研究者去讨论记者是否及如何善辩,而不是评判记者行为对错与否的理论意义。■
注释:
①1989Blair, J. (2004). Burning Down My Master’s House: My Life at the New York Times. Beverly HillsCA: New Millennium Press.
②Bromley, M. (1997). The End of Journalism Changes in Workplace Practices in the Press and Broadcasting in the 1990s, in M. Bromley and T. O’Malley (eds) A Journalism Reader, pp. 330–350. London: Routledge.
③BeckerH. (1970). Sociological Work: Method and Substance. New BrunswickNJ: Transaction Books.
④HughesE. (1964[1958]). Men and their Work. GlencoeIL: Free Press.
⑤陈力丹、王辰瑶、季为民:《艰难的新闻自律:我国新闻职业规范的田野观察、深度访谈、理论分析》,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⑥MoynihanD. (1993). Defining Deviancy Down. The American Scholar62 (1): 17–30.
⑦BugejaM. (2007). Making Whole: the ethics of correction.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2 (1): 49-65.
⑧JosephN. (2011). Correcting the record, Journalism Practice, 5 (6): 704-718.
⑨Kampf, Z. & Daskal, E. (2014). Communicating Imperfection: The Ethical Principles of News Corrections. Communication Theory, 24: 165–185. 潘祥辉:《“我们错了”:中国式媒介更正与致歉的政治社会学考察》,《传播与社会学刊》2015年总第 33 期
⑩[11]DickinsonR. (2007). Accomplishing journalism: Towards a revived sociology of a media occupation. Cultural Sociology1 (2): 189-208.
[12]JosephN. & Boczkowski, P. (2012). From principle to practice: Expanding the scope of scholarship on media ethics. Ethical Space9: 16-26.
[13][23][27][28][29][30][31]GlasserT. & Ettema, J. (2008). Ethics and eloquence in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9 (4): 512-534.513.524.525.
[14]Gramsci, A. (1988). An Antonio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readings, 1916-1935David Forgacs (Ed.)New York: Shocken Booksp. 346.
[15]HabermasJ. (1993). Application and Justification: 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 Ciaran P. Cronin (Trans.)CambridgeMA: MIT Pressp. 22.
[16][17]GadamerH. (1988).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 ednJ. Weinsheimer and D. G. Marshall (Trans.)New York: Continuum.
[18][20]刘蕙苓:《数位汇流下的伦理自觉与抉择:以台湾电视记者引用新媒体素材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2015年总第 33 期
[19]The Code of Ethics of the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revised in 1996http://www.spj.org/ethicscode.asp.
[21]FeigheryG. (2011). Conversation and Credibility: Broadening Journalism Criticism Through Public Engagement.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6 (2): 158-175.
[22]WardS. & WassermanH. (2010). Towards an Open Ethics: Implications of New Media Platforms for Global Ethics Discourse.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5 (4): 275-292. Ward, S. & WassermanH. (2015). Open Ethics: Towards a global media ethics of listening. Journalism Studies16 (6): 834-849.
[24]SchudsonM. (1995).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 30.
[25]Carey, J. (1974). Journalism and Criticism: the case of an undeveloped profess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36 (April): 227-249.
[26]HabermasJ. (1990). Communicative Ethics and Moral ConsciousnessChristian Lenhardt and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Trans.)CambridgeMA: MIT Pressp. 211.
[32]Zelizer, B. (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0 (3): 219–237.
[33]MannikL. (2015). Writing Individual Journalist's Memories into Collective Memory. Journalism Studies16 (4): 562-576.
[34]这三篇文章在正式发表后在互联网上可见:林珊珊(2014)。《马航事件中,作为一名人物记者……》,见http://www.nfmedia.com/cmzj/cmyj/jdzt/201405/t20140512_363705.htm;石扉客(2014)。《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记者报道灾难现场》,见http://www.nfmedia.com/cmzj/cmyj/jdzt/201405/t20140512_363707.htm;孙旭阳(2014)。《无力尽数展现又以展现为业》,见http://www.nfmedia.com/cmzj/cmyj/jdzt/201405/t20140512_363706.htm。
邓力/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本文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转型期社会冲突事件中的媒体角色与公众认知”(14SHC035)资助,本文的写作同时受到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与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