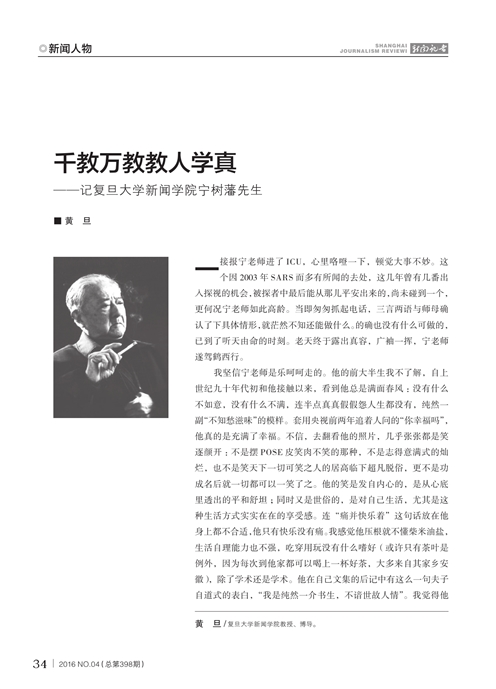千教万教教人学真
——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宁树藩先生
■黄旦
一接报宁老师进了ICU,心里咯噔一下,顿觉大事不妙。这个因2003年SARS而多有所闻的去处,这几年曾有几番出入探视的机会,被探者中最后能从那儿平安出来的,尚未碰到一个,更何况宁老师如此高龄。当即匆匆抓起电话,三言两语与师母确认了下具体情形,就茫然不知还能做什么。的确也没有什么可做的,已到了听天由命的时刻。老天终于露出真容,广袖一挥,宁老师遂驾鹤西行。
我坚信宁老师是乐呵呵走的。他的前大半生我不了解,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和他接触以来,看到他总是满面春风:没有什么不如意,没有什么不满,连半点真真假假怨人生都没有,纯然一副“不知愁滋味”的模样。套用央视前两年追着人问的“你幸福吗”,他真的是充满了幸福。不信,去翻看他的照片,几乎张张都是笑逐颜开:不是摆POSE皮笑肉不笑的那种,不是志得意满式的灿烂,也不是笑天下一切可笑之人的居高临下超凡脱俗,更不是功成名后就一切都可以一笑了之。他的笑是发自内心的,是从心底里透出的平和舒坦;同时又是世俗的,是对自己生活,尤其是这种生活方式实实在在的享受感。连“痛并快乐着”这句话放在他身上都不合适,他只有快乐没有痛。我感觉他压根就不懂柴米油盐,生活自理能力也不强,吃穿用玩没有什么嗜好(或许只有茶叶是例外,因为每次到他家都可以喝上一杯好茶,大多来自其家乡安徽),除了学术还是学术。他在自己文集的后记中有这么一句夫子自道式的表白,“我是纯然一介书生,不谙世故人情”。我觉得他还是有自知自明的。他如己所愿证成了自己,没有理由临走时不开心。
宁老师是有福气的。记得在那年《宁树藩文集》出版发行的仪式上,不少知情人直言,这本文集蕴藏着宁师母的巨大功劳,亏了她里里外外一把手,使得宁老师可以无虑衣食沉迷书房。不过我总觉得这也是相得益彰,用现在的口水学术话语,是互相建构的。外在条件固然需要,个人品性和趣味又是一回事。在这一点上,我信奉那句老话,“人的精神是占第一位的”,条件如何与能否活成这样的“一介书生”不存必然。岂不闻“饱暖思淫欲”,然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照样能使“回也不改其志”么?放眼望去,在目今累遭诟病的高校管理体制中,无奈为五斗米折腰者比比皆是,如鱼得水乐此不疲锦上添花再添花的也不知凡几。境由心造,路在人择,由于人和人差别实在太大,遂也就千姿百态丰富异常,像宁老师这样把教书治学作为自己唯一的生活目的而不是手段,并以此托起整个人生的,很是稀罕。齐美尔说,只有十分高雅和纯洁的心灵,能够依赖它们最固有的内心世界生存,只有这种心灵才能够把客观物体吸纳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反之。做成了教师的,未必就做得了这样的“一介书生”。李渔说,“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宁老师似乎是本能自发地亲近“溪山清静”。
或许与个人秉性有关,我向有近朱者赤,沾染点宁老师这种气息的愿望。不过自己很明白,这至多是心向往之。学问是可以下苦功的,在书房黄灯枯坐也不是难事,但学问背后的那种境界和心态:与名利无干,投入全身心享受治学过程之乐,生活在世俗似又不在世俗——直如“草色遥看近却无”,不是凭努力想要就能要到的,毕竟经历、状况、修为差别太大,牵上十条阿尔法狗也枉然。阿尔法狗即便成为全世界的独孤求败,围棋在它那里永远都是一种算计。所以,我大多也只能将宁老师作为励志片一类的,不时闪回一下“溪山清静”的画面,以免在“奔波碌碌”中发热昏,失去了自己的本分。
宁老师生活简单,看人断事也简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天真。我怀疑在他对人或者同学的评判框架里,只有两类标准:喜欢学术的和不喜欢学术的。喜欢学术的,就是一个好学生。要是再加上喜欢新闻史,那就更棒,就是大大的好人。不喜欢学术的,他也不讨厌,更多的是不理解。在他看来,世上哪还有比看书思考更有乐趣更美好的事情呢?况且,读书而对学术没有兴趣,他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对一些他认为的可塑之才最终没有走上学术,就感到十分的惋惜,时常会不止一次地念叨,某某某挺好的,跑去做其他事情真是可惜了,语调中充满无尽的感慨,好似人生因此就被荒废了似的。或许正因如此,凡有学生上门求教,他总是高兴异常,不存门户,没有亲疏,来者不拒,倾情相待。在他的认知中,这就是喜欢学术的表现,一律视为同道中人,从来不关心其动机和目的。他亲切热情,没有任何架子,又是有求必应,很受同学的爱戴和喜欢。加上我念博士的那会儿,他的家就在来往复旦南区研究生宿舍的必经道口上,人和加上地利,特地登门拜访的不少;顺路经过,带便就拐进去到他家坐坐的也是不少,无所谓什么预约不预约。对于这一切,他也早已是习以为常,好像本来就是如此,总是热情洋溢,笑吟吟招呼你坐下,然后泡上一杯茶。有意思的是,无论聊天时间是长是短,每当临别时,宁老师都是觉得意犹未尽依依不舍,起身送你到门口,一定是真诚而不是客套地叮嘱下次有空再来,让你都觉得不好意思不再去,否则就是有负期望。我在博士论文后记中说,在复旦三年,宁老师是我求教最多的老师之一,就是与这样的情形有关。
与宁老师交流无拘无束,是一件很轻松很愉快的事,他不会给人沉重感,没有什么师道尊严,纯属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谈话常常是从最近看到什么,有什么好想法开始,无论你说什么,他都听得兴致勃勃,对于一些他所不知道的新鲜事(哪怕是八卦),更是有着浓厚的好奇心,不断追问,希望知道得更多。家事、国事、天下事,他统统笑纳。他是一个健谈的人,甚至有点人来疯,凡与人交谈,常常会显得兴奋,滔滔不绝,少有冷场,聊两三个小时都是常态。聊着聊着,有时冷不丁也会冲你提一个问题,这问题很可能就是他最近正在思考的,有的是他自己已经想明白了的,借此不过是想知道别人的想法,或者也就是希望分享他的思考。所以,无论是否能够回答,都无需紧张。若他自己已有答案的,就会随之亮出观点。这个时候,他就会略显得意,觉得发现了一个你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就像一个小孩,突然间把身后的手伸到你面前,展示手掌中的那个新奇玩具,希望让你吃一惊。他从不掩饰自己,都是直言直说,喜欢论辩。尤其是对于自己所认准了的东西,既不会随便改变,也不会轻易被人说服,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性和求胜心。论辩时的宁老师,会越说越激动,脸孔涨红,两眼圆睁,语速加快,腮帮一鼓一鼓,嘴唇飞快颤动着,那气势就像要吃掉谁,连话语都不是连贯而出,像是迫不及待互不相让地拥挤着出来,因此反而堵塞了通道,语音出口远远慢于嘴唇颤抖的频率。他的发音部位稍有点靠后,加上安徽口音,本来听得就吃力,着急之下更是让人有囫囵吞枣之感。讲了半天,我们听明白的可能不足二分之一。宁老师大学念的是外语,现在想来很遗憾,没有让他说几句英文听听,不知是否也是这样的咬字不清且带有浓重的安徽腔?不过与宁老师争论,我们是毫无心理负担,也不会因他年纪大就诺诺顺从,那反而是对他的不尊重。有时还要调皮一下,故意唱反调,让他着急。当然,唯有一点需要提防,千万不能惹他血压上升。
记得有一年他曾和复旦一位教授就如何评价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发生过一番争论,我看过双方的文章,都是刀来枪去直逼命门。这篇文章被收入了文集,宁老师还专门做了个附记,称“真是不打不相识”,“经过文字交锋,我们建立了良好关系”。这种惺惺相惜,好比武林道上,亮招过手后,抱拳作揖互道久仰久仰。当然,这属于很老派的了,可能只能对那辈人适用,在目今已不时兴。新闻传播圈本来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学术交锋,若有所争,大多也是纠缠于一般逻辑上的你错我对之类。像问题的提出及其来由,材料的举证,理论的脉络和使用的合理性,研究者自身的立场预设等等的学术规范,没有人予以关心。其实也不是不关心,而是没有这方面的基本训练和敏感。新闻传播研究没有积累、没有传承、形不成自身的学术脉络,甚至缺少对学术的起码敬畏,并不是没有来由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学生都可以来报考新闻传播的研究生,而新闻传播的学者少有迈出圈外,与其他学科的人坐在一起同台讨论,就足以说明问题。学术不仅成为与一己生命无关的技术活,甚至沦入逢场作戏,讲究的是互捧与自捧,追求的是知趣和投桃报李,注重的是人气而不是真才实学,学术能力体现在如何经营关系,而不是读了多少书,否则就OUT了。新媒体的使用,更是助虎添翼,单是大拇指的起起伏伏,飞来飞去的红包,真真假假的各种笑脸表情,就让人目不暇接头昏眼花。近日在网上买了几个书架,立马收到店主一个短信,“宝贝显示已到达您手中,跪求您赐予我一朵小红花”,一定“孝敬您8元现金红包到账户”。学界商界看来遵循的都是同一个规矩,学术场就是生意场。齐美尔发现货币作为一种均等化媒介,拉平了交往的关系,但他定是做梦也料不到,新媒体的介入直接抹去了士商的界限。
宁老师的上课与他的聊天亦同亦不同。同的是他在课堂上也是富有激情,不同的是,他的课以问题为线,以提问逼迫你思考。我们念博士时,他和丁淦林老师上的是同一门课,印象中名字叫“新闻事业与社会”,每人一个学期。宁老师讲古代和近代,丁老师则负责现代部分。丁老师上课的风格是以文献为主,围绕某段历史,摆出一个又一个材料,意在展示其前因后果的种种复杂面向,从而对一些约定俗成的说法,进行修订和纠正。宁老师则以问题见长,他或者先抛出问题,然后切入某个现象;或者在述说史实过程中,概括出某个问题,促使大家在理解上能再深入一步。如果说丁老师着重于增加历史厚度,改变我们惯有的单一性思维;那么宁老师则是以锋利见长,直接挑开那些我们常见而又不见的面向和关系,给我们来一个当头棒喝。宁老师的这些问题,当然都是他平时追根究底的结果,当时所受到的震动自不必言。尽管他所提的那些问题,已经大部分都不记得,但他的那种提问方式,那种对于材料的细密解读,却铭刻在心、影响至今。
宁老师对于学术的一丝不苟且又充满真意,还可以在另一个地方得到昭示,那就是他给不少论著所写的序。不知有多少人注意到,他的文集后记中有这么一句话,书中“另有若干书序、书评稿,也还是认真写的”。看上去轻描淡写,但我却深深感觉到它的份量。若清楚宁老师的为人以及遣词造句的谨慎,就了解他一般不会轻易给自己的东西标出“认真”两字。既然直告“还是认真写的”,就意味着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东西,没有一个是随便敷衍应付的,而且也是希望勿因其小而忽之。因此他紧跟着又接上了一句:“我的有些专业思想和学术见解,就是从这些文稿中提出来的。”我的亲身经历或许可为之做一注脚,以便能领会内中的寓意。我的《新闻传播学》一书是宁老师作的序,这是由当时长我一辈的杭州大学同事桑义燐老师提议并热心帮助联系的,因为桑老师毕业于复旦新闻系,与宁老师多有交往,我与宁老师从未谋面。后来宁老师寄来的序也是由桑老师转我,其中还有一封写给桑老师和我的信。在宁老师去世后,我特地翻检出珍藏至今的这个手稿,真是感慨万千。信中先对序的拖延表示了歉意,然后说道:“黄旦同志的书稿,我原检好拟带来美国,可是临行心烦事乱竟忘记了,好在我已将书稿全部读完,有些部分读过几遍,颇有印象,还是能够写成的。”书稿“全部读完,有些部分读过几遍”,以致书稿不在身边也能完成序言。这样的写作,哪里仅仅是一篇序言,分明是倾心与作者的对话,否则也不可能生发出他所谓的“专业思想和学术见解”。因而,宁老师的序,不是标准化类型化的,不是空洞浮泛的,总是一篇一个模样的“量身定制”,无论作者是陌生人、小人物还是知名学者,均一视同仁。序的文字,就像他的为人,宽厚实在不说半句套话,更没有超过底线的“与人为善”,总是实事求是地尽量抉发书中的各种长处,该肯定的肯定,该褒奖的褒奖。至于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即所谓的“专业思想和学术见解”,都是从正面来阐发,看上去好像只是借书的由头说自己的话,实际上正是他对书的看法有所保留之处。当我们今天也可以装模作样为人作序时,完全能够体会为此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不是一个沉重负担的话。我粗略数了一下,在文集中不算书评收有九篇序,也就是九本书。少一点算,以平均每本十五万字计,“全部读完”的字数就近一百四十万。最早的一篇序注明时间是1989年,也就是说,宁老师是从近七十岁之后陆续“全部读完”这一百四十万字的东西,还要加上“认真写”,且是在自己看书治学不能松懈的同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量?目今还有多少人是出于如此的态度来作序的呢?在今天花花绿绿姹紫嫣红的序言中,又有多少是可以读出一丁点此种真意(专业思想和学术见解)的呢?就我眼目所及,目前一些所谓的序,不用说是“全部读完”书稿,甚至粗略翻过都做不到,有的干脆就是他人捉刀代笔然后堂而皇之押上自己大名的。言不及义尚还是好的,胡说八道与书稿扯不上关系的也非少数。若以“狗尾续貂”衡之,书是否成“貂”暂且不论,序为“狗尾”,则是货真价实。此种以空名幻化空名,以虚浮博取实利的作为,与宁老师的一对照,恍然是时空转接换了人间。由此说,宁老师早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很可惜,宁老师未能在生前将自己晚年倾尽心血的地方新闻史书稿出版,如果说留有什么遗憾,或许这就是他唯一的念想。前几年碰到,每当问起研究进度时,他的眼神里会流出很少有的一丝惆怅和无奈,用缓慢的语调告诉说,年纪大了,眼睛也看不清,要用放大镜,做得很慢,做不动了。好像他自己也有预感,所以在《宁树藩文集》出版之际,通过后记为自己的学术人生做了一个自传式总结,从而为理解他的经历和心路有了一个基本依据。
依我解读,文集的论文分为两类:一是关于报刊史的,一是关于新闻理论(包括新闻史研究和编写的设想)。读了他的报刊史文章,首先得到的一个印象,文章的格局气象大,视野很是开阔,即便是那些个案式的研究,一般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尽量延展到各个方面,努力把握其复杂性。其次,文章不跟着既有定论走,总是尽力说出自己所感所思,哪怕在改革开放前也是如此(比如写于1962年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第三,宁老师文章所展示出的思辨色彩之浓,在治报刊史学者中是少有的。我在纪念丁淦林先生的文章里说到过,复旦的新闻史研究是有自己特色的,那就是不仅注重史料而且也注重理论,甚至可以说,在宁、丁诸老师一代中,论与史似没有太大的界限。王中、余家宏、李龙牧等都是如此,宁老师又是一个上好的例证,而且也是尤其突出的一位。以此见,他后来由史而论,在新闻理论研究上有所建树,也是不令人意外的。
要是让我一定挑选最能代表上述宁老师风格的报刊史研究文章,我会指出三篇,那就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评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评述》和《辛亥革命前中国报业发展的地区轨迹》。前二者属于个案,后者则是面上的研究。一般而言,历史评述文章的最大难处,在于评与述的分寸。述为主,则变成材料的堆砌;评抢先,就有以己之念驾驭材料之嫌。当然,如果仅以此来说明宁老师这两篇文章评述火候把握得当,还不能道出其出色之处。我之所以喜欢这两篇文章,在于作者大处着眼小处落笔,通过由小到大的多维度考察,托展出两个刊物的立体面貌,并自然揭示出人物、社会背景、刊物特征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具有的影响和意义。文字干净利落而直指要害,逻辑层次简明而不简化,性质特征评定明确而又有厚实依托,并对以往将传教士报刊简单粗暴贴一“文化侵略”之标签的做法提出了质疑。由于之前写的一篇文章牵涉到晚清的传教士刊物,接触了一些以往的研究文章,相比之下,宁老师的这两篇文章不愧为其中的力作。宁老师要是能延续这样的路数,一个一个往下做,比如《六合丛谈》《遐迩贯珍》,甚至《中国丛报》,形成一个系列就好了。我知道他手头有资料(现在这几个刊物都影印出版了),而且也有兴趣,在我跟前提到过,尤其是《中国丛报》,他又有英语基础,是多么合适的人选!最终未能如愿,估计也是“年纪大了,做不动了”的缘故吧!只是中国报刊史研究也因此留下了大缺憾。
《察世俗》和《东西洋考》两篇是小题大做,《辛亥革命前中国报业发展的地区轨迹》则算得上是大题大做,没有十分的功力,是不敢碰的。该文将1822年《蜜蜂华报》开始到辛亥革命之前分为三个段落:1822~1894年,从外报的进入到全面垄断,形成沪、港、粤、津和汉五大报业基地,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影响下,原先的报业重镇广州衰落,港沪两地南北对峙的格局出现,并最终是沪后来居上,成为全国外报之中心。第一阶段报刊是随着商人和传教士的足迹沿海、沿长江,由北及南,由东向西伸展,而在甲午战争爆发到1898年这第二个阶段,报业是追随维新运动的潮流,由沿海向内地推进,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兴盛并取代外报居于报业发展的主流。办报城市的增多,打破了原来线性的地域格局,开始结成片,造就了在全国有影响的若干报业地区,出现北京、上海、长沙、天津四大龙头城市。到了1899和1911年这第三个阶段,中国不仅报刊数量大发展,更重要的是报刊结构开始多元:官办报刊、政党和政治派系报刊、商业性报刊、科技文化教育报刊以及外国人在华报刊五大类报刊各呈所能,其中又重点展示了政党和政治报刊与外国人在华报刊的具体变化。五大报刊的分流而进,引起中国报业地区总形势的多方面变化,出现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以粤、港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以哈尔滨和沈阳(奉天)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并开始形成的西北地区。文章气势宏大,通过时间来演示空间,描画出将近百年的中国报业变化示意图,要是没有对于中国报刊变化的深刻把握,根本无从着手。然而,该文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通过总体的变化来比较不同地方的报刊实践及其特色,用我的概括来说,宁老师已经意识到要从“地方性知识”着手来研究报刊,这就打破了目前已有的所有通史类报刊写作的思路,是中国新闻史书写在思路上的重大创新。我猜测该文应该是他那本地方新闻史的绪论或者引言部分,要真是如此,这本地方新闻史就很值得期待。
宁老师自己表白,年逾六旬之后,所倾情的还在新闻理论方面,也就是我所谓的第二类。不过我不准备在一些具体观点(比如关于新闻定义、新闻特性)上花太多笔墨,当然不是这些不重要,恰恰相反,今天读来仍然有着诸多启发(比如新闻与媒介实践的关系,在今天的新媒体环境下又一次成为突出的问题)。我是打算把重点放在读解此类研究背后的动力和追求的目标,以便可以将宁老师的作为与复旦这一辈人放在一起来讨论,也算是从宁老师这里学到的由小到大吧。文集中关于新闻史研究和书写设想之类,也正是因此与新闻理论研究文章并置一起。
先说新闻理论,很显然,宁老师主要精力,就是围绕如何划清广义新闻学和本义新闻学的界线,直白了说,他希望把新闻本身和新闻(媒介)实践和操作分开,后者可以形成知识体系,前者则事关理论体系,从而解决新闻学理论抽象层次低,无法自成一体的老大难。再看他关于新闻史写作的诸多文章,则是从倡议改变新闻史从属于革命史状况开始,逐渐明确提出强化新闻史的“本体意识”,目的则在于确立新闻史自身的学科特性。由此,史论两个方面的研究,殊途同归,扭结到一个焦点:即回到新闻自身(新闻本位)。宁老师的实际目的,是要以新闻为起点,从史论两方面开弓,为建立合理科学的新闻学科开路铺石,显示出强烈且挥之不去的学科情结。他指导的一个博士生,就做过有关新闻学教科书的梳理和研究的博士论文,这都与他的这个情结有关。
丁淦林老师曾经提到,复旦的新闻史大纲,起初来自于中央党校,实际上是根据苏联的教学范本制订的。宁老师在其后记中也回顾道:1959~1963年夏,他承担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的编写,这个稿子实源于高级党校所编的《中国现代报刊史》。如果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待宁老师的这些思考,我们大致能够理解他的心思和努力方向,那就是要打破原有的框框,重新推动创建中国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有这愿望和心结的不只是宁老师一个人,暂时不提其他高校,就复旦而言,基本就是宁老师那一代人的梦想。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丁淦林、李龙牧的新闻史教材,徐培汀的《中国新闻学术史》等等,无不如此。宁老师在文集中还提到一件事,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是“文革”结束不久在王中先生的过问下所写,目的是反“左”,也就是要推翻原有的书写逻辑。写作过程中两人多有讨论,完成后请王中先生过目时,王中还在上面加上了一段话,完了再亲自送一位哲学老师看一遍,以防在哲学观点上出现不妥,可见其共同志向。放大一点看,这种努力并非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其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尤其是1956年王中执掌新闻系时,就已经着手,当时对于教学方案、教材编写、学术研究、资料搜集、师资培养等等,多有创造性改革设想和举措,包括资料收集(文集后记中涉及不少,读了令人感慨不已)在内。举一例子,就是在1956年,复旦新闻系制定了一个《新闻系十二年科学研究工作纲要(草稿)》,对于教学科研有过具体的构想(可参拙文《走自己的路:新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先声”》)。宁老师这一辈似乎对于学科的创制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几十年来从未松懈过。宁老师的研究正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并且在另一个向度上的呈现。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多多,主要当然是和大背景的变化以及中国新闻学科的特殊渊源有关,就不在这里展开了。正因如此,我把这一代人称之为复旦新闻传播学科建制化的一代。新闻学科能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是跟这一代人的奋力推动、努力实践分不开的。当今天享受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可否还能想得起他们的艰难和辛劳?
宁老师晚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苦苦思索两个新闻定义的划分。我明白,这在他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因为他认为这关涉新闻学科的理论体系和未来发展的基础。在他看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余下的就可以迎刃而解。他为自己还没有想透,还不能提出一个完整的想法而苦恼。因此,那一段时间,凡是到他家聊天,必定绕不开这个话题,非缠着你讨论不可,简直就是不疯魔不成活。在他过世的第二天,我在学院遇见他的亲属,她告诉我,宁老师住院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已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思维和说话功能都不听指挥了。但当说到他日思夜想的“新闻的两个定义”时,居然可以把平时经常念叨的那一整套,流利地脱口而出,没有任何障碍。闻之令人唏嘘不已也震撼不已。学术与他,完全融为一体,若非纯然一介书生,岂能如此?他用自己的生命对之做了最好的诠释。值得再读一遍他文集后记中的最后几句话:
我是纯然一介书生,不谙世故人情,碌碌无所作为。可对学术却结下不解缘。虽少有成就,却情结老而弥深。总把扬帆于知识的海洋,展翅于智慧的天空作为最大乐趣。此生不息,探索不止!
他如是说也是如是做,没有半点虚假。马克思·韦伯说,以学术为业者,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才有人格可言。在我心目里,宁老师就定格于这样的大写“人格”里,其“本真的存在”永远“伫立在现时中”(马丁·布伯语)。
近日,我又专门看了一眼新闻系七七级系友送给学院的那副油画,文科楼老旧资料室的一长条桌前,端坐着各位论文答辩委员,神态各异,有认识有不认识,但却让人感受到充盈环绕其间的一股精神气质。盯着画面,一时间脑海里直接蹦出的竟是古人早已说烂了的几个字: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随着宁老师的最后谢幕,复旦新闻学科建制化的这一代人,也就集体告别了他们所钟爱并付出毕生的新闻学院和新闻学科。人去楼新,底蕴不存,他们的一切随着他们远去而烟消云散。
马上就是清明节了,不知宁老师是否正兴致勃勃,与这批重新聚齐的老同事们一起踏青,并高谈阔论他的两个新闻定义?无论如何,在这阴阳交接之际,我要像平常一样,笑嘻嘻和他打声招呼:“宁老师,多保重!”同时,也燃起一瓣心香,向在另一世界团圆的复旦这一个前辈群体,深深鞠上一躬,奉上我这后学的绵绵敬意!■
黄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