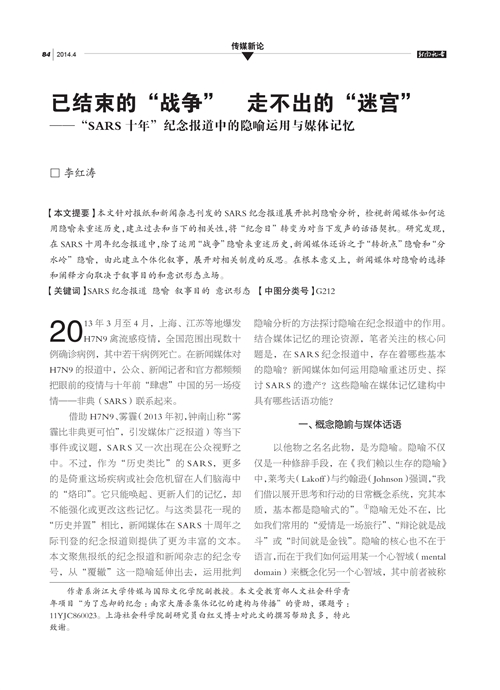已结束的“战争” 走不出的“迷宫”
——“SARS十年”纪念报道中的隐喻运用与媒体记忆
□李红涛
【本文提要】 本文针对报纸和新闻杂志刊发的SARS纪念报道展开批判隐喻分析,检视新闻媒体如何运用隐喻来重述历史,建立过去和当下的相关性,将“纪念日”转变为对当下发声的话语契机。研究发现,在SARS十周年纪念报道中,除了运用“战争”隐喻来重述历史,新闻媒体还诉之于“转折点”隐喻和“分水岭”隐喻,由此建立个体化叙事,展开对相关制度的反思。在根本意义上,新闻媒体对隐喻的选择和阐释方向取决于叙事目的和意识形态立场。
【关键词】 SARS纪念报道 隐喻 叙事目的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G212
2013年3月至4月,上海、江苏等地爆发H7N9禽流感疫情,全国范围出现数十例确诊病例,其中若干病例死亡。在新闻媒体对H7N9的报道中,公众、新闻记者和官方都频频把眼前的疫情与十年前“肆虐”中国的另一场疫情——非典(SARS)联系起来。
借助H7N9、雾霾(2013年初,钟南山称“雾霾比非典更可怕”,引发媒体广泛报道)等当下事件或议题,SARS又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不过,作为“历史类比”的SARS,更多的是倚重这场疾病或社会危机留在人们脑海中的“烙印”。它只能唤起、更新人们的记忆,却不能强化或更改这些记忆。与这类昙花一现的“历史并置”相比,新闻媒体在SARS十周年之际刊登的纪念报道则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本。本文聚焦报纸的纪念报道和新闻杂志的纪念专号,从“覆辙”这一隐喻延伸出去,运用批判隐喻分析的方法探讨隐喻在纪念报道中的作用。结合媒体记忆的理论资源,笔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SARS纪念报道中,存在着哪些基本的隐喻?新闻媒体如何运用隐喻重述历史、探讨SARS的遗产?这些隐喻在媒体记忆建构中具有哪些话语功能?
一、 概念隐喻与媒体话语
以他物之名名此物,是为隐喻。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莱考夫(Lakoff)与约翰逊(Johnson)强调,“我们借以展开思考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究其本质,基本都是隐喻式的”。①隐喻无处不在,比如我们常用的“爱情是一场旅行”、“辩论就是战斗”或“时间就是金钱”。隐喻的核心也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我们如何运用某一个心智域(mental domain)来概念化另一个心智域,其中前者被称为始源域(source domain)(比如“旅行”/“战斗”/“金钱”),后者被称为目标域(target domain)(“爱情”/“辩论”/“时间”)。在此意义上,隐喻即是“概念系统中跨域的绘图过程”(cross-domain mapping in the conceptual system),而“隐喻表达”则是这一概念化过程在语言层面的落实和呈现。②
在概念和认知层面,隐喻(无论是习以为常的隐喻,还是新的隐喻)帮助我们界定现实。由于隐喻总是用某一概念来描绘另一概念的特定侧面,隐喻的运用必然会遮蔽目标域概念的其他侧面。③隐喻对现实的“强化”与“遮蔽”,不仅影响了我们对现实的认知,也影响我们如何作出推断、设定目标、作出承诺并执行计划。④ 因此,跳开日常生活的范畴,隐喻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运用,不仅会遮蔽现实的特定面向,还会束缚我们的生活。⑤ 基于此,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夕,莱考夫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批评围绕伊拉克问题的政治与媒体话语充斥着各种隐喻——战争即政治/生意、伊拉克即萨达姆、正义战争的童话等等,而布什政府正是运用这些隐喻来正当化战争举动。⑥ 他指出,对于特定情境的隐喻式理解通常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存在相对固定的一套隐喻,它们影响着我们的思考方式;二是存在一套隐喻式的界定,将上述隐喻应用到特定情境中去。
对新闻媒体而言,隐喻是构建现实和生产意义的重要手段之一。甘姆逊(Gamson)等人在运用建构式话语分析时,就将隐喻作为构成意识形态集束(ideological package)的重要架构工具(framing device)之一。⑦ 对新闻隐喻的研究大致聚焦两个层面,一是新闻媒体如何使用隐喻来描述新兴事物、界定事件或议题的本质及其意义。赫尔斯坦(Hellsten)以克隆羊多莉为例,比较了《泰晤士报》所代表的新闻话语和《自然》杂志所代表的科学话语。作者发现,二者都借用“批量生产/复制”这一隐喻来形容“克隆”,但《泰晤士报》将其视为“低劣的复制品”,而《自然》杂志则强调它们是“有用的产品”。此外,由于新闻媒体调用的隐喻往往与更为广阔的文化迷思和解释框架相契合,《泰晤士报》将克隆羊比作“弗兰肯斯坦的怪物”(Frankenstein’s monster)——即毁灭创造者的怪物,而《自然》则将之看作科学进步的象征。⑧ 与之类似,奈里其(Nerlich)等人分析了新闻媒体如何运用隐喻来报道克隆和转基因作物等生物工程领域的争论。⑨
二是新闻隐喻与意识形态的关联。由于隐喻具有“不可证伪”性,它“成为媒体话语巧妙地、不露声色地传达意识形态、偏见、刻板印象的最佳工具”。⑩卡迪斯(Kitis)等以《时代》周刊一篇有关希腊和马其顿的报道为例,揭示出新闻话语中的隐喻如何建构意识形态。该文认为,新闻话语中的支配性隐喻实际上是较高层次的文本组织特征,它们借助较低层次上的词汇选择(包括附属性的隐喻)和语法结构,将“描述性-叙事性”的文本结构转化为“争辩式”的结构。[11]隐喻对现实特定面向的选择性“强化”与“遮蔽”,构成了新闻再生产意识形态的基础。杰克·鲁尔(Jack Lule)延续莱考夫对伊拉克战争的批判,聚焦新闻语言中的隐喻和它们对战争报道的意义。通过分析NBC夜间新闻在伊战前夕六周内的相关报道,该文发现,在“摊牌”(showdown)“倒计时”(countdown)等结构隐喻之下,媒体最常用的隐喻包括时间表、萨达姆的游戏、白宫的耐心、兜售计划等。通过运用这些隐喻,媒体将战争视为不可避免的结果,从而将“辩论”、“谈判”、“审议”等其他隐喻和行动选择排除在外。[12]甘莅豪比较了中美媒体对南海问题报道中的隐喻建构,他发现,两国媒体运用了大致相同的隐喻类型,但这些隐喻服务于不同的“修辞意图”,并建构出不同的自我和他者形象。[13]邓育仁和孙式文以台湾政治新闻里的路途隐喻为例,强调隐喻具有系统性和融贯性,新的政治隐喻可以提供新的看待政治情境的方式,而隐喻竞争对政治事实的建构产生深远影响。[14]这两个研究思路,都体现在研究者对SARS媒体报道的隐喻分析之中。对医学界、政府和媒体而言,SARS是一种全新的传染疾病(这从中国最初将之称为“非典型肺炎”可见一斑)。鉴于“疾病常常被描绘为对社会的入侵,而减少已患之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的种种努力则被称作战斗、抗争和战争”,[15]沃利斯(Wallis)与奈里其认为,环绕艾滋病等疾病的“战争”和“军事”隐喻也应该被用来描述SARS,但是他们对英国报纸SARS报道的研究发现,“战争”和“瘟疫”隐喻统统缺席。与此相反,媒体主要运用“杀手”隐喻来描述SARS。[16]不过,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SARS在英国并没有发展到严重程度。
在中国以及其他SARS重灾区,情势则完全不同。江文瑜和段人凤比较了中国台湾地区的《自由时报》《联合报》和大陆的《人民日报》对SARS、非典报道中的隐喻运用。她们运用批判隐喻分析(CMA)理论,分析了报道的命名策略(SARS、非典和“煞”)和对自我与他者的建构。她们发现,两地媒体都广泛运用“疾病作为战争”这一概念隐喻,但是它们却建构了不同的自我和他者,例如《人民日报》将非典建构为唯一的他者,而台湾媒体则倾向于将民进党政府(《联合报》)或在野党(《自由时报》)以及中国大陆建构为他者。[17]概而言之,不同媒体的隐喻运用折射出它们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取向。媒体通过运用战争隐喻,将SARS呈现为政治话语而非医学话语。SARS不再是一种疾病,而变成了政治意义上的一场战争或灾难。
延续这一研究思路,本文拟处理的研究问题包括:十年之后,在中国媒体的纪念报道中,“战争隐喻”是否还占有垄断性的地位?媒体是否调用其他隐喻来建构纪念叙事?纪念报道与日常报道在隐喻运用方面有何差异?媒体如何运用隐喻来重构历史、建立过去与当下的关联?在不同的叙事目的下,媒体选择、运用隐喻的方式是否有所不同?不同媒体在隐喻选择和运用上是否存在差异,它们折射出怎样的意识形态意涵?
二、 研究材料与方法
SARS十周年之际,官方并未举行任何全国性的纪念仪式或活动,地方层面的纪念事件(如纪念抗非烈士)偶尔见诸报端,但它们在媒体主动发起的“纪念报道”中居于非常边缘的位置。为确定哪些媒体在十周年刊登了纪念报道,我们首先在中文报刊数据库搜索关键词“非典”、“SARS”,将时段设定在2012~2013年,再依据单篇报道的线索选定刊登多篇报道的媒体。《南方人物周刊》等六种新闻杂志[18]、《南方日报》等三份报纸刊登的非典十年“封面报道”或专题报道(表1 表1见本期第86页)构成本文的研究材料。
如表1所示,六种新闻杂志的封面报道共刊发157版、34篇文章,其中《三联生活周刊》刊登76.5版、12篇文章,其他杂志的封面报道均占15版左右。三份报纸的专题报道共刊登34版、41篇文章。[19]其中,《新京报》16版的十周年特刊和《外滩画报》14版的封面报道均没有刊登任何广告,由此构成了相对纯粹的纪念空间。在纪念报道的呈现方式上,新闻杂志均采用封面报道的方式,而报纸则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在一段时间内刊登系列报道,比如《南方日报》的“抗击非典-十年十章”分十次刊出。另一种是在某一天刊登多个版面的“类杂志化”专刊报道,比如《新京报》的“SARS拾年 中国抗体”、《东方早报》的“非典病人”。系列报道中时间跨度最长的是《南方日报》,十篇报道的第一篇出现于2013年2月25日,第二篇3月1日,第三篇至第十篇从3月25日至4月3日依次刊出。在第二篇和第三篇之间相隔24天,是因为从3月3日开始该报集中报道全国两会和“学习两会精神”的相关活动。
在命名策略方面,封面报道或专题名称共涉及到九个命名,其中五个是“非典”,四个是“SARS”。众所周知,“非典”是“非典型肺炎”的简称,是在尚未确定病源时中国医学界赋予SARS的早期名称。十年之后,SARS作为世卫组织确定的疾病名称,很明显是更为准确的命名。为何媒体仍然在专题名称和正文报道中大量使用“非典”这一称呼?这大概是因为相比由英文字母组成的SARS,“非典”(以及“抗击非典”而不是“抗击SARS”等口号)在疫情爆发时更为深入人心、也打下了更深的情感烙印。媒体对“非典”这一称呼的广泛运用,显示出媒体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公众记忆的呼应与强化。
与多数被纪念的历史事件(比如战争胜利、英雄死难日等)不同,SARS并没有实际上的或者官方认定的“纪念日”。从2002年底在广东出现,2003年2月、3月在全国范围爆发,并扩散至东南亚和全球,再到2003年6月世卫组织确认北京不再是疫区,SARS疫情绵延半年之久。新闻媒体会选择什么时间刊登纪念报道?这一方面取决于媒体认定的SARS疫情关键时间点,另一方面则受到媒体之间新闻竞争的影响。在本研究所涉及的媒体样本中,纪念报道刊发的时间跨度也相当长,最早是《博客天下》于2012年11月15日推出的封面报道,之所以选择这个纪念时机,原因是“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人庞佐尧发烧进入医院。这是有据可查的非典起点”。
多数杂志和报纸的纪念时机介于2013年2月底~3月底之间。正是在十年前的这段时间,SARS不再是局限于广东等地的地方“疾病”,而向全国、全世界扩散,具有了更大的显著性。最晚的是《凤凰周刊》2013年5月3日的封面报道,在该刊报道中,当时爆发的H7N9成了“重访”SARS的契机和由头,“截至4月24日,中国大陆已确诊H7N9禽流感病例108人 巧合的是,此次疫情正值SARS疫情十周年”。
本文对SARS纪念报道中隐喻运用的分析受到批判隐喻分析的启发。批判隐喻分析建立在语料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批判话语分析的基础上,意在揭示语言使用者背后所暗含的(或无意识的)意图。查特里斯-布莱克(Charteris-Black)将隐喻分析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隐喻识别、隐喻阐释与隐喻解释。隐喻识别聚焦“概念意义”,研究者通过仔细阅读文本,发掘出“备选的隐喻”,再结合语料语境判定特定关键词是隐喻还是字面表述;隐喻阐释聚焦隐喻的“人际意义”,研究者试图发掘出经由它们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识别出概念隐喻。隐喻解释则聚焦“文本意义”,研究者将隐喻与情境关联起来,通过分析文本的生产者和他们的说服目标,揭示隐喻的话语功能及其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和修辞意图。[20]本文参照查特里斯-布莱克的批判隐喻分析方法,但更多采取质性的分析取径。[21]我们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穷尽纪念报道中运用的每一个概念隐喻(比如下文提及的“SARS是一面镜子”),而是希望借助对文本的深入阅读、反复比较,建立SARS纪念报道中的“隐喻链条”或“隐喻网络”,揭示隐喻如何嵌入新闻叙事的文本结构、参与现实建构和意义生产。举例来说,下文论及的“战争”隐喻的运用不仅牵涉到特定的语言表达(如“攻坚战”、“遭遇战”、“阻击战”、“抗击非典”),也牵涉到对SARS不同侧面的隐喻界定:谁是敌人?谁是英雄?谁是受害者?抗击的是天灾还是人祸?战争以胜利还是失败告终?更重要的是,质化取径有助于研究者跳脱微观的、孤立的字词、句法,以更为整体化的研究视野观照媒介话语的不同层面,将隐喻的运用与新闻文本的宏观结构和生产逻辑——如关注当下、青睐人情味故事、叙事结合文字与视觉语言、依赖消息来源建立叙事权威等——结合起来。
三、SARS及其隐喻
(一)“战争”隐喻与重述历史
如前所述,战争和军事隐喻非常频繁地出现在新闻媒体对SARS的报道当中。十年之后,媒体也广泛运用战争隐喻来重述历史,包括表1的专题标题中《南方日报》所运用的“抗击非典”的表述。在纪念报道中,“疾病即战争”这一基本隐喻被应用到SARS情境之下,转化为众多非常具体的隐喻表达或界定。
引文1:SARS 是一场遭遇战,无论是个人、医护人员还是国家,以毫无准备之血肉之躯,面对来势汹汹的神秘病毒。(“前言”,《新京报》)
在这里,存在两个基本的概念隐喻,一个是“SARS是一场遭遇战”,一个是“国家是血肉之躯”。后者将国家作拟人化处理,一方面是在将“病毒”对身体的侵袭和“SARS”对国家、社会的挑战相叠加,另一方面则清晰划定“遭遇战”的“敌我”关系:神秘病毒是敌人,而个人、医护人员和国家则属于同一阵营。这两个概念隐喻相互呼应、拓展,衍生出如下几个方面的隐喻表达:一是对SARS的隐喻,比如 “怪病”、“神秘病毒”、“元凶”、“恶魔”、“谜一样怪兽一样的SARS”、“疫症”、“疫魔”、“瘟疫”、“疫情”、“灾害”、“袭击北京的那场战争”、“屠夫”、“潘朵拉魔盒中的恶魔”等。
二是对SARS爆发过程的隐喻表达,比如“非典袭来”、“发起挑战”、“来势汹汹”、“闪电战”、“一步步逼近”、非典“横行”、“肆虐一时”、“(病毒)不断复制,依靠人体为介质,维持在人间的杀戮链条”、“疫情重灾区”、“SARS一去而不复归”、“我们可能会永远不与SARS再次相逢!”等。
三是对“反抗者”的隐喻表达,包括“抗非旗手”、“旗帜”、“战士”、“战友”、“病毒猎人”、“抗非英雄”、“一线指挥”、“火线厅长”、“抗击非典的总参谋部”等。
四是对应对SARS过程的隐喻表达,包括“保卫战”、“遭遇战”、“伟大斗争”、“抗击非典大战”、“SARS战役”、“与SARS的一战”、“打一场硬仗”、“我们上来就被它打个措手不及,甚至狼狈不堪”、“医院的溃败”、“(传染病区)陷入瘫痪”、“让象征生存的医院成为生命的雷区”、“狩猎病毒”、“中医是抗非重要武器库”、“每一名医生都在走钢丝”、“没有临阵逃脱”“军心动摇”、“上千名医护人员写下请战书”、“前线”、“抗非主战场”、“迎战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在看不见的战场,跟看不见的敌人作斗争”、“奋战五个月”、“从‘抗非’一线倒下”、“临危受命”、“深入救治一线慰问医护人员和烈士家属,极大激励了士气”、“防线设计”、“打赢这场战役”、“惊心动魄的战斗画卷”、“十年筑起防疫堤”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十年之后SARS已经不再是新发传染疾病,纪念报道中大量运用战争隐喻并不是为了界定一种新的疾病。这显示出,战争与军事隐喻已经构成重述作为历史事件的SARS的基本概念框架。在借助隐喻对SARS进行重述的过程中,尽管媒体倾向于使用“战争”及相关联的隐喻,但通过赋予隐喻以具体的解读和阐释方向(战争的起因、经过与结果),不同媒体所重构的历史版本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如下两段引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引文2:2003年初,一种全新的非典病毒从广东开始,向全人类发起挑战。广东省委、省政府率领全省人民奋起抗击,打响了悲壮而惨烈的“广东保卫战”。这是为人民健康而战,更是为人类尊严而战。那场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推动了科学发展观思想在广东的率先提出。(“编者按”,《南方日报》,2013.2.25)
引文3:在10年前袭击北京的那场战争里,它最强大(的)武器只是陌生和速度。如果只靠这两点,它顶多造成一些个体的悲伤命运,不足以摧垮一个城市,但长期处于安逸状态的人们的侥幸心理,还有行政上的官僚主义和缺乏专业眼光,成为它在人类阵营内的两个帮手, 造成万人空巷的空城局面。(《北大医院:有关SARS的知识和记忆》,《三联生活周刊》)
如引文2所示,党报在纪念话语中对抗击非典的“官方”叙事进行了浓缩与转化:战争突如其来,政府科学决策,人民奋起抗击,最终走向胜利,由此捍卫了全人类的尊严。更重要的是,这种胜利与政府的“统帅”作用和更宏大的意识形态主题(“科学发展观思想”)直接勾连起来。而在引文3所代表的市场化媒体的纪念话语中,战争基调没有如此明朗,敌我关系并非如此清晰分明(“政府-人民-全人类”的同一阵线与SARS在人类阵营中的“两个帮手”),抗击非典的过程也不是一出干净纯粹的英雄赞叹,而是充满了波折和挫败。市场化媒体与上述“官方”叙事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遭遇战”性质的界定,它们倾向于挑战战争隐喻的“自然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敌我关系界定),而聚焦SARS危机中的“人祸”成分。
引文4:2002年底,SARS降临南中国像是一次天灾,而接下来相关的政府部门及其他方面应对的态度更像是一场人祸,对真相的遮蔽、隐瞒和怠于应对,直接造成了2003年春天疫魔的大面积肆虐,引发了一场罕见的全国性危机,直至危及全球。(《SARS十年:改变的和未变的》,《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等市场化媒体均触及到SARS爆发初期官方对疫情的隐瞒、媒体报道的缺位、流言的蔓延和高官的免职。就上述引文而言,它仍然借重了隐喻链条中的“疫魔”“、大面积肆虐”等表达,但它对政府部门和应对机制的批评,挑战了政府作为“英明决策者”和“统帅”的角色,对“人祸”的强调也削弱了国家“无辜受害者”的形象。因此,无论是对战争本质、自我与他者的隐喻界定,还是对战争过程与结果的描绘,市场化媒体和党报生产出的不同历史版本,都折射出战争隐喻的多元阐释空间。
二者之间的差异还表现在纪念报道的叙事方式上,一是对历史叙事主体——“战争”的“主角”的选择。党报把纪念当作对“阻击战”胜利的回顾和英雄事迹的歌颂,倾向于选择领袖、高层和英雄人物,而同时关注战争“阴暗面”的媒体则还会选择被问责的官员、SARS病人和后遗症患者。我们统计了出现在纪念报道中的专访对象、口述文章作者和新闻标题中出现的人物及报道的主角。[22]如(表2 表2见本期第90页)所示,《南方日报》和市场化媒体在战争隐喻“主角”的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南方日报》15位“抗击非典”主角中,7位为政府官员,包括广东省副省长和省卫生厅厅长、副厅长。而市场化媒体聚焦的25位人物(某些人物不只出现一次)主要包括SARS(及其后遗症)患者、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在6篇关于政府官员的专访或报道中,两篇以免职高官或在SARS后卷入贿赂窝案的疾控官员为主角,它们再次折射出政府官员在“抗非”战争中角色的复杂性。
二是对这些人物的呈现方式。《南方日报》对15位“抗非”主角的报道全都是人物专访,与其他新闻采访形态不同,专访无法带入记者观察、相关事实和其他消息来源,因而最具叙事的“权威性”。在某种意义上,人物专访就像是战争胜利后对专访对象的“加冕”:专访对象充当着抗非战争中抵抗者阵营的“代言人”,讲述着战争的进程、他们在战争中的角色和对其结果的影响,而市场化媒体则综合运用人物专访、口述和记者报道,在自上而下的视角之外,更多讲述普通见证者在战争中的遭际。概而言之,在“战争”隐喻的运用上,《南方日报》展示的是领袖的“运筹帷幄”和战士的“英勇抗争”,而市场化媒体则更多聚焦战争的“受害者”和抗争的“残酷性”。
(二)“转折点”、“分水岭”:历史与当下的隐喻关联
如(表2 表2见本期第90页)所示,普通生命个体与SARS的纠缠在市场化媒体的纪念话语中占有更显著的位置。在这些媒体讲述个体悲喜故事过程中,除了“战争”隐喻,它们也广泛运用“命运转折点”、“迷宫”等替代性的概念隐喻。
引文5:这个普通家庭的生活也被这场瘟疫撕裂为一个个碎片。邓若静和黄文斌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一路碎片拼起来,作为“后非典时代”这座迷宫里前行的指引…… 10年之后的这个瞬间,是邓若静和这个家庭走出非典迷宫的标志——她终于可以恢复到一个普通妈妈的状态,这是属于她的最重要的身份。(《母亲的迷宫》,《博客天下》)
在这段引文中,媒体运用了一个新的概念隐喻,“非典是一座迷宫”。一方面,它将SARS从战争层面转移到个体命运层面,而与新闻媒体在纪念报道中对个体化叙事的强调相互呼应。另一方面,在战争隐喻中,SARS疫情消失被当作战争的终点和“抗非战役”的胜利。但“‘后非典时代’这座迷宫”和“走出非典迷宫”这样的隐喻表达则意味着,“这些关键人物的命运,也以非典结束为起点,缓慢前行”(“编者按”,《博客天下》),或者“对于一些曾经的非典患者,痛苦并未结束,激素治疗带来的副作用陪伴了他们十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东方早报》)。
在聚焦个体命运的纪念报道中,媒体更多运用另外一个经典的隐喻,即“命运转折点”,而“迷宫”隐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转折点”隐喻的变体。例如,“10年前的‘非典’,是武震命运轨迹改变的起点”、“二○○三年,对于非典患者而言,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非典’给我的人生提供了一个轨道道岔,让我有机会去选择另外一条路”、“那场已经成为记忆的灾难从未远离他们的生活,他们一直并且还将沿着被它拧转的命运轨迹生活下去”等等。在这些引述中,“人生是一条道路/轨道”,而“非典则是命运的转折点”。这一概念隐喻被广泛应用在两类人物身上,而他们的故事,也代表了在宏大的战争叙事之外,普通人进入SARS纪念话语的两种基本方式。
一是对新闻当事人的重访。《博客天下》杂志的纪念专题名为“非典十年·命运”,该专题追踪的普通人均是SARS事件中的“新闻人物”,例如世界上第一位被确诊的非典病人、造成大面积感染的“毒王”和全球首例感染非典病毒的孕妇等。对于部分新闻人物特别是病患而言,SARS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是“创伤”、“阴影”和“歧视”,因此他们希望自己被“遗忘”。“转折点”隐喻将十年前对新闻当事人的叙事延伸下去,为纪念报道提供了具有新闻价值的素材,也将对个体SARS经历的重述(“过去”)与对其当下生活状况的叙述(“现在”)关联起来。
二是对SARS后遗症患者的报道。《外滩画报》杂志的封面报道以“后非典病人”为题,在14页的篇幅内讲述了7位(个)后遗症患者(家庭)的故事。《东方早报》的专题报道“非典病人”同样聚焦后遗症患者,而《中国新闻周刊》和《新京报》的纪念报道也都触及到这一群体。在“命运转折点”这一概念隐喻的基础上,媒体也使用其他相互关联的隐喻描述SARS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例如“有后遗症的人,日子被定格在非典里”、“后遗症患者被从原来的生活中甩出,定格在2003年那个春天”、“10年过去了,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翻开了无数新的篇章,而方渤的好日子似乎永远停留在了2003年”等。“定格”、“篇章”等表达对应的概念隐喻分别是“人生是一场电影”、“人生是一本书”。与新闻当事人(特别是病愈患者)不同,在后遗症患者身上,SARS继续以“病痛”(股骨头坏死——“不死的癌症”)的形式得到延续。而这些隐喻表达传递出的则是“生命停滞”的含义。与“定格”或“停留”相对应的,则是其他一些隐喻表达。《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沉重的翅膀”的摄影报道,照片中后遗症患者站在自己的胸透片前。报道文字这样解释照片背后的意蕴:
引文6:SARS患者的胸透片几乎全部呈现白色,而正常人的胸透片则黑白相间、看似一对翅膀。许多SARS后遗症患者,多么希望2003那年能在自己的胸透片上看到那对翅膀。这10年来,在“不死的癌症”的阴影下,后遗症患者们奋力携手,期待在逆境中展翅。
在这段引文中,我们看到一个新的隐喻的形成过程:胸透片-翅膀-(折翼的)后遗症患者“展翅”飞翔,它与象征“生命停滞”的隐喻(“定格”)形成鲜明的对照。有趣的是,《新京报》的一篇报道也运用了类似的隐喻来形容SARS病毒感染者的肺片,“白炽灯下,黑色肺片上的白斑清晰可见,像死神展开的翅膀”。市场化媒体在纪念叙事中运用这些隐喻,不仅仅是为了建构个体化的叙事。更重要的是,它们以SARS十周年为话语契机,将之前被媒体忽视的后遗症患者群体带入公共视野。
在将“过去”与“当下”相关联的过程中,新闻媒体还会运用另外一套概念隐喻,即“SARS是分水岭”或“里程碑”。借助这套隐喻,新闻媒体重新将目光聚焦国家和社会,探讨“非典遗产”,反思SARS带来的种种制度变化。
引文7: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来说,SARS疫情的爆发是一个里程碑,SARS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被长期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十年已经过去,而这场SARS疫情,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面镜子,照出了公共卫生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同时也映现出仍然存在的种种问题。(“卷首语”,《中国新闻周刊》)。
这段引述中存在两个概念隐喻,一个是“SARS是里程碑”,一个是“SARS是一面镜子”。这些隐喻在样本媒体中的运用非常广泛,特别是《凤凰周刊》的封面报道“大陆疾控体系十年再检讨”、《新京报》的“SARS拾年:中国抗体”专题报道。问题是,SARS是哪方面的里程碑(SARS带来哪些遗产)?镜子里照出的是“进步”还是“困局”?正是在这些方面,暗含着新闻媒体对隐喻进行阐释的空间和方向。
《南方日报》《中国新闻周刊》和《凤凰周刊》等媒体更多将SARS的“遗产”局限在公共卫生或疾控体系的范畴之内,而《南方人物周刊》和《新京报》则将反思的触角延伸到更多领域。例如,《南方人物周刊》列出信息公开、新闻发言人制度、医疗防疫体制、官员问责、国际合作等法规制度在“SARS前”和“SARS后”的变化,而《新京报》的专题封面制图则引出了对应制度反思的一个新的概念隐喻。图片上方是一颗胶囊,倾倒出绿色颗粒物,上面布满大大小小的文字,“疫情公开”、“公众知情权与健康权”、“信息公开制度”、“疾控直报”、“国际合作”、“政务渐明”、“防治升级”、“领导问责制”、“政府发言人”、“危机应对制度”、“疾控体系”等。这些颗粒物在画面下方汇成四个大字“中国抗体”。特刊前言对此作出如是解释:
引文8:正如人体遭受病毒后,会产生抗体,得以抵御这种病毒下一次袭击;中国遭遇SARS侵袭后,也逐渐产生“抗体”。 十年前,叶欣们用血肉之躯抵抗SARS;十年后,国家抗体承担起庇护国民的重任。
这段引述运用了两个概念隐喻,一是“中国是遭到侵袭的身体”,二是“制度是抗体”。呼应该期专题的封面制图,“抗体”所涵盖的各种制度构成了胶囊的治病成分。在这里,“抗体”隐喻扮演着重要的话语功能。首先,它强调,在应对与SARS类似的公共危机时,制度构成的“抗体”比医护人员的血肉之躯(以及非制度化的应对方式)更有效,其中自然也隐含着对SARS爆发时应对失据的批评。《南方人物周刊》也指出,相较于“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全面动员式运动,法规与制度的完善意义更为深远。其次,SARS前、SARS后的对举,使得市场化媒体将纪念日转变为话语契机,由此回顾制度的成形过程,并对当下的制度运行作出批判性的观察与评价。
结语
新闻媒体对历史事件的纪念报道是重要的公共记忆形态。[23]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公共危机,SARS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叙事线索和多样化的纪念空间。笔者聚焦报纸和新闻杂志对SARS十周年的纪念报道,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及相关的分析手段,检视新闻媒体如何运用隐喻生产媒体记忆。研究发现,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媒体将“疾病即战争”这一概念隐喻转化为众多具体而微的隐喻表达。但在对隐喻意义的阐释上,党报和市场化媒体在战争性质界定、战争主角的选择与呈现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而言,前者更强调高层的决策和英勇抗争过程,把“抗非”建构为一场最终取得胜利的英雄赞歌,而后者则聚焦SARS转变成危机过程中的“人祸”成分。
对于纪念话语而言,重述历史并不是唯一的叙事目的。由于新闻媒体总是关注“当下”并致力于讲述富有新意的故事,它们也努力在纪念报道中建立“过去”与“当下”的关联。研究发现,媒体纪念报道中的个体化叙事主要聚焦两类人,一是新闻当事人,二是SARS后遗症患者。在对个体故事的讲述中,媒体广泛运用“命运转折点”这一隐喻,既强调SARS并未终结,发掘出富有人情味的悲喜故事,也将后遗症患者这一被忽视的人群带入公共话语。而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媒体将SARS视为公共卫生、政府管治等众多领域的“分水岭”或“里程碑”,这一隐喻使得市场化媒体将“纪念日”转变为对当下议题发声的话语契机,围绕SARS带来的制度变化及其当下运作展开批判性的检讨。“转折点”和“分水岭”实质上是同一个概念隐喻的不同表达,它们强调的是历史事件在个体和国家社会层面带来的不同影响。
批判隐喻分析致力于揭示语言表达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从本文的研究发现看,党报和市场化媒体即便运用同样的“战争”隐喻,也会建构出不同的历史叙事,传递出不同的意识形态意涵。此外,纪念报道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文本,不同的叙事目的——重述历史、建构个体化叙事、建立“过去”和“当下”的关联/探讨过去的“遗产”——都会影响它们对隐喻的选择和运用。而从媒体记忆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媒体的纪念报道会延续新闻报道中运用的隐喻,这种延续性有助于新闻媒体呼应并强化公众记忆。另一方面,从SARS这一个案中发掘出的个体层面的“命运转折点”隐喻和国家层面的“分水岭”隐喻,也可能存在于新闻媒体对其他历史事件的纪念报道当中。■
注释:
①③④⑤LakoffG. & Johnson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 310158236.
②LakoffG. (1993).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2nd edn) (pp. 202-25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⑥LakoffG. (2012[1991]). Metaphor and war: The metaphor system used to justify war in the Gulf, Journal of Cognitive SemioticsIV (2): 5-19.
⑦GamsonW. A.& LaschK. E. (1983).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In S. E. Spiro & E. Yuchtman-Yaar (Eds.)Evaluating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pp. 397-415). San DiegoCA: Academic Press; Gamson, W. A.&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51-37.
⑧ HellstenI. (2000). Dolly: Scientific breakthrough or Frankenstein’s monster? Journalistic and scientific metaphors of cloning. Metaphor and Symbol, 15 (4)pp. 213-21.
⑨Nerlich, B.Clarke, D.& Dingwall, R. (2000). Clones and Crops: the use of stock characters and word play in two debates about bioengineering. Metaphor and Symbol, 15 (4): 223-39.
⑩[13]甘莅豪 :《媒介话语分析的认知途径:中美报道南海问题的隐喻建构》,《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8期
[11]Kitis, E. & MilapidesM. (1997). Read it and Believe it: How metaphor constructs ideology in news discour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28557~90.
[12]LuleJ. (2004). War and its metaphors: News language and the prelude to war in Iraq, 2003. Journalism Studies5 (2): 179-190.
[14]邓育仁、孙式文:《隐喻框架:台湾政治新闻里的路途隐喻》,《新闻学研究》2001年总第67期
[15][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第8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16][21]Wallis, P.& NerlichB. (2005). Disease metaphors in new epidemics: The UK media framing of the 2003 SARS epidemic.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02629-2639.
[17]ChiangWen-Yu & DuannRen-Feng (2007). Conceptual metaphors for SARS: “War” between whom? Discourse & Society18 (5): 579-602.
[18]严格意义上说,《外滩画报》不能算新闻杂志,但这篇题为“后非典病人”的封面报道是很典型的人物特写报道。
[19]版面数均为排除广告的结果。另外,新闻杂志和报纸的版面大小不一样,不可以直接对比。
[20]Charteris-Black, J. (2004).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pp. 34-43.
[22]报道主角是指该人物在报道中占据至少一半以上的篇幅。
[23]李红涛:《昨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媒体记忆、集体认同与文化权威》,《当代传播》2013年第5期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为了忘却的纪念: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播”的资助,课题号:11YJC860023。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白红义博士对此文的撰写帮助良多,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