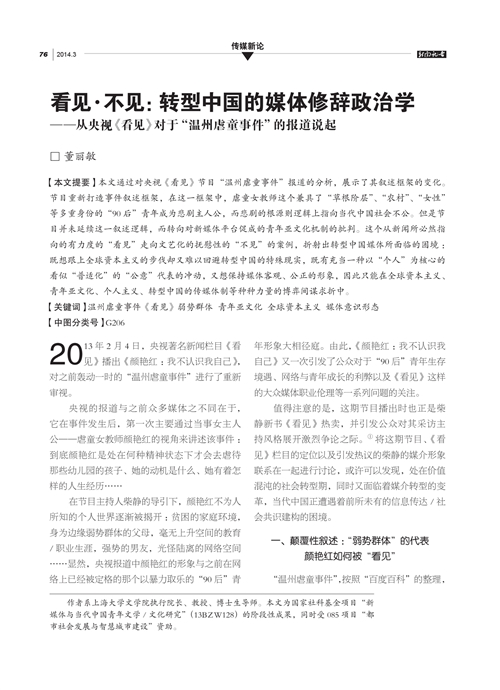看见·不见:转型中国的媒体修辞政治学
——从央视《看见》对于“温州虐童事件”的报道说起
□董丽敏
【本文提要】 本文通过对央视《看见》节目“温州虐童事件”报道的分析,展示了其叙述框架的变化。节目重新打造事件叙述框架,在这一框架中,虐童女教师这个兼具了“草根阶层”、“农村”、“女性”等多重身份的“90后”青年成为悲剧主人公,而悲剧的根源则逻辑上指向当代中国社会不公。但是节目并未延续这一叙述逻辑,而转向对新媒体平台促成的青年亚文化机制的批判。这个从新闻所必然指向的有力度的“看见”走向文艺化的抚慰性的“不见”的案例,折射出转型中国媒体所面临的困境:既想跟上全球资本主义的步伐却又难以回避转型中国的特殊现实,既有充当一种以“个人”为核心的看似“普适化”的“公意”代表的冲动,又想保持媒体客观、公正的形象,因此只能在全球资本主义、青年亚文化、个人主义、转型中国的传媒体制等种种力量的博弈间谋求折中。
【关键词】 温州虐童事件 《看见》 弱势群体 青年亚文化 全球资本主义 媒体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G206
2013年2月 4日,央视著名新闻栏目《看见》播出《颜艳红:我不认识我自己》,对之前轰动一时的“温州虐童事件”进行了重新审视。
央视的报道与之前众多媒体之不同在于,它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次主要通过当事女主人公——虐童女教师颜艳红的视角来讲述该事件:到底颜艳红是处在何种精神状态下才会去虐待那些幼儿园的孩子、她的动机是什么、她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
在节目主持人柴静的导引下,颜艳红不为人所知的个人世界逐渐被揭开:贫困的家庭环境,身为边缘弱势群体的父母,毫无上升空间的教育/职业生涯,强势的男友,光怪陆离的网络空间……显然,央视报道中颜艳红的形象与之前在网络上已经被定格的那个以暴力取乐的“90后”青年形象大相径庭。由此,《颜艳红:我不认识我自己》又一次引发了公众对于“90后”青年生存境遇、网络与青年成长的利弊以及《看见》这样的大众媒体职业伦理等一系列问题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节目播出时也正是柴静新书《看见》热卖,并引发公众对其采访主持风格展开激烈争论之际。①将这期节目、《看见》栏目的定位以及引发热议的柴静的媒介形象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或许可以发现,处在价值混沌的社会转型期,同时又面临着媒介转型的变革,当代中国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信息传达/社会共识建构的困境。
一、颠覆性叙述:“弱势群体”的代表颜艳红如何被“看见”
“温州虐童事件”,按照“百度百科”的整理,基本被描述为一个由网友“人肉搜索”所引发的网络介入现实的“草根民主”事件:
2012年10月24日,有网友在微博中转发了一张虐童照片。在这张照片中,一位幼儿被年轻女教师揪起双耳拎离地面数十厘米,表情十分痛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女教师居然面带微笑,带着明显的“秀”的兴奋。这张照片激起了网友们的公愤,被疯狂转发,同时对当事人展开人肉搜索,很快确定虐童者为浙江温岭蓝孔雀幼儿园教师颜艳红。颜艳红的个人信息也随之被曝光。
虐童事件的当事人颜艳红,1992年4月出生于温岭农村,初中毕业后进入温岭市教师进修学校学习,其后进入民办温岭蓝孔雀幼儿园工作,无教师资格证与上岗证。在颜艳红个人QQ空间中,还有十余张虐童照,有的是把孩子扔进垃圾桶,有的孩子被蒙住面孔,有的嘴巴被贴胶带封住……网友们惊呼:“虐待孩子的恶行不是第一次了!罪证都是现成的!”颜艳红因此被斥为“变态老师”、“不良少女”甚至“禽兽”、“畜生”。②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温岭市教育局迅速做出反应,当即要求涉事幼儿园整改并开除颜艳红。浙江省教育厅也于10月26日专门下达文件,要求“立即处置并严肃处理,坚决防止和制止任何伤害学生的行为,尤其要坚决杜绝虐待学生事件的发生”。随即温岭市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罪”对颜艳红予以刑事拘捕,后因“不构成犯罪”而撤销刑事诉讼,并对颜艳红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温岭警方还报告称:“经我们调查,颜艳红涉嫌虐待儿童与个人感情没有太大关联。据供述,她只是为弥补内心空虚,寻求开心,仅此而已。” ③
为什么“好玩”这个看似无厘头的诉求居然能够成为决定当事人行为的关键要素?这成为《看见》节目要回答的问题所在。④由此出发,《看见》在报道中,并没有简单地重述这一恶性事件本身,而是将受虐儿童和家长的愤懑与哭诉作为叙述的由头,把讲述的重心放到了施虐主人公颜艳红身上。《颜艳红:我不认识我自己》选择了以颜艳红自己的讲述作为新闻的主线,辅之以家人、男友、同事、好友、园长、老师、家长等人对事件的反应及对颜艳红的看法,着重展开对颜艳红特定心理状态的发掘,由此形成了以下几个剖析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进路:
1.成长环境
颜艳红贫寒的农村家庭出身首先被《看见》所关注。用招贴画作为挡风玻璃的“楼板已经塌陷的”破旧的家,用了“十几年的老电视”,“少言寡语,有肺结核,不能干重活” ⑤的父亲,因接二连三丧子而“精神有点反常”、“几乎从来不下楼”的母亲,以及因为贫病交困、因为怕村里人“看不起的”眼光而基本上没有社会交往的孤独的人生……当摄像机用长镜头一一扫过这些具有隐喻意味的沉浸在黑夜中的颜艳红的生存世界要素的时候,画面的凝滞、压抑和晦暗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颜艳红在她QQ空间中的感慨:“为什么要有我的出世,原来都是痛苦,受不了。”在这样的叙述中,无论是颜艳红还是隐藏在摄像机背后的叙事人,显然都颇为认同时下流行的“拼爹”逻辑,即,颜艳红的人生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幸的,而不幸的根源在于她出身贫寒,无法掌握有用的社会资源。
而对这一看似不可逆的人生起点命定性的揭示和渲染,显然会在使人将目光转移到让其绝望的当代中国给底层年青人所制造的恶劣的成长环境上。而颜艳红的感慨,更是清晰地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固化、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空间的堵塞,使整个节目具有了对当代中国社会不公的揭露和批判的意味。由此,通过将叙事者眼光内化为当事人的立场,《看见》以“同情的理解”的姿态探索了一种具有翻转意味的叙述修辞政治:原本被贴上了道德沦丧标签的颜艳红,因为既被当作是当代中国社会“拼爹”病症的一种表征,同时又被看作是这种病症的牺牲品,其人生就具有了可以被多面解读的歧义性——相对于更为弱小无助的孩子,丧失基本职业伦理甚至人性的颜艳红当然会引发众怒;但是相对于当代中国大众最为痛恨的权贵阶层与生俱来的“原罪”,草根阶层出身的颜艳红所阐发的来自生命起点的无奈与无助,又会让人对其不由自主地产生同情。
2.教育与职业经历
《看见》对颜艳红教育背景以及职业生涯的进一步挖掘,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印象。“从小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倒数第几名的状态”,因为“幼师学费少,好找工作”,颜艳红在初中毕业后便报考了温岭市教师进修学校表演艺术专业幼师方向。在“混日子”式的学习生涯结束后,她如愿以偿地成为了蓝孔雀幼儿园这一位于温岭城乡结合部的私立幼儿园的一名教师,然而每月工资只有1500元,“这在处于浙江东南部,经济发达的温岭来说,是很低的月收入,她的衣服都是从服饰城几十块钱买来的,在微博上她感叹‘要饭的都比自己有钱’”。
在从“家庭人”走向“社会人”的过程中,“教育”无疑一直是被当作填平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创造新的平等机遇、打破阶层固化的主要手段。然而,节目中颜艳红的经历却表明,这一功能似乎是落空了:因为成绩平平,颜艳红只能接受地方性的中等职业教育,在人才市场上缺少竞争力而无法获得优质薪酬的工作;因为是女生,她为未来就业所选择的学习专业似乎也很有限,只剩下打上鲜明女性气质烙印的“幼教”行业;因为上述种种原因的综合,甚至连就业地点也只能是各方面条件较差的“城乡结合部”……
在这样的讲述中,可以看到,在当代中国,经过教育,颜艳红也没有获得多少新的社会资源,而更像是对苦苦挣扎在底层的父母命运的一种简单复制。而这一观点,显然与廉思在《蚁族》中对青年低收入群体的调查结论不谋而合,即,毕业于“地方院校和民办高校”的“80后”大学生更容易成为“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即“蚁族”。⑥教育在当代中国显然不仅没有再生产出社会公平,反而使得年青人在“出生”起跑线上已经出现的差异进一步拉大。
3.两性关系
尽管如此,对于颜艳红来说,改变人生似乎还存在着其他可能性。在《看见》中,颜的女性朋友直言不讳:“反正一开始时候,选择幼师,没打算一辈子做”,因为幼师工作只是“青春饭”,以后可以通过嫁人另谋生计。但对于颜艳红而言,这条路似乎也走得不顺。由于交往的男朋友“有点管不住自己,总打游戏,和别的女孩暧昧,争吵的时候对女朋友大吼”,颜艳红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感受到的种种压力和情绪无法在男友处得到转移和缓释,相反,还要经常委曲求全地扮演主动求和的角色,她的内心深处反倒堆积了更多的负面情绪垃圾。在她的QQ空间中,这些情绪垃圾被以一种充满暴力的言语宣泄形式表达出来:“你能给我什么,滚”,“伤痕累累的想死”,“你要是敢,我拿菜刀砍死你”……
在《看见》如此细致入微地挖掘中,与颜艳红原本让人印象深刻的强悍的网络/现实形象截然不同的脆弱一面被呈现了出来——这是一个心灵受伤而得不到抚慰的饱受家庭冷暴力影响的受害者形象,也是一个恪守在传统的“男强女弱”的两性关系结构中无法挣脱的软弱者形象。与这样的形象相匹配,她发布在网络的暴力性言辞似乎也就具有了女性亚文化意义上“抵抗”的正当性意味。
4.《看见》的颠覆性叙述框架
立足于上述三个面向,很容易得出一个初步印象就是:《看见》试图借助颜艳红这一个案,另辟蹊径,重新打造“温州虐童事件”的叙述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是颜艳红这个兼具了“草根阶层”、“农村”、“女性”等多重身份的“90后”青年,而不是那些被她虐待的孩子,成为了悲剧主人公。制造这一悲剧的,主要是“出身”所暗含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教育”所指向的后天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不合理,以及“爱情”所挟带的传统的两性不平等关系。因而,如果要进一步来分析这一悲剧的根源的话,一定会指向对当代中国社会不公的抨击,指向夹杂了阶级压迫、代际压迫和性别压迫等多重因素的转型中国族群区隔甚至断裂的内在困境。
《看见》由此似乎复制了人们所熟悉的立足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叙述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官/民、男性/女性、城市/农村、权贵资本主义/草根阶层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叠加,构成了故事的基本结构与行进动力,而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呼声则夹杂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满而浮出历史地表。其潜在指向的,显然是对社会制度重组的政治性企盼。而这,与网络世界中对颜艳红进行道德指责的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差异。
二、叙述逻辑的突变:QQ空间、虚拟社会化与青年亚文化
耐人寻味的是,《看见》对颜艳红故事的讲述最终并没有完全顺着上述框架滑行,得出一个看似合理的抨击当代中国社会痼疾的结论,而是出现了峰回路转。
1.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讲述逻辑
在节目后半段,《看见》提供了不同于上述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另一种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讲述逻辑:尽管颜艳红在自己的QQ空间中曾表示:“对某些人(男友)的火,全发泄在学生们身上。烦。”然而,在接受《看见》采访的时候,她对此却矢口否认,更强调其在QQ空间中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言不由衷的伪装与掩饰,“都是写给别人看的/就是发泄自己,心理情绪,然后故意给别人看,”并不真实。而《看见》经过简单的时间比对,也认为颜艳红的虐童行为“的确与感情刺激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些照片的拍摄基本上是从她建立QQ空间开始”,认为对QQ空间的过度依赖,使得颜艳红甚至“没意识到说这是在虐待,或者伤害孩子”。
由此,“QQ空间”这一新媒体时代的特有信息平台被推到了前台,成为《看见》讨论颜艳红虐童动机的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全新视角,而这一新视角的出现,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冲淡并转化了前面虐童事件所负载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
《看见》发现,“QQ空间”对于颜艳红来说,具有“精神上的寄托”的意味,借助这一平台,颜艳红“想要有另外一个自我的形象”,一个“光鲜亮丽,然后就很要强”的现代强势女性形象。为了打造这一形象,她标榜自己是“豹纹控”、“吃货”、“喝酒就要喝百威”、“哪里有酒就去哪儿”,而且通过上传大量浓妆艳抹的生活照,通过展示身上另类的“烟疤”刺青,通过散布“没有考试,是托关系进去的”虚假入职信息,通过诸如“不动手打你,你不知道我文武双全”等宣泄性的暴力话语,“来掩盖难堪”。
藉由“QQ空间”,颜艳红建构起了一个与日常生活中的自己截然不同的网络形象/身份,并且因为对于这样的虚拟形象/身份的过分迷恋和认同,而逐步影响到了自己的真实世界——在日常生活中,她“感到的失败感和不耐烦越来越强”,“每天早上拉个脸打的来上班,跟白痴一样一天坐到底等下班后打的回去,不想上课,动也不想动。能懒就懒”。而大量虐童照片就是在这一阶段被密集上传的。
2.虚拟社会化机制提供的“想象性抵抗”
社会学者指出:“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浪潮的高涨,虚拟社会化机制将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真实社会化与虚拟社会化的断裂”将导致“青年角色认同危机”。⑦很显然,在《看见》的视野中,颜艳红的所作所为,正是两种“社会化”之间彼此对立、互为作用而产生的青年角色认同危机的表征。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危机直接导向了青年亚文化的出现,导向了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所指出的青年亚文化在现实功能上的“双重意味”:一方面,它们事先向“正统”的世界发出警告,它们是一种邪恶的存在,是一种差异的存在,并且招致了模糊的猜疑和不安的笑声,以及“把人气得脸色发青、瞠目结舌”;另一方面,有人却把它们当作暗号或咒语来使用,并赋予它们以圣像的地位,对他们来说,这些物品则变成了“被禁止的身份符号和价值观的源头”。⑧
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将颜艳红这样的弱势群体抛出了社会主流轨道之外,让她们感受到了无力感与无助感,然而这种无力感与无助感却并没有积聚为一种正能量,而是因为有了“QQ空间”等可以进行身份虚拟的媒体手段的介入,蜕变为各种具有“想象性抵抗”意味的亚文化符码:一方面青年弱势群体通过“类强者”的妆饰、表演和展示,建构起了与主流价值观念既认同又背叛的具有悖论性的青年亚文化身份认同,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缓释来自现实世界作为“失败者”的焦虑情绪;另一方面,青年亚文化身份认同的内在断裂所制造的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紧张关系,又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虚拟世界中越是光鲜亮丽,越会烛照出现实世界的黯淡压抑,反之亦然。如何在心态失衡的怪圈中寻找新的平衡点,成为势之必然。某种意义上,在《看见》看来,颜艳红欺凌远比自己更为弱势的幼童群体,正是新的心理平衡点制造的路径选择之一。
3.青年亚文化及其发生机制视角的展开
在这里,通过引入“QQ空间”,《看见》将温州虐童事件的发生根源从政治经济层面引导到了传播技术层面——似乎是“QQ空间”这样的网络虚拟平台对于青年现实不满情绪的默许、纵容和反向发酵,才是推动颜艳红沦落的直接因素。在这样的描述中,很自然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并不是那些先天和后天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将颜艳红推入反社会、反伦理的道德深渊——很大程度上,这些因素只是潜在的风险,只有当它们与青年亚文化/身份认同得以产生和运行的网络媒介榫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产生出类似虐童事件这样的严重后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社会方方面面是否对青年亚文化及其发生机制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看见》后半部叙事的重点。
《看见》指出:“她的QQ空间最初是公开的,朋友和一部分同事都可以看到。除了一个陌生人之外,没人向她提出过不妥。”周围环境的宽容显然成为颜艳红那个奇装异服、行为叛逆的“自我”得以在网络世界中膨胀的重要条件;与此相呼应的,是现实世界中的颜艳红的“外形和情绪的明显变化,也没有在她工作的蓝孔雀幼儿园引起重视”,并且由于“教室没有装监控的摄像头”,“门一关,老师跟孩子发生的一切就关在了里面”这也被认为是虐童事件得以发酵的现实基础;而国家层面上的法律对此类虐童事件的监管和处罚存在盲区,《教师法》中相关规定在现实情形中的执行不力,也成为《看见》讨论虐童事件的重要依据。甚至,《看见》还将反思的目光延伸到作为受害者一方的幼童家长。那些与颜艳红一样来自社会底层的家长们,因为生计所迫而对孩子照顾不周的内疚以及在此事件后的追悔莫及,在《看见》的特写镜头中,也被放大为虐童事件得以发生的一种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转型中国“家长监管缺位”的问题。
4.转型中国的媒介修辞特色
从社会政治经济层面到媒介传播、社会监管层面,《看见》对于温州虐童事件的讲述,显然充满了转型中国的媒介修辞特色——一方面经历了一个讲述重心转移、反思力度减弱的过程,但必须注意到,其在处理主人公的立场、基调方面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
无论在哪个层面,《看见》所呈现的颜艳红更像是一个涉世未深、无知软弱的可怜者,而不是老谋深算的施暴者:在政治经济层面所把握到的颜艳红是底层弱势群体的代表;在媒介传播层面所分析出的颜艳红是被新的媒介技术蛊惑而不能自拔的懵懂无知者;在社会监管层面所发掘出来的颜艳红则是监管缺失的受害者。
《看见》节目报道中对颜艳红的形象颠覆,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中国大众伦理道德意识,而有触犯众怒的危险,其用意相当耐人寻味。
从叙述表层来看,通过将颜艳红叙述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弱势群体代表,《看见》很大程度上以“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态,推动整个事件从对某个人道德与职业伦理的指责转移为对导致这一后果的当代社会的反思,从而超越了作为行动者的个人层面,延伸到了社会结构、传播技术、法律监管等外在的层面。这一视角有助于打破既有的叙述/呈现对于“问题青年”的刻板印象,使其可以在更为复杂的格局中被认识。⑨但同时,这一视角也会因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迎合甚至承认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群体特别是网络青年亚文化群体中弥漫的反主流、反体制、反社会的激进情绪,又有沦为片面为其代言而忽略真正的弱势群体(如那些受虐的孩童)的危险。
这一“双刃剑”效应,暴露了《看见》预设立场的伦理争议性所在。即,如何有分寸地把握颜艳红作为“问题青年”与“弱势群体”双重代表其所值得同情之处;这种令人同情之处是否可以与那些被她所虐待的孩童相提并论;还有,对于颜艳红的同情是否有必要因为其容易在群情激愤之时被忽视而被格外强调出来……
而当《看见》采取主要从颜艳红的视角来梳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时候,显然对上述一系列容易导致道德伦理困境的问题未予更多思考,由此又凸显了在其视野中,作为“个人”的“青年”的重要性及其必须作为切入问题的基本单位的不容置疑性。这一立足点,显然呼应了198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个人中心主义思潮,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暗合了全球资本主义对以“青年”为主体的个体劳动力询唤的需要——事实上,对“青年”及“青年意义”的强调,正如吉利斯(G.R.Gillis)所指出的:“是工业化以及社会近代化的需要及其结果。近代工厂的出现,将年轻人们从传统的家庭/共同体中吸引(或驱赶)进城市,使其成为产业大军的生力军。” ⑩而将上述两方面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其间的曲径通幽处——以“现代化”的个人主义利器所展开的对传统中国社会及其伦理体系的质疑乃至解构,正是1990年代之后驱使当代中国青年以原子化劳动力形态大量涌现并进入世界工厂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青年亚文化所天然流露出的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冷漠、疏离与对立,既有着对当代中国国家威权主义的反感与逃避的成分,又在很大程度上加固了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须的个人主义,从而也潜在地成为建构全球经济-市场一体化合理性的推动性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看见》对颜艳红这样的“问题青年”的同情,就可能不只是对青年亚文化的一种理解式认可,而更需要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区域扩张所需要征用和建构的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甚至可以被视为是后者的合谋者了。
5.弥合媒介身份的努力
尽管《看见》意欲凸显“个人”价值、凸显“青年”意义的意图历历可辨,然而,当颜艳红的故事还是被放置在从政治经济层面向网络传播、法律监管层面转换的叙述结构中来进行的时候,其实又是在提醒我们,《看见》所探索的叙述可能性及其限度所在。处在央视这样的新闻媒介平台上,《看见》多多少少还是意识到了作为国家主流媒介应该承担的责任,某种意义上,以折中方式来处理内容与方式之间存在的分裂,可以被看作是弥合这一分裂的努力——从其传达的内容上看,《看见》对各种现实压迫性因素的发掘,仿佛正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需要高度呼应而充溢着现有社会体制的挑战激情,而这,显然是与其作为国家主流媒体的责任有所悖逆的;从其叙述结构上看,《看见》规避了与“颜艳红如何成为弱势群体”的现实政治真正的短兵相接,而在很大程度上将其降落在由新媒体为主导的青年亚文化上,强调技术、法律对青年亚文化进行调适和监管的重要性,这显然是一种避重就轻,可以视之为是其本应承担的主流媒体责任一种回光返照式的介入的结果,也是其恪守现有传媒体制格局而进行自我约束的一种选择。因而,作为这一充满了张力的叙述形态设计的必然结果,青年亚文化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伴生物,以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的姿态被迅速推到了本不应有的高度上;相应地,则是主流媒介所本应承担的介入/引导现实从而激发其正能量的责任的无声消逝,以及犬儒意义上的技术维度分析的大行其时。
三、媒体呈现的政治:“二次曝光”与“抵达真相”
正如费斯克(John Fiske)所指出的,新闻对负面事件的报道,一般是为了肯定“我们的社会规范”、“肯定我们的主流认识”。[11]那么对于“央视”这样具有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权威新闻平台上的《看见》来说,这一功能显然会得到强化。如果要进一步来分析上述媒体意识形态得以形成的根源的话,显然还须充分注意到转型中国的当下现实、媒介格局,特别是传媒人站位的复杂性。因而,《看见》本身是否真的导向了“看见”,就成为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
1. 《看见》:建构“二次曝光”的后发优势
简单扫描一下《看见》自2010年底开播以来的轨迹,就可以发现,类似“温州虐童案”的新闻叙述绝非个案,特别是在其一系列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专题报道中,有关底层故事的叙述,在视角、立场、结构等方面往往给人似曾相识之感。比如:《十五元停车费引发的悲剧》(2011年1月30日)、《“名人”赵作海》(2011年3月25日)、《专访药家鑫案双方父母》(2011年8月16日)、《潇湘救赎》(2012年2月19日)、《孝子弑母》 (2012年7月15日)、《少女抗暴杀人案》(2012年12月9日)、《兰考弃儿》(2013年1月13日)、《十年牢狱谁之过》(2013年4月8日)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聚焦具有巨大道德伦理争议的社会底层违法犯罪案件;具有转型中国社会特殊烙印的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往往既是作品无法规避的背景又是其试图挑战的目标;或激烈、或执拗、或压抑地挣扎在此漩涡中不能自拔的年轻人飘忽不定的身影时常是摄像机捕捉的目标;而一种无法被冰冷的镜头所隐匿的打上“普适性”印记的人道主义同情,则是叙事者基本的切入立场。
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如同“温州虐童案”一样,许多新闻线索最初也来自网络。在自媒体(We Media)和社交媒体(Social Media)飞速发展的时代,像《看见》这样的传统新闻媒体往往要等到事件已经在网络上酝酿、发酵乃至成型之后才会介入:“网络舆论推动并裹挟着传统媒体持续关注的热度,并不断为传统媒体设置议题,传统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网络媒体议程设置的实施者。” [12]在这样的情形下,较之于网络媒体,像《看见》这样的传统媒体只能进行“二次曝光”式的报道,因而就面临着一种信息传递的困境——当网络世界的“乌合之众”已经形成相对凝固的舆论之后,如何来建构“二次曝光”的后发优势,并且能力挽狂澜改变大众通过互联网所获得的第一印象?[13]《看见》显然相当清楚自己的处境。[14]作为一档记录现实的专题新闻节目,《看见》自2010年12月6日问世之后,一直以关注“观察变化中的时代生活,用影像记录事件中的人”作为节目宗旨。[15]这一定位,显然既与网络媒体的呈现重心有所不同,也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差异。《看见》栏目主编王开岭这样解释道:“《看见》之初,我们斟酌最多的即如何界定与‘新闻’的关系:既和‘新闻’保持一定的亲密性,又试图在公共注意力之外增补自己的注意力……我们与新闻的关系是:既服从,又反抗。新闻不是我们的本位和目的,它仅仅被我们当成地图,充当选题会的桌面。” [16]在新闻报道过程中,《看见》更为注重的是人文情怀的传达:“在其(新闻)上,我们要放两只‘人文’的杯子,即栏目的两个单元:人物访谈和纪录风格的故事。前者侧重对新闻人物的精神访问(尽量在热点事件和规定人物中安置自己的注意力和精神路径,追求‘新闻抵达’之上的‘精神抵达’,从而把对人和事的‘了解’升级为‘理解’);后者向观众推荐我们自以为珍贵的人性故事和精神活动(在公共注意力之外繁殖自己的注意力,这些故事多具隐蔽性)。” [17]当“精神抵达”被看作是比“新闻抵达”更为重要的新闻目标的时候,对“人性”、“精神”等人文维度的强调,无疑为新闻中的“人”理直气壮地出现在新闻的前台,也为新闻制作者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叠加到新闻中去建构了某种合法性。
2.柴静:发掘“新闻中的人”的立场
而作为《看见》的主要出镜记者,柴静自2002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以来,就坚定不移地认同并实践了发掘“新闻中的人”的立场。[18]柴静曾这样阐释自己对于新闻采访的理解,“采访是呈现,不是评判”,“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在这一前提下,柴静认为“媒体的职责不是提供‘热’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动社会的热情,媒体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由此,采访者就应该将现实角色与职业角色进行有效区分,将新闻事件与新闻中的“人”区别对待:“我现在对自己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事苛刻,对人宽容。”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突破概念”,“抵达一个真实的人”。[19]当“抵达一个真实的人”被当作新闻专题节目的核心甚至是其基本符码的时候,可以看到节目制作者对于传统新闻文化的微妙修改。如果说第一时间传递信息被当作传统新闻的追求目标的话,那么,将滞后的“信息”藉由“个人”这一中介编织为一种文本,一种充满了故事、耐人咀嚼的“文艺节目”,[20]同时有意识地覆盖上新闻采访者“理解”的“目光”,分明成为《看见》在网络信息爆炸时代处在后发位置的媒体所能想到的突围之道。这一修改,一方面似乎可以越过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而无限“抵达真相”——假如各种“个人”的叙述可以还原现场的话;另一方面,却又不免会在新闻最为注重的“客观性”维度上招致各种非议:如何来验证新闻现场中的“个人”其讲述的可靠性?如何来验证采访、组织、编辑这些“个人”的叙述的记者其立场的客观性?打上了新闻采访者自身价值立场和情感向度烙印的“真相”是否具有公信力?
3.一场并无实质性分歧的争论
正是在这样的疑虑中,围绕电视新闻节目《看见》以及柴静的新书《看见》,展开了一场有关新闻媒介呈现尺度的争论。[21]凤凰卫视著名记者闾丘露薇在自己的博客中对柴静的专业素养提出批评:“有人说记者采访是‘一种抵达’,我想了半天,就是不明白。其实采访一点也不玄乎,就是提问,把事实弄明白,把原因找出来。也因为这样,新闻采访,强调的是要有新闻点,一个人再有名,如果没有新闻点,那就不是新闻记者应该采访的对象。” [22]在闾丘露薇的视野中,“人”与“新闻”显然不能混为一谈,“人”只是进入“新闻”、传递“新闻”的一种符码,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新闻”是由“新闻”决定的,“人”本身并不能超越“新闻”而成为独立的被采访内容。在此前提下,她又对记者的职责进行了梳理:“如果一个记者,做新闻只关心新闻中的人,而不是新闻事件背后的原因,那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倾听者,这是不称职的,……如果只是关注人而不去寻求这个人的遭遇背后的原因,那这样的新闻报道是不合格的。当然,这样做会很安全,也很讨巧,但是最终受益的,是媒体人本身,却不是公众。” [23]闾丘露薇相当明确地区分了“记者”(新闻)和“主持人”(娱乐)之间的差异性,认为记者的功能显然应有别于政府人员,也不同于公益人士,应该通过还原事件来追溯真相,通过个案最终关注公众利益,因此,新闻记者必须要恪守如何真实地传递“信息”这一边界,也要据此处理好自己在事件报道中的位置和角色,因而记者并不适合喧宾夺主地活跃在新闻前台,尽管他或她也很有人文情怀。
央视主持人董路认同闾丘露薇的看法,他进一步批评道:“柴静的表演以情绪为主,她一个又一个丰富中透着呆板的表情动作,引领着观众的喜怒哀乐。外景地里就像戴安娜,差点喊一句‘乡亲们受苦了’。”“柴静像雷锋,雷锋不论帮助了多少人,人记住的都只是雷锋,柴静不论采访了多少人,人们记住的都只有柴静” [24]在董路看来,柴静对于访谈类新闻的把握无疑出现了偏差,从一个应该犀利地剖析新闻事件的采访者蜕变为一个引导采访对象/观众进行情绪宣泄的抚慰者,这种风格可以看作是柴静借着新闻在“表演”,成全了柴静自己在镜头前的富有爱心和现实关怀的女性公共知识分子完美形象,却无助于事件真相的开掘。
面对闾丘露薇等人的指责,柴静保持了沉默,倒是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和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杜骏飞先后在网络上为其辩护。张志安认为:“记者可以有不同种类。通常来说,寻求个人遭遇背后的原因,具有重要性;而当个体心智被道德判断遮蔽或制度归因无甚新意时,关注人性本身尤有意义”。[25]作为《看见》编导范铭的老师,杜骏飞在长微博《我们怎样抵达新闻?》中指出,“自《哈钦斯报告》以来,纯粹的经验主义的新闻学已不再是唯一的理念诉求:一方面,新闻业必须真实和公正;但另一方面,新闻也必须将‘信息流、思想流和情感流送达每个社会成员’”,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新闻还不是事件,而是人;最重要的新闻报道还不是发现事件,而是发现人——发现人的情感、权利和尊严”。因此,“柴静的新闻文本聚焦于人,绝非是没有价值的,更没有违反新闻旨趣”。[26]很显然,无论是张志安还是杜骏飞,都将人性、自由、权利等作为当代中国新闻报道的核心关注点所在,在这一前提下,无论是事件中的个人还是作为讲述者的个人,都获得了毋庸置疑的合法性;“新闻”由此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对人的发现,而不是对事件的呈现。通过将“个人”意义放大,一方面,杜骏飞等人以欧美新闻传播学的最新进展为比附,认为“新闻”不能简单建立在以“客观性”为基础的“新闻专业主义”之上,这种观念因为与欧美“前沿”新闻理念同步而仿佛具有了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们显然也不避讳“重个人、轻事件”的新闻立场选择,其实就包含着当代中国忽略人性、权利的基本判断在里面,因而凸显个人正是指向了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而这正是他们所更为推崇的。
此后,闾丘露薇再次回应:“新闻事件当然离不开人,新闻之所以是新闻,就是不能只到个案为止。追寻背后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为了让社会进步,让个体更有尊严,最终还是回到人。”她同时指出:“既然作为一个新闻人无法正常地做新闻是事实,那就要大方承认,而不是自我欺骗,同时也欺骗大众,让大家以为,做新闻就是这样做的。” [27]在新闻是为了让社会进步、让个体有尊严这一点上,闾丘露薇显然与张志安等人形成了共识,只是在当代中国需要怎样的新闻及新闻呈现技巧上,双方分歧依然存在——闾丘露薇更愿意相信硬性新闻的重要性,所谓“百年来,不断发展的新闻职业理念和一系列操作性规范都在要求记者要尽可能‘专业’地去观察和记录事实,而不是制造事实或成为事实的一部分”,[28]因而仍然对柴静更多具有抚慰当代人心作用的软性主持风格颇有微词。
可以说,双方关于《看见》的争论主要在新闻呈现的“真实性”与“有效性”这两个维度上,具体表现为对新闻记者的角色与功能、新闻报道的构成要素是事件还是个人、新闻的作用等方面的不同看法,其焦点是新闻记者作为特殊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硬性还是柔性面对/介入当代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作为新闻前提的当代中国,双方在判断上其实并无多大分歧——在他们的视野中,当代中国无疑是一个新闻人无法正常做新闻的时代,也是人性、权利、尊严得不到保障的有问题的时代;因而对于要以人(作为新闻对象的“个人”和作为呈现者的“个人”)为出发点和归宿来组织新闻,双方也形成了默契。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究竟是硬性还是柔性地做新闻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能否在反思全球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以单个的“人”为中心来考量国家/社会的简单模式问题的基础上,超越新闻(个人)与国家(社会)这样立足于公民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规避因为过于同情原子化的个人而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亚文化认同而简单地“反国家”、“反社会”的危险?显然,这样的追问无论在《看见》中还是在围绕《看见》所展开的讨论中是缺席的,而这才是当代中国各种媒介以及媒介人普遍的盲区所在,也是转型期中国媒介意识形态更大的危机所在。
小结:作为症候的“地方”媒体意识形态
回到《看见》对于温州虐童事件的呈现个案上,可以发现,《看见》通过征用多种看似并不完全一致的话语资源,其实是形成了一种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相呼应的“有问题的” “地方”媒体意识形态:《看见》以倾听者的姿态“看见”了那个因为违背伦理道德被大众口诛笔伐而无法发声的虐童主人公颜艳红,并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却也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主流认识”而导致了自己作为权威媒体的位置发生了位移,也因为担纲了抚慰者的角色而偏离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伦理。《看见》“看见”了网络大众所没有看见的颜艳红贫穷而纠葛的日常生活,却又迅速地避开了“全球资本主义”这一最为重要的讨论维度,而是简单地将其纳入到由网络所引发的青年亚文化的分析框架中,从而使得对这一事件的挖掘更多只停留在外围和细部,而无法推动其完成从“个人”事件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公众”事件的转化。《看见》“看见”了网络形塑青年角色/身份的强大,但却仍然选择了主要将“网络”作为抨击的对象,这一单一路径选择也显示出其作为传统主流媒体对于新媒体崛起挥之不去的敌意以及保守的心态。
从新闻所必然指向的有力度的“看见”走向文艺化的抚慰性的“不见”,《看见》折射出转型中国媒体所面临的困境:既想跟上全球资本主义的步伐却又难以回避转型中国的特殊现实,既有充当一种以“个人”为核心的看似“普适化”的“公意”代表的冲动,又想保持媒体客观、公正的形象,因此只能在全球资本主义、青年亚文化、个人主义、转型中国的传媒体制等种种力量的博弈间谋求折中。
然而,当年轻的制作者们总是不假思索地从带有鲜明的自我认同色彩的“个人”出发,来进入新闻采访的时候,这一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全球化推进步伐的立足点已经决定了,其反思转型中国社会征候的全部努力,只能指向空洞化、碎片化和盲目化,而无法形成真正的结构性的力量来对抗全球资本主义。■
注释:
①柴静的新书《看见》2012年上架一周后,销量即达百万。《柴静和〈看见〉:什么样的节目就有什么样的人看》,http://www.imeee.cn/life/xiuxian/020GLF922013_2.html
②《百度百科·颜艳红》,http://baike.baidu.com/view/9497123.htm
③《河北青年报调查:还原一个真实的颜艳红》,http://www.yiqigogo.com/post/388.html
④《颜艳红:我不认识我自己》在一开头的解说词中就说:“谈到虐待动机时,她始终只说两个字‘好玩’。这样一个常识看起来残忍粗暴的行为为什么在一个正常人的精神世界中被视为‘好玩’,今天颜艳红接受我们的访问,她说愿意呈现她之前一直想向他人隐瞒的另外一面。”
⑤引自《颜艳红:我不认识我自己》解说词,下文引文如无特别说明,皆出自于解说词。
⑥廉思:《蚁族》第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⑦风笑天、孙龙:《虚拟社会化与青年角色认同的危机——对21世纪青年工作与青年研究的挑战》,《青年研究》1999年第12期
⑧[美]迪克·赫伯迪格著,陆道夫等译:《亚文化:风格的意义》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⑨《看见》的这一选择与中国青年社会学研究的当前走向有不谋而合之处。何绍辉、黄海在研究“青少年问题”时就指出:“将街角青年作为‘问题青少年’在研究,我们对街角青年本身带有一种‘刻板印象’,我们关注的核心不是‘青少年问题’,而是‘问题青少年’,于是,再怎么调查、发现与研究,我们都逃脱不了既有的研究困境。”因而他们呼吁:“对于乡村‘越轨’青年群体的研究,应该跳出研究对象本身,多从社会而非从个体去寻找原因、获得理解”。何绍辉、黄海:《社会病视角下的“越轨青年”研究——以街角青年与乡村混混为例》,《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2期
⑩G.R.Gillis: Youth and History: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青年与历史:欧洲年龄的传统与变化》),转引自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第2~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美]约翰·菲斯克著,祁阿红等译:《电视文化》第410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2]马骏:《〈看见〉:自媒体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电视研究》2012年第5期
[13]傅剑锋指出:“在微博时代,由于它强大的舆论场力量,可能正在使传统媒体的记者与编辑陷入这样的一种危险:对一条带有强烈社会情绪的新闻,站立场变成了第一位,还原与调查事实反而降到次要位置”。《“我爸是李刚”报道的群体症候》,《南方传媒研究》2011年第27辑
[14]《看见》主持人柴静在一次访谈中,就表明了这样的忧虑:“网络时代,尤其是有微博之后,信息传播非常快也非常短,很容易跨越事实直接进入评论环节,成见很容易形成,偏见也很容易加深,而且这种社会情绪会因互联网而加快加重。”耿欣、蒋玉鼐:《柴静如何“看见”——对话央视综合频道“看见”栏目主持人柴静》,《中国记者》2012年第1期
[15]《看见》官网。http://cctv.cntv.cn/lm/kanjian
[16] [17]王开岭:《看见:一种目光和态度》,《中国电视》2013年第3期
[18]尤蕾:《“看见”柴静》,《南风窗》,2013年第1期
[19]柴静;《采访是一场抵达》,《商周刊》2012年11月 12日
[20]话剧人牟森认为:“《看见》不是新闻节目,是文学节目。”见张卓:《“看见”柴静》《中国周刊》,http://news.sohu.com/20111206/n328081868.shtml[21] 这一讨论同时在很多网络公共平台展开。如在新浪微博的“微话题”中,由《闾丘露薇批评柴静是“表演”采访,引记者行业标准争议》这一帖子引发的网友讨论11820435次,截止2013年4月21日,共有9436名网友赞同闾丘露薇的看法,4856位网友支持张志安的观点。http://huati.weibo.com/27251?from=522#!/27251?from=522&order=time
[22][23]闾丘露薇:《说说记者这行吧》,http://dajia.qq.com/blog/212033018962909.
[24]来源http://news.sohu.com/20111206/n328081868.shtml[25] 来源http://ent.sina.com.cn/r/m/2013-01-25/10343844554.shtml?wbf=more。
[26]杜骏飞:《我们怎样抵达新闻?》,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525-46899.shtml
[27]《闾丘露薇谈新闻理念:新闻不能只到个案为止》,“中新网”2013年1月24日,http://hlj.sina.com.cn/news/s/2013-01-24/073034649_3.html
[28]王辰瑶:《新闻人要避免成为新闻话题——也谈闾丘柴静之热议》,《新闻实践》2013年第3期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与当代中国青年文学/文化研究”(13BZW128)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085项目“都市社会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