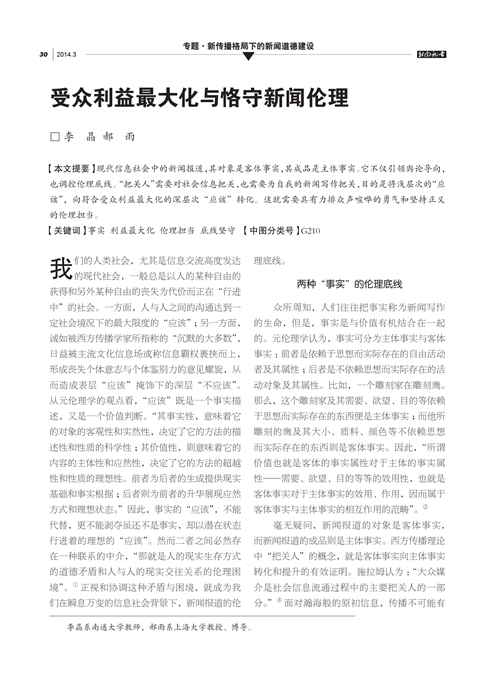受众利益最大化与恪守新闻伦理
□李晶 郝雨
【本文提要】 现代信息社会中的新闻报道,其对象是客体事实,其成品是主体事实。它不仅引领舆论导向,也调控伦理底线。“把关人”需要对社会信息把关,也需要为自我的新闻写作把关,目的是将浅层次的“应该”,向符合受众利益最大化的深层次“应该”转化。这就需要具有力排众声喧哗的勇气和坚持正义的伦理担当。
【关键词】 事实 利益最大化 伦理担当 底线坚守
【中图分类号】 G210
我们的人类社会,尤其是信息交流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一般总是以人的某种自由的获得和另外某种自由的丧失为代价而正在“行进中”的社会。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达到一定社会境况下的最大限度的“应该”;另一方面,诚如被西方传播学家所指称的“沉默的大多数”,日益被主流文化信息场或称信息霸权裹挟而上,形成丧失个体意志与个体鉴别力的意见螺旋,从而造成表层“应该”掩饰下的深层“不应该”。从元伦理学的观点看,“应该”既是一个事实描述,又是一个价值判断。“其事实性,意味着它的对象的客观性和实然性,决定了它的方法的描述性和性质的科学性;其价值性,则意味着它的内容的主体性和应然性,决定了它的方法的超越性和性质的理想性。前者为后者的生成提供现实基础和事实根据;后者则为前者的升华展现应然方式和理想状态。”因此,事实的“应该”,不能代替,更不能剥夺虽还不是事实,却以潜在状态行进着的理想的“应该”。然而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一种联系的中介,“那就是人的现实生存方式的道德矛盾和人与人的现实交往关系的伦理困境”。①正视和协调这种矛盾与困境,就成为我们在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背景下,新闻报道的伦理底线。
两种“事实”的伦理底线
众所周知,人们往往把事实称为新闻写作的生命,但是,事实是与价值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元伦理学认为,事实可分为主体事实与客体事实:前者是依赖于思想而实际存在的自由活动者及其属性;后者是不依赖思想而实际存在的活动对象及其属性。比如,一个雕刻家在雕刻鹰。那么,这个雕刻家及其需要、欲望、目的等依赖于思想而实际存在的东西便是主体事实;而他所雕刻的鹰及其大小、质料、颜色等不依赖思想而实际存在的东西则是客体事实。因此,“所谓价值也就是客体的事实属性对于主体的事实属性——需要、欲望、目的等等的效用性,也就是客体事实对于主体事实的效用、作用,因而属于客体事实与主体事实的相互作用的范畴”。②
毫无疑问,新闻报道的对象是客体事实,而新闻报道的成品则是主体事实。西方传播理论中“把关人”的概念,就是客体事实向主体事实转化和提升的有效证明。施拉姆认为:“大众媒介是社会信息流通过程中的主要把关人的一部分。” ③面对瀚海般的原初信息,传播不可能有闻必录,必须依照一定的标准和需要对信息进行取舍,而这个取舍的过程就是把关的过程。④新闻报道是整个媒介传播的重要环节,写作主体对于新闻对象的选择,对于新闻文本的制作,都体现着把关人的需要、欲望和目的,其所传播的事实,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状态的事实,而是经过主观化(主体化)了的事实。同时,新闻写作文本传播之后。所带来的社会效应,特别是意见群体的螺旋上升,都毋庸置疑地彰显着新闻写作的导向作用。如果说新闻编辑是把关的第二重门,而新闻写作则是把关的第一重门,它不仅引领着社会舆论的导向,也影响和调控着社会伦理的公平底线。
现代社会正义论是由三部分构成的,即机会公平、程序公正和分配公正。这里的机会公平是正义论的核心体现。但要确保机会平等,就必须要有程序公正作支撑。程序公正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条例及其他政策时所凭据的理由应当是公正的;二是这个“制定过程”本身应当是公正的。其中后者更为重要。作为新闻报道的成品,经过媒介传播,必然产生预想不到的社会影响。有人将这种影响称为“媒介霸权”,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此,新闻报道的伦理底线,应建立在尽可能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努力使任何社会成员的尊严维护和利益的获得都不应该建立在有损他人的尊严和利益之上,也就是说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合理的规则体系中都是公平自由的。⑤如马克思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的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挥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⑥也就是说新闻写作须把握为更多人谋利益的伦理底线,不论是正面褒奖,还是反面的贬斥,都须考虑到信息接受者的整体反映;不论是褒奖的对象,还是贬斥的对象,作为社会信息强势一方的媒介,在某种意义来说,就已经具有了倾向性,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程序的公正。因为任何新闻文本一旦完成,其本身就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状态的事实,而是主观化(主体化)了的事实。尽管这种被主观化、被主体化了的事实,经过把关人的处理,以“倾向”和“导向”的姿态,促使社会的公正与进步,然而这仍然只是一种“应然”和“理想”,只有经过接受群体的反馈与社会实践的证明,才能成为新的纯粹的、自然状态的客观事实。
孔子有一段很著名的轶事。是说当时有不少鲁人沦为他国奴隶,鲁国为此布告,凡出钱救赎同胞者,可到国库领取补偿甚至奖励。子贡赎回了一些鲁人,却拒收补偿。对弟子的行为,孔子非但没有夸奖,反倒给予责备。认为他尽管树立了一己之道德标杆,却消弱了更多人的救赎热情。因为大多数人不如子贡富有,承担不起高昂的救赎费用。⑦子贡的“好心”,并未受到老师的“好报”,倒不是说弟子的道德水准不高,而是说他的道德义举,只能作为精神的高标,而没有普遍推行的可能。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文化空间中,我们的新闻报道也存在一个道德悖论,即精神的高标与普泛价值的脱节。比如对先进模范的重点歌颂,在弘扬社会主流意识之余,也会有部分接受者因差距较大,而失去对于榜样的向往和社会参与的热情;对娱乐明星报道过多,在进行了文化作为生产的有效社会实践之余,也会弱化社会精神的力度、浅化思想探索的深度;在对“雷人”的社会热点过分迷恋之后,也会疏远对于具体的国计民生的殷切关注。总之,新闻报道任何时候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所制造的专供传播的各种信息,都无疑成为所有可能的接受者,越过自我实践的原点,使之成为自我的知识储备,并成为他们个体经验的导师,从而引起社会的群体效应。因此,不可不把握好新闻报道的最基本的有利于最广泛大众的伦理底线。
“应该”与新闻受众利益最大化
笔者看到2013年对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报道,发现瑞典舆论界并不是将此项大奖看得特别重。典礼会场内外的布置,乃至典礼宴会,都十分普通,真是以平常心对待这项国际上影响最大的奖项,恰好体现了更多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对于新闻人来说,违反这个原则,便是越过了新闻写作的伦理底线。因此,对任何人物和事件的侧重报道,都应该把握“最普遍性”的伦理底线。正如黑尔所认为的,“一个人说‘我应该’,他就使他自己同意处在他的环境下的任何人应该”。⑧如果越过这个伦理底线,便是非道德的。因为“非道德应该便因其是行为对于千差万别的个人目的的效用,而不具有可普遍化性:它是张三的应该,却不是李四的应该。反之,道德应该则因其是行为对于任何社会都一样的道德目的的效用,而具有可普遍化性:它是每个人的应该”。⑨当对一方说“是”的时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对另一方说“不是”;当对一方“肯定”的时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对另一方的“否定”; 当对一方实施“给予”的时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对另一方的“剥夺”。
对新闻报道的主体来说,这或许形不成“故意”,但效果有时会适得其反,使得另一方——意见大多数的一方,感到其形象受到了影响,利益受到了侵害。这种积极参与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导向的新闻媒介与新闻报道,尽管初衷是可以理解,也是合理的,但因媒介与新闻报道的双向承继作用,在上,承继部分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功能;在下,尽力附庸着最为接近媒介与新闻报道的接受者的群体心理,有时只是附庸一种对大众接受的娱乐喜好。这样,媒介与新闻报道如果不能把握住新闻伦理的底线,就有可能不仅不能做好广大民众的代言人,而且还有可能造成对于广大民众的误导,从而不仅不能改善,而且还可能加剧社会的刻板印象。
我们以新闻报道中对女性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为例。美国学者乔治·格伯纳研究发现,当女性在屏幕上或其他新闻报道中出现时,常常扮演着边缘的点缀的角色(诸如男主角的母亲或妻子等形象)。在美国早期广告中所呈现的女性角色中,75%的女性被塑造为厨房和浴室用品的使用者。即便是表现为职业妇女,也多以秘书、护士等服务型、辅助性职业为主,往往被表现为男性同伴的次要形象。在我国的媒介传播和新闻报道中,也可随处看到对于女性歧视的刻板印象。我们不时可以看到林志玲走光不慎露底、女大学生为高档服装化妆品一夜千元卖淫、贪官难过美色关、三陪女的直白等极力渲染事实,强调女性性别特征的报道。由于大众媒介的传播及报道的推波助澜,使社会默认并遵循这种性别塑造的方式。似乎男性就是优势的、活跃的、积极进取的和有权威的,而女性则是劣势的、消极的、被动的和边缘性的。媒介传播与新闻报道不仅参与了社会性别的塑造过程,而且以信息霸权的姿态,肯定了性别角色的自然特性及其不平等,使得女性由大众传媒通过忽略、谴责或贬低而被“象征性地歼灭”。⑩
在某些新闻报道中的农民工形象也是如此。《武汉晨报》上有一篇题为《3月高空坠落事件频发安全意识“淡”,民工“很受伤”》的报道,在对农民工安全事故进行归因时,报道“归责”于农民工的安全意识淡薄。其导语是这样写的:“短短11天,12人坠楼,其中11人是民工。据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昨天统计的数据表明,我市民工安全意识十分淡薄。”这种语言的表达不是“报告”,而是“判断”,是记者的“自我投射”。[11]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污名化(stigmatization)过程,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12]某报的一篇报道《重庆上百“夜莺”当街揽客》,揭露夜晚在重庆储奇门滨江路猖獗的卖淫嫖娼活动黑幕。在报道中,作者曾两度提到“民工”一词。第一次是,“装扮民工模样、手撑雨伞的记者刚一走上人行道不足5米,就见……”叙述记者假扮民工,去靠近卖淫者打探内幕的情况。第二次是,“3名40岁民工模样的男子先后从旁边一红衣女子处走过来主动上前……”介绍了男子与女子攀谈进行交易的情况。该报道在不经意间已表露了记者的偏见。[13]即使这些偏见可能有着一定的社会事实作为支撑,然而,作为新闻记者,还理应秉持无职业身份偏见的伦理底线,在其采写的新闻报道中,应该采取更为公平而公正的写作立场。
众声喧哗下的新闻伦理坚守
毋庸讳言,大众传播媒介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一个自由而又多样化的媒体行业是一个社会民主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提供了不同的声音,传递了不同的看法,并以此给公众提供信息,影响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并促成政治辩论。它们促进了健康的民主社会所具有的多元化的产生,也有助于一个国家文化结构的形成,有助于形成认同感和共同的目标。” [14]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大众传播的无明确对象性和强制性,“使传播方彻底掌握了传播的主动权,可以任意以多频次、高重复率传播给受众”。[15]特别是到了电子传播时代,比如“人肉搜索”所带来的导向作用就十分明显。通过网络被强制披露的个人信息,不仅可能侵犯个人隐私,而且还可能导致网络及现实中的暴力行为。这些通过网络所实施的针对个人的骚扰行为,就超越了“合法”的界限和伦理的底线。这种发育尚不十分健全的所谓“网络民主”,也被称为“民主暴力”,“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一些舆论环境的逼仄、言论的拘谨和信息公开性的不足”。[16]而保持“中立”的大众传播媒体则通过新闻报道或娱乐新闻的方式,在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更为广泛传播的角色,从而在坚持民间立场表层“应该”的虚饰下,实施了超越新闻伦理底线的“不应该”。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一些知识分子都把知识当作手电筒,不是用它去照亮世界,而是反过来,把自己弄得眼花缭乱。[17]起着社会舆论导向作用的新闻人,其手中之笔与法官断案的手中之笔同等重要。比如美国编辑人协会早在1923年制定的报业信条中就明确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感觉和思想,均有赖于新闻报道而互相了解,这是报纸的基本任务。所以担负此项任务的人,必经有渊博的知识,广泛的见闻与经验,以及天赋与专业训练而成的深刻观察力以及最明智的理解力。新闻记者有立言记事的机会,必须尽到教育者与解释者的责任。”在“公平”一条中美国编辑人协会指出:“新闻的记载与意见的发挥,两者是有区别的,不可混淆。意见与事实分开,……每一新闻不可掺杂任何私见和带有任何偏见。”在“正直”一条中美国编辑人协会指出:“报纸不可侵犯私人的权利与伤害私人的感情,以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公众的好奇心与公众的权益,二者截然不同。” [18]《南方周末》编委会所制定的“新闻职业道德伦理规范”也规定,“努力找到报道的主体对象,给他们对自己以往的行为做出反应的机会”; “除非传统的公开的方法不能得到对公众至关重要的信息,不要采用秘密的或窃听似的方法获取信息。如果使用了这样的方法,在报道中应该加以说明”; “检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并避免将这些价值观念强加给别人”;“观察人时不要被性别、年龄、宗教、种族、地理、性取向、是否残障、外貌或社会地位这些因素影响”;“对那些可能因为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们表示同情”;“只有当公共需要十分迫切时,侵入任何人的私人领域获取信息才是正当的”;“坚持高品位,避免迎合任何低级趣味”。[19]行业所制定的新闻伦理规范最起码在理论上彰显了对人的尊重,特别是对于因媒介传播与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们”的尊重。新闻传播的总体正义性,与法制健全过程中的因社会因素所造成的阶段性“霸权”,始终以“双刃剑”的形式引起世人的担忧与警惕,这当然是人类走向更健康更文明社会所带来的必要代价。■
注释:
①崔秋锁:《伦理学创新与方法转换》,《光明日报》2009年12月22日
②⑨王海明:《伦理学方法》第253、252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③[美]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第161页,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④⑤[13] [18] [19]郎劲松、初广志:《传媒伦理学导论》第233、253、257~258、262、312~313、327~32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⑦王朝明:《“孔融让梨”与“孔子责贡”》,《光明日报》2009年12月24日
⑧R.M.Hare: Essays in Ethical Theory, Clarendon PressOxford, 1989P179
⑩塔什曼:《大众传播对妇女的象征性歼灭》,考恩等编:《新闻的制造》第183页,伦敦1981年版
[11]李彬:《传播学引论》第71页,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12]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的流动》,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第1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4][英]卡伦·桑德斯:《道德与新闻》第18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5]杜志红、张帆:《论商业行为中的强制传播现象》,《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
[16]郭镇之、吕露英:《“人肉搜索”与法律监管》,《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3期
[17]杨光祖:《文学批评要讲真话》,《人民日报》2009年12月29日
李晶系南通大学教师,郝雨系上海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