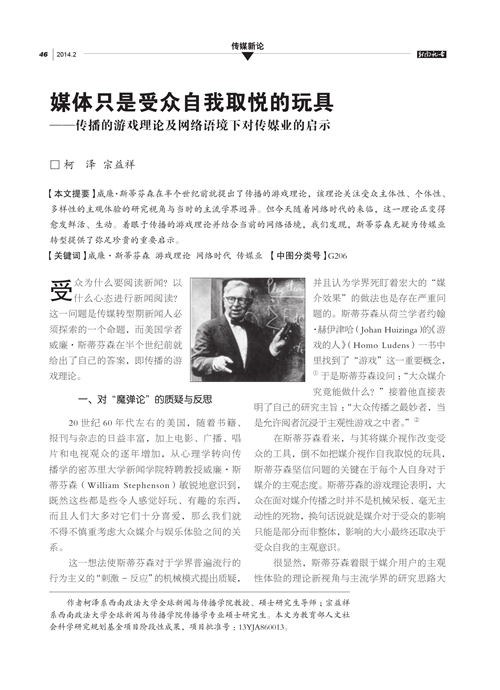媒体只是受众自我取悦的玩具
——传播的游戏理论及网络语境下对传媒业的启示
□柯泽 宗益祥
【本文提要】 威廉·斯蒂芬森在半个世纪前就提出了传播的游戏理论,该理论关注受众主体性、个体性、多样性的主观体验的研究视角与当时的主流学界迥异。但今天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这一理论正变得愈发鲜活、生动。着眼于传播的游戏理论并结合当前的网络语境,我们发现,斯蒂芬森无疑为传媒业转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 威廉·斯蒂芬森 游戏理论 网络时代 传媒业 【中图分类号】 G206
受众为什么要阅读新闻?以什么心态进行新闻阅读?这一问题是传媒转型期新闻人必须探索的一个命题,而美国学者威廉·斯蒂芬森在半个世纪前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传播的游戏理论。
一、对“魔弹论”的质疑与反思
20世纪60年代左右的美国,随着书籍、报刊与杂志的日益丰富,加上电影、广播、唱片和电视观众的逐年增加,从心理学转向传播学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敏锐地意识到,既然这些都是些令人感觉好玩、有趣的东西,而且人们大多对它们十分喜爱,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慎重考虑大众媒介与娱乐体验之间的关系。
这一想法使斯蒂芬森对于学界普遍流行的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的机械模式提出质疑,并且认为学界死盯着宏大的“媒介效果”的做法也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斯蒂芬森从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的《游戏的人》 (Homo Ludens)一书中里找到了“游戏”这一重要概念,①于是斯蒂芬森设问:“大众媒介究竟能做什么?”接着他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研究主旨:“大众传播之最妙者,当是允许阅者沉浸于主观性游戏之中者。” ②
在斯蒂芬森看来,与其将媒介视作改变受众的工具,倒不如把媒介视作自我取悦的玩具,斯蒂芬森坚信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个人自身对于媒介的主观态度。斯蒂芬森的游戏理论表明,大众在面对媒介传播之时并不是机械呆板、毫无主动性的死物,换句话说就是媒介对于受众的影响只能是部分而非整体,影响的大小最终还取决于受众自我的主观意识。
很显然,斯蒂芬森着眼于媒介用户的主观性体验的理论新视角与主流学界的研究思路大异其趣,但与此同时,传播学界正经历着由20世纪早期的“魔弹论”向60年代左右的“有限效果论”的重大转变,传播学界自发掀起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恰恰与斯蒂芬森的传播游戏理论彼此呼应。
斯蒂芬森1964年发表在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上的《新闻阅读的鲁登尼克理论》一文中,特别指出了施拉姆建立在弗洛伊德的“快乐-现实原理(Pleasure-reality Principle)”之上的“即刻或延缓回馈理论”的深层谬误。施拉姆曾认为:一个人因为今天的坏新闻而身心痛苦,但这却有利于将来的身心愉悦,因为对于飞来横祸的提前准备将会有利于人们直面残酷的现实。③斯蒂芬森则认为,施拉姆的理论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人类“无意识”的基础之上的,简而言之它是一种“非自我投入(Non-ego-involving)”的过程,然而恰恰相反的是,新闻阅读则是一种“高度自我投入(Highly-ego-involving)”的心理状态。
接着,斯蒂芬森直言:“至少三年前,笔者就发现新闻阅读所具有的一种‘类似游戏的特性(Play-like Character)’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了。” ④在斯蒂芬森看来,新闻阅读的发达形式是“主观性游戏(Subjective Play)”,为此他还借用了托马斯·莎茨(Thomas Szasz)的“传播快乐(Communication-pleasure)”这一重要概念来阐释这种高度自我参与的主观体验乐趣。至于“传播快乐”,斯蒂芬森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当两个人相识而谈,事后或许会欣然回味一番。他们交谈时会以一种复杂的形式相互影响,时而严肃认真,时而诙谐幽默,时而话不投机,时而相见恨晚。这种交谈不带有明显可见的目的性——一方并不需要说服另一方,或者让另一方甘拜下风,或者谋取些什么功利性的好处;同样,他们也不是为了取悦对方——这就是‘传播快乐’。” ⑤并且斯蒂芬森还指出了与“传播快乐”迥然相异的“传播痛苦(Communication-pain)”概念,并且认为这是一种需求性传播,它与行动命令或者寻求帮助相关,它是工作的、功利性与痛苦的。
二、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
斯蒂芬森认为,从人的主观性方面来讲,新闻阅读具备了游戏的所有特性。他认为阅读游戏包括“原始形式”与“高级形式”:原始形式是一种“弱社会化”的阅读方式,它是一种“纯粹游戏”的层次,人们在阅读时可以一会儿读点这,一会儿又读点那,并且不同时刻读的东西可以互不相干。比如,读者可以从一件魅惑人心的婚外情的报道一下子跳转到一场引人入胜的谋杀案。而阅读游戏的“高级形式”则表现在读者具备了阅读诸如《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的技能,一个人可以按照他的阅读习惯上演一出复杂的思维小步舞,这种阅读过程显得秩序井然、富于仪式元素并且具备高度的游戏性,人的自我意识也会贯穿在一切阅读过程之中,而这仿佛是置身于一场富有规则的比赛那般紧张刺激。当一个读者如痴如醉地沉浸于新闻阅读之后,他便会由衷地发出赞叹:阅读赋予人们难以言喻的乐趣。
斯蒂芬森将新闻阅读总结为是一种“纯粹游戏态度”的主观性游戏,但同时也带有比赛中所具有的比赛规则与自我意识的特征,他将之称为“鲁登尼克理论(Theory Ludenic)”,而“鲁登尼克”则是纯粹游戏与比赛的意思。
为了说明阅读游戏的规则性,斯蒂芬森举了《泰晤士报》的例子:“它那雷打不动的头版设计里夹杂着分门别类的广告;人们日复一日地在相同的位置发现出生、死亡、人事信息等内容。中间两版的特色性紧随其后,在这里重要的新闻会编排在报纸的左侧,而社论及信件会放在右侧。甚至于社论的编排也是秩序井然的:第四篇社论往往诙谐风趣,让人会心一笑。读者对于每一版的大概内容都了如指掌,甚至能精确到在哪一栏、哪一页。此类种种与高度秩序化的鲁登尼克的新闻阅读是一致的。” ⑥斯蒂芬森认为,没有什么能比成熟的鲁登尼克情境更具迷狂性与随意性了,人们会追随着正文或者注释抵达未曾预料之境。
斯蒂芬森进而建议编辑们:“这不纯粹是一个熟悉的问题,也不建议回归传统或一本正经的风格。一份符合鲁登尼克理论的报纸或者杂志应该促使并激励人们达到聚精会神的境界……成熟的鲁登尼克阅读需要一切内容各就其位,各就其序,以便读者可以在外国新闻、社论、信件、喜剧乃至注释上有序转换,这就如同在进行一场秩序井然的比赛那般。插图、广告也要各就其位。这并不是说要强调对报纸形式进行组织化安排,而是纯粹对于读者的‘游戏’过程考虑更多,并且激励人们培养一种成熟的鲁登尼克阅读习惯。” ⑦
特别地,斯蒂芬森指出了新闻阅读的自愿性质,认为这绝非出自某种工作的压力或者必尽的义务,它也与现实的功利性报酬无关,换句通俗的话:爱读不读,自己做主。
此外,斯蒂芬森还指出了新闻阅读的时空独立性:“读报也不是人们普通的真实生活的必要部分——它只是一段插曲,一种‘假想’行为,一个暂时事件,一种自我满足,仅此而已。”⑧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他还特地引用了库利(Kooley)的观点:“新闻阅读是与世隔绝的,人们沉浸其中——无论是早餐时间,或是咖啡小憩,或是乘车途中,抑或是晚上穿着拖鞋躺在椅子上,它总能以不同方式占据着人们的日常时间。因此新闻阅读与日常工作相互隔离,这就特别像小孩子在家中划出一部分空间用来做一会儿游戏那般,而孩子的游戏情景往往与家中的整体环境也显得格格不入。” ⑨
总体而言,斯蒂芬森的游戏理论强调一种站在受众立场上的自我参与式的主观体验,这种类似“游戏”的心理状态包含着自愿性、非功利性、时空独立性、规则制约性、身心愉悦性与不确定性等游戏特征。
1967年,斯蒂芬森在《新闻阅读的鲁登尼克理论》的基础之上出版了《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该书是斯蒂芬森由心理学界跨入传播学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在该书中斯蒂芬森系统、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传播游戏理论及其Q方法⑩的运用,该书中还涉及到了许多看似对立实则互补的二元概念:比如“社会控制”与“选择性会聚”、“工作”与“游戏”、“工作性传播”与“游戏性传播”、“传播快乐”与“传播痛苦”、“自己(Self)”与“自我(Ego)”、“Q方法”与“R方法”等等。囿于篇幅的限制在此无法一一作具体阐释,但一言以蔽之: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是对于主流学界“传者中心主义”的信息传递观的互补性颠覆,它从传播本体与研究方法上进行了一场令人措手不及的革命。他竭力主张的关注大众主体性、个体性的主观心理体验的研究视角无疑与其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显得“格格不入”。施拉姆就曾略带嘲讽地评论说:“如果斯蒂芬森的著作读起来比较容易,如果他也像麦克卢汉那样善于创造新名词的话,商业娱乐媒体本来可以选择把他而不是麦克卢汉捧为名人。” [11]从学理上来看,斯蒂芬森的传播游戏理论及其Q方法需要我们摆脱许多学界惯有的研究套路,寻求一种整体性、互补性、多元性的研究视角来看待复杂多变的传播问题,同时对于我们在思维方式与知识背景上也带来巨大的挑战。斯蒂芬森就曾自我调侃道:自己的《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没有多少人能看得懂,加之被誉为“传播学鼻祖”的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一书中的误解甚至歪曲,总体而言,传播的游戏理论一直以来在中西方主流学界的巨大遮蔽下默默无闻。
三、受众转向网媒的原因
斯蒂芬森曾对上世纪60年代纽约城市地铁里美国大众的读报情形进行了一番观察与描述:“纽约城市列车终点站里遍地都是旅客翻完便丢弃的报纸,但在旅途过程之中,人们三三两两,并肩而坐,各自沉浸于手头的报纸里——甚至如痴如醉到能突然与身边的陌生人欣然相识,彼此攀谈。每天早上,人们熙熙攘攘,并肩而坐,手持报纸,一片寂静。” [12]现在假如我们将此语境之中的“报纸”换成“手机”或者其他现代移动终端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在今天的网络时代,移动互联网的全时空式的覆盖使人们进行新闻阅读、网络游戏、聊天交友等活动变得如此轻而易举、司空见惯了,并且传统报纸与网络终端所带来的用户体验真的不可同日而语,游戏、视频、音乐、图片、新闻、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功能的开辟几乎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随时随地享受一场自我陶醉的主观性游戏所带来的乐趣,并且这种乐趣的主动性、多样性、刺激性远远超出了传统媒体时代相对被动与单一的局限。于是,笔者逐渐意识到,斯蒂芬森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提出的传播游戏理论正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变得愈发鲜活、生动与富有启示意义了。
传播的游戏理论诞生于20世纪中期,而整个20世纪几乎都是广播、电视与大众报刊的天下,当时广播风头强劲,电视尚未风靡,大众报刊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随身“移动终端”。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尤其是报业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不禁要问: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
2009年4月,美联社前主席奥斯博尔就曾表示:“以往,报纸近乎垄断新闻界,负债经营,大家认为‘报业盛宴永不会结束’,即使是在互联网到来时……然而,眼下消费者决定一切,他们决定什么才是新闻。” [13]可以说,奥斯博尔认为消费者决定一切的判断恰恰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并且这突然让我们再次听到了斯蒂芬森的谆谆告诫:“大众传播之最妙者,当是允许阅者沉浸于主观性游戏之中者。”传播问题的关键取决于大众自身的主观态度。
实际上,传统媒体如今对网络是典型的爱恨交织。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大众会主动选择网络媒体而放弃传统媒体?笔者认为,正是网络的自主性、个体性、多样性、交互性、及时性及虚拟性等诸多“游戏”特征满足了大众进行个性化的主观性游戏的需求,所以才使得大众变得“喜新厌旧”起来。如今大众不再愿意拿着“粮票”到粮站按照票面上雷打不动的品种与斤两来被动接受大众媒介的灌输了,而是更乐意坐在餐厅里指挥大厨按照自己的个性化需求来制作一顿色香味俱全的饕餮大餐。
曾经的“受众”之所以为沦为受众,那是因为他是传统媒介眼中的被动接受者,而今天网络使得大众逐渐获得了一种彰显自我意识的渠道,“受众”不再是被动接受的死物,而是富有生命灵性的自由人,他们会聚在纷繁复杂的媒介产品中根据自己的主观喜好来选择中意的东西,于是传统媒介就必须转变成听由大众摆布的服务生——很显然,传统媒介假如无法适应这种身份的巨大转变,那么它就无法获得网络时代大众的青睐。
四、游戏理论对传媒业的启示
美国学者艾斯洛克在2005年为斯蒂芬森及其传播游戏理论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敏锐地指出:“或许此种大众传播研究的优点在今天要比过去更为凸显。随着新传播方法的激增,传统的电子与印刷媒介在我们眼前摇身一变,于是传统的大众媒介假设与推论亟需我们重新进行审视。在一个媒介碎片激增的时代,一对一营销、个性化信息服务、网页定制、视频点播系统以及其他可供个体消费者选择的创新服务显得越来越重要,那么我们这些传播学者就亟需一种新方法、新思路来聚焦媒介的个体消费者的个性特征与主观心态。” [14]网络时代无疑是“游戏人”的时代,我们如今正面临着一场学界与业界的深层次变革,我们唯有转换思路,考虑大众的主体性、个体性、多样性与互动性的游戏体验方能扭转危机四伏的窘境。假如传统媒体不愿转变运营思路,不能站在受众立场上考虑问题的话,它们的前景将堪忧。
那么,传统传媒业是否在网络语境下就毫无优势可言了呢?斯蒂芬森的游戏理论是否成了指导网络时代下一切传媒理论研究与业务经营的唯一指南?笔者认为,斯蒂芬森的游戏理论的价值与争议都在此。
实际上,斯蒂芬森从没有想借传播的游戏理论来否定传播的信息理论的意图。因为在他看来,关注主观性、个体性的游戏理论与关注客观性、整体性的信息理论并不矛盾,它们二者是优劣参半、彼此互补的。基于此,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必须吸取游戏理论的理论启示,改变以传者为主的惯性思维方式,充分调动大众的参与热情,积极吸取并接受大众的意见与建议,并且可以让网络技术为我所用,借此与大众保持密切的互动联系。
总体来说,网络媒介正在引领着学界与业界从“传者中心主义”向“受者中心主义”转变,而网络崛起的背后,技术推动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决定作用源自大众的主观需求,而这种需求则是大众不断成长的主观性、个体性、多样性的“游戏”精神的彰显。
网络时代的来临正在挑战着我们的传统思路,它迫使我们重新发掘斯蒂芬森的传播游戏理论的重大价值。如果说斯蒂芬森的游戏理论在50年前提出真的有点儿“不合时宜”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便又会觉得游戏理论“太合时宜”了,以至于变得司空见惯起来——这恰恰折射出了斯蒂芬森超越时代的惊人洞察力与预见力。曾经斯蒂芬森无疑在挑战传统、挑战他所处的时代,而今天斯蒂芬森则站在网络时代的潮头挑战着作为后继者的我们。■
注释:
①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②StephensonW.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M].New Jersey:Transaction,inc.New Brunswick1988
③Schramm,W.The Nature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1949(26):259-269
④⑤⑥⑦⑧⑨[12] Stephenson, W.The Ludenic Theory Of Newsreading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964(41):367-374.
⑩斯蒂芬森于1935年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宣布发现了一种可将人类主观性进行操作性测量的Q方法的诞生 ,Q方法源于传统“因素分析”法,简单来说它需要研究的参与者按照自己的主观偏好对一个特定研究论题的大量陈述条目进行排序(这就是“Q排序”),然后研究者再借助因素分析法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勾画出受访者对于相应话题的个人看法。总体而言,Q方法注重对于人类主观性与个体性的考察,这是一种科学人本主义的研究方法,它与冯特所开创的科学实证主义心理研究传统大相异旨。
[11]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第29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13][美]伯尔·奥斯博尔:《纸媒仍拥有未来》,《新闻前哨》2009年第6期
[14]EsrockS L. Review and Criticism: Research Pioneer Tribute—William Stephenson: Traveling an Unorthodox Path to Mass CommunicationDiscovery[J].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2005(49):244-250.
作者柯泽系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宗益祥系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3YJA86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