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也当“改文风”
□李彬
自三十年前执教新闻传播学以来,有个疑惑始终若隐若现,萦绕于心:学术研究应有怎样的文体与文字。具体说来,除了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学术著述是否容许突破一板一眼的论文体?学问之道可否如兵法所云,水无常势,兵无常形,只要胜利就师出有名?条分缕析的逻辑能否容纳形象灵动的思路与文辞?理性的表达与形象的呈现是南辕北辙还是对立统一?文体仅仅关乎形式?文字仅仅属于工具?等等。
也许心性所在,偏好所向,我对既有内涵又有灵气、既有思想又有文化的著述情有独钟,而引人入胜的首先是文体与文字等,就像语言总是显露文明的第一缕晨曦。古往今来,出色著述多有独到的文体与文笔:先秦诸子、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钟嵘的《诗品》、古希腊哲学、《五灯会元》《古兰经》、帕斯卡尔的《思想录》、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真是恍若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应接不暇。仅看王国维那段脍炙人口而意境幽深的文字即可略见一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至若新闻传播领域,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风景同样让人目不暇接。不算林林总总的各国名作,仅仅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马南邨(邓拓)的《燕山夜话》《梁厚甫通讯评论选》、范敬宜的《总编辑手记》、梁衡的《人杰鬼雄》、甘惜分的《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李金铨的《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等中文传世之作,或萧萧瑟瑟,风清月白,或浩浩汤汤,山高水长,就已蔚为大观。年轻一辈也不乏其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郭镇之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电视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高钢教授的《新闻报道教程——新闻采访写作的方法与技术》、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嬿如教授的《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等,既学问俨然,又文采斐然。
遗憾的是,文体或文字在新闻传播学科不仅一直“妾身未分明”,而且往往不无“雕虫小技”、“华而不实”、“不科学”、“不严谨”之嫌。乃至富有灵气的修辞、浑然天成的比喻、各领风骚的文体等,隐然有如艳妆浓抹的风流女子,常常避之犹恐不及,仿佛一旦有染就玷污了正大光明的科学羽毛,就降低了峨冠博带的学术水平。传播研究更是只谈学术价值,不论文体与文字,充其量在“科学研究”之余,关注一下“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时贤觉得,中国的传播研究之所以落后(当然是相较西方或美国),一是没有科学理论,一是没有科学方法,故需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改造我们的学习”。与此相应,有个虽未明言而颇为通行的观念:文体越板正越好,文字越奥博越好,唯其如此,才见水平。此类想法并非毫无道理,尤其面对就事论事的课题式研究、经验式研究或黄旦教授所言“记者式研究”等,基本的研究规范与严谨的学术表达尤为必要,笔者也曾如此主张并身体力行,1995年还在《现代传播》上著文,少年气盛地侈谈《学统与学院派》。然而,结果似乎并不乐观,除去漫天塞地的“理论平移”、“话语旅行”、“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学习借鉴或学术训练另当别论),由于文体与文字不入法眼,“机械性僵硬”的问题也日甚一日,犹如科举时代八股文。于是,传播之学越来越高深莫测之际,也越来越像会计账单、实验报告、病理解剖图、工程规划表等,无怪乎“童子莫对,垂头而睡”。针对类似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学者黄纪苏曾经批评道:
为什么一篇写戏剧的文章尽是些“A层面上的D线效应与E层面上的F线效应”?为什么红楼梦研究要“首次引进数理统计”——不过是统计了贾政有几房老婆、乌头庄交来几种年货?为什么谈人跟人这点破事非要表啦公式啦模型啦捣鼓得跟晶体管线路图似的?
如此学问,如此著述,如何激发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以及生命力、创造力与想象力呢?且不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更不说解释世界、改变世界。在《“谢氏文体”——又一种批评》一文里,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就此谈道: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认定了一种共同的学术文体,以为学术表达,就一定得是这种语体和格式。加之对所谓“学术规范”愈来愈严厉的强调,我们看到了一道枯燥无味的风景:一年一度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在用同样的语体、同样的格式表达同样的观念。对个性化表达的无休止地打压,使大量的学术论文成为学术公文。格式化的培养机制以及有关学术机构对学术著作的若干明文规定,最终使学术著作成了无性别、无调性、无具体写作人的公共文体。对这种文体的合法性、合理性,我们从未有任何论证。我们也视而不见那些被我们研究、被我们奉若神明的经典思想家们,其学术表达却并非都是“规范化”的。
“公共文体”的特征:依仗成串的抽象术语、各种抽象性程度很高的概念以及各种理论资源(大多为外来),明确标榜使用了何家的研究方法,再加上一系列固定不变的写作格式和要求。它最大的敌人是形象化语词,以及形象化的语词表达。形象化似乎是与规范化冲突的,是天敌。我们在潜意识中接受了一个看法:对形象化的接纳必将导致学术性的降低,甚至最终会毁掉学术性。因此,我们看到在学术著作中对形象化语词的回避。从文章著作的题目到文中的表达,都力求术语以及抽象性语词,并形成了一个没有加以证明的共识:术语越多,运用抽象性概念越多,就越具有学术性。近几十年的学术文章、著作的写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贬抑、轻看和驱赶形象化语词的过程。
此处所说的“谢氏文体”,是指北京大学谢冕先生的学术著述。这位当代诗坛的批评家,一方面以别开生面的思想呼应中国现代诗的崛起,一方面也以形象丰满的文辞拂去日积月累的八股尘埃,为学术界吹来一缕春草碧色、春水绿波的清风:一个世纪的背影、暴风雨的前奏、和新中国一起歌唱、死水下面的火山、在新的崛起面前、暗流涌出地表……如下灵光乍现的文字,更是这种谢氏文体的典范:“一旦新诗潮涌起,恍若密云的天空透进了一线炫目的光亮。这对于陷入庸常的诗界而言,不啻是一声惊天的雷鸣。”显然,谢冕先生对文体与文辞具有鲜明的自觉意识,正如曹文轩教授所言,他崇尚形象化词语,坚信形象化词语同样具有入木三分的理性力量。
这些看似非学术化表达的句子,在他看来,不是一般的陈述句,而是意思圆满的判断句。“崛起”、“一起歌唱”、“背影”、“暗流”……不仅是对一种状态的描摹,也是对一种性质的判断。它们与“同构”、“吊诡”、“悖反”、“场域”之类的抽象术语,具有同样的理性功能。
此类反思与批评虽然针对精神性的人文学,但未必不适用于实践性的社会科学,包括新闻传播学。作为揭示普遍联系、探究一般规律的社会科学,是不是只宜用“学术公文”以及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的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呢?耐人寻味的是,早年写出《逻辑哲学论》的维特根斯坦,晚年走向相反方向,并以推崇日常语言的《哲学研究》清理了前期思想。就文体与文字而言,晚近一批华人学者的著述也提供了耐人寻味的范本: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阎云翔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私人生活的变迁: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王迪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20—1930》、吴毅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等。应星教授的这部博士论文尤为典型,不看注释就像一部长篇小说或报告文学,有对话、有人物、有情节、有场景,一波三折,扣人心弦。除了严谨的事实爬梳与细密的文献剔抉,这种学术文体以及表达也使研究对象得到“全方位、多角度、立体感”的呈现,达到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论述中国问题时所希冀的“多体、多面、多角”的境地。其实,如前所述,古今大家的学术表达并非都是正襟危坐的,且不说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等谈话体经典,即使现代学科意义的著述同样千岩竞秀,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均为学术史上的里程碑。特别是,索绪尔与陈旭麓的经典之作甚至都是由弟子根据生前授课素材整理而成的。作为一种对比,当下学术评价机制常将此类著述排斥在外,只认峨冠博带的“学术专著”,效法前贤的拙著《中国新闻社会史》也曾遭遇这番尴尬。按照时新标准,许多对学术思想贡献丕大的名山之作不知该属何方神圣,更不用说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关于现代文学、清华大学徐葆耕先生关于电影、复旦大学葛兆光先生关于思想史等精彩的课堂讲录了。
那么,说来说去,学术研究应有怎样的文体与文字呢?尽管难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总是学术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吧。换言之,不同的学术思想竞相鸣放而不必独尊一家,不同的学术流派包括风格竞相绽放而不必我花开后百花杀。由此,庶几形成一种刘勰揭橥、巴赫金阐发的众声喧哗“场域”:“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
末了,借机想对一位卡莱尔说的“诗人英雄”或列宁说的“文化英雄”略表由来已久的心仪,这就是学者出身的张承志。他对山川大地与精神天宇的赤子情怀,对人民生活及其“心灵史”的礼赞,对“伪学”及“伪士”的敬而远之,对文字出神入化的感悟与把握等,构成当代中国的一抹恒远亮色,尤其是“以笔为旗”的气象,在一片倒伏的降旌中愈发虎虎生风,猎猎招展,无需更多置喙。这里只想特别提及一点,其文体与文字所彰显的形而上意味:在浑然天成的字里行间——无论文学还是学术,既充盈着清洁的精神、丰润的人生、自然的情怀,又洋溢着学识、真知与启示的神采。上世纪八十年代,当笔者懵懵懂懂进入学术领域时,他的一句暮鼓晨钟般的话不时回荡心中:印刷垃圾的黄土高原深深淹没了学术思想的金矿。在世纪之交那篇不似论文而胜似论文的《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中,他满含深意呼唤道:
从文明母亲的胎液里爬出来的孩子,在高等学府或上层社会,在思潮、教科书和恩师论文的烟海里被改造。无疑,书本的知识,尤其是必要的基本知识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已经到了指出的时候:求学有时也如断奶,“学者”好像特别容易发生异化。不能否认,一部分人在认知的路上南辕北辙,他们傲慢地挣脱着健康的母体,从不回头,越来越远。
旧的时代该结束了,泥巴汗水的学问刚刚登场。我们只是呼唤真知实学,我们只是呼吁,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
这篇境界辽远的学理文章作为开篇,收入张承志学术文集《常识的求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文集自序中有段平淡而灼人的文字,宛似西部大漠刺目阳光:
我摸索着用文字的形式,去完成学者的题目。也用这样的语言,竭力地反抗了来势汹汹的异化、对学术初衷的背离,以及侵犯民众文化权利的大潮。
而这,也是笔者遥遥瞩目的境界——纵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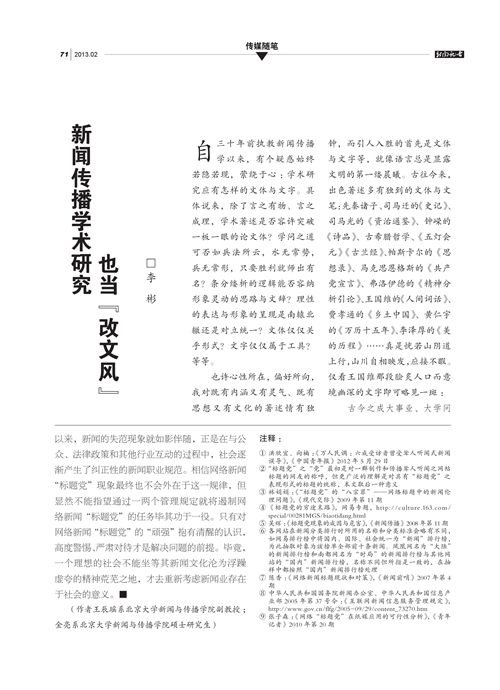
 制作维护
制作维护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