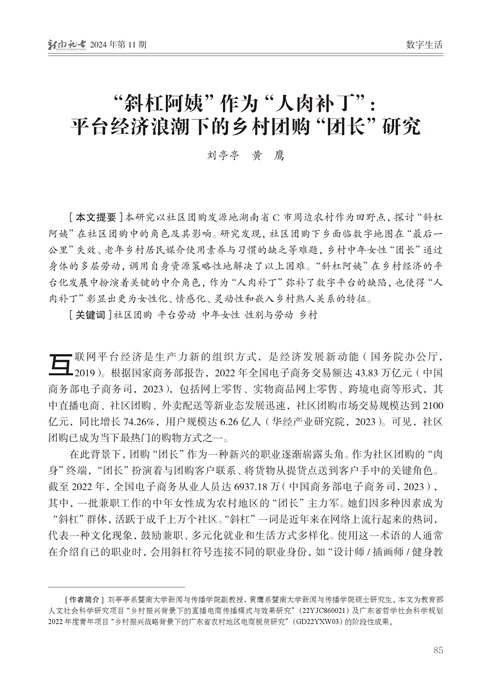“斜杠阿姨”作为“人肉补丁”:平台经济浪潮下的乡村团购“团长”研究
刘亭亭 黄 鹰
[本文提要]本研究以社区团购发源地湖南省C市周边农村作为田野点,探讨“斜杠阿姨”在社区团购中的角色及其影响。研究发现,社区团购下乡面临数字地图在“最后一公里”失效、老年乡村居民媒介使用素养与习惯的缺乏等难题,乡村中年女性“团长”通过身体的多层劳动,调用自身资源策略性地解决了以上困难。“斜杠阿姨”在乡村经济的平台化发展中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作为“人肉补丁”弥补了数字平台的缺陷,也使得“人肉补丁”彰显出更为女性化、情感化、灵动性和嵌入乡村熟人关系的特征。
[关键词]社区团购 平台劳动 中年女性 性别与劳动 乡村
互联网平台经济是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新动能(国务院办公厅,2019)。根据国家商务部报告,2022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43.83万亿元(中国商务部电子商务司,2023),包括网上零售、实物商品网上零售、跨境电商等形式,其中直播电商、社区团购、外卖配送等新业态发展迅速,社区团购市场交易规模达到2100亿元,同比增长74.26%,用户规模达6.26亿人(华经产业研究院,2023)。可见,社区团购已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购物方式之一。
在此背景下,团购“团长”作为一种新兴的职业逐渐崭露头角。作为社区团购的“肉身”终端,“团长”扮演着与团购客户联系、将货物从提货点送到客户手中的关键角色。截至2022年,全国电子商务从业人员达6937.18万(中国商务部电子商务司,2023),其中,一批兼职工作的中年女性成为农村地区的“团长”主力军。她们因多种因素成为“斜杠”群体,活跃于成千上万个社区。“斜杠”一词是近年来在网络上流行起来的热词,代表一种文化现象,鼓励兼职、多元化就业和生活方式多样化。使用这一术语的人通常在介绍自己的职业时,会用斜杠符号连接不同的职业身份,如“设计师/插画师/健身教练”,这种表达方式在青年群体中尤其流行,富有探索、闯荡和自我实现的意味(牛天,2022)。在对中年女性“团长”的访谈中,我们也观察到她们展现了类似的多元就业特征。然而,由于生命阶段和技能背景的差异,“斜杠阿姨”与“斜杠青年”亦有明显差异:“斜杠阿姨”处于人生的中年阶段,她们在追求职业多样性的同时,还必须平衡母职、妻职、女儿身份及相应的社会责任。“斜杠青年”多处于职业生涯的早期,更注重职业探索和个人生活的多样化体验,而“斜杠阿姨”选择兼职通常是出于经济需求和家庭支持的考虑。由于家庭责任的约束,“斜杠阿姨”的闯荡范围有限,她们的兼职尝试往往只能在不影响现有工作和家庭责任的条件下进行,且很少能够长期离开家乡——参与数字团购正为她们提供了绝佳的“斜杠”机会。
锚定中年女性的数字参与和“斜杠”体验,本研究选取社区团购的发源地——湖南省C市周边的农村作为研究地,旨在探究社区团购这一平台经济深入乡村后,对村落、村民以及担任“团长”的个人产生的各种社会效应。值得关注的是,在乡村地区,社区团购面临着数字地图在“最后一公里”失效的问题,同时乡村居民在媒介使用素养和习惯方面存在不足。本文将揭示,中年女性团长如何以“人肉补丁”的方式,凭其乡村生活经验和社区熟人关系灵动地校正数字地图、弥补现有平台的缺陷;本文亦欲探讨,作为特殊的“人肉补丁”,较之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跨境代购、电商客服、内容审核员、教育平台助教等平台劳动者,“斜杠阿姨”显现出何种独特性。
一、文献综述
现有平台劳动研究硕果累累,多侧重于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讲述资本对于平台劳动者的控制与剥削。许多学者指出数字平台对劳动的控制与传统劳动过程不同,呈现更加碎片化特征,同时资本更加注重对劳动结果进行控制,让在线控制变得更强、也更隐蔽(吴清军,李贞,2018)。例如为了获取更高的评分,无论是外卖员还是网约车司机,都设法通过情感劳动获得消费者的好评(孙萍,2019),优步(即Uber)宣扬“放手式”管理给予司机自主性,但实际上进行了更高级别的监控,如记录司机一系列的个人数据,包括评分、接单率、拒单率、在线时长、行程次数以及与其他司机的表现对比等(亚历克斯·罗森布拉特,2019:159-194)。外卖平台同样如此,通过高精准性的监控、引导与压缩实现对骑手的控制,使得骑手不得不实践“超级流动”(陈龙,孙萍,2021),从而“困在系统里”,甚至劳累猝死。而这种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数据分析结果作用于骑手使劳动秩序牢不可破的“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资本控制手段不仅正从专制转向霸权,而且正从实体转向虚拟(陈龙,2020)。深圳“的哥”与滴滴出行长达8年的“斗智斗勇”亦表明另类数字劳动是一个劳动者被折损、平台技术及背后的资本被赋值的过程,数字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制造能动”并“反噬对抗”的新权力装置(丁未,2021)。从研究对象上来说,现有平台化劳动研究集中关注热门行业与岗位,如网红主播、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而对于同属于平台劳动、快速增长、服务6.26亿团购用户的社区“团长”缺乏应有关注。根据研究者的实地观察,农村社区团购“团长”受“控制”与“剥削”的情况与前述研究并不完全一致。现有研究难以窥探团购平台的具体运营逻辑。尤其是作为团购发展的重要一环,“团长”的角色扮演、劳动方式及其运作过程等方面都无法从现有平台劳动研究得到答案。
而目前针对社区团购的研究主要围绕社区团购商业模式、影响消费者使用因素展开。个别研究展现了疫情期间团购志愿者与居民的关系构建(易若彤,2022),“团长”对于基于邻里信任的网络交易关系的作用(任美娜,刘林平,2022),以及“团长”如何运用情感来建构人际信任与消费需求,从而有意识地“制造熟客”的过程(燕道成,李菲,2021)。此外,根据行业报告和既有研究,“团长”工作是一项高度性别化的劳动(康正煜,王楠,陆晔,2024),大多数“团长”为20至59岁的中青年女性。①2022年4月发布的《上海团长白皮书》(ShanghaiWOW,2022)显示,在上海全域进入静态管理的情况下,有13万个保供型“团长”在帮忙团购蔬果肉蛋、米面粮油,还有超过65万个改善型“团长”为无数居民带来更加多样化的物资。其中,女性成为“团长”主力军,比例达77%。年龄构成中,31至40岁的“团长”人数最多,占总数的54.3%。紧随其后的是41至50岁的“团长”,人数占比为28.0%。同时,超过89.1%的“团长”都有本职工作,从事贸易、消费、制造行业和服务、零售业的人数最多,两类各占16.0%。《2019~2020中国快速消费品流通渠道报告(社区团购篇)》(新经销,2020)也显示中年女性为“团长”主力军,女性“团长”占比78%,其中30~40岁为62.4%,四线城市及以下地区占比46.1%。在本文的田野观察中,乡村中年女性“团长”亦彰显出这一特征。
性别与年龄构成了本研究探讨数字团购劳动的双重轴线。即有社区团购研究多从经济学角度展开,社会科学尤其是性别研究的视角较为缺乏,未能充分讨论平台劳动及其引发的社会效应(孙萍,赵宇超,张仟煜,2021),这与社区团购深入居民日常生活的现实不符。上海女性“团长”在危机情境下的社区应对行动研究已表明,女性在应对公共危机时积极参与社区行动,但学术界对此类行动的公共价值尚缺乏足够的探讨和认可(康正煜,王楠,陆晔,2024)。在平台经济向乡土社会扩展的过程中,面临与基层性别关系、家庭结构、熟人网络及市场利益的新挑战和协商需求(孙萍,刘姿君,王从健,2024),这种新常态下的社会流动性凸显了超越“流动-不动”二分关系的媒介意义(林颖,许天敏2022),亦需进一步研究。在年龄这一轴线上,既有研究认为,中老年妇女受制于家庭和劳动能力双重约束,很难与正规就业市场进行有效对接(卢青青,2021)。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为农村妇女提供诸多非正规就业机会,如村镇工厂凭借其产业属性、务工门槛等特征很好地衔接了农村女性通过务工实现增收的现实需求,团购平台灵活用工的模式也在客观上迎合了农村留守女性就近就业的需求(邢成举,2020)。数字平台的配送依托于数字地图,但鉴于我国乡间地形复杂多变,不同时节的道路可能由于天气、农事需要而出现难以通行等情况。目前数字地图应用程序难将其复杂路状可视化,导致数字平台下乡面临着难以触达“最后一公里”的困局。“团长”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了何种作用?为什么“团长”以中年女性为主?这些乡镇乡村的中年女性为什么在已有主业的情况下愿意以“团长”作为自身副业?为什么同样作为平台经济衍生的灵活就业,“团长”并未凸显出被资本算法控制与监控的状态?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发现“斜杠阿姨”作为“团长”——数字平台下乡过程中关键的破局者,通过协调平台下沉过程中的货物和数据流,充当了一种新型的性别化“人肉补丁”。这一概念的运用响应了媒体研究“身体转向”后的重要理论问题:在乡村团购的平台化发展中,线上与线下的连接,以及身体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根据刘海龙等(2021)的研究,“网络化身体”,如跨境代购和外卖骑手的身体实践,显示了身体作为非人化中介与网络的连接,具有网络“补丁”(弥补缺陷)与“病毒”(连接失灵或破坏秩序)的双重功能。此外,探讨跨境代购中身体的物理属性(位移)、符号属性(再现)和话语属性(权力的生产对象)丰富了对身体作为移动媒介的理解(谢卓潇,2021),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本研究还将探讨,为何特定群体(如乡村中年女性及她们的女儿)有意愿并有能力成为乡村团购的关键角色,而其他群体(如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则不能。同时,探讨在社会话语层面中被忽视的“斜杠阿姨”,如何通过物理位移(利用生活经验如在乡野、田间识别最佳路线进而送货)和符号再现(通过微信群与客户沟通),展现其独特的能动性。
综上所述,中年女性的劳动参与问题是女性就业实践与保障、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乡村中年女性“团长”的研究更有实践意义与人文关怀,也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看见平台经济发展、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建设中生动的女性力量。本研究借助平台劳动视角,融合性别、城乡、家庭、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分析团购平台对“团长”的管理,呈现“团长”劳动的过程,并从性别与劳动的视角切入,将这群中年女性“团长”的平台劳动放置于她们整体的社会活动和乡村社会关系中考量,展现农村中年女性的非正规就业实践,并呈现社区团购下乡给农村带来的系列社会效应。
具体而言,本研究拟解决以下问题:农村中年女性成为“团长”的原因是什么?为何“团长”工作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化特征?乡村团购“团长”如何围绕平台展开工作?“斜杠阿姨”作为数字平台的“人肉补丁”具有哪些显著特征?“斜杠阿姨”在乡村社会的平台化发展过程中承担了何种角色?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调查方法,主要包括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法,并以湖南省中部地区L村作为田野点。选择该村作为田野点主要基于以下考量:首先,该村位于社区团购的发源地湖南省C市周边地区,且受该地区经济一体化与社区团购下沉市场影响,该村社区团购进驻时间已达四年之久,村民有浓厚的团购使用氛围,满足研究需要。其次,当下最为火热的几大团购平台(包括兴盛优选、美团优选、多多买菜)在该村均有驻点,可丰富观察体验。再次,该村入驻最早、最主要使用的社区团购平台为兴盛优选,该平台面向消费者销售米面粮油、水果蔬菜、肉类水产、生活日化、数码电器等家庭日常消费品,还针对农村消费者出售家禽饲料等商品,更具地域特色。最后,该村为研究者之一成长生活的地方,基于研究者的生活经验和人际网络,该村更利于调研开展。本项调研起始于2022年1月,项目持续进行至2023年7月。
L村现有户籍人口3464人,共计1039户,划分为两个片区。其中,A片区设有3个社区团购驻点,B片区因交通便利、集市发达,设有7个团购驻点。也即是说,全村共有10个团购驻点和10名“团长”。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涵盖该村所有10名“团长”——其中7名年龄超过45岁并育有成年子女的“斜杠阿姨团长”是本研究的主要对象,其余3名青年“团长”则提供补充和参考(表1 表1见本期第90页)。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还访谈了34位村民顾客及其家人(涉及村里与在外务工成员)(表2 表2见本期第90页),帮助研究团队理解为何某些人成为了“团长”而其他人没有——以确保数据的代表性和研究的深度。本研究中涉及的“团长”皆为“斜杠阿姨”,即具有多重身份、兼任多职的中年女性。这10名“团长”在“团长”之外从事的业务以经营食品零售店为主。这一情况回应了全国范围内“团长”的普遍现状。
研究期间,研究者线上参与团购、观察“团长”群互动,线下参与“团长”清货送货过程,深入了解“团长”的劳动,并对其与家人、村民的互动予以记录。同时对“团长”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内容包括个人及家庭情况、过往工作经历、成为“团长”的原因、“团长”日常工作内容、平台管理模式、个人营销策略、工作感受、工作角色认知等,访谈时间为1小时至5小时不等。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对受访者的个人信息都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三、“斜杠阿姨”成为团购“团长”的多重原因分析
由于家庭因素和人力资本限制,中年农村妇女在正规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然而,随着平台经济进一步扩展到农村地区,各平台积极“争抢”着吸引中老年农村用户,兼职“团长”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劳动选择。在考虑到工作性别属性和主营业务的平衡后,越来越多的“斜杠阿姨”受到平台的吸引和女儿的鼓励,加入了这一行业。
(一)电商平台下乡积极招揽
自2016年社区团购正式诞生,而后经历资本入局、爆火、调整,到现如今固定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社区团购这场消费变革已经从城市蔓延至广大的农村地区。以自诩为社区团购开创者的“兴盛优选”为例,其在全国8个省份,千余个地(县)级城市的十万个乡镇、农村②进行了布局,而商业巨头“美团优选”同样提出了“千城计划”,③旨在实现全国“千城”覆盖,并逐步下沉至县级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壮大“团长”队伍成为各团购平台扩大市场的必要环节。例如,“美团优选”提出了“携手百万‘团长’,服务一亿家庭”的愿景,④而“兴盛优选”在全国超过十万个乡镇农村实施布局,同样体现其对“团长”的积极招募。
在平台积极下乡的过程中,农村中年女性以业务员上门推广、微信招引、临近“团长”拉拢等方式加入其中,成为“团长”群体的一分子:
当时他们业务员过来安利,哎呀你搞一个,如何如何(形容非常)赚钱,我们就搞了,搞了这么久就继续搞。(A3)
第一次是“团长”拉进来,后来因为单量不够被关团了。第二次通过微信,在一个推单量的群里面,兴盛优选的上一级给我们推荐,我就加他(指推广员)微信,又重新申请“团长”。他就让我申请,资料提上去,然后我去长沙面签。(B4)
我做兴盛是经开芙蓉兴盛的人介绍,他最开始做,现在他冇做了。那时候他拉我加盟,我还去长沙培训签约。(B2)
在成为“团长”后,一旦遭遇业务上的困扰,平台工作人员会积极帮助解决。例如B2在“兴盛优选”上开团时,自家营业执照因水灾淹没未修复,因此借用邻居的商铺营业执照申请开团,而后对方也想做团购不得不收回,于是涉及平台团购站点的后台转让。在这其中,兴盛优选的管理人员积极帮助B2应对这一困难:
一开始我拿了别人的营业执照,转都不能转,后来我联系这个创始人L姐,她给我转。我和他们也有微信,可以联系。L姐很平易近人,她告诉你、指导你怎么去做。她还跟你微信聊,她也怕流失她的客源。她算做的比较好的,是很精明的一个女人。(B2)
(二)女性“团长”的性别化考量
如前文所述,团购平台的数字地图难将乡间复杂路状可视化,导致数字平台下乡面临着难以触达“最后一公里”的困局。然而,乡村男性理应同样熟悉“最后一公里”的送货路线,那么为什么“团长”以中年女性为主?在研究中,受访者普遍认为“团长”工作是男性不愿从事、不适合从事的职业。她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哪个男的愿意做‘团长’?”根据女性“团长”的观点,这项工作的特点包括工作任务细碎、工作时间不固定、收入不稳定,性质很像家务活,因此男性不从事“团长”工作在女性“团长”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男的,像这样的琐碎事,有几个愿意做?除非那男的特别勤快。(A3)
女性才耐得烦(形容有耐心)。男人家赚了这点钱,拿着那东西一丢,懒得搞了,这是最直接的,确确实实赚不了什么钱。像城里好点的“团长”随便几百块钱一天能赚,而且还不要送货,像我们还要送货,这是个好麻烦的事,费力,又不赚钱。(B2)
好多男人家看着赚这几块钱,他不想去送,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不养家糊口,赚了几块钱,送过去还七里八里(啰嗦),不喜欢策(逗闷子),不喜欢解释这点东西。男人觉得这点东西丑死把人(拿不出手),要面子。别人一讲,男的弄大钱的送起这几块钱的东西。(B3)
除了男性意愿缺乏之外,一些女性“团长”认为男性还欠缺做“团长”的能力——诚然,这是基于长期的社会化过程和性别角色的学习、浸润形成的。例如,受访者B2提到,只有那些能够忍耐繁琐事务的女性才能胜任“团长”的工作。“团长”工作涉及清货、送货上门、处理售后等任务,需要“团长”细心核对清单、与村民积极交流,并准确记录每户人家的购买商品和地址,才能顺利完成工作。这种要求的细致性在“团长”的丈夫代替她们送货时更加明显,例如对于不熟悉的网名、记不清的路线以及难以一一匹配的人名和住址,男性在体验“团长”工作时经常需要妻子的帮助。研究者切身体验了一次男性代做“团长”的无助:在一次参与B1的送货途中,因两份货品路线不同,需要B1的丈夫派送,B1在详细说明何种袋子写的何人姓名、装的何种商品、应该送往何家后,其丈夫在此后近一个小时里,又打来三次电话进行询问确认:
他(指受访者丈夫)搞不清。天天送那个人家的家伙,还不晓得是哪个。只要他送一路货,那电话要打无数个。打个比方昨天送了的人家,今天送那家保证又不晓得了,又要问我。我讲你别的事就国灵泛(这么聪明),这事你总记不起啊,记性这么硕(差、不好)。我要他记别个的网名,他就是“这是哪个,这又是哪个”,总搞不清。(B1)
在工作的性别属性之外,农村女性面临的现状成为另一个推动因素。多数中国女性普遍同时肩负家庭抚幼及社会生产的双重责任(李勇辉,沈波澜,李小琴,2020),这种情况在农村更为普遍,“你在乡里呆久了会发现,在屋里的基本都是女的,男的基本上都在外面做事,你不管他做什么行业,基本上很少待屋里”(A3)。因此,家庭的分工也决定了在农村的“团长”以女性为主。一方面,在实体店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细碎的工作不会占据“团长”大量的时间,使得“团长”在工作之余可以顾全家里的主营业务,做好家务,并在与电商的竞争中“夹缝生存”;另一方面,家庭的育儿责任也基本由女性负责,而“团长”工作的属性能够兼容育儿职责,并帮补日常生活开销。如前文所述,“团长”工作的性别化不仅因其具有类似家务的特征,而且还匹配“斜杠阿姨”必须平衡的母职、妻职和女儿身份及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一需求。家务、育儿等家庭责任常将“斜杠阿姨”限制在家中,再加上赚钱的压力和作为本地居民所拥有的地方性资源,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农村中年女性与团购“团长”这一灵活非正规工作形成天然的契合:
碰到要送货,别人要买什么,买点烟搭着送下。你不出去,别的生意都会丢了去,这店子更加会淘汰去。有了团购,实体店生意还好点,可以上门给人带货。(B3)
我在屋里带人冇得什么事,就搭着做点。我的细(小)伢子细(小)的十岁了,毕竟还细,我陪在身边好些。大的今年十五岁了,从出生到现在他们一直是我带。他们在读书,平时我要去接送,周一送,周五接。我老公在外面做事。我搞“团长”,赚点油盐钱。(B4)
(三)“数字原住民”女儿的推动作用
在受访的“团长”中,有多位“团长”表示成为“团长”主要因为她们的数字原住民儿媳妇或女儿的推动。通常是她们居住在城里的儿媳妇或女儿注册了“团长”身份,而这些“斜杠阿姨”才是团购活动的具体执行者:
这是我儿媳妇搞的,我儿媳妇是站超市的(超市服务员),她先接触到“兴盛优选”。业务员跟我儿媳妇对的口(沟通),讲利润有多少,我也冇运神(没有思考)。我没管她的事,她不在屋里,平时清货送货就是我,售后是她。(A2)
研究表明,数字化对女性就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李建奇,2022),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儿媳、女儿,便是平台浪潮下积极响应的个例。而后,其将日常性“团长”事务交与A2,而其负责平台的售后事宜。有时候,子女也会扮演数字反哺的角色,帮助她们作为“团长”的母亲。正如周裕琼(2014)所说,在新媒体知识学习方面,子女对父母的反哺要远远超过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作为一项数字化业务,团购在申请过程中给A1带来一些操作上的困难——她的身份信息无法通过审核,拍摄的照片也未能达到要求。这时,女儿通过自己的手机帮助A1完成了注册流程。在日后的工作中,A1遇到一些售后问题需要向平台寻求解决,她的女儿同样一一指导她应该如何处理。研究中,未发现“团长”的儿子参与类似的业务——这也再次印证团购“团长”工作的性别化特征。
综上所述,“斜杠阿姨”成为团购“团长”实际上是数字平台和农村女性之间的双向选择。通过她们远超男性的耐心和熟练操作,“团长”工作逐渐成为一项高度女性化的职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团长”的身份,她们中的许多人还从事着其他主营业务。丰富的商业经验培养了她们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同时也使得她们能够在平台下乡的最初阶段就占据信息优势,成为“第一波吃螃蟹的人”。
四、乡村团购“团长”的劳动方式分析
从注册开团到吸引顾客下单,再到派发货物及等级评定,“团长”的工作紧密依托平台系统进行,并显示出非正规就业的高度灵活性。在与平台及其他“团长”的竞争和互动中,从业者的职业心态经历了变化,农村女性“团长”在成为数字平台“人肉补丁”的过程中显现其不可或缺性。尽管作为平台的“人肉补丁”,“斜杠阿姨”凭借独立的生计和收入,加上乡村团购点的稀缺性(从本文的研究对象数量中可见一斑)及平台在农村地区数据收集和劳动监控方面的不足,展现出对平台约束一定的抵抗性。她们能自主管理时间和劳动方式,灵活安排副业,有时甚至能从平台的无理要求中抽身。鉴于“斜杠阿姨”在公共话语中的相对隐形,以下将重点参考谢卓潇(2021)在研究跨境代购这一“人肉补丁”中关于物理移动和符号再现两个面向进行分析。
(一)适应数字化的团购工作
“团长”的工作紧密围绕平台进行,依赖手机作为主要工具。微信群和平台下单小程序是其收入的关键来源,而数字化的提成界面和表格化的订单页面则是推动订单和分拣货物的有效支持。部分平台的等级制度也加强了“团长”与系统的联系。以下田野笔记记录了“团长”B1在一天中如何通过平台劳动,展示了她作为数字平台“人肉补丁”的工作方式。
首先是身体和注意力与手机的持续绑定。持续在微信群发出消息、回复和处理订单等信息。
早上7点,B1在自己429人的团购微信群内向大家道声早上好,并发出兴盛优选的下单链接。7:30,群内村民TAJ发出语音信息,拜托B1购买喂养家禽的饲料,B1回复说好。9:58,B1派出微信红包,提醒大家“10点爆款”,并@所有人。红包共26个,手气最佳者得0.26元,其余人几分、一毛两毛不等。随后发出表情包“准备好了吗”、“10点活动来了”。随后每隔半小时至一小时,B1都在群内发一次下单链接……
一天下来,B1在群内发送下单链接18次,文字提示催单2次,发红包1次。通过频繁地发送微信信息,B1尽可能地保持着群内活跃,使得顾客任何时候看到的最先消息都是下单链接,而无须费力寻找。并希冀能够弹窗至顾客手机,从而勾起顾客的购买欲。后台每一笔订单后提示的提成数目,也使得B1可以很清楚哪部分货物利润更高,方便其有选择性地推单。同时后台设有“高佣商品榜”,方便“团长”直接推单。在顾客页面,顾客自身也可在收到货后在平台申请售后、评价“团长”和订单,但多数情况下,因部分村民对平台的操作生疏以及秉承“从哪买的找哪个负责”的逻辑,多向“团长”反馈,由“团长”统一处理。
其次,在清点、分拣和运送货物的过程中,B1需要付出较为密集的体力劳动,身体的物理移动属性被凸显。
13:00,B1继续整理小部分未分拣的货物。清理完毕,B1拿上扫帚清扫自购的送货工具——电动三轮车车厢,随后将装袋的商品按送货路线一一摆好。13:40左右,B1带上订单页和满车的货物,从常住的娘家出发,向村民家驶去。路上,已经收到货的一村民发来微信信息,讲述商品的质量问题,B1回复回去申请售后处理,并表示抱歉。
除与货物直接相关的活动之外,“团长”浸润在情感化和数字化运营的氛围中,不仅要熟练运用数字化情感和交流策略与客户维持友好的联系,还需要熟悉平台运营中的相关数字手段,包括“团长”的等级管理制度、订单的数据分析与管理等。当天晚上22点42分,团长在微信群内发出最后一则催单信息。
美团优选的“团长”,其工作模式同兴盛优选稍有区别。该平台会在“团长”的微信群派驻下单机器人“小助手”,并可由“团长”取名。A1的小助手名为“小可爱”。每日小助手会同“团长”一起在群内发送下单链接,发送次数可由“团长”控制。同时平台采取等级制度“对团长”进行管理,“团长”可通过后台知晓自己的等级,以及升级所需要完成的目标,等级每日进行更新。
(二)乡土社会及关系网络中灵活而有弹性的工作安排
与跨境代购、电商客服、内容审核员、教育平台助教等其他平台“人肉补丁”相比,“团长”接受的平台监控和数据管理相对较宽松,工作时间更为灵活,对其收入影响较小。这首先是因为团购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乡村社会的关系网,顾客关系更具有人情味,顾客不会随意向平台投诉“团长”;其次,由于乡村团购点的稀缺性,平台不能随意对“团长”进行惩罚或解雇。这使“团长”可以自主安排推单和送货时间,根据情况选择一次性完成送货或分批次进行。例如,在春节前销售高峰期,由于货物量大,部分“团长”将常规的“次日达”服务调整为“隔日达”,这种调整通常得到顾客的理解,且没有引发投诉。
春节前几天,因为年底货多,又下雪,平台送货司机下午五时才送达,待清货完毕,已是黑夜。B1团购群中个别客户发来信息询问为何货物还未送至家中,B1解释还在清货,随后B1群发信息:“各位亲朋好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货到得晚,才清理完,天气冷有的亲可能准备睡觉了,不好意思啊明天上午再送过来啊。”群内成员并未提出异议。此种“隔日达”的情况在农历新年到来前一直持续,村民与B1亦达成了默契,在随后的几天中,B1并未在群内说明却依旧是第三日上午才送货,依然未见纠纷产生。
由于“团长”们都有自己的主营业务,当主营业务繁忙时,团购工作也可能会被短暂搁置。例如A2从事的木材业,“我有时候去割树,司机送他的货,放里面就些得,我屋里面有摄像头,又冇事,东西不得丢,反正我中午会回”。待到午饭过后,主营业务完成,A2才开始清货、送货。可见,对于团购工作的安排,“团长”皆有自己的考量,呈现“我是‘团长’我做主”的状态。
(三)“佛系”工作,拒绝“内卷”
团购平台不断推出等级制、提成制的薪资计算方式,“团长”偶尔也不得不面对平台的管理和规训。根据美团优选后台显示,“团长”等级分为V0~V5共六级,不同等级对应不同权益,由经营分决定,分为下单件数、下单用户数、团推次数三个不同指标统计。与此同时,用户在下单地点超过自提点30公里的订单、“团长”用户在自己或他人自提点的订单、部分大规格商品等均不参与“团长”等级分数。分门别类的计算规则,让“团长”不得不按照不同指标进行推单,如一日必须拉满多少客户、购买多少件数才能达到经营分标准。
等级制推行下,有些“团长”也尝试过“卷一卷”。比如说,A3深谙其道,除了其本人和小助手一天高达31次的推单以外,还会根据每日订单量在平台当日统计即将截止时,发红包让好友帮忙下单。在平台的“悬赏”之下,从首位“团长”为了方便村民消费而发起“送货上门”服务后,几乎所有“团长”都迅速跟进,从“自提点”化身为“上门团长”。一句“你不送,别人送,冇办法”透出大家的无奈。
然而,不久后,“团长”们发现“五花八门”的揽客手段并未能给“团长”带来显著收益,甚至因此“节外生枝”,让村民间产生不悦之感:
有的客户买了好多货,我送一坨(包)纸。后面一看别人买一两样东西,只赚了一角多,买三四样,赚了冇得(没有)五毛钱,就冇送了。别个问怎么不送,我说你可以看一下,以前利润高些,现在利润跌了。(B3)
(给了优惠)后面还有争议,客户讲那为什么用不得(指前述优惠券),我今天有事去了(前述规则必须当天用)。后面我干脆不发红包了,你去争,而且好多待在群里专门领红包的,他也不买东西。正经买东西的永远只有那几个人。(B7)
当“团长”们未从激烈竞争中获益,反而发现个人利益受损、人际关系紧张时,她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佛系”态度。她们不再执着于顾客必须通过她们下单,也减少了在“团长”业务上的时间投入——如是,平台的等级制和提成制对她们的管束便自然而然地失效。在这场与团购平台的微观斗争中,“斜杠阿姨”“团长”们无疑展现了其他类型的平台“人肉补丁”少有的能动性。
五、“斜杠阿姨”作为数字乡村发展中的协调者角色
社区团购下乡体现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实际效果,不仅为乡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重塑消费生态,还带来深远的社会文化影响。这一现象反映了乡村与城市在社会交往模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及其相互作用。除了作为数字平台的女性化“人肉补丁”,“斜杠阿姨”们还充当老年数字难民的“解困人”,担任老年人的“人肉数字界面”和家庭代际礼物的传递者等多重角色。
(一)数字平台的女性化“人肉补丁”
受物流发展水平、农村消费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村电商物流网点在空间结构层面呈差异化分布特征,调研地L村就属于此种状况。尽管近年来随着“快递下乡”的推进,农村的物流体系逐渐完善,但受制于农村聚居空间布局的分散性,物流成本高,货物依然无法同城市般实现送货上门。在L村,众多村民便因为要去快递网点自取、退货麻烦等原因而不愿意进行网购。在此情况下,“土生土长”的“团长”凭借着对村庄的了如指掌,能够快速定位每一户村民的居住方位,成功弥补了前述网购的弊端,使得货物上门看得见摸得着、售后有人找,成为数字平台的“人肉补丁”:
淘宝对村里影响没有这么大,现在就很具体了,平台都是生活用品,好齐全。以前村里网购的少,就是青年人买,团购就是连中老年人都买了。因为今天订了货,明天就到,很方便。(A1)
团购到货快,网购都冒得(没有)这么快,最少也要两三天,这个今天买货明天到货,又可以看到,你不满意你可以退。不晓得退了就可以找“团长”,这嗲嗲娭毑(指代老年人)总要面对面来搞。你像鞋子看不中你可以退货,不要产生任何费用。你像网购运费要自己贴,有的还不晓得搞。(B4)
在选择交通工具时,“团长”还会考虑农村地区分散的居住空间、多变的地形以及不同程度的道路硬化情况,灵动选择合适的交通方式。鉴于成本和效率的考虑,他们通常不倾向使用速度更快、动力更强的摩托车或汽车,而选择成本较低且不需高额油费的电动车。由于电动车的载重限制,“团长”常常在电动车上安装两个大型周转筐,前后各一个,以优化派送效率。在订单量大或个人时间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部分“团长”则会切换使用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稳定性较差,面对村庄内起伏连绵的地形时,驾驶需格外谨慎,尤其是在需要频繁上下坡或遇到坑洼路段时——唯有当地居民才能稳定又安全地送货。
(二)数字难民的“解困人”与“人肉数字界面”
老年群体因年龄、经济、思想观念、生理机能等原因在网络空间处于劣势地位,通常被看作是“数字难民”、“数字弱势群体”,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由于受到区域经济的限制,数字融入之路就更为艰难。此种情况在L村普遍存在,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老年群体对于数码产品,无从学习。“像我隔壁的老人家,有智能手机但不晓得如何打电话,一打电话就是到我这里来”(B2)。因此,对于老年群体而言,网购是他们很难考虑的事情,更别说要从平台经济中获益。但这一情况因“团长”的出现而发生了变化。老年村民开始关注村内的社区团购,在得知货物更便宜后还会主动要求“团长”作为他们的“人肉数字界面”帮忙下单。出于热心以及受提成制的刺激,“团长”也会在送货过程中加强与老年群体的联系,相互成就。
有一次,一对80岁的老年夫妇见到前来送货的“团长”B1,向其提出要购置一个小型电饭煲。随后“团长”拿出手机,向老人展示平台商品。老人在两款产品中犹豫不决,“团长”提出帮其购买两款,待第二日再进行实物挑选,老年夫妇对此十分满意。第二天,“团长”带来两个不同型号的电饭煲,并一一打开为其展示,待老人仔细端详、触摸后,选择了其中一个。而后,B1又为其插电试用,并告知其使用的注意事项、售后事宜等,并叮嘱其保留包装。此番细致入微的服务,最后也获得了老年夫妻的称赞。可以看到,在两天的购买电饭煲过程中,“团长”B1不论是从选品购买,还是现场交易、叮嘱售后等方面,其均扮演了“人肉数字界面”角色,使得老年群体对平台购物的体验十分满意,“数字难民”不再为难。
(三)家庭代际礼物的传递者
许多家庭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地区存在着广泛的代际支持失衡现象,此种代际失衡和代际紧张,促使学界提出“孝道衰落”的论断(贺雪峰,2009)。基于工业化的发展,家庭代际分离的情况也渐趋普遍,年轻人外出务工、老年人留守在家,成为众多乡村的普遍现象。媒介的出现在弥补家庭情感交流的同时亦带来一定的副作用。
根据笔者的观察与访谈,社区团购的出现,能在满足情感交流的同时增进亲人间物质联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代际关系,促进家庭交流频次,增进家庭关系亲密度。例如青年群体外出务工时,会以团购下单的形式为家中的父母、老人购置水果蔬菜、牛奶面包等,以弥补个人在外无法及时关照家中的不足。在此之前,家人间只能依靠电话、视频的方式进行情感交流,而缺乏实质性的物质互动。即便有网购存在,也因为派送受限和商品种类受限,以及其背后的节日、生日等时间节点特性,而难以实现对家庭日常生活的关照。如今借助团购平台,年轻者通过选购下单的方式,使得留守在家的父辈、祖辈能感受到远在他乡工作的亲人给予的关怀与照顾,家庭“日常生活的礼物”得以流动创造。
在这其中,“团长”积极承担起了礼物的传递者:
有的老人家在屋里,子女在外面,就要我把他加到这群里买,买了要我送到他爸爸妈妈手里。他们在深圳买了寄过来还要一些天,这里第二天就送了。这种情况比较多,年轻人出了钱,你又送到他(老年人)手里,客客气气的,那几(多)好,他们笑眯的。(B3)
综上所述,社区团购的积极下乡不仅为农村的物流体系提供了完善和便利,也为农村家庭和老年群体带来了重要的社会意义。“团长”们基于自身的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人解决问题,为村庄走上平台经济的道路做出重要贡献。
六、结语
总体而言,在数字平台进入乡村空间并为之赋能的这一过程中,受限于乡村地理位置偏僻及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以及数字平台使用不稳定、数据覆盖面不全、后台监控范围有限等技术特征,选择成为社区团购“团长”的乡村中年女性以“人肉补丁”的方式弥补了团购平台现有的缺陷,为乡村社会的数字化、平台化发展贡献着独属这一群体的社会价值。同时,“人肉补丁”也凸显出女性化的特征,女性的身体被征用成为平台数据与货物流动的中介。在农村独特的聚居空间,女性“团长”们集合了城市中的骑手、“团长”等多重职责在身,为促成和承担货物流动贡献了密集的身体劳动。
结合中国乡镇乡村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本文展现了乡村团购“团长”的平台劳动图景,呈现了其及村民的日常互动。可以看到,“团长”不仅担负着沟通平台与村落的中介作用,更是数字乡村发展的催化剂,发挥着重塑村民的日常生活,促进乡村社会的数字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本文也呈现了农村中年女性在非正规就业中的具体考量与现实情况,揭示了数字平台下乡过程中非正规劳动的性别化特征,展现了乡村中年女性对于数字乡村建设的贡献,以及她们在与平台的深度合作与微观斗争之中凸显的主体性。■
注释
①此处年龄划分,依据罗淳关于人口年龄组的重新划分及其蕴意,参见:罗淳(2017)。关于人口年龄组的重新划分及其蕴意。《人口研究》,41(05),16-25。
②详情请参见兴盛优选官网“关于我们”。
③详情请参见美团优选官网首页。
④详情请参见美团优选官网“成为团长”。
参考文献
陈龙,孙萍(2021)。超级流动、加速循环与离“心”运动——关于互联网平台“流动为生”劳动的反思。《中国青年研究》,(04),29-37。
陈龙(2020)。“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35(06),113-135+244。
丁未(2021)。遭遇“平台”:另类数字劳动与新权力装置。《新闻与传播研究》,28(10),20-38+126。
国务院办公厅(201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检索于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8/08/content_5419761,htm?trs=1,2019-08-08/2022-12-26。
贺雪峰(2009)。农村代际关系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社会科学研究》,(05),84-92。
华经产业研究院(2023)。《2023年中国社区团购行业市场研究报告》。
康正煜,王楠,陆晔(2024)。从家庭“权宜之计”到社区公共关怀:危机情境下上海女性“团长”的社区应对行动研究。《妇女研究论丛》,(04),57-72。
李建奇(2022)。数字化变革、非常规技能溢价与女性就业。《财经研究》,48(07),48-62。
李勇辉,沈波澜,李小琴(2020)。儿童照料方式对已婚流动女性就业的影响。《人口与经济》,(05),44-59。
林颖,许天敏(2022)。新流动性范式下媒介技术与社会联结的再造——基于疫情时期“社区团购”的考察。《中国网络传播研究》,(02),62-80+218-219。
刘海龙,谢卓潇,束开荣(2021)。网络化身体:病毒与补丁。《新闻大学》,(05),40-55+122-123。
卢青青(2021)。半工半家:农村妇女非正规就业的解释。《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03),402-410。
牛天(2022)。内卷化与去内卷化:斜杠青年的工作困境及出路.《当代青年研究》,(05),100-108。
ShanghaiWOW(2022)。《上海“团长”白皮书》。检索于https://www.baogaoting.com/artical/12309,2022-05-05/2023-04-07。
孙萍(2019)。“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思想战线》,45(06),50-57。
孙萍,刘姿君,王从健(2024)。“家庭作为方法”:县域平台化语境下的劳动、性别与社会关系。《新闻与写作》,(09)15-24。
孙萍,赵宇超,张仟煜(2021)。平台、性别与劳动:“女骑手”的性别展演。《妇女研究论丛》,(06),5-16。
吴清军,李贞(2018)。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关于网约车司机工作的混合研究。《社会学研究》,33(04),137-162+244-245。
邢成举(2020)。村镇工厂与农村女性反贫困研究。《妇女研究论丛》,(01),47-55。
谢卓潇(2021)。身体作为移动媒介——跨境代购中的具身传播实践和身体问题。《国际新闻界》,43(03),40-57。
新经销(2020)。2019-2020中国快速消费品流通渠道报告(社区团购篇)。检索于http://123.57.61.103:8099/35a2034c6fe5445ab021cf8dc9afc2a5.pdf。
亚历克斯·罗森布拉特(2019)。《优步:算法重新定义工作》(郭丹杰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159-194。
燕道成,李菲(2021)。制造熟客:社交媒体时代网络情感营销的意旨——以社区团购“团长”为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3(07),129-134。
易若彤(2022)。差序格局与信任困境:疫情之下社区团购志愿者与居民的关系建构。《传媒观察》(05),49-56。
张思雨,刘鸣筝(2021)。农村地区老年人数字融入困境与路径分析。《中国发展》,21(03),66-71。
中国商务部电子商务司(2023)。《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2)》。检索于http://images.mofcom.gov.cn/dzsws/202306/20230609104929992.pdf。
郑亚琴,陈慧娴(2022)。基于社区团购的生鲜电商产品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研究。《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9(01),73-85。
周裕琼(2014)。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36(02),117-123。
Bianchi,S.M.,Milkie,M.A.Sayer,L.C.(2000). Is anyone doing the housework? Trends i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Social forces, 79(1)191-228.
Bianchi,S.M.,Robinson,J.P.,Milke,M.A.(2006). Changing rhythms of American family lif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Muntaner. C.(2018). Digital PlatformsGig Economy,Precarious Employment,and the Invisible Hand of Social Clas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48( 4) ,597-600.
Graham,M., Hjorth,I.,& Lehdonvirta,V.(2017).Digital Labour and Development: Impacts of Global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and the Gig Economy on Worker Livelihoods. 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23( 2) :135-162.
[作者简介]刘亭亭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黄鹰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直播电商传播模式与效果研究”(22YJC860021)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2 年度青年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广东省农村地区电商脱贫研究”(GD22YXW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