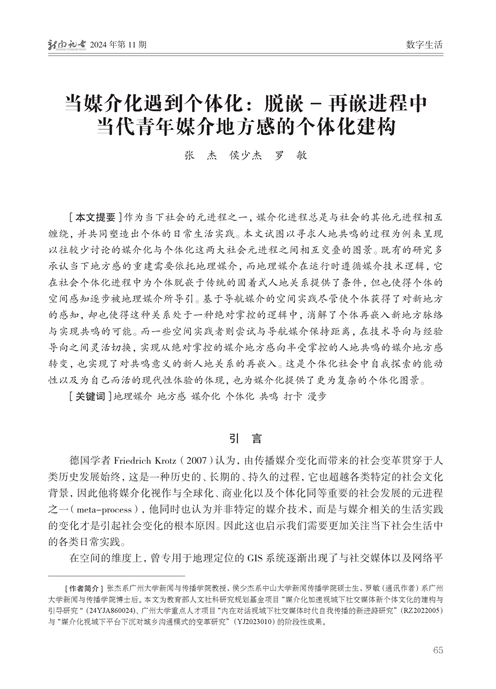当媒介化遇到个体化:脱嵌-再嵌进程中当代青年媒介地方感的个体化建构
张杰 侯少杰 罗敏
[本文提要]作为当下社会的元进程之一,媒介化进程总是与社会的其他元进程相互缠绕,并共同塑造出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本文试图以寻求人地共鸣的过程为例来呈现以往较少讨论的媒介化与个体化这两大社会元进程之间相互交叠的图景。既有的研究多承认当下地方感的重建需要依托地理媒介,而地理媒介在运行时遵循媒介技术逻辑,它在社会个体化进程中为个体脱嵌于传统的固着式人地关系提供了条件,但也使得个体的空间感知逐步被地理媒介所导引。基于导航媒介的空间实践尽管使个体获得了对新地方的感知,却也使得这种关系处于一种绝对掌控的逻辑中,消解了个体再嵌入新地方脉络与实现共鸣的可能。而一些空间实践者则尝试与导航媒介保持距离,在技术导向与经验导向之间灵活切换,实现从绝对掌控的媒介地方感向半受掌控的人地共鸣的媒介地方感转变,也实现了对共鸣意义的新人地关系的再嵌入。这是个体化社会中自我探索的能动性以及为自己而活的现代性体验的体现,也为媒介化提供了更为复杂的个体化图景。
[关键词]地理媒介 地方感 媒介化 个体化 共鸣 打卡 漫步
引言
德国学者Friedrich Krotz(2007)认为,由传播媒介变化而带来的社会变革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始终,这是一种历史的、长期的、持久的过程,它也超越各类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他将媒介化视作与全球化、商业化以及个体化同等重要的社会发展的元进程之一(meta-process),他同时也认为并非特定的媒介技术,而是与媒介相关的生活实践的变化才是引起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这也启示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各类日常实践。
在空间的维度上,曾专用于地理定位的GIS系统逐渐出现了与社交媒体以及网络平台相融合的趋势,生产出被Jeremy Crampton(2009)称为“空间媒介”的新技术形态,这使个体的日常空间实践发生变化,也推动了个体与地理空间关系的重构。这种技术现状也激发起传播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地理位置系统的媒介化,还是媒介组织方式的空间化,一个能够同时激发起两大学科思考与讨论的议题是:“空间媒介”如何影响个体与地理、空间以及移动的关系(Ash,Kitchin,Leszczynski,2019)。在回应这个跨学科议题的过程中,空间媒介技术曾一直被置于思考的核心。然而对技术的思考并非回应当下社会技术境况的终点,如潘忠党(2014)所言,在被技术媒介影响、框限的过程中,个体始终具有能动性与创造力。在人地关系的维度上,地理知识与空间感知源于个体、技术以及空间地方的多维度互动(黄显,2021)。因此,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在空间媒介技术发挥影响之后,个体如何重新组织起其与特定地方的联系?想要更为充分地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将视线从空间媒介技术转移至日常生活中个体的空间媒介实践。
基于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本研究选择日常生活中为个体所广泛应用的电子地图导航作为具体的空间媒介,着眼基于导航媒介的个体空间实践,来探讨寻求建立地方感的过程中,个体如何调适自我与地理媒介的关系,以及个体如何在运用技术、反思技术的基础上重新建构自我与地方的关系,并寻找自我与地方的共鸣。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正如Nick Couldry与Andreas Hepps(2013)所言,伴随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技术媒介已经越来越构成一种独立的制度性力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面向,媒介化已经成为我们所需要应对的社会现实。在空间维度上,媒介化体现为空间与地方日益由媒介所表征与建构,而空间实践日益由各类地理媒介所中介(杨家明,景宜,2023),在人类的经验域内,空间与地方也逐渐从直接经验变为间接经验,因此也如Jansson(2017)所言,媒介如何影响人们对空间的想象或期望已经成为空间媒介化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多研究也已表明,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感建构需要依托技术中介,从而生成媒介性的地方感,并藉此而生发出个体与地方的联系。如一些研究者发现数字媒介的地点“标记”功能有助于建立起个体关于城市或地方的熟悉感与参与度(Humphreys,Liao,2011),而最主流的基于标记地点的空间实践就是“打卡”。地理位置媒介使个体能够“以物理移动和使用信息传播技术两种方式参与到多种地理尺度”(亚当斯,2020:184),在个体的使用过程中,地图与导航的技术可供性时刻提供“在何处”、“能做什么”的信息(许同文,2020),与此同时,基于地理位置的在线社交互动生产出他者关于地方的经验(Frith,2015),塑造出个体关于特定地方的感知。打卡者利用电子地图与导航穿梭于都市之中,在移动的过程中,个体同时生成了自我建构与表达(吴筱玫,2016;Saker,2017)、感知都市形象(孙玮,2020)以及重塑地方感(曾一果,凡婷婷,2022;王东林,孙信茹,张忠训,2023)等多重维度的意义。基于打卡的空间实践的研究体现了研究者们在关于空间媒介如何影响人的空间实践,以及个体如何利用新技术重建地方感这两个核心问题上的乐观态度。但必须意识到,当位置信息被内化为平台服务逻辑之时(束开荣,2022),作为中介的地图导航就受到政治经济要素的影响,地方感的重建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依循政治经济逻辑。有学者就认为地理媒介固然创造了感知新地方的可能性,但其所创造的地方感也存在着滑向消费式凝视的可能(厄里,拉森,1989/2016:2),如蒋晓丽(2020)等人就讨论了打卡体验之真实性的问题,认为打卡体验或许介于真实与被建构之间,因此基于技术中介而获得的空间认知是否能够上升为“对地方的依恋、爱以及认同”(邵培仁,2010)亦有待商榷。也因此,既有的关于媒介性地方感的讨论与批判实际上均聚焦空间实践的技术中介,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关注媒介技术的移动可供性,而批判路径的研究所针对的是媒介化空间实践中媒介技术的非独立以及非透明性,这种批判的取向最早可追溯至列斐伏尔(1974/2015:24),这些研究聚焦于媒介技术以及空间生产,揭示了媒介化空间实践的偏向性,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的主观体验。
在重建人地联系这一议题的讨论上,既有研究往往倾向于在媒介化社会的语境下将技术置于思考核心,强调媒介技术的可供性,而忽略了地方感知也是一种个体的主观体验(段义孚,1974/2018:13),这与个体化进程中的自我“再嵌入”具有一致性(Beck,2001),即将地方作为建构自我生活的资源,通过体验地方来寻找生活的意义感,因此它在本质上也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个体化的“再嵌入”问题。贝克(Ulrich Beck)认为,个体化包含去传统化、制度性抽离的脱嵌过程与寻求再嵌入的过程,最终落点为寻求“为自己而活”,也即寻求自我生活的意义(贝克,2002/2011:26)。个体与地方的关系是主观且非制度化的,其曾被视作传统共同体的构成要素之一,如滕尼斯曾以血缘、地缘与精神划分“共同体”(滕尼斯,1887/1999:67),人文地理学先驱段义孚亦将地方情感与“爱国主义”、“故乡之爱”等归属性意义相连结(段义孚,1974/2018:146)。在人地联系的维度上,个体化进程亦包含“脱嵌”与“再嵌入”两个维度:脱嵌进程体现为对传统固着式人地关系的脱嵌,数字技术正实现了以可供性赋予个体能动性、以新秩序实现个体脱嵌(王敏,潘志超等,2023)的结果,对传统人地联系的脱嵌体现为将传统的“归属性”的恋地情结转化为“审美”式的恋地情结(段义孚,1974/2018:137),这既呼应了既有的以媒介技术寻找新地方感的研究,也呼应了既有的对“被建构的”地方视觉景观的批评;而再嵌入进程则正是在现代性背景下个体化进程所带来的对传统地方的普遍脱嵌,以及由此招致的“无地方”遍在的情况下(Jacobs,Appleyard,1987),重新寻找“归属性”的地方感以及在视觉感知之外寻找基于人地联系的共鸣。
媒介技术实现了个体对传统地方的脱嵌,但却难以实现对新人地联系的建立并完成个体化的“再嵌入”,因为这一进程是主观个体化进程。正如前文所述,利用媒介技术以及通过“打卡”等中介性的空间实践所建立的地方感知是“审美性”的地方感,“归属性”地方感是建立在将地方作为直接经验对象的基础上,经由个体遭遇、体验与感知而生发出的情感(段义孚,1974/2018:141),在个体化进程中,追寻意义与价值往往依赖于个体的“自反性”(Beck,Lau,2005),在地方感的维度,就是认为此地于我而言有意义,而非仅仅被视觉奇观所撼动,而这才能够被视作对新地方的真正意义上的“再嵌入”。在技术中介的空间实践过程中,这种自反性表现为超越技术中介以及都市设计者的空间规则去追寻人地联系(李耘耕,2021),“为自己而活”表现为以更加“不受技术掌控”的形式去体验自我与所在地方的交流与共鸣(罗萨,2021/2022:64),具体表现为一种脱离媒介技术的倾向,即放弃对地图导航的使用。从这个角度看,不同于前述批判路径质疑实践技术中介的非中立、非透明性的取向,个体化理论所反思的是个体的中介化空间实践能否真正建立起新的人地联系,以及在基于地理媒介而获得客观地方认知的基础上,能否更进一步地在主观上获得意义感。
但从脱嵌到再嵌入并非一种纯粹线性的或历时性的进程,前者在当下社会主要由新媒介技术可供性所推动,而后者则依托于个体在空间实践中追寻地方感的自反性与能动性。Friedrich Krotz(2009)认为,媒介化进程与个体化进程是相互交叠的,因此当下社会中才同时存在着或通过依托媒介(曾一果,凡婷婷,2022)或通过逃避媒介(张昱辰,2020)来寻求建立地方感的不同实践。正如Couldry(2004)所言,逃避媒介与选择媒介共同构成了媒介化背景下的媒介实践,这些媒介实践与个体化社会为自己而活的自主个体实践趋势共同构成了当下媒介化-个体化社会的复杂图景:空间实践既是媒介性的实践,但同样也是个体化的人的实践。
因此,本文试图将个体置于思考的核心,从个体化“脱嵌-再嵌入”进程出发来考察当下试图建立人地联系的空间实践,继而尝试勾画复杂的媒介化-个体化图景,并回应前述的核心问题:地图导航对人的空间实践产生影响后,个体如何在反思地图导航技术的基础上重建人与地方的联系,完成对新人地关系的再嵌入。同时也尝试呈现个体化与媒介化这两个较少讨论的元进程之间如何纠缠。
既有研究往往倾向于将认知地方等同于地方感,本文认为,人地联系或地方感需要在认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涉一种“身处此地”的意义感与共鸣感。基于此,本文以电子地图导航为研究对象,探究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如何通过调适自我与电子地图导航的关系,来寻找地方感,基本研究问题进一步明确为:第一,中介化的空间实践对地方认知而言产生了何种影响?第二,在寻求人地联系的过程中存在着哪些类型的实践者?他们所建立的“地方感”有何差异?第三,在个体化“再嵌入”的进程中,个体如何实现从“审美性”的地方感“复归”至“归属性”的地方感?导航对于个体的“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再嵌入进程而言意味着什么?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研究者试图去回应媒介化-个体化进程中的人地联系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媒介化强调对导航媒介的媒介素养,个体化强调自我探索、自我反思,由此,本研究将研究对象设定为初入社会或即将脱离校园、进入社会的青年群体,理由如下:第一,此群体大多出生于世纪之交,在生命历程中完整地经历了传统权威衰弱和现代化的进程,他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在生活实践中表现出更加强烈的追寻个人生活意义与价值以及为自己而活的倾向(段然,2021);第二,此群体作为“数字原住民”,拥有更加丰富的技术使用经验,能够从中更好地窥视为建立地方感而进行的实践;第三,此群体经历了从校园到职场的变动,这既是个体生命历程的变动,也是空间环境的变动,这意味着他们在未来一段生命历程中将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展新的地方感建构的媒介实践,这也为研究者收集经验材料提供了便利。
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研究者遵循适度代表性和可接近性的原则,基于资料饱和度的判断标准,访谈了20位受访者,初期的受访者来自研究者的现实人际网络,研究中后期的受访者则来自于基于人际网络的滚雪球招募以及线上招募。其中,在访谈时,Y1~L1、K2为处于实习状态的在校大学生;L2、G1~S3均具有1~3年职场经历,除J1返校深造外,其余均仍在职。访谈时长约为1~1.5小时,囿于时间限制,在线上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2~3次补充访谈。基于对研究资料的分析,归纳出两种空间实践类型,在感知地方的活动中(不包括目的性的空间实践),全程依赖地理媒介及社交媒体导引的视作打卡者,不依赖或半依赖导引的视作漫步者,多数受访者存在前后两种实践类型的转变,均为由打卡者转向漫步者。
三、媒介化空间实践对个体化“人-地”关系进程的影响
当电子地图成为智能手机的基础应用之一时,它就嵌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使用者通过地图导航来决定自己前往何处以及如何前往,这构成了空间实践的媒介化:一方面,电子地图增强了个体的移动性,个体对空间的感知让位于数字中介,身体借助地图与导航得以前往地点,另一方面,他们的空间实践也受到技术中介的影响(Hjorth,Pink,2014)。如金鳞(2020)所言,电子地图与导航媒介介入的移动,不仅仅是物理的移动,它更是虚实混杂的、被媒介化的移动。当下媒介化空间实践表现为日常空间过程中对导航的使用与依赖,如本研究受访者均经历了(因求学、实习或就业而导致的)空间环境的变化,因而这样的依赖在他们遭遇环境变化初期得到了凸显,如L1的经历具有代表性:“导航对我最大的用处就是它让我敢一个人去更远的地方了……我还记得第一次和闺蜜去珠海,我们那次出去玩的体验很好。因为刚上大学,我们其实都是第一次独立地去家以外的另一个地方,怎么去高铁站,怎么打车,都是全程用导航。刚开始会有些害怕,但很快就感觉得心应手……在外面看地图我就能知道附近的情况,然后决定下一步去干什么,导航帮我们省了很多事。”
在不断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导航逐渐嵌入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以至于失去导航将影响身处陌生地时的正常空间活动。在本文受访者们的描述中,初次对导航的频繁使用始自初入大学时。如C1表示:“如果没有导航的话,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会很紧张,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
K1亦表示:“导航肯定是有用的,特别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一个人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很需要安全感……我得看着地图知道我在什么地方,然后需要弄清楚路怎么走……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它会把你导到那里,不会让人迷路,也不会多走很多路。”
但依赖导航的空间实践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它为个体实现赋能的同时,也使得基于媒介技术的目的性空间实践成为常规;第二,作为一种中介化的空间实践,它使对空间与地方的感知逐渐成为一种间接经验。目的性空间实践的常规化以及地方经验的间接化使个体与地方的关系逐渐成为一种沉默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感知地方的可能性也被遮蔽了,这两种后果往往相互重叠,共同呈现于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
导航嵌入日常生活所带来的第一个后果是将目的性的导引化作生活常规。目的性空间实践的常规化体现为所有的空间活动均被转化为实现特定目的的技术性行动方案。如电子地图的空间呈现与导引更倾向于连接城市基础公共交通,导航并非以最短距离为先,而是往往导向交通基础设施,这事实上会产生与实际地方体验不同的技术路线常规。
Z2就表示:“有的时候导航会很奇怪,比如有一次晚上回我们的出租屋,平常走那条小路晚上路灯不多,很黑,所以我想去走外面的大路,其实离我们的出租屋应该不远,但是导航还是让我走到一个公交站台,坐公交车到另一个站,然后才步行导航到我们的出租屋,这样走实际上会绕远。”
除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外,地图更倾向于呈现地标性建筑,例如一些大型公共设施或商业点,而具体位置则往往容易被遮蔽,这就导致电子地图的定位服务往往会存在偏差。这类定位的误差几乎所有访谈者都会碰到。可见,通过电子地图导航,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城市地标与基础设施,从而提升空间活动的效率,然而这样的技术行动方案在交通基础设施不够发达和缺乏标志性建筑物的非主干区域,就会出现误导。段义孚(1977/2017:112)认为,“停顿是使地方可能成为感受价值的中心”,常规化的目的性空间实践与技术行动方案排除了一切停顿的可能,因此它们难以使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地方感。受访者们使用导航的经历也能够体现这一点,如Y2表示:“尤其是步行导航的时候,必须得全程看着导航,有时候可能因为信号问题,你一个不注意就走错了,就忽然显示你偏离路线,也可能路比较复杂,总之如果是为了导到某个地方,特别是在外面,比如像广州户外都很热,那更要专心看导航,避免导错。”
媒介化空间实践所带来的另一后果是导致对地方感知的间接化。基于地图所建立的地方经验是一种间接的空间经验,它在认知层面增加了个体对空间的确定性感知,但这样的感知始终是抽象的。段义孚(1977/2017:13)认为,空间是一种以移动和有目的的自我为中心的坐标系,它不存在已经成型的、具有人类意义的固定模式;而地方则是一种稳定的,使已确定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也是一种人们可以在其中居住的物体。当人们使用地图中介进行空间实践时,实际上将具体地方简化为抽象的空间坐标系,尽管复杂的不确定性被简单直观的平面投射所消除,但这种简化同样使具体的地方受到遮蔽。地图所呈现的抽象图形,以及因使用地图而设计的抽象路线与具体地方现实之间往往出现偏差,而这样的偏差又会直接影响到个体对具体地方的感知。在访谈过程中,数位受访者均曾出现过对某地“既熟悉又陌生”的体验,以至于多次前往的地方仍然需要导航来定位、寻找和规划。尽管已有研究者认为,导航媒介的运用会在媒介上留下个人化的记忆,从而建立人与地方的联系(金鳞,2020)。然而本研究发现,使用者对导航的具体实践恰恰体现了人与地方的关系是脱嵌的,地图和导航提升了使用者对通行空间的掌控能力,但对个体地方感的建立却无甚帮助。本次深访的受访对象多为生活在广州的大学生,日常出行几乎难以离开广州地铁,而当被问及对地铁口附近的地方体验时,多人表示“从地铁口出来以后往往一时半会找不到方向”。研究者还让多人指认广州南站的基本方向,尽管所有受访者都有多次前往广州南站的经验,并且能够迅速说出前往广州南站所需依赖的交通线,但无一人能够指认出广州南站所在方位的基本方向。C1、S1均表示前往广州南仍需利用导航寻找公交与地铁,然后才能顺利到达。
目的性导引的常规化与地方感知间接化在具体空间实践中往往带来误导的结果,所有受访者均表示拥有被导航误导的经历。通过访谈,研究者发现受访者的被误导经历具有一定的共性,往往是由于空间和道路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使得导航对地方的空间绝对掌控能力下降引发的偏差导致。但也有地方本身的生活经验逻辑无法通过导航的空间技术来标绘引发的“误导”。在这些情况下,技术性行动方案出现了失灵,地理媒介所提供的间接经验也难以呈现出生活世界中人类直接地方经验的丰富性。
受访者F1向研究者讲述了她的一次被误导的经历:
第一次去(实习单位)的时候,实习老师说要我在单位的门口等他,然后我就用导航去导,最后导航把我带到了那个单位的门口,但是我等了好久都不见实习老师,后来收到他的电话,我才知道,他要我去的那个门是正门,但是导航给我导的那个门不是。
研究者了解到,F1所在的实习单位一共有两个门,并且事实上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正门”或“后门”的叫法,该单位所谓的“正门”是该单位的西南门,只是因其正对主要交通线,因而平时人流量多,故单位内员工习惯将其称作“正门”,而地图则不会识别,故在导航时任意一处门都可作终点。如果说常规意义上的误导来自技术自身的偏差,那么以上案例则向我们展现了地理媒介所提供的间接经验与关于地方的直接经验之间的冲突。
通过诸多受访者的经验可以指向一个基本的结论,电子地图导航对空间实践的介入为个体的自由移动实现了赋权,在地理媒介的加持下,处于生命历程转折阶段的青年群体得以摆脱固着地点的限制,获得在陌生地进行全新生命历程实践的自主性,这体现了个体化进程中当代青年对传统人地关系的脱嵌。然而,导航在增强个体的空间移动性的同时,也遵循效率提升原则,因而它将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转化为目的性导引,导航强调的是对地方的数字意义的精确和绝对掌控,因而在提供关于地方间接经验的同时也就弱化了个体对地方的直接感知。人文地理学认为,日常的空间实践是生成地方感的重要来源(段义孚,1977/2017:118),而地图导航将日常空间实践转化为基于间接经验的目的式的实践,也因此,地图导航事实上无法提供基于生活世界经验的地方知识,生活世界经验的共享性和意义感被数字导航所遮蔽,从而偶尔会出现误导意义的实践冲突。
当然,伴随技术进步,导航软件也在不断优化自身功能,如F1号受访者的误导经历在当下已经很少发生,这样的优化不仅仅是对导引精度的优化,更意图将人类关于地方的直接经验进行数字化呈现。高德地图技术专家方兴(2019)表示,将使用更多的人工采集数据进行模型训练,以使导航功能更加适应一些需要直接人类经验的情境,如室内导航。时至今日,导航早已能够实现精确到“小径”级别的路线规划导引,并能够根据交通及路况提供最优的导引规划。然而误导概率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其有利于协助使用者实现对新人地关系的再嵌,技术的优化恰恰意味着对目的式、间接性空间实践的强化,原本作为城市以及地方属性的街道或建筑被转化为交通枢纽,这在实践中也降低了自我与地方之间相互触-动、敞开的双向关系建构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基于数字掌控的地图导航在个体化进程中推动了个体对传统固着式地方关系的脱嵌,个体获得移动的自由,依托导航,当代青年群体得以适应(因升学、实习或工作等生命历程变化而发生的)新空间环境的变化,这为建立新人地联系与实现再嵌提供了契机,但日常的、媒介化以及目的性的电子地图导引难以协助个体建立起新的地方感,因而也难以实现个体对新人地关系的再嵌入。
四、“再嵌”进程之一:“打卡”—— 掌控性的地方体验
个体化的“再嵌入”进程是一种主观的自我筹划,是个体在脱嵌于传统制度后对自我生活与价值观的重新整合。阎云翔(2021)认为,“为自己而活”作为当下中国社会个体化的主要命题,其公共话语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在日常生活运作层面,能够超越“为他人而活”的主流道德传统,从而解放出更多的自由,如决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第二,在第一层次的基础上,追寻意义与价值,超越浮于表面的“自由”。地理媒介同时提供了实现这两重维度个体化的可能: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地理媒介所带来的移动力使个体获得移动的自由,去往任意想去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体验不同的地方而获得脱离常规的差异性体验,并从中寻找意义、价值与共鸣(王学基,解佳,孙九霞,2019)。由于地理媒介所介入的日常常规式空间实践难以实现个体化进程的主观“再嵌入”,部分个体尝试发挥地图导航的移动可供性,试图通过探索新地方、体验陌生地来寻求建立新的人地联系。
而当下的现实在于个体不仅得以利用地图导航来体验陌生地,而且也逐渐通过媒介来掌控陌生地,即新地方感不再源于对新地方的“遭遇”,而源于通过地理媒介对地方信息的全方位掌控。这其中,如文献部分所述,打卡的空间实践引起了研究者普遍的关注。打卡(check in),即经由媒介(往往社交媒体与地图导航共同发挥作用)获取特定的位置信息,并在实践中以体验该地点为目的的一种实践方式。在打卡的过程中,个体通过导航媒介进行位置导引,在特定地点进行位置上传,因此打卡也是一种基于导航媒介的空间实践,其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目的式导引,只不过此时寻求人地联系成为目的本身。落到个体层面,这也是媒介化社会背景下,个体借助媒介技术赋权来发挥能动性,通过打卡来体验不同地方,并以之构成个体的生活内容。在打卡体验中建立起的地方感则构成个体化生活的意义来源之一。对于本研究受访者而言,打卡既是一种体验式的生活方式,也是认识与熟悉地方的途径。
G1表示:“打卡就是为了去放空啊,换个环境,平常我要一直坐在一个地方工作,低头是屏幕,抬头是天花板,所以有空了去打卡,起码让我感觉我的生活没那么单调。”
在常规式的目的性空间实践难以建立起地方认知的前提下,受访者就将打卡作为一种认识地方、建立地方感并实现“再嵌”的方式。如K1表示:“我愿意去打卡,或者打卡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能在玩和体验的同时也去认识新地方,比如刚来广州上学,我之前对这个城市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象,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就会通过打卡来了解。我觉得现在导航软件上的那些城市足迹,其实也有点这个意思。”
但作为一种媒介化的空间实践,打卡者在进行体验时往往不自觉地依循着媒介的导引(既包括社交媒介,也包括地理媒介)。本研究的受访者中,多数都有打卡经历。尽管他们打卡的动机不尽相同,但多数打卡行动的初始意愿都来自社交平台,如L1去H市博物馆打卡是因为在小红书被“安利”,“很多人都去,所以自己也想去”,F1到G市创业园打卡则是因在小红书上看到网友分享的照片“觉得那个地方好玩”。这表明地点打卡的动力源于媒介性视觉奇观的刺激。传统人文地理学所秉持的观点是,地方感与人地联系诞生于身处特定地方所衍生出的情感与意义链接(Kyle,Graefe,2004),即人地联系源于内在的体验与情感;而打卡则是一种相反的模式,打卡者往往首先获得的是关于特定地方的(视觉)或他人的外在化体验,而后才前往目的地打卡,这种颠倒的顺序也是近年来网红打卡被质疑为一种全新文化工业的主要原因(柳莹,2021)。打卡行动源于外在化的体验,打卡者也在实践中尝试重复这种体验。
X1在分享自己打卡经历的过程中表示:“去拍照的时候肯定要把一些东西拍进去啊,不然怎么能说你来过这里?比如说华南植物园的粉红牡丹,就是有很多标志性的东西,就像你去巴黎肯定要去一次埃菲尔铁塔啊,要不然不就白去了。”
外在化体验构成了打卡的动力和主体,这表明经由打卡所获得地方感是“审美性”的地方感。当然,段义孚认为,恋地情结恰恰始自外化的审美体验(段义孚,1974/2018:137),因此诸多研究者对其抱有乐观态度,认为其开启了技术媒介时代人地联系的全新可能,即流动性的人地联系(魏然,2013),在这个过程中,以地图导航为依托,个体获得了位置的自主游移性,创造了一种新的基于媒介的移动的地方体验。
X1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宅”的人,平日较少外出,但曾有一段时间每当他在小红书上刷到自己所在城市的网红打卡点,他就会在周末或假期前去游玩打卡。“其实也是找一个机会出去走一走,在网上看到别人会去那里拍照,很好看,很有意思,那我就也会觉得那个地方很有意思,也想去玩,过去之后就会知道,原来广州还有这种地方……觉得自己对这个城市又多了一些了解。”
研究者在此并不否定打卡所蕴含的构建地方感知的可能,因为体验(虽然是外在化的体验)的确构成了打卡实践的核心;但同样需要重视的是,奇观才是打卡(视觉)体验的来源。这与景点旅游拥有相似的逻辑,即令感官投入奇观带来的刺激。对于打卡者而言,日常及周遭不会成为打卡地,地理位置媒介不仅成为打卡的工具,而且成为打卡的逻辑:路途所遭遇的日常生活不再重要,终点只有打卡地。对于打卡者而言,超出打卡点的地方也变成了无意义的空间,因此,由打卡而来的体验不仅是外在的,同时也并不是整体的,它失去了人文地理学所强调的对地方纹理的感知,也难以复归于“归属性”的人地联系,它也由此难以实现经由对地方的敞开体验来获得真正的人地共鸣,继而追寻自我意义的可能。因此,打卡也成为一种“凝视”的后果(厄里,拉森,1989/2016:126、179),打卡者通过打卡上传实现了观看者与被观看者身份的来回移动。作为观看者,个体经由社交媒介观看打卡地之时已经形成了既定的期待和外在化体验,在重复了地方体验、进行打卡上传后,个体又转而成为被观看者,打卡地以及打卡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被反复讨论、强调以及认同,从而形成了一种“从社交媒介上来,到社交媒介中去”的反复循环。原本经由地图导航所创造的感知地方的可能,也在他者的凝视下转化为对媒介化地方的掌控,真正的地方,在这种凝视和外在化体验中陷入了沉默。由此,打卡也由感知地方的具身实践,转化成为进行奇观生产、自我建构与寻求他者认同的媒介实践(Firth,Wilken,2019)。
本研究中的部分受访者曾在打卡结束后将所拍摄照片或视频上传至微信朋友圈、微信视频号或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分享体验与情感的方式。
S2表示:“我在网上看到别人说一个地方很好玩,然后我闲下来的时候就跑去这个地方放松一下,休息一下,拍拍照,打个卡,发发朋友圈,告诉我的朋友们,我也来这个地方了,我现在很开心。我觉得这是一种日常分享,当然也可以说是安利,因为如果那个地方不好玩,我也不会发朋友圈。”
L1则在经历过几次不愉快的打卡经历后,逐渐对这种活动产生了反感。“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一味按照这些旅游打卡攻略走,我一定错失了许多更有趣的小店铺,或者小风景。而且在小红书上提前看了某个景点精修过、最漂亮的照片之后,后面再亲自抵达目的地,我更多的是有落差感,就是被照骗了。”
这也印证了打卡实践与目的式实践的同一性,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掌控逻辑,它体现在对身体感知以及地方的双重掌控。经由中介性的媒介地方图像,个体获得对体验的掌控而非探索,“我”通过媒介的地方呈现和他人体验产生此地值得一去的意图,经由中介性的位置媒介,“我”略过了体验途经其他未知地方的可能,最终实现了媒介性地方体验与经由打卡上传、分享、互动所建构的自我认知的双重结果,但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的意义脉络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见的,打卡能够留下印象,却难以制造共鸣(resonance)。正如哈特穆特·罗萨(2021/2022:26)所言:在掌控逻辑下,世界变成我们要认知、管控或利用的客体,因此,各种充满张力的生命经验,在具体地方实践中实现个体与地方触及与共鸣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
个体经由位置与导航媒介去打卡,得以认知与体验更多的地点与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将个体身份、自我建构以及自我认同融入移动性、媒介性的地方体验之中,实现了当下媒介化与个体化的第一次际遇(encounter)。打卡者具有空间能动性,但他们的能动性在于对社交媒体、导航地图等技术中介的媒介性的适应。他们的审美来源与方式、意图的生成与明确、感知某具体地方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均由媒介掌控,打卡的意义也在于对地方的媒介图像、自身地理位置的上传,继而获得媒介空间陌生人群体的互动与认同。
但是,这种基于媒介的对地点的外在化体验也并不意味着自我对地方的敞开、触及与共鸣。因此,尽管地图导航所生成的可供性在个体化维度上实现了为个体的赋能,使之得以保持空间层面的流动性,并以之为资源建立起自我呈现或身份认同,创造了再嵌入新人地关系的可能,但它在实践中,却使个体成为遵循媒介导引,通过媒介来掌控地方的个体化行动者,这种掌控中的地方是悬浮于媒介中的,脱离了真实人地关系,地方成为媒介地方,成为行动者空间媒介实践掌控的对象,吊诡的是,真实的地方世界因而无法真正向个体敞开,成为沉默关系,因而也就无法实现个体化的再嵌入进程,也即实现嵌入新地方脉络并寻求意义的进程,无法在空间实践中寻求人地共鸣进而探索“为自己而活”的意义感,成为真正的个体化行动者,而成为悬浮于媒介地方的媒介化行动者,也因此,个体通过发挥技术赋能寻找地方感的这一实现“再嵌入”的尝试最终是无法实现的。
伴随媒介化进程的深入,媒介使用者在逃避技术对人地关系的媒介化掌控的过程中逐步增强了自我反思性,个体化进程使得部分实践者更进一步强化了对自我的反身,最终衍生出了更加多样化的个体化意义的空间媒介实践。
五、“再嵌”进程之二:“漫步”——自反性的地方体验
对由地理媒介所中介的日常空间实践以及打卡实践的反思表明,尽管新媒介技术在推动社会个体化进程中为个体赋予了能动性,但在适应媒介化生活的过程中,个体也逐渐形成了对技术的依赖,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关于技术依赖(蒋俏蕾,郝晓鸣,林翠绢,2019)、技术成瘾(付晓燕,罗霭彤,2023)以及技术断连(黄典林,董晨宇,杨润苗,2022)的讨论。个体脱离了传统制度、传统关系的支配,却遭遇了来自于技术的隐形支配,日常的生活实践被转化为充斥着媒介技术逻辑的媒介化实践,因此这也表明纯粹地借助媒介技术难以实现个体化的最终目标,即使个体对新制度与新关系的“再嵌入”,也难以在被媒介逻辑所支配的实践活动中寻得意义感与共鸣感。
而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在追求“为自己而活”的过程中也使得其同样具有自反性,在地理媒介逐渐导引空间实践的过程中,个体也逐渐开始有意识地通过不依赖媒介来建立起对地方的直接感知。本雅明曾使用“闲逛者”概念去描述发达资本主义时代能够在移动中通过陌生人群和地方寻求刺激的个体。19世纪的法国社会在经历经济与政治变革后,人与人的关系从迪尔凯姆所说的机械团结转向了有机团结,从固定于一定空间内的人的关系转向流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城市中的人群逐渐成为个体隐匿自身,平衡自身个体独立性与社会团结张力的去处。在此过程之中,闲逛者在人群中、在现代资本主义城市拱廊街的穿梭中开启全部感官,他们所获得的感受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时刻变化的刺激,本雅明称之为“惊颤”(瓦尔特·本雅明,1969/2014:136),这样的体验方式源于现代都市的兴起对传统地方的影响与冲击。
承继对闲逛者体验性特征的思考,研究者将访谈中那些重视非目的性的内在体验的空间实践者视作城市漫步者,这类空间实践者具有相对较强的空间感,他们能够随时在地图导航与日常生活经验导向之间进行切换,从而实现了对位置与导航媒介的自主性。他们重视地方体验和生活世界的意义感,能够与具体地方建立起一种灵活联系。在追求地方感的过程中,漫步者并不拒绝导航技术与交通基础设施,而是能够根据情境适时放弃导航或在个人经验引导与定位导航之间进行平衡,即在关注空间电子导航的同时注重对具体地方和生活世界意义的感知。
在访谈对象中,T1的经历能够体现出城市漫步者的特征,即个体通过向地方的陌生性(而非提前掌控)敞开来触及和沟通地方。研究者得知,T1有时会抽出时间专门开展一些漫无目的的城市旅行。T1在分享其经历时表示:
我没有去规划具体一定会到哪里,也没有规划具体会发现什么东西,……比如说把自己丢在一个公交车上,或者丢去一个地铁,随便看到哪个名字顺眼,你就下车了……在一个地方熟悉了,就必须要去找一些意义感,就是有序之中的无序和意外,去找一些不期而遇的惊喜。
除了如T1这样本身就拥有无规划漫游习惯的受访者,多数受访者是在经历打卡体验的“非真实感”后选择开展“漫步式”的地方实践。如L1表示:“有些地方还是很值得去打卡的,但是其实很少,而且我感觉自从打卡这个行为出圈了以后,好像很多地方就在制造打卡点,你过去了一看就感觉那些东西很廉价……所以后来我更喜欢去一个地方随处走走,而不是专门去看什么东西。”L2亦表示当下越来越难找到“误入藕花深处”意义的漫步体验。
漫步者的体验来自向地方的陌生性敞开、相互触及所带来的共鸣感受,但他们也不会放弃导航,他们注重导航的工具性使用,但不会使导航的位置信息以及向导信息主导自己的空间实践。如Y1表示,在外游玩时,在“玩的状态”下,自己并不喜欢使用导航,但在不熟悉的地方,却需要通过导航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感”,在确认到达大的目的地以后,他就会放弃导航,投入“玩的状态”,他表示,“导航只是为了赶时间或者赶效率”,而不是为了追求敞开意义的体验。
于是,在逃避绝对掌控以及自我探索、自我反思的过程中,个体化与媒介化实现了第二次际遇:那就是弱化对媒介技术的依赖,并强化对其的工具性使用。他们一方面使用地图导航获得对全新地方的认识与初步体验,另一方面则试图脱离社交媒介和地图导航转而依赖自身向地方敞开所获得的内在经验,如通过方向感、具体的建筑方位来获得对陌生地方的全面体验,进而实现触及、交流与熟悉,在此过程中,除视觉外,往往还伴随着触摸、问询、嗅觉以及听觉。这种行为使得自我不再是悬浮于技术中的自我,而是一种始终保持灵活性与生活世界脉络性的自我。漫步者身处个体化社会,作为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对于他人与技术,他/她时刻保有对人际关系和人与技术关系的移动与停留的可能,从而成为in-between关系意义的既保持流动能力,又对关系负有责任、抱有热情的个体,他或在陌生性中寻找自身与地方的联系与区分,或在熟悉性中对地方脉络进行反复铭刻与书写,最终目的是建立人与地方的交流关系,从而获得本体意义的安全感和与地方世界的共鸣。
如J1在出游的探索过程中体验到个人体验与地方之间的共鸣:“去年夏天去鼓浪屿的时候,我其实都没有想到,我有一个心经杯,是李叔同出家以后写的,他写的那个心经我觉得特别好……我当时去了鼓浪屿,知道那里有一个寺庙,就是弘一法师在那里苦修了多少年,我就临时起意想要去一下,到了那边看到有一个弘一法师造像,我突然想起我的杯子,上面有一句偈句,写的是‘花枝春满,天心月圆’,这什么意思呢?当时我对于这些东西的理解没有那么深,但它其实讲的就是清净自信,就是在那一刻,就是在厦门,在弘一法师修行过的那样一个场景,那些偈句和这个特殊的地方,以及我的那个杯子,然后还有我对于佛学的这种热爱,它突然就凝聚到一起。”
G1则在前往旅行目的地的中途意外地经历了一次共鸣的体验:“我有一次去云南旅行,我们当时定了一个目的地……但是去的途中路过一片很大的湖,真的很大,而且很漂亮,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天空之镜’……还有周围的环境和当时的气候都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让人一下子就明白什么是拥抱自然,这是一种很少体验过甚至从没体验过的感觉,我们甚至从没听过那片湖的名字,但当时就直接停下了,感觉所有的安排都不重要了,我们最后就在离湖最近的一个地方住了下来,也没有去目的地。”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不再是打卡点,而是需要个体去感受、触及、敞开的真实空间,同时个体也在自我与地方互动的过程中重新意识到被遗忘的自我面向。
去中介感知的意义在于,对于具体的地方而言,地方的脉络不再由个体与地方以外的第三者来书写;而对于个体而言,相对于依托媒介的空间活动,漫步者不会受到媒介导引的约束,个体的流动性一方面带来了感知的自由(王学基,孙九霞,黄秀波,2019),另一方面也使其能够把握更加敞开的地方形象,重新寻回目的地以外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遭遇着地方,而地方也在个体漫步的过程中向自我敞开和相互触及。
地方信息固然能够从媒介中获知,但人文地理研究者认为,唯有经历具身的实践,在空间实践中遭遇、认知并解读地方知识,个体方才能够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情感与共鸣(Collins,2020)。例如T1有探地名的习惯:“就比如说在北京……在央视周围的这些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比如金台夕照,然后这里叫什么十里,比如这个什么桥,那个什么庄……然后我就从我住的地方,一路走下去,然后有时候路边你就能遇到某一个牌子,它就解释,这里以前是什么……这会让我有种历史感。”
同时,对技术媒介掌控性的反思以及去中介的空间实践也进一步强化了个体在探索地方过程中的自主性与能动性。近年来兴起的City Walk即是一个例证。如果说地图导航制造了日常空间活动的常规,那么这些去中介的、旨在重新探索地方的漫步则试图打破这种技术常规,重新寻找被位置媒介所遮蔽的地方(张昱辰,2018),这种去中介的具身实践在一些文化中甚至被赋予了连接土地、朝圣国家的神圣色彩(Collins & Kliot,201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漫步者这样的从“导航”走向“非导航”、从“被导引”到“自我能动”在具体的空间实践中并非一种截然的二元对立和转变。Y2是一个在陌生地方向感相对较差的人,她表示:“我以前出去逛之前几乎必刷小红书做攻略……用导航把我带到目的地,然后逛完了去另一个地方就继续用导航……如果没有导航,在外面几乎寸步难行,特别在陌生的地方会感到很无力。”
但Y2却并不喜欢使用导航的体验:“可以想象一下,我本来在我们的现实空间里走得好好的,但是我不得不拿出手机去看一下地图,去走进这个2D甚至3D的世界里面……尽管现在的VR地图已经能够实现傻瓜式导航了,但对我这样的晕3D的人来说,是会有一些生理不适的……但是为了到达某个地方,你又不得不去使用这个东西。”
身处陌生地的不安全感与焦虑是其使用导航的主要原因。然而,在一次前往重庆的出游中,Y2逐渐摆脱了对导航的依赖。“因为重庆的地形真的挺复杂的,我们知道导航也已经‘尽力了’,但是还是会找不着地儿,所以我们在重庆基本都是打出租车,只有当地的老司机才知道路怎么走。”最终,Y2通过问询当地司机获得了自己所需的地方信息,并且收获了基于位置媒介与社交媒体所难以获得的信息:“重庆的司机师傅都很nice,他们确实驾驶熟练,而且健谈……他们会给我们推荐去处,比如餐厅,我们本来打算去大众点评上看到的一家,司机听到了就告诉我们不要去,然后给我们推荐了另一家在犄角旮旯的饭店,真的很好吃,还告诉我们在洪崖洞门口不要花钱让别人拍……某个地方有某个历史遗迹,是抗战时期留下的……”
在Y2的案例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取代技术背后的工具理性与掌控逻辑,从而建立起更加丰富更加具体的人地关系,地方不再是一个视觉意义上的景观,而是充满人类经验与意义的场所,个体与地方之间不是一种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绝对掌控关系,而是相互敞开、相互触及从而有生发人地共鸣的可能性。
也由此,在反思技术导引的基础上,通过去中介、半掌控式的空间实践,个体既寻得了身处特定地方的意义感,也实现了对新人地关系的再嵌入。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漫步”与“打卡”之间的界限在实践中并不泾渭分明,二者更像是理念型光谱的两极,个体的空间实践在其中有所偏向,打卡实践是掌控性的,在经历过不愉快的打卡体验后,一些打卡者仍会继续打卡,但他们将打卡范围逐渐放大,如开始尝试在打卡地的周遭进行漫游;漫步实践虽体现了个体化进程中的自反性,但在现实层面,热衷于完全无规划漫游的空间实践者亦不多见(本研究中仅有3位受访者有此习惯),而城市漫游如City Walk等实践形式也在近年来出现了“网红化”趋势,前往“热门路线”进行城市徒步成为一种另类打卡。也因此,对打卡或漫步的讨论更多取决于具体空间实践过程中的偏向性。
六.当媒介化遇到个体化:深度媒介化时代下的个体自由
作为当下世界的两种元进程,媒介化的进程是嵌入社会个体化进程之中的,两种进程相互交缠,并在个体的空间实践中遭遇,从而生成了不同类型的空间实践者:打卡者与漫步者。二者较之传统的空间实践者而言,其共通点在于依靠媒介技术实现了对固着人地关系的脱嵌,但其个体化方式由于对媒介化的反思程度差异而呈现出“依媒介而活”和“为自己而活”的差异,其与地方的关系也由于其对媒介化反思程度的差异,呈现出掌控媒介地方(悬浮于真实地方)和再嵌入人地共鸣关系的差异。概言之,在人地关系这一非制度化领域中,个体化进程呈现为“脱嵌”与“再嵌”两个阶段,媒介技术的赋能得以实现个体对固着地方的脱嵌,但纯粹的依赖技术却难以实现对新地方,以及与新地方联系的再嵌(见表2)。
研究发现,地理媒介的介入固然提供了全新的移动性以及感知新地方的可能,但它也创造出了中介式、目的性的空间实践常规,这阻碍了个体通过日常的空间实践来建立新的地方感。打卡与漫步均为寻求对新人地关系“再嵌入”的尝试,但如前文所言,打卡者难以通过依赖媒介来建立内在的真实地方感知,难以实现遭遇和敞开意义的人地共鸣,而这样的地方感知与共鸣正是个体化所寻求的生活意义。而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逐步发展出的反身和反思性——即对意义与价值的追寻使之尝试弃用导航,或仅维持“半掌控”的状态,并以此来追寻遭遇陌生、认识地方以及与地方共鸣的体验,进而实现对新地方关系与新地方脉络的再嵌入。
相较于强调依恋、亲切与熟悉的传统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感,地方与恋地情结均生成于对“故乡”的停留,继而生发了基于时间脉络的地方体验;媒介性地方感则是在以地理媒介为中介进行空间实践的过程中而生成的地方感,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感的生成不依赖于时间维度上的停留,而依赖于现代性社会背景下大范围空间实践过程中的流动性遭遇,因而媒介性地方感是强调审美、陌生、差异与刺激的地方感。其中本文所讨论的“打卡”与“漫步”是两种生成媒介式地方感的空间实践类型,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打卡”的过程中,体验源自地理媒介所提供的行动方案,因而通过打卡能够获得遭遇奇观、体验差异的地方感知,但也因此,其丧失了探索的自由与刺激;而在“漫步”的过程中,地理媒介仅作为行动的辅助工具,个体以“半掌控”的方式触及地方,半掌控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从被媒介掌控走向不受掌控的实践状态或媒介经验,而且意味着一种新型人地关系模式的建立,这种关系模式包括从对媒介的半掌控到对地方的触-动、敞开三个环节。半掌控式的媒介实践一方面为个体提供了身处陌生地的安全感,另一方面也确保其能够真正触及地方,这样的触及不仅仅是身处此地的感官知觉与对文化及地方历史脉络的感知,同时也是对地方的身体意义的体验、对地方的尊重和尊重基础上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直接性的地方体验避免了中介干扰,因而也确保了个体与地方的相互敞开,个体将其“放置在、裹入到并关联着一个作为整体的世界”(罗萨,2021/2022:35),由此而产生的地方感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地方感。也如本文的受访者们所言,他们感受到了生理上的快感,漫步者对地方的触及得到了地方的回应,地方不再是沉默的掌控对象,而是实现了与个体之间的相互触及,是双向的触动和身心意义的相互敞开,因而这也是实在的、人与地方交互的共鸣式的地方感。
正如罗萨(2021/2022:50)所言,共鸣并非纯粹的刺激,而是触动、回应以及吸纳转化的过程,它往往是不可掌控的,而导航与位置媒介所依循的恰恰是掌控的逻辑,因而中介式的感知性空间实践难以建立起共鸣性的人地联系。因此个体不断脱嵌、不断追寻自由、追寻共鸣的努力也呼应了西方学者所讨论的“如何实现美好生活”的命题,也因此,唯有在遭遇地方、再嵌入地方脉络的过程中生发出共鸣体验,个体方能体验 “过自己的生活”的意义感。从依赖技术到脱嵌技术再到再嵌入地方的脱嵌-再嵌入的个体化进程,这也对应着罗萨所总结的“本质-异化-复归”的过程。关于人与技术、人与媒介关系在传播学既往的讨论中,伴随技术普及而来的媒介化论断与强调人对技术工具性使用的驯化论断成为分析人与技术关系的二元对立的基本思路。通过对漫步者的讨论,研究者发现漫步者的实践以及其对导航媒介的工具性使用并非仅仅是驯化,而且是一种对媒介地方及其背后的掌控逻辑的反思与反身,是对地方生活世界的个体内在体验的追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与地方之间相互敞开的共鸣关系的再嵌入。
因此,思考地理媒介问题不能仅仅将之视为媒介化。媒介化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嵌入在现代性的其他元进程之中的,媒介化这一进程需要放置在现代性体验这一基础性的社会背景下去考量。伴随着晚期现代性的到来,现代性体验已经从早期现代性的陌生人的震惊体验(闲逛者就是一个典型)逐步转化为个体化社会的自我探索。如果说早期现代性强调的是从流动性中拥抱陌生性,获得不断的碎片性的交往惊颤的话,个体化进程作为晚期现代性的社会形态,恰恰是在无穷的流动和碎片体验中通过个体的自我探索去获得相对的确定性和意义感,实现为自己而活,这种意义感是社会加速背景下的基于半受掌控的从容相互触及、敞开的共鸣,为自己而活也是创造人与世界共鸣关系中的自我的美好生活。因而,“漫步”可以看作是个体化社会中的现代性体验,是个体化社会中我们寻找个体意义与半受掌控的共鸣意义的个体自由的媒介实践。这种实践更强调个体的探索,通过对媒介的灵活使用,与现实生活世界重新建立起半受掌控的共鸣联系、获得脉络的意义感,从而获得个体意义的相对自由。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通过对媒介的自主反思与使用,通过对人地共鸣关系的追寻,从而获得为自己而活的可能性。这种基于自我探索意义的、在人与世界的共鸣中的为自己而活恰恰是这个时代里我们所追求的自由。
也因此,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与突破在于两点:第一,地方感建构问题在当下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一方面,在空间活动范围空前扩大的当下,地方感建构需要依赖地理媒介的辅助,另一方面,地方感又是一种主观体验,纯粹依赖技术方案难以建构起真正的地方感。既往研究往往集中讨论了前者,而忽略后者,以至于在相关话题(如打卡)的讨论中出现了矛盾的观点,本研究认识到了这一复杂性,通过“脱嵌-再嵌”的框架对之进行了分析,从而从个体感受出发重新解释了当代青年所进行的媒介地方感建构过程。第二,在既往的媒介化研究传统中,研究者们更多讨论的是媒介化与全球化、商业化等社会元进程相互影响的后果(Krotz,2007),而本研究则为过去尚未被讨论过的媒介化与个体化这两大社会元进程如何相互缠绕提供了初步的经验研究和理论阐释。■
参考文献
保罗·亚当斯(2009/2020)。《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袁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段然(2021)。“积极个人”:个体化视角下都市青年的职业选择及其另类实践。《中国青年研究》,(09),63-70+55。
段义孚(1974/2018)。《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段义孚(1977/2017)。《空间与地方》(王志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方兴(2019年10月23日)。向场景化、精细化演进的定位技术。检索于https://developer.aliyun.com/article/721954。
斐迪南·滕尼斯(1887/1999)。《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付晓燕,罗蔼彤(2023)。媒介化社会中的照片投资——18位修图成瘾者的科技生活史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01),152-160。
哈特穆特·罗萨(2021/2022)。《不受掌控》(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亨利·列斐伏尔(1974/2015)。《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黄典林,刘晨宇,杨润苗(2022)。弹性断连、专注力管理与数字化时代的自我边界工作。《新闻与写作》,(06),14-26。
黄显(2021)。数字地理研究中的媒介和传播:人与技术的会遇。《新闻记者》,(06),15-27。
蒋俏蕾,郝晓鸣,林翠绢(2019)。媒介依赖理论视角下的智能手机使用心理与行为——中国与新加坡大学生手机使用比较研究。《新闻大学》,(03),101-115+120。
蒋晓丽,郭旭东(2020)。媒体朝圣与空间芭蕾:“网红目的地”的文化形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0),12-17。
金鳞(2020)。适地性媒介研究与城市特质探讨:以移居香港的中国大陆居民之地方经验为例。《新闻学研究》(台湾),(145),101-146。
柳莹(2021)。青年网红打卡文化的符号消费及反思。《江西社会科学》,(09),238-245。
潘忠党(2014)。“玩转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4),153-162。
邵培仁(2010)。地方的体温:媒介地理要素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记忆。《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5),143-148。
束开荣(2022)。构建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平台规训、算法协商与技术盗猎——基于“送外卖”的田野调查。《新闻与传播研究》,(09),39-58+126-127。
孙玮(2020)。我拍故我在 我们打卡故城市在——短视频:赛博城市的大众影像实践。《国际新闻界》,(06),6-22。
瓦尔特·本雅明(1969/2014)。《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
王东林,孙信茹,张忠训(2023)。位置媒介与数码地貌:对一位普米族青年数字足迹的田野考察。《新闻大学》,(09),104-116+121。
王敏,潘志超,钟秋怡,郭大豪,劳家荣,林晓炀(2023)。个体化数字乡村实践与空间重构:以广州桂峰村为例。《人文地理》,(05),126-134。
王学基,解佳,孙九霞(2019)。在路上:道路旅行者的流动实践及其意义解读。《旅游科学》,(05),1-13。
王学基,孙九霞,黄秀波 (2019)。中介、身体与情感:川藏公路旅行中的流动性体验。《地理科学》,(11),1780-1786。
魏然(2017)。媒介漫游者的在地存有:位置媒介与城市地方感。《新媒体与社会》,(04),285-299。
乌尔里希·贝克(2002/2011)。《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筱玫(2016)。网上行走:Facebook使用者之打卡战术与地标实践。《新闻学研究》(台湾),(126),93-131。
许同文(2020)。 复合空间中的移动实践:作为移动力的移动地图。《新闻学研究》(台湾),(145),147-195。
阎云翔(2021)。“为自己而活”抑或“自己的活法”——中国个体化命题本土化再思考。《探索与争鸣》,(10),46-59+177-178。
杨家明,景宜(2023)。 媒介行为:认识“空间媒介”的“第三重进路”。《新闻与传播研究》,(08), 46-62+126-127。
约翰·厄里,乔纳斯·拉森(1989/2016)。《游客的凝视》(黄宛瑜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曾一果,凡婷婷(2022)。 重识“地方”:网红空间与媒介地方感的形成——以短视频打卡“西安城墙”为考察中心。《新闻与传播研究》,(11),71-89+128。
张昱辰(2020)。重构“恋地情结”:城市徒步中的传播与文化政治。《媒介批评》,(00),24-36。
Ash,J.KitchinR.&Leszczynski,A.(2019).Introducing Digital Geographies. In AshJ.KitchinR.& LeszczynskiA.(Eds.).Digital Geographies(pp.1-10).LondonUK:SAGE.
Bilandzic, M.& Foth, M. (2012). A review of locative mediamobile and embodied spatial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 Computer Studies70(1)66- 71.
BeckU.&Lau,C. (2005). Second modernity as a research agend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s in the ‘meta-change’ of modern socie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 56(4)525–557.
BeckU.&BeckE.(2001).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London:Sage.
CramptonJ. W. (2009). Cartography: maps 2.0.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33(1)91-100.
Couldry,N.& Hepp,A.(2013). Conceptualizing Mediatization: Contexts, Traditions, Argume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23(3)191–202.
Couldry,N.(2004)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14(2). 115-132.
Collins-Kreiner,N.(2020). Hiking, Sense of Placeand Place Attach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The Israeli Case. Sustainability. 12(11):4548.
Collins-Kreiner,N.&Kliot, N.(2015). Particularism vs. Universalism in Hiking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56)132-137.
de Souza e SilvaA. (2013). Location-aware mobile technologies: Historical, social and spatial approaches.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1(1)116-121.
Frith, J. (2015). Smartphones as locative media.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0(4)511-511.
Frith, J.& Wilken, R. (2019). Social shaping of mobile geomedia services: An analysis of Yelp and Foursquare.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4(2)133-149.
Humphreys, L.& Liao, T. (2011). Mobile geotagging: Reexamining our interactions with urban spac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6(3)407-423.
HjorthL.& Pink, S. (2014). New visualities and the digital wayfarer: Reconceptualizing camera phone photography and locative media.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2(1)40-57.
Jansson,A.(2017). “Critical Communication Geography: SpaceRecognitionand the Dialectic of Mediatization”. In AdamsP.C.GlynnC.K.Jansson A.& Moores S.(Eds). Communications/Media/Geographies(pp.132-159). New York,NY:Routledge.
JacobsA.&Appleyard,D.(1987). Toward an urban design manifesto.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53(1)112-120.
Krotz, F. (2007). The meta-process of `mediatization’ as a conceptual fram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3(3)256-260.
Krotz, F. (2009). Mediatization: A Concept with which to grasp media and societal change.In Lundby K(Ed.)Mediatization: ConceptChangesConsequences(pp.21-40). New York,Peter Lang.
KyleG.Graefe,A.ManningR.& BaconJ.(2004). Effects of place attachment on users’ perceptions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a natural setti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4(2)213–225.
Saker, M. (2017). Foursquare and identity: Checking-in and presenting the self through location. New Media & Society19(6)934-949.
[作者简介]张杰系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侯少杰系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罗敏(通讯作者)系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媒介化加速视域下社交媒体新个体文化的建构与引导研究"(24YJA860024)、广州大学重点人才项目“内在对话视域下社交媒体时代自我传播的新进路研究”(RZ2022005)与“媒介化视域下平台下沉对城乡沟通模式的变革研究”(YJ202301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