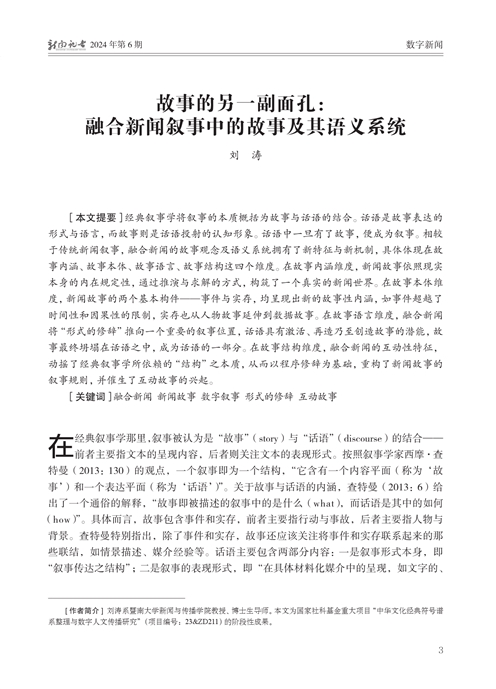故事的另一副面孔:融合新闻叙事中的故事及其语义系统
刘涛
[本文提要]经典叙事学将叙事的本质概括为故事与话语的结合。话语是故事表达的形式与语言,而故事则是话语投射的认知形象。话语中一旦有了故事,便成为叙事。相较于传统新闻叙事,融合新闻的故事观念及语义系统拥有了新特征与新机制,具体体现在故事内涵、故事本体、故事语言、故事结构这四个维度。在故事内涵维度,新闻故事依照现实本身的内在规定性,通过推演与求解的方式,构筑了一个真实的新闻世界。在故事本体维度,新闻故事的两个基本构件——事件与实存,均呈现出新的故事性内涵,如事件超越了时间性和因果性的限制,实存也从人物故事延伸到数据故事。在故事语言维度,融合新闻将“形式的修辞”推向一个重要的叙事位置,话语具有激活、再造乃至创造故事的潜能,故事最终坍塌在话语之中,成为话语的一部分。在故事结构维度,融合新闻的互动性特征,动摇了经典叙事学所依赖的“结构”之本质,从而以程序修辞为基础,重构了新闻故事的叙事规则,并催生了互动故事的兴起。
[关键词]融合新闻 新闻故事 数字叙事 形式的修辞 互动故事
在经典叙事学那里,叙事被认为是“故事”(story)与“话语”(discourse)的结合——前者主要指文本的呈现内容,后者则关注文本的表现形式。按照叙事学家西摩·查特曼(2013:130)的观点,一个叙事即为一个结构,“它含有一个内容平面(称为‘故事’)和一个表达平面(称为‘话语’)”。关于故事与话语的内涵,查特曼(2013:6)给出了一个通俗的解释,“故事即被描述的叙事中的是什么(what),而话语是其中的如何(how)”。具体而言,故事包含事件和实存,前者主要指行动与事故,后者主要指人物与背景。查特曼特别指出,除了事件和实存,故事还应该关注将事件和实存联系起来的那些联结,如情景描述、媒介经验等。话语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叙事形式本身,即“叙事传达之结构”;二是叙事的表现形式,即“在具体材料化媒介中的呈现,如文字的、电影的、芭蕾的、音乐的、哑剧的或其他的媒介”(查特曼,2013:8)。
尽管学界对叙事给出了不同的界定和阐述,但“叙事=故事+话语”之论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就叙事的内涵而言,“叙事学界公认的‘故事’和‘话语’的区分适用于不同媒介的叙事作品”(申丹,王丽亚,2010:20)。基于话语的表征作用,文本承载了相应的内容,并成为一种叙事文本。实际上,叙事学所强调的话语,本质上是一个文本形式范畴的概念,即一种有关故事的言说方式。因此,故事的形成与呈现,必然取决于一套能够“讲述”故事的话语形式。查特曼(2013:11)甚至给出了一个更简洁的表述:叙事乃是一种“有意义的结构”。进一步讲,叙事体现为一种表征,但并非所有的表征都是叙事,只有那些能够承载故事、唤起故事、言说故事的表征,才具备成为叙事之可能。正如玛丽-劳尔·瑞安(2014:7)所说:“叙事可以是故事与话语的结合,然而,正是其在心中唤起故事的能力,使得叙事话语同其他文本类型区别开来。”换言之,当一种表征最终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具有讲述故事的潜能时,其对应的便是叙事的概念。简言之,话语中一旦有了故事,便成为叙事。
就故事的观念与内涵而言,狭义的叙事即是“讲故事”。叙事无法脱离故事而存在,故事也因为叙事而成为故事。法国叙事学者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将故事视为叙事的生命和灵魂,认为故事乃是叙事的“果实”。正如热奈特(1990:9)所说:“叙事、叙述话语之所以成为叙事、叙述话语,是因为它讲述故事,不然就没有叙述性……还因为有人把它讲了出来,不然它本身就不是话语。从叙述性讲,叙事赖以生存的是与它讲述的故事之间的关系;从话语讲,它靠与它讲出来的叙述之间的关系维系生命。”
不难发现,叙事学将故事推向了叙事研究的核心位置——正是源自对故事的不同理解,叙事形成了不同的内涵与外延。那么,如何认识融合新闻的叙事观念?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立足数字叙事学的基本理念与方法,重返经典叙事学的核心命题——故事,尝试以“新闻故事”为考察对象,揭示融合新闻叙事区别于传统新闻叙事的数字性之本质。正如瑞安的著作《故事的变身》(Avatars of Story)之标题所揭示的那样,数字叙事的显著特征便是赋予了故事无限“变身”之可能。那么,相较于传统新闻叙事,融合新闻中的故事是如何“变身”的,又呈现出何种“模样”?基于这一基础性的问题意识,本文聚焦于融合新闻的基本特征及其物质属性,总体上沿着故事的内涵、故事的本体、故事的语言、故事的结构这一认识路径展开,以期勾勒融合新闻叙事中的故事观念以及故事生成的语义系统。
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一是回到叙事学的理论原点,探讨故事的内涵及形成机制,并在与文学故事比较的基础上,回答“何为新闻故事”这一命题;二是以“事件”与“实存”这两个基本的故事“构件”为研究对象,通过检视其在融合新闻中的新表征与新内涵,回答“新闻故事何以变身”这一命题;三是聚焦故事的语言问题,通过批判性地审视故事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回答“故事如何生成”这一命题;四是将目光延伸到故事的结构与规则维度,以融合新闻叙事的显著特征——互动性为考察对象,进一步探讨互动故事的兴起及其重构的故事观念。
一、从故事到新闻故事
经典叙事学中的故事,一方面在时序结构中形成,另一方面又在空间结构中发生。因此,时间和空间,构成了故事的两个基本存在向度,相应地也就形成了“故事-事件”和“故事-实存”两个理论命题——前者对应的是时间维度,后者则指向空间维度(查特曼,2013:81)。“故事-事件”意为故事在时间结构中的序列与过程,“故事-实存”意为故事在空间结构中的存在与关系。显然,事件与实存构成了故事的存在基础。而要进一步理解故事的生成语言,便不能不提及叙事中的话语问题。正因为话语的存在与作用,故事拥有了文本化的存在形式,并成为文本中的故事。
(一)故事:话语投射的认知形象
早在经典叙事学给出“叙事=故事+话语”这一理论模型时,实际上已经预设了故事与话语之间的二分结构,即故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在话语中“显现”,但并不受制于话语的“摆布”。查特曼在叙事学的经典著作《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中将故事与话语视为叙事结构形成的两个向度,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二分结构。
按照经典叙事学的一般理解,故事与话语属于不同范畴的叙事问题,二者结合为叙事,但依然存在区分、离析的可能。故事与话语的分离,可以从故事的跨媒介性维度加以理解,“若同一故事可由不同的媒介表达出来则可证明故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不随话语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申丹,王丽亚,2010:20)。因此,话语并不决定故事的本体,其更多地作用于叙事的形式维度。例如,记者通过专业调查,发现了现实中的事件或真相,而后诉诸一定的新闻文体以及叙述形式,将事件和真相转换为文本意义上的故事。由于故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话语主体上体现为新闻文体范畴的表达形式,即一种对故事的“编织”、“传导”或“输送”方式,而非对故事的“创造”方式。借用一句熟悉的广告语:话语并不直接生产故事,其不过是故事的“搬运工”而已。
作为叙事的两个基本构成模块,故事与话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经典叙事学中,故事主要体现为一种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而话语则是故事的表达形式或存在形态——话语是故事的“载体”,亦是故事的“居所”,其更多地发挥着表征、再现的叙事功能;故事则是话语的“果实”,其依赖于话语的表达,但并不完全受制于话语的束缚。在以小说、电影为代表的虚构性叙事文体中,话语拥有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亦具有较为灵活的呈现形式。所谓的故事,首先“停泊”在话语流经的“岸边”,其主体上表现为作者对世界的一种想象方式。正是在想象层面,话语拥有相对充分的“发挥”自由——当话语遵守一定的“语言”规则时,其便可以自由地建构故事,形成不同的故事世界。
当话语中流淌着故事时,话语便拥有了生命,文本也成为一种叙事性文本。因此,话语乃是故事的表现形式,而故事则是话语投射出的认知“形象”。在经典叙事学那里,故事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故事存在于话语之中,但话语并非故事的原生母体,因此并不参与故事的直接创造,其仅仅为故事提供了一种显现方式。相应地,话语不过是故事的形式,其功能便是对已经“存在”的故事进行组织和表达——话语的出场,并非实现了故事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将一种形态的故事,如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事件、作者想象中的虚构形象、潜藏于世界中的事实或规律等,转化为一种文本化的心理意象,以便于人们在文本维度加以识别、感知和理解。由此可见,故事是一种建立在话语表征基础上的感知形象。正如瑞安(2014:7)所说:“故事,就如同叙事话语,是一种表征,但又不像话语,它并非编码在物质符号里的表征。故事乃一个心理意象、一个认知建构,关涉到特定类型的实体,以及这些实体之间的联系。”
对于传统新闻叙事而言,故事往往先于话语而存在。尽管话语会影响故事的感知体验,但必须承认,这种影响仅仅停留在形式与修辞层面,无法动摇故事的内容及本质。这是因为,故事形成的要素和条件,往往存在于现实之中,而话语的作用机制,不过是将故事转化为一种可接触、可感知、可阐释的文本形式。概括而言,在传统新闻那里,话语之于故事的影响,仅仅发生在形式维度,而非作用于内容本身。尽管话语与故事的结合,形成了文本意义上的叙事,但在不同的叙事文体那里,二者之间的“结合”方式却呈现出不同的逻辑与语言,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叙事方式。例如,虚构性文本与纪实性文本不仅对话语提出了不同的语言规则和形式要求,而且在故事与现实的关系上也给出了不同的映射标准和方法,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故事观念。
(二)新闻故事:情节的可能性模式及其超越
为了理解新闻故事的内涵,首先需要回到叙事之中,探讨新闻故事有别于文学故事的独特内涵。故事的核心特质是情节性,难以想象没有情节的故事,也难以想象没有事件的情节。正因如此,“传统叙事在传达过程中必然要传达情节,即诸事件的轮廓”(斯科尔斯,费伦,凯洛,2015:10)。情节的形成,不仅依赖于时间上的行动与变化,而且依赖于空间上的主体与关系。正是在情节基础上,叙事的故事性成为一个显性的意义命题。
情节本质上涉及对事件的组织与安排,其目的是赋予故事一定的戏剧结构。当米克·巴尔(1995:12-19)将叙事界定为事件与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情节问题主体上指向故事深层的叙述语法。那么,事件究竟是依照何种原则与规律被组织、被安排的?这一问题则涉及情节生成的可能性模式。按照经典叙事学的基本假设,事件发展的方向、路径与原理,遵循的是一种偶然性原则。偶然性意为因果关系所依赖的解释原则,体现为可能性逻辑,如开头的事件是可能的,中间的事件是或然的,结尾的事件是必然的。相应地,“生产情节(至少是某些情节)就是削弱或窄化可能性的过程”(查特曼,2013:31-32)。显然,偶然性原则意味着事件发展存在多种可能的方向和路径,而事件之间的作用关系亦存在多种可能的勾连方式,每一种可能都会“导向”不同的后果,并形成不同的故事,这无疑赋予了创作者更为自由的发挥空间。
新闻叙事在表达层面也遵循可能性模式,如对事实或真相的可能原因进行推理。但不可否认,新闻叙事追求的是一种有限的可能,即通过验证与排除的原则,对诸多可能进行论证,最终在选择与否定中抵达唯一的可能。简言之,如果说文学叙事的可能性模式最终打开了无限可能,新闻叙事则是在对无限可能的验证与排除中最终抵达一种可能。尽管新闻叙事也遵循可能性模式,但其并未像文学叙事那样以想象为基础,完全滑向“路径依赖”,并进入一个不受束缚的“可能之网”。相反,新闻叙事在对可能性的选择与应变上,保持了极大的警惕和反思,其预设了一个唯一合法的可能路径,以此确立故事的“展开”方式。显然,面对可能的行动与方向,新闻叙事并不会不假思索地进入“可能空间”,而是依照事实逻辑进行判断和选择,以此进入唯一合法的事件结构。
作为情节的重要特征之一,“变化”揭示了故事形成的事件之本质。如果说文学故事中的“变化”,主要关注语篇与情节意义上的变化之“链条”问题,即“变”向何处,那么,新闻故事所关注的“变化”,则更多地转向了变化之“点位”问题,即缘何生“变”。由于文学叙事和新闻叙事具备不同的事件性内涵,二者形成了不同的故事观念——文学叙事中的事件及其携带的行动与变化之本质,旨在以合理性为基础,打开一个想象的世界,相应地,事件中的行动与变化,是想象的后果,是情节的表象,是故事的动人之处,更是悬念与冲突的动力之源;新闻事件中的行动与变化,主要是选择,是推演,是求解,其目的便是依照现实本身的内在规定性,在局部事实与整体事实之间建立一种合法的推演逻辑,以构筑真实的新闻世界。所谓新闻世界,意为由新闻叙事建构的认识世界,其合法性来源是客观世界,但本质上又体现为一个意义世界(王润泽,米湘,2024)。因此,每一种变化的推演,每一次行动的走向,都建构了局部的新闻事件,亦建构了局部的新闻事实。因此,如果说文学叙事中的故事世界是想象的、多元的,新闻世界则是现实的、确定的。如同游戏中的选择与闯关,只有当所有的可能性都能够沿着一种“正确”的路径前行时,局部事件才能由点连线、由线成面、由面织网,最终形成一个结构化的整体事件,进而完成从局部事实到整体事实的“拼图”。倘若新闻事件未能处理好叙事中的可能性问题,那么,以可能性为推演基础所形成的新闻世界,便难以达到调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目的。
显然,新闻叙事并不接受可能性的肆意发挥和自由延伸,其在可能性的“处理”方式上,主要依据的是现实性原则而非文学叙事的合理性原则。即便是当前备受关注的融合新闻形态——新闻游戏,也是通过一定的程序修辞机制,尝试在互动中抵达一种确定的事实结果。用户的每一次互动操作,都打开了一个可能的空间,但这种选择却受制于某种引导性的数字修辞机制,其目的是形成一种确定的认知图景。
二、事件与实存:从经典故事到数据故事
按照经典叙事学的观点,故事实际上包含了两部分内容:一是事件,二是实存。前者意为“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变”(巴尔,1995:12-13),其主要体现为一个时间范畴的叙事概念;后者意为在事件中“实实在在”存在的实体性对象,如人物和背景(查特曼,2013:82),其主要表现为一个空间范畴的叙事概念。查特曼(2013:98)对此给出了一个形象的解释:“只有在事件和实存同时出现之处,故事才会发生。不会有‘无实存的事件’。诚然,一个文本可以有实存而无事件(一幅肖像、一篇描写性散文),但没有人会把这叫作叙事。”
融合新闻的数字性与融合性特点,决定了故事的“事件”和“实存”——所言之“事”与存在之“物”,必然呈现出有别于传统新闻的独特属性。由于数字环境下的叙事话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新闻叙事所依赖的结构主义原则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以数字叙事学为理论基础的融合新闻叙事,不断冲击着“事件”的本质与“实存”的形态。因此,唯有重返叙事学的初始语境,重访故事形成的两个基本“构件”——“事件”与“实存”,深刻挖掘其在数字叙事语境下的“变身”之可能以及“化身”之内涵,才能真正把握融合新闻叙事的故事观念。
(一)时间与因果:事件的“变身”
叙事与事件密切相关。没有了事件,叙事之“事”便荡然无存,这也是叙事被定义为“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来再现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事件”(申丹,王丽亚,2010:2)的原因所在。事件在故事中具有决定性的存在意义,离开事件,故事也就无从谈起。热奈特(1990:31)认为故事的本质是事件,而事件则意味着一种序列和关系。由于经典叙事学主体上在时间范畴中讨论故事,因此,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的条件——关系和结构,主体上体现为一种时间维度的因果关系,即由“因”到“果”的变化之过程。而这里的“变化”,即是叙事学中情节的核心要义。爱德华·摩根·福斯特(2009:74)给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故事是按照时间逻辑排列的事件,而情节则主要指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基于对“因果关系”的发现与识别,事件被赋予了“来龙去脉”的深意,从而具有了“构筑”故事之可能。传统新闻中的事件,主要体现为人物、动机、行动、过程、结果的集合。对比而言,融合新闻叙事中的事件,又呈现出何种内涵与特质?
按照经典叙事学的故事观念,事件意味着一个“展开”的行动与关系——“展开”的方向是时间,“展开”的语言是因果,“展开”的表征是序列。显然,一种叙述话语被称为事件的必要条件,便是其具有行动意义上的过程性、动态性和情节性。由此可见,事件本质上并非空间性的,而是时间性的,其揭示了故事的时间之本质。一则说明性的新闻消息,之所以很难称为故事,是因为其并未提供一个基于时间逻辑的新闻事件。正是在时间结构中,事物不仅具有开始、发展、转折、结果的内涵,而且拥有过程、序列、脉络、轨迹的深意。由于时间上升为事件表征与形成的本体属性,因此其赋予了事件一种根本性的界定方式和认知维度,这也是经典叙事通常被称为时间叙事的原因所在(刘涛,薛雅心,2023)。为什么一幅图像很难讲述一个故事?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图像所捕捉的是世界的瞬间——作为现实断片的瞬间,压缩了时间的存在方式,亦凝缩了事件的展开结构。人们很难在瞬间中识别出某种戏剧性的转变或过程,故而无法形成一种事件性的观念或意识。只有将图像置于一个互文结构中,赋予其时间性内涵,并在时间维度上揭示某种因果关联或演进变化时,图像才会上升到事件的维度,成为图像事件(image event)。由此可见,倘若一种叙述话语未能揭示时间维度的变化,那便难以称之为事件。
在传统新闻叙事中,事件延续了经典叙事的一般属性和内涵,即事件性本质上意味着以时间性为基础的行动与变化。然而,有别于经典叙事中的事件形成逻辑,新闻事件存在一个明确的“行动”逻辑和“变化”方向。具体而言,如果说一般事件的“变化”主要体现为戏剧性基础上的情节问题,新闻事件则对“变化”的逻辑和方向提出了严苛的规定——是否沿着事实推演的方向展开,是否在论证结构上建立了一种因果逻辑,是否打开了一幅不为人知的事实图景?巴尔(1995:20)立足“素材”这一分析工具,提出“叙述圈”的概念,用以说明事件之间的作用关系和结构。叙述圈具有三种叙事内涵:一是可能性,即事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二是事件性,即事件的实现过程;三是结果性,即事件发展的结果。相比较而言,文学故事的结果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部分小说为了追求特定的美学风格,在叙事的关键情节线上戛然而止,形成一个意味深长的“留白”,以便于读者进行自由想象并加以“填充”。然而,新闻叙事的目的则是在信息维度上消除公众认知的不确定性。因此,新闻事件拒绝模糊性结果,也拒绝开放性意义,亦拒绝想象性留白,其追求的是一种确定的事实结果,否则便难以被称为新闻事件。诚然,现实具有不同的存在面向,事实也仅仅是对现实的一种抵达方式或观察结果。所谓的确定性,并非强调一种整体的真实性,而是强调记者所“占有”的事实之确定性。在新闻叙事中,倘若一个事件缺乏事实层面的信息价值,或者说在事实与真相问题上隔靴搔痒,那其便不具备“讲故事”的前提和条件。
因此,唯有回到“事实”这一根本性的认识视角,才能真正揭示融合新闻叙事中的事件之本质,进而理解其中的故事之观念。根据经典叙事的基本原理,事件的本质是时间性和因果性。这两大特性铺设了传统新闻中故事形成的叙事规则,也决定了新闻故事的结构和语言,甚至可以说,结构乃是时间性和因果性综合“建模”的结果。然而,融合新闻则在时间、因果问题上给出了独特的解释,甚至超越了原初的理论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事件的内涵与外延。
一方面,在时间性问题上,融合新闻摆脱了时间的根本性束缚,不仅赋予时间线更为自由的形式与结构,而且将事件的生成语言从时间维度延伸到空间维度,使得空间化的故事表征成为现实。按照经典叙事学的观点,“一个叙事均由一个状况开始,然后根据叙事因果关系的模式引起一系列的变化;最后,产生一个新的状况,给该叙事一个结局”(波德维尔,汤普森,2015:90)。显然,事件发生在时间设定的坐标结构中,亦受制于时间逻辑的限定。正如巴尔(1995:5)所说:“事件,不论如何微不足道,实际上总要花费时间。”有别于其他的认知语言,时间性铺设了一种基础性的意义图式。在康德的图式论中,十二大范畴都服从于时间的规则,如时间序列、时间内容、时间次序、时间总和等,并在本质上体现为时间的规定(康德,2004:143),如因果性强调的是时间上的“相继”,协同性强调的是时间上的“并存”……正是在时间结构中,事件被视为一种序列、一个过程、一段经历,并拥有了“发展”、“演进”的方向与意涵。按照查特曼(2013:17)的观点,“叙事是交流,这就很容易被想象为从左到右、从读者到受众的箭头运动”。不难发现,经典叙事意义上的故事,根本上体现为一种基于时间图式的时间性故事——正是在时间提供的线性逻辑中,事件得以发生,因果得以识别,故事得以形成。离开时间所发挥的基础性的组织功能与图式作用,故事赖以存在的事件、因果、情节都将不复存在。热奈特(1990:13-106)将叙事中的时间区分为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时序(order)、时距(duration)和频率(frequency)三个维度加以考察。然而,融合新闻的数据性、互动性、融合性等特征,改写了时序、时距和频率的内涵,并赋予新闻叙事无数的“生成之线”,由此制造了一幅前所未有的时间图式,即一种嵌套的、网络的、拓扑的、面向未来的时间图式(刘涛,薛雅心,2023)。当叙事不再一味地依附于时间逻辑,甚至可以摆脱时间逻辑而存在时,融合新闻便从根本上颠覆了经典叙事中事件形成的线性逻辑,从而赋予故事一种多元的“变身”。
另一方面,在因果性问题上,融合新闻的事实呈现与真相挖掘,越来越多地转向一种数据化的论证结构,由此改写了传统新闻叙事的论证语言,并形成以数据论证为基础的新闻事件。任何符号系统都包含了一个关系之网,关系是事物存在的根本属性(Capra,1996:37)。按照经典叙事学的观点,事件以序列的方式呈现——“它们的联系是从原因到结果,结果又导致另一个结果,直到最终结果”(查特曼,2013:31)。因此,在传统新闻的叙事观念中,事实主要依赖于对因果关系的识别和认知——正因为揭示了“因果”,叙事才有了“发现”。倘若一个事件未能揭示一种因果联系,那便意味着叙事的“结果”是苍白的,是徒劳的,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事件便难以称之为新闻故事。作为一种认识范畴的逻辑结构,因果性揭示了一种极为普遍的认识关系,即一种由“因”及“果”的认识逻辑。早在牛顿时期,因果性便被赋予了科学的本质——正是在寻找“因”的过程中,现代科学随之诞生。以数据新闻为代表的融合新闻则将相关关系推向了一个重要的认识位置,从而形成了以相关关系为基础的新闻论证体系。区别于传统新闻的论证“语言”,数据新闻提供了一种基于社会科学的论证体系(曾庆香,陆佳怡,吴晓虹,2017)。必须承认,相关不等于因果,前者关注“是什么”,后者关注“为什么”(舍恩伯格,库克耶,2013:83);前者属于非决定论范畴,后者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决定论思想。
相比较而言,传统新闻的论证基础是因果性,融合新闻则将其延伸到了相关性与类比性,尤其是在数据的相关与类比基础上发现新闻真相,讲述新闻故事。换言之,并非所有的相关和类比都意味着“讲故事”,倘若一种叙述在相关或类比基础上发现了难以识别的关系,且这种关系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空间,如揭示了鲜为人知的事实与真相,那么,这一叙述便意味着一种戏剧性的意义结构。正是在相关或类比结构中,原本陌生的数据走到了一起,并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叙述语境——当数据从原始的关系结构中挣脱出来,进入一种对比性的关系结构时,其便不再偏居一隅,也不再仅仅意味着一个纯粹的数字,而是向彼此“敞开”,具有了再阐释、再解读的可能,从而具有了重新发现并认识现实之可能。例如,美国的移民和犯罪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犯罪率高的原因归于移民问题。2018年,美国非营利新闻组织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roject)联合纽约时报推出的数据新闻《犯罪移民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Criminal Immigrant),通过追踪美国200个城市在40年间的犯罪情况统计,以可视化的方式直观地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即城市犯罪和移民人口之间并无相关性,从而有力地回击了特朗普对移民问题的不实指责。该数据新闻以相关性为思维基础,发现了躲在暗处的事实真相,从而讲述了一个建立在数据论证基础上的新闻故事。显然,经由可视化的组织、编码与展示,原本散落一地的数据被勾连到一个全新的数据语境之中,这使得数据之间的推演和比较成为可能。正是在推演性的论证结构中,数据具有了“编辑”现实的可能,亦具有了“言说”故事的潜能。由此可见,如果说传统新闻中的事件,主要体现为一种因果维度的行动与过程,融合新闻的事件则延伸到了相关性,使得相关意义上的故事构建成为可能。
概括而言,融合新闻的互动性、数据性、融合性等特征,赋予了新闻叙事一种全新的事件性内涵:由于新闻事件并非想象的事件,而是一种真实发生的事件,因此,事件形成的必要条件——行动与变化,必然体现为一种向事实与真相“靠拢”的推演与论证过程。换言之,并非所有的融合新闻都是在“讲故事”,只有那些诉诸一定的论证过程,并在事实呈现上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结构”的新闻叙事,才可谓是“讲故事”。
(二)数据与符号:实存的“化身”
故事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故事,对应广义上的叙事概念。在广义层面,叙事实际上被视为一个隐喻意义上的概念——任何承载并传递意义的形式,都可谓是一种叙事。当叙事被泛化为一种意义行为时,原本被经典叙事理论排除在外的诗歌、抽象艺术等,也因其具有文本特征和意义属性而被归入叙事的范畴。相应地,故事不过是“意义”或“叙事”的代名词。然而,这一观念遭到了一定的质疑,认为其泛化了叙事的外延,将叙事学拱手让渡给了符号学的意义研究,致使叙事失去了自己的学科“领地”。因此,广义的故事愈发趋近于叙事的概念,其超越了具体的事件与行动范畴,而意味着一种有关意义的文本化组织形式。正因如此,故事离开了表象的范畴,并进入结构与形式维度。相应地,故事被定义为“从叙述信息中独立出来的结构”(胡亚敏,2004:118)。
狭义的故事,主要指向人物与事件的范畴。常见的故事形式是由人物的动机与行动驱动的故事,即人物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查特曼将人物和背景视为叙事之“实存”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经典叙事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其更多地在文本与表征层面讨论叙事问题。因此,叙事并未“升维”为一个普遍的意义组织问题,而是指向一种具有实存基础的故事表达活动。相应地,叙事的基础是讲故事,而故事则被简单地视为“事”与“人”的结合。在经典叙事学给出的“故事=事件+实存”这一较为普遍的理论框架中,如果说“事件”强调的是故事中“事”的属性,“实存”则主要指向故事中“人”与“物”的存在。概括而言,一个叙述中有了“人”,有了“物”,又有了能将“人”与“物”组织起来的“事”,这一叙述便进入叙事范畴,成为一个故事。必须承认,尽管结构主义将人物推向了叙事的核心位置,但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人物是情节的产物,其地位是‘功能性’的”(查特曼,2013:96)。换言之,人物只是叙事的手段,而非叙事的目的——故事中的人物,往往作为情节中的参与者或行动元,受制于情节的摆布,服从于情节的安排,在叙事中仅仅发挥着功能性的作用。后来的叙事学逐渐转向开放的人物理论与观念,认为人物并非情节的产物,亦非情节的注脚;相反,人物是事件的主体,是动机的载体,是故事的灵魂,其不仅主导了叙事的情节内容,而且主导了故事的内涵与本质——一个没有人物的事件,往往难以引发深刻的情感共鸣,亦难以形成有效的叙述认同。
如果说传统新闻叙事中的实存主要体现为人物,新闻故事也更多地还原为人物故事,那么,融合新闻的数据化特征则将新闻故事的实存对象延伸到数据维度,即除了一般的人物故事,新闻故事的发生主体还体现为数据。其中,数据新闻更是将数据视为一种基本的故事构成要素。相应地,数据故事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的故事形态。传统新闻为了增加情节的连贯性与完整度,通常基于因果关系所铺设的认识逻辑来组织和编排新闻要素。同时,为了提升新闻故事的美学效果,并打开可能的消费空间,叙述者往往采用文学化的描述手法、戏剧化的表现风格、奇观化的展示方式等。这种故事化的新闻讲述方式在非虚构性写作中较为普遍:新闻故事一般聚焦于事件中的微观个体,通过对冲突和悬念的精心设置与布局,将微观命运与时代主题相勾连,打通主题呈现的情感认知向度,从而在个体命运上编织一定的社会价值。尽管传统新闻也使用数据,并在数据基础上推演主题内涵,但故事的核心形态依然是以事件为基础的人物故事,数据的“出场”往往会影响故事呈现的连续性与可读性(刘涛,2019)。融合新闻则总体上建立在数据结构之上,数据成为事实挖掘和故事呈现的“主角”,其背后隐匿着人们难以察觉的事实真相。因此,新闻故事的生成与识别,不再依托于单一的人物故事,而是越来越多地转向数据驱动的事件及事实真相。相应地,新闻故事所形成的论证逻辑,主要体现为数据意义上的类比、归纳、演绎等实证方式。在此过程中,时间之于故事进程的主导逻辑被弱化了——“数据云图”中的时间,主要发挥着揭示数据关系、发现数据变化、呈现数据冲突的“节点”功能,离开数据所揭示的“关系”、“变化”和“冲突”,时间的存在向度便不复存在,或至少难以形成相应的时间意识。
当数据主导了实存的主体内容时,融合新闻则通过重构实存的内涵,进一步重构了新闻故事的观念,即从传统新闻所关注的“人物实存”,逐渐延伸到“数据实存”,由此形成了一种以数据为叙事主体的故事形态——数据故事。斯大林曾言:“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只是个统计数据”(转引自彼得斯,2017:388)。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数据都意味着一种故事化的数据实存,只有那些进入特定语境,并在符号学意义上具有指示性(indexicality)功能的数据形式,才具有“言说”故事的潜能。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人民日报推出融合新闻《2018致1978:四十年,见字如面》。该作品站在2018年的时间节点,以“书信”的形式向1978年讲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波澜壮阔的光辉岁月。书信选择了一系列极具时代印迹的数据形式——关键词,如“实”、“女排”、“WTO”、“神舟”、“速”、“奥运”、“博”、“大阅兵”、“脱贫”、“新时代”等,并以此为故事线索,串连起四十年来的历史往事。每一个关键词都对应着一个特定的历史瞬间,并诉说着一段难忘的历史故事——“实”的背后,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大幕由此揭开;“女排”的背后,是1981至1986年中国女排五次蝉联世界冠军,以及四十年间中国运动员共获得3314项世界冠军;“速”的背后,是一系列值得铭记的历史瞬间,如2006年7月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17年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到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里程总量三分之二……显然,这里的数据形式,已然超越了传统新闻中的数据范畴,而上升为一种意味深长的符号形式,并最终指向一个个鲜活的历史故事。不难发现,尽管数据新闻并未直接讲述故事,但数据主导了叙事中实存的核心内容,其更像是一个有待展开的指示符号,凝缩了事件,凝缩了所指——在数据的褶皱里,藏着一个个有待被挖掘、被讲述的故事。
三、故事的生成语言:“形式的修辞”与故事的重新发现
话语之于故事的影响方式,主要体现为文体意义上的形式与修辞问题。必须承认,叙事存在一个基础性的修辞向度,无论是宏观上的“讲故事”,或是微观上的“如何讲”,在一定程度上都绕不开修辞的作用机制。实际上,巴尔在论及故事问题时,早已肯定了修辞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认为叙事话语并非素材的简易排列,而是基于修辞语言的素材组织与编排。正如巴尔(1995:6)所说:“除已在素材层次加以描述的行为者、事、地点和时间之间的必要的关系外,其他关系(符号的、讽喻的,等等)也可能在一系列成分间存在。”
在新闻叙事实践中,故事更多地作为一种修辞资源出场。相应地,“讲故事”则意味着一种较为普遍的修辞手段,其目的便是以故事为“媒”,抵达表象的“彼岸”,进入更大的主题世界。新闻叙事的常见思路便是以“讲故事”的方式“讲道理”,达到启人悟道的叙事目的。必须承认,当我们关注故事的“功能”维度时,实际上便是在修辞意义上讨论故事问题——故事如同一种被征用的修辞资源,服务于整体性的谋篇布局。例如,“华尔街日报文体”产生的叙事背景主要是将“故事”引入主题性新闻的“讲述”之中,从而以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实现“硬新闻”在故事维度的“软着陆”。这里的故事发挥着修辞意义上的双重功能:一是“媒介”功能,即以故事为“桥梁”,铺设一条服务于主题建构的故事化认知“管道”;二是论证功能,即以微观故事和个体命运为观照视角,为新闻主题的形成,提供相应的“佐证”案例和故事“载体”。例如,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第一财经于2018年推出的短视频系列报道《40年40人》,通过讲述40位财经人物的故事,串起改革开放40年来的风雨历程,从而以人物故事为微观切口,讲述“中国奇迹”这一宏大主题。显然,故事既是新闻叙事的主体内容,又是主题表达的修辞手段,这使得故事维度的主题识别与发掘成为可能。必须承认,这里的故事已然超越了文本表意的内容维度,而上升为一种总体性的“修辞语言”,铺设了文本叙述的基本形态,亦设定了文本叙事的基本结构。
故事具有不同的“存在”形态,亦存在不同的“言说”方式,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接受体验。当文本携带着一定的叙事目的,开始思考故事的讲述方式,即“如何讲”的问题时,便已经进入了文本叙事的修辞维度。正如在蒙太奇规则所设定的“语言”世界中,不同的镜头组接方式传递了不同的意义逻辑,亦创设了不同的接收体验。叙事语言存在一个深刻的修辞认识向度,无论是故事形态层面的话语问题,抑或是文体表达维度的话语问题,都涉及修辞意义上的语言艺术。这意味着文本叙述中的“现实”,实际上是修辞建构的产物——无论是语义规则的策略性使用,或是语言符号的策略性编码,抑或是文体美学的策略性书写,本质上都体现为一种面向“形式”的修辞,其目的是在形式修辞的基础上打开故事的世界。
必须承认,传统新闻受制于时间逻辑的根本性束缚,加之新闻职业理念和伦理规范的系统性限定,因此,新闻叙事主要强调以客观、公正、理性的方式讲述新闻故事,话语所能“发挥”的空间较为有限,这无疑束缚了形式的修辞想象力。例如,电影叙事中的蒙太奇,具有更为自由的组接可能,而电视新闻则依附于时间叙事的主体框架,所谓的蒙太奇语言,也仅仅体现为按照时间逻辑对事件发展的过程和脉络加以呈现。尽管修辞的作用不容小觑,但其并未改写故事的“真容”,亦未动摇故事的“根基”。在新闻事实的“肉身”里,话语不仅受制于新闻伦理的“牵引”,而且受制于新闻事实的“摆布”,这使得新闻叙事中的戏剧性大打折扣。不同的话语形式,形成的依旧是同一故事的不同“变身”——万变不离其宗,故事内容层面的人物、事件、过程等核心要素依然独立于话语而存在。
相反,融合新闻的数据化、图像化、情感化、游戏化、互动化等特征,从根本上释放了形式的想象力,并将形式的修辞问题推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叙事位置。相较于传统新闻叙事,融合新闻叙事拥有更为自由的叙事语言,并以形式的修辞为基础,弥合了经典叙事学中故事与话语之间的距离。按照经典叙事的基本观点,“故事与话语的区分是以二元论为基础的”(申丹,王亚丽,2010:31),尽管也存在一元论的叙事观点,但基于方法论的考虑,经典叙事学主体上还是将故事与话语区别“对待”,认为故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故事与话语属于不同范畴的叙事命题,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区隔与界限。如果说经典叙事中的话语,依旧属于形式范畴,其更多地体现为故事的表征语言,即话语的功能是对已然存在的故事加以再现,而非对故事的直接创造,那么,融合新闻叙事则将故事本身带入话语维度,赋予了故事一种基础性的话语生成模式,即话语的功能不仅仅是对故事的再现,更是对故事的替代性生成。换言之,融合新闻叙事中的故事与话语,并非简单的内容之于形式的决定关系,亦非纯粹的形式之于内容的反映关系;相反,新闻故事拥有根本性的形式基础——故事不再是独立于话语之外的意义实体,而是依赖于话语的形式而存在的,并随着话语的变化而形成不同的故事。因此,融合新闻中的故事,转向了对话语的根本性依赖,并在话语维度上重构了一个新的现实。概括而言,如果说传统新闻叙事中的故事独立于话语而存在,且话语的形式与语言同样依附于故事的内在规定性,那么,融合新闻中的故事则不仅依赖于话语,而且存在于话语之中——故事因话语而存在,并在话语维度上被识别、被发现、被建构。
话语之所以具有激活、再造乃至创造故事的潜能,是因为融合新闻拓展了话语的修辞潜力。如果说传统新闻叙事中话语的“发挥”空间较为有限,融合新闻则以形式的修辞为基础,拓展了话语的语言体系,由此释放了故事的修辞想象力,这使得修辞维度的故事构建成为现实。正是在形式的修辞根基上,故事的大厦耸入云霄。因此,不同的话语形式,赋予了故事不同的生成语言,由此再造了不同的新闻故事。例如,数据新闻的可视化过程本质上意味着一种视觉修辞实践(刘涛,2016)。可视化意味着将数据关系转化为一种图像关系,即以图像化的方式来“展示”数据背后的故事。然而,不同的可视化方式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的修辞“方案”,相应地也就在话语维度形成了不同的事实“图景”。倘若一种“图景”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或真相,或者打开了一个未曾触及的情感认知空间,抑或复盘了一个已然逝去的新闻事件,那么,这一“图景”便具备了“讲故事”的潜能。为了呈现2003至2011年间伊拉克战争的死亡情况,南华早报于2011年制作了数据新闻《伊拉克残忍的死亡数字》(Iraq's Bloody Toll)。在具体的视觉修辞策略上,该新闻一改常规的可视化“语言”形式,将传统的坐标进行“翻转”处理,以红色且倒置的柱状图表现美国联盟军和平民的死亡人数,以此制造了一种“流血”的符号意象(图1 图1见本期第16页)。当用户进入新闻界面时,大片的红色便映入眼帘,仿佛鲜血在汩汩流淌。显然,通过形式的修辞,该数据新闻重构了一种新的“现实”,由此激发了公众压抑已久的悲痛情绪。正是通过对视觉要素的修辞处理以及对视觉意象的巧妙挪用,数据新闻《伊拉克残忍的死亡数字》以数据为基础,直观而形象地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从而在情感维度上打开了一幅反思战争合法性的可视化“图景”。可见,正是通过形式的修辞,话语不仅发现并照亮了那些躲在暗处的新闻故事,而且再造了一个全新的新闻故事。
概括而言,相较于传统的叙事方式,融合新闻借助可视化、互动化、智能化技术,赋予故事一种全新的生成语言和理解方式。这种发生在话语维度的“形式的修辞”,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基础性的叙事向度加以概括。一方面,从时间维度来看,融合新闻不再一味地依赖时间维度上的因果逻辑,而是将时间序列视为一种整体性的结构图式,并沿着数据逻辑和互动逻辑重构故事的生成方式。具体而言,其一,融合新闻能够在数据的演进、类比、冲突中发现故事,从而超越了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经典叙事模式,并形成了一种以数据为基础的论证性故事;其二,融合新闻的互动性特点将用户从创作者精心编织的线性时间序列中解脱出来,并赋予其操控时间、改变序列的潜能,由此形成了一种以互动为基础的参与性故事。另一方面,从空间维度来看,融合新闻叙事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物理内涵和场景属性,将空间上升为一种叙事变量,在现实与虚拟、经验与想象、观看与体验、身体与精神之间打开了一个有待“填充”的故事世界(刘涛,黄婷,2023)。当空间上升为一种叙事变量时,新闻叙事的时间图式逐渐延伸到了空间图式,并形成了一种以空间性为生成规则的新闻故事形态。
四、故事结构及其“变奏”:互动故事的兴起
经典叙事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因此,结构问题被推向叙事研究的中心位置。甚至可以说,叙事学主体上是围绕结构问题衍生出来的一套知识话语。相应地,叙事中的故事,亦存在一个来自结构的认识向度,即故事具有一个可识别、可分析的结构。按照结构主义观点,结构意为“关于世界之表达层面的符号学形式”(格雷马斯,2011:43)。当结构上升为叙事学的核心命题时,故事的语言与形式,存在一个普遍而深刻的结构认识向度。甚至可以说,故事呈现出何种语言与形式,不过是结构的微妙注脚。正因如此,查特曼(2013:11)给出了一个简洁的论断:叙事是一种“有意义的结构”。按照结构主义的基本假设,结构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意义图式。正因为结构的存在,文本拥有了一种可以进行结构化分析的语义模型。换言之,结构所发挥的功能,便是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一种框架性的脚本和图纸,亦为人物与事件在故事中的“相遇”提供了基本的游戏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结构意味着一种意义生成的装置与程序,其不仅决定了故事的形式,而且决定了故事的语言。倘若失去了结构这一灵魂性的骨骼,血肉将无所依附,故事将难以寄托,文本也就失去了表征的形式。
如何理解融合新闻叙事的结构及其深层的故事观念?这一问题需要回到数字媒介的叙事可供性层面寻找答案。由于媒介属性深刻地嵌入叙事维度,数字叙事最终体现为一种以数字媒介的媒介性为基础的中介化故事(mediatized stories)(Lundby,2008)。综观数字媒介的诸多技术属性,“互动性是最能区分新旧媒介的属性”(瑞安,2014:95),其作为新媒体的核心特征之一,直接影响着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的形成(van Dijk,2006:6)。互动与叙事的“相遇”,引发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叙事后果——叙事学逐渐从原始的“舒适区”中走出来,开始面对接受者在叙事活动中的“输入”行为,并深入思考数字媒介语境下的“再出发”问题。
唯有深入思考互动性之于叙事性的作用方式,才能进一步揭示融合新闻叙事对于传统新闻叙事的“超越”方式及其打开的故事观念。实际上,互动性之于新闻叙事的影响,是深刻的,是变革性的,亦是颠覆性的——互动技术不仅以结构为“操作”对象,重构了新闻文本的形式、语言与结构,而且借助程序修辞(procedural rhetoric)重构了新闻表达的叙事规则,还通过对情景与环境的数字化配置,改写了新闻与用户的“相遇”方式。
当互动超越了叙事语言维度,而上升到叙事规则维度时,叙事研究便开始转向一种新兴的数字叙事形式——互动叙事,与之相关的故事形态——互动故事亦随之诞生。互动叙事存在一个漫长的探索和发展过程。早期互动电影的情节推进模式,便蕴含着互动叙事的最初构想。作为一种探索性的艺术实验,互动电影最早可追溯到1967年的影片《自动电影:一个男人与他的房子》。在展映之前,场馆内的每个座位上都安装了红、绿两色按钮。在影片放映过程中,当剧情推进到特定节点时,屏幕下方便会出现按钮提示观众参与投票以决定后续的剧情走向,影片将根据票数结果进入相应的支线情节。在这一叙事形式中,互动理念主要体现为一种选择性,互动的结果便是将受众推向了游戏玩家的角色位置。这种将情节的决策权让渡给受众的叙事方式,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以观众意志为基础,并随着观众意志变化而实现情节同步转移的另类“蒙太奇”(Perron,2003:237-258)。由于观众的个体偏好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叙事结构,因此,互动性逐渐上升为一种叙事要素及结构方式,奠定了互动电影叙事的理论基础。数字媒介技术赋予了互动叙事一种全新的表达形式。数字叙事中的互动,不仅成为情节设计的创新理念,而且实现了不同媒介形式之间的融合。换言之,互动消解了媒介形态之间的边界,使得不同媒介在互动意义上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融合趋势。例如,随着全动态影像游戏(full motion video game)的崛起,“电影的游戏化”和“游戏的电影化”趋向融合。《底特律:变人》、《夜班》、《暴雨》、《隐形守护者》、《她的故事》、《地堡》、《超凡双生》等交互式电影游戏通过整合电影的视觉质感和游戏的互动优势,正式宣告电影与游戏的“媒介融合”已成事实。
如果说叙事是对文本意义的一种编排和组织,互动叙事则意味着意义组织是以互动为基础,并通过互动的方式完成的——互动既是人机会话的基本配置,也是故事形成的驱动力量,亦是用户参与的常见形式。根据用户对文本的干预程度和方式,常见的互动形式包括反应性互动、选择性互动与生产性互动(Ryan,2001:205),其对应的互动“操作”分别为界面响应、路径选择与角色扮演。不同的互动形式铺设了不同的叙事规则,并限定了故事与话语之间不同的“结合”方式。在此过程中,结构亦呈现出不同的“变奏”方式,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互动故事。
首先,反应性互动主要体现为界面响应,即用户对设定好的内容进行感知与反馈,如点击、滑屏、缩放、输入信息等操作,以此推进叙事内容的呈现。反应性互动并不会影响新闻的叙事内容,但可以改变信息的呈现方式:一方面,用户借助一定的界面操作,改变内容的呈现方式。反应性互动在数据新闻中的应用较为普遍,如不同的选项对应的是不同的可视化方式,从而赋予数据不同的表征“形式”,最终形成不同的数据故事。另一方面,互动行为的发生,使得时间线呈现出不同的“变身”,原本由生产者所支配的叙事进程被迫中断,用户则可以自主地控制故事的“展开”节奏,并获得多元化的故事体验。
其次,选择性互动主要体现为路径选择,即互动叙事预设了不同的行动路径,由此生成不同的故事情节。这意味着新闻叙事实际上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故事之网,其中嵌入了诸多可以自由“组合”的事件,所有的事件最终按照“树”的方式进行拆解,亦根据“树”的结构进行组织。例如,“二叉树”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意味着一种选择性的条件设置,不同的选择往往“导向”不同的故事脉络,从而形成了一种以“路径依赖”为基本特征的新闻故事。当前,融合新闻的选择性互动叙事,并不满足于文本界面维度的“路径依赖”,而是延伸到现实空间的数字实践维度,形成了一种以路径选择为基础的场景叙事系统。例如,AR新闻的现实“增强”方式之一便是增强位置叙事——其根据用户在现实空间中的位置信息,呈现出相应的AR景观,并引导用户在现实空间中进行游历和探寻,进而触发不同的事件节点,最终“拼接”出一个开放的故事。
最后,生产性互动是一种参与过程更为深入、更为彻底的互动形式,其主要表现为一种游戏化的角色扮演叙事,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一种以“自我”为第一视点的个性化故事。作为生产性互动的典型形式,新闻游戏将用户直接带入故事空间,使其以化身的方式进行游戏操作,遍历不同的可能,构建不同的关系,整合不同的行动,最终触发不同的故事结局。当游戏规则的设计遵循一定的事实基础或科学模型时,新闻游戏中的故事便发挥着现实认知的功能,即打开事实的不同“断面”及其可能存在的或然状态,进而抵达现实“褶皱”里的多元世界。在游戏过程中,用户的参与时间与故事时间始终呈现出“进行时”的状态,这意味着用户所经历并占有的故事,乃是一种实时“提取”的故事,而非经典叙事中基于阅读而“加工”或“建构”的故事。2010年,在海地地震10个月之后,加拿大媒体基金、贝尔新闻媒体基金、加拿大教育电视台(TVO)为提高公众的灾后生存能力,联合推出了一款新闻游戏《海地大地震背后》(Inside the Haiti Earthquake)。在该新闻游戏中,时间不再是连贯的存在,而是断裂的、碎片化的——用户可以在时间的“游戏”中自由跳转,行走于不同的情节之间,一方面了解海地地震的相关背景和事实,另一方面在游戏中获取一定的灾难应急知识。该新闻游戏为用户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角色选择,即救援者、幸存者和记者。每一种角色都会面临不同的困境,经历不同的情节,触发不同的结局,从而形成不同的新闻故事。
在互动性铺设的新闻叙事系统中,用户获得了更大的选择权和自由度,新闻故事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参与性的互动故事——每一种参与方式和互动行为,都是对结构的一次“进犯”,这势必引发结构的“变奏”。当结构拥有了更为灵活的“伸展”可能时,传统新闻叙事所依赖的时间逻辑和因果链条便随着结构的“变奏”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不仅改写了新闻故事的生成方式,而且重构了新闻故事的内涵与观念:一方面,每一次互动,必然意味着对时间连续性的一种暂停、隔断与重组。相应地,用户不仅仅是故事的聆听者,还是故事的讲述者。在从“聆听”到“讲述”的转变中,新闻故事逐渐超越了传统新闻中较为普遍的故事观念,即将故事视为一种手段、一种工具、一种修辞,其目的是以故事为认知“媒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道理,如“华尔街日报”文体中的人物与故事,不过是为了实现“硬主题”的“软着陆”而已。相反,融合新闻中的故事,除了具有言说“道理”、揭示“主题”的一般功能,还具有本体性的认识功能——由于用户进入故事之中,故事并非道理的绝对载体,而是作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新闻的全部,因此具有积极的新闻价值。另一方面,叙事赖以存在的因果链条,亦不再局限于从条件到结果的发生过程,而是体现为以互动为发生机制的从起点到终点的遍历过程。相应地,新闻故事的内涵,便摆脱了因果逻辑的绝对束缚,而以参数和变量为设置条件,最终“输出”不同的故事。杭州文广集团于2021年推出的H5新闻《地下党恋人,迟到了38年的“遇见”》,借助沉浸式的互动剧情讲述了毛仲倩与张秀文两位中共地下党人相识、相知的动人故事。用户能够通过点按书信、破译密码等界面互动操作,深度参与到两位中共党员的奋斗历程之中,并见证他们的每一次人生抉择。显然,每一种“输入”方式都是对叙事参数的一次个性化设置或调整,从而打开不同的情节脉络和推进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新闻故事。
必须承认,互动性赋予了用户一定的参与空间,新闻故事由此呈现出一种“双向交流”的生成结构。但是,基于互动技术的新闻叙事仍然受到计算机程序修辞的影响和限定,不同的触发方式所抵达的故事世界依然存在一定的有限性,即用户的选择必然体现为一种“有限的自由”。尽管用户拥有一定的自主探索空间,但在程序修辞的深层作用下,依然徘徊于主动与被动的缝隙之中。
概括而言,经典叙事学给出了一个经典的理论模型——“叙事=故事+话语”。话语是故事的“载体”或“居所”,属于叙事形式层面的问题;故事则是话语投射的认知形象,属于叙事内容层面的问题。话语中一旦有了故事,便成为叙事。如果说话语是一条河流,故事则是其中顺流而下的一叶小舟——正是在河流中,小舟的属性得以体现,并拥有了“船”的意义。显然,这里的河流与小舟,更像是话语与故事的关系:在二者的相遇中,彼此的内涵和功能均得到了显现和拓展。从传统新闻到融合新闻的演进过程中,新闻故事的观念及语义系统发生了一定的偏移,我们可以从故事内涵、故事本体、故事语言、故事结构这四个维度加以认识和理解。第一,在故事内涵维度,经典叙事学将故事的核心特质概括为情节性,认为情节遵循的是可能性模式,即故事层面的行动与变化,主体上以合理性为基础,其打开的是一个想象的世界,然而,新闻故事则依照现实本身的内在规定性,通过推演与求解的方式,构筑了一个真实的新闻世界。第二,在故事的本质维度,融合新闻中的故事之所以会发生“变身”,主要原因在于故事的两个基本构件——事件与实存,均呈现出全新的故事性内涵,如事件超越了时间性和因果性的限制,而呈现出一种推演的、论证的生成语言,实存也从人物故事延伸到数据故事。第三,在故事语言维度,如果说传统新闻叙事的修辞空间较为有限,融合新闻叙事则将“形式的修辞”推向一个极为自由的话语位置,由此颠覆了经典叙事学所预设的故事之独立性内涵——话语具有激活、再造乃至创造故事的潜能,故事最终坍塌在话语之中,成为话语的一部分。第四,在故事结构维度,融合新闻的互动性特征,动摇了经典叙事学所依赖的“结构”之本质,从而以程序修辞为基础,重构了新闻表达的叙事规则,并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故事形态——互动故事。■
参考文献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2009)。《小说面面观》(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2015)。《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曾伟祯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格雷马斯(2011)。《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吴泓缈,冯学俊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胡亚敏(2004)。《叙事学(第二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康德(2004)。《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刘涛(2016)。西方数据新闻中的中国:一个视觉修辞分析框架。《新闻与传播研究》,(02),5-28+12。
刘涛(2019)。理解数据新闻的观念:可视化实践批评与数据新闻的人文观念反思。《新闻与写作》,(04),65-71。
刘涛,黄婷(2023)。融合新闻的空间叙事形式及语言——基于数字叙事学的视角。《新闻与写作》,(02),56-67。
刘涛,薛雅心(2023)。“序列”结构及其超越:融合新闻的时间叙事形式及语言。《新闻记者》,(12),3-21。
罗伯特·斯科尔斯,詹姆斯·费伦,罗伯特·凯洛(2015)。《叙事的本质》(于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玛丽-劳尔·瑞安(2014)。《故事的变身》(张新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米克·巴尔(1995)。《叙事学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热拉尔·热奈特(1990)。《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申丹,王亚丽(2010)。《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润泽,米湘(2024)。新闻世界:新闻学元概念和问题的新探索。《新闻大学》,(01),33-47+120。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2013)。《大数据时代》(盛杨燕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西摩·查特曼(2013)。《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2017)。《对空言说》(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曾庆香,陆佳怡,吴晓虹(2017)。数据新闻: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闻论证。《新闻与传播研究》,(12),79-91+128。
Capra, F. (1996). The web of life. London: Harper Collins.
LundbyK. (2008). Mediatized stories: mediation perspectives on digital storytelling. New Media & Society10(3)363-371.
PerronB. (2003). From gamers to players and gameplayers: The example of interactive movies. In Mark J. P. Wolf & Bernard Perron. (Eds.). The video game theory reader (1st ed.) (pp.237-258).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RyanM. L. (2001). Narrative as virtual reality: Revisiting immersion and interactivity in literature and electronic media. Baltimore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van Dijk, J. (2006). The network society: Social aspects of new media. London: Sage.
[作者简介]刘涛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化经典符号谱系整理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3&ZD2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