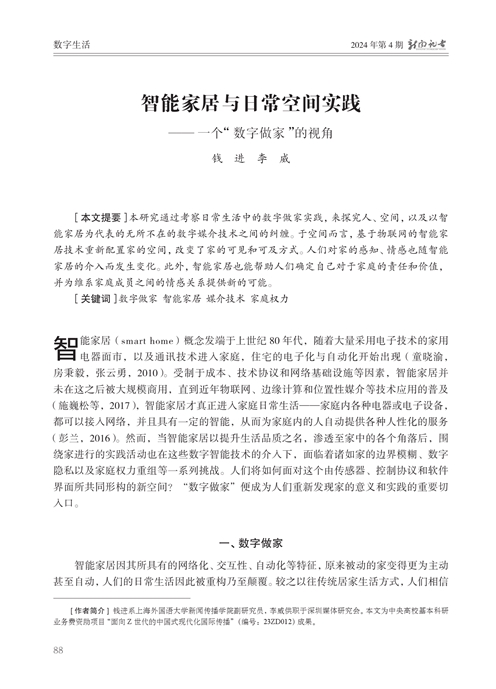智能家居与日常空间实践
——一个"数字做家"的视角
钱进 李威
[本文提要]本研究通过考察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做家实践,来探究人、空间,以及以智能家居为代表的无所不在的数字媒介技术之间的纠缠。于空间而言,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家居技术重新配置家的空间,改变了家的可见和可及方式。人们对家的感知、情感也随智能家居的介入而发生变化。此外,智能家居也能帮助人们确定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和价值,并为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提供新的可能。
[关键词]数字做家 智能家居 媒介技术 家庭权力
智能家居(smart home)概念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大量采用电子技术的家用电器面市,以及通讯技术进入家庭,住宅的电子化与自动化开始出现(童晓渝,房秉毅,张云勇,2010)。受制于成本、技术协议和网络基础设施等因素,智能家居并未在这之后被大规模商用,直到近年物联网、边缘计算和位置性媒介等技术应用的普及(施巍松等,2017),智能家居才真正进入家庭日常生活——家庭内各种电器或电子设备,都可以接入网络,并且具有一定的智能,从而为家庭内的人自动提供各种人性化的服务(彭兰,2016)。然而,当智能家居以提升生活品质之名,渗透至家中的各个角落后,围绕家进行的实践活动也在这些数字智能技术的介入下,面临着诸如家的边界模糊、数字隐私以及家庭权力重组等一系列挑战。人们将如何面对这个由传感器、控制协议和软件界面所共同形构的新空间?“数字做家”便成为人们重新发现家的意义和实践的重要切入口。
一、数字做家
智能家居因其所具有的网络化、交互性、自动化等特征,原来被动的家变得更为主动甚至自动,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被重构乃至颠覆。较之以往传统居家生活方式,人们相信媒介技术的力量能够带来更为美好的生活,事实上,智能代表了当代生活各个方面的终极理想状态(Strengers,2013)。
对智能家居进入家庭日常生活的乌托邦式想象(Strengers,2013),也促使很多研究聚焦于其独特的数字技术系统构成(Kumar,2014;Jose & Malekian,2015;Xu et al.,2016;Feng et al.,2017),以及它在家庭医疗健康(Chan et al.,2008)、协助老年人或肢体行动不便者生活(Demiris & Hensel,2008)、协助家务(Chen et al.,2017)和对家的远程管理(Masuda,2005)等方面所带来的可能性。由此,智能家居被视为被人们引入到家中的工具性存在,是对既有家中媒介技术在功能上的拓展与增益。
然而,家(home)意味着房子不仅仅是提供遮风挡雨的庇护所,亦或是装满家具等物件的容器,它还是个人与社会意义根植的地方(Papastergiadis,1998)。因此,家是既具体(有明确的物理边界与物质性存在)又抽象(家庭中的各种关系与个体实践)的双重空间,是饱含意义、情感、经历和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生活的中心(Blunt & Varley,2004)。Blunt和Dowling(2006)就认为,家是需要通过日常生活进行维护的,这个过程称为“做家”(home-making)。在由人们之间亲密关系和具体生活场所构成的家中,做家意味着个体利用自身的家庭文化知识,在家庭生活中进行自我定位,生产情境化的家庭形态的持续实践的过程(张少春,2014;章立明,2021)。因此,做家便是在人与地方之间创造家的情感联系,即人要使自己感觉在家(feel at home)的状态。
而当媒介技术进入家庭后,传统的家庭文化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受到极大挑战(Lally,2002;Morley,1986;Morley & Silverstone1990;Silverstone & Hirsch,1992;Spigel,2001)。关于家中生活关系性、动态性的社会技术和社会物质研究也表明,人、技术、实践和空间通过纠缠和编排,建构了“家”这个情感凝聚和意义沉淀的特殊地方。在对诸如智能玩具(Brito et al.,2018)、智能手机(De Reuver et al.,2016)和移动媒体(Hartmann,2013)等智能设备和应用如何参与到日常生活实践的考察都表明,讨论家中的日常生活如何受到媒介的改变时,仅仅观察技术是如何被带到家中并嵌入到房子中是不够的,因为这些人工制品正在重组家庭中的互动、社会秩序和关系(Urquhart et al.,2019)。
智能家居像电视等媒介一样,形塑、建构了家庭权力与文化,尤其是智能家居对家的边界的重新定义,影响到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变化,进而产生一种基于数字做家的家庭日常。这其中包括女性主义视角下数字家务中的性别角色建构(Rode & Poole,2018)、智能家居对性别数字鸿沟的加剧(Richardson,2009)、智能家居技术的使用塑造家庭体验并在家庭内部建立权力结构(Ehrenberg & Keinonen,2021),以及智能家居如何干预了家的领土和边界(Humphry & Chesher,2021)等。正如Strengers(2018)所述,智能家居的技术属性,包括研究、升级、更新、维护和集成智能家居技术等新型家庭劳动大都由男性完成,这可能会给家庭中男性带来更多的工作,进一步加剧了“数字”和“传统”家庭管家之间的性别分歧。
Pink和Leder Mackley(2013)提出的“环境/地方-实践/移动-感知/感官具身体验”的三维框架,尝试去回应,在家中媒介饱和的情况下人们对家的感知,以及人们如何通过日常使用媒介让自己感觉在家、进行家的地方制造。智能家居不再仅仅是由单个设备所构成的集成技术系统,经历着技术的生命周期——即媒介技术进入家中,最后从家中被淘汰的过程;而是作为一种媒介实践,被嵌入人们的数字做家实践中,以及人们如何在这个新的、由技术协议、交互界面以及硬件所构成的新的家的空间,完成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家的意义构建。本文将从空间配置、人的感知和家庭内部关系这三个角度入手,分别去探究:人们如何进行技术和空间的挪用,从而将智能家居整合到家的日常生活中,并重新构建家的空间性?人们如何基于自己的情感和感官体验,使用智能家居创造“在家”的感觉?人们如何通过与他人(主要是家庭成员)协商、传达、共享家的意义,将对家的个人情感转换成共享情感?
本文将选取市场主流的智能家居品牌和产品,包括小米米家、Aqara绿米、海尔智家等,考察它们所使用的网络协议、生态系统架构、安装和操作方式、产品发布会和广告宣传片等。同时,研究将分析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智能家居应用软件中对智能家居使用的讨论和分享,如智能家居产品分享、相关安装和设置知识分享,以及打造的智能家庭分享等。此外,研究访谈了12位智能家居用户(见表1),他们多居住在一线城市,对智能家居有一定的使用经验。事实上,智能家居的目标用户多定位为城市的中青年群体(韦向洁,2021)。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这些受访者经验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智能家居的主要使用场景——城市中产家庭,当新的智能技术被引入家中后,人们的做家实践是如何展开的。
二、家的拓扑与空间的自动化
智能家居的各类产品通过物联网技术相互连接,而不再与传统的家居或家电一样保持彼此独立。Brause和Blank(2020)认为,相互连接的设备所蕴含的潜力,尤其是对家的空间产生决定性影响。物联网的核心概念是通过独立完整的地址分配机制连接我们周围各种各样的事物,例如标签、传感器以及智能家电等,使网络中的各个节点能够互相通信,最后达到被人们感知、控制的目的(Atzori et al.,2010)。网络通信协议处在整个智能家居系统的核心位置,影响着设备之间的连接与家庭空间的配置方式。
目前主流的智能家居通信协议多以无线为主,包括Wi-Fi、Bluetooth蓝牙、Bluetooth Mesh和ZigBee,此外还有苹果的HomeKit、华为的HiLink、Matter协议等。较之有线通信协议,无线网络组网方式具有构建复杂度小和网络拓扑结构灵活等优点,但智能家居设备需要在同一个通信协议之下才能通畅互联。以Wi-Fi为例,智能家居设备需首先接入家中的Wi-Fi路由,当在家中通过手机等终端操控一个智能家居系统时,连入同一Wi-Fi的终端会将信号发送给路由器,路由器再把信号传输给智能家居设备的服务器,然后服务器再与设备进行通信,设备收到信号后执行相应的指令(见图1)。在Wi-Fi协议下,设备只接受来自服务器的指令,一旦家中网络或远程服务器出现问题,设备便不能正常运行。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2022年6月发生的小米服务器崩溃事件,有受访者表示因此弃用Wi-Fi协议:
小米那边服务器挂了,导致所有米家设备失灵,感受到了没有智能的不便利,然后连夜买了可以离线使用的网关。(J)
因Wi-Fi协议在网络连接稳定性上的缺陷,大多数厂商都转向Bluetooth Mesh或ZigBee协议。一旦有新设备连接到Mesh网络中,其余设备就会与之进行组网,终端控制设备只要连接其中任意一端,就可控制所有设备。因家用路由器通常不具备蓝牙功能,所以仍需要专门的蓝牙设备——即受访者J所提到的网关——用来连接家中的蓝牙Mesh智能家居设备,再将网关插上网线,这样便可使用网络来控制这些设备了(见图2)。ZigBee与之类似,功率更低但造价更昂贵。这种协议的优势在于绕过了设备服务器,设备的管理能在一个局域网内进行,无需与厂商进行数据交换。
但无论Wi-Fi还是网关,两者的连接同样有距离和数量限制,一旦接入同一个Wi-Fi或网关的设备数量过多,网络就会产生拥挤。同时,当家的面积过大时,单个Wi-Fi或网关便无法满足覆盖全屋智能设备的需求,因此就需要布置分布式网络,即在家中设置安放多个路由器或网关以确保每个设备都能顺畅连接。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们需要重新考虑各种路由器或者网关的数量,以及在家中摆放的位置,以达到各个智能家居设备网络流量的平衡:
(智能家居设备的安装)在最开始时就考虑好了,(无线协议)并不需要改变家里面的布局,会让原来的东西更加好用,也不用布线。(J)
随着无线网络的普及,技术物摆放地点的限制正在减少(Baillie & Benyon,2008),智能家居设备的摆放也更为自由。在物理位置上获得自由后,智能家居技术也便拥有对家的空间使用的自由。这种使用超越实体空间限制,通过网络协议传输的信号在家内外四处穿行,给家带来全新的空间性和人们“做家”的全新体验。空间的自动化,便是这种新体验中最突出的特征。智能家居的自动化很大程度上依赖着传感设备。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监测器需要实时监测家中的环境,并将监测结果量化为数据分享给其它智能家居设备,从而完成整个自动化过程。
然而,家的数据化并不仅仅指数据在不同设备之间的共享,还意味着家的空间对于住户来说更为可见。构成智能家居系统的智能湿温度计、气体传感器和智能电表等设备实时收集家中的环境数据,并传输到终端设备上,原本不可见的湿度、温度和气体浓度等都变得可见。而监控摄像头则能穿透被物理结构遮蔽起来的家,使对其的远程观看成为可能。
人们甚至可以依靠智能家居的中控系统,将家中各智能设备所产生的数据进行集成,并通过与家的平面图相结合的方式,以全知的上帝视角,创造出一副基于数据的家的全景图。Speake(2017)曾对城市的全景图做出如此评论:全景图成为商业和政治策略的目标,因为商业和政治利益集中精力在一个地方创造视觉区分、文化和象征联想,这种全景图与凝视、想象和象征密切相关。只不过现在这种全景图从房地产商和建筑师的手里下放到人们手中,从而赋予人们重新审视、想象自己的家的能力。
此外,智能家居不仅使家对于住户变得透明,家之于外界也变得更为透明。智能家居的技术网络存在于更大的社会网络之中,它们收集的数据通过网络通讯协议跨越家的边界,从智能电视、智能手机、监控摄像头,到社会互动和护理,智能家居系统都需要与服务提供商交换用户的个人信息,而这些对于个人信息的让渡必然会触及用户的隐私问题:
电子猫眼的视频记录会上传到云端。很多设备并不敢用,比如对着家里拍的摄像头。如果我以后要装的话应该会买普通的监控摄像头,数据存本地的服务器里,不会买带云功能的摄像头。(D)
家在象征性和物质上都是自我的延伸(Marcus,2006)它作为一个私人场所需远离他人的凝视(Steierhoffer & McGuirk,2018),因此任何侵犯家的感觉都会产生不安,甚至是本体论危机(吉登斯,1991/2016)。随着智能家居构成家的空间本身,家也变得“多孔”,许多潜在的眼睛与耳朵正透过这些孔洞窥探。智能家居在给予住户可见性的同时,也将这种可见性给予了他者。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也被一系列的硬件配置与软件界面折叠起来,变得更为隐秘,从而成为另一种不可见。家的四壁被凿穿了,以往是由于各种管道和线的介入,而现在则是因为数据的渗透与外溢。智能家居使家成为一个“他者”,一个不再只属于个体的、神秘的、独立的空间。
三、数字化感知中的秩序与氛围
智能家居构成的是一个生活空间,而不仅仅是设备的集合(Ehrenberg & Keinonen,2021),因此数字做家需要处理如何在家的日常生活中整合和感知数字技术,从而使家的感觉是对的,即作为杂乱的技术和物如何帮助人们赋予家庭空间意义和秩序,以便使其作为组织和建造家的永久项目的一部分(Swan et al.,2008)。智能家居中的自动化管家,便是帮助人们赋予自己家以秩序与意义的重要功能。
在智能家居系统下,用户能够设定物与物之间的联动,通过“IF”语法(在特定环境下如果A发生了,则判定触发B操作)实现基本的自动化管理。这种自动化管理能将人们从一些简单而重复的操作中解放出来,例如上面提到的开关操作,智能家居能够随叫随开或者随叫随关,并且在“晚安”或“回家”的指令后执行预先设定的指令:
我设置了夜灯蓝牙板,在特定时间段环境光暗时会自动开启灯光空调和电脑,并且在下班回家开门会触发,能够省不少事。(G)
我基本上大部分智能家居和传感器都在联动里,可能90%以上的执行是由自动化触发的。门厅灯联动门锁这些场景非常好用、方便……自动化的东西还是方便的,特别是每层楼一个扫地机器人,离家模式中午自动扫地,省了很多事。(J)
事实上,通过这种场景联动的自动化,原本繁琐而无关联的家务活动以一种更为有效率的方式被重新组织起来。独立存在的物(智能家居)在由传感器与数据所构成的智能管家的中介下,与家中的人发生了更为积极的互动。在设备、人和家的空间之间,一种新的、关于家的秩序感被建立起来。对于这种秩序感的维持,不仅在人们居家时发生,还可以在离家时通过监控家中发生的意外情况,来规避那些潜在的、对秩序的威胁:
安全的确是智能家居中重要的一部分,比如浸水传感器和天然气传感器,可以第一时间知晓家中漏水和煤气泄漏这样的意外。智能门锁让我随时知道家中开门关门信息,结合摄像头使用,可以实时监控家中的状况。(C)
通过构建秩序感,智能家居让人们获得一种居家的安心,从而营造了一种基于数字控制技术的家的氛围。事实上,家是充满情感的地方,家庭成员以不同的角色和与技术的关系生活在一起(Baillie & Benyon,2008)。智能家居技术往往对情感体验本身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人们的环境变得更加智能时,他们的日常生活将会更加快乐和愉悦(Nakajima et al.,2005)。
有学者将与情感相关、产生或持续情绪的技术描述为情感计算(Picard,1997),其通常出现在智能氛围(smart atmosphere)语境中。智能氛围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特殊的环境所创造的特殊氛围,经常结合某种形式的情感(Streitz,2005)。数字媒介技术不该仅仅被视为信息处理器,它们也是重要情感体验的提供者(Sellen et al.,2009),在智能家居领域,模仿某种氛围的技术正在越来越多地塑造我们对空间的体验(Bille,2014),并且涉入我们的情感。人与智能家居的综合实践正在创造家的氛围,一种家的感觉,Pink和Mackley(2013)就指出,与媒介的感官接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通过日常使用媒介来让家感觉正确。
在智能家居所创造的智能氛围中,光照是人们感受家的重要来源。例如环境中灯光的颜色(暖光与冷光)可以作为一种情绪诱导剂,并以消极或积极的方式影响参与者的情绪(Knez,1995)。照明系统作为最早纳入智能家居系统的部分,与场景化和自动化的结合便是其突出的特点:
智能灯光可以根据日出到日落室外的亮度,逐渐调整家庭中灯光的明暗、色温,在工作啊、娱乐啊、休息啊这些不同环境下烘托氛围。(C)
在人的照明实践中,通过对光、黑暗、辉光和阴影的强度之间相互关系的利用,来不断创造差异性的氛围(Bille,2014),Ingold(2011)认为,这不是物理世界的现象,或者内心心灵之光的一种体验。对视力正常的人来说,它有居住在可见世界的体验,如光辉和阴影、色彩和饱和度以及这种体验的变化。光在照亮空间的同时也成为空间本身。人们通过控制灯光模式的变化,从而改变自身的空间体验。一方面,从窗户里透出的灯光通常是家的象征之一;另一方面,人们可以根据需要改变灯光设定,通过灯光的变化来促使心情转变,进而创造出在家的舒适气氛:
每当我下班回家后,家里面的灯光就会自动打开,好像有人在等我一样,虽然我老婆可能还没下班……感觉比没有的时候更温馨一点。(B)
我房间的(智能彩灯)是个可以调颜色的RGB灯泡,我房间顶灯是装三个灯泡的,想换个灯光颜色换个心情的时候可以调成任意颜色。(F)
改变家里的智能灯光模式,例如舞会或万圣节模式,或者用语音命令启动家庭影院模式,有一种强烈的好玩元素(Humphry & Chesher,2021):
我家目前有几组灯具来适应不同的场景模式,有极光灯、灭蚊灯、月亮灯,卫生间灯当作夜灯,射灯来照亮餐桌等重点空间,两组管灯做大面积照明,还有各种落地灯、舞厅彩灯、鱼缸灯,给飞镖的靶盘也单独设置了照明,可以在屋里用各种方式玩。(J)
当人们将使用智能家居视为参与游戏,他们在智能家居空间中亦获得了一种游戏的体验,从而与其具体功能脱钩,转变成更为纯粹的感官交互体验,并且也通过这种可玩性给家赋予不一样的意义。而灯具的造型和颜色除能够装饰空间外,这种具有新的交互性和可玩性的灯光也加入到重塑原有空间意义的过程中。正如Edensor(2012)在考察光的变革潜力时所指出的那样,因为光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颜色和形状的感知,它既是一个离散的、由一个个元素组合而形成的物质,同时也具有跨越空间的属性。
与此同时,听觉也是智能家居与住户创造家的氛围的重要感官,尤其对于那些使用智能音箱的人群来说,它是在家中与智能家居交互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事实上,人们一直有着通过使用广播、电视等媒介制造声音来烘托一种在家感觉的传统(Emmett,2021)。而在家的智能家居化后,人们可以通过语音,随时呼叫智能音箱播放音乐、新闻等,从而在家中制造声音,创造一种在家的氛围感。在移动网络的加持下,人们甚至可以在回家之前就能操控家中音乐的播放,或者将耳机中的音乐自动流转到智能音箱上,使声音的跨空间接力与不间断播放成为可能(Brause & Blank,2020)。许多独居人士,也通过声音的持续播放给家带来生气。智能音箱的语音问答功能便是这种声音实践的一种,即通过智能音箱中所发出的模拟人声,为独居者们提供一个数字化的陪伴者:
确实会给家带来一些活力,自己一个人在家也没有人能够说话,虽然它(智能音箱)不一定是在跟你聊天,但是这个感觉也挺奇妙的。(J)
部分智能音箱还支持修改语音为方言的功能,这进一步提升人们“在家”的感觉,尤其对于那些远离家乡的人来说,乡音是他们与遥远家乡的重要连接。通过将乡音引入到家的空间中,丰富了家的意义以及所承载的情感连接。受访者G是一名独居者,他家中的智能音箱可以设置为四川话,这与他的家乡话西南官话很接近,用家乡话进行问答确实让他感觉更加本地和亲切。
对人们来说,家是一个独特的、能与其他空间区隔开来的地方,它能够使人们进入外这个空间便感觉在家。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人们的做家实践更能创造这样一种情感氛围,它作为一种中介而存在,是感官和情感体验的中心(De Molli et al.,2020),能够帮助人们将家的空间转化为段义孚所说的具有情感意义的地方。人们从外部空间逃离,躲进这一方天地,而这种逃避并不意味着跨越或离开某个空间的边界,而是通过纠缠的运动和感官体验以及特定的一系列物体和技术而产生的情感力量(Clark & Lupton,2021)。另外,家的氛围不仅仅是被创造出来,Duff(2010)就提出身体被地方所情动(affected by place),这种情感氛围的创造不仅给人们带来了相应的情感体验,更进一步激发人们的情感实践,让家变得更具独异性。
四、权力关系的转换与情感维系
智能家居系统与手机、电脑等私人性质的设备不同,作为家庭的“基础设施”,在家中更具公共性。作为日常生活中彼此交换感情的情感纽带,家庭成员通过智能家居实践给家庭内部关系带来了新的可能。
智能家居被引入家的空间,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将人们从繁琐而无趣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在家庭关系中,人们经常会因为某件家务而起分歧和争执,而智能家居的自动化、远程化有时会解决家人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的争端:
(智能家居)让我们从家务中解放,有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娱乐、休息上,并且最大的感受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喜欢呆在家里,也减少了家庭成员之间不必要的嫌隙。(C)
智能家居通过承担起这一部分工作,像纽带一样维系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即便是当对如何使用这些设备产生争执时,它也会演化成一种家庭成员之间对技术使用的协商行为,并从中生产出情感意义。受访者D与他的妻子就电动窗帘的使用曾产生过分歧:
我觉得自动开窗帘挺好用,但我老婆就很不喜欢,她甚至讨厌到会把自动打开的窗帘关掉。我们俩主要是对使用方法有点分歧。我的想法是在天亮之前拉开,这样随着天亮,房间会逐渐变亮,这样可以自然醒。但是我老婆把拉开窗帘视为闹钟一样的标志,另外窗帘电机深更半夜还挺响的,她睡得又比较浅……现在的话还在纠结窗帘怎么设置,应该最后不会去用这个功能,或者就按她的想法设成和闹钟同步。
分歧的存在并不一定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反而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对某个功能使用的共识,并在这种分歧的解决过程中增进彼此的认同和情感。而对于智能家居一些功能的非规范使用,也能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制造意外,来增强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连接:
有一天晚上,我老公远程控制智能洗衣机洗衣服,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吓得以为家里有小偷了。所以它的技能是吓人,假装家里有人。(D)
韩国SK电讯制作的一则宣传片就展示了丈夫如何通过远程操控家里面的灯光和扫地机器人,给家中妻子制造节日惊喜。事实上,这些关怀隐藏在每一次使用体验里。受访者A就表示:
下班回到家后家里的灯自动亮起会感到温馨,因为这是我老公设置的。
因此,灯光在产生氛围的同时,家人的设置也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卷入。通过日常生活的仪式化行动,智能家居帮助人们维系起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而虚拟在场,则是这一过程中重要的构成要素。家庭成员并不总“具身”一起在家中,无论是外出工作,还是与父母长辈分开居住,短暂或长期的分离是现代家庭生活的常态。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的家庭正向个体化转变,家庭结构也变得更为多元与流动。受访者J就表示,自己不和父母一起居住,但两边家中都有智能摄像头和智能屏,有时会用智能屏来视频通话。而更多的时候,则是通过智能摄像头来互相照看:“老人会通过摄像头看我们在干什么,想我们了就会看看”。
通过主动性暴露行为,即将自己的生活通过智能摄像头展示给远方的家人,从而缓解老人的担忧与孤独,即老人能够实时地观看自己儿女家里面的情况,仿佛自己“在场”。受访者C,夫妻双方都是上班族。他们的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因此孩子独自在家的时间比较多。出于安全和陪伴考虑,他们利用家中的智能摄像头对独自在家的孩子进行远程照看:
为了确保小孩的安全,小孩在家的时候我会看看。孩子是知道有摄像头的,目前小朋友还小,没有隐私概念,他也会通过摄像头和我主动打招呼,因为有麦克风,还可以对话。
人们通过智能家居创造一种虚拟的在场,即使家庭成员不是具身地在彼此身边,也能通过这种数字具身化营造亲密关系的场域,进行交流和维系家庭的情感关系,而人们对家的情感依恋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加深。
然而,在智能家居维系家庭成员关系的背后,是大量不可见的技术劳动。无论是专业安装的集成智能家居系统,还是使用不同的设备组合,抑或在设备之间出现断连从而需要进行故障排除和重新设置,都需要用户自己去探索和实践,以创建出个性化智能家居系统。因此,对这些智能设备的配置以及日常的维护工作,构成了一种对家的维护(Atkinson,2006):
我不是因为想要某个智能的产品就去买某个产品的,是要基于自己的生活场景去设置不同设备之间的联动,或者说去满足生活的需求。你有了这样一些设备之后,你能够去通过你想要的场景去把它给联动起来,让每一个单独的设备在你自己的生活场景里面发挥更大的价值。(B)
作为通常是主动往家中引进智能家居的角色,男性承担起了在家中进行数字DIY实践的工作。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更为主动地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
我本身处于相关行业内,对这类信息比较敏感,借一次装修的契机我就进行了主导和提议,我妻子也愿意接受。后来我也去看一些网站和自媒体的产品评测。(C)
传统上技术是男性的领域,而家则属于女性的领域(Strengers & Nicholls,2018)。由于男性在技术产品设计和开发上所处的主导性位置,其所具有的权力和认知偏见,也导致主流技术文化趋向男性化规范。也正因此,男性以一种“骑士精神”(Rode,2018),主动承担起数字技术的相关工作。家庭中的女性,则往往因为对数字技术本身没有足够的热情或者掌握足够的知识,无法过多地参与到智能家居的配置与维护的工作:
在安装和配置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我来负责,然后有一些时候我老婆会跟我一起。这涉及电器和网络的知识和操作,还是我比较熟一点。(B)
智能家居的安装调试通常是由个人主导的方式进行,但这种配置过程往往需要照顾到其他家人的感受与体验,即从家人共同的日常生活习惯出发,而非仅按一方的意愿展开的实践。作为承担主要规划和设置工作的男性,需要将更多关注与情感投入家的劳动中,从而保证智能家居能嵌入家中既有的习惯与秩序,从而保证其能在家的空间中正常运作。
使用智能家居的初衷是解放用户的时间,但在享受被称为“快乐”的日常体验的同时,也增添了许多新的工作,从而导致家庭维护工作的再分工。在对家庭劳动的传统认知中,技术设备的配置和维修等工作属于男性的“休闲娱乐”活动,而传统的家政领域如清洁、洗衣、烹饪等“家务”多归属于女性。这些家务正逐渐被机器所替代,而这些机器的维护又被认为属于男性的家庭职责范围内。例如受访者B就表示是他负责对扫地机器人等机器进行清洗。
智能设备进入到家的日常生活中后,男性也更多地、自觉地参与到家庭维护的工作中,这也更能帮助男性确认他们在家的身份,并增加对家的责任感与情感,正如所有男性受访者都表示他们“有义务”担当起智能家居的安装与维护工作。然而,一旦这种配置需要的知识过于复杂,或者后续的维护工作过于复杂和频繁,这种被认为是休闲娱乐的行为也可能会退回成传统的家务,男性参与到这些技术劳动热情也会衰退。
五、结语
家和媒介技术存在于一种相互确认的关系中——媒介技术通过融入家庭的空间/时间节奏而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亲密方面(Church et al 2010),同时它们的存在也标志着我们已经回家了。作为数字技术的智能家居不仅挑战了人们对媒介技术与家庭空间设计之间关系的认知,更挑战了人们对家的理解。对由协议、软件界面和传感器等所构成的新的家的空间而言,做家试图去调和这样一组矛盾关系,即人们一方面希望家是一个可以从外界逃离的世外桃源,另一方面却主动邀请外界进入家中。家中的智能技术使家超越了物理概念,延伸到数字化的虚拟领域。高速网络连接促使家对虚拟领土的扩张,这种扩张加速了家庭内外的通信交换,而数据的流动中也暗涌着来自家内外的权力与控制争夺。■
参考文献
安东尼·吉登斯(1991/2016)。《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彭兰(2016)。万物皆媒——新一轮技术驱动的泛媒化趋势。《编辑之友》,(3)5-10。
童晓渝房秉毅张云勇 (2010)。物联网智能家居发展分析。《移动通信》,34(9),16-20。
施巍松,孙辉,曹杰,张权,刘伟 (2017)。边缘计算:万物互联时代新型计算模型。《计算机研究与发展》,54(5),18。
韦向洁(2021)。中国智能家居行业概览:产业链与趋势观察。检索于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103181473198927_1.pdf。
吴飞(2009)。“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社会学研究》,(2),177-199。
章立明(2021)。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的全球"做家"实践。《公共外交季刊》,(1),59-66。
张少春(2014)。“做家”:一个技术移民群体的家庭策略与跨国实践。《开放时代》,(3)13。
AtkinsonP. (2006). Do It Yourself: Democracy and Design.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19(1)1-10.
AtzoriL.Iera, A.& Morabito, G. (2010).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 survey. Computer Networks, 54(15)2787-2805.
Baillie, L.& Benyon, D. (2008). Pla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Home.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CSCW)17(2-3)227-256.
Bille, M. (2014). Lighting up cosy atmospheres in Denmark. Space and Society15(3)56-63.
Blunt, A.& DowlingR. (2006). Home. London: Routledge.
Blunt, A.& Varley, A. (2004). Geographies of home. Cultural Geographies11(1)3-6.
BrauseS. R.& BlankG. (2020). Externalized domestication: Smart speaker assistants, networks and domestication theory.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3(5)751-763.
Brito, R.Dias, P.& Oliveira, G. (2018). Young children, digital media and smart toys: how perceptions shape adoption and domesti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9(5): 807-820.
ChanM.EstèveD.EscribaC.& CampoE. (2008). A review of smart homes—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challenges. Computer methods and programs in biomedicine91(1)55-81.
ChenS.LiuT.GaoF.Ji, J.Xu, Z.Qian, B.... & Guan, X. (2017). Butler, not servant: A human-centric smart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55(2)27-33.
ChurchK.Weight, J.BerryM.& MacDonaldH. (2010). At Home with Media Technology. Home Cultures, 7(3)263-286.
Clark, M.& Lupton, D. (2021). Pandemic fitness assemblages: The sociomaterialities and affective dimensions of exercising at home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Convergence27(5)1222-1237.
De MolliF.Mengis, J.& van MarrewijkA. (2020).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Hybrid Space: The Atmosphere of the Locarno Film Festival. Organization Studies41(11)1491-1512.
De Reuver, M.NikouS.& BouwmanH. (2016). Domestication of smartphones and mobile applications: a quantitative mixed-method study.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4(3): 347-370.
Demiris, G.& Hensel, B. K. (2008). Technologies for an ageing societ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mart home’ applications. Yearbook of Medical Informatics333-40.
DuffC. (2010). On the Role of Affect and Practice in the Production of Pl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28(5)881-895.
Edensor, T. (2012). Illuminated Atmospheres: Anticipating and Reproducing the Flow of Affective Experience in Blackpool.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30(6)1103-1122.
Ehrenberg, N.& Keinonen, T. (2021). The Technology Is Enemy for Me at the Moment: How Smart Home Technologies Assert Control Beyond Intent. Proceedings of the 2021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1-11. Yokohama Japan: ACM.
EmmettI. R. (2021). Feeling at home: Soundaffect and domesticity on radio soap operas. Radio Journ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Broadcast & Audio Media19(1)23-39.
FengS.Setoodeh, P.& Haykin, S. (2017). Smart Home: Cognitive Interactive People-Centric Internet of Things.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55(2)34-39.
HartmannM. (2013). From domestication to mediated mobilism.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1(1): 42-49.
Humphry, J.& ChesherC. (2021). Visibility and security in the smart home.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27(5)1170-1188.
IngoldT. (2011). 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 Oxford: Routledge.
JoseA. C.& Malekian, R. (2015). Smart Home Automation Security: A Literature Review. The Smart Computing Review, 5(4)269-285.
KnezI. (1995). Effects of indoor lighting on mood and cogni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5(1)39-51.
Kumar, S. (2014). Ubiquitous Smart Home System Using Android Appl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Networks & Communications, 6(1)33-43.
Lally, E. (2002). At Home with Computers. Oxford: Berg.
MarcusC. C. (2006). House as a Mirror of Self: Exploring the Deeper Meaning of Home. Newburyport: Nicolas Hays, Inc.
MasudaY.Sekimoto, M.NambuM.HigashiY.Fujimoto, T.ChiharaK.& Tamura, Y. (2005). An unconstrained monitoring system for home rehabilitation. IEEE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magazine, 24(4)43-47.
MorleyD. (1986).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Comedia Publishing Group.
MorleyD.& SilverstoneR. (1990). Domestic 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 and meanings. MediaCulture & Society12(1)31-55.
NakajimaT.Fujinami, K.& Tokunaga, E. (2005). Building intelligent environments using smart daily objects and personal devices. In CIT 2006: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CIT2006). Citeseer.
PapastergiadisN. (1998). Dialogues in the diasporas: essays and conversations on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Rivers Oram Press.
PicardRW.(1997).Affective computingThe MIT Press.
PinkS.& Leder MackleyK. (2013). Saturated and situated: Expanding the meaning of media in the routines of everyday life. MediaCulture & Society35(6)677-691.
RichardsonH. J. (2009). A ‘smart house’ is not a home: The domestication of ICTs.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11(5)599-608.
RodeJ. A.& PooleE. S. (2018). Putting the gender back in digital housekeeping. Proceedings of the 4th Conference on Gender & IT - GenderIT, 1879-90. HeilbronnGermany: ACM Press.
SellenA.Rogers, Y.Harper, R.& Rodden, T. (2009). Reflecting human values in the digital age.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52(2)58-66.
Silverstone, R.& Hirsch, E. (1992). Consuming Technologies: Media and Information in Domestic Spaces. London: Routledge.
SpeakeJ. (2017). Urban development and visual culture: Commodifying the gaze in the regeneration of Tigné PointMalta. Urban Studies54(13)2919-2934.
SpigelL. (2001). Media homes: Then and no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4(4)385-411.
SteierhofferE.& McGuirkJ.eds. (2018). Home Futures: Living in Yesterday’ s Tomorrow. SouthwarkUK: The Design Museum.
Streitz, N.Magerkurth, C.Prante, T.& Rocker, C. (2005). From information design to experience design: Smart artefacts and the disappearing computer. Interactions, 12(4)21-25.
Strengers, Y. (2013). Smart Energy Technologies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Strengers, Y.& Nicholls, L. (2018). Aesthetic pleasures and gendered tech-work in the 21st-century smart home.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166(1)70-80.
SwanL.Taylor, A. S.& Harper, R. (2008) Making place for clutter and other ideas of home. 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15(2)9-24.
UrquhartL.Reedman-Flint, D.& Leesakul, N. (2019). Responsible Domestic Robotics: Exploring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Robots in the Home. Journal of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and Ethics in Society17(2)246-272.
XuK.Wang,X.WeiW.Song,H.& MaoB. (2016). Toward software defined smart home.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54(5)116-122.
[作者简介]钱进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李威供职于深圳媒体研究会。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面向Z世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编号:23ZD01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