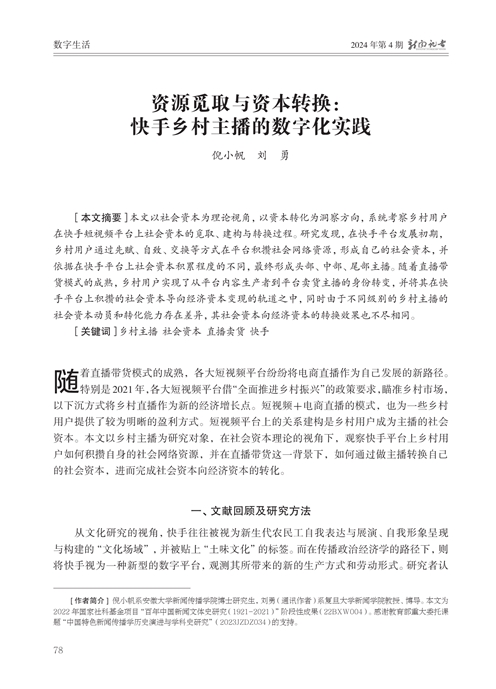资源觅取与资本转换:快手乡村主播的数字化实践
倪小帆 刘勇
[本文摘要]本文以社会资本为理论视角,以资本转化为洞察方向,系统考察乡村用户在快手短视频平台上社会资本的觅取、建构与转换过程。研究发现,在快手平台发展初期,乡村用户通过先赋、自致、交换等方式在平台积攒社会网络资源,形成自己的社会资本,并依据在快手平台上社会资本积累程度的不同,最终形成头部、中部、尾部主播。随着直播带货模式的成熟,乡村用户实现了从平台内容生产者到平台卖货主播的身份转变,并将其在快手平台上积攒的社会资本导向经济资本变现的轨道之中,同时由于不同级别的乡村主播的社会资本动员和转化能力存在差异,其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效果也不尽相同。
[关键词]乡村主播 社会资本 直播卖货 快手
随着直播带货模式的成熟,各大短视频平台纷纷将电商直播作为自己发展的新路径。特别是2021年,各大短视频平台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要求,瞄准乡村市场,以下沉方式将乡村直播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短视频+电商直播的模式,也为一些乡村用户提供了较为明晰的盈利方式。短视频平台上的关系建构是乡村用户成为主播的社会资本。本文以乡村主播为研究对象,在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下,观察快手平台上乡村用户如何积攒自身的社会网络资源,并在直播带货这一背景下,如何通过做主播转换自己的社会资本,进而完成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方法
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快手往往被视为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表达与展演、自我形象呈现与构建的“文化场域”,并被贴上“土味文化”的标签。而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下,则将快手视为一种新型的数字平台,观测其所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形式。研究者认为,快手平台为受教育程度较低、边缘化程度较高的草根群体提供了创意工作的机会。创意工作者以在快手平台上展示与销售“贫困”的方式,来换取微弱的经济收益,并以此作为一种生存方式(Lin,Kloet,2019)。在“平台”商业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这些草根个人的创造力、生命力和个性,日益演变为市场盈利活动,导致了自主传播实践的异化(范英杰,李艳红,2020)。董晨宇、叶蓁(2021)从关系劳动的视角出发,指出社交媒体为用户之间建立和维系关系提供了基础性功能,而建立在此种“关系”基础上的劳动已经成为文化生产者普遍的工作形式,也为用户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中带来了新的职业身份。因此,基于短视频平台的关系建构是主播生成的前提条件。整体观之,大部分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成为主播之后的平台劳动及其过程。那么,在成为主播之前,乡村用户是如何建构、积攒其平台关系资源?又如何将关系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本?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跳脱单一的文化研究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尝试以社会资本为理论视角,以资本转化为洞察方向,观照乡村主播对短视频平台社会资本的觅取、建构与转换的过程。
本文的“乡村主播”是指立足乡村,基于短视频平台与用户互动,完成“带货”——销售实体商品的群体,其所出售的商品大多源自当地的自然资源。乡村主播以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为主,同时也包括一些外来群体。本研究以快手播放量第一的乡镇江苏省连云港的H村(以下简称“H村”)①作为研究对象。H村传统上是个渔业村,约3100人口的小村庄却拥有300多位销售海鲜的主播,每天晚上都有上百个直播间在快手平台销售商品。本文第一作者的田野工作历时一年(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通过对H村乡村主播实践的参与式观察,结合对H村头部、中部、尾部等20位乡村主播以及部分乡镇干部的访谈,尝试在深描乡村主播数字化实践的基础上,聚焦短视频平台的乡村嵌入的传播图景。具体要回答如下问题:快手如何征召和吸纳乡村主播参与平台实践?乡村主播如何在数字化实践中从平台觅取资源,继而实现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
二、从赋权到赋能:技术普惠下的资源分配
在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分布和媒介活动主要围绕城市展开,目标市场更多着眼于城市,目标受众也更多指向城市市民。与之相对照,大众传媒上的乡村用户则常常隐匿不见。伴随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为农村受众提供了一个自我言说与展演的舞台。
2013年后,快手转型为短视频社区,并提出“平等普惠”的价值观,用户下沉,凸显“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路线。2017年7月,快手平台推出宣传片《生活,没有什么高低》,文案以“每个人都值得被记录”为核心。2020年6月6日,快手发布宣传片《看见》,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平凡大众以及看见的力量”。这一阶段快手强调的是通过技术帮助用户获得传播权。技术赋权论认为,新媒介的普及有助于形成对既有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构,能够让弱势群体形成另类表达,从而抗衡主控话语(范英杰,李艳红,2020)。快手平台通过向普通人“赋权”的方式,鼓励乡村用户也来参与平台的内容制作与分享,集聚了自己的用户资源和平台内容架构。由此迅速完成初创期的用户规模扩张,乡村用户逐渐成为快手的主流用户。
技术赋权之后,快手平台在其“第二次言说”中,将注意力视为一种资源、一种能量,强调为更多普通人提供机会(快手研究院,2019:8)。2021年2月5日,快手联合创始人宿华在快手上市的致辞上表示:“在快手平台上已经有2000万人获得了收入。” ②当平台的注意力资源也能转化为一定的收入,当村民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使用不仅能够进行自我展演,同时还能增加收入、成就自我时,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心甘情愿”地投入到平台的数字化实践之中。从赋权到赋能,快手平台通过两次言说的转变,商业话语最终代替了文化话语,也迎合了乡村用户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
三、资源的觅取与争夺:个人社交网络资源的建构
人们在日常实践中依靠某种“社会资本”来展开竞争。按照林南的界定,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亦即个人所建立的社会网络,“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最终表现为借此所能动员和使用的网络中的嵌入资源”(Lin,2001)。个人资源的建构则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种是继承或者先赋,另一种是对自己资源的投资或者是努力来获取(即自致),最后一种是交换(林南,2005:41)。短视频平台本身所具备的社会关系网络编织功能,能够帮助乡村用户建立起个人社会网络。依循林南划分的三种途径,本文根据村民的入场时间、平台流量、个体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个人资源的多少和在网络社会结构中占据位置的高低,分为先赋资源者、资源自致者、资源交换者三类主播群体,考察他们的实践特点。
1.先赋资源者:平台流量资源偶得
在H村使用快手的村民可以划分为三类,分别是早期入场者、中期入场者和晚期入场者。早期入场者的入场时间为快手短视频平台发展初期,多为外出捕鱼的渔民,他们使用快手记录自己的出海生活。此种对自己生活的记录、分享,不仅在快手平台上获得了较大的曝光量,还获得了上热门的机会。除了在入场时间上占据优势外,平台流量的关照也使其成为短视频平台发展过程中的受益者,并在此契机下迅速完成粉丝的积累,进而在网络空间中占据优势地位,部分还成为头部主播。本文考察的头部主播的粉丝数量为300~500万,他们较早开启了直播卖货的实践。一位受访的头部主播表示:
2015年,我开始用快手,最初只是简单分享一下自己的航海生活,没有想到观看的人还很多,但是很多粉丝不是冲着我的视频来的,而是来问我海鲜怎么卖,我从那时就接触电商了。(访谈对象S3)
也就是说,乡村用户在快手平台的赋权之旅中,开始只是记录个体的日常生活,但是对于受众来说,除了关心这种远处的生活,同时还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其所拍摄的产品上,从而带动乡村用户对快手平台使用目的的转变:
以前卖海鲜都是卖给渔货贩子,渔民自己获利很少,销量也不高,通过快手卖货后,现在收入成百万和上千万都不是问题,电商对我们这里的生活和经济影响太大了。(访谈对象S2)
2017年下半年,快手平台迎来了发展的风口,资源先赋者由于前期在平台上个人粉丝的积累以及快手平台扩张过程中给予的流量扶持,搭上了快手平台发展的顺风车。个人的社会资源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也会带来越来越多的“淘金者”进入快手平台。
2.资源自致者:身体的“伤害”以期获得平台流量的关照
在社会学视域中,权威是权力的一种方式。权力指的是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的角色和地位上所表现出来的迫使他人产生遵从性的能力或影响力,而权威就是这种能力或影响力的合法化,它更多地体现出受权力控制的人对权力拥有者的赞成和承认(翟学伟,1999)。在H村,早期入场者在短视频平台上成功的卖货实践,不仅使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树立了自己的个人权威,而且通过平台卖货取得巨大经济收益,使得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认可短视频平台上个人资源的价值。但不同于早期入场者拥有平台给予的先赋性资源,中期入场要想在平台上获得个人资源就需要付出一定的自致努力。
在H村,中期入场者已无法享受随便拍摄就可以上平台热门的机会,想获得更多的注意力资源,就要对自己的短视频内容进行创意化生产,同时每天不断地拍摄,以此来希冀算法的倾斜。中期入场者的粉丝数量一般在100~200万之间,其中受访的中期入场者表示:
自己是第二批入场的,并没有享受到早期平台的流量红利,每天都花费一定的心思在视频拍摄上。刚开始拍段子,观众稀少,一直持续拍了好几天都没有什么起色,可是没想到在想要放弃的最后一刻,自己拍摄的八爪鱼“爆头”视频火了,上了平台热门,收获数万粉丝。(访谈对象S7)
快手账号名叫“彩云海鲜”的乡村主播,在早期入场者的带动下入场,入场后因为直播风格生猛,更具个人特色,吸引了一大批受众的观看,现在该主播粉丝高达206万,粉丝数量也超过部分早期入场的乡村主播。
就像“彩云海鲜”一样,由于大部分乡村主播都是渔民出身,本身并没有多少才艺,所以只能靠一些夸张的“身体展演”博出位:
有一次,从滚烫的油锅中拿东西出来吃,结果烫掉了一颗牙,牙肉也烫伤了,但还是一面忍着剧痛,一面大声对观众喊“老铁,给我500个双击”。(访谈对象S3)
身体的展演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缺乏才艺技能的乡村用户为了获得平台资源的关照,在没有任何先赋性资源的情况下,只能将身体做为展演的景观和商品,依靠对身体的伤害迎合消费者猎奇心理,以吸引流量。身体图像建构可以产生视觉快感,强化视频的冲击力(徐亚萍,李爽,2021),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发了“土味”视频的形成。
3.资源交换者:跨越层级的攀附与合作
在H村,还有一部分村民在平台主播饱和的背景下入场,不但不存在任何先赋性资源优势,而且虽然认真展演,但其在平台上的涨粉速度依旧很慢,这类人的粉丝数量在100万以下,在本研究中被界定为尾部主播。在乡村社会地缘优势的背景下,一部分尾部主播为了获得社交平台上的个人资源,采取对头部主播的攀附策略,主要表现为配合头部主播短视频的拍摄,成为头部主播短视频中的配角,以期通过在头部主播视频中曝光自己获得账号涨粉:
现在拍短视频涨粉太难了,我的粉丝数量只有1.8万,主要是玩的时间太晚了,我玩了快两个月了,涨了1万粉还不到,他们大主播粉丝数量多,订单量也大,我现在给大主播打打酱油,在粉丝面前混个脸熟。(访谈对象S17)
入场较晚的乡村主播在视频拍摄的内容和题材的选取上也往往缺乏一定的创作能力和个人特色,多通过对头部主播的模仿、依附,甚至不惜丑化自己的方式来换取快手平台的注意力资源,并最终形成依附头部主播的圈层效应。
四、转化与变现:从社会资本到经济资本
按照社会学的理路,人们从自己的社会关系中会积累到一定的资源和利益,这即是“社会资本”。个人投资的工具性概念是社会资本的核心,亦即进行社会关系投资的个人总是期待着投资的回报(Lin,2001)。乡村用户在短视频平台积累的个人粉丝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在社交平台中的社会资本,而其对于平台上关系资源的维系最终是为了获得回报和收益,因此,资源的觅取成了资本谋求的前奏。当乡村主播在社交平台上致力于自我利益的实现时,就要进行资源动员,将其投入资本增值中。
伴随着直播电商时代的到来,直播卖货成为短视频平台更为有效的变现方式,村民们也从简单的内容生产者转向商品售卖者,并纷纷开启直播卖货的数字化实践。在H村,乡村主播由于社会资本积累程度的不同,分别形成了头部主播(200~500万粉丝)、中部主播(100~200万粉丝)和尾部主播(100万以下粉丝),在资源向资本转换的过程中,不同层级主播拥有的社会资本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其动员方式和社会资本的转化率也不尽相同。
1.头部主播:虚拟关系的维系与高效的动员能力
社交短视频平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线上交往空间,在这里人们不仅能够与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保持联络和互动,还可以与虚拟空间中的用户培育新的社交关系。头部主播通过在快手平台记录个人生活,逐渐构建了具有相对持久性的数字关系网络。头部主播的粉丝对其有着高度的情感认同,直播卖货表现出一种信任关系的维系和情感的交流:
我和老婆结婚的时候,婚车都是快手老铁们出的。其实大家线下都没见过,但都愿意来给我捧场。所以我卖的产品都是保质保量的,要对得起老铁对我的信任。我不搞那些虚的促销,他们(其他主播)先抬高价格,然后再去打折,那没意思。我通常在直播间对下单的铁子干一杯表示感谢。(访谈对象S1)
在中国社会,“关系”即有助于互惠交往的人际间的联系,往往是通过聚餐发展和维持起来的(边燕杰等,2004)。因此,在中国的关系消费空间中,饮食空间成为动员社会网络的重要场所之一。头部主播在无法与粉丝见面建立情感联系的基础上,通过在直播间吃饭、做饭,并对着镜头宴请、干杯等做法,将线下的交往搬到线上虚拟空间,在这个场域中进行关系的维系,进而推动粉丝在直播间下单。
此外,在社交媒体环境下,个体行动者变现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其媒介传播能力和动员能力。头部主播因其自身具有的粉丝数量以及在网络空间占据资源优势位置,故在社交空间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根据为期一年的线上观察,本研究发现头部主播凭借对真实场景的展现以及自身的影响力,大多是通过不定时的2个小时直播,完成自家产品的售卖,以较快的速度完成经济资本的转化:
最近的八爪鱼十分肥美,我撇开中间商,直接从渔船上进货。向粉丝们直播运输、包装和进冷库的全过程,同时也直播分享为粉丝们压低价格的经过。八爪鱼被分成500多份包装,在直播期间内“秒没”。(访谈对象S2)
头部主播通过将压价过程全流程地展现,增强了直播间卖货产品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从而能够促使消费者快速下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粉丝的信任和黏性,同时也提高了头部主播的工作和变现效率。
2.中部主播:普遍互惠与信任机制的建立
大众媒介实施的“脱域”与“再嵌入”的双向过程,是安东尼·吉登斯(1998:252)所描绘的晚期现代性的典型特征。社交媒体时代,人们的社会活动彻底摆脱时空的束缚,使得人们能整合超越“在场”的自然与社会资源。当下,乡村主播已经嵌入到数字化工作空间,其工作内容在于网络空间中人际关系的建构与维系。但是网络空间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是基于弱关系形成的浅度信任型社会资本,中部主播要想动员自己的社会资本并获得收益,必须建立适当的互惠规范。帕特南认为,普遍的互惠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因此,在中部主播直播卖货过程中,往往通过互惠机制与信任机制的建立,加强与粉丝之间的信任关系网络的建构。
中部主播在直播时,其直播间内观看的人数一般在300~500人,因其不具备头部主播超高的人气流量优势,所以需要以互惠方式进行资源动员。最典型的是在中部主播的直播间内存在着人情社会中讨价还价的现象。例如主播刚开始以99元10包虾尾起售,直播间内部分粉丝则要求99元12包,带动其余消费者跟风,最后往往以主播的妥协完成买卖双方的交易。这种建立在价格优惠基础上的互惠规范,加速中部主播的社会网络关系资源向经济资本的转换:
有时适当的降价、优惠,能让直播间的受众感受到你的真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产品的成交量,因为大部分顾客都是奔着实惠来的。(访谈对象S6)
此外,中部主播还注重与粉丝之间信任机制的建立。为了建立粉丝对直播间产品品质的信任,打消购买的疑虑,中部主播还在卖货过程中,提供包邮免费试吃的服务:
30包39.9元,我给你们发30包,不好吃退给我27包,其中3包算我免费送给你们试吃的。不好吃免费退,来回运费都算我的。就问你们还在犹豫什么?(中部主播在直播间的实况)
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指出,“每一起商业交易都内在地含有信任成分”。中部主播通过适当让利来获取粉丝的信任,进而使得交换关系可以持续进行,从而促进直播带货的可持续发展(袁宇阳,张文明,2021)。
3.尾部主播:拼时长完成经济资本的积累
如果行为主体没有对社交媒体上的社会关系资源网络倾注一定时间和精力去长期维持,那么由此形成的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就变得微乎其微。在H村,最后入场的尾部主播,对于短视频平台的使用更多是以经济变现为导向。大部分尾部主播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直播卖货实践,既缺乏经验且又多是跟风行为,导致观看人数也很少,主播也潦草应付,经常出现人在直播间却没有声音的现象。比如,不少尾部主播简单地在直播间重复讲解产品与介绍价格,或者将价格表贴在身上,自己低头玩手机完成整场直播。对于这些既缺乏表达能力又缺乏资源优势的尾部主播,更多是选择挂机、拼时长来完成自己的可见性,积累自己的日单交易量。一位尾部受访主播在直播间表示:
每天下午2点直播到晚上11点,一直开着自己的直播间,运气好的时候,有时候能成交1000多单裙带菜,运气差的时候十几单都有。(访谈对象S20)
当平台的注意力资源可以转化成订单量,当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时,资本的力量会不断激励主播延长直播时间,但只是通过加大对平台工作时间的投入,以此来弥补平台社会关系资源的不足,注定无法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社会资本。此种维系虽然能够转化一定的经济资本,但是与头部主播和中部主播相比,其资本转换的效果仍有较大的差距:
我有点播不下去了,每次进直播间的人都很少,还不如好好经营自己的实体店铺。(访谈对象S19)
头部、中部、尾部主播,由于自身在短视频平台上社会资本积累水平不同,致使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效果差异。头部主播凭借对社交平台上关系资源的维系,推动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迅速转化;而中部主播,通过普遍互惠和信任机制的建立,推动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尾部主播由于社会资本缺乏先在性的不足,动员能力弱,其对短视频平台上的关系投资,最终转向资本剥削而非资本增值的轨道。
五、平台下沉与数字乡村新图景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3.08亿,短视频用户规模首次突破10亿,用户使用率高达94.8%,③短视频平台用户量实现了突破式发展。快手短视频平台通过技术赋权,不仅帮助乡村用户实现了传播权利的激活与重塑,而且主动融入乡村振兴的政治话语之中,形成数字乡村新的传播图景。
1.个体重塑:乡村民众的数字化就业
短视频平台作为一种新媒介,在乡村用户的职业转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乡村用户借由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自我展演,进而建构自己的社交网络关系,再结合地方性生产资源的优势,转向直播卖货的数字化实践。短视频平台不仅给乡村民众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乡村民众的职业:
自从三子在快手平台上爆火后,好多人都玩起了快手,现在村里人人都是主播,什么理发师、幼儿园老师,甚至一些大学生都返乡回来在快手上创业了。(访谈对象S10)
在直播带货的热潮下,H村村民们基于对快手主播高收入的向往,越来越多地转向数字化就业。原先赶海的渔民由于冬天气温较冷,出海不容易,开始加入带货主播行列;有些原本是厨师、理发师、幼儿园老师等职业的村民,也积极加入带货主播职业之中。此外,数字化就业还产生了一定的“虹吸效应”,大量外出务工的本地人再次回归乡村。
2.劳动转型:家庭生产方式的重构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家庭是基本生产单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就业机会少且工资低,中国出现了亿万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的现象。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妇女、老人、儿童留守在家,通过家庭合作完成劳动转型。
短视频下乡带来了家庭生产模式的重构。“全家齐上阵”成为H村每一位乡村主播的主要经营模式。青年人作为直播间前台的主播,负责产品的售卖与讲解,而备货、加工、包装、发货这一系列工作则由家中其他成员或邻近留守村民前来协作完成。在电商经济的刺激下,家庭生产方式由以往务农、捕鱼转向经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民们因就业而带来的外向型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空心化现象和乡村“留守儿童”问题:
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带货获得的收入,比我外出打工还要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当然是首选留在家里,顺便可以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访谈对象S11)
3.乡村再造:乡村经济发展的新样式
2021年是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之年,因此,地方行政力量也积极介入乡村主播的直播卖货实践中,并对其进行重点扶持。一方面,当地政府对于乡村主播进行技能培训。由于H村的乡村主播仍只是靠吃播以及以同质化商品售卖的模式吸引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引起了受众的审美疲劳和消费疲劳,部分乡村主播甚至已经出现对于个体社会资本动员乏力的现象。为此,当地政府与外界MCN公司合作,借以提高乡村主播的数字媒介素养,推动乡村主播的专业化发展。另一方面,当地政府积极调动地方性社会资源,利用乡村空间资源优势,积极搭建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人、货、场一体的网红小镇,全面推动数字化乡村发展。H村党支部书记表示:“我希望我们村里的主播不仅仅只是做吃播的主播,也不仅仅只是能卖海鲜的主播,而是像李佳琦这样什么都能卖的全能主播。”可以说,短视频正成为推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农具”。
六、结语
直播带货毕竟是数字时代乡村传播的新生事物,其发展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本文在对主播类型的划分上仍有简单化之嫌,对主播与短视频平台自身调整发展的互动缺乏深入考察。这些都是本文尚存的问题。不过,本文引入社会资本理论视角观照乡村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数字化实践,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也尝试提出三点洞察:其一,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看待乡村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数字化实践,跳脱以往文化研究视角、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于乡村用户的文化展演和乡村主播的劳动分析,从动态视角下勾勒出乡村用户在使用短视频过程中,其是如何通过积累与动员在平台上的社会资本,完成村民——平台内容生产者——平台主播的身份转变;其二,短视频平台已经远远超越纯粹的社交媒体功能,兼具社会与平台资本的双重属性。本文以资本转化为洞察方向,探究乡村主播在网络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资源、占据的位置,以及自身资本的动员能力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转化效果。最后,虽然乡村主播正成为短视频平台的劳动者,并呈现出一定的异化特征,但是数字平台在中国的发展,仍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出了乡村的活力,成为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注释:
①H村:2018年,快手播放量前十名的乡镇中,连云港H村独占鳌头。全村大概有300多位主播,家家户户卖海鲜。每天晚上八九点有上百个直播间开播,2018年H村全镇电商交易额超过3亿。
②环球网:《快手宿华、程一笑上市演讲:坚持为用户和社会创造长期价值》,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0825809145071719&wfr=spider&for=pc.。
③帕特南:《社会资本与制度成功》,https://www.163.com/dy/article/FVR7F8J00519953A.html。
④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1312742418509029&wfr=spider&for=pc。
参考文献
安东尼·吉登斯(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
边燕杰,刘翠霞,林聚任(2004)。中国城市中的关系资本与饮食社交: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开放时代》,(02),93-107。
董晨宇,叶蓁(2021)。做主播:一项关系劳动的数码民族志。《国际新闻界》,43(12),6-28。
快手研究院(2020)。《被看见的力量》。北京:中信出版社。
范英杰,李艳红(2020)。草根全球化、技术赋权与中国农村青年的非洲叙事:对快手平台上三个视频主播的分析。《国际新闻界》,42(11),76-98。
林南(2005)。《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和行动的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斌(2020)。自我与职业的双重生产:基于网络主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实践。《中国青年研究》,(05),61-68。
徐亚萍,李爽(2021)。疾痛身体的媒介化“活力”——对癌症患者社交视频日志的内容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8(07),59-78+12。
袁宇阳,张文明(2021)。社会资本视角下乡村直播带货的困境及其破解。《中国流通经济》,35(10),74-81。
翟学伟(1999)。个人地位:一个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中国日常社会的真实建构。《中国社会学》,(04),3-5。
周敏(2019)。“快手”:新生代农民工亚文化资本的生产场域。《中国青年研究》,(03),18-23+28。
Bourdieu. P (1977).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u, J.X.ZhangY.H.(2022). “Selling Poverty” on Kuaishou: How Entrepreneurialism Disciplines Chinese Underclass Online ParticipationGlobal Media and China0(0) ,1–20.
Lin, N(2001).“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in N.Lin, K.Cook& R. Burt eds.,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pp.3-30),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
Lin, N(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ong C , Pan S L , Newell S , et al(2016)。The emergence of self-organizing e-commerce ecosystems in remote villages of China: a tale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rural development,MIS Quarterly40(2)475-484.
Lin JKloet J D.(2019)Platformization of the Unlikely Creative Class: Kuaishou and Chinese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ion.Social Media + Society(4).
[作者简介]倪小帆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勇(通讯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本文为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中国新闻文体史研究(1921-2021)”阶段性成果(22BXW004)。感谢教育部重大委托课题“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历史演进与学科史研究”(2023JZDZ034)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