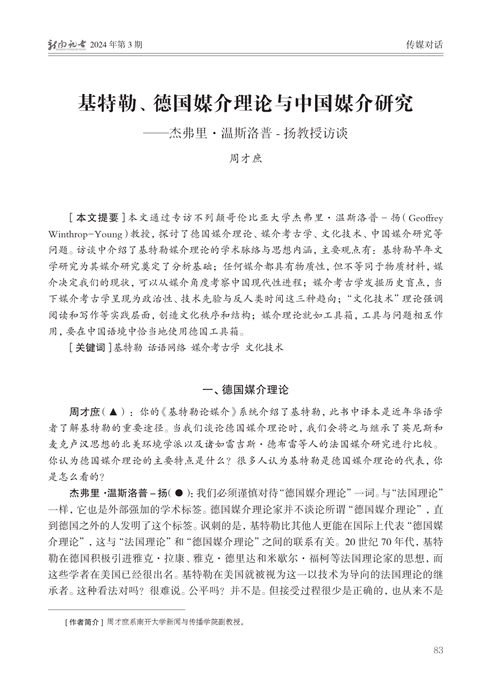基特勒、德国媒介理论与中国媒介研究
——杰弗里·温斯洛普-扬教授访谈
周才庶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专访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杰弗里·温斯洛普-扬(Geoffrey Winthrop-Young)教授,探讨了德国媒介理论、媒介考古学、文化技术、中国媒介研究等问题。访谈中介绍了基特勒媒介理论的学术脉络与思想内涵,主要观点有:基特勒早年文学研究为其媒介研究奠定了分析基础;任何媒介都具有物质性,但不等同于物质材料,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可以从媒介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性进程;媒介考古学发掘历史盲点,当下媒介考古学呈现为政治性、技术先验与反人类时间这三种趋向;“文化技术”理论强调阅读和写作等实践层面,创造文化秩序和结构;媒介理论就如工具箱,工具与问题相互作用,要在中国语境中恰当地使用德国工具箱。
[关键词]基特勒 话语网络 媒介考古学 文化技术
一、德国媒介理论
周才庶(▲):你的《基特勒论媒介》系统介绍了基特勒,此书中译本是近年华语学者了解基特勒的重要途径。当我们谈论德国媒介理论时,我们会将之与继承了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思想的北美环境学派以及诸如雷吉斯·德布雷等人的法国媒介研究进行比较。你认为德国媒介理论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基特勒是德国媒介理论的代表,你是怎么看的?
杰弗里·温斯洛普-扬(●):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德国媒介理论”一词。与“法国理论”一样,它也是外部强加的学术标签。德国媒介理论家并不谈论所谓“德国媒介理论”,直到德国之外的人发明了这个标签。讽刺的是,基特勒比其他人更能在国际上代表“德国媒介理论”,这与“法国理论”和“德国媒介理论”之间的联系有关。20世纪70年代,基特勒在德国积极引进雅克·拉康、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柯等法国理论家的思想,而这些学者在美国已经很出名。基特勒在美国就被视为这一以技术为导向的法国理论的继承者。这种看法对吗?很难说。公平吗?并不是。但接受过程很少是正确的,也从来不是公平的。
▲:除此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因素使得他具有国际影响力?
●:基特勒一直试图解决马歇尔·麦克卢汉已经提出的问题。但是,麦克卢汉的预言来得太早,而他在有生之年并未获得足够学术声誉。基特勒虽然严厉批评麦克卢汉,但他还是在麦克卢汉离开的地方继续前进。
▲:麦克卢汉是媒介研究的重要先驱,他的格言和主张影响了许多人。你把麦克卢汉和基特勒放在一起讲,给了基特勒很高地位。我想,基特勒产生国际影响在于他的研究方式,而不是因为他去了美国传播他的理论。
●:我同意。基特勒不是个谦虚的人,不过他并不像某些法国理论家那样积极地在国外宣传自己。基特勒与美国的联系让他获益匪浅,美国学界认为基特勒理论替代了陈旧肤浅的媒介传播理论。他的国际声誉始于美国,他在德语系的知名度低于英语系和媒介研究系。基特勒理论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始于《话语网络》,真正的突破则是《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这本书比较简单,不那么德国化,探讨了新媒介,其中包含大量英美文献。
▲:许多人认为媒介研究领域诸如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马克·汉森(Mark Hansen)、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等美国学者都受到了基特勒的影响。
●:海勒当然读过基特勒的书,但没有受到直接影响。她的《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写得很好,主要观点是批判把心灵和身体分开的传统人文主义理解方式,如果用哲学化拉丁语来说,就是把res cogitans和rex extensa分开。如果你相信这种本体论上的分离,那么你可能会相信,你可以把你的思想或意识从身体中取出,下载到网络空间,从而成为一个不朽的数字生命——这正是一些硅谷亿万富翁梦寐以求的。海勒说这太天真了,人类意识是具身的,没有与之共同进化并赖以生存的身体,就没有心灵,所以这种分离是无稽之谈。基特勒也会同意这种观点,但他认为这并不重要。
马克·汉森一开始是批评基特勒的,指出基特勒忽视了人的身体。基特勒确实嘲笑过那些在文化批评中迷信身体的人——这么做的人太多了。但如果你现在读马克·汉森的文章,他更倾向于说,基特勒的有趣之处在于,他是最早——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坚决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之一。 我认为,这回答了你关于基特勒在北美影响力的问题。他的角色是避免其他批判性较弱的思想家产生过大影响。不过谁知道呢?中国对基特勒的吸纳和接受也是如此。你不必接受他的所有观点,但是你可能会因为理解了基特勒而对其他理论家更加挑剔。
▲:学界有“基特勒学派”、“基特勒青年”的传说,毫无疑问您是其中重要成员,而且你是英语世界基特勒著作的主要译者。有人说其中主要成员还包括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 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马库斯·克拉耶夫斯基(Markus Krajewski)、诺伯特·博尔兹(Norbert Bolz)、伯恩哈德·多茨勒(Bernhard Dotzler)和科妮莉亚·维斯曼( Cornelia Vismann)等人。你认为这可以形成一个学派吗?关于媒介研究,其中哪些学者值得我们更多关注?
●:这不是一个学派。“学派”一词意味着一致性和连贯性,而不是一群学生说着与导师相似的话。海德格尔有很多学生,最差劲的学生是那些像海德格尔一样思考和说话,却从未说得比他更好的人;最厉害的学生则是以自己的方式出名,像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冈瑟·安德斯(G ü nther Anders)、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尤其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如果没有海德格尔,他们可能不会成为现在的样子,但他们发展了自己的想法,而且其中一些人逐渐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基特勒也是如此。如果你想谈论法律和媒体技术,你可以阅读科妮莉亚·维斯曼(Cornelia Vismann);如果您想研究文化技术,请阅读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和马库斯·尼夫(Markus Krajewski);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对控制论历史做出了精彩分析;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发展了媒介考古学最新最激进的方法。他们曾在某个时候坐在基特勒的研讨课堂上,如果他们不坐在那里,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成为学派,也没让他们成为“基特勒主义者”。
▲:你认为海德格尔是否对基特勒产生很大影响呢?
●:基特勒进入弗莱堡大学时,海德格尔正式退休了,不过仍在弗莱堡。他们没有直接联系,基特勒曾经开玩笑说,他最接近海德格尔的时刻是在洗手间偶遇他。基特勒还说,他认识的一些学生曾求见海德格尔,然后被他的才华击垮,以至于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并退学,这就是他自己远离海德格尔的原因。这些故事是真的吗?我不知道。基特勒年纪越大,就越有编故事的习惯——不过许多故事比无聊的真相更有启发性也更有趣。
海德格尔痴迷于“存在的历史”——德语称之为Seinsgeschichte。人类在世界上经历了不同的存在关系,这些差异源于我们对语言的使用、与语言的关系。海德格尔晚期一直强调我们如何被语言所塑造。语言不只是工具:语言被诉说,如其所是;语言说我,正如我说语言。我说故我在。现在基特勒来了,他说:我同意,但是,除非我们认识到媒介技术和文化技术(特别是调控语言的技术)与不断变化的存在息息相关,否则这一切都含糊不清。简言之,基特勒的目标是更新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说,之于基特勒,语言及其媒介技术才是存在的家园。
●:我首先想到了许煜,他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一书中探讨海德格尔在技术和形而上学之间所关注的古希腊-西方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中国。直截了当地说,海德格尔本体论是否易于传播?他传播得好吗?还是回答你的问题,基特勒旨在调和海德格尔与数学,他会明确指出:能让语言成为存在家园的媒介技术,是能够处理从古希腊元音字母表到当代计算机语言和数字的技术。
二、基特勒与文学研究
▲:基特勒曾在弗莱堡大学攻读德国语言和文学、罗曼语语言文学和哲学,早年教授文学。然而,随着他的作品不断被译介,人们主要将他看作媒介哲学家而忽略了他的文学研究。你认为他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在其媒介哲学中起到什么作用?文学在他的媒介理论中扮演什么角色?
●:是的,基特勒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文学学者的身份起步,但在 1980 年代,他的研究越来越侧重于媒介。有人说他离开文学研究是因为他不再认真对待文学。事实并非如此。基特勒转向媒介研究是因为他觉得既有文学研究无法充分分析文学。请注意,如果不读基特勒早期作品,你就无法完全理解他所说的话。但是他的早期作品并没有全部被翻译出来,因为涉及德国文本,对于非德国人来说,它很难阅读,很难翻译,也不太感兴趣。但在基特勒那里,文学文本意味着文化的适应和书写的形成,它的深层次运作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学方法(无论是诠释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方法)所能把握的范围。要充分理解文学的影响和运作,就必须进入媒介研究。否则,你只是在重复文学的自我言说。简而言之,文学是一种媒介,文学是基特勒进行全面研究的第一种媒介,文学为他日后研究其他媒介确立了分析基础。
▲:基特勒的文学研究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更专注于语言层面?
●:是的,但他关注于文学语言的变化如何在历史上开展与实施。为了理解我们如何被文学所塑造,我们就需要理解这些深层次的变化。毕竟,让我们初次与文字语言相遇的并不是文学,早在我们阅读之前,我们就在听与说了。我们很早就被我们所听到的词语所塑造,它们描述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基特勒的“话语网络1800”有个著名分析,他指出,18世纪末婴儿接触语言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新型资产阶级家庭中,慈爱的母亲教导孩子说话。这极大地改变了语言的作用和影响。语言成为沟通的亲密媒介,它可以解锁一切,因为背后总有母亲舒缓的声音作为允诺。而这正是文学与哲学将语言作为同质、可靠的交流媒介来使用的先决条件。
▲:您刚提到20世纪70年代基特勒研究文学,以及他对18世纪的语言分析,你认为他的观点是否适用于英语世界?
●:《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是他国际化传播最成功的著作。读《话语网络1800/1900》的人要少一些,原因之一就是此书前半部分涉及所谓的“歌德时代”,即1770年至1830年的文学和哲学。美国的英语系不太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美国文学真正始于19世纪中期,因此,大多数美国英语系学者研究1850年以后的文学作品,对于早期文学作品,他们的兴趣就少了许多。
▲:即便歌德是这么一个重要且著名的作家……
●:你上一次读歌德是什么时候?
▲:十几年前吧。
●:那也是因为你比大多数人更热爱文学,并且受教育程度更高。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对许多人来说,阅读基特勒对《德古拉》或《万有引力之虹》等小说的评价要有趣得多。这些小说创作时期较晚,比歌德的任何小说都更具娱乐性,而且充满了现代意味。
至于文学在基特勒的研究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是更实际的答案:你想了解基特勒关于话语网络和媒介技术的奇特理论吗?阅读他的文学案例研究吧。你想了解“话语网络1800”的秘密吗?阅读 E.T.A.霍夫曼的著名故事《金罐》,然后阅读基特勒在《话语网络》中对该故事的解读吧。你想了解“话语网络1900”中新型模拟媒介的作用和影响吗?阅读《德古拉》,然后阅读基特勒对这部小说的解读吧。你想了解20世纪不断变化的声音技术的影响吗?听听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暗面》,然后阅读基特勒对歌曲《大脑损伤》的分析吧。
▲:基特勒《话语网络1800/1900》一书的主要主张是,文学、哲学和科学是内在关联的,它们受到19世纪新技术和媒介的强烈影响。基特勒强调了媒介的物质性,以及媒介在意义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您如何解释基特勒所说的媒介物质性?
●:所有媒介都具有物质性。问题是,物质性的消失或凸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媒介信息的存储、处理和传播。媒介在最不被注意的时候最有效——当我们把它们视为中性的、顺从的、无形的工具时,它是最有效的。
▲:我近来读一些美学家的论文,它们在讨论艺术媒介时,时常把媒介看作是物理材料,只把媒介视作工具。
●:这是天真的工具主义。基特勒攻击过这些论点。伟大的加拿大媒介理论先驱麦克卢汉与伊尼斯也攻击过,当然还有海德格尔。让我回到你关于文学的问题。当我说英语“tree”、德语“Baum”、法语“arbre”或中文“树”时,这些词只是符号,与我谈论的任何一棵树都有任意关系。但是,如果我用数码相机给一棵树拍照,那么这个图像就是物理效应。光从树上反射,与感受层产生反应,留下树木的痕迹。这种图像似乎比“树”这个词更真实或者说更接近真实的事物,这很关键,它将改变人们对“树”这个词的理解与使用。照片本身并不是现实的,但是它为“现实主义”确立了新的层次与标准,这会影响词语在文学文本中的呈现方式。于是,基特勒说,这对于理解文学实践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
▲:索绪尔说“能指”与“所指”,新技术与新媒介改变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我想打断一下,索绪尔很棘手。这也是基特勒很少谈及索绪尔的一个原因。让我们记住,能指与所指的差异不是符号与真实事物的差异。能指是一个任意的声音图像,而所指是我们对树形成的心理图像。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共同构成了符号。以基特勒和其他许多人的批判眼光来看,这发生在没有真实事物的情况下,而这正促使了包括德里达在内的所谓后结构主义的哲学演进。但是基特勒“话语网络1900”的整体思想是,像照相机、留声机等模拟媒介与真实事物的物质性有一种索引式关系——它们存储了事物的真实痕迹(参考符号学家皮尔斯,而不是语言学家索绪尔)。
▲:媒介的物质性如何影响了基特勒对于文学的历史化考察?这又如何影响到你提到的有关“现实主义”的观念?
●: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塞斯·雅各布维茨(Seth Jacobowitz)有本有趣的书《明治日本的书写技术》(Writing Technology in Meiji Japan)。雅各布维茨经常提到基特勒,这是有道理的。这是关于日本的基特勒式的分析。事实上,雅各布维茨是在日本做研究时第一次听说基特勒的。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它开启了 19 世纪末日本的现代化进程。雅各布维茨解释说,其中一个关键在于引入新的书写和记录技术,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日语的身份及其社会化结构。其基本目的是创造统一民族使用的共同语言,主要的创新之一是新的速记书写系统(日语中为“sokki”),它最初是为行政目的和转录政治演讲而引入的。很快,新的留声媒介技术引入,它在忠实记录语音方面更胜一筹。早在明治时代,日语中就有一句标语“utsushitori shisutemu”,表达了“如实记录”的意思。翻译成德语,非常接近 aufschreibesysteme——字面意思是“写下来的体系”,当然这也是基特勒《话语网络》的德语原名。这些新的誊写和记录技术,所有这些“如实记录事物”的想法,很快就影响到文学领域,并引发了现实主义观念。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被不断变化的记录和存储设备促成和定义的。现实主义是媒介生态变化的结果。
▲:在中国“现实主义”也是重要议题,在你所说的语境下,“现实主义”具体怎么
讲呢?
●:假设你讲授中国现实主义的课程,比如讲鲁迅。如果问学生“什么使得鲁迅成为现实主义作家”?这是不够的。问题应该是:“假如我们承认鲁迅是现实主义作家,那么为什么之前的作家不够现实主义?20世纪初,中国语言生态发生了什么,使得鲁迅区别于其他作家?”当然,中国不是日本,中国没有这种在短时间内引发社会、政治、文化和媒介技术剧变的明治维新。基特勒会说,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出现并不需要一边与技术和物质,一边与教育和话语的变化相结合,或许只有后者发生了变化。
▲:中国文学具有“现实主义”的漫长传统。20世纪初我们产生“新文化运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语言革命,就是说,文学语言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家。你的解释提供了独特而有意义的视野。那么,回到基特勒,他认为媒介不只是物质材料。
●: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经常被忽略。假如基特勒只谈论硬件和媒介设施,他可能就真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所说的,是技术决定论者。但他不是。我们刚说到“歌德时代”、“话语网络 1800”,即人们学习说话和写作的新方式,它取代了基特勒称为“学者共和国”的早期话语网络,但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媒介技术变革。相比之下,“话语网络1900”与新型模拟技术的发明以及打字机带来的书写机械化有关。同样,德川时代与明治维新之间的差异也涉及许多技术变革,包括从旧式木版雕刻到现代排版印刷的转变。但在 1770 年前后,当“话语网络1800”取代“学者共和国”时,却没有发生任何类似的变化。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但我们的处境可以在媒介硬件不变的情况下发生巨大变化。
▲:基特勒说“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这是他最出名的句子。
●:是的,很多人引用这句话,但没有人引用完整的句子:“媒介决定了我们的现状,是受之影响,抑或避之影响,都值得剖析。”(Kittler,1999:xxxix)请看后半句。虽然媒介决定了我们的现状,但我们仍然要剖析它。我们可以从外围观察。回到你关于文学作用的重要问题上,对基特勒来说,这是我们必须研究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基特勒完全同意麦克卢汉的著名观点,即媒介有一种麻醉作用,当我们沉迷其中就不再真正注意到它。文学就成为一种陌生化途径,打破媒介对人的麻醉,因为在新媒介发展早期阶段,文学文本描绘了新媒介的所有希望与恐惧。这些早期文学文本揭示了媒介认识论和经验论领域中的利害关系。因此,回过头来看早期现实主义文本,与其说它们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是荒诞主义的,因为它们书写了伟大的新幻想,好像事情果真如此。一言以蔽之,这些文本展示了现实主义有多么荒诞。
三、法兰克福学派
▲:约翰·杜伦·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说:“基特勒的作品不应与诠释学或法兰克福学派混为一谈,后两者广为流传,但如果你认为基特勒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觉得技术理性会导致堕落,那就大错特错了。”(Kittler,2010:2)您认为基特勒与德国诠释学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是否存在继承或反叛的学术关系?基特勒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文主义传统不同,基特勒是否摒弃了以人为核心的人文主义
传统?
●:彼得斯说得对。基特勒喜欢攻击法兰克福学派。我们都读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产业”的分析。基特勒认为这种论述是无知的表现,因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媒介一无所知。在这本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写到了荷马和奥德赛,基特勒又认为他们无知,因为他们对荷马使用的希腊元音字母表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不会说希腊语!但基特勒之所以如此批判,也许是因为两者有潜在的相似。阿多诺关注我们以何种方式被资本主义文化产业制度所诱惑与规训;基特勒关注的是我们以何种方式被媒介-技术体制的话语秩序所奴役与驯服。两人都声称找到了我们被欺骗的根源,但只有一人是对的。
诠释学也是如此。基特勒与伴随他成长的诠释学传统虽不协调,但又颇为相似。诠释学在文本之外解释微妙而隐蔽的途径,揭示真理与文本意义;基特勒则在文本之中解释微妙而隐蔽的途径,分析真理的效果。但公平地说,基特勒在法兰克福学派和诠释学那里都学到了很多。
▲:基特勒吸收的理论资源多样而复杂,有人认为他深受福柯知识考古学、德里达书写理论、拉康主体概念和香农信息论的影响。有人曾这样评价您:“杰弗里·温斯洛普-杨(Geoffrey Winthrop-Young)是英语世界中对基特勒最敏锐的评论家,他称基特勒为‘身着战斗服的伊尼斯’”(Kittler,2010:6)。您认为哪种哲学学派对基特勒影响最大?
●:让我们再次抛开“学派”这个成问题的术语。如果说哲学影响,那么最重要的人就是海德格尔,当然还有黑格尔。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种联系更有启发性。在某种程度上,基特勒的媒介理论改写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看看基特勒最后十年推崇的叙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种符号系统,即希腊元音字母表,它能够编码语言、数学和音乐数据。这个原始的统一体逐渐瓦解,各种艺术和媒介发展出了自己的符号系统。辩证地看,这种差异使它们逐步数学化和技术化。在阿兰·图灵的脑海中,数字处理方式重新统一了各种媒介格式。第一步:统一;第二步:差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专业化;第三步:更高层次的统一。
当然,两者有很大差异。对黑格尔来说,人类心灵(生活在对的时间与对的国家,即 1830 年前后的普鲁士)是绝对精神观察世界并达到自我认识的特权场所。在基特勒眼中,你我都太渺小、太迟钝、太肤浅,无法成为有效的平台。我们充其量只是暂时的占位者,自然与精神的伟大融合将在数字机器中实现,而我们将被远远抛在后面。
当然还有以德里达、福柯和拉康为首的所谓法国哲学家。尽管基特勒有时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德里达”,但他并没有从德里达那里借鉴很多——事实上,他批判德里达。他从福柯和拉康那里学到很多。他从拉康那里学到语言的主体性,我指的是双重意义上的主体,它使你隶属于主体,又让你成为主体。更戏剧化的是,它通过把你变成主体来使你成为隶属者。拉康是结构主义者和精神分析师,他很少关心时间、政治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和教育体制。这成为福柯的切入点。基特勒从福柯那里了解到,存在着不断变化的认识论、不同的真理体系、不同的话语条件,它们决定了可说与不可说、睿智与愚蠢。基特勒的贡献在于将他们结合起来:我们有不同的认识论,也就是他所说的话语网络,基于不同的媒介条件和传播物质性,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将你主体化。如果结合福柯和拉康,加之以媒介理论基础,这是描述基特勒最辉煌时期的学术的最快捷方式。
四、媒介考古学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提出了一种历史性地理解知识发展的方法论。你提到基特勒从福柯那里学到了很多,基特勒也被说成是媒介考古学的理论家。能否请您阐释一下“媒介考古学”?
●:这是个复杂的话题。首先,基特勒并没有称自己是媒介考古学家。自称为媒介考古学家的人也没有把基特勒称为真正的媒介考古学家。其次,我相信理论家很难对“媒介考古学”的含义达成一致看法。再次,我隐隐怀疑许多人使用这个词是因为它听起来比“媒介历史”更酷、更前卫、更复杂——尽管在我看来,他们所做的仍然是媒介史。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考古学”这一术语与“媒介”结合在一起时所蕴含哲学的和反向的含义。
让我从头开始解释。你听到“考古学”这个词。你会联想到什么?也许是几个人拿着铁锹站在挖掘现场,凝视着罗马神庙或秦始皇兵马俑的遗迹。现在请仔细看看这个场景。考古学涉及从过去到现在的物质痕迹。过去和现在相互冲突和融合,文物的发掘打破了我们在特定时间内对事物逐一进行排序的规整方式。不同时期突然相遇、彼此共鸣,而不再被时间清晰地区分。借用瓦尔特·本雅明的观点,此时此地可能是我们可以直接理解过去的时刻,因为后一个时刻已经在希望或绝望中伸出援手。但是,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那一刻的联系将永远消失。
从这个角度理解,考古学不是历史学。相反,它是这样一个概念——挑战我们如何将时间塑造成历史的传统方式。哲学一点说,考古学凸显了历史的盲点。仅仅知道术语的含义是不够的,你还需要知道这个术语反对的是什么。在我们的语境中,考古学是一个反向概念,它对历史的批判是其意义的一部分。
▲:这个解释很有意思,“考古学凸显了历史的盲点”。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记得一些重要事件,却忘记了许多细节。考古学不仅意味着记忆,也意味着遗忘。考古学回溯人类的记忆和遗忘,它是过去通往当下的路径。当我们将考古学与媒介联系起来时,会发生什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指出,媒介考古学并不是考古学第一次脱离原初语境,与另一门学科结合。这种情况最早出现在哲学中。事实上,就像思想史上许多真知灼见一样,媒介考古学的根源与一个人相关,他是一位心怀不满的德国哲学家,坚信自己是对的,其他人都是错的。1790 年代初,伊曼纽尔·康德看到了由普鲁士学院赞助的征文比赛,讨论“形而上学历史”的最新进展。康德记下了一些想法。在他看来,形而上学和哲学是不受时间或实证推理影响的永恒理性结构,但历史恰恰相反。他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哲学考古学”——正如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在一篇妙文中所描述的。康德是第一个针对历史使用考古学一词的人。
▲:康德在《逻辑学》中说:“每一个哲学思想家都是在别人的废墟[auf den Trümmern]上建立自己的作品”,“人们不能学习哲学,是因为它还没有被给予”。康德可能没有想到,两百年后,一种媒介理论会以他的“哲学考古学”概念为基础。
●:康德可能没有想象过媒介考古学,但他会理解媒介考古学,因为他对历史的基本反对意见依然存在。更不用说福柯的考古学变体也与康德的认识论有关。
目前,媒介考古学有三种突出倾向。第一种更具政治性,关注被忽视、遗忘、排斥和压制的古老媒介技术,希望挖掘和复盘这些技术。例如,他们关注非西方媒介,并问:它们在消失之前的历史是怎样的?他们审视那些看似突然出现的媒介,比如19 世纪的模拟技术,并问:它们真的那么新吗?以前就没有出现过吗?所有被遗忘的前者都在哪里?为了让现在显得如此伟大,有多少过去被抹掉?这有点像审视曾经失败的抵抗运动,或者像从被压迫群体的角度重写历史。他们通过提供另一种微观考古学和技术反历史来纠正官方历史的不公正。尽管这些批判性故事可能具有反叛性,但它们非常符合既定的历史学范式。赢家和输家会变,但故事结构不会变。
第二种是继承福柯的媒介考古学。在福柯看来,考古学与探索起源的矛盾概念有关,他称为“历史先验”(historical apriori)。“先验”意味着某些东西从一开始就是既定的,它在事物开始之前就存在,并设定了基本条件,“历史”意味着它是在时间中成长和变化的东西。基特勒来了,说道:很好,但这种历史性先验必须被更清楚地解释为一种技术性先验,它在一定制度持续期间设定了运行的技术条件。这也是对传统历史理解的挑战和违抗。但你可以看到这与康德的潜在联系:康德理性认识论的永恒先验变异为话语规则的历史先验。
第三种是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提出的最为激进的媒介考古学。“激进”一词表示一种非-人类或反-人类的机器时间,它与人类历史更为矛盾。比如,你用电脑来记录我们的实时对话,它按照机器时间运行。如果我们的对话足够有趣,它可以在1000年后的这个时间重放。它不仅显示未来面对此刻的物质痕迹,而且体现机械时间与人类时间的冲突。我们面对机器时间的传输和操控。我们把一段时间从历史中抽取,随后又再次置入。未来需要机器让你的这台机器运作起来,就像你现在需要数字工具来加强19世纪老式留声机中的模糊录音一样。因此,媒介本身就是考古。
这三种媒介考古学的变体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和重叠之处,应该把它们看作是连续体中特别突出的部分。但基本范畴还是你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即这个词的反向意义。这种考古学针对的是什么?历史。媒介考古学传递的主要信息是:历史太重要了,不能留给历史学家。虽然为了对历史学家公平起见,有些人会争辩说媒介考古学跟不上历史学方法论的最新进展,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我有时觉得,21世纪媒介考古学主张是以 19 世纪的历史写作方法为前提的。
五、文化技术
▲:有人说万物皆媒介。这样就使得媒介这个术语在严格的学术分析中显得庞大且模糊,一些德国媒介理论家由此转而研究“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iques)。基特勒是如何谈论“文化技术”的?
●:这里有好几层意思。“文化技术”的德语原词是 Kulturtechnik,它是德语中著名的复合名词。一个词融合了两个领域,尤其是在德语中,这两个领域彼此相距甚远。一方面,我们有“文化”——音乐家莫扎特、贝多芬和作家歌德的高雅世界;另一方面,我们有“技术或科技”——科学和工程的冰冷实用世界,传统上被视为与文化相对抗的。现在,这两者放置在一起,结果是相互借鉴:文化被技术化,技术被文化化。基特勒当然对此深有体会。
“文化技术”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他20世纪 80 年代初的著作中,比如在他有争议的学位论文《话语网络》中。据我所知,他在教育学语境下初次接触到这个词。20世纪50年代末,人们把说、写、读称为“基本文化技术”,当时它的定义是能够获取、保存和传播文化的行为。你可以看到正在发生什么:现代社会,理解文化是以操作和实践为中心,而不是以内容和价值为中心。
现在,基特勒策略性地使用了这个术语。这一术语使得他那些有争议的论点更容易被学术界所接受,因为这是对已有概念的再次使用,而不是那些难以理解的、华而不实的法语术语。不过,这一点还远不及其他方面重要:谈论文化技术,需要关注阅读和写作等实践层面,它们在“读者”和“作者”的身份出现之前实现了具体化和客观化。这个术语宣示着把各种想象结构分解为潜在操作,而这正是当今文化技术理论的标志。尽管如此,基特勒并没有非常突出地使用这个术语,但你可以感觉到,他在使用这个观念,并用它来对抗他自己的独特术语:媒介。
▲:我想你不认为基特勒是技术决定论者,正如你所写的:“谴责基特勒是技术决定论者,一方面,对他煽动性言论做出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这却是通过揭露他人的偏见来掩盖自己的偏见。”(Winthrop-Young,2011:15)
●:我之前提到,基特勒做出了一些历史性分析,这显然不是技术决定论的。再强调一下,话语网络1800并不涉及任何技术变革,这里没有新的硬件、新的工具,它归结为文化技术的彻底变革。我认为技术决定论的指控是无知和错误的,也是无端和自私的。
从历史上看,对技术决定论的指控源于对经济决定论的类似指控。在美国语境下,它始于20世纪初人们开始担心一些经济理论,它们声称经济是一切的基础,如果我们解决了经济问题,一切都会迎刃而解。这种经济决定论演变成了技术决定论。现在,技术支配和统治着一切。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正确编程将解决气候危机。
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廉价的道德批评。如果你指责某个人是技术决定论者,会让自己显得正确。这是一种堕落的行为,没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还记得以前的苏联共产党吗?当他们想谴责别人时,就称他们为“形式主义者”: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形式主义者,但这是一个方便的标签,表示道德沦丧和良知缺乏。因此,在我看来,关于技术决定论的指责,只能体现出使用这个词的人的懒惰无知。
六、中文语境中的基特勒
▲:我们来谈谈中文语境中的基特勒。有时候我会想,英文或中文语境中的基特勒还是德国的基特勒吗。1993年,中国已出现对“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简要介绍。不过基特勒著作中译本2017年才出版,你的《基特勒论媒介》中译本则是2019年出版的。近年来,关于基特勒的论文越来越多。你如何评价中国的“基特勒热”?
●:我不了解,难以回答,还是应该由你来回答。中国理论家为什么读基特勒?
▲:我想这是一种“理论旅行”,原因很复杂。中国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落后于发达国家,如今中国更好地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经历着重要的媒介演变,每个普通人都参与其中,体验媒介演变带来日常生活的变化。知识分子也热衷于媒介相关问题。
●:你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媒介理论在特定国家的情况及其重要性与该国经历的媒介技术变革有关。如果这些变革是突如其来的,或是在长期拖延之后才发生的,或是为了弥补以前错过的变革,那么它的影响就会特别大,而且有可能是灾难性的。让我们以日本为例。日本历来在媒介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我认为,在媒介理论方面,曾经有一段很长时间,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就像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一样。请记住,尽管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德国和日本在19世纪晚期共同经历了快速、令人不安的现代化进程,这也是1930年代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这种加速的现代化与突然出现的新媒介结构密切相关,也与保留下来的旧有社会结构相关。这两个国家都在技术上先进,在社会上保守。我认为,战后媒介理论(尤其是基特勒理论)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和技术这种奇怪的脱节现象。如果你对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对基特勒的兴趣就与这样一种猜想有关,即只有对媒介采取足够激进的态度,才能探究媒介创新带给中国的深层变化。
▲:我要说,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与19世纪末德国、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截然不同。首先,中国文化不是外向型、侵略型的。儒家思想就强调仁义礼智,追寻和平生活。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近70年。郑和下西洋时,中国与沿路国家开展贸易,但没有占领领土。其次,中国已经经历了 100 多年的现代性进程。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与西方国家相似,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再次,中国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其他思想资源。我们在进行媒介理论研究时,一方面基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实,另一方面吸收欧美媒介思想。回到基特勒,学者对基特勒理论的热情,显在原因可能是他在美国受欢迎,而且他继承了欧洲的学术传统,随后便在中国流行起来。
●:同意。分析现代电子技术的起源,或战争和军事在媒介演变中的作用时,基特勒这样的人很重要,但我们能否提出更具体的原因或策略呢?冒着自取其辱的风险,让我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基特勒是一位激进的媒介间性理论家,是辨识前后情景差异的理论家。在你们的历史中选择一个时间点或边界,尝试从不同的媒介技术体制角度,分析这一时间之前和之后的差别。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模拟媒介技术来查看相关变化。用基特勒的话说,就是中国的“话语网络1900”是何时出现的?但需要提醒一点:不要重蹈覆辙,不要把100年前的中国视为脆弱的媒介生态,把西方媒介技术当作入侵物种,杀死了所有本地野生动物。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来面对这些相遇,而这些方式是由该国之前的媒介历史来决定的。要理解你说的第四次革命,就要看看之前的革命——换句话说,要对革命进行媒介考古。
其次,縄田雄二(Yuji Nawata)曾建议我们像基特勒看待希腊元音字母那样看待中国文字。中国文字当然不是元音字母,但它们都是多功能的。这也是基特勒对希腊元音字母如此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它曾被用来抄写单词、数字和音调。这种多功能性一度丧失,直到我们开发出数字处理代码后才重新出现。现在,基特勒会问,能否在中国写出一部计算机编程考古学,取代或绕过通常的西方历史,在中国文字和现代数字技术之间建立联系?基特勒当然会补充道:第一个功能齐全的二进制系统是什么?是《易经》卦画的断断续续的线条。谁是最早了解《易经》的欧洲人?哲学家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当时做了什么?他提出了一种可以记录一切的数字代码。
▲:当前,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中国新媒体产业发展得很快。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各种形式的自媒体非常活跃,这深深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交流方式、审美经验和日常生活,同时也给传统文学艺术带来挑战。这与基特勒分析的19 世纪和20世纪的媒介状况有所不同。此外,人工智能、ChatGPT 和大型语言模型迎面而来,面对21世纪的数字技术革命,您如何看待基特勒媒介理论对这些现象的阐释力?
●:我常常想,基特勒会对ChatGPT和大型语言模型说些什么。他很可能会责备我们重复使用二进制,把人类的文字创造性与算法驱动的文字机器对立起来。什么是大型语言模型?它是一台学习算法的机器,能够使用超大数据库识别、总结、翻译、预测和生成内容。这难道不就是对讲述者的精准定义吗?
请记住,基特勒痴迷于现代社会的伟大理论梦想,寻找能够有效且系统地决定文本和言辞的生成规则,就像语音、语言和句法规则决定声音、单词和句子的生成。这不正是他迷恋福柯的真正原因吗?福柯《事物的秩序》分析了言语的秩序,它确定了正式规则下话语的有效性和意义,它控制了已经说出的与本可以说的话之间的关系。青年基特勒认为,福柯盲目地叩击香农的信息论之门,但他缺乏跨过这道门槛的数学专业知识。归根结底,福柯式的话语制度或基特勒式的话语网络不过是更大的语言模型。
更激进的说法是:有了ChatGPT,书面语言终于独立了。现在,语言揭示其操作原则,而无需在人类大脑和嘴巴那里绕道。而你我只是更小的机器。比起ChatGPT,我们读得更少,说得更慢,书写方式也过时了,但是拯救人类的还是人类的观念,人类观念与其控制劣势能力不如受制于高超技术。我并不同意这种诊断,但这是很好的出发点,借此对媒介文化进行冷静分析,减少人文主义妄想的危害。
至于脸书、抖音或微博,基特勒几乎没写过什么关于社交媒体的文章(他对社交媒体不屑一顾)。总的来说,他不喜欢预测事物。根据他的理论,我们被话语秩序所塑造,我们无法知道当这些话语秩序发生变化时会发生什么。此外,根据基特勒的观点,我们的社会革命已经被机器所取代,我们怎么能知道它们会走向何方呢?
福柯喜欢把他的书形容为工具箱。这听起来是毫无害处的比喻。这里有锤子、扳手、螺丝刀,你需要什么就拿什么。你不需要全部用上,有些可能永远用不上。首先,确认你的问题。有颗钉子冒出来?那就拿起锤子。这是一个新奇的工具箱,在中国房间里使用德国工具箱。你必须做两件事:你还是得看看自己的房间,决定哪些地方需要修补 。你还必须看看这些新工具,想想它们能修什么。现在,关键点来了:对这些工具并不熟悉,你可能会意识到未曾知道的问题;这些德国工具并不是为中国房间设计的,你可能会以它从未被使用过的方式来使用它。工具与任务,或媒介与信息之间存在着持续复杂的相互作用。问题决定工具,但工具也决定问题。这不正是媒介理论的真正开端吗?■
参考文献:
JacobowitzSeth. (2015)Writing Technology in Meiji Japan: A Media History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Visual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ttler, Friedrich. (1999).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TransGeoffrey Winthrop-Young and Michael Wutz.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ittler, Friedrich. (2010). Optical Media. Cambridge: Polity.
Winthrop-Young, Geoffrey. (2011). “Krautrock, HeideggerBogeyman: Kittler in the Anglosphere.” Thesis Eleven, 107(1): 6-20.
[作者简介]周才庶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