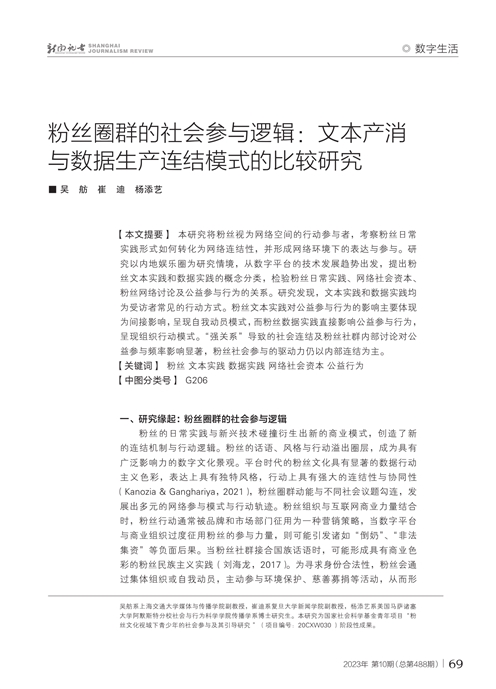粉丝圈群的社会参与逻辑:文本产消与数据生产连结模式的比较研究
■吴舫 崔迪 杨添艺
【本文提要】本研究将粉丝视为网络空间的行动参与者,考察粉丝日常实践形式如何转化为网络连结性,并形成网络环境下的表达与参与。研究以内地娱乐圈为研究情境,从数字平台的技术发展趋势出发,提出粉丝文本实践和数据实践的概念分类,检验粉丝日常实践、网络社会资本、粉丝网络讨论及公益参与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文本实践和数据实践均为受访者常见的行动方式。粉丝文本实践对公益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间接影响,呈现自我动员模式,而粉丝数据实践直接影响公益参与行为,呈现组织行动模式。“强关系”导致的社会连结及粉丝社群内部讨论对公益参与频率影响显著,粉丝社会参与的驱动力仍以内部连结为主。
【关键词】粉丝 文本实践 数据实践 网络社会资本 公益行为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研究缘起:粉丝圈群的社会参与逻辑
粉丝的日常实践与新兴技术碰撞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创造了新的连结机制与行动逻辑。粉丝的话语、风格与行动溢出圈层,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数字文化景观。平台时代的粉丝文化具有显著的数据行动主义色彩,表达上具有独特风格,行动上具有强大的连结性与协同性(Kanozia & Ganghariya, 2021),粉丝圈群动能与不同社会议题勾连,发展出多元的网络参与模式与行动轨迹。粉丝组织与互联网商业力量结合时,粉丝行动通常被品牌和市场部门征用为一种营销策略,当数字平台与商业组织过度征用粉丝的参与力量,则可能引发诸如“倒奶”、“非法集资”等负面后果。当粉丝社群接合国族话语时,可能形成具有商业色彩的粉丝民族主义实践(刘海龙,2017)。为寻求身份合法性,粉丝会通过集体组织或自我动员,主动参与环境保护、慈善募捐等活动,从而形成粉丝驱动的网络公益力量。
传统研究视角更多将粉丝文化理解为一种文本中心的实践——粉丝通过文本消费与生产共享意义、建构身份、建立情感性联系(Fiske, 1992),进而获得群体内部的连结性力量 (Zhang, 2016)。中国粉丝研究者将费斯克、詹金斯等学者的论述作为重要理论资源,将粉丝视作具有文本创造力与网络连结性的青年文化群体,将粉丝文化与公共生活建立联系,探讨粉丝的社会参与潜力(陈昕,2018)。新近的粉丝研究则强调粉丝文化的数据行动主义特征,认为粉丝将平台的算法和数据原则内化成一种新的情感寄托物和话语游戏(Yin & Xie, 2021),通过共同参与平台实践形成连结性。综合以上两个视角,本研究通过概念化文本实践逻辑与数据实践逻辑,理解粉丝群体连接性的形成机制,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法,探究粉丝的文本实践和数据实践与粉丝社会参与动员机制的关系。
本研究的创新意义在于将粉丝理解为通过文本实践(作为读者的粉丝)与数据实践(作为平台用户的粉丝)形成多元连结方式、基于多元的行动逻辑嵌入文化公共空间的网络圈群。既往研究多将粉丝实践理解为“文本/阅读”关系或建立情感性联系的过程,文本实践是相对传统的粉丝参与方式,即粉丝通过阅读各类符号性资源获得意义与愉悦的过程,包括关注偶像的音乐、剧集或粉丝生产的同人作品、讨论等。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数字平台的数据化策略和算法文化视角出发,界定了粉丝数据实践的概念,将数据实践定义为平台环境下的新行动方式,指粉丝通过生成、制造可见的平台数据建立关系、参与粉丝社群的形式,包括轮博、控评、打榜、投票等。我们量化测量了粉丝的文本实践与数据实践,为量化研究粉丝的多元实践提供了方法基础。实践层面,既往研究多从粉丝社群内部出发分析社群运作及自我组织机制,此类研究区隔了粉丝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本研究将粉丝群体看成网络空间的参与者,同时关注粉丝在圈群内部和外部形成的连结,考察粉丝文化与整体公共生活的关联。情境层面,我们以内地娱乐圈为研究情境,考察数字平台时代粉丝实践的变迁。内地娱乐工业日臻成熟,市场及受众边界逐渐清晰,“内地娱乐圈”(简称内娱)这一概念随之形成。“内娱”粉丝群体热衷消费本土生产的娱乐内容,追随在大陆发展的偶像艺人,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符码、实践方式和价值认知,成为重要的网络文化景观。内娱的商业运作逻辑与数字平台时代的内容生产方式耦合,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因素深度绑定,构成了粉丝社会参与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个案。
二、理论框架:粉丝实践、连结性与社会参与
(一)平台时代的粉丝实践变迁:数据生产与文本产消并存
经典粉丝研究沿袭文化研究脉络,重视粉丝的文本实践——即粉丝与各类流行文本的卷入过程,强调粉丝在接收、阅读、改写与创作媒介文本过程中产生的意义。文化研究学者强调流行文化粉丝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体现在对文本的解读与创造性使用的过程中。例如,费斯克将粉丝群体看成“过度的读者(excessive readers)”(Fiske, 1992),强调粉丝在文本实践中体现的“文本生产力”。詹金斯强化了“文本盗猎”的实践(Jenkins, 1992),看重粉丝在挪用与改编流行文本的过程中展现的巨大创造力。由此可见,既有研究普遍强调粉丝实践的文本中心属性。随着传播技术环境的变迁,以数字平台模式为代表的新信息组织模式正在重塑流行文化生产(Nieborg & Poell, 2018)。过去十年内,中国大陆娱乐工业逐渐成熟,粉丝群体迅速扩张,个人网站等小规模网络社群无法承托巨量的粉丝群体,一批功能各异的商业互联网平台(如新浪微博、Bilibili、乐乎等)开始成为粉丝日常活动的主要空间。在平台机制的中介下,粉丝实践出现了两方面彼此联系的变化。
首先,社交媒体的出现促使粉丝文本实践的外延扩张。传统媒体时代的粉丝研究聚焦粉丝与媒介文本之间的关系。影视剧、音乐、流行文学等文本作为粉丝消费、阐释、挪用以及再创作的对象,被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粉丝通常被理解为媒介文本市场的 “产消者”。研究者将是否投入同人文、粉丝自制影片等文本产制与消费作为粉丝的界定标准(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然而,在Web 2.0时代,粉丝交谈经过社交媒体中介,形成参与对象更广泛的、非即时性的参与式消费,粉丝交谈等类文本实践与粉丝文本创作的边界变得模糊,成为粉丝文本实践的一部分(Hills, 2013)。此外,后现代的流行文化消费有轻叙事而重要素的趋势,是为“数据库消费”,角色的魅力由类型化的外貌、性格等要素特征构成,可以轻易脱离原作故事,被挪用、拼贴、重组,流通于不同的文本乃至粉丝的想象(Azuma, 2012),文本的叙事不再仅限于故事的讲述和呈现,而是关于一个文化社群所有知识的总和 (Booth, 2016)。在此背景下,内娱粉丝的文本实践的外延大幅扩张,除了官方产制的文本和粉丝创作的同人作品之外,还包括大量以娱乐偶像为中心的“社交媒介文本”,例如明星自行发布的社交媒体信息、明星工作行程信息、粉丝在社交媒体的讨论等。
与此同时,数字平台环境下的粉丝实践具有数据化的趋势,成为与文本实践并行的粉丝日常实践。自2005年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的粉丝聚集于百度贴吧以来,商业互联网平台逐渐取代个人网站和论坛,成为粉丝圈群文化实践的主要虚拟空间,平台技术的发展和文化实践的变迁相互形塑(吴舫,2020)。数字平台作为当下的技术文化基础设施,其主要特征为收集、管理和计算用户数据的能力。数据化是数字平台商业模式的核心策略,即通过捕捉、计算用户互动和行为痕迹,将其转化为信息商品,形成精准信息投放的依据并以此牟利(Van Dijck, Poell & De Waal, 2018)。在数字平台环境下,平台机制和粉丝实践相互收编,平台通过策略性的功能设计和规则制定,将粉丝自发、松散的媒介实践转化为结构化的、可见的数据,形成基于“算法文化”的粉丝实践数据化(Data-ization)趋势(Yin, 2020)。数字平台基于算法的广告信息投放规则使粉丝、经济公司、艺人与文化管理部门同时与平台机制互动,共同管理和塑造数据流动,形成以平台数据为中心的多元复杂的循环模型(Zhang & Negus, 2020)。粉丝在平台生成可见的数据,为偶像的商业价值明码标价,微博热搜、微博超话排名、签到数、豆瓣讨论量、知乎浏览量等数据被跨平台收集和分析,作为品牌寻找商业合作的量化依据;品牌出售商品时,会设置销量比拼等数据规则,督促粉丝投入更多金钱、时间和情感(吕鹏,裘然然,2022)。粉丝有理由相信,粉丝集体的数据贡献与偶像的事业发展息息相关,粉丝在与偶像的关系中获得了更强的话语权,甚至与偶像发展出更紧密的“类亲缘关系(parakin relationship)”(Yan & Yang, 2020)。这使得粉丝有更强的驱动力将“做数据”视为日常实践的一部分,具体包括打榜、控评、轮博、反黑等以评论、转发、点赞、回复、举报等功能影响内容排序和可见性的重复性集体行为。
从宏观文化工业变迁角度来看,这样的趋势暗合了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与西莉亚·卢瑞(Celia Lury)指出的表征形式的“物化”(拉什,卢瑞,2010),即文化中符号体系逐渐增强可操作性(operationality)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对粉丝的分析不仅需要从文本接收或解码的角度出发,更需要关注物质性实践的方向。互联网世代的粉丝数字劳动既包括同人创作、同好交流等“参与式劳动”,也包含点击、浏览、投票等以制造流量数据和信息商品为目的的“数据劳动”(高寒凝,2022)。据此,我们试图概念化与粉丝文本实践并存的粉丝数据实践,用以描述粉丝以数字平台的算法逻辑和数据化运营规则为基础,以在数字平台生产可见的、可量化的流量数据(而非创造式地消费官方或粉丝产制的媒介文本)为目的的日常实践。虽然在广义的定义中,媒介文本属于数据的一部分(范·迪克,2021),本研究中数据实践的概念聚焦于打榜、轮博、控评、反黑等粉丝基于对数字平台算法规则的摸索与想象影响可见性数据的日常实践。
(二)网络粉丝群体的连结性:社会资本、网络讨论与社会参与
粉丝不仅通过平台技术形成社会网络,产生信息交流,也通过共同的“热爱”和审美体验,形成基于文化生产、情感和仪式的多维凝聚力(胡岑岑,2018)。因此,本文重点关注粉丝在数字平台空间的连结性。在传播学文献中,连结性并非一个完善的概念,在不同研究中的所指存在差异。很多时候,研究者将连结性理解为个体用户借由移动设备或社交工具所获得心理上的临场感或情感联系(Lai, 2014)。本研究将连结性定义为粉丝借助网络化的日常实践形成的彼此关联。我们将粉丝连结性操作化为网络社会资本、网络讨论以及公益活动参与三个层面。网络社会资本反映了连结性的结构关系维度,粉丝网络讨论与公益活动参与则指向连结性的行为后果。
社会资本指个体或群体通过行动在社会网络中获取的资源(Lin, 2001)。社会资本对社会参与具有积极作用。当一个社群积累较多社会资本时,社群会更加团结,成员间更加信任,更容易参与公共活动(Putnam, 2000)。互联网社群成员之间频繁交流,在虚拟空间中形成纽带,因而生成基于网络关系的社会资本。基于Ellison, Steinfield和 Lampe(2007)的经典研究,本文将社会资本区分为结合式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与桥接式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两种形式。其中,桥接式社会资本与人际关系中的“弱连接”相关,通常可以为个人提供新的信息或观点,但较少涉及情感支持。而结合式社会资本则来源于“强关系”,除了基本的信息交换,还包含情感性的关联。
人际网络讨论是青年群体获得公共事务知识和社会参与机会的重要方式(崔迪,2019)。基于认知中介模型,网络上的人际讨论可以帮助青年群体整合接触到的信息,结合自己以往的知识和经验,将信息转化为公共事务知识,形成观点,提升社会参与的自我效能和动机(Eveland & Hively, 2009)。粉丝的网络讨论可分为社群内部讨论和与一般社交媒体用户的网络讨论。以往研究认为,两类网络讨论都有促进社会参与的潜力,但影响机制不同。作为社交媒体用户的粉丝在网络讨论中,能接触到比日常生活中的社交网络异质性更强的讨论群体、更广泛的讨论议题、更多元的社会参与方式,从而提升社会参与的可能性(Xenos, Vromen & Loader, 2014)。而粉丝在基于趣缘形成的相对紧密的社会网络中,更容易受到社会参与积极成员的影响,学习他们的参与方式,通过增加集体层面的政治效能感提升社会参与动机(Velasquez & LaRose, 2015)。
社会参与是公民参与的一个维度,是与选举、政治运动等显性政治参与相对的、非显性的参与类型,主要包括慈善捐款、志愿服务、参与公益活动等(Adler & Goggin, 2005; 王新松,2015)。社会参与可被视为政治参与的前提,公民个体通过参与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表达对社会事务的关切,对政治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王新松,2015)。粉丝群体虽然因参与“饭圈出征”等政治行动受到广泛关注,但粉丝日常实践中的公民参与潜力主要体现在非政治或半政治性的社会参与层面。在粉丝研究情境中,粉丝公益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参与行动,本研究将粉丝的社会参与行为作为粉丝连结性的后果,考察粉丝的群体动能转化为社会动能的潜力。
社会资本、网络讨论和社会参与是粉丝日常实践的结果。早期粉丝研究基于“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的概念,分析粉丝通过共享文本阅读、意义生成的规则形成的连结 (Fish, 2004)。在数字平台环境下,粉丝面对更加多元且复杂的文本来源,没有单一的力量能够决定粉丝消费的文本构成。个体粉丝试图进入追星的符号世界,通常需要借助社交关系和平台算法推荐构建文本流。例如,粉丝会关注偶像本人、明星个站、大V粉丝等重要的微博账号,刷微博“超话”,加入社交媒体粉丝群,从同辈群体中获取源源不断的信息。一方面,粉丝在创制和消费粉丝文本的过程中,形成共通的情感与审美经验,构建和维系网络社区(胡岑岑,2018)。另一方面,粉丝在日常实践中会通过后援会、官方粉丝群、自发组建群组等形式,聚集散落的粉丝,实现个体粉丝间的协作互惠。此外,数据实践亦是粉丝组织网络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粉丝的数据实践通常需要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庞大粉丝群体共同完成(童祁,2020)。一般情况下,粉丝数据组是结构性较强的粉丝组织,数据组核心成员会根据不同任务情境制定数据策略、分配任务、激励数据组成员、验收数据结果等。粉丝在平台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实践与偶像及其他粉丝形成了一种新的联系方式,进而形成网络社会资本。
粉丝通过日常实践形成的网络连结性能否转化为参与动能,在公共空间协同表达或行动,是粉丝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费斯克和詹金斯认为,在融合文化环境下,粉丝的文本创造性可能形成集体智慧,并有机会转化成社会参与(Jenkins, 2006)。Van Zoonen认为粉丝的社群结构、情感结构与行为模式都与政治参与群体有相似性(Van Zoonen, 2004)。张玮玉结合社交媒体理论、网络社会理论及行动者网络理论,从“关系”和“网络”的角度把握公众,进而将粉丝群体与公众的概念进行勾连(Zhang, 2016)。基于此,本研究将粉丝群体建构为具有参与潜质的公众,以疫情期间粉丝的公益活动参与行为及相关网络讨论作为粉丝社会参与的案例,分析中国内地网络粉丝群体的日常实践、网络社会资本、网络讨论及社会参与间的关系。基于以上文献概念,本研究探索如下研究问题(分析框架图1 图1见本期第75页):粉丝的文本实践是否会影响其网络社会资本、公益相关网络讨论与公益活动参与?粉丝的数据实践是否会影响其网络社会资本、公益相关网络讨论与公益活动参与?粉丝的网络社会资本是否会促进粉丝的公益相关网络讨论与公益活动参与?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方法
本研究结合网络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收集粉丝日常实践、网络社会资本和新冠疫情爆发期间粉丝的网络讨论以及公益活动参与数据。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在豆瓣小组、微博超话等粉丝聚集的社交媒体平台和微信、QQ粉丝群发放问卷链接,邀请粉丝参与填答。问卷发放时间为2020年2月13日至14日,共回收有效问卷816份。受访者平均年龄23.10岁(SD = 4.88)。其中女性764人,占93.6%。据艺恩调研数据,娱乐粉丝画像中女性占86%,问卷样本特征符合粉丝群体女性为主的人口学特征(艺恩数据,2021)。受教育程度众数和中位数均为大学本科或专科(n = 622,76.2%)。深度访谈采用目的抽样法,以参与和组织过粉丝公益活动为抽样标准,通过粉丝聚集的社交媒体平台和粉丝在线社区招募共计20名受访者。作者对2名男性与18名女性粉丝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时间为2022年9月至10月,以语音电话或面对面的形式进行,每次访谈时间为40分钟到1.5小时不等。
(二)测量
问卷调查基于归纳逻辑,从疫情期间对粉丝公益行为(philanthropic behaviors)的新闻报道中,总结出捐助行为(捐赠金钱、捐赠物资)、组织协调行为(筹款、募集物资)、信息扩散行为(向亲人朋友分享、评论或转发粉丝社群中相关信息)和监管行为(监管自己所在粉丝社群的公益行为、监管其他粉丝社群的公益行为)等8个题项。问卷要求参与者回答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项公益活动的参加次数(0 = “0次”,1 =“1次”,2 = “2次”,3 = “3次”,4 = “4次”,5 = “5次”,6=“6次及以上”)。该变量作定序变量处理,公益参与行为变量值为8个题项的均值(Cronbach’s alpha = .87,M = 2.07,SD = 1.15)。其中,15.1%的受访者(n = 123)在疫情爆发到接受访问期间,从未参与过公益活动。
网络讨论(online discussion)的测量使用七级量表(1 = “从不”,7 = “非常频繁”),题项改编自Eveland和Hively(Eveland & Hively, 2009)以及Kwak,Williams,Wang和Lee(Kwak et al., 2005)关于政治讨论的研究。测量粉丝社群内部讨论的题项包括“与粉丝群中的其他粉丝讨论疫情”、“在粉丝群中转发疫情相关的信息”、“浏览粉丝群中的疫情相关信息并发表观点”(Cronbach’s alpha = .93,M = 2.68,SD = 1.86),测量粉丝与其他互联网使用者间的网络讨论的题项包括“在网络上发表自己对疫情的观点”、“ 网络上对疫情相关内容进行评论”、“ 在网络上转发疫情相关内容”以及“在转发疫情相关的内容时加以自己的意见或评论” (Cronbach’s alpha = .90,M = 3.47,SD = 1.68)。
本研究测量了粉丝的结合式网络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桥接式网络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测量量表来自Williams(Williams, 2006)以及Skoric,Ying和Ng (Skoric, Ying & Ng, 2009)关于网络社会资本的研究,测量使用七级量表(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测量结合式网络社会资本的题项包括“当需要做重要决定时,有些网上的朋友可以给我建议”、“ 我在网上认识的人会帮助我争取正义”、“ 我可以信赖一些网上的朋友帮我解决问题”、“ 我可以跟一些网上的朋友自在地讨论私人问题”、“ 当我感到孤单时,我可以找到一些网上的朋友倾诉”(Cronbach’s alpha = .91, M = 3.62,SD = 1.60)。测量桥接式网络社会资本的题项包括“与网上认识的人交流,我感到融入了更广阔的生活图景”、“与网上认识的人交流,我对不一样的想法感兴趣”、“与网上认识的人交流,令我想尝试新鲜的事物”、“与网上认识的人交流,我意识到世界上人和人都是彼此相连的”(Cronbach’s alpha = .93, M = 4.48,SD = 1.67)。
我们通过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总结出12项常见的粉丝日常实践行为,作为研究中的变量测量题项。我们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数据降维,识别粉丝日常实践的基础类别。因子分析前的KMO检验和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p < .001),KMO值大于.08(KMO = .88),表明问卷具有结构效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在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筛选原则下,正交旋转后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粉丝的12项日常实践被提取为两个因子(见表1),分类符合本研究对文本实践与数据实践之定义。其中,粉丝文本实践包括“听偶像的音乐”、“ 观看偶像参与的综艺节目”、“ 观看偶像参演的电影、电视剧”、“看偶像的照片资源”、“ 关心偶像的行程和安排”、“ 阅读粉丝的讨论帖子”、“ 阅读同人文/图”(Cronbach’s alpha = .81,M = 5.02,SD = 1.27),数据实践包括“为偶像轮博(转发微博)”、“控评”、“反黑”、“打榜或投票”、“制造播放量”(Cronbach’s alpha = .88,M = 3.50,SD = 1.69)。
本研究控制的人口学变量为性别(二分类变量)、年龄、受教育程度(1 = “小学及以下”,2 = “初中”,3 = “高中或中专”,4 = “大学本科或专科”,5 = “硕士研究生”,6 = “博士研究生”)。此外,考虑到受访者日常公益行为习惯对疫情期间公益行为参与的可能影响,本研究控制了受访者在粉丝社群之外的日常公益参与行为频率(七级量表,1 = “从不”,7 = “非常频繁”, M = 3.21,SD = 1.76)。
四、研究发现
(一)粉丝实践的基本描述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表2 表2见本期第75页),粉丝最常参与的文本实践类型为“看偶像的照片资源”(M = 5.82,SD = 1.61),最不常参与的文本实践类型为“阅读同人文/图”(M = 3.56,SD = 2.26)。受访者文本实践以偶像照片与偶像参与生产的文本为主,作为粉丝参与式消费重要形式的同人作品,并不是受访者文本消费的主要对象。在各类数据实践中,受访者最频繁参与的是“打榜/投票”(M = 4.18,SD = 2.01),最少参与的是“控评”(M = 3.09,SD = 2.10)。内容平台通常将“打榜/投票”结果与明星的名次、曝光度直接关联,促使粉丝提高对平台的使用频率和经济投入,这可能是受访者数据实践的主要动因。
(二)粉丝实践对网络社会资本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阶层线性回归方法,检验受访者文本实践和数据实践对两种社会资本的影响(表3 表3见本期第76页)。分析结果发现,粉丝的文本实践和数据实践均与粉丝的社会资本显著相关。文本实践(β= .28, p < .001)和数据实践(β= .12, p < .01)均能显著影响受访者的结合式网络社会资本(文本实践:β= .28, p < .001;数据实践:β= .12, p < .01)和桥接式网络社会资本(文本实践:β= .35, p < .001;数据实践:β= .09, p < .05),其中,文本实践的影响效应值均大于数据实践。
(三)粉丝实践、网络社会资本对网络讨论的影响
以网络讨论为因变量的阶层线性回归结果显示(表4 表4见本期第76页),文本实践(β= .12, p < .001)和数据实践(β= .09, p < .05)均与受访者的粉丝社群内部讨论显著相关,文本实践的影响效应值大于数据实践。两种粉丝实践中,仅有数据实践显著影响社群外部网络讨论(β= .09, p < .05)。文本实践可以显著影响粉丝在社群内部对疫情相关话题的讨论,而数据实践对两种网络讨论形式均有影响。
结合式网络社会资本和桥接式网络社会资本均能显著影响粉丝在社群内部(结合式:β= .32, p < .001,桥接式:β= .11, p < .05)和外部(结合式:β= .14, p < .01,桥接式:β= .12, p < .05)的网络讨论频率。其中,结合式网络社会资本的影响效应值均大于桥接式社会资本。可见,互联网中获得的“强连接”更能促使受访者参与网络讨论。
(四)公益行为参与的影响因素
在816位受访者中,123人从未在疫情期间参与过公益行为,公益行为参与变量值在0处聚集,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本研究对公益参与行为变量做数据转换处理,先使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受访者是否在疫情期间参与公益行为的影响因素,再对参与公益行为的子样本进行阶层线性回归分析,探究公益行为参与频率的影响因素(表5 表5见本期第77页)。
逻辑斯蒂回归中,Hosmer-Lemeshow模型拟合度卡方检验结果不显著,说明模型拟合度在可接受范围。分析结果发现,粉丝社群外部的疫情相关网络讨论会增加受访者参与公益行为的可能性(Exp(B)= 1.27, p < .001),而粉丝社群内部讨论未见显著影响(Exp(B)= 1.13, p > .05)。在网络讨论加入回归模型后,结合式网络社会资本与桥接式网络社会资本均未显著影响受访者在疫情期间参与公益行为的可能性。在网络社会资本与粉丝网络讨论加入回归模型之后,数据实践对受访者是否参与公益行为仍有直接影响(Exp(B)= 1.30, p < .001),而文本实践的影响已不显著(Exp(B)= 1.13, p > .05)。阶层线性回归结果显示,粉丝社群内部(β = .32, p < .001)与外部(β = .08, p < .05)网络讨论均会显著影响公益行为参与者的参与频率,粉丝社群内部讨论的影响效应值更大。与二元逻辑斯蒂回归结果类似,在网络讨论加入回归模型后,两类网络社会资本均未显著影响公益行为参与者的参与频率。而在网络讨论和网络社会资本加入回归模型后,数据实践仍对公益行为参与者的参与频率有直接影响(β = .22, p < .001),而文本实践的影响已不显著(β = .00, p > .05)。
(五)粉丝公益参与行为的多元驱动机制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粉丝文本与数据实践频率对公益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第一,文本实践和数据实践频率均与粉丝的社会资本显著相关,但文本实践的影响效应值大于数据实践。第二,文本实践频率较高的粉丝更多参与社群内部的公益相关讨论。第三,在回归模型中引入社会资本和网络讨论之后,文本实践的影响完全被社会资本和网络讨论中介,而数据实践对粉丝公益参与的可能性和频率仍有很强的直接影响。可见,在本研究中,社会资本与网络讨论解释了粉丝文本实践频率与其公益参与行为的相关性,但并不能有效解释数据实践对公益行为的影响机制。粉丝并非通过单一模式形成社会参与动员,粉丝圈群社会参与逻辑具有多元特征。本研究通过访谈发现,粉丝的文本实践会以相对松散的形式促进粉丝公益参与的自我动员,而数据实践自上而下的组织模式会被应用于动员粉丝参与公益活动,呈现组织行动模式的特征。
1.文本实践与自我动员模式
我们通过访谈发现,粉丝文本实践对社会参与的影响机制体现出连结式自我动员的特征。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使用者会受社交网络好友的态度和行为等外部因素影响,出于获得同侪认可、积累社会资本等目的,形成社会参与的自我动员。在数字平台时代,官方产制文本的中心性下降,粉丝在商业社交媒体平台聚集,消费、分享和讨论粉丝产制的视频、照片、同人作品等,粉丝文本实践与网络社会连结的建立紧密相关。这种连结过程不依赖严密的组织结构,粉丝站子、后援会管理人员、文本产出者以及在圈群内部具有影响力的大粉通常是重要网络节点。粉丝在日常实践中,通过这些重要节点获取供消费的文本,而在自然灾害等社会事件发生时,这些重要节点会成为社会参与过程中的意见领袖。而普通粉丝通过发送、接收、编辑、再创作信息,共同参与关于社会议题的叙事和情感表达,这种连结过程具有自发性、多元性和碎片化的特征。如受访者桃子提到,在特定情境中,她会使用作为“大粉”的社会资本,“根据当时情况写文案,比如号召大家和我们一起贡献爱心,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我作为)大粉可以起到这种号召的作用”。而粉丝出于获得他人认可、顺应社群规范等外部因素,自发参与公益活动,“跟风或者效仿去捐款”(受访者z)。可见,粉丝在消费媒介文本和泛文本过程中,能够通过重要网络节点,获得并进一步传递参与社会讨论和公共事务的机会,以相对松散的方式,形成社会参与的自我动员。
此外,公益行为亦可成为粉丝文本叙事的一部分。访谈过程中,受访者m提到,偶像明星杨超越具有好运的公众形象,被称为“锦鲤”,其相关轶事、图片、表情包作为强势模因文本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粉丝会在社交媒体向杨超越许愿,如愿望达成,即向杨超越粉丝站或后援会发布的公益链接捐款,作为“还愿”。核心粉丝、边缘粉丝和被称为“路人”的社交媒体用户通过模因文本消费共同完成“锦鲤”的叙事,并将公益行为作为模因传播的一部分,实现自我动员。
2.数据实践与组织行动模式
数据实践对社会参与的影响特征与文本实践不同。本研究通过访谈发现,粉丝的部分公益活动参与由粉丝组织通过数据实践完成集体动员,呈现出组织行动模式的特征。社会参与的组织行动模式表现为由具有共同身份、目标的组织通过整合和分配资金、人力、文化和社会网络等资源进行的参与动员。我们从访谈中发现,在一些特定情境中,粉丝后援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组织筹款,以实现特定的公益
目标。
粉丝公益参与的行动组织模式与平台的数据化运营逻辑有关。在日常实践中,粉丝组织通常自上而下统筹人员,利用粉丝对偶像的支持,内化平台设置的游戏规则,如数据、排名和曝光量等,激励粉丝自愿参与集体的数据行为,以达到粉丝所追求的清晰目标,最终验收成果。在统一目标的号召以及高效的组织管理下,从“打投”、“控评”、“轮博”、“反黑”等数据实践活动到粉丝公益等社会实践活动,粉丝群体形成强大的行动力。公益捐款的成果也会被视为一种可见的数据表现,直接受数据实践动员影响。如受访者茉莉提到,“我了解到每年微博明星的排行都有各种指标,公益数据也是指标。我觉得其实也是为了给爱豆做数据,公益也是一种数据”。在疫情期间,粉丝会以偶像的名义为疫情严重地区的居民和医务人员集资捐款和募集物资,公益行为结果会以数据形式呈现,作为偶像声誉的积累和粉丝群体组织能力的体现。如受访者z在访谈中表达,“我做粉丝公益还有一方面就是希望在跟别的明星做比较的时候,希望我们是拿得出手的”。
五、结语
随着数字平台成为新的传播基础设施,粉丝群体深度嵌入互联网平台,发展出了区别于“文本产消”的“数据惯习”——一系列以生产流量数据为目的而组织实践的原则。在数字平台时代,文本产消和数据惯习共同构成了粉丝社群连结性的新来源。据此,本研究在粉丝行动主义的网络逻辑基础之上,提出粉丝社会参与的多元行动逻辑。文本实践和数字实践对粉丝网络连接性的影响存在差异,粉丝社会参与受不同连结机制的驱动。
从文本实践角度而言,社交媒体、视频平台等数字媒介为粉丝提供了虚拟互动空间,在网络平台中,粉丝因共同兴趣聚集,形成线上类缘网络(online affinity networks),粉丝在其中交流信息,交换资源,相互提供情绪与社会支持,在此过程中,粉丝将获取的知识、素养转化为社会参与机会(Ito et al., 2019)。文本实践创造的连结性更具情感性与认同性,作为文本产消者的粉丝基于对偶像的崇拜和群体认同自发参与社会公共活动,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低,大量的普通粉丝作为情感公众进行日常实践。
从数据实践角度而言,互联网平台通过功能设计迎合粉丝的实践需求,粉丝在获得专属的技术空间同时,也贡献更多数据和流量,为平台所利用。部分粉丝将数据化逻辑内化为文化参与的底层逻辑,将社会参与作为数据实践的结果,以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方式实现集体层面的参与。在此行动逻辑之下,粉丝公益成为数据结果,是粉丝“竞争性”的游戏及“情感性”的体验的副产品。数据实践带来的连结性并非自下而上生成,而是自上而下地由平台及粉丝经济模式传递给粉丝群体,数据实践促成的连结性意义与感情成分相对稀薄,因而显得更加“目标导向”,但是这种相对机械的连结具有更严整的结构和更高的动员效率。
不管是文本实践还是数据实践,不管来源于情感意义还是市场逻辑,所生成的连结性都指向粉丝之间实存的关联,如分析所示,这些关联可以转化为一定的社会资本并形成社会讨论。在平台环境下,粉丝群体的连结性源于复杂的技术、商业、文本的多元互动。尽管来源不同,粉丝连结性作为一种结构力量,可以指向不同的目标。当市场相关者过度利用这种连结性时,可能引发负面的行动后果;当连结性接合对社会公众有益的目标时,则可能产生正向积极的行动力量。
最后,本研究存在如下不足。第一,本研究作为初探研究,目的仅为测量粉丝实践、网络社会资本和社会参与的情况,初步描述变量间关系。研究在概念和操作层面简化了文本实践和数据实践的关系,将其视为粉丝实践的两个不同类别。然而,在现实中,这两类实践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例如,粉丝观看偶像的节目视频,也是制造播放数据的实践。后续研究需进一步探索文本与数据实践的区别与联系。第二,本研究使用目的抽样,在多个社交平台和粉丝群发放问卷,在保证抽样目的的同时尽可能确保样本的多样性,但是非随机样本的本质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可扩展性,本研究的主要发现需谨慎向样本之外的群体推广。第三,本研究以“内娱”粉丝为主要研究对象,虽然研究样本全部来自内地重要的社交媒体平台及粉丝社群,但不排除存在少量关注“内娱”之外偶像的粉丝。此外,本研究中女性样本占比偏高,后续研究需优化抽样方法和样本结构。第四,本研究为减轻受访者的认知负担,将因变量公益参与行为设置为定序变量,而非定比变量,未来研究可通过询问公益参与具体次数改善测量方法,提高测量效度。■
参考文献:
陈昕(2018)。情感社群与集体行动:粉丝群体的社会学研究——以鹿晗粉丝"芦苇"为例。《山东社会科学》,(10),37-47。
崔迪(2019)。作为媒介效果的公共事务知识获取与信息效能——一项基于高校学生的调查。《新闻大学》,(3),85-100+119-120。
高寒凝(2022)。“数字劳工”们的战争:“饭圈”乱象与互联网时代的偶像工业生产机制。《文艺理论与批评》,(4),163-174。
何塞·范·迪克(2021)。《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晏青、陈光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海龙(2017)。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27-36。
吕鹏,裘然然(2022)。从示范到失范:偶像与粉丝的互动及其治理。《新闻记者》,(8),13。
胡岑岑(2018)。网络社区、狂热消费与免费劳动——近期粉丝文化研究的趋势。《中国青年研究》,(6),5-12。
斯科特·拉什,西莉亚·卢瑞著(2010)。《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要乐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童祁(2020)。饭圈女孩的流量战争:数据劳动,情感消费与新自由主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73-80。
王新松(2015)。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概念辨析与理论解读。《浙江学刊》,(1),204-209。
吴舫(2020)。“何以为家”?商业数字平台中的同人文写作实践研究。《中国青年研究》(12),30-37。
Abercrombie, N.& LonghurstB. J. (1998). Audience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London: Sage.
Adler, R. P.& Goggin, J. (2005). What do we mean by “civic engagement”?. Journal of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3(3)236-253.
Azuma, H. (2012). Database animals. In ItoM.OkabeD.& TsujiI. (Eds. ). Fandom Unbound: Otaku Culture in A Connected World (pp. 30-67).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ooth, P. (2016). Digital fandom: New media studies. Switzerland: Peter Lang.
Edwards, B.& McCarthy, J. D. (2004). Resources and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In: Snow, D. A.SouleS. A.& Kriesi, H. (Eds. ).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pp. 116-150). Oxford: Blackwell.
Eveland Jr, W. P.& Hively, M. H. (2009). Political discussion frequencynetwork size, and “heterogeneity” of discussion as predictor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9(2)205-224.
FishS. (2004).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In J. Rivkin & M. Ryan (Eds. ).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2en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Fiske, J. (1992).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fandom. In L. A. Lewis (Eds. ).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pp: 30-49). London: Routledge.
Hills, M. (2013). Fiske’s ‘textual productivity’ and digital fandom: Web 2. 0 democratization versus fan distinction. Participations, 10(1)130-153.
Ito, M.Martin, C.PfisterR. C.RafalowM. H.SalenK.& WortmanA. (2019). Affinity online: How connection and shared interest fuel learning.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enkins, H. (1992).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Jenkins, H. (2006).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Kanozia, R.& Ganghariya, G. (2021). More than K-pop fans: BTS fandom and activism amid COVID-19 outbreak. Media Asia, 48(4)338-345.
KwakN.Williams, A. E.Wang, X.& LeeH. (2005). Talking politics and engaging politics: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uctural features of political talk and discussion engagem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1)87-111.
Lai, C. H. (2014).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untangling mediated connectedness with online and mobile media.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120-26.
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ieborg, D. B.& PoellT. (2018).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eorizing the contingent cultural commodity. New Media & Society20(11)4275-4292.
PutnamR. D. (2000). Bowling Alon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SkoricM. M.Ying, D.& Ng, Y. (2009). Bowling online, not alone: Online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4(2)414-433.
Van DijckJ.PoellT.& De Waal, M. (2018).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 Zoonen, L. (2004). Imagining the fan democrac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1)39-52.
Velasquez, A.& LaRose, R. (2015). Youth collective activism through social media: The role of collective efficacy. New media & society17(6)899-918.
WilliamsD. (2006). On and off the’ Net: Scales for social capital in an online er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1(2)593-628.
Xenos, M.Vromen, A.& Loader, B. D. (2014). The great equalizer? Patterns of social media use and youth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three advanced democracie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7(2)151-167.
Yan, Q.& Yang, F. (2020). From parasocial to parakin: Co-creating idols on social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23(9)2593-2615.
Yin, Y. (2020). An emergent algorithmic culture: The data-ization of online fando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3(4)475-492.
Yin, Y.& XieZ. (2021). Playing platformized language games: Social media logic and the mutation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s in Chinese online fandom. New Media & Societyonline first.
Zhang, Q.& NegusK. (2020). East Asian pop music idol produ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data fando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3(4)493-511.
Zhang, W. (2016). The Internet and new social formation in China: Fandom publics in the mak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吴舫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崔迪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杨添艺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传播学系博士研究生。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粉丝文化视域下青少年的社会参与及其引导研究 ”(项目编号:20CXW030 )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