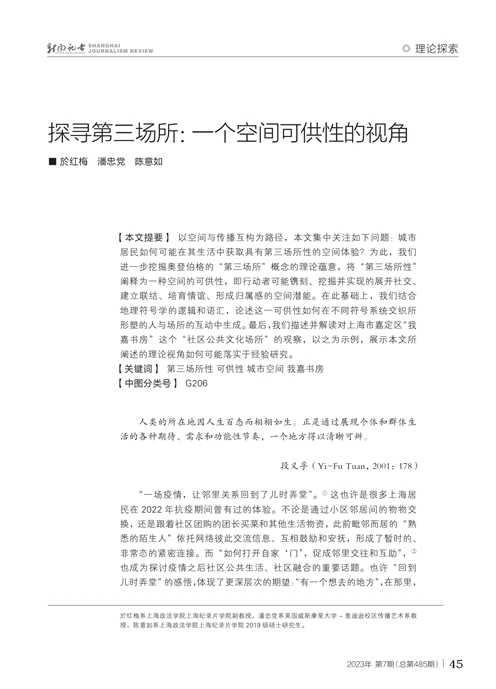探寻第三场所:一个空间可供性的视角
■於红梅 潘忠党 陈意如
【本文提要】以空间与传播互构为路径,本文集中关注如下问题:城市居民如何可能在其生活中获取具有第三场所性的空间体验?为此,我们进一步挖掘奥登伯格的“第三场所”概念的理论蕴意,将“第三场所性”阐释为一种空间的可供性,即行动者可能镌刻、挖掘并实现的展开社交、建立联结、培育情谊、形成归属感的空间潜能。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地理符号学的逻辑和语汇,论述这一可供性如何在不同符号系统交织所形塑的人与场所的互动中生成。最后,我们描述并解读对上海市嘉定区“我嘉书房”这个“社区公共文化场所”的观察,以之为示例,展示本文所阐述的理论视角如何可能落实于经验研究。
【关键词】第三场所性 可供性 城市空间 我嘉书房
【中图分类号】G206
人类的所在地因人生百态而栩栩如生。正是通过展现个体和群体生活的各种期待、需求和功能性节奏,一个地方得以清晰可辨。
段义孚(Yi-Fu Tuan, 2001:178)
“一场疫情,让邻里关系回到了儿时弄堂”。①这也许是很多上海居民在2022年抗疫期间曾有过的体验。不论是通过小区邻居间的物物交换,还是跟着社区团购的团长买菜和其他生活物资,此前毗邻而居的“熟悉的陌生人”依托网络彼此交流信息、互相鼓励和安抚,形成了暂时的、非常态的紧密连接。而“如何打开自家‘门’,促成邻里交往和互助”,②也成为探讨疫情之后社区公共生活、社区融合的重要话题。也许“回到儿时弄堂”的感悟,体现了更深层次的期望:“有一个想去的地方”,在那里,可以与人自在交往、相互支持并从中获得身心的愉悦和生活的信念。③
对这类地方的构想,贯穿于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城建规划当中。④这是一类嵌入城市生活的空间,它们通常是开放、休闲和自由交往的场所,有别于家居和工作场所,被社会学家们称为“第三场所”(third places)。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Ray Oldenburg, 1999)甚至称它们为都市日常生活中“绝好的地方”(great good places),因为在那里,人们可以脱离家和工作的结构性束缚,放松心情,愉快交往。
显然,一座城市需要打造一些第三场所。但是,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第三场所的作用应当不限于用来辨析空间类别,而在于可以作为一个理论视角,分析人与行动场所的动态关联,以及其中蕴含的人们展开行动的广泛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应关注城市空间的“第三场所性”(the third-placeness)(Calderon,2016)。借用美国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 2015)的语汇,⑤就是发掘不同形态的城市空间——实体或虚拟的——如何生成特定类型的“可供性”(affordance),也即激发居民展开社交、建立联结、培育情谊、形成归属感的潜能。
作为一个阐释概念,第三场所性概括了空间某些属性及其生成和呈现。这其中既包括物质维度的空间生产,即城市规划和建设,也包括空间使用者将特定空间转换为行动情境的建构。采用美国人类学家塞瑟·洛(Setha Low, 2009)的说法,第三场所的生成和呈现,关涉空间的社会生产和建构这两个相互交织的过程。因此,对它的考察不能局限于描述实体空间的物理特性,并以之判断它是否为第三场所,而是要呈现第三场所性如何得以表达并实现,以捕捉其中人与场所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空间与人的行动互构视角下,场所不局限为背景或容器(曾旭正,2010),而是表意的文本,在霍尔意义上的编码和解码(Hall, 1980)社会过程中,展示出其意义生成的潜力。如此展开的经验分析,既需要解读构成场所的“空间文本”(spatial text)(Ravelli & McMurtrie, 2016),也需要通过田野观察和访谈,理解空间使用者如何解读这文本,建构其意义并从中获取身心体验。
因此,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城市居民如何可能在其生活中获取具有第三场所性的空间体验?⑥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解析第三场所的理论概念及其运用,在此基础上,阐释“第三场所性”,探讨它如何体现为一类空间的可供性,如何展开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借用地理符号学(geosemiotics)的分析视角、方法和语汇(Scollon & Scollon, 2003),探寻这种可供性如何得以表述、解读并落实。最后,本文以上海社区公共图书馆“我嘉书房”作为示例,展示本文所阐述的理论视角如何可能落实于经验研究。
一、作为理论棱镜的“第三场所”
“场所”并非文化地理学中place概念的唯一中文译名;不同中文译名,体现不同理论意涵(曾旭正,2010)。本文落脚于经验层面,关注人的行动和体验,解析其中的空间性和物质性,因此采用“场所”这个译名。场所有多种呈现和被体验的形态(Tuan, 1977/2001),而且生成于和其他实体的互动中,在不同物质实体、意义和实践这三者共同作用、相互联系和不断协商与转换中形成(Cresswell, 2009:170-174),因此,场所具有多样、流动和关系的特性(Massey, 1994:117-124)。考察场所,也就需要采纳一个基于过程、动态的框架,强调人的行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行动场所之间的关系。来自都市社会学的“第三场所”概念即是如此,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连接。
(一)“第三场所”概念的提出及其历史场景
奥登伯格和布里塞特(Oldenburg & Brissett, 1982)提出“第三场所”这个概念时,针对的是与城市化相伴的各种社会连接衰退的病症(malaise),也是对二战后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批判。在奥登伯格看来,这种发展模式强调经济效益,专注于发展高速公路网络、封闭的摩天大楼、私密化的私人住宅、不断扩张的郊区;它无视空间使用者个体间非正式的、随时相遇和“纯粹社交性”(pure sociability)的活动,消除可能容纳并鼓励这类社会交往的“场所”,前所未有地限制了用户对空间的调适型使用(unprecedented resistance to user modification)(Oldenburg, 1999:265)。在奥登伯格看来,这一趋势的发展进一步导致了美国“非正式公共生活”(informal public life)的衰落。
奥登伯格和布里塞特(1982)认为,在家庭和工作地这两个站点之间,人们的生活还需要一些开放的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悬置来自家庭和工作的结构性身份界定,展开“纯粹社交性”的交往,在其中追求愉悦、活力和慰藉。奥登伯格后来在《绝好的地方》一书中对第三场所展开了进一步阐述,强调它们的公共性,认为在这些场所的活动有助于社区共同体的生成,成为社区运作的润滑剂,并可生成民主运作所必需的社会资本。⑦他认为,自由、宽松、便利是一个实体空间成为“第三场所”的三个前置条件,在此的社交也是平等、开放的,能培育人的归属感。在他的描述中,“第三场所”既没有在“第一场所”的家庭角色束缚,也没有在“第二场所”的职场等级和工作绩效等制约,它是一个公共交往的地方,是“非正式公共生活的核心场景”(the core settings of informal public life)。奥登伯格提炼出了第三场所的八个特征,其核心是,这样的场所对各方人士具有吸引力,它们的进入性和容纳性很高,具有休闲玩乐的氛围,人们在此展开交谈,并从中获得一种“在家”的感受(at homeness)。
由此可见,第三场所是一个理论上的理想类型,它囊括各种形态的、人们可轻松进入的公共空间,概括其容纳并鼓励非正式社会互动的功能,包含对资本主导的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批判,揭示这一模式如何抑制城市空间所应有的人们自由流动、自在交往的空间可供性。在这些分析中,奥登伯格秉持了齐美尔(Georg Simmel)对“纯粹社交性”的理论阐释,以及它被赋予的价值期待,表达了与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和帕特南(Robert Putnam)等人共享的对于美国公共生活衰落的担忧。⑧他认为,城市的空间布局,必须有利于展开“纯粹社交性”的非正式公共生活,因为这是“人类经验的关键领域”(Oldenburg & Brissett, 1982:282)。
在其概念阐释中,奥登伯格(Oldenburg, 1999)汲取了大量西欧的历史经验,并从中提炼出与美国历史经验的相通之处。在他看来,伦敦和维也纳的咖啡馆、德国的餐厅(Gasthaus)、美国的客栈或邻里酒吧,甚至美国南部地区小镇的广场树荫(人们玩扑克牌和棋类游戏的地方)等,都是可容纳甚至鼓励“纯粹社交性”交往的第三场所。他的论述与哈贝马斯(Habermas, 1989)关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论述有相通之处。
第一,两人都从类似的实体场所以及在其间展开的非正式社交中获得了灵感,但他们的理论旨趣不同。哈贝马斯关注的是在这些场所理性公共话语生成的可能,以及它在形成公众及其意愿中的作用,并因此将这种互动所蕴含的社会生活领域称为“公共领域”,考察其历史形态及功能的转型。奥登伯格则注重非正式社交场合的愉悦体验,它给人们带来有情感基础的社会连接和归属感,以及以此为机制的社区或共同体的生成与维系,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可能减缓或阻止公共生活的“衰落”。但第三场所的公共性内涵,至少在描述的层面,契合了哈贝马斯的分析。对此,奥登伯格与其合作者在一篇题为“第三场所,真正的公民空间的”短文中做了更为简洁明了的表达。这篇短文在奥登伯格去世后于2023年3月刊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使》杂志上。⑨
第二,两人都以从历史经验中提炼理论抽象为途径,创建了各自的理想类型——公共领域和第三场所。奥登伯格提出的“第三场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应和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值得指出的是,奥登伯格在毫无迹象表明他阅读过哈贝马斯的著作并从中受益的情况下,提出并阐释了自己的概念。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英译本直到1989年才出现,比奥尔登堡首次阐释“第三场所”概念晚了7年,而1989年也恰是奥登伯格的经典之作《绝好的地方》首次出版的年份。
(二)“第三场所”引发的研究及其语境
在经验层面,奥登伯格描述了多种形态的实体空间,如德国移民们的啤酒花园和小镇的商业街,各式酒吧、咖啡馆、理发店等消费型场所或“社区活动中心”,以及一些被社会学家怀特(Whyte, 1980)称为“微型都市空间”的地方。这些描述和分析,体现了奥登伯格的理论旨趣,即思考日常生活及其中的社会经纬,探讨“社区或共同体如何可能”、“民主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社会学的基础”等问题。因此,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很多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都看到了第三场所概念中可挖掘的理论蕴意。
此后的研究,大多是将奥登伯格归纳的理想型当作标尺,用以鉴定具体的空间单元是否为第三场所,或在哪些方面满足了第三场所的典型特质。在这些研究中,既有关注实体空间的,也有考察虚拟空间的,还有的是探索两者的交织,其中的基本逻辑是分析这些形态的空间如何生成为第三场所并以此发挥作用。比如,实体形态的快餐厅(Cheang, 2002)、咖啡馆(Rosenbaum et al., 2007)如何成为人们日常自发交往、获得社会支持并产生依恋的地方;网络中介的交往互动如何可能搭建第三场所(Soukup, 2006);“大型多人在线游戏”(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games)活动构成的虚拟空间如何提供了具有“第三场所”意义的社会互动,并生成特定类型的社会资本(Steinkuehler & Williams, 2006);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如何影响在咖啡馆这样的第三场所中展开的社会交往活动(Memarovic et al.,2014);再或是在都市中新兴的介于传统工作地(如办公室)和咖啡馆之间的合作办公场所,是否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第三场所形态,有助于培育和鼓励社会交往和协作分享(Brown, 2017);还有研究探讨人们如何就某议题组织在推特上的交谈,从而搭建数字网络上的临时性“第三场所”(McArthur & White, 2016)。
也有研究者(Wright, 2012)试图连接“第三场所”和哈贝马斯,认为在虚拟世界中展开的日常交往或非正式聊天,可能涉及政治话题,并可能显示出商议的(deliberative)特质。作者在互联网场景中重新批判地审视“第三场所”概念中蕴含的结构性和参与性的特质,提议采用“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的概念,以突出由交往构成的网络空间既实际存在又超越实体地方的特性,以及如何突破了哈贝马斯等人的规范理论对日常非正式交谈的忽略。
国内对于“第三场所”概念的关注和使用,则可回溯到21世纪初。⑩整体而言,将这一概念挪用到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语境的研究,大多围绕社区生活,而考察的对象仍以实体空间为主,比如网吧(雷蔚真,2004)、城市居住小区(李晴,2011)、社区体育公园(刘臻,2017)、图书馆(周芸熠,2013;程大立,吴春祥,2019;刘志国等,2021),等等。这些研究都显示,“第三场所”与“社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当下移动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还带来了新的可能,即具有第三场所性的所谓“移动社区”(谢静,2021)。
国内外的这些研究,以不同方式描述了不同形态的社会空间。无论何种形态,它们与家和工作场所有别,是更为轻松、开放、自由的空间,是具有可进入性、兼容并蓄、以交往为核心特征的场所,具有生成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社会功能。不过,多数研究倾向于考察空间单元的物理特性,推断其可能导致的活动或具备的社会功能。这样的分析,往往将场所看作人们所处的时空点、展开行动的场地或平台;而且将构成生活世界的三类实体空间,看作是各自特性既定、承载不同类型活动的容器。采用这一路径,一些更具历史动态的阐释性问题可能被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譬如,奥登伯格描述的酒吧、理发店等休闲消费类场所,为什么可能成为人们获取社交愉悦的第三场所?随着城市化的深入,散落于街坊的各类休闲消费场所逐渐被大型商场取代,那么,还有哪些城市空间在哪些条件下可能生发出不同程度的第三场所性?随着网络和移动媒体的普及,不同空间形态如何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生成第三场所性?具体到抗疫期间出现的小区或居民楼的微信群等网络空间互动场所,它们是否或如何可能获得某些第三场所的特性?
这些问题貌似混杂,但都指向一个研究设问的转换,即从“哪些空间可被认定为第三场所”转换为“空间的第三场所性如何生成”——前者是相对静态的类别分析,后者则是偏向动态的过程分析;前者聚焦实体空间的物理特性,后者着眼行动者与实体空间的互动,并将之视为一个信息传递、意义建构的过程。
二、“第三场所性”的表达和实现
如前所述,第三场所为非正式的、纯粹社交性的互动提供了广泛可能性。随着数字技术的日益普及,社交媒体、移动智能手机和Wi-Fi网络日渐成为空间构成的一部分,并且不断形塑人们在特定场所的社交方式,也使第三场所不再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实体空间类型(Brown, 2017;McArthur & White, 2016;谢静,2021)。[11]也就是说,人们可能在多种情境下感知或发现“第三场所性”,并以自己的交往活动体现这一特性。我们可将这个判断作为逻辑起点,探索一条适应当下多方位变迁的研究路径。这是一个针对空间设计格局与空间使用实践之间如何对话的研究路径。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别解答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如何理解第三场所性?第二,第三场所性如何体现为一种空间的潜能?第三,这一潜能如何在人与空间的交互中得以表达并实现?
(一)理解“第三场所性”
关于“第三场所性”,我们能够找到的文献是墨西哥裔研究者罗伯托·卡尔德隆(Roberto Calderon)在201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卡尔德隆探讨了如何将“第三场所性”编码于信息技术平台和应用当中,通过用户界面的设计予以表达并传递,从而促发具有某些特性的交往互动。他认为,第三场所性体现在可能支持社会资本的生成及维系的人际互动和情境信息当中(Calderon, 2016:36)。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推论,任何具有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促成某些特定形态的社交活动的实体或虚拟空间——包括型构这些交往的数字技术——都可能传递出第三场所性,而人们使用特定空间/技术展开这些形态的社交,即是对第三场所性的某种程度和方式的实现。这里所说的社交,指的就是奥登伯格所描绘并寄予规范性期望的人际交往,它们是非结构性的,自发、平等、给人带来身心愉悦,且重复发生或至少可重复,具有着共同体生成潜力的人际交往(Calderon, 2016:33)。
“第三场所性”因此强调特定内涵的人际互动体验,这些互动有助于信息流动和社会强连接的形成,而行动者通过自由自在的交谈与互动也可获得群体和地方归属感。卡尔德隆(2016)认为技术设计可考虑在三个方面促成这些体验:“社交性”、“公共性”和“物理性”。在这里,社交性指向社会连接的结构和规范性特征,包括互惠性、密集度、中心性等关涉社会资本生成的社会网络特征。人们的社会交往动态地生成这些特征;这些交往也大致对应了奥登伯格和哈贝马斯分别构想的人们自由自在的交谈,在这交谈中人们可能获得表达与相知的愉悦,以及经此而可能形成共识、建立稳定的关联。公共性的维度涵盖了空间治理的各个方面,尤其关系到信息拥有权、空间或技术的可进入性、个人隐私等议题。这些方面的规则或规范,形塑人们获取第三场所体验的社会互动类型,可与奥登伯格期待第三场所是“中立之所”、“家外之家”,具有“可进入性”和“陈设朴素”等特征相呼应。第三个维度是物理性,指的是技术和场所的物理特征,它们关涉交往的物质维度,包括技术支持和适当场所,支持人们展开具有第三场所体验的交往,尤其是其中的重复性、舒适和轻松感,也即奥登伯格概括的丰富和活跃第三场所中的“常客”和“玩乐的氛围”,以及“家外之家”那种心理和情感上的归属感。
卡尔德隆的理论阐述远非充分,但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路径,并可走出对数字技术平台的分析领域,以考察技术和空间设计,探寻其中所蕴含的支持与维系特定社交活动的潜能,以及对这潜能的可被感知的表达。在卡尔德隆关于社交性、公共性和物理性三个维度的论述中,我们需要补充并稍作展开的是,从社区创建或共同体形成的角度来看,社区内信息交流的网络和媒介技术及其布局,即传播基础设施,有助于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的创建和维护,这包括人们相互间的互动交流、社区的组织形态以及媒介技术设施的铺设,还包括人们表达、分享和塑造社区身份及归属感的叙事、信息及想法。搭建这样的传播基础设施对于培育认同、公民参与以及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形成等具有至关重要的支持和容纳的作用(Hayden & Ball-Rokeach, 2007; Kim & Ball-Rokeach, 2006)。也就是说,信息和媒介技术是赋予空间的社区形成潜能的基础设施。
沿此路径,第三场所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其意义不在于帮助我们区分不同的城市空间类型,而是有助于我们分析第三场所性如何被编码和表达在空间的建构当中,空间使用者又如何解读其中的意义,据之展开交往活动,并落实为自己身处第三场所的体验。
(二)作为“可供性”的第三场所性
如此观之,第三场所性即是空间的一种“可供性”,可概括为容纳和促发社会资本生成与增值的潜能。近年来,“可供性”在包括新闻传播和多个相邻学科都受到较高关注,因为它“为我们把握主体能动性(subject agency)和技术效能(technological efficacy)之间这难以琢磨的空间,扮演着重要的解析性角色”(Davis & Chouinard, 2016:246)。
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围绕这一概念也展开了多元的理论和经验层面的探讨。其范围包括:从译名辨析与范式/概念之变(孙凝翔,韩松,2020)以及本体论层面探讨(胡翼青,马新瑶,2022),到分析数据基础设施如何具有可供力(马中红,胡良益,2022)、平台和用户之间如何可感知并互动(张志安,黄桔琳,2020),再到考察B站美妆视频社区中“能动的”可见性(曾丽红等,2021),等等。此外,作为连接技术的物质性维度与文化社会性维度的纽带,可供性被用以分析技术变迁环境下的新闻转型,比如为数字新闻学提供了认识论视角(黄雅兰,罗雅琴,2021)、数字新闻的时间可供性(王海燕,范吉琛,2021)、数字新闻生产网络的生成(徐笛等,2022),以及数字新闻的再定义(常江,田浩,2021)等。
如此构成的文献让我们看到了“可供性”概念的理论魅力。不过,针对本文所关注的“第三场所性”,我们需要回到可供性的原初意涵。吉布森(Gibson, 2015)生造这个词,为的是表达人与环境之间互补和协调的动态关系,指代其中环境对于具有感知和行动力的主体而言所蕴含并传递出的潜力。因此,吉布森意义上的可供性,并非引发行为的动因,而是邀约行为的潜能;它既不可简约为环境(或技术)的自身特性,也不存在于行动者的主观认知,而是生成在二者交互的界面,更准确地说,是在这界面形成的过程中。这一理解,为行动者的能动性(agency)留出了阐释的空间,而且是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去理解(Withagen et al., 2012)。因此,可供性跨越了主客观的二分法,如吉布森所言,它同时指向两个方面:环境和观察者(Gibson, 2015:121)。
这一表述未免有些因其主客兼顾而难以把握,但其意正是为凸显并聚焦人与环境的互动及其过程。对此,澳大利亚学者戴维斯和舍纳德(Davis & Chouinard, 2016)试图再作推进,指出可供性的理论建构需要论证其形成机制,也就是要回答可供性如何发生的问题。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个由机制及其展开条件所共同构成的突出动态过程的理论支架。前者,即可供性的机制,指物件所传递的可能性及其传递方式,包括对可能行动的规制、邀约、许可、启迪、鼓励、拒绝等;后者是展开条件,显示哪些行动者在什么具体条件下可感知这些可能性,并获有行动力,而且具备必要的文化和制度的正当性以落实这些可能性。
这个理解,补充了诺曼(Don Norman)此前对“可供性”概念的阐述和运用。在醉心产品设计的诺曼看来,“所有人造物件都有设计”(Norman, 2013:4),而设计,运用符号学语汇,即编码,也就是把物件的性能、用途、如何使用,以及人与技术之间可如何互动等,不仅具身于物件,而且展示为物件的醒目特征。这些特征即是活跃于物件-用户界面中的“能指”(signifiers),呈现该物件如何可与用户的使用行为结合,从而实现为特定的可供性体验。这样来看,好的设计是构造一个有效的交流体系,建立起一种物件与用户之间的关系,[12]可供性生成于这样的动态关系中。如诺曼所言,“可供性并非属性,而是关系”(Norman, 2013:11)。用经典的文化研究术语来说,这个关系是一个由编码和解码这样两个意义建构的时刻(Hall,1980)共同构成的动态界面。
如此分析我们关注的“场所”,可以看到的就不仅是如奥登伯格所呈现的第三场所的多样形态,更是人们如何运用特定空间而展开社区/共同体导向的社会交往。也就是说,这样的场所并非是设计决定了的,而是可能由身处其中的使用者形塑的;它们可以有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使用方式,这些使用方式与空间本身的设计密切相关。但设计是布局,传递出可展开行动的各种可能,而非对用户调适型使用的设计性拒绝(Peters,2019)。简言之,空间设计中内嵌了展开多样形态活动的可能性,即空间的可供性。体现这一视角的经验研究包括如对博物馆(Wineman & Peponis, 2010)、工作场所(Vilnai-Yavetz & Rafaeli, 2021)、学校学习环境(Young & Cleveland, 2022),以及街道布局中那些可能促发社会交往的“共享空间”(Peters,2019)等的考察。以博物馆为例,研究者关注其布局设计如何有可能引导参观者的移动(spatially guided movement),而非仅是由空间秩序既定的(spatially dictated movement)或是随意漫游式的参观(spatially random movement)。这样的分析是考察博物馆展览设计中如何通过空间的句法(spatial syntax)构建,传达不同层次或重要程度的信息及意义,而其接收程度则取决于参观者的兴趣以及选取的路径(Wineman & Peponis, 2010)。
简言之,“第三场所性”是在人与行动场所互动中体现出的一种空间的可供性,也即奥登伯格所期待的那类社交活动得以在具体行动场所展开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一方面表述在空间设计或技术界面当中,另一方面体现或落实在使用者对一个空间的感知、解读和转换的行动当中。
(三)第三场所性的表述和解读
那么,城市居民如何可能获取具有第三场所性的空间体验?以上的讨论显示,这是个探寻的过程,由空间的双阶建构(co-production of space)(Low, 2009)而组成,即行动主体——包括城市建设者和空间使用者——对空间文本在交往情境中的编码和解码。
当然,用编码和解码来概括可供性生成和落实有些简单化,而且也遮蔽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即将它们抽离其得以展开的物质世界,褪去其“在地”(in place)这个基本的具身特性。在有些学者看来,这是文本中心模式的体现(参见Packer & Wiley, 2012)。其实不然,之所以运用这两个符号学用以指代行动过程的概念,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将空间的建构和使用置于经验分析当中,以考察空间转换为场所的这个过程,分辨牵涉其中的不同符号体系及其相互交织。
对此,语言学家斯克伦夫妇(Scollon & Scollon, 2003)的一些论述颇有启迪。他们倡导地理符号学(geosemiotics),以考察在日常生活中符号和话语如何在地并由此生成意义。他们认为,首先,所有的符号只有在地才有意义;其次,所有的符号都是集合体,在其在地和使用中,与其他符号发生对话,并由此而获得意义。斯克伦夫妇将这些论断分别表达为“索引性原则”(principle of indexicality)和“对话性原则”(principle of dialogicality)。而且,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主体的行动都坐落于具体情境,也即选择部分在地的符号作为前台关注,而将其他符号隐为背景,这是所谓“选择的原则”(principle of selection)。虽然斯克伦夫妇可能有些泛化索引性这种表意方式,但却显示出了意义建构的物质性维度,它体现为主体在地的行动。
行动之所也即意义生成之地,它由多种符号系统生成。斯克伦夫妇将它们区分为三类:交往秩序(interaction order)、视觉符号学(visual semiotics)和场所符号学(place semiotics),三者通过索引性而相互关联。[13]采纳这一分析框架展开的研究多考察场所的可辨认特性、场所特性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等,比如分析不同食品市场或高档餐饮店中各种语言符号的在地使用(参见Lou, 2017;Theng & Lee,2022),或是唐人街这样的特定城市旅游景观如何经由空间的、语言的、符号的和物质的资源打造而成(Lee & Lou, 2019);再或是考察在城市中心广场中人们如何通过解读广场的设计及周遭的建筑、他人的行为(代表了互动秩序)和缺失的视觉符号(如标牌标识)以及这些系统间的相互作用,进而采取驻足、歇息、穿行等多样的行为(Peters, 2019);等等。
概括地说,首先,作为社会行动的场所,其生成牵涉(1)遵循特定规则的行动(如购物、游玩、处理业务),(2)有着物质具身的符号及其组合(譬如商店招牌、广告招贴、交通指示牌、友情提醒标识等),以及(3)实体空间的构成物件及其相互间的结构性关系(譬如建筑、道路、公园、自然地貌等);其次,这三类符号系统通过符码/规则的“筛选”(code preferences)、“铭刻”(inscription)和“置位”(emplacement)这三个过程机制而交织,共同界定一个社会行动的场地(site of social actions),即场所。正如英国地理学家克雷斯韦尔(Cresswell, 2009)所言,场所是物质性、意义和实践的结合。
这些论述给我们提示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以考察社会行动者探寻并获取第三场所体验的过程。首先,三类符号或意义生成系统相互关联并对话,共同构成一个作为文本的场所,或是“空间文本”(Ravelli & McMurtrie, 2016)。不同场所之间有差异,其中一部分源自斯克伦夫妇(Scollon & Scollon, 2003)所概括的“话语间的对话性”。通俗一点说,这是指不同符号系统相互间的协调程度。其次,三类符号系统各自内部及其相互间的对话都内含了不确定性,用符号学的术语说,即能指与所指之间、符号与符号之间、符号与所在地之间都是经由社会协议而成的关系,不具有决定性。也就是说,对场所的文本有采取不同立场展开解读的可能(Hall, 1980),而场所亦是可展开不同行动或交往的弹性空间。
我们可以这两个方面的理解,采用开放程度和设计程度这两个连续性坐标来区分不同的城市空间(Scollon & Scollon, 2003:169)。第一,就开放程度而言,一端是相对开放的社会空间,可容纳不同行动者展开各种活动,包括没有预设脚本的活动(如公园),另一端则是相对封闭的空间,甚至是对应了特定类型或功能的社会行动空间(如教室)。其次,就设计程度而言,一端是高度设计和按设计管控的空间(如上海浦东的陆家嘴环路和世纪大道交汇的环岛),以其设计抑制空间使用者的“调适型使用”行为,另一端则是设计和管控松散的空间(如一些上海弄堂和鲁迅公园),对调适型空间使用持基本开放甚至邀约的态势。而奥登伯格等经验考察的各类“第三场所”,在这两个坐标上都介于两端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1)开放性(openness,即对造访者基本不设限),(2)可达性(accessibility,即不需特殊的努力或能力即可进入),(3)弹性(elasticity,即活动形式可以多样且可临场发挥),和(4)可读性(legibility,即空间的功能,尤其是其潜能对使用者清晰可见、可感)。
我们由此可推论:第一,人们可获取第三场所体验的城市空间类型范围很广,形态各异;第二,人们探寻第三场所体验的方式本身符合地理符号学的分析路径,即对一个城市空间就上述三个符号系统展开解读,选择适合的地点作为其特定的行动场所,选择契合特定场所的交往形态在此展开交往;第三,在以数字编码、网络连接和移动接入等为基本要素的新技术时代,技术的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地成为空间及其动态的一个必备维度(参见Adams & Jansson, 2012;McGuire, 2008),以卡尔德隆(Calderon, 2016)指出的三个维度的设计路径,参与到配置和表达第三场所性这类空间可供性的过程中。
选择是这里的关键词,指代了行动者能动性的一个基本构成元素。这种选择是人综合其感受、情感和认知等信息而作出决策,并落实为行动;选择贯穿行动者环境建构的全过程(Tuan, 2001)。选择也是在地的表达,内容包括人的内心感受,对环境的理解,某种价值追求,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在相对开放的空间,这种追求和表达,不仅是面向某类观众的展演(Simpson, 2011),也是一种交往。这种综合性选择,体现为对城市空间不同方式的使用。我们根据城市空间上述四个方面的差异,以及它们的交织所蕴含的对交往秩序的规范性期待(Scollon & Scollon, 2003),大致区分出四种获取第三场所体验的空间使用方式:
(1)有些城市空间对会友、交谈而言,是在以上四个方面“配置适当”的场所,或者说,这些地方约定俗成地邀约非正式交谈的交往秩序。当然,它们相互间可能又索引了不同话语而适合不同群体的人,或者不同类型的会友和交谈。譬如,咖啡店和茶馆可能有区别,它们分别是指向不同文化体系的符号,索引了全球与本土交织时代的不同话语体系。但是,尽管有这些不同,它们仍是某种“现成的”或按其设计适合会友、交谈等社交活动的场所(Simon, 2009),因此,人们选择它们展开非正式社交可能“顺理成章”,表现为匹配式空间使用。
(2)有些城市空间可能更为开放,可达度更高,而且对活动类型的包容更具弹性,譬如城市公园(包括街角公园),对该空间可如何使用的可读性也很高。开放的空间格局和宽松的规则,使得多样活动可以在那里展开。比如,一早一晚,我们在很多大城市的公园都会看到居民们各自形成群体,以各类群体活动,如下棋、踢毽子、打太极、歌咏、聊天等,分割和重组公园这个公共空间。这些重组式空间使用,体现了以人口特征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划分,以及群体内以兴趣和友情为基础的社会交往。
(3)还有些城市空间具有突出的主功能活动,譬如餐馆以饮食活动为主,商场以商品交易活动为主,书店以展示和交易书籍等文化产品为主,这些都意味着对空间使用方式不同程度的限定。但是,它们依然在开放、进入门槛和活动类型的弹性等方面相对宽松,而且这些宽松规范的可读性也比较高。因此,人们可能在那里进行拓展式空间使用,譬如朋友在餐馆聚会,以社交(而非一定是饮食)为核心目标;朋友们约好了逛商场,利用其多种功能(譬如旱冰场、茶饮、影院等)而展开社交,而不是一定购物;再譬如在书店,人们围绕书籍和文化产品展开交流,如读书会、与作者见面会等,但未必购书。
(4)有些城市空间则可能被临时征用,颠覆其设计限定,将其主功能转换为必要的辅助型活动,我们可称之为转换式空间使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各大城市有时出现的“快闪”活动,它们往往发生在城市商贸广场、大的购物中心等开放空间。“快闪族”(flash mob)是个松散的爱好者群体,他们通过网络联系,在约好的时间、地点聚集,展开表演。这个特定的短暂时刻,既体现他们的集体身份,又将购物和逛街的人群转换为他们的观众,或即兴的参与者,将购物和逛街的空间暂时转换为表演的舞台,并以此激发多种可能的非正式交往。
这四类使用方式既未涵盖所有可能,也未必相互截然区分。我们提出它们,只为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以显示人们如何通过解读空间文本,选择适宜活动,以获取第三场所的体验,也就是各种形态的非正式社会交往以及由此获得的身心愉悦。其中的转换式空间使用方式,最可能体现对空间设计的“颠覆”,但它通常也是在制度许可或可容纳的范围内。换言之,“第三场所性”的内核是保守的,它以自发交谈、嬉戏表演、身心愉悦等构成元素,活跃于人们日常的生活世界,为刚性的体系提供缓冲和支撑。
三、我嘉书房:一个经验的示例
本文的旨趣是理论建构,但是最初的触动则来自一项经验研究,即对上海市嘉定区“我嘉书房”的田野考察。[14]正是对这个经验案例的分析,令我们感受到了现成理论的局限,在此基础上的反思,促使我们逐渐将“第三场所性”看作是空间的一种可供性,分析它如何生成于行动者与场所的互动过程中。为完成这个理论建构之旅,我们现在回到“我嘉书房”这个案例,以一个非常简略的呈现,审视本文所阐述的理论框架如何可用于观察和分析经验现象。
在奥登伯格(Oldenburg, 1999)如数家珍般陈列的第三场所中当然找不到“我嘉书房”,因为美国没有,在中国也很独特。作为社区公共图书馆,至少就其设计而言,它不以“令人愉悦的非正式交谈”为核心活动,而且,它也不是一个空间点:从2017年1月第一家建成启用后,有30家陆续得以建设并开放。它们各具特色,镶嵌在嘉定区多个社区内。作为一个“为社区打造的公共文化场所”,它们现已成为嘉定乃至上海的一个符号,是“城市文化地标”之一。那么,人们在“我嘉书房”这样的城市空间如何可能获得第三场所的体验[15]遵循本文阐述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从三个方面做出简单呈现,以回答这个问题。
(一)视觉符号系统
在功能设计上,我嘉书房是嘉定区公共图书馆的延伸服务点。2013年嘉定区图书馆(裕民南路新馆)开馆后,被美国权威设计杂志Interior Design评选为“全球最佳公共图书馆”。在以“深度城市化”为口号的进一步城市建设中,[16]为提升公共服务在城市更加均等的分布(邵宇等,2013),嘉定区开始展开深入景区、商圈、社区、园区的我嘉书房建设。
我嘉书房的商标设计,就体现了延伸嘉定图书馆的服务这一功能性意向,以及建设本地居民“家外之家”的理念。如图1所示,商标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左边的图标为翻开的书本,与嘉定图书馆的实体建筑(图1 图1见本期第55页 右边的图片)的外形遥相呼应。商标的右边是“我嘉书房”四个中文字,其中“嘉”字以字号加倍的隶书显示,非常突出,下方则是全部大写的英文黑体字,HOME STUDY。
这些视觉符号具有突出的索引功能。首先,商标中翻开的书本这一图示,索引了图书馆的文化功能。它被用作整个嘉定区图书馆的通用图标,出现在区和街镇图书馆以及我嘉书房的门楣上方,也贴在我嘉书房陈列的图书书脊上。如此的分布,使这个图示成为视觉标识,展现嘉定图书馆服务网点的空间分布。其次,凸显的“嘉”字,不仅索引嘉定区,而且“嘉”与“家”谐音,视觉上凸显的“嘉”似乎在敦促人们体会它的声音,激发对“自家书房”的想象。对人均居住面积有限的多数都市家庭而言,这样24小时运营的自助图书馆往往成为家门口的“书房”,可弥补私人空间的不足。[17]如一位被访者所说,“我家没有书房,那就去我嘉书房呗”。第三,英文对此作了进一步直白表达,采用了突出家居空间的home,而非表达家庭的family,这其中蕴含了对“家外之家”这一话语的索引,也即第三场所性的一个核心要素。
界定我嘉书房的视觉符号也被置于城市的实体空间,成为一种地理标记。如(图2 图2见本期第56页)所示,在道路交叉口的路标,以视觉的符号不仅表达了我嘉书房是个独特的城市空间,而且也呈现了它的空间方位。作为在地的符号,它们与周边的道路布局和设置关联,对空间使用者显示我嘉书房在所处地理环境中的意义,提示抵达的路径。比如(图2 图2见本期第56页)左边的指示牌,显然是南翔老街旅游景点这个符号系统的一部分,它呈现我嘉书房是步行可达的一个去处。而右图则不仅是指示方向的路标,更是一个宣传的海报。“菊园·绿地天呈”这家书房,位于社区内,置于社区入口处的指示牌,成为房产广告的一部分,将我嘉书房呈现为“人文住宅,高阶圈层”的构成元素之一。
体现信息技术作为空间构成的一个维度,界定我嘉书房的视觉符号系统还活跃在虚拟空间。在嘉定区政府打造的“文化嘉定云”平台上,我嘉书房有着突出的位置,它是“文旅地图”板块的三个栏目之一,其他两个是“文化场馆”和“文化创意空间”。点击“我嘉书房”会出现清晰标记了各处我嘉书房的动态地图。(图3 图3见本期第56页)是这个地图的一部分。点击地图上任何一个我嘉书房的图标,系统就会弹出一个新窗口,显示该处我嘉书房的名称、地址、电话和活动室数量,以及“探路”和“查看详情”的按钮。点击“探路”按钮,系统就链接到地图的App,呈现该处的地理方位,并可进入导航系统;点击“查看详情”,系统会弹出新窗口,显示该处的图片和详细地址。“文化活动”板块则以一张张数码卡片方式,陈列各项文娱活动的内容、时间、地点,以及如何参与(如网上订票或“直接前往”),各处我嘉书房安排的活动也陈列其中。这些数码物品(digital objects)是界定我嘉书房的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在功能、结构性关系、地理方位等方面,赋予由各个场馆落点构成的我嘉书房作为活动场所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意义。
(二)空间格局和相应的活动
有别于作为“知识殿堂”的传统图书馆,我嘉书房是一个工作和家庭之外以广义的文化为基本内容的休闲和社会活动场所,官方将之界定为“社区的公共文化场所”。它所蕴含的“第三场所性”,也以“文化”为基调或限定,以“社区”为其人文和社会指向。这些基本的理念,体现在每一家书房的设计当中。空间的格局也准允或鼓励一些特定形态的活动,成为场所的基础经纬。
首先,除前面所提到的选址之外,每一家的门面和内部空间设计,都试图融入所在的社区(如文化街区、工业园区、居民生活社区等),而且体现“一馆一品”的特色。(图4 图4见本期第57页)呈现了四家随意选取的我嘉书房门面。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以嵌入所在社区为基调。北虹桥时尚馆(见图4a)位于北虹桥时尚创意园,体现创意园改建旧厂房、修旧如旧的整体特色,该处“我嘉书房”的入口非常简约。位于菊园的这家(见图4b)以“嘉悦”为名,因为它建在嘉悦社区内,在“嘉定文化云”的“文旅地图”中显示的地址为“秋竹路801弄41号金色领域小区居委一楼”,且在官方介绍中也特别强调它用了“北欧工业风”的设计,以“社区治理自治”的努力,服务所在的以“高学历年轻家庭为主”的嘉悦社区居民。[19]位于南翔老街景区的我嘉书房开在了一家古宅内,宅子的第一进是“名士居”版本书店,“我嘉书房”为第二进,且以“名士居”为其馆名。从图4c我们可以看到,这家书房是以现代材料重新装修了的古宅风格,包括门楣上的匾额都用了古色古香的木板和篆体字。图4d显示的是环同济创智城馆,它位于同济大学嘉定校区附近的绿地大厦一楼,与巴尼咖啡馆合体,号称“致力于打造城市第三空间,为周边社区居民、同济大学学生提供文化交流、生活美学的学习分享平台”。[20]这个现代咖啡厅的门面和户外的桌椅,都体现了这个设计理念。
其次,每家书房的内部空间格局和氛围营造,也都体现出“一馆一品”的特色,体现设计者对它所在社区特征、居民需求等的想象。一些媒体报道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譬如2021年9月,东方网刊出图文并茂的介绍文章,名为《哪家“我嘉书房”最符合你的气质呢?快来选出你心中的最爱》。文章分上、下两篇,逐一介绍了部分书馆。[22]我们在此选择三家作为示例。
“我嘉书房(南翔·名士居)”被称为“上海首家以连环画为主题的公共阅读空间,也是全上海最具古雅韵味的百姓书房”。设计中保留了“吱呀作响的木结构老房子”,内部空间与古宅风格一致,采用了木质家具,简约而古朴,书架上还陈放了似乎随意而置的假山和植物盆景,空间安排错落有致,由书架和读书的桌椅区隔;二楼另有较大的交流活动空间,桌椅可自由变换移动,以适应不同的活动。无论是在读书还是活动的空间,透过木雕窗棂,人们都可以欣赏明末大儒李流芳故居檀园的景色。显然,这家“我嘉书房”不仅是读书、会友的地方,还是各种文化活动的场所,也是南翔老街景区的旅游打卡处。
非常不同的是前面提到的“我嘉书房(安亭·环同济创智城)”。书房内采用了沙发座椅,还有书架下的两级台阶,上面陈放一些座垫,可以随意取书坐下阅读。整个格局显得放松、休闲。与巴尼咖啡馆合体,也使书房飘逸着咖啡香味,帮助营造一种“小资氛围”。书房还有大的活动空间,为举办各种活动所用,包括公益活动、读书沙龙以及每季度一期的“国际毗邻节”和不定期的音乐节。为体现所在的环同济创智城的特色,这家书馆还把“我们学习,我们分享,我们把世界带给你”作为其各种活动的设计理念。
“我嘉书房(菊园·绿地天呈)”也是一个独具风格的书房。据设计师说,“书房运行主体给予设计方很大的构想空间:要将300多平米的空间打造成一处既具备24小时自助图书室、社区文化空间、公益休闲等多元功能的场所,又要在设计风格上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为此,设计者们决定采用“美式工业风格”,以水泥墙体现工业风的主调,用旧红砖墙呈现老旧的“摩登感”,用裸露的天花板与包装成黑色的管线显示出极简风格,这些与旧木的书架和桌椅、生铁锻制的造型简单的吊灯等,共同营造一种“轻松、闲散的空间气息”。[23]书房内还创设了多个小众的主题空间,增强读者与书房的多元互动。
第三,空间的格局并不决定使用它的活动类型,在特定空间设计下展开的活动是人们组织和创作的结果。“我嘉书房”的不同书馆,各自都会组织多种活动。前文已经提到如“我嘉书房(安亭·环同济创智城)”举办的一些活动。类似的例子很多,而且一般都反映了一家书馆的格调。譬如,“我嘉书房(南翔·名士居)”举办的“捉笔写秋英|中秋国庆扇面绘画体验”活动,感兴趣的人可以在“文化嘉定云”上报名取票入场。书房还举办名为“微阅读·文化行走”的活动,内容包括在书房观看历史资料影片,或走进同处老街的历史文化陈列馆,聆听南翔古镇的故事。
前面提到在“文化嘉定云”平台上的各种文化活动预告和订票信息,包括了安排在不同书房的各种活动。譬如,2020年10月11日,在“我嘉书房(菊园·绿地天呈)”的非遗体验课的活动内容,是由三位非遗传承人教孩子或是家长一道来完成马赛克烛台的制作;2022年12月24日,“我嘉书房·宝龙店”安排了“亲子绘本阅读《100个圣诞老人》”。这些活动多以“政企结合”的管理模式以及部分书房(如菊园的四家书房)设有的志愿者服务项目来组织支持。通过“政企结合”的机制,“我嘉书房”吸引了多个行业或专业的第三方参与书房建设。书房还通过志愿者的参与,以提升对其社区的自治管理。在这些组织结构的背后,是文化地理建设的理念,与空间格局、活动内容和技术设施等一道,共同构成斯克伦夫妇(Scollon & Scollon, 2003)概括的“符号的集成”(semiotic aggregate),使得这些书房成为风格各异且容易辨认的活动场所,体现出对造访者的高度开放,对进入的高度无障碍,以及活动种类在一定范围内的弹性。
(三)使用者的体验
“我嘉书房”究竟如何被用作特定的行动场所,则须由使用者自己来描述。如段义孚(Tuan, 2001:6)所言,“在体验当中,空间的意义就融入了场所”。体验并非仅限于被动的感受,也不限于感官对外物的接收,它是一个主动的过程,牵涉人的选择,以身体动作与空间发生互动,并在认知层面对直接的感知展开解读和想象,将这些感知和以符号的手段所传递和分享的社会知识相整合。在此,我们择取一些来自田野考察的访谈资料,从三个方面简略呈现这些复杂、多样、主观、亲密的个人体验,以及其中体现第三场所性的成分。
第一是“家”的感觉。“我嘉书房”在位置和时间上均具有很高可进入性。在时间上,它每天24小时开放,任何人可使用上海全市通用的“读者证”进入,没有证的则可用书房门口的自助机即时办理。在空间上,书房选址在社区,而且优先选择建在一楼,方便社区居民步行抵达并进入。如一位居民说,“我住在嘉定,想去上海图书馆看书,我得走多长时间呢?我要用2个小时在路上,去看2个小时,回来又2个小时,6个小时,但是‘我嘉书房’的话,我从家里面走出来也就50米,我坐两三个小时,看看书,挺好”。
有些来访者强调“我嘉书房”的“家”的感觉:“这里比较温馨……,突破了之前图书馆的定义,营造了回到家的感觉……我家住在这里,如果看书,我一定会来这里。”书房设有免费Wi-Fi,账号和密码或张贴在书房墙壁的显眼位置,或置于书架上方,便于来此的人们联网。一位在此办公的被访者说,“我电脑带过去的话,就可以用插座充电和连接Wi-Fi,跟家里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即便在疫情闭馆期间,还是有人来到“我嘉书房(菊园·绿地天呈)”,利用户外陈放的桌椅办公,因为书房的“Wi-Fi还是开着的”,比“家里移动免费赠送的网络”网速要快。
第二是感受私人空间。“我嘉书房”并不一定是以交谈为核心的“第三场所”,在读书的空间,这里是安静的,人与人之间的交谈也是轻声细语。码放了书的书架分割了空间,让一些人很享受在“书架间读书的意境”;对有些来访者而言,这“给我们阅读者有一个相对隐蔽点的空间……,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隐私性”。书房安静的氛围使得一些人觉得能够“更专注于你要做的事情”,又能够多些“自觉性”、“比较静心”,摆脱在家中“一会吃两口零食”、“看一会书就想去躺一会”的状态。静谧的空间,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可以在纷繁的工作生活琐事之后“陪陪自己”,静静地“坐一两个小时”,“回归自己的小角落”。还有些人喜欢在这里读书,因为在这里读书,“就是去品书、品咖啡、品生活,就是这种意境让你会更舒服一点”。
第三是社交与分享。“我嘉书房”经常围绕“书”和“阅读”举办互动活动,它们以互动和体验为主,为的是“好玩”,注重参与者的“体验感”。譬如在前文提及的“名士居”举办的“捉笔写秋英|中秋国庆扇面绘画体验”活动中,参与者们在彼此陪伴和互动中,感受“古人高雅的文化生活”。看似高深的国画,在活动中变得更“接地气”,让参与者获得“时间过得真快”、“得再来”的感受。参与者中还有人将当天拍摄的照片和自己的评论发布到“大众点评”这个第三方点评的信息分享平台。在书房举办的亲子绘本阅读和全职妈妈手工活动,就是“通过这些公共空间聚在一起……,边缝着东西,边聊娃的事情,比如说慢吞吞这个事情原来是共性,可能你的心态就会平和一点……大家相互认识之后,比如我想去医院,就会有人给你支招应该去哪个医院之类”。
书房的空间格局及其各类标识,也昭示它是一个兼容并蓄(inclusive)的地方。一个退休老人的诗词社团选择在“我嘉书房(南翔·名士居)”聚会,因为享受“不被打扰地读诗”这份乐趣。一位医生平日工作忙碌,却坚持每周带4岁儿子参加我嘉书房(菊园·绿地天呈)的“非遗体验课”活动,因为孩子在得到“知识性的收获”的同时,也“能交到一些朋友”。另一位带着5岁女儿参加这项活动的全职妈妈说,“不管她以后能不能做,首先她要了解要知道,这样其实就是传承,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成为匠人,但是你知道这些东西、了解这些东西,会给你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些在实体空间的感受,也给人们创造了机会和条件,运用信息技术以拓展分享与参与的空间。譬如,诗词赏析吟诵活动参与者通过这一活动建起了微信群,在疫情爆发初期,这个微信群变成了诗词爱好者作词、诵诗的平台,表达他们身处上海、心系武汉的关切。空间的拓展也可能就在书房的实体空间。譬如,“我嘉书房(菊园·绿地天呈)”一角有一面“我嘉相册”的“记忆墙”,活动参与者贴出记录他们活动的照片,这既是连接不同人参与不同活动的记忆,也是在时空维度上拓展了书房这个场所。
结语:空间与传播的互构
本文的一个基本论点是,“第三场所”不限于根据奥登伯格陈列的几类特征所辨析的具体场所,作为一个理论棱镜,它指向具有可塑性的空间;而“第三场所性”,指的是这类空间容纳、支持和鼓励非正式社交这一社区/共同体生成机制的可能性,也即是一种特定的空间可供性。将这一论点与经验层面的分析相联系,我们采用地理符号学的逻辑和语汇,展示这一可供性如何可在不同符号系统的交织所形塑的人与场所的互动中生成。我们还以上海市嘉定区“我嘉书房”这个“社区公共文化场所”为例,显示这一理论视角如何体现在对经验观察的搜集、描述和解读当中。
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我嘉书房”的案例其实是我们反思“第三场所”概念的开始。我们意识到,套用第三场所概念的研究,往往导致相对静态的分析,它可能指向两极,要么为第三场所的消逝而与奥登伯格(Oldenburg, 1999)一样,感叹“往日不再”,要么从大型多人在线游戏或街坊邻居时常光顾的快餐店中觅得第三场所的新形态,并为之振奋。这个反思也让我们看到,第三场所概念其实有更深一层的理念蕴意,即“第三场所性”关系到日常生活的社会经纬如何被编制、维系和巩固。我们将第三场所性看作是行动者与空间互动的结果,并蕴藏于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据此,我们针对经验世界的设问,就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空间“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为“第三场所”这类问题,而是着眼于“第三场所性的体验如何可能”的问题。
如此设问将理论阐释引向了空间与传播的互构(潘忠党,於红梅,2015),我们在本文更具体表达为空间设计格局与空间使用实践之间的对话。首先,第三场所性是在空间与人互动过程中生成的一种可供性,即行动者可能镌刻、挖掘并实现的展开社交、建立联结、培育情谊、形成归属感的空间潜能。这种潜能通过体现社交性、公共性和物理性等的实体和/或数字界面设计(Calderon, 2016)而得以传递,并且被空间使用者所感知。这里的界面,即是可供性生成的人与环境/空间的互动过程,具有如“界面”一词所表达的空间性。
其次,借用地理符号学的框架和语汇(Scollon & Scollon, 2003),[24]我们显示,这个互动过程由不同符号系统交织着的编码和解码活动为元素,也就是空间设计和符号标记镌刻了规范行动的不同机制,如期待、准允、鼓励、启迪、制止或拒绝等(Davis & Chouinard, 2016),空间使用者感知并以自己的行动落实或突破这些潜能的表达,以不同方式的空间使用,包括匹配式、重组式、拓展式和转换式,获取第三场所体验。这些使用方式的区分,借鉴了霍尔(Hall,1980)对文本解读或意义建构的三种立场的论述,突出了场所的生成是一个交往互动和意义建构的过程这个基本原理。
第三,具体到获取第三场所的体验,“第三场所性”概念也限定了必要的空间属性及其表达,这包括卡尔德隆(Calderon, 2016)所提出的三个维度,以及本文提出的对空间四个方面的衡量:开放性、可达性、弹性和可读性。这些论述都是在强调,人们可获取第三场所体验的实体(或虚拟)空间,必须具有足够的开放、自由、宽松、便利等基本特性;这样的空间通常蕴含了规范性的期待,即平等、开放、培育归属感的活动,包括交往活动。
应用这个理论视角,我们呈现了“我嘉书房”如何成为“社区的公共文化场所”。由30家场馆组成的“我嘉书房”,是一个多样的去处,使用者可以因不同的动机造访它们,期待并获得不同体验,体现了空间使用的能动选择特性,还讲述着社区/共同体的群体身份。不仅如此,以什么方式、为获取怎样的体验而使用也因人而异,但这些体验的内容都与奥登伯格(Oldenburg,1999)所概括的自在、放松、愉悦、社交、活力、新鲜感、归属感等同类,从而可能具有“第三场所性”。
虽然本文限于篇幅未能展开讨论,但仍有必要提及的是,“我嘉书房”这个示例还说明,国家在打造具有第三场所性潜能的城市空间方面是主导力量,从建设规划到实施,再到论述它们的政策话语,政府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作为一组城市空间,“我嘉书房”具有蕴含第三场所性潜能的开放性、可达性、弹性和可读性,但同时也具有刷卡进门、读书区禁止喧哗、活动区可预定使用并用以展开文化类活动等的限制。不仅如此,活动的许可和安排,以及“嘉定文化云”这个虚拟平台的设置,也都是政府决策的结果;人们参与这些活动,也基本上是以非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形态,自发而主动地进入主流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参与表达和体验传统文化和国家意识。也就是说,奥登伯格未曾想到,不仅第三场所是“适度”开放和设计的空间,而且这个“度”的差异可能很大,在不同体制下,它蕴含的意义也大不相同。概括来说,在宏观层面,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会以其特定方式探寻与体制吻合的“第三场所”。
我们再回到本文开篇的实例:2022年春上海疫情期间居民楼或社区微信群的建设与使用。我们引用了相关报道,尤其是其中“回到了儿时弄堂”这个意象。这个实例也为本文设置了一个基调:探寻第三场所的感受可以有多种形态,有些是直接、实体在地的,有些可能是经过媒介技术中介的,甚至主要在虚拟空间。也就是说,第三场所性并非仅是实体空间的一种可供性,虚拟空间或者虚拟和实体空间的接合地带都可能具有第三场所性。本文对数字媒介在第三场所体验的形成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只是初步涉及,但是,第三场所性的概念本就源自卡尔德隆(Calderon, 2016)对数字技术平台和界面设计的考察,而本文将之进一步阐释为空间与使用者互动过程中的一种可供性,提出了衡量空间的四个方面,以及人们获取第三场所体验的四种空间使用方式。这些意念的组合,形成了一个概念的框架,可以逻辑地用以分析虚拟空间或数字媒介参与的空间。本文开篇的微信群例子和将“我嘉书房”的活动拓展到虚拟空间的观察,都至少提示了这一点。
不过,引入数字媒介,也在警示我们“作为可供性的第三场所性”这个论点可能的局限。本文的理论阐述预设了已有状况作为分析的起点,具体为“我嘉书房”这一组城市空间。如果我们加入日新月异的数字媒介技术,譬如社交媒体平台、算法和AI等开辟各种空间和行动的可能,我们必须把这个分析起点看作是移动、多变的。那么,我们就需要考察不断变换着——未必变幻莫测,但至少是变化多端——的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可能,需要能容纳这复杂多变的界面的理论概念。这是本文阐述的理论视角所需推进的一个方向,也需另文展开。■
注释:
①“一场疫情,让邻里关系回到儿时弄堂”,来源于澎湃新闻·澎湃号·人间像素,2022-05-18。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128684。
②澎湃新闻·市政厅主办的主题为“后疫情社区如何更加融合”(2020年6月26日)线下讨论会会议内容整理。检索于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262111。
③以波士顿为背景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干杯酒吧》(Cheers,1982-1993)主题曲的歌词,其中写道:“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人知道你姓甚名谁,他们都很高兴你的到来。你会想去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们知道我们彼此青睐。”
④2016年8月,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发布了《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提出了15分钟生活圈的建设目标,其中包括建设“绿色开放、活力宜人的公共空间”。参见https://up.caup.net/file/life-circle.pdf。
⑤吉布森在其1979年出版的《视觉的生态学方法》(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Visual Perception)中单辟一章(第8章)系统阐述其“可供性理论”(The theory of affordance)。本文采用的是2015年根据1986年版刊发的经典版。
⑥此处的“体验”即是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所说的experience,中译本(2017)将之译为“经验”。参见段义孚(2017),《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本文的引用,采用了2001年第八次印刷的1977年英文版。
⑦中文对community一词有社区或共同体这两种不同译法,体现了对其不同内涵的强调。参见黄杰(2019)对“Gemeinschaft”语词历程的文本解读;还可参见陈鹏(2013)对于“社区”概念本土化历程的解析。我们认为,“共同体”的译名更凸显一个文化或社会群体内人与人之间情感、经验、文化等层面的连结,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身份认同和归属(identity)。它凸显成员相互交流的频率和深度,强调交流的社会、认知和情感的建构作用。而“社区”的译名往往指的是在特定基础上(如身份、居住地、兴趣、活动等)相互联系密切的一群人。在传统社会学的研究中,社区往往与居住地相关联,暗指了有限的地理空间。在当下新媒介技术环境下,这样的“社区”也可能是基于共同兴趣(如共同的阅读爱好)或活动(如一起玩多人线上游戏)的群体,未必限定于某地理空间,在时间维度上可能更为短暂。但是,在经验的层面,社区不直接等同于共同体,因为后者更强调的共享的身份、归属和认同,携带了个体成员们相互间在心灵深处的平等沟通、和谐以及以此为内核的情感连结。可参阅[德]马丁·布伯(2002):《我与你》(陈维钢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⑧这里指的是二人对于非正式公共生活与公共性和社会资本培育之间关系及其历史趋势的分析。参见Richard Sennett(1992/1976),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Robert Putnam (2002)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⑨原文刊载于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的网站,https://courier.unesco.org/en/articles/third-places-true-citizen-spaces。还可参见Ray Oldenburg & Karen Christense (2023)Third Places: A Very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Great Barrington, MA: Berkshire Publishing Group。
⑩本文第三作者于2021年6月20日在“中国知网”以“第三场所”、“第三空间”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并对所得文献进行逐一浏览。奥登伯格提出的the third place概念,通常译作“第三场所”,但也有部分论文将其译为“第三空间”或“第三地方”。
[11]正如前文提及,奥登伯格和哈贝马斯都从西欧历史经验中挖掘灵感与资源以展开其理论建构。一如哈贝马斯的历史研究,奥登伯格在提出第三场所的概念时,信息和媒介技术尚未对社会产生与当下可比的深度影响。今天,书籍和告示牌已不若手提电脑、电子屏幕等醒目,实体空间壁垒已部分地被Wi-Fi所消解。简言之,数字和网络技术已经成为日常生活肌理和城市空间配置的一部分,这也拓展了人们获取第三场所体验的手段和平台,丰富了公共生活的形态、元素和过程,但这并不表明断裂式的历史变革。
[12]物件按照设计所生产出的可感线索(譬如车门把手、手机屏幕上App图标等),是提示或引导用户的“能指”,用户以其认知能力和过程感知这些能指,并解读出它们所表达的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s),包括对如何使用物件、它的功效等的理解,以此引导对物品的使用。诺曼对可供性和能指两者间的区别作了更为具体的说明。他指出,可供性指代人与物展开互动的可能性,能指则是这些可能性的信号,能指的形态多种多样。诺曼强调,好的设计应当是采用符合人的直觉、易被感知和准确解读的能指,引发用户选择适用的概念模型,并收取有效反馈,以调整自己的使用行为。
[13]这些在斯克伦夫妇看来都是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的系统;任何社会行动的场地(site of social actions)都有三者的交织。其中交往秩序可被理解为一个场所蕴含着对社会交往及其方式和形态的期待,它们大多是非正式的行事规则,由携带各种惯习的行动者心照不宣地体现于其行动之中。视觉符号学可被理解为一个场所对其性质、功能以及社会交往期待的表述,往往诉诸人们的视觉感官,虽然其它感官可能参与,拓展并丰富我们对空间的体验(Tuan,2001:16)。而多感官参与的可能,就来自于第三套系统,即场所符号学。斯克伦夫妇将此表述为前两者之外的自然景观和人工建造环境的各种符号系统的聚合(aggregate of semiotic systems)。引用戈夫曼,斯克伦夫妇论述道,社会行动者携带着运用各类符号的“符号设备”(sign equipment),处理这些符号以形成自己的社会行动。
[14]这个示例的经验材料部分来自本文第三作者的硕士论文。研究者在初步经验考察基础上,依照最大化差异原则,从三十家中选取了三家不同落点及风格的书房,并于2020年1月至11月期间,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它们展开了参与式观察。在考察过程中,研究者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对37人展开了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书房管理者、活动承办人以及志愿者,也包括空间的使用者。研究者还于2021年1月和3月数次回访了这三家书房,以期进一步印证本文所呈现的描述和解读。在本文中,我们将被访者的表达置于引号内,为阅读方便,我们将不一一陈列被访者。需了解田野考察展开的细节,可参考陈意如(2021)。第三场所理念下城市社区公共图书馆的传播实践研究:以“我嘉书房”为例。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未发表)。
[15]对深度城市化,官方的宣讲包括:(1)在已有城市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总体与局部水平(顾海兵,2002);(2)以人的城市化为核心的“城市化2.0”,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经济增长、城市宜居和社会和谐三个目标的共赢(陆铭等,2019),迈向城市的“人人共有”(city for all)。
[16]图片来源:(1)“我嘉书房”的商标来自上海嘉定:@嘉定人!“我嘉书房”有专属商标了!。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_l0KFpeItNvzvWo7Lt_Uvw;(2)嘉定图书馆外观来自“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17]黄艺芹,洪伟成:“我嘉书房”为百姓打造“家的书房”。检索于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307/c403992-29852490.html。
[18]第三作者分别摄于2020年1月20日和9月27日。
[19]“岁末再添两家!隔着屏都能感受到的满满书香!”。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eKZRBdsG8iMmwf7aLR5RlQ。
[20][22]“哪家‘我嘉书房’最符合你的气质呢?快来选出你心中的最爱”,上篇:http://www.jiading.gov.cn/jzpd/jztt/content_746543;下篇:http://www.jiading.gov.cn/jzpd/jztt/content_747089。
[21]图片来源:4a,第三作者摄于2020年10月10日;4b,“文化嘉定云”;4c,“上观”(https://www.jfdaily.com/sgh/detail?id=838983);4d,“上观”(https://sghexport.shobserver.com/html/toutiao/2021/09/08/532240.html)。
[23]“解密‘我嘉书房’|设计师手记”。检索于https://freewechat.com/a/MzA4MDE5NjUwNg==/2652640638/1。
[24]我们借助了斯克伦夫妇建构的地理符号学,但是,我们在本文的理论旨趣和经验关注与他们不同。他们关注在地的语言或具有语言特征的符号系统如何表意,我们更关注的是人在特定场所的行动,包括社交和分享的互动,关注这些行动如何通过解读在地的符号系统对场所的界定而展开。
参考文献:
常江,田浩(2021)。生态革命:可供性与“数字新闻”的再定义。《南京社会科学》,(5),109-117+127。
陈鹏(2013)。“社区”概念的本土化历程。《城市观察》,(6),163-169。
程大立,吴春祥(2019)。图书馆第三空间建设研究综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2),40-45。
胡翼青,马新瑶(2022)。作为媒介性的可供性:基于媒介本体论的考察。《新闻记者》,(1),66-76。
黄杰(2019)。“共同体”,还是“社区”?——对“Gemeinschaft”语词历程的文本解读。《学海》,(05),10-15。
黄雅兰,罗雅琴(2021)。可供性与认识论:数字新闻学的研究路径创新。《新闻界》,(10),13-20。
顾海兵(2002)。再城市化:深度城市化与逆向城市化的同步推进。《江海学刊》,(2),73-77。
雷蔚真(2004)。中、日、韩网吧发展初步对比研究。《国际新闻界》,(2),40-43。
李晴(2011)。基于“第三场所”理论的居住小区空间组织研究。《城市规划学刊》,(1),105-111。
刘臻(2017)。基于“第三场所”理论的城市修补实践——以珠海市社区体育公园为例。《持续发展 理性规划——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7城市设计)》,1269-1280。
刘志国,陈威莉,赵莹,刘蕾(2021)。第三知识建构场服务——基于理论基础演绎的图书馆空间服务认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38-45。
陆铭,李杰伟,韩立彬(2019)。治理城市病:如何实现增长、宜居与和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22-29。
[德]马丁·布伯(2002)。《我与你》(陈维钢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马中红,胡良益(2022)。数据基础设施:作为纵深维度的隐蔽可供性研究。《国际新闻界》,(8),6-27。
潘忠党,於红梅(2015)。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开放时代》,(3),140-157。
邵宇,王鹏,陈刚(2013)。重塑中国:新型城镇化、深度城市化和新四化。《金融发展评论》,(1),1-37。
孙凝翔,韩松(2020)。“可供性”:译名之辩与范式/概念之变。《国际新闻界》,(9),122-141。
王海燕,范吉琛(2021)。数字新闻的时间可供性:一个研究框架的提出。《国际新闻界》,(9),116-135。
谢静(2021)。移动社区:沟通性视域下的第三地方——兼论新游牧主义的社区传播。《南京社会科学》,(11),102-112。
徐笛,许芯蕾,陈铭(2022)。数字新闻生产协同网络:如何生成、如何联结。《新闻与写作》,(3),15-23。
曾丽红,叶丹盈,李萍(2021)。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女性“能动”的“可见性”——兼对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可供性”考察。《新闻记者》,(9),86-96。
曾旭正(2010)。地点,场所或所在论“place”的中译及其启发。《地理学报》,(58),115-132。
张志安,黄桔琳(2020)。传播学视角下互联网平台可供性研究及启示。《新闻与写作》,(10),87-95。
周芸熠(2013)。基于“第三空间”的图书馆范式转换。《情报资料工作》,(3),40-43。
Adams, P. C. & JanssonA. (2012). Communication Geography: A Bridge between Disciplines. Communication Theory, 22299-318doi:10. 1111/j. 1468-2885. 2012. 01406. x.
Brown, J. (2017). Curating the “Third Place”? Coworking and the Mediation of Creativity. Geoforum, 82112-126.
CalderonR. (2016). Third-placeness: Supporting the Experience of Third Place with Interactive Public Displays. PhD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Graduate and Postdoctor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Canada.
CheangM. (2002). Older Adults’ Frequent Visits to A Fast-food Restaurant: Nonobligatory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lay in A “Third Place. ”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16303-321.
Cresswell, T. (2009). Place. In R. Kitchin & N. Thrift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pp. 169-177). Amsterdam: Elsevier.
Davis, J. L.& ChouinardJ. B. (2016). Theorizing Affordances: From Request to Refuse. Bulletin of 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36(4)241-248. DOI: 10. 1177/0270467617714944.
GibsonJ. J. (1979/2015).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Habermas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By Thomas Burger). 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
Hall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 Willis (eds. ). CultureMediaLanguage (pp. 128-138). London: Unwin Hyman.
HaydenC.& Ball-Rokeach, S. J. (2007). Maintaining the Digital Hub: Locating the Community Technology Center in A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New Media & Society9(2)235-257.
Kim, Y. C.& Ball-Rokeach, S. J. (2006). Community Storytelling NetworkNeighborhood Contextand Civic Engagement: A Multilevel Approach.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4)411-439.
Lee, J. W.& LouJ. J. (2019). The Ordinary Semiotic Landscape of An Unordinary Place: Spatiotemporal Disjunctures in Incheon’s Chinatow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16(2)187-203.
Lou, J. J. (2017). Spaces of Consumption and Senses of Place: A Geosemiotic Analysis of Three Markets in Hong Kong. Social Semiotics 27 (4): 513-31.
Low, S. M. (2009). 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Space and Place. Semiotica175-1/421-37. DOI 10. 1515/semi. 2009. 041.
MasseyD. (1994). SpacePlace and Gender. Oxford: Polity Press.
McArthurJ. A.& WhiteA. F. (2016). Twitter Chats as Third Places: Conceptualizing A Digital Gathering Site. Social Media+Society, July-September, 1-9. DOI: 10. 1177/2056305116665857.
McGuire, S. (2008). The Media City: MediaArchitecture and Urban Spa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Memarovic, N.Fels, S.Anacleto, J.Calderon, R.GobboF.& CarrollJ. M. (2014). Rethinking Third Places: Contemporary Design with Technology. Journal of Community Informatics. 10(3). https://doi. org/10. 15353/joci. v10i3. 3440.
NormanD. A. (2013).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 Revised and Expanded. New York: Basic Books.
Oldenburg, R. (1999). The Great Good Place. New York: Marlowe & Company.
Oldenburg, R.& Brissett, D. (1982). The Third Place. Qualitative Sociology5265-284.
Oldenburg, R.& ChristensenK. (2023). Third Places: A Very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Great Barrington, MA: Berkshire Publishing Group.
PackerJ.& WileyS. B. C. (Eds. ) (2012). Communication Matters: Materialist Approaches to MediaMobility and Network. London: Routledge.
PetersS. (2019). Sharing Space or Meaning? A Geosemiotic Perspective on Shared Space Design. Applied Mobilities, 4(1)66-86.
PutnamR. (2002)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Ravelli, L. J.& McMurtrieR. J. (2016). Multimodality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Spati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Rosenbaum, M. S.Ward, J.Walker, B. A.& Ostrom, A. L. (2007). A Cup of Coffee with A Dash of Love: An Investigation of Commercial Social Support and Third-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10(1)43-59.
Scollon, R.& ScollonS. W. (2003).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 London: Routledge.
Sennett, R. (1992/1976).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Simon, B. (2009). Everything but the Coffee: Learning about America from Starbuck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impson, P. (2011). Street Performance and the City: Public SpaceSocialityand Intervening in the Everyday. Space and Culture14(4)415-430.
SoukupC. C. (2006).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s A Virtual Third Place: Building Oldenburg’s Great Good Places on the World Wide Web. New Media & Society8421-440. DOI: 10. 1177/1461444806061953.
SteinkuehlerC. A.& Williams, D. (2006). Where Everybody Knows Your (screen) Name: Online Games as “Third Plac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1885-909.
Theng, A. J.& LeeT. K. (2022). The Semiotics of Multilingual Desire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s Elite Foodscape. Signs and Society10(2)143-168.
TuanY. F. (1977/2001).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Vilnai-YavetzI.& RafaeliA. (2021). Workspace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Linking the Symbolic and Social Affordances of the Workspace to Employee Wellbeing. Sustainability, 13(21)11985.
Whyte, W. H. (1980).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 New York: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Wineman, J. D.& PeponisJ. (2010). Constructing Spatial Meaning: Spatial Affordances in Museum Design.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2(1)86-109.
WithagenR.de Poel, H. J.AraújoD.& PeppingG. J. (2012). Affordances Can Invite Behavior: Re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ordances and Agency.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30250-258.
WrightS. (2012). From “Third Place” to “Third Space”: Everyday Political Talk in Non-political Online Spaces. Javnost-the public, 19(3)5-20.
Young, F.& ClevelandB. (2022). AffordancesArchitecture and the Action Possibilities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Future Directions. Buildings1276; https://doi.org/10.3390/buildings12010076.
於红梅系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纪录片学院副教授,潘忠党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教授,陈意如系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纪录片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