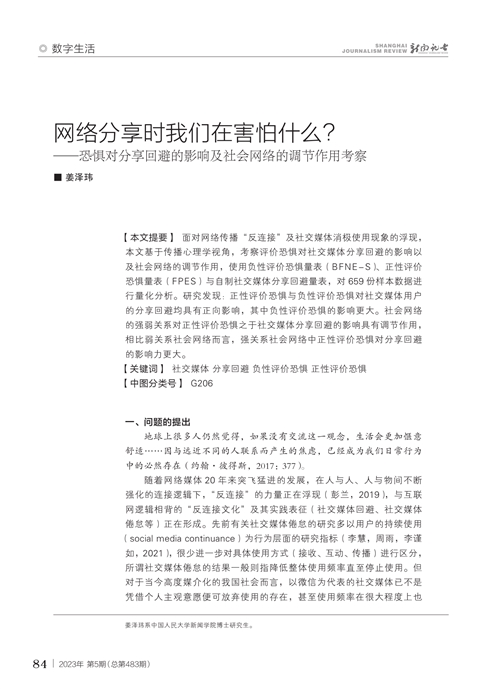网络分享时我们在害怕什么?
——恐惧对分享回避的影响及社会网络的调节作用考察
■姜泽玮
【本文提要】面对网络传播“反连接”及社交媒体消极使用现象的浮现,本文基于传播心理学视角,考察评价恐惧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的影响以及社会网络的调节作用,使用负性评价恐惧量表(BFNE-S)、正性评价恐惧量表(FPES)与自制社交媒体分享回避量表,对659份样本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正性评价恐惧与负性评价恐惧对社交媒体用户的分享回避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负性评价恐惧的影响更大。社会网络的强弱关系对正性评价恐惧之于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相比弱关系社会网络而言,强关系社会网络中正性评价恐惧对分享回避的影响力更大。
【关键词】社交媒体 分享回避 负性评价恐惧 正性评价恐惧
【中图分类号】G206
一、问题的提出
地球上很多人仍然觉得,如果没有交流这一观念,生活会更加惬意舒适……因与远近不同的人联系而产生的焦虑,已经成为我们日常行为中的必然存在(约翰·彼得斯,2017:377)。
随着网络媒体20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人与人、人与物间不断强化的连接逻辑下,“反连接”的力量正在浮现(彭兰,2019),与互联网逻辑相背的“反连接文化”及其实践表征(社交媒体回避、社交媒体倦怠等)正在形成。先前有关社交媒体倦怠的研究多以用户的持续使用(social media continuance)为行为层面的研究指标(李慧,周雨,李谨如,2021),很少进一步对具体使用方式(接收、互动、传播)进行区分,所谓社交媒体倦怠的结果一般则指降低整体使用频率直至停止使用。但对于当今高度媒介化的我国社会而言,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已不是凭借个人主观意愿便可放弃使用的存在,甚至使用频率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个人能够把控,相比之下,分享回避、互动回避等作为传播者层面的消极使用在反映社交媒体倦怠这一现象上更为现实。尽管社交媒体发展至今已融合了多种功能,但用户分享行为仍是支撑社交媒体运作乃至当今整个互联网传播体系运转的基本动能。
社交媒体倦怠往往伴随着用户的矛盾心理,有关持续使用层面的研究揭示了感知有用性、感知趣味性与疲劳感、时间消耗之间的矛盾(Han, 2018)。对于分享行为而言,用户则处于如下两种力量的对抗之中:一方面是人们渴望分享、交往、互动的感性动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担心、害怕、恐惧的理性风险感知,当前者盖过后者时,用户可无所顾忌地在社交媒体中频繁分享内容并享受互动过程;而当后者彻底压过前者时,分享回避便得以形成。更多的时候人们则居于二者之间,网络传播实践中的“朋友圈分组”、“可见周期设置”、“阅后即焚”等社交媒体的功能设置及用户使用行为正是对这两种对抗力量的一种调节机制,以使社交媒体分享行为能够在感性与理性、动力与阻力间寻得平衡点,从而维持社交媒体生态的运行。依照传播学“使用满足”的基本理论逻辑,先前大量研究已揭示了不同情境下,网络用户内容分享的动因、满足及其心理活动机制,但对于“不使用的满足”的理解却相对匮乏,除媒介与社会环境构成的各种结构性影响外,心理学中的“评价恐惧”理论或可从社交媒体的用户心理出发,为这一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视角。
网络社交中的个体时时处于表演与自我审查之中,人们在参与各种分享活动时,都需要从他人的角度考虑自己言行的效果与后果(彭兰,2019),当这种考虑达到一定程度后所引发的担忧、紧张、恐惧便形成了评价恐惧的心理。评价恐惧又可分为正性评价恐惧和负性评价恐惧两类,二者作为两个独立的心理结构(叶友才,林荣茂,严由伟,2021),以不同的机制作用于人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负性评价恐惧指人们惧怕自己的社会行为可能会引起他人的负面评价,因而往往会以更好的一面进行自我呈现。正性评价恐惧指人们对自身社会行动可能招致的正面评价的恐惧(Weeks et al., 2008),这一心理活动机制一般认为来自他人过多的正面评价将导致自己在他人心目中期待、要求、标准的提升(Reichenberger, Blechert, 2018),同时也可能引发来自他人更多的竞争与妒忌,由此产生不安与恐惧(Weeks, Howell, 2012)。那么,对于社交媒体分享行为回避而言,究竟是哪一种评价恐惧的心理机制发挥了作用?或是二者兼有,抑或是并无关系?对于个体而言,正性与负性的评价恐惧可能以不同程度的水平同时存在,但在不同的传播语境下,二者作用于社会行动的影响力可能存在差异,这便需要进一步分析在何种情况下负性评价恐惧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的影响更大?何种情况下正性评价恐惧的影响更大?从而才能进一步细致与深入地洞察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的心理机制。本文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RQ1:正性与负性评价恐惧是否均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具有影响?二者的影响力有无
差异?
RQ2:在不同传播语境下,正性与负性评价恐惧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的影响有无变化?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核心变量:评价恐惧与社交媒体分享回避
自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产生并发展至今,用户在社交媒体使用中已表现出诸多负面心理及行为,先前新闻传播学、心理学、情报与信息科学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社交媒体倦怠”、“社交媒体回避”、“社交媒体焦虑”等关键词展开。在梳理各学科先前研究间的主要关联及脉络后发现,“社交媒体倦怠”作为一种用户心理现象处于相关研究的核心位置,Ravindran等(2013)认为,社交媒体倦怠是一种由疲倦、烦恼、恼怒、失望、戒备、兴趣丧失、动机减弱等情感构成的主观用户体验;Lee等(2014)认为,社交媒体倦怠是指与社交媒体有关的疲劳、烦恼和厌烦的感觉;社交媒体倦怠的心理进而会导致或反映社交媒体的回避行为(代宝,罗蕊,续杨晓雪,2019)。从行为层面看,社交媒体倦怠所对应的行为表现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接收行为回避(不刷朋友圈、微博,不看新闻资讯等);(2)互动行为回避(不给他人点赞、评论,延缓或忽略消息回复,不主动与他人在线聊天等);(3)分享行为回避(不发朋友圈、微博等)。三个层面的整合即为社交媒体消极使用、不持续使用或停止使用。先前相关研究的问题及研究对象彼此层次不同,既有对作为整体性概念的社交媒体回避、消极使用或停止使用的研究,也有对某一个具体层次(接收、互动或分享)的研究,不同层面的回避行为具有不同的成因,但彼此也存在关联与互动。本研究所考察的对象是信息分享层面的回避行为,这一层面的研究现状在以“社交媒体倦怠”为核心概念的问题域中尚处较为薄弱的地位,对分享回避成因的进一步研究也有助于全面理解作为整体性概念的社交媒体倦怠心理及消极使用行为。
在各类社交媒体倦怠心理及回避行为的成因中,隐私担忧(申琦,2015;牛静,孟筱筱,2019)、公私界限模糊(赵晨等,2021;张铮,陈雪薇,邓妍方,2021)、广告侵扰(宣长春,2021)、低质量内容(张大伟,王梓,2021)是先前研究涉及最多的因素,其中后三项主要指向信息接收行为而非分享行为。有关分享行为回避的研究中,申琦(2015)对上海市大学生的微信移动社交应用的研究表明,隐私关注与隐私保护对社交媒体自我表露行为产生负向影响,但仅仅通过隐私问题的角度仍不足以完全解释社交媒体分享回避行为,“隐私悖论”理论便说明了人们的隐私关注与表露行为之间的矛盾性。也有实证研究发现隐私关注对用户表露实际上并无直接影响,而是其他中介变量在发挥作用(Toddicken, 2014)。用户在发布内容时所担心或恐惧的并非只有他人对自己的认知,还包括来自他人可能的态度与评价,Zeng等(2021)的一项针对微信样本的研究发现,正性与负性评价恐惧均对网络自我表露量(AOSD)有显著负向影响,知道自己会被广泛的受众观察和评价的人会更加谨慎地在社交媒体上暴露自己,从而降低了他们在社交空间中更新动态的积极性和热情。从社交焦虑这一心理学概念的角度看,先前多项研究已证实负性评价恐惧可以显著预测社交焦虑(彭顺等,2019),Alkis等(2017)编制的社交媒体用户社交焦虑量表(SAS-SMU)的四个维度中包括“内容发布焦虑”(shared content anxiety),可以看出内容发布焦虑是构成线上社交焦虑的重要指标,进而导致社交媒体使用的疲劳感、倦怠感以及消极使用的态度与行为(Straus, 1979;陈必忠等,2020)。在SAS-SMU量表中同时也涉及“评价焦虑”的维度,反映了“评价焦虑”与“内容发布焦虑”均与线上社交焦虑,社交媒体回避、倦怠、消极使用等心理活动及行为有关。从正性评价恐惧的心理机制看,主体恐惧的是积极评价可能引发的被他者妒忌以及来自他者过高的要求或期待(Weeks, Howell, 2012)。心理学相关研究表明,“隐藏行为”是社交中个体避免成为被妒忌者而常使用的一种应对策略,具体表现为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所获奖励、优秀表现、身份地位等(刘得格等,2018)。由此可见,在社交媒体中减少或回避分享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主体对自身可能遭致妒忌的担忧。综合先前有关社交媒体用户的负面心理及行为的研究以及正负性评价恐惧的特征,本研究假设:
H1:负性评价恐惧正向影响社交媒体分享回避。
H2:正性评价恐惧正向影响社交媒体分享回避。
(二)调节变量:强弱社会网络关系
社会学中强弱关系的概念源于社会网络研究,所谓社会网络一般指“一定范围的个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贺寨平,2001),Granovetter(1973)将社会网络中关系的强度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并提出了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测量强弱关系的维度。先前研究已证实关系性压力是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因素之一(赵启南,2019),不同的社会网络会形成不同程度的人际关系结构与关系性压力,从而影响用户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也有诸多研究证实,网络自我表露行为同所处的网络传播环境及匿名程度具有密切关系(Ben-Ze’ev, 2003;Barak, 2007),尤其是由强弱关系构成的传播情境对社交媒体倦怠具有显著影响(徐颖,于雨禾,张桓森,2021),因而可以假设,社交媒体用户所处的不同社会网络将影响正负性评价恐惧在社交媒体分享回避中的作用机制。在社交媒体传播中,社会网络一般可分为以微信为代表的强关系社交媒体与以微博为代表的弱关系社交媒体,强关系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多处于“熟人圈子”之中,信息传播的覆盖面较小;弱关系社交媒体的使用者更大程度上面对的是“陌生人圈子”,信息传播的覆盖面也相对更大。在网络舆论的生成过程中,基于陌生网民互动的“网络暴力”、“人肉检索”、“键盘侠”等互联网群体传播现象显现出了鲜明的负性评价,当舆论场中的负性评价与非理性因素相勾连并走向偏激后,对涉事个体的伤害将极其巨大。对于“熟人圈子”构成的强关系社交媒体而言,“面子理论”认为社会交往中的行动者双方会考虑到对方的“面子”,达成相互的服从、尊重与恭敬,“面子”既是彼此的期望,也是彼此给予对方的回报(王轶楠,杨中芳,2005),这也可解释何故微信朋友圈中的负面评价远远少于微博、知乎等平台。正性评价恐惧并非完全拒绝自我的良好形象,而是对自我良好形象可能引发的竞争加剧与他人的高期待、高要求的恐惧(叶友才,林荣茂,严由伟,2021),这些问题则主要出现于熟人社会。由此本研究假设:
H3:在强关系为主的社交媒体中,正性评价恐惧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的影响更大。
H4:在弱关系为主的社交媒体中,负性评价恐惧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的影响更大。
(三)控制变量:社会人口因素
年龄与性别是社会研究中常用的社会人口因素变量,先前部分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用户的性别、年龄等因素均对社交媒体倦怠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徐颖,于雨禾,张桓森, 2021;刘天元,2019)。但也有研究发现年龄与性别对社交媒体自我呈现、持续使用等行为并无直接与显著影响,虽然不同性别与年龄阶段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心理及行为可能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是线性的直接关系,而是多元与复杂的(Kisilevich, Ang, Last, 2011;Han, 2018)。因此,本研究将用户的年龄与性别纳入控制变量。
我国社会具有显著的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农村社会的网络关系规模较小、稳定性强、文化结构较为单一,且多为强关系的私人联系;城市中的社会网络关系规模较大、流动性强、多元文化交叉、弱关系所占比重大。先前诸多研究显示,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差异形成了舆论场的分化(张晋升,刘蓓,2016),媒介技术基础、用户使用习惯等多方面的差异(张苏秋,王夏歌,2021;吴信训,高红波,2011)。由此看来,城乡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对于社交媒体用户的分享行为可能产生影响,本研究将用户的户籍(城镇-农村)纳入控制变量。
“体制内外”是我国社会特有的一种职业划分方式,有学者指出,21世纪以来体制内外群体在个人生活、社会生活满意度、不平等感受程度、社会冲突意识等多方面的社会态度及利益诉求具有较大差异(李春玲,2011)。也有研究发现,网络圈子效应存在“体制内-体制外”的组别差异,体制内个体更容易受到网络圈子的影响,其中越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受到来自业缘圈子的贬抑效应越强烈(夏倩芳,仲野,2021)。因此,本研究将用户的职业(体制内-体制外)纳入控制变量。
社会经济地位是受众研究中的重要因素,在成熟的互联网社会中线上行为将越来越多地反映出线下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不平等关系(Deursen, Dijk, 2014;王正祥, 2010)。Swirsky等(2022)的一项研究发现,青少年在青春期的社会地位与社会目标会正向激励社交媒体中的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自我表现(self-presentation)等使用行为,也有研究证实,信息共享和地位寻求满足对新闻共享有显著影响,在社交媒体中分享低质量内容将损害传播者个人的社会地位(Thompson, Wang, Daya, 2020)。相比社会地位较低者,高社会地位者对参与网络传播的风险感知更强,从事风险行为的可能性也较小(Hwang et al., 2010)。因此,本研究将用户的社会地位(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纳入控制变量(本研究的控制变量编码见表1 表1见本期第88页)。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社交媒体用户的评价恐惧程度作为研究的自变量,评价恐惧又可分为负性评价恐惧与正性评价恐惧两种不同的心理结构。以社交媒体分享回避作为研究的因变量,由强弱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作为研究的调节变量(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 图1见本期第88页)。
三、研究方法
(一)概念界定及测量
1.社交媒体分享回避
社交媒体分享回避是构成社交媒体倦怠及其消极使用行为(接收、互动、分享)的三个层面之一,也可看作是社交媒体语境下的自我表露回避。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是个体对他人表达情感、想法与观点的窗口(蒋索,邹泓,胡茜,2008),有研究将网络自我表露定义为“个体在网络上运用多种方式向他人传递信息,以达到维持网络沟通或获得个人需求的网络行为”(谢笑春,孙晓军,周宗奎,2013)。先前研究中尚未见到直接针对社交媒体分享行为回避的量表,相关研究有在自我表露量表的基础上对陈述问题进行修改,使之有针对性地面向微信媒介,以此测量微信用户的分享回避行为(Zeng, Zhu, 2021)。目前心理学研究中常使用的自我表露量表(Self-Disclosure Index, SDI)(Miller, Berg, Archer, 1983;李董平等,2006)及其他相关量表并不适合直接挪用于对社交媒体分享行为的测量,因而需制定专门用于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的量表。本研究从“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与“其他事物的描述或评价”两个范畴出发,编制了内含8个题项的社交媒体分享回避量表,所制量表可供后续相关研究进一步检验及修正(表2 表2见本期第89页)。在本研究中,社交媒体分享回避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9, KMO值为0.836,其中日常生活自我呈现范畴下4个题项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47,KMO值为0.762;其他事物的描述或评价范畴下4个题项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36,KMO值为0.758。
2.负性评价恐惧
Leary(1983)提出的简版负性评价恐惧量表(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Straitforward,BFNE-S)是心理学研究中对负性评价恐惧测量时较多使用的量表,共包含12条陈述,使用“1至5分”的李克特式五级评分表示“完全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的评价。原表含8条正向表述,4条反向表述,Weeks等(2005)的研究表明,原表的反向表述可能造成错误与混淆,因而本研究只参考其中8条正向表述,经研究者自行翻译制定问卷内容(表3 表3见本期第89页)。在本研究中,负性评价恐惧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46, KMO值为0.895。
3.正性评价恐惧
相比负性评价恐惧的概念而言,正性评价恐惧作为心理学概念的正式提出较晚,Weeks等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叶友才,林荣茂,严由伟,2021),将之定义为“对他人给予的积极评价感到恐惧,并因此而担忧的一种情绪反应”(Weeks et al., 2008)。对于正性评价恐惧的测量,Weeks等提出了包含10个陈述条目的正性评价恐惧量表(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Scale, FPES),使用“0至9分”的李克特十级评分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的评价,其中第5题和第10题为减少用户回答问卷的默认反应偏差而设置,反向计分且不计入总分(Weeks, Heimberg, Rodebaugh, 2008)。该量表在先前相关研究中的普及度较高(杨鹏等,2015;Zeng, Zhu, 2021),本研究同样使用Weeks等提出的FPES量表测量正性评价恐惧,具体表述由作者结合英文内容及中文语境自译(表4 表4见本期第90页)。在本研究中,正性评价恐惧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0,KMO值为0.852。
(二)数据收集
问卷调查面向中国内地社交媒体用户,研究中分别以微信与微博两个平台代表强关系与弱关系社交媒体,通过分发并统计来自不同平台用户的问卷数据以检验社会网络关系的调节作用。问卷制定以上文所述量表为基础,共分三个部分:(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2)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程度;(3)正负性评价恐惧程度。共31项问题。问卷通过网络社交媒体滚雪球式发放,回收到面向微信用户与微博用户的两套问卷共691份(微信358份,微博333份),排除32份无效作答的问卷后,①以659份问卷的数据作为量化分析的总样本(微信338份,微博321份)。其中,男性300人(45.5%),女性359人(54.5%);城镇户口481人(73%),农村户口178人(27%);体制内325人(49.3%),体制外334人(50.7%);领导职务192人(29.1%),非领导职务467人(70.9%);年龄分布从16岁至92岁(M = 41.78,SD = 17.89)(表5 表5见本期第90页)。
四、数据分析
(一)核心变量关系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分享回避”(N = 659, M = 25.273, SD = 9.255),自变量为“负性评价恐惧”(N = 659, M = 22.774, SD = 8.884)与“正性评价恐惧”(N = 659, M = 20.399, SD = 7.221),数据分析首先对以上四个变量的基本关系进行检验(表6 表6见本期第90页)。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分享回避”同“正性评价恐惧”(r = 0.383, p < 0.01)与“负性评价恐惧”(r = 0.479, p < 0.01)均显著正相关,其中“负性评价恐惧”同“分享回避”的相关性更强。此外,“正性评价恐惧”与“负性评价恐惧”之间也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608, p < 0.01)。
(二)评价恐惧对分享回避的影响
数据分析采用分层回归方法,研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以及调节变量增加时带来的模型变化,本次分层回归分析共涉及2个模型,“模型1”中的自变量为“负性评价恐惧”与“正性评价恐惧”,“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性别”、“年龄”、“户籍”、“职业”、“地位”5个调节变量,模型的因变量为“社交媒体分享回避” (表7 表7见本期第91页)。
由“模型1”可知:“负性评价恐惧”和“正性评价恐惧”可以解释社交媒体分享回避24.5%的变化原因,该模型通过F检验(F = 106.694, p < 0.01)。其中,负性评价恐惧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B = 0.410, t = 9.205, p = 0.000 < 0.01),正性评价恐惧也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B = 0.187, t = 3.409, p = 0.001 < 0.01)。回归方程为:分享回避 = 12.136 + 0.410 * 负性评价恐惧 + 0.187 * 正性评价恐惧。
由“模型2”可知:在“模型1”的核心变量基础上加入“性别”、“年龄”、“户籍”、“职业”、“地位”5个调节变量后,核心变量仍旧呈现出显著的影响关系,具体表现为:负性评价恐惧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 = 0.463, t = 10.074, p = 0.000<0.01),正性评价恐惧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 = 0.118, t = 2.098, p = 0.036 < 0.05)。加入控制变量后的“模型2”的解释力度由24.5%上升到34.4%,F值呈现显著性(F = 48.761, p < 0.01),意味着控制变量加入后模型具有解释意义,且控制变量可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产生9.9%的解释力度。
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具体表现为:性别会对分享回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B = -2.127, t = -3.171, p = 0.000 < 0.01),即男性用户的社交媒体分享回避高于女性用户。年龄不会对分享回避产生影响(t = 1.79, p = 0.074 > 0.05)。户籍会对分享回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B = -2.112, t = -2.72, p = 0.007 < 0.01),即城镇用户的社交媒体分享回避高于农村用户。职业会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B = -3.522, t = -5.175, p = 0.000 < 0.01),即体制内用户的社交媒体分享回避高于体制外用户。地位会对分享回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B = -3.946, t = -5.835, p = 0.000 < 0.01),即领导职务用户的社交媒体分享回避高于非领导职务用户。总结分析可知:负性评价恐惧与正性评价恐惧均会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负性评价恐惧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的影响力更大,证实假设H1、H2。
(三)社会网络的调节作用
在分析调节效应前首先对研究变量的数据进行处理,本研究的自变量(评价恐惧)与因变量(分享回避)为定量数据,调节变量(社会网络[0 = 强关系,1 = 弱关系])为定类数据,因此对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对调节变量进行虚拟变量处理,以“强关系社会网络”作为参照对比项(见表8)。
对“社会网络”变量的调节效应检测中,设置“负性评价恐惧 * 弱关系社会网络”与“正性评价恐惧 * 弱关系社会网络”两个交互变量,生成线性回归模型。结合表9、表10与图2可知:“负性评价恐惧 * 弱关系社会网络”的交互项未呈现显著性(t = -1.563, p = 0.119 > 0.05),“正性评价恐惧*弱关系社会网络”的交互项呈现显著性(t = -2.703, p = 0.007 < 0.01)。由此可以证明:由强弱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并不影响负性评价恐惧(自变量)与分享回避(因变量)的关系,但正性评价恐惧(自变量)与分享回避(因变量)的关系却会因所处社会网络关系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调节变量在不同水平上的影响差异具体表现为:相比弱关系社会网络而言,强关系社会网络中的正性评价恐惧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的影响更大,由此证实假设H3,推翻假设H4。
五、总结与讨论
以“反连接”文化与社交媒体倦怠为核心的用户消极使用心理及行为是网络媒体传播发展至今尤须重视的问题。作为技术力量的社交媒体并未对人实现彻底的宰制,在“万物皆媒”、“万物互联”的当下,人们仍旧会努力地从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出发,理性且能动地利用媒介而非全然顺应技术的逻辑。本研究证实了正负两种评价恐惧心理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的影响作用,以及在不同强弱关系的传播语境下,正性评价恐惧对于分享回避影响力的变化。由此可见,此前未受到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评价恐惧”是理解社交媒体用户心理及行为的一项重要因素。综上所述,以下对本文研究发现及结果进行汇总与简要阐释:
其一,研究发现了社交媒体用户的评价恐惧心理对其分享回避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负性评价恐惧与正性评价恐惧两种不同的心理机制均正向影响社交媒体分享回避行为,其中负性评价恐惧的影响力更大。以往研究对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内容分享回避的解释多集中于隐私问题,但隐私担忧并不能完全解释各种情境下用户放弃内容分享的心理机制。自我呈现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必须牺牲个人隐私,只要隐私的让渡可以带来正面社会效应、促进自我形象管理、增加生活的幸福感与满足感,个体隐私并非必然阻碍分享回避。但反之,若我们让渡了个人隐私也并不能得到期望的正面回馈,却可能引发来自他者与社会的负面评价,进而对自身在集体与社会中的生存造成威胁,隐私担忧对分享回避的影响效应便得以显现。因此,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交媒体分享回避心理及行为,其更深层且更直接的动因可能来自对自身社会评价的恐惧及其可能产生的风险。
其二,研究发现了社会网络关系在评价恐惧与社交媒体分享回避间的调节作用,正性评价恐惧之于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的影响效应在强关系社会网络中更为显著。过往心理学研究更多关注负性评价恐惧,正性评价恐惧作为较新概念尚缺乏广泛关注与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对社会网络调节效应的研究发现,未来尤其在理解强关系社交媒体的用户心理及行为时应更加重视正性评价恐惧的作用。在以微博为代表的弱关系社交媒体中,用户分享内容时的担忧更多来源于对负面评价的恐惧,而在以微信为代表的强关系社交媒体中,正性评价恐惧的影响力得到提升,兼由正负两种评价恐惧带来的社交焦虑则更为矛盾与纠结。一方面,分享者会担心发布内容可能给自己带来负面的社会评价,因而试图采用各类技术性手段以提升自我的正面形象,运作着社交媒体中的印象管理;但另一方面,积极的自我形象所带来的正性评价也并非好事,也可能引发他者及其所处群体的妒忌、竞争,以及对自身要求与期待的提升,由此产生来自社交媒体分享的正性评价恐惧。在正负两种评价恐惧心理同时发生效应时,社交媒体使用者的分享意愿便陷入了“两难”的处境,面对失去工具理性价值的社交媒体分享行为,用户最终不得已选择“回避”这一最为简便的对策以降低社会生存的不确定性。
其三,研究发现了部分社会人口因素与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的关系。其中值得后续研究进一步关注的几个饶有趣味的变量有“体制内外”、“城乡户籍”以及“领导/非领导职务”对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的影响。例如相比体制外、农村户籍以及非领导职务的用户而言,体制内、城市户籍以及领导职务用户在社交媒体中的分享意愿可能更低。由此将引发我们面向未来网络话语空间的应然与实然、趋势与走向、技术可供性与使用者需要、平台逻辑与用户逻辑等关系的进一步思考。未来社交媒体的话语空间会逐渐走向以哪些群体的声音为主的场域?哪些人正在积极展演中“入场”?又有哪些人正在暗处凝视中悄然“离场”?
面对我国社会与日俱增的社交媒体倦怠及分享回避现象,结合本研究所揭示的正负性评价恐惧心理之于社交媒体分享回避的影响效应,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指向实践的意见建议:
第一,从社交媒体所处的社会环境看,因网络言论而引发涉及自身、家庭、单位以及国家社会的舆情事件、危机事件、负面事件增多,由社交媒体内容分享引发的具有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加重网民的评价恐惧心理,这也让许多人最终彻底放弃在社交媒体中分享内容。现阶段我国的互联网治理主要以打击不良信息为主,但要营造真正清朗的网络空间不仅是“做减法”,同时也需要“做加法”。互联网治理应注重培育良好的社交媒体生态环境、保障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明确网络言论的边界及清晰的法律责任,为来自多元群体积极、理性的清朗之声提供土壤。
第二,从社交媒体内部系统及其技术可供性看,目前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分享及互动功能仍旧较为单一,未来社交媒体的技术开发及运营工作应关照用户群体中新兴的心理现象及使用需求,提供更为丰富、多元、个性化的互动功能。例如:社交媒体中的“点赞”功能可以提供“仅对方可见”、“指定好友可见”、“分组好友可见”、“共同好友可见”、“任何人均可见”等多元化的呈现选项;用户分享内容的“可见周期”可以由“三天/一周/半年”等客观时间尺度向用户定制化发展,以不同观看者的初次浏览时间为起点设定分享内容的可见周期,同时应由发布者自行决定内容是否可以保存(复制/下载/转发),观看者在保存社交媒体中其他用户的分享内容时,内容发布者应收到系统提示或准许通知。
第三,从社交媒体用户的媒介素养看,培育与提升我国民众的媒介素养一直以来都是网络与社会治理工作致力追求的目标,但以往更多关注作为信息接收、识别层面的“观看者媒介素养”,未来应更加重视对“分享者媒介素养”的培育。面对个体情绪层面的分享欲望以及理性需要层面的印象管理,社交媒体用户需要知悉与学习如何更好地、更为细致与科学地进行自我形象管理;还可通过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在用户编辑内容或发布内容前提示分享内容可能存在的伦理法规问题、虚假信息、不当内容、负面效应、情感过激等,一方面有助于网络安全治理由“事后控制”转向“事前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作为“不确定性”的评价恐惧的“确定性”或“可预见性”,以此降低评价恐惧心理对社交媒体内容分享的影响。
最后,在研究局限性与后续研究方面,本研究的抽样方法并非随机抽样,受限于所选样本及非概率抽样的局限性,研究结果是否能推至更大范围的一般人口仍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的问题在于探究多个变量间的关系而非单独对某一变量进行分析,故一般人口的随机样本并非是必需的(黄宏辉,2020),本次实证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具有意义的研究发现,丰富了对于评价恐惧与社交媒体分享回避关系的理解。在评价恐惧与社交媒体分享回避关系的后续研究中,诸如:评价恐惧对分享回避的影响机制同隐私感知之间的关系、同用户自身人格的关系如何,评价恐惧对分享回避的影响机制同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又处于何种互动关系,可作为下一阶段的研究任务。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质性文本的自我报告也是测量自我表露意愿及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通过量化研究所考察的是作为个体稳定心理状态的评价恐惧与整体使用上的分享回避程度间的关系,而访谈法可以从更微观的视角对用户的某一次具体回避行为及其心理活动进行分析,这种情景式与独特性的资料是量化研究所不能揭示的。尤其可进一步关注那些只在信息分享层面体现出消极状态,而在信息接收层面却属于积极或正常使用者的对象,破除既往研究将“社交媒体倦怠”不加分层地看作整体性概念的误区。在以社交媒体倦怠为核心的问题域中,如何将接收、互动、传播等不同层面的社交媒体消极使用心理与行为进行勾连,构建更为全面的评价体系,生成更加系统化的理论尤为重要,如此方能使该领域的研究逐渐由既见“树木”走向也见“森林”。■
注释:
①微信和微博分别代表强关系与弱关系社交媒体,研究中分别采集样本以检验调节变量的效应。
②以下情况被视为无效作答:(1)全部问题均选择一个选项,(2)作答时间小于60秒,(3)评价恐惧量表的内部逻辑明显错误。
参考文献:
陈必忠等(2020)。社交媒体用户社交焦虑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的初步应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6),1190-1193+1198。
代宝,罗蕊,续杨晓雪(2019)。社交媒体倦怠:含义、前因及后果。《现代情报》,(9),142-150。
黄宏辉(2020)。青年群体社交媒体倦怠的成因和对在线社区脱离意向的影响。《新闻记者》,(11),38-53。
贺寨平(2011)。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76-82。
蒋索,邹泓,胡茜(2008)。国外自我表露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1),114-123。
李春玲(2011)。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社会》,(2),125-152。
李董平等(2006)。青少年自我表露和自我隐瞒的特点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4),83-90。
李慧,周雨,李谨如(2021)。用户正在逃离社交媒体?——基于感知价值的社交媒体倦怠影响因素研究。《国际新闻界》,(12),1120-141。
刘得格等(2018)。被妒忌:一种矛盾体验。《心理科学进展》,(1),118-133。
刘天元(2019)。年轻女性为何热衷在网络社区分享“好物”?——基于动因理论的分析。《中国青年研究》,(7),91-97+112。
牛静,孟筱筱(2019)。社交媒体信任对隐私风险感知和自我表露的影响:网络人际信任的中介效应。《国际新闻界》,(7),91-109。
彭兰(2019)。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国际新闻界》,(2),20-37。
彭顺等(2019)。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基于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心理发展与教育》,(1),121-128。
申琦(2015)。自我表露与社交网络隐私保护行为研究——以上海市大学生的微信移动社交应用(APP)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4),5-17+126。
吴信训,高红波(2011)。《我国城乡IPTV需求与发展的失衡与对策——上海、河南两地受众调查的实证研究》。《新闻记者》,(4),79-83。
王轶楠,杨中芳(2005)。中西方面子研究综述。《心理科学》,(2),398-401。
王正祥(2010)。社会经济地位与汶川地震消息的扩散——来自安徽淮北的调查结果。《国际新闻界》,(7),38-42。
宣长春(2021)。广告侵入性对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影响:不同文化紧密度的差异化表现。《现代传播》,(10),135-140。
谢笑春,孙晓军,周宗奎(2013)。网络自我表露的类型、功能及其影响因素。《心理科学进展》,(2),272-281。
夏倩芳,仲野(2021)。网络圈子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吗?——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国际新闻界》,(11),84-110。
徐颖,于雨禾,张桓森(2021)。何因生倦怠,何素调节之?——一项关于社交媒体倦怠的元分析研究。《图书情报工作》,(13),31-43。
【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2017)。《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杨鹏等(2015)。社交焦虑大学生对正性评价解释偏向的初步探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2), 933-938。
叶友才,林荣茂,严由伟(2021)。树大招风:社交焦虑者的正性评价恐惧。《心理科学进展》,(6), 1056-1066。
赵晨等(2021)。策略性网络社交回避形成机制:在线工作——生活打断的作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5),71-83。
张大伟,王梓(2021)。用户生成内容的“阴暗面”:短视频平台用户消极使用行为意向研究。《现代传播》,(8),137-144。
张晋升,刘蓓(2016)。网络信息传播中的舆论偏向与社会治理——基于两起网络虚假信息事件的传播分析。《新闻记者》,(4),66-70。
张苏秋,王夏歌(2021)。媒介使用与社会资本积累:基于媒介效果视角。《国际新闻界》,(10), 139-158。
赵启南(2019)。关系性压力下青年使用者社交媒体倦怠影响及其行为结果。《新闻与传播研究》,(6),59-75+127。
张铮,陈雪薇,邓妍方(2021)。从浸入到侵入,从待命到疲倦:媒体从业者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国际新闻界》,(3),160-176。
Alkis, Y.Kadirhan, Z.SatM. (2017).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social media user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2296-303.
Ben-Ze’evA. (2003). Privacyemotional closenessand openness in cyberspac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9(4)451-467.
Barak, A.Gluck-OfriO. (2007). Degree and reciprocity of self-disclosure in online forums. Cyberpsychology & . Behavior, 10(3)407-417.
Deursen, V.Dijk, V. (2014). The digital divide shifts to differences in usage. New Media & Society16(3)507-526.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ume78(6)1360-1380.
Han, B. (2018). Social Media Burnout: Definition, Measurement Instrument, and Why We Care.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58(2)122-130.
Hwang, M. J.Yoon, D. P.Shim, W.LimK. E. (2010). The Impact of Social Status and Risk Behaviors on Health Status Among Elderly Individuals in Korea. Social Work in Public Health, 25(2)223-236.
KisilevichS.AngC. S.Last, M. (2011). Large-scale analysis of self-disclosure patterns among online social. networks users a: A Russian context.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32609-628.
Lee, C. C.Chou, S. T. H.HuangY. R. (2014). A Study o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ocial Media Fatigue-Example of Facebook Users. Lecture Notes on Information Theory, 2(3)249-253.
Leary, M. R. (1983). A brief version of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9371-375.
MillerL. C.Berg, J. H.Archer, R. L. (1983). Openers: individuals who elicit intimate self-disclos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6)1234-1244.
Ravindran, T.Chua, A. Y. K.Hoe-LianG. D. (2013).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Network Fatigue. 2013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w Generations ( ITNG ) , IEEE, 431-438.
Reichenberger, J.Blechert, J. (2018). Malaise with praise: A narrative review of 10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of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in social anxiety. Depress Anxiety35(12)1228-1238.
StrausM. A. (1979). Measuring Intrafamily Conflict and Violence: The Conflict Tactics (CT) Scales.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4(1)75-88.
Swirsky, J. M.RosieM.XieH. L. (2022). Correlates of Early Adolescents’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The Role of Pubertal Status and Social Goal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51(1)74-85.
Taddicken, M. (2014). The “Privacy Paradox” in the Social Web: The Impact of Privacy Concern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and the Perceived Social Relevance on Different Forms of Self-Disclosur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2)248-273.
ThompsonNik.Wang, X.Daya, P. (2020). Determinants of News Sharing Behavior on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60(6)593-601.
Weeks, J. W.Heimberg, R. G.RodebaughT. L.Norton, P. J. (2008).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 22(3)386-400.
Weeks, J. W.Howell, A. N. (2012). The bivalent fear of evaluation model of social anxiety: Further integrating findings on fear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41(2)83-95.
Weeks, J. W. et al. (2005). Empirical validation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in patients with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7(2)179-190.
Weeks, J. W.Heimberg, R. G.RodebaughT. L. (2008). The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scale: Assessing a proposed cognitive component of social anxiety.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 22(1)44-55.
ZengR. X.ZhuD. (2021). Fear of Evaluation and Online Self-Disclosure on WeChat: Moderating Effects of Protective Face Orient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1-11.
姜泽玮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