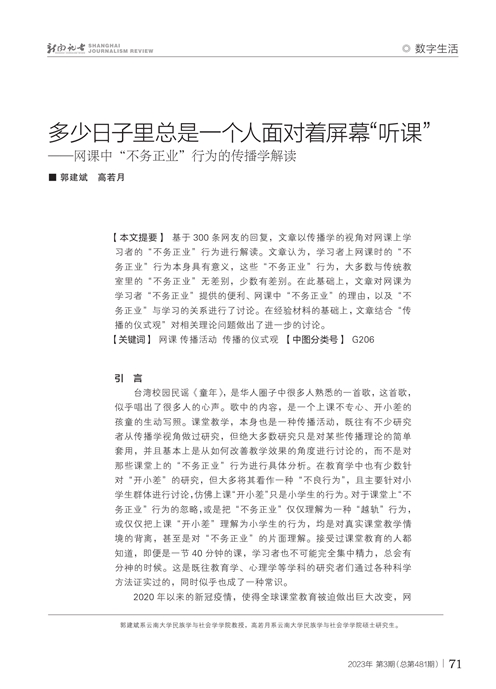多少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屏幕“听课”
——网课中"不务正业"行为的传播学解读
■郭建斌 高若月
【本文提要】基于300条网友的回复,文章以传播学的视角对网课上学习者的“不务正业”行为进行解读。文章认为,学习者上网课时的“不务正业”行为本身具有意义,这些“不务正业”行为,大多数与传统教室里的“不务正业”无差别,少数有差别。在此基础上,文章对网课为学习者“不务正业”提供的便利、网课中“不务正业”的理由,以及“不务正业”与学习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文章结合“传播的仪式观”对相关理论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讨论。
【关键词】网课 传播活动 传播的仪式观
【中图分类号】G206
引言
台湾校园民谣《童年》,是华人圈子中很多人熟悉的一首歌,这首歌,似乎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歌中的内容,是一个上课不专心、开小差的孩童的生动写照。课堂教学,本身也是一种传播活动,既往有不少研究者从传播学视角做过研究,但绝大多数研究只是对某些传播理论的简单套用,并且基本上是从如何改善教学效果的角度进行讨论的,而不是对那些课堂上的“不务正业”行为进行具体分析。在教育学中也有少数针对“开小差”的研究,但大多将其看作一种“不良行为”,且主要针对小学生群体进行讨论,仿佛上课“开小差”只是小学生的行为。对于课堂上“不务正业”行为的忽略,或是把“不务正业”仅仅理解为一种“越轨”行为,或仅仅把上课“开小差”理解为小学生的行为,均是对真实课堂教学情境的背离,甚至是对“不务正业”的片面理解。接受过课堂教育的人都知道,即便是一节40分钟的课,学习者也不可能完全集中精力,总会有分神的时候。这是既往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们通过各种科学方法证实过的,同时似乎也成了一种常识。
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使得全球课堂教育被迫做出巨大改变,网课这样一种授课方式很快在大中小学普及。在这一过程中,对网课的“吐槽”也不断出现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在这样一种关于网课的众声喧哗中,本文作者于2022年9月新学期开学伊始,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个问题——当你在上网课时,除了听课,你通常在干什么?问题虽然简单,但是经过几个好友的转发,一共有366位网友做出了回答,剔除无效、意思不明的,还剩下300条有效回复,这300条回复网友的IP地址遍及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具有一定的地域上的广泛性。①在初步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作者感到虽然资料量不大(更无法谈代表性),但是这些有限资料所指向的问题十分有趣。这些问题,也是既往的相关研究、讨论较少关注的。同时,这些问题背后,或许还潜藏着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教育与传播之间的关系。
上述问题,可以表述为以下研究问题:网课中听课者的“不务正业”行为,具有怎样的传播学意义?新的媒介技术为学习者网课中的“不务正业”提供了怎样的便利?较之传统的课堂教学,学习者在网课时的“不务正业”又有哪些变化?“不务正业”与“学习”之间,是否一定是矛盾的?作为一种在“传播的仪式观”下具有意义的“不务正业”行为,在网课的特定语境中又有着怎样的特定理论意义?
一、理论综述
1982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来华,通常被视为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再次获得发展生机的标志性事件(罗昕,2017)。但是对于施拉姆来华的最初动机,从事传播研究的人似乎不太关注。施拉姆来华对于中国电化教学的发展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似乎也未见到太多讨论。②其实,1982年4月下旬,施拉姆来华第一站是在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一共进行了为期7天共7个专题的学术演讲活动,参加讲习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化教员三百余人”(刘家林,2013)。此前,广东省教育局局长以及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到香港学习考察,并在香港中文大学认识了施拉姆,其目的是向“当时‘电化教学’比较先进的香港地区‘取经’学习”(刘家林,2013)。这样一个传播学术史上的“插曲”,无意中把中国的传播学和教育学中的电化教学连结到一起。不过,这次“偶遇”,似乎并未拉近后来兴起的传播学与此前就有的教育学之间的关系。关于传播与教育之间的相关讨论,并未彻底转到把教育(尤其是课堂教学)视为一种传播活动的思路上。相关研究或是十分宽泛地使用“传播”来表述,如“课堂教学的知识传播过程的实质是知识的生成与生长过程”(谢利民,2001)、“知识传播的实质是激活与播种、生成与生长知识”(谢利民, 2002),或是考察不同传播方式对课堂教育的影响(文喆,2000),或是对新媒体传播环境对于高校教学方式的变革进行讨论(周红春,梁静,2013),等等。当然,如何在更为彻底的意义上把教育(尤其是课堂教育)视为一种传播活动,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理解“传播”。在这一点上,似乎只能从传播学的相关讨论中来寻找理论证据。这个距当下更近的理论证据虽然来自传播学,但是这个理论证据的根源,则是在教育学中。
本文所提供的理论证据,具体来说,就是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对于传播观念的讨论。凯瑞把人类传播的观念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一种是“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凯瑞,2019:14)。对此,本文作者之一也曾做过简要归纳,认为前者是一种线性模式,后者是一种场模式(郭建斌,2006),同时,本文作者之一也曾以课堂教学为例,从“传递观”与“仪式观”的角度进行过简要说明(郭建斌,2014)。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本文为上述例证补充了进一步的证据。
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第一章开篇,就有这样两句话:“几年前我决定认真研读传播学著作,一位明智之士建议我从约翰·杜威开始。这个建议让我终身受益”(凯瑞,2019:12)。此后,凯瑞也引用了杜威(John Dewey)那个被很多从事传播研究的人反复引用的关于社会与传播的关系的观点,即“社会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凯瑞,2019:14)。但是很少人注意到,杜威的这个观点,是在讨论教育与传播的关系时提出的,具体出现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③当然,杜威这里所说的教育,并非学校教育,更非课堂教育,而是“更为基本的和更为持久的教导方式”(杜威,2001:9)。但是,在作者看来,即便是在一个具体的课堂教学情境中,凯瑞在借鉴杜威的观点之后所提出的“传递观”与“仪式观”,同样是并存的。既往那些对于传播与教育(尤其是课堂教育)的研究、讨论,几乎都是从“传递观”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的,很少看到其中的“仪式观”方面的意义。这也是既往关于传播与教育相关讨论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忽略了课堂教学中“仪式观”的意义,仅仅把课堂教学理解为师生之间的传受关系,即便有不少论者也强调师生之间的互动,仍不能说是彻底地把教育(尤其是课堂教育)视为一种传播活动。从詹姆斯·凯瑞“仪式观”的理论视角来对课堂教学进行考察,更能充分彰显那些课堂上“不务正业”行为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一个真实的课堂,也才是《童年》那首歌之所以打动人心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所说的网课,其实是前面讲到的电化教育(学)的一种当代形态。1982年施拉姆来华实现了中国传播学与电化教育的一次“偶遇”,但是此后,两者似乎很快就分道扬镳了。有学者在二十年前把中国电化教育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视听教育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和“信息化教育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3年)”,第二个阶段的标志,即是“教育信息高速公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多媒体网络教育系统的建设并投入使用”(南国农,2003)。这篇文章虽然是写于近二十年前,但是目前的电化教育,同样属于作者所说的“信息化教育阶段”的延续,因为作为这个阶段的核心——计算机、互联网等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在传播学领域,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出现了“网络传播”等表述。
就本文所讨论的网课而言,它与电化教育中的“远程教育”、慕课(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等不尽相同,那些课程均是事先录制好的,而本文所说的网课,基本上是直播。由于新冠疫情的突发性,网课也不仅限于传统的那些教育技术平台,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一切可能的技术渠道。市场也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及时推出各种在线会议软件,除了可用于网课,也可以举行“在线会议”。
传统的师生面授课堂呈现出的是具有线性特征的“知识传递型”教学形态,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传播媒介的改变使得线上课程或者说网课成为可能,并为学生提供了一种便利,使得他们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及时地进行学习。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一种能动的活动,绝不是教师片面灌输的被动活动”(韩立福,2012)。网络直播教学,区别于慕课的特征在于师生时间同步、临场感强、互动性高(焦建利等,2020),但由于缺乏由上至下的监管,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学习从“他控”转为“自主”,要求学生作为行为主体主动、独立、自控地进行学习(郭文良,和学新,2015)。但是,在开源的平台上进行学习本身意味着海量信息的摄入,这些多余的信息对个人来说无疑会消耗其珍贵的精神资源——注意力(李志昌,1998)。学生居家在线学习的注意力失焦行为主要体现在注意力分散、社交媒体吸引和思维游荡(陈长胜,隆景云,2020)。在线教学面临的困境是学生上课时打开多个聊天工具,各种群聊侵占了其大部分注意力(胡小平,谢作栩,2020),学生的学习意图受到社交媒体的惯性行为及其愉悦经历的吸引(Lee et al., 2014),频繁的媒体多任务处理与注意力调节使得学生更容易走神,分散的注意力也使得其产生了较高的冲动水平和较低的自我抑制水平(Wiradhany & Koerts, 2019)。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虚拟现实融合,产生了普遍的“注意力增量”现象(Quiles et al., 2020),但是学生有限的注意力与增量的信息之间本身存在张力。
如同既往对于传播与教育的相关研究、讨论,在关于网课的研究中,同样主要是一种“传递观”的视角。网课这样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与既往线下课堂教学自然有着较大差别,同时在网课上那些学习者的“不务正业”行为,可能也会与线下课上的有较大不同。具体情况,本文后面将做详细说明。
二、研究方法
本文所说的“不务正业”,是作者收集资料时的问题(当你在上网课时,除了听课,你通常在干嘛?)所指的那些具体行为的形象化表达。因为在一般的观念里,上课听课是“务正业”,听课之外的行为,自然属于“不务正业”。这主要是出于类型划分的考虑,尽量规避价值判断。
虽然作者在收集资料时并未要求回答者表明其身份,但是从所回复内容判断,绝大部分是大学生,并且相当一部分是当下在读的大学生。因此,本文所说的学习者,主要指的是在读大学生。
如前所述,作者通过新浪微博发布问题,收集到了300条有效的回复。在对这些回复进行反复阅读之后,作者最终决定采用DiVoMiner平台④对文本进行编码。首先对300条回答中所提到的行为进行详细列表,然后又对列表中的行为进行归类,最终形成了26类,隶属于“做什么”类目。由于新浪微博的所有回复中均显示了地点,因此,作者也把“地点”作为类目二(按微博上的显示分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起始时间是2022年9月7日
14 : 15至2022年9月19日0 : 31。且绝大部分回复是9月7日的,9月12日作者再次转发了原来的微博,又得到了一些回复。
根据类目二编码结果,300条回复一共涉及中国的31个省级行政区,只有福建、香港和澳门地区没有样本。此外,部分样本来源地为英国、美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具体情况见附录1。
在正式编码开始前,本文两位作者分别进行了信度测试,类目一的霍尔斯蒂信度(HCR)为0.84,这里的出入主要在于不同编码员对回复中所提及的多种“不务正业”行为有的做了全部勾选,有的则有遗漏,即便是遗漏的,也可以理解为是次要行为。对于所选择的行为判断,两位编码员几乎没有差别。因此作者认为该信度完全可以接受。类目二霍尔斯蒂信度(HCR)为1.00,即两个编码员完全没有差别。类目一和类目二的霍尔斯蒂信度(HCR)为0.90。
三、与传统课堂无差别的“不务正业”
歌曲《童年》这样唱道:“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这显然是在讲那个顽皮的小男孩上课开小差了,当然也明示了小男孩初恋的冲动。网课听课的环境与传统的教室不同,但是调查数据显示,上网课过程中的很多“不务正业”行为,其实与传统的教室课堂并无太大不同。
在作者分出的26类行为中,其中的21类,在作者看来,应该是与传统课堂无差别的,具体情况见表1。
上述21类与传统课堂无差别的“不务正业”,占比达到83.9%。当然,由于网课通常脱离传统课堂的空间及其他限制,使得上述那些与传统课堂无差别的“不务正业”更加成为可能,甚至更加肆无忌惮。比如睡觉,若是在课堂上,通常是趴在课桌上睡,但网课上,正如一位网友的回答:“打开外放然后躺下”(9-07,22:47⑤)。再比如“护理身体”一类,在课堂上学生也会有剪指甲、弄头发等行为,但是这里所说的“护理身体”,范围显然要广得多。正如一位网友回复的:“公共选修课,晚上七点开始,因此一般边听边进行吃饭、洗漱、护肤……”(9-07, 19:05)
在上述21类行为中,“刷社交媒体”、“聊天”、“玩游戏”、“玩手机”、“吐槽”、“查相关资料”、“看影视”、“网购”、“追星”、“玩电脑”、“冲浪”等11类直接与媒体相关,且这些行为占到了全部“不务正业”行为的46.60%,占上述21类行为的55.72%。也就是说,随着手机这样的移动智能媒体的普及,即便在传统的教室上,学生也可以做这些事情。这是新的媒体环境给传统课堂带来的变化。也是与《童年》那首歌里那个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太阳为什么下到山的那一边”感到疑惑的小男孩所生活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时代。那些通过社交媒体在课堂上不断在现实时空与网络时空中穿梭的学习者,似乎也失去了去追问这样问题的童真。这正是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讨论的问题——“印刷术如何创造了童年,电子媒介又如何使之‘消逝’”(波兹曼,2011)。
四、传统课堂无法实现的“不务正业”
在资料整理过程中,作者发现,有些“不务正业”行为,则是在传统的课堂上完全不可能出现的(见表2)。
“做家务”反映出了学生上网课的地点是在家里,这里所说的“做家务”,包括了做饭、洗碗、拖地等。如有网友回复的:“做饭,特别是中午十一点还在上的时候”(9-07,
15:29)、“上午课程一般是在做饭”(9-07,15:01)、“做饭洗碗拖地走路的bgm(背景音乐)”(9-07,18:53)、“吃饭,买菜,做饭,在Wechat上和同学讨论或者吐槽上课内容”(9-08,07:37)、“如果在家的话,中午会一边做饭一边听课”(9-10,11:20)。若在课堂上听课,课后可以直奔学校食堂,自然不用考虑吃饭的问题,但是在家上网课,若家里没人做饭,学习者只能自己做饭。
由于脱离传统课堂空间的限制,有学习者在上网课时还进行健身或运动。如有网友所说:“我经常会在听网课的时候健身,尤其是久坐之后……会边听边做一些俯卧撑与卷腹运动”(9-12,23:37);“在跟欧阳春晓做运动哈哈哈哈哈”(9-07,21:13);“会做开肩和一些拉伸运动”(9-08,08:13);“取决于上网课的时间,早上在吃早饭,接近中午在午休,甚至还在房间练瑜伽”(9-07,18:06)。
“玩宠物”同样也是很难在传统课堂上出现的“不务正业”行为,在300条网友的回复中,有4条讲到了这方面情况。如“玩猫,把它抓来一起听课”(9-09,18:22);“玩狗”(9-07,14:33);“玩手机,发呆,睡觉,处理别的事情、撸猫,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听课做笔记”(9-07,18:27)。
至于“干其他杂事”,情况较为复杂,如有“做点不会过于分神的事情,比如织毛衣以及反复确认自己有没有不小心开麦”(9-08,12:51);“昨晚一边上网课一边参加校招面试”(9-07,20:14);“今天听这个老师说,连线一个学生回答问题,他说在练车”(9-07,19:14);“在排队做核酸……”(9-07, 18:02);“有约的话会去赴约,耳机播放着当做背景音”(9-07,17:58);“戴蓝牙耳机变成听播客,早上可能在做早餐午餐,下午可能出门办事比如看医生之类的,那天一边开车一边听课的时候,突然想到安静的网课要是把大家的视频都打开,那简直是锣鼓喧天热热闹闹的生活画面”(9-07,16:21),等等。
五、网课,“不务正业”的便利
离开了传统教室空间限制、教师的注视以及同学之间的相互约束,网课通常是一个人面对屏幕上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的确为学习者“不务正业”提供了太多的便利。教室通常是一个公共空间,学习者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自然会遵守该公共空间的规约,这些规约,倒不一定是像某些学校教室里张贴的“文明公约”,而是学习者心照不宣的“常识”。但是,网课学习者如果在家里学习,此时的空间就是私人空间。在私人空间里,正如有些网友回答时所讲到的:“除了听课什么都干”(9-07,17 : 44;9-09,18 : 19)。尽管在课堂里有些学习者也是这样的,但他(她)总不能像上网课时一样去洗澡、拖地,甚至是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除了上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区分,对于网课而言,还有另外一组空间,即实体空间与网络空间。传统教室是一个实体空间,而网课的教学,则是发生在网络空间中。在传统的教室里,由于学习者拥有手机等移动互联媒体,他(她)在上课时也可能在网络空间里“遨游”,实现不同空间之间的穿梭,但其身体存在于某个具有公共性的实体空间中,其身体是受该实体空间限制的。但是在网课上,由于移动终端的出现,学习者除了在家庭这样的私人空间里学习之外,也可能是在移动的空间中进行学习,如前面所讲到的,有人边听课,边看病、约会,甚至是排队做核酸。
六、网课,“不务正业”的理由
如上所述,学习环境的变化,的确为在网课中“不务正业”提供了诸多便利。虽然在作者收集资料时提出的问题中并未询问学习者“不务正业”的理由,但是在300条回复中,相当一部分回复明确地讲到了“不务正业”的理由。这些理由虽然同样不具代表性,但是似乎也可以从中看出目前网课存在的某些问题。下面选择一些涉及网课“不务正业”理由的回答:
老师讲得好我就认真听,老师光朗读PPT我就自己看书或者玩手机或者睡觉(9-19,00:31)。
如果讲得太糟,那就直接跑路了(9-12,23:47)。
感觉还是看老师,有意思的课会认真听,如果是比较水的课,有时候就挂着(一般都是躺着听,刷刷微博(9-12,23:14)。
有趣的课会边听边写笔记,偶尔查一下资料;水课会边听边和同学聊天,顺带刷刷微博小红书等(9-12,16:37)。
老师的第一节课非常重要,会直接影响我对这节课是否需要认真听的判断。有些课很水,感觉老师也不太专业,我接下来大概率就会单纯挂着(9-11,10:35)。
如果讲得生动有趣,或者信息量大,就会感慨为什么讲得这样好,这老师我爱了爱了!如果讲得很机械,感觉到老师是在对付,就会心里暗骂浪费时间,从第一遍到第n遍(9-9,15:46)。
看什么课吧,专业课、考试课就听一些重点,其他课就做做家务(9-7,20:47)。
视课程而定:1.专业课(1)有趣的专心听记笔记;(2)枯燥的平板分屏,一半网课一半网上冲浪。2.通修课,用电脑挂着(1)互动的:网上冲浪,被点到,向舍友求助,回答完继续冲浪;(2)不互动的,尤其是早八的,直接睡晕过去。3.公共选修课,晚上七点开始,因此一般边听边吃饭、洗漱、护肤……(9-7,19:05)。
这要根据课程的重要程度以及是否吸引人来分,如果是很重要很有趣的课自然是认真听讲、记笔记、查资料等,当然不排除中间开小差回手机消息之类,这和线下上课的活动基本差不多;如果是不得不挂着听的课,基本就是社交媒体全部打开刷一遍,和同学吐槽一下,或者查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看(9-7,16:49)。
……
以上只是节选了一部分学习者的回复,其中共同的一点,即网课是否“不务正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取决于学习者对课程的兴趣以及讲课老师的授课情况。如果只是照本宣科,或是不调动学生参与到课程学习中,往往就会成为网课学习者“不务正业”的充分理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课也对教育者(教师及教育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七、“不务正业”未必是不学习
本文开头讲到,若从“仪式观”的角度对网课进行考察,课堂上的传播并非仅仅是“传递”或“互动”,那些课堂上的“不务正业”者,具有“具身在场”(embodied presence) (邓建国,2022),同时也具有“在场”的意义(郭建斌,2019)。同时,在整个40分钟的课堂上,学习者也不可能始终保持专注,总有某个时段或片刻,会分神、开小差。在对300条网友的回复进行反复阅读过程中,作者发现网课上的那些“不务正业”,未必完全是不学习、“摆烂”,正如某些网友所说:“有时候玩消消乐等小游戏。因为这些游戏不用动脑子,手上不无聊脑子还可以听课(一般是课程内容一般或节奏太缓慢)”(9-8,09:49)。从前面表1中也可以看出,有些“不务正业”者,他(她)或是在“学习其他东西”,或是在“阅读”、“查阅相关资料”、“做其他作业”,这些在作者看来,同样是在学习,这些占所有“不务正业”行为的14.20%,应该说这一比例并不算太低。还有网友这样回复:“会突然被某个名词或例子吸引,然后去百度搜”(9-7,14:52)。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甚至是互联网为现代学习者提供的便利。即便在大学课堂上,也有些教师鼓励学生使用手机上网查阅相关资料。
若从广义的学习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同样是“务正业”。正如有网友回复的:“线上课程会感觉更自在,因为没有同学的目光注视,没有老师的眼神压迫,更想去自由地表达观点”(9-7,15:52)。
对有限的资料做进一步挖掘,作者利用DiVoMiner平台提供的“情感分析”(正负面)对300条回复进行处理,结果如图1所示。
从结果来看,中立、正面的情感占三分之二多,负面情感不到三分之一。由此可以推断:学习者对于网课中“不务正业”行为的回答,其情感总体倾向是积极的。
进而,作者又利用DiVoMiner平台提供的“情绪分析”对300条回复进行处理,结果如图2所示。
从“情绪分析”结果来看,在300条回复中,厌恶、悲伤等消极情绪所占比重较低,仅为5%,快乐等积极情绪占比超过了10%。
从以上两项分析来看,网友对于网课中的“不务正业”行为,在情感、情绪上,均倾向于积极态度。这也意味着,学习者那些网课上的“不务正业”行为,也并非完全是“摆烂”、不学习,而是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调节”。
八、总结与讨论
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网课中的“不务正业”行为进行阐释,一方面是视教育(或教学)活动为一种传播活动,这方面的讨论出现在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之前,这些理论资源也是传播思想史研究中绕不过的内容。但是在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中提及这方面内容时,往往忽略了其教育学的学科背景。1980年代初期施拉姆来华无意中实现了中国传播研究与电化教育的“偶遇”,但是在此后的研究中,传播研究与教育学之间的关联,更多只是一种术语上的借用,真正把教育活动视为一种传播活动并对其进行深入讨论的并不多见。并且,即便是把教育活动视为一种传播活动,对于传播的理解,主要是一种“传递观”的思路,很少涉及“传播的仪式观”。
借鉴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的理论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为全面、真实的课堂,而不是仅仅基于“传播的传递观”那样一种简单的传受关系。在这样的课堂上,既有学习者专注听讲的情景,也有分神、开小差的时候。在凯瑞看来,“传递观中的‘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理空间扩展信息”(凯瑞,2019:18)。传递观视角下的教学活动,道理亦是如此。前文讲到杜威对于传播问题的讨论,是在讨论民主主义与教育问题时讲到的。在杜威那里,其实已经有了后来凯瑞所讲的“传播的传递观”与“传播的仪式观”的某些思想雏形,只是当时杜威并未形成这样的表述。杜威心目中的理想教育,一定不是“传递观”意义上的,而是“仪式观”意义上的。“仪式观”意义上的教育,不仅仅只看到教育(或教学)活动中传递的方面(凯瑞也明确说过“传递观”与“仪式观”不可分),更看到了那些“游离”于传递关系之外的存在。那些课堂上的“不务正业”行为(也包括本文所关注的网课上的“不务正业”行为),在“仪式观”的理论视角下,均是有意义的,而不仅是某种“越轨”行为。从这一点来看,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十分宽容的理论。如前所述,这一理论的思想源头,其实是在教育学中。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对“不务正业”行为的解读,仿佛是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教育学中。为什么会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教育学研究中有关杜威对传播的理解或许还不够透彻,甚至是走向了杜威理想中的作为传播活动的教育活动的对立面。若此,经由传播学者凯瑞,再度回到杜威,似乎并非完全多余。
对于某些饱受传递观主导的传统课堂教学禁锢的学习者来说,网课似乎是一种解脱,尤其是对于某些中国互联网的“原住民”而言,他(她)们似乎能更快地适应、接纳网课这样一种教学方式。由于脱离了传统教室物理空间的限制,没有了教室与学习者“具身在场”所形成的监督、约束,使得网课中“不务正业”变得更加自然而然。从前文所列举的经验材料来看,的确有这样的情况,但也并非为所欲为。正如有网友在回复中写的:“若授课老师讲解精妙,对课程内容感兴趣,愿意记上一记;反之,把时间交给社交媒体去,但网课还需挂着,仪式还是要有”(9-07, 14:43)。这样的情况,本质上和传统的课堂教学并无太大区别,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回复者这里所讲到的仪式,与凯瑞的“仪式观”有着相近的意思,或许这位回复者就是学新闻传播学的?
本文借鉴詹姆斯·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对网课中“不务正业”行为进行解读,但绝不是简单地套用,毕竟凯瑞在提出该理论观点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互联网并未在全球普及,人类社会尚未进入所谓的“网络时代”。并且,凯瑞所关注的主要是新闻(或传媒),而不是课堂教育。就网课这样一种新近迅速普及的教育方式,那些网课中“不务正业”行为,是否能够达到凯瑞所讲的“传播的仪式观”的目的?以及用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来对网课上的“不务正业”进行解读又可能存在怎样的理论上的缺陷?本文将做进一步阐明。
在凯瑞看来,“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召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并且,“仪式观明确的宗教起源虽然同样已被削减,但它从未脱离这一基本的宗教隐喻”(凯瑞,2019:18)。无论是凯瑞在隐喻层面上所讲的仪式,还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等在实体层面上所讲的仪式,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经由仪式形成某种“有机”联系。在涂尔干对宗教仪式的讨论的基础上,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提出了“情感连带模型”,并认为“群体团结”是互动仪式的最为重要的结果(柯林斯,2012:80)。在《互动仪式链》中,科林斯专门对由电话、电视录像以及电脑等构成的“远距离的交流方式”是否能产生相互关注与连带情感进行了讨论,他的结论是:“人类社会活动越是通过远程媒介、以强度较低的互动仪式来开展,人们就会越觉得缺少团结感,也越会缺乏对共同符号物的尊重,而且以EE⑥形式所表的热情的个人动机会越少。”(柯林斯,2012:100)网课在教师与学习者以及学习者之间是通过柯林斯所说的“远程媒介”连接的,作为学习者个体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但是却有可能造成柯林斯所说的“团结感”的缺失。正如近年来有网友调侃的:“读了几年书,还不知道老师和同学长啥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网课上的那些“不务正业”行为,虽然在表面上具有凯瑞所说的“仪式观”的意义,但是经由网络这样一种中介所建构起来的“仪式”,由于科林斯所说的“团结感”的缺失,很难达到凯瑞在讨论“传播的仪式观”时所说的“共享”的目的。尽管科林斯为通过远程媒介连接的高水平情感连带开出了药方——“可以想象将来的通讯设备能够尝试着通过神经系统之间收发信号,而这些信号能够增强共享体验”(科林斯,2012:100),但是目前的网课系统以及其他通讯手段,显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
虽然网课使得学习者的那些“不务正业”行为更加不受限制,但是网课的时间、内容,基本上也是按学校的课表来安排的。这些方面,学习者并不能改变。学习者在网课上的某些“不务正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网课时间、内容的抗拒。这样的抗拒,具有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说的“弱者的武器”(斯科特,2007)的意义。但是这样的抗拒对于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其力量是微乎其微的。这也正是通过詹姆斯·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对网课上“不务正业”进行讨论时无法看到的方面,同时这也是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可能存在的缺陷。无论是那些仪式研究者们所关注的仪式,还是詹姆斯·凯瑞在“隐喻”的层面上使用仪式的表述,其背后均存在着一个詹姆斯·斯科特所说的“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斯科特,2021)。就本文所讨论的网课而言,教学时间、内容等正是“隐藏的脚本”的具体体现。这些“隐藏的脚本”构成了网课最为宏观的权力框架,所有学习者在网课上的“不务正业”行为,则是在这一宏观权力框架下的“小打小闹”,对宏观权力不一定构成直接威胁。
补记:
在撰写本文时,媒体上刚刚爆出“网课爆破”这样一个新词,这是网课实践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甚至也是一种“不务正业”。但是,本文对于网课上的“不务正业”行为的讨论,一定不是“网课爆破”的理论依据!本文所关注的网课上的“不务正业”行为,是在不违背现行教育框架、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的前提下的一些行为,不能对他人造成伤害。对此进行讨论,其目的在于,对作为一种教育传播活动的网课有更为全面、完整的认识,同时,这样的讨论与教育的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止于至善。
本文作者之一的孩子目前正在上高中二年级,因为疫情,2022年已经在家上了三周的网课,看到他每天面对着屏幕“听课”,有时也偷偷地刷手机。此时,我多么希望他能把窗帘拉开,看看窗外的真实世界里的风景,或是像《童年》里唱到的:“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但似乎这也只是一种奢望……■
注释:
①在此,本文作者对所有回复的不知名的网友(包括那些被剔除的样本)表示衷心感谢。网友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该问题触及不少网课学习者的“痛点”。
②2013年11月,《电化教育研究》杂志刊登过一个祝贺华南师范大学创办新中国第一个电化教育本科专业30周年的广告,其中提到了施拉姆的名字。见:《热烈祝贺 华南师范大学创办新中国第一个电化教育本科专业30周年 30年的风雨 30年的辉煌》,《电化教育研究》,2013年第11期。
③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16年,由New York: Macmilan出版社出版。该书有多个中译本,在由王承绪翻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出版的《民主主义教育》一书中,凯瑞所引用的话在第9页,由于翻译的原因,此处译者把communication翻译成了“沟通”,在具体的中文表述上也略有不同。
④在此对DiVoMiner公司曹文鸳女士对本文的编码等所提供的技术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⑤出于操作的方便,本文选择了网友回复时间作为资料编号,即日期+时间(时-分)。
⑥EE指“情感能量”。
参考文献:
陈长胜,隆景云(2020)。大学生居家在线学习的注意力失焦行为研究。《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4),57-63。
邓建国(2022)。我们何以身临其境?——人机传播中社会在场感的建构与挑战。《新闻与写作》,(10),17-28。
郭建斌(2006)。理解与表达:对凯利传播仪式观的解读。《中国传媒报告》,(3),50-59。
郭建斌(2014)。如何理解“媒介事件”和“传播的仪式观”——兼评《媒介事件》和《作为文化的传播》。《国际新闻界》,(4),6-19。
郭建斌(2019)。“在场”: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媒体人类学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11),37-54。
郭文良,和学新(2015)。翻转课堂:背景、理念与特征。《教育理论与实践》,(11),3-6。
韩立福(2012)。“先教后学”、“先学后教”和“先学后导”的教学思维探析。《教育理论与实践》,(35),48-50。
胡小平,谢作栩(2020)。疫情下高校在线教学的优势与挑战探析。《中国高教研究》,(4),18-22+58。
焦建利,周晓清,陈泽璇(2020)。疫情防控背景下“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案例研究。《中国电化教育》,(3),106-113。
兰德尔·柯林斯(2012)。《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志昌(1998)。信息资源和注意力资源的关系——信息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106-116。
刘家林(2013)。传学东渐考——纪念施拉姆来华讲学30周年。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46-152。
罗昕(2017)。被忽视的登陆点: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35周年的历史考察。《国际新闻界》,(12),22-33。
南国农(2003)。从视听教育到信息化教育——我国电化教育25年。《中国电化教育》,(9),22-25。
尼尔·波兹曼(2011)。《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喆(2000)。学习方式、传播方式与课堂教学改革。《人民教育》,(12),18-21。
谢利民(2001)。课堂教学生命活力的焕发。《课程.教材.教法》,(7),19-23。
谢利民(2002)。现代课堂教学的理念:知识的传播与生成。《教育科学研究》,(7),7-10。
约翰·杜威(2001)。《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詹姆斯·W·凯瑞(2019)。《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詹姆斯·C·斯科特(2007)。《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詹姆斯·C·斯科特(2021)。《支配与抵抗艺术》(王佳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周红春,梁静(2013)。新媒体传播环境下高校教学方式的变革。《中国电化教育》,(8),91-94+109。
Lee, Y. H.ChengC. Y.& LinS. S. J. (2014).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of self-control and self-esteem and the grouping effect on adolescent quality of life across two consecutive yea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4(2)523-539.
QuilesC.Prouteau, A.& VerdouxH. (2020). Assessing metacognition during or after basic-level and high-level cognitive task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a non-clinical sample. L’Encéphale, 202046(1)3-6.
Wiradhany, W.& Koerts, J. (2019). Everyday functioning - related cognitive correlates of media multitasking: a mini meta-analysis. Media Psychology, (6)1-28.
郭建斌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高若月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