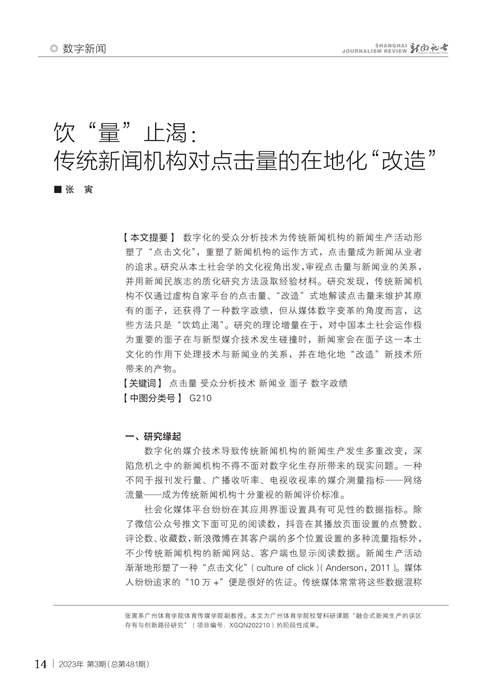饮“量”止渴:传统新闻机构对点击量的在地化“改造”
■张寅
【本文提要】数字化的受众分析技术为传统新闻机构的新闻生产活动形塑了“点击文化”,重塑了新闻机构的运作方式,点击量成为新闻从业者的追求。研究从本土社会学的文化视角出发,审视点击量与新闻业的关系,并用新闻民族志的质化研究方法汲取经验材料。研究发现,传统新闻机构不仅通过虚构自家平台的点击量、“改造”式地解读点击量来维护其原有的面子,还获得了一种数字政绩,但从媒体数字变革的角度而言,这些方法只是“饮鸩止渴”。研究的理论增量在于,对中国本土社会运作极为重要的面子在与新型媒介技术发生碰撞时,新闻室会在面子这一本土文化的作用下处理技术与新闻业的关系,并在地化地“改造”新技术所带来的产物。
【关键词】点击量 受众分析技术 新闻业 面子 数字政绩
【中图分类号】G210
一、研究缘起
数字化的媒介技术导致传统新闻机构的新闻生产发生多重改变,深陷危机之中的新闻机构不得不面对数字化生存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一种不同于报刊发行量、广播收听率、电视收视率的媒介测量指标——网络流量——成为传统新闻机构十分重视的新闻评价标准。
社会化媒体平台纷纷在其应用界面设置具有可见性的数据指标。除了微信公众号推文下面可见的阅读数,抖音在其播放页面设置的点赞数、评论数、收藏数,新浪微博在其客户端的多个位置设置的多种流量指标外,不少传统新闻机构的新闻网站、客户端也显示阅读数据。新闻生产活动渐渐地形塑了一种“点击文化”(culture of click) (Anderson, 2011)。媒体人纷纷追求的“10万+”便是很好的佐证。传统媒体常常将这些数据混称为点击量,并以之反映它们的融合传播能力。①
作为一种数字化技术的点击量深刻地影响着新闻业务实践。点击量这只“看得见的手”较为强势地将新闻消费者(用户)的偏好作用于新闻生产者,在影响新闻生产上具有较强的统合能力(谢静,2019)。点击量也会限制新闻机构的新闻生产活动,导致“采编人员围着点击量干活”等情况的出现。
诚然,点击量是获取受众数据的网站分析技术产物,在其与传统新闻机构发生碰撞后,新闻业先是抗拒、怀疑,后来逐步将其正常化。不过,中国新闻业对此似乎缺乏批判性的审慎态度,而是将其视为具有创新意义的新闻工作,表现出积极、热情的拥抱态度(白红义,2019)。由此可见,“点击量在传统新闻机构的新闻生产活动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核心问题
(一)从技术视角审视点击量与新闻业的关系
对新技术的采纳不仅更新了新闻生产的固有模式(白红义,2018),还使得传统新闻机构与平台新闻业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研究指出,传统新闻机构的新闻生产活动倘若没遵从平台媒体的规则,新闻推送的情况会受到显著影响(Nielsen & Ganter, 2018)。从这一角度而言,传统的新闻生产技巧、模式并不一定会在平台媒体的传播上奏效,传统新闻机构的发展受制于平台新闻业的技术逻辑。
虽然《纽约时报》等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在打造自己的平台上取得了成果(常江,何仁亿,2021),但多数媒体在打造新平台上往往效果一般,有些甚至沦为一种面子工程下的“摆设”(张寅,2022),或是放弃自家的新传播渠道,而加入互联网巨头搭建的平台媒体之中(王辰瑶,2018)。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传统新闻机构在“嫁接”数字互联技术以实现媒体融合发展的进程中,都与平台发生关联。新闻业不得不依赖平台这类基础技术设施谋求发展,并在与平台的互动中形成平台逻辑(白红义,2022)。点击量便是平台逻辑主导下的一种技术产物,毕竟数据的获得与呈现更为方便、直观。
虽说技术并不是改变新闻业务实践的唯一、关键要素,但技术常常与一组复杂的科技物、规章、标准等相互作用后产生影响(江淑琳,2016)。包括点击量在内的数字技术产物无不影响新闻记者及其组织日常性的协商(彭芸,2017:49)。不仅新闻生产的一线从业者需要关注点击量,新闻机构的决策层亦要通过点击量了解传播效果。于是乎,点击量渐渐地成为评估新闻工作的重要指挥棒,并给新闻室的内容生产带来了不可小觑的影响(陈昶文,2019)。
(二)从劳动视角考察点击量与新闻业的关系
在技术视角的提示下,作为受众分析技术的点击量固然会引发其与新闻业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但上述的一些研究忽视了点击量对从业者数字新闻劳动的影响。
流量新闻生产中的数字劳动变化对西方新闻记者这一职业群体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数字新闻生产权力体系构型引发了记者追求流量的从业压力,冲击着新闻劳动力(王维佳,周弘,2021)。在中国,新闻记者的数字劳动也深受点击量的影响。点击量作为一种管理手段,控制着新闻从业人员的劳动过程,一旦从业者将点击量作为专业标准和考核标准,新闻生产模式便将追求具有“病毒式传播潜力”的内容作为主流(余沐芩,宋素红,2022)。此外,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闻从业者新的绩效考核制度,即从挣工分(夏倩芳,2013)嬗变为挣流量,新闻室产生出一种“流量锦标赛机制”,使记者成为挣流量的数字信息劳工,甚至出现记者“买流量”的情况(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2)。
可以肯定的是,在数字新闻生产环境下,不仅有新出现的永动机式工作模式(王海燕,2019),还有追求较高的点击量的工作目标,这些情况都深刻地改变了新闻工作者的劳动状况。
(三)在地文化视角下的点击量与新闻业
平台作为点击量的技术依托实则是一种隐喻。作为一种精巧的话语装置,平台隐喻往往让我们不加批判地拥抱新技术(刘战伟,2022)。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点击量除了作为一种考核记者、编辑的新手段外,它还意味着什么?又是在哪些因素的作用下,形塑了这些“意味”?
更为重要的是,点击量这一媒介技术产物与新闻文化存在着紧密的互构关系。点击量不仅由数字化的媒介技术直接产出,其在地化的使用还受到社会文化、新闻生产权力关系等多方面的影响。这就提示我们,除了上述的技术视角和劳动视角会折射出点击量与新闻业之间的关系外,我们亦可从新闻研究“文化转向”(Zelizer, 2005:200)的角度,来考察点击量介入新闻室后所引发的新闻生产文化的变化,特别是产生了哪些“地方性知识”。
无论是批判对点击量的狂热追求,还是警惕点击量对新闻从业者职业文化权威的挑战与侵蚀(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2),在面对点击量与新闻业之间的关系时,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点击量与新闻机构发生互动后,传统新闻机构在文化方面出现了哪些新的情况?其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三、研究设计
有关中国的新闻社会学研究可以汲取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资源,挖掘具有本土特色的新闻生产文化表征(张寅,2020b)。作为一项本土化的新闻社会学研究,笔者采用新闻民族志这种质化研究方法,试图通过观察新闻室的生产活动、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深度访谈和对有关微信群的观察互动、同被访谈者的微信朋友圈互动留言等方式,获得经验材料。
为了获得较为丰富的经验材料,使观察与访谈的内容更加丰盈,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是一家省级广播电视总台(以下简称“总台Z”)旗下的两个广播频率(分别是新闻综合频率“广播J”和城市私家车频率“广播S”)和一个电视上星频道(以下简称“电视W”)。研究时间主要涉及两段:一是2016年9月到2018年7月,二是2019年11月到2022年4月。第一个时间段里,笔者以“广播J”新媒体部“负责人”的身份主持该频率的融合新闻传播活动。在此期间,笔者对点击量的问题格外关注,并秉持问题意识,观察点击量对广播J的种种影响。另外,还对广播S、电视W的相关新闻从业者进行线下访谈、网络社交互动。第二个时间段里,笔者不再担任“广播J”的新媒体部“负责人”,而是以节目责任编辑这一“旁观者”的身份审视点击量与新闻业的问题。在前一个时间段里,笔者的身份介于“完全参与者”和“参与观察者”之间;而在后一个时间段里,笔者的身份则处于“参与观察者”和“局外观察者”之间。从某种程度而言,角色的转换更有助于研究者全面地审视研究问题。
广播J、S和电视W都较早地加入了微博这一平台。不过,加入微信平台的时间则有所不同。由于广播在传统媒体中的互动性较强,广播J和广播S从微信公众平台诞生初期就纷纷加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新闻、与听众实现数字化的语音、图文互动;而电视W介入微信公众平台的时间相对较晚,起初也并不十分重视微信传播。总台Z没有设立代表总台的新闻类微博、微信账号,但是它于2013年正式上线了自建的新闻客户端。不过在若干年后,这个新闻客户端的一部分人员加入电视W,客户端的建制归属也从原先总台Z旗下的网站部门归到电视W,而另一部分人员则被解聘。此外,广播J、S和电视W亦在抖音平台爆火后,陆续在这一短视频社交平台上开设官方账号。
本研究涉及的访谈对象有35人(广播J:20人,广播S:9人,电视W:6人),②涉及一线的记者、新媒体编辑、广播新闻节目编辑、主持人、广告营销业务员和领导岗位的处级干部(频率/频道总监级)、科级干部(部主任级)。访谈采用半结构化的提问形式,访谈意图都向受访者进行了交待说明,访谈内容趋于饱和。
四、研究发现
笔者通过民族志调查发现,受众分析技术在与总台Z的新闻生产发生碰撞后,点击量成为各个频率、频道追捧的指标。除此之外,一个更有本土化意味的现象引起了笔者的关注:点击量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面子工程”存在于总台Z。如果一篇稿件的点击量高,记者、编辑和领导会觉得自己的融合式新闻传播活动成功,获得了用户关注甚至认可,如此一来就很有成就、很有面子;反之,点击量低的时候,记者等从业人员往往闭口不谈,选择各种手段进行回避。
(一)虚构自家平台的点击量:想要“有面子”,但也会适得其反
不同于商业机构开设的社交媒体平台,不少传统新闻机构自建的新闻客户端平台仍处于Web1.0时代的信息展示模式,缺乏Web2.0时代所强调的网络社交互动形态。但这并不妨碍传统新闻机构的新闻客户端展示页面的点击量。电视W新媒体编辑02曾在总台Z的新闻网站部门工作,担任网络新闻编辑。到电视W后,她仍从事新媒体编辑的工作:
App上的点击量,大家都懂得啦!你在那上面看到的数字就是一个“虚”的数,我们的后台技术人员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对这个数的增长方式进行设定。比如说,第一个人点进这条新闻后,上面的点击量显示的是“1”;但第二个人点进来之后,这个数可能就直接变成“1050”了。当然,我们内部会有一个实际的数据统计,给到各个供稿的广播频率、电视频道和总台有关领导。谁想让自家的新闻点击量那么难看啊,不仅记者不好受,我们也经常遭到“批评”,指责我们这个客户端没有多大的影响力。
电视W新媒体编辑02所说的情况不仅说明了部分新闻机构自建平台的传播效果不理想,还反映了为了维护传统新闻机构固有的权威面子所不得不虚构点击量的生成现象。面子是一种社会的地位或声望(金耀基,2013:51),传统新闻机构在融合发展过程中试图维护其原有的影响力,但现实却不断地向其“泼出冷水”,于是乎,总台Z就采取了虚构自家平台点击量的方法,以维护自己的面子。
虚构点击量的行为与前些年被声讨的虚假收视(听)率问题颇为相似:一方面是想要确保自己的影响力能换得丰厚的广告投入,另一方面反映出传统新闻机构长期固有的“争第一”的面子行为。收视(听)率的造假会遭到同类型媒体同行的声讨,这是因为“收视率=收看某一节目的人数(或家户数)/总人数(或家户数)”(刘燕南,2006:77)。毕竟,收看A节目的人一般不会在同一时间收看B节目。不过,虚构自家平台上的点击量不太会被频率(频道)指责,毕竟大家都可以去跟网站工作人员提出需求。
虚构的点击量还会给报道合作单位带来面子。广播J主持人01十分喜欢使用搭建在广播直播间的网络视频直播平台。从媒介变革(黄旦,2019)的角度而言,这显然是一种认知错误。舍弃声音在网络中的一维传播,而运用自己并不擅长的视觉呈现,是对广播声音传播固有优势的极大损害(张寅,2020a)。但这位男主播并不在意这种媒介学理上的论断,他追求的是可观的数字所带来的关系维护与面子:
有一次我对某个事业单位的嘉宾进行了一期访谈,我也没告诉后台新媒体编辑和技术人员具体在什么时间节点把这期节目的网络观看量显示到一个较高的数量。这个单位的通讯员在节目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微信截图,上面就是这期节目视频直播时的点击量——98万。当然,她也知道这个数据是有水分的。不过,拿着这个数据在朋友圈里晒的时候感觉也是美滋滋的。
人情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样式,是一种带有社会交换性的社会行为(翟学伟,2017:69)。通过后台技术实现的虚构点击量维护了男主播与通讯员之间的关系。虽然可能实际的传播效果很一般,但虚高的点击量却给足了双方面子,满足了日常联络交往中的人情世故原则。长此以往,总台Z的一些新闻从业者也不在乎自家平台点击量到底是真是假,毕竟这个数据可以让自己同通讯员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通讯员也心知肚明这些媒体自家平台点击量是虚高的,但不会刻意揭穿,反倒是在需要之时借助这种点击量来彰显自己单位的宣传公关能力。
虚构的点击量确实可以给足人情,维护各方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并不会次次奏效,一旦揭开虚构的“面纱”,就会给新闻机构带来一种“耻”的后果。广播J广告业务员03在一次“拉广告”时,就遭到过赤裸裸的揭露:
我到下面一个县域的文旅局去谈合作。我们台最近的外场活动拉到过一些地方赞助,所以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谈这个业务,之前和这个文旅局也有过一次合作。不过这次谈业务的过程,让我太难受了。对方工作人员直接说,你们总台Z的客户端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在手机里的应用商店里下载,怎么可能有你提供的这么高的点击量?我当时脸就红了,感觉好没面子啊。
用广播J广告业务员03的话来说,这位基层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具有很强的责任心、事业心,就是要把经费花在“刀刃”上,切切实实地宣介好当地的文旅资源。相对地,当虚构的点击量被戳穿时,一种耻感便在媒体人身上油然而生。
通过平台技术形塑的虚构点击量,固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使新闻机构、新闻从业者“有面子”,但毕竟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虚构之量被无情地戳穿时,想要获得面子、维持人际关系的行为就会适得其反。
(二)改造对点击量的解读:为点击量操碎了心
传统新闻机构自建的平台往往不具有商业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力,入驻商业平台完成数字新闻生产活动几乎成为所有新闻机构的现实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各平台的推送分发机制是不同的,新闻媒体往往搞不清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的点击量是如何计算的。广播S新媒体编辑01说:
我也做了几年新媒体编辑了,微信公众号上显示的阅读数到底是怎么算的,大家都没有搞清楚。比如说,针对某一新闻推文,我在这一天点进来N次,到底是算1次,还是算N次?如果算1次的话,我第二天再点进来还算不算增加1次?抖音后台的点击量,我们也没太搞懂。看过一次,向下滑动之后,如果往上翻回来再看一次,算不算新增1个点击量?还有就是,面对这些网络平台,我们也没有形成一套有规律可循的高点击量策略。有时候,我们认为很不起眼的一则推文,往往会在一个月后实现“10万+”。
面对不得不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局面,虽说传统新闻机构不能自行方便地虚构点击量,但新闻决策者、一线从业者会选择一种“以我为主”的解读方式,试图表明自己有着很强的融合传播能力。在第二段研究期间,广播J在其新闻室的走廊里悬挂了一张很大的宣传海报,题目是“深度融网 精做融合 打造融媒体新型广播”。这张海报还印制在广播J的对外宣传册上。海报上的几个内容值得注意:
(1)拥有20个融媒体矩阵传播渠道。
(2)广播J在微信+微博+抖音+今日头条4个平台上总粉丝数超800万。
(3)广播J今日头条号全国广播第*名,③
平均每天有一条内容点击量突破30万,单条创500万点击量。
(4)广播J抖音号截至目前已经超过250万粉丝,点赞数超1.1亿,总点击量超26亿人次,聚焦突发和正能量故事,多条视频单条点击量破亿。
颇为吊诡的是,广播J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用户必然会有重合,机械地将微信、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上的粉丝数相加,目的就是彰显自己的用户数多;将今日头条平台上的点击量进行平均化的运算也是为了凸显数据好看,从而遮蔽了那些点击量很低的推送内容;宣介抖音平台上的点击量采用了一种累积式的策略,因为以“亿”为单位的点击量很能说明数据之高。可是,广播J的一些新闻从业者对此并不买账。广播J记者03表示:
唉!这不就是对外显得好看、有面子么!自己人谁不知道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呢?可能领导就是想着,能赢得一个广告客户就是一个吧。我的很多舆论监督报道在微信上的点击量并不算高,很一般,但这些稿件却着实推动了一些问题的解决,很有成效,这不是能用点击量衡量的。我的看法是,点击量并不一定与稿件的影响力成“正比”。现在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思考,那就是记者为点击量操心、编辑为点击量操心、领导为点击量操心、广告业务员也为点击量操心,我们现在就是为点击量而活。我在这里干了十多年的新闻采写工作,以前可从来没有这么操心过。
为了获得高点击量,一些记者不得不舍弃对新闻稿件质量的追求,他们往往直接复制粘贴通讯员提供的新闻故事,或者为了追求热点快速地发布简讯新闻。当受众分析技术介入总台Z后,旗下各广播频率、电视频道一开始注重的是如何提高点击量,后来则逐渐放弃思考“如何提高点击量的方法”,而纷纷选择如何改造对点击量的阐释,进而为自己所用。
现实中还存在另一种对点击量的“改造”式解读。无论是广播J、广播S,还是电视W,各频率、频道自家的新闻室微信群中的一些人往往会让其他群内成员转发某一条平台推送链接到个人的微信朋友圈中。广播J处级干部01坦言:
现在不就是有这种“朋友圈文化”!大家纷纷转发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那总会让总台领导、主管机构的领导、记者跑线单位的领导看见。经常有厅级领导跟我说,我们台哪篇哪篇报道不错,谁谁谁都转发了。
一些新闻机构的决策者十分注重这种人情世故,各种类型的点赞、表扬都可以给自己带来一种受到领导赏识的面子。而这种面子又会向下传导,影响到新闻从业一线人员。换言之,因某些领导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表扬或点赞,一些在微信等平台上点击量并不高的新闻推文获得了一种有面子式的好评。
面子在中国具有浓厚的社会性,是一个有多少、大小的“量”的概念,也因此,是可以减少或增多的(金耀基,2013:58-59)。围绕点击量所形成的一种面子土壤渐渐在总台Z扎根。脸面不等于“能力”,但脸面随后者的相对变化发生同向改变(佐斌,1997:72)。要看到,面子问题不仅存在于不同的新闻工种之间(张寅,2020b),还存在于技术与人之间。为了追求所谓的高点击量,新闻机构选择一种“改造”式解读的方法,来彰显自己拥有高点击量的传播能力。当传统新闻机构通过自行设计的方法“改造提高”了它们在社交网络平台上的点击量后,新闻决策者或是一线从业者的面子便随着这种在地化的“改造”而更加被夯实。
(三)“面子事情”下的一种全新数字政绩
“面子事情”是本土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它用来解释个人之所以采取举动,纯粹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或是给别人面子(胡先缙,2010:65)。虽说“面子事情”通常是个人不太情愿做的事,但它却给总台Z旗下各广播频率、电视频道带来一种全新的数字政绩。广播S科级干部01说:
点击量是一种数字呈现,它很直接,如果这个数字高,能从一个触达率的角度说明我的受众面是很广的,但确实这个数字不能说明“点头率”的问题。很多“10万+”的推文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信息,在新闻的公共性、监督性上是没有力度的。而我们的一些主题性较强的东西确实不会有很多受众来看,但是各台还是会发动力量,在多个平台发布,最后写总结的时候就一个总计的量就行了,上面的领导也会“点头”认可。不会有人去深究你在微信上有多少、微博上有多少,即便微信上的数据是惨不忍睹的。
用虚构的点击量或者经过“改造”式解读的点击量来宣介自己的成绩,成为总台Z旗下各频率、频道的惯用做法,也为它们带来了一种“点击量高”的从业政绩。这在各处级干部的年度公开汇报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几乎每一位处级干部都会在他(她)的汇报中提及有关高点击量的工作内容、成绩等。早先电视W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的新闻推文的点击量较低,用其记者、编辑的话来说,如果点击量超过1万,那就算很高的了。在总台Z某一年的年度总结大会报告里,电视W一条点击量“10万+”的主题报道内容被写了进去。电视W记者01对此表示:
这个事情说来也是搞笑,全年这么多篇公众号推文中就这么一条“10万+”,这条内容发动了不少市级台、县级台的新闻采编人员在个人的微信朋友圈中转发,好像有关人士也买了一点点击量。就这么一条“10万+”能被宣传得这么淋漓尽致,不就是能给领导带来一些面子么!进而说明我们电视W在微信上的传播能力不错。这种政绩汇报性的内容给一线记者、编辑,还有广告业务员,带不来什么真正的“功效”。
“不接受制度对人的刻板约束,而试图让制度本身也很有弹性”(翟学伟,2013:72),成为通过“改造”制度获得面子的一种手段。平台制定的点击量规则固然不能被传统新闻机构改变,但总台Z旗下的各广播频率、电视频道通过所谓的“高点击量”的成绩,也能获得自己的数字政绩。广播J新闻节目编辑02对点击量带来的数字政绩表示“悲哀”:
这种环境损害了记者好好采新闻这件事!现在,多少记者就是拿拿通稿,然后改一改,就发在社交平台上了。确实,有一些重要的内容需要通稿信息,也需要及时发布,往往也能获得比较好的点击量。可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一种非常浮躁的工作状况,点击量把大家搞得团团转,我们原有关注本地民生公共议题的那种很扎实的稿子越来越少,都快“绝迹”了,而且我们的广告创收也没有因高点击量而获得改善。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新闻人的一种“悲哀”。
要指出的是,总台Z并未通过从媒介形态意义上的数字融合变革(黄旦,2019)来进行真切的“融媒体”式发展。在研究中,笔者深感总台Z的各个新闻室宁可舍弃对一些新闻内容深入的关注与采写,也要通过“高点击量”表明自己的媒体融合程度之高,毕竟这种数字政绩会给各频率、频道带来面子上的好处,即便这并不会给新闻业带来营销创收上的可持续保障。
一言以蔽之,点击量从其介入传统新闻机构的数字新闻生产活动后,决策层和一些一线从业人员便通过虚构、改造等手段获得了面子。这也为他们带来了一种数字政绩。受众分析技术带来的点击量与新闻从业者的面子、机构的数字政绩构成了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也就是说,总台Z的新闻从业者运用虚构、“改造”式解读等策略处理点击量这一受众分析技术的产物,以遮蔽自己在融合发展进程中的“本领恐慌”等缺陷,这深刻地印证了中国日常社会运作的一种框架——“真实社会的建构是社会个体运用行动策略同现存的社会结构相权衡的产物”(翟学伟,2005:231)。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中国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从“面子运作”、“面子事情”等角度剖析了传统新闻机构与受众分析技术带来的点击量的互动关系,揭示了新闻从业人员为了获得面子而虚构、“改造”解读点击量的行为。要警惕的是,像总台Z旗下新闻机构对点击量的虚构、“改造”式解读,对新闻业的变革而言都只是饮鸩止渴。这是一种脸面文化下的“变通”,饮“量”止渴更是使新闻业逃避了如何处理好融合发展等关键问题。
本研究主要有三个发现:(1)在传统新闻机构自建新闻客户端不能发挥出商业性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力度时,新闻机构采用了虚构自家平台点击量的方式,试图维持其原有的面子,但这种虚构行为一旦被广告客户等群体揭穿,便会适得其反,进而“丢了面子”。(2)传统新闻机构虽无法左右各商业平台的推送分发机制,但却可以通过对点击量进行“改造”式解读,来彰显自己拥有获得“高点击量”的能力,进而赢得面子。(3)无论是虚构点击量,还是改造对点击量的解读,都深刻地表明传统新闻机构并未按照数字传播的规律进行变革;凸显“高点击量”已然成为传统新闻机构在“面子事情”运作下的一种全新数字政绩。
在面子的作用下,传统新闻机构发现,相比进行更为复杂的系统性数字变革,通过各种手段凸显“高点击量”更为容易,这既能使自己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有面子”般的认可,更能使自己获得数字政绩,切实的变革被延迟或“放弃”。本研究的理论增量在于,对中国本土社会运作极为重要的面子在与新型媒介技术发生碰撞时,新闻室会在面子这一本土文化的作用下处理技术与新闻业的关系,并在地化地“改造”技术带来的产物。
或许,当传统新闻机构的从业人员真正地掌握好数字新闻生产的本领技能,利用好数字监测、分析等技术,才有可能真切地“有面子”、获得“好成绩”,引领新闻业在数字变革的潮流中走得更好更远。这也成为后续新闻研究中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注释:
①依据传统新闻机构新闻生产的实际情况,若无特殊说明,本文将社会化媒体平台有关内容的阅读浏览或访问点击等各类数据统称为“点击量”。
②访谈对象的相关信息详见“附录”。
③未具体写明是第几名,是为了做到匿名化处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写在海报上的排名并不低。
参考文献:
白红义(2018)。重构传播的权力:平台新闻业的崛起、挑战与省思。《南京社会科学》,(2),95-104。
白红义(2019)。点击改变新闻业?——受众分析技术的采纳、使用与意涵。《南京社会科学》,(6),99-108。
白红义(2022)。“平台逻辑”:一个理解平台—新闻业关系的敏感性概念。《南京社会科学》,(2),102-110。
常江,何仁亿(2021)。数字新闻生产简史:媒介逻辑与生态变革。《新闻大学》,(11),1-14+121。
陈昶文(2019)。“流量逻辑”如何影响内容生产?——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实证考察。《新闻春秋》,(5),4-13+20。
胡先缙(2010)。中国人的面子观。载黄光国、胡先缙等(著),《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第45-7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旦(2019)。试说“融媒体”:历史的视角。《新闻记者》,(3),20-26。
江淑琳(2016)。探索数位即时新闻生产之物质性的可能研究取径。《传播、文化与政治》(台北),(总4),27-54。
金耀基(2013)。“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载金耀基(著),《中国社会与文化》(第49-74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
刘燕南(2006)。《电视收视率解析:调查、分析与应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刘战伟(2022)。凸显什么?遮蔽什么?——作为隐喻的“平台”:连接、中介与基础设施。《新闻记者》,(6),54-66。
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2)。从“挣工分”到“挣流量”:绩效制度下的市场、共谋与流量锦标赛。《国际新闻界》,(6),130-153。
彭芸(2017)。《数位时代新闻学》。台北:双叶书廊有限公司。
王辰瑶(2018)。新闻融合的创新困境——对中外77个新闻业融合案例研究的再考察。《南京社会科学》,(11),99-108。
王海燕(2019)。加速的新闻:数字化环境下新闻工作的时间性变化及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10),36-54+127。
王维佳,周弘(2021)。流量新闻中的“零工新闻”:数字劳动转型与西方新闻记者角色的变迁。《新闻与写作》,(2),14-21。
夏倩芳(2013)。“挣工分”的政治:绩效制度下的产品、劳动与新闻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9),28-36。
谢静(2019)。新闻时空的转型与“转译”——基于“上观新闻”的移动新闻客户端研究。《新闻大学》,(8),61-76+122-123。
余沐芩,宋素红(2022)。流量指标意味着什么?——数字时代新闻从业者的劳动控制与自主性研究。《新闻记者》,(6),17-29。
翟学伟(2005)。《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翟学伟(2013)。中国人的关系向度及其在互联网中的可能性表达。载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第61-7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翟学伟(2017)。《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张寅(2020a)。车轮子上的“声音景观”文化:广播的媒介学想象。《传媒》,(16),43-45。
张寅(2020b)。“小编”与记者的“脸面观”:媒体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中的人际关系向度。《新闻记者》,(11),13-25。
张寅(2022)。融合式新闻生产:一个媒体式的“面子工程”?——基于组织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新闻大学》,(4),29-41+120。
佐斌(1997)。《中国人的脸与面子——本土社会心理学探索》。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AndersonC. W. (2011).Between creative and quantified audiences: Web metrics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newswork in local US newsrooms. Journalism, 12(5)550-566.
Nielsen, R. K.& Ganter, S. A. (2018). Dealing with digital intermediaries: A case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ublishers and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20(4)1600-1617.
Zelizer, B. (2005). The culture of journalism.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 198-214). London: Hodder Arnold.
张寅系广州体育学院体育传媒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广州体育学院校管科研课题“融合式新闻生产的误区存有与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XGQN20221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