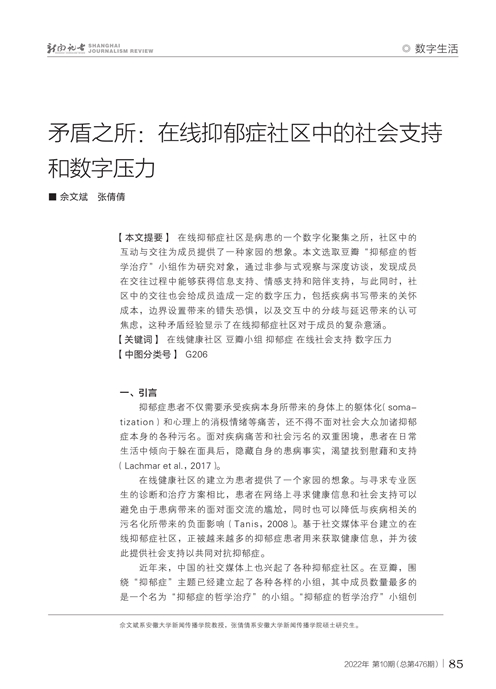矛盾之所:在线抑郁症社区中的社会支持和数字压力
■佘文斌 张倩倩
【本文提要】在线抑郁症社区是病患的一个数字化聚集之所,社区中的互动与交往为成员提供了一种家园的想象。本文选取豆瓣“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非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发现成员在交往过程中能够获得信息支持、情感支持和陪伴支持,与此同时,社区中的交往也会给成员造成一定的数字压力,包括疾病书写带来的关怀成本,边界设置带来的错失恐惧,以及交互中的分歧与延迟带来的认可焦虑,这种矛盾经验显示了在线抑郁症社区对于成员的复杂意涵。
【关键词】在线健康社区 豆瓣小组 抑郁症 在线社会支持 数字压力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抑郁症患者不仅需要承受疾病本身所带来的身体上的躯体化(somatization)和心理上的消极情绪等痛苦,还不得不面对社会大众加诸抑郁症本身的各种污名。面对疾病痛苦和社会污名的双重困境,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倾向于躲在面具后,隐藏自身的患病事实,渴望找到慰藉和支持(Lachmar et al., 2017)。
在线健康社区的建立为患者提供了一个家园的想象。与寻求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相比,患者在网络上寻求健康信息和社会支持可以避免由于患病带来的面对面交流的尴尬,同时也可以降低与疾病相关的污名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Tanis, 2008)。基于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的在线抑郁症社区,正被越来越多的抑郁症患者用来获取健康信息,并为彼此提供社会支持以共同对抗抑郁症。
近年来,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兴起了各种抑郁症社区。在豆瓣,围绕“抑郁症”主题已经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小组,其中成员数量最多的是一个名为“抑郁症的哲学治疗”的小组。“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创建于2020年8月26日,目前已经拥有5万多名成员。作为豆瓣上最大的抑郁症社区,该小组旨在探讨和寻求抑郁症的“哲学治疗”方式,认为“哲学治疗最重要的部分是通过阅读、思考和行动完成的”。它有着明确的分区限制和管理方式,自2020年9月21日起,该小组将所有已发和将发的帖子归入五个专区:“抑郁症结”、“哲学治疗”、“文哲武库”、“生成之在”和“刀锋独语”,试图用理性讨论的方式来引导成员的交流和参与,这样一种“规范化”的社区究竟会给抑郁症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选取“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为个案,来探讨一个边界明确的在线抑郁症社区对于患者的实际意义。
关于在线健康社区对于成员的影响,既有研究侧重于从社会支持的角度进行探讨,主要认为在线健康社区可以给成员提供信息和情感支持,帮助年轻人感到不那么孤立和孤独,并帮助他们的经历正常化,情感和信息上的同伴支持在线上交流中是很明显的(Prescott, Hanley & Ujhelyi Gomez, 2019)。“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无疑也为抑郁症患者提供了交换信息、抱团取暖的平台,研究者同时也注意到,小组的宗旨和愿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未充分落实,家园的想象与实际的交往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尤其是社区中的参与往往也会给成员带来一些焦虑和困扰。
数字压力(digital stress)是理解数字媒体使用和社会心理结果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Steele et al., 2020)。作为一个通用术语,数字压力也用来描述由社交媒体使用的特定方面所带来的压力(Reinecke et al., 2017)。“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成员的矛盾经验显然也与社区使用所带来的数字压力有关,数字压力是检视在线健康社区影响的一个易受忽略的方面。基于此,本文不仅关注该豆瓣小组能够提供哪些类型的社会支持,还试图以数字压力为概念化工具,探讨小组中的交往会给成员带来何种困扰,以揭示在线抑郁症社区对于成员的复杂意涵。
二、文献回顾
(一)在线健康社区对成员的影响
在线社交网络的持续发展和公民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促进了在线健康社区的兴起和繁荣(刘璇等,2017)。与传统的以医生为中心的医疗健康服务模式相比,在线健康社区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就健康医疗相关问题进行信息交流、经验分享、问答咨询及社会支持的开放式网络平台(Maloney-Krichmar & Preece, 2005)。
关于在线健康社区的研究中,一个重要面向是在线健康社区中的参与对于成员(患者)的影响,成员原本也是基于某种需要参与社区中的互动的。Benetoli等人(2019)讨论了在线健康社区对成员的积极意义,包括“便利、用户友好、更好地理解健康信息、赋权以及社会和情感支持”。Wilson与Stock(2021)通过对15名患有长期疾病的年轻人的采访,探讨了他们更广泛地使用社交媒体以及在线健康社区的经验,指出在线健康社区对不同年龄的特定长期疾病的个体具有以下好处:相互支持关系的发展、减少孤立/孤独、减少抑郁/增加情感支持、有用的经验知识分享、感觉“正常”。
线上的支持与交流并不是万能的,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倾向于进行向上社会比较的成员可能会对自己产生负面情绪,并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困难处境,以及网络社区的匿名性也可能导致辱骂、欺骗等负面的交流形式(潘文静,胡敬凡,2020)。Benetoli等人(2019)指出,在线健康社区可能产生“信息过载、浪费时间、负面情绪、对网上信息可信度的怀疑以及在线互动中产生的问题”。Wilson与Stock(2021)也指出在线健康社区使用具有“坏的一面”,主要反映在以下子主题中:(1)关系:减少面对面接触;(2)比较:消极(向上)比较;(3)社区:感觉被遗漏;(4)情绪:痛苦传染;以及(5)知识:对衰退的恐惧。
总体看来,参与在线健康社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可以归纳为内容、技术、交互与伦理等四个方面。在内容方面,主要包括成员对于信息可信度的怀疑、信息过载以及可能存在的负面情绪的传染。在技术方面,主要是指技术上的延时性,有时一个话题不会被看到,也可能不会得到回复(Prescott, Hanley & Ujhelyi Gomez, 2019)。在交互方面,存在误解的可能以及在线环境让人们大胆地发布粗鲁、轻率的评论(Turner, 2017)。在伦理方面,主要包括身份和欺骗、隐私和保密性等问题(Demiris, 2006)。
可见,双重影响是一个更加全面和平衡的视角,也更为符合用户使用在线健康社区的实际经验。
(二)在线社会支持
既有研究主要以社会支持作为理论视角讨论在线健康社区对于用户的积极影响。社会支持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在对自杀的研究中发现,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与自杀率有关,社会关系/支持的丧失是导致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倪赤丹,2013)。20世纪70年代,社会支持的概念被正式引入精神病学研究。Cobb(1976)认为社会支持是指在人与人互动沟通时,个体感受到他人给予自己的爱护、尊重和重视等,并且这种支持性的互动能够帮助个体抵御生活压力对健康产生的不良影响。社会支持的类型主要可以归纳为情感支持、物质支持(物资、金钱和服务)、信息支持和陪伴支持(Walker, Wasserman & Wellman, 1993)。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上的社会支持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西方学者提出了“基于计算机中介的社会支持”(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ocial support)、在线社会支持 (online social support)等概念(常李艳等,2019)。
在线社会支持的研究中,量化或质化的类型分析是一个基本路径。Bambina(2007:28)针对一个癌症患者论坛设置了一套在线社会支持编码方案,将在线社会支持分为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陪伴支持三种类别,每一种在线社会支持类别都细分出子类,比如情感支持包括理解/共鸣、鼓励、肯定/认可、同情、关心/担心这几个子类,信息支持包括建议、参考和教授,而陪伴支持则包括闲聊、幽默/调侃和团体性。
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一是揭示在线社区支持的新的类型,如有的在线健康社区也能提供一定的具体/有形的物质和服务支持。二是从情境入手关注社会支持类型与社区的关系,包括特定社区所能提供的具体社会支持类型,如张惠蓉等(2008)通过分析PTT精神疾病及整形美容两版的帖文内容,比较了两版在资讯支持、自尊支持、网络支持以及情感支持方面的差异,并探讨了其与两版讨论主题、性别以及非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
有关在线社会支持的研究中,抑郁症群体也是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如施建锋和马剑虹(2003)将社会支持视为个体能为他人提供的同情和帮助,这种帮助或同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个体的各类不良情绪,如焦虑、紧张、抑郁等。也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缓解产后抑郁症的可能性(Leahy Warren, 2005)。相反,失去社会支持将会导致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和行为的增加(Joiner et al., 2009)。潘文静和刘迪一(2021)基于从网页抓取的在线抑郁症互助论坛公开数据,讨论结构化社会资本与礼貌原则对获得社会支持的影响。
(三)数字压力
在早先的研究中,表示数字压力的更广泛的术语是所谓的“技术压力”(Technostress),该术语由Brod(1984:16)首次定义为“无法以健康的方式适应或应对新的计算机技术”。当前数字压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数字媒体,数字压力是由“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强大使用、甚至几乎永久使用所带来的压力……这是由永久获得不可思议的(社交)内容的数量和多样性的访问所引发的”(Hefner & Vorderer, 2016)。该术语还用于识别伴随来自社交媒体的通知或实际使用社交媒体的认知、情感和生理唤醒(Thomée et al., 2010)。Steele等人(2020)在文献检阅的基础上,将数字压力定义为“在个体的社会和关系环境以及应对资源(coping resources)的背景下,对事件、条件或刺激(即‘压力源’)的主观体验”。
Steele等人(2020)进一步归纳了数字压力的四个组成部分,包括可用性压力(availability stress)、认可焦虑(approval anxiety)、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和连接过载(connection overload)。Hall(2020:164)则将Hampton等人(2016)提出的另一种类型的数字压力,即“关怀成本”(cost of caring)加入进来,提出了五种可能的数字压力类型。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许多定性和定量的研究都提到了数字压力,但它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术语来指代相似或相同的结构(Steele et al., 2020)。
对于数字压力的来源,Tarafdar等人(2007)用“技术压力创造者”(technostress creators)来表示,主要包括技术过载、技术入侵、技术复杂性、技术不安全性、技术不确定性五个方面。Weinstein与Selman(2016)确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数字压力源(digital stressors),第一类主要是指敌意关系,包括“恶意和骚扰性的人身攻击”、“公开羞辱”和“冒充”(impersonation),第二类源于青少年使用数字技术来寻求联系,主要包括“感到窒息”、“遵守访问请求的压力”和“侵入数字账户和设备”。Maier等人(2015)则归纳出六种“SNS压力创造者”(SNS-stress creators):复杂性、不安全性、侵入、披露(disclosure)、模式(pattern)与社交过载。
数字压力研究集中关注数字媒体使用的社会心理后果,显示了对既有的描述性研究进行理论归纳的尝试,可以作为揭示在线健康社区对于用户负面影响的相对集中的视角。
结合文献的梳理,立足于现实经验和采用平衡立场,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1.通过参与豆瓣“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成员主要获得了哪些类型的社会支持?
2.“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的成员在参与过程中是否感受到数字压力?这些数字压力主要源自哪里?
3.在线抑郁症社区本身的特质对于成员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和所感知的数字压力有何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非参与式观察法
在2021年6月至2021年8月这三个月里,研究者一直在线上观察小组成员的交往情形,并从8月初开始密集关注小组成员的发帖内容与互动情况,及时整理、分类小组成员的发帖内容。由于不想扰乱小组成员的正常互动,以及研究者在身份上的考虑,所以本研究采用的是非参与式观察法,研究者只加入了小组,但并没有在小组内发帖、回帖。
(二)深度访谈法
在深度访谈过程中,研究者首先通过豆瓣私信的方式联系访谈对象,向其表明访谈意向,并明确了访谈内容仅用作学术研究。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文中皆隐去其在小组中的用户名,改用代码表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受访者的特殊性,为了尊重受访者以及确保访谈的顺利进行,本次深度访谈均采用线上文字访谈的方式。此外,本次研究采用的是半结构式访谈,在访谈问题的设置上,第一部分是关于受访者的一些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年龄、目前的抑郁情况等。第二部分是关于受访者在该豆瓣小组中的一些使用情况和个人感受。访谈对象的具体情况参见表1。
四、研究发现
(一)在线社会支持的类型
本文选用Bambina(2007:28)的编码方案作为在线社会支持类型的参考框架,发现“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成员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是信息支持、情感支持和陪伴支持。其中,信息支持更多来自于知识的分享,此外,即便是一个倡导理性讨论的抑郁症社区,情感和陪伴支持仍然显著,这也是在线社区中交流的意涵所在。
1.信息支持:知识的分享
“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只讨论抑郁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典型心理病症的哲学治疗”,旨在探讨“如何运用思考的力量进行个人治疗”。组长在谈到建组目的时表示:“我觉得治疗抑郁症光靠正能量不行,还需要对真实的世界有一个切近的认识,哪怕这些哲学思考来自所谓‘负能量’。”
对于疾病认知的强调,使小组中的知识和意义探究多于具体的医学建议。如在“文哲武库”分区,最常见的帖子是对于哲学类、心理学类书籍的推荐,一些成员还通过读书笔记、摘录、阅读感悟的方式分享阅读经验,引介理解抑郁症的各种思想资源。有成员发帖谈到“书籍的力量”时表示:“看到楼里的前辈发的‘给青年的12封信’,对于去年一整年收(受)到同龄人打击的我,去年一年都在自暴自弃,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慢慢地走出来了,阅读了12封信,瞬间明白了,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时代,都有与我相似的人,困扰相似,我不必自甘堕落,与我相似的人一直都在。”
在“哲学治疗”分区里,成员所提供的经验分享大多也是基于精神层面的思考,而不是对医治手段的讨论。例如针对困扰组内成员的生死意义的问题,有成员认为:“我们活下去可能并不需要‘意义’……真正让自己活着的动力,只来自于自己内心深处对一切感知的渴望,对穷尽生命可能性的追求,和一切不甘”。受访者中也有人谈到了自己会从对疾病的思考和感悟出发,分享一些个人理解:
最近发的一个是哲学治疗,写的是我从抑郁状态走出来后对当时一些困惑的自我反思……我一般是在自己有抑郁倾向的时候来这个组看看,那个时候主要是看帖,现在觉得状态变好之后就不怎么看帖,会写一些东西发帖,希望对组里成员有帮助。(受访者Q)
会看或写一些逻辑自洽,自我感悟的帖子。因为抑郁一些东西想不通,看看有没有人想通了,或者我想通了,发出来。(受访者E)
其他人的疾病经历本身就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Ziebland & Wyke, 2012),这些信息可以帮助缓解恐惧、增强信心(Lowe et al., 2009),并通过将症状及其影响与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进行比较,建议或确认自己和医生的诊断(Armstrong & Powell, 2009)。小组里提供的这些信息支持虽然主要不是疾病经历方面的建议、参考和教授,但提高疾病认知对于应对疾病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成员们对此也给予了肯定的态度,如有受访者表示:
有些人会发一些帮助走出抑郁和如何理清思路的方法,这个有一点点用。(受访者Z)
我觉得挺好的,像个病友组,我现在已经很少看组里了,好了许多,但是很多其他无法自己走出来,也没有能力治病或者不愿意的,还有一个聚集地,组里偶尔还是有些干货帖的,对他们是有帮助的,至少我的帖子对许多人似乎有所启发,不管是互相拥抱也好,互相帮助也好,都是正向且有反馈的,作为社群,已经可以了。(受访者E)
因为那时候有抑郁,然后看到这个小组,发现里面的内容都比较优质,所以加入了。(受访者M)
2.情感支持:共鸣与鼓励
网络中的情感支持对患者无疑是一种有效的补充和替代,甚至成为个体患病后最重要的情感支持来源(涂炯,周惠容,2019)。在“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中,情感支持也是成员所获得的一种十分明显的社会支持类型。由于成员基本上都是抑郁症患者,他们有很强的共情基础,因而能够彼此理解和形成共鸣,并且也倾向于互相鼓励。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成员之间的理解和共鸣在小组的帖子中随处可见。一种直观表现就是帖子的评论里经常会出现“世另我”、“我也是”等词语。在小组中,有三种类型的帖子较常产生即时的呼应。第一,当谈论到自身的抑郁症结时,家庭因素是大多数成员都提到的一点,有成员表示:“被妈妈发现抑郁症药物……完全就是一副不相信的样子,说我就是太闲了,每天才有时间七想八想,都是自己作的……”,随后就有成员评论道:“有这样的家人真是让人窒息,我父母也是一直不理解,病情反反复复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我工作了才意识到这是严重的病。”第二,当成员谈到自身目前的生活状态时,如“私以为是‘麻木’,不是悲伤、痛苦,也不是愤怒……”,就有成员表示感同身受:“我也是,目前就是这个状态,没有情绪的感知能力了。”第三,当有成员分享个人的经历和感悟时,帖子里有人回复:“这几天我仔细看了两遍,中间忍不住泪目,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能更加赞同了”。“后面写到你的朋友打电话劝你的部分十分能让我共情,读得我眼角湿润了”。
受访者也多谈到了在小组中能够感受到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共鸣,进而从中能够获得安慰:
最大的收获大抵是看到许多人比自己还痛苦吧,心理平衡了些。反而是我自己把它当作了一个平台分享自己的心得获得一种认同感。(受访者E)
大家都是生了病的人,一起熬过去。(受访者R)
让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会从别人的发帖中获得一些共鸣,互相安慰鼓励。(受访者Q)
以前忍不住会点开吧,想看看那个人具体说什么,是不是和我一样,就是自己抑郁比较严重的时候……如果我情绪非常不好,它会给我一些安慰。如果我情绪好点,看这些帖子会让我压抑。(受访者Z)
我会在心情低落时看些和我的处境、想法差不多的帖子,平时看的不多……这样我会找到共鸣和安慰感。(受访者H)
成员之间的理解和共鸣也使他们倾向于互相鼓励,小组中就有帖子写道:“这几天在这个小组里看到一些同类也深受着这黑狗的折磨,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毕竟自己也深陷其中,只是希望你们能比我勇敢和坚强,等来云开雾散,重回到那个充满阳光的世界。”这种鼓励不仅能够给看到帖子的人带来慰藉,也能够给发帖者带来积极影响,受访者G就表示从中能够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并获得前行的力量:感觉自己发帖也启发到了很多人,慢慢地在记录里也通过吃药、运动走出来了。
3.陪伴支持:闲聊与纪事
在观察小组中的交往互动时,发现有很多闲聊话题的帖子,这些帖子意在唤起日常对话而不是寻求治愈知识和经验。小组中常常会看到诸如“大家有什么难受的时候会听的歌吗”、“大家看过哪些剧觉得有被治愈到”、“大家每天的快乐是什么呢”这类问答贴,这种帖子常常也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回复。有成员在组里发帖“可以请大家写出最喜欢的食物吗”,随后就有大量的成员开始互动:“我一周前在大理沙溪翕庐饭馆连吃了三天的松茸土鸡汤,味道特别鲜美”、“一时想不到具体的,但是我好喜欢热乎乎的饭,裹着好吃的菜和汤汁一大口塞进嘴里,口腔被填满的感觉很快乐”。这种帖子虽然看起来和抑郁症毫无关联,但就像楼主所言:“在楼主自己的经历中,因为难受而躺在床上想要一直躺下去的时候,常常是从‘去吃一口面包’这样简单的想法获得开启一天的动力”。
在小组中,有许多人甚至以“求救”的方式来寻找人聊天,以满足自己排遣孤独的需要。例如有成员发帖:“我不行了,有没有人跟我讲讲话,谈些什么内容都行”,而对于这样的一些“求救帖”,很多成员都会在帖子下方进行回复,和楼主对话并鼓励楼主,这些回复的确能够温暖到“求救者”,有发帖者就直接在帖子里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回复,发了帖子之后好几个小伙伴私信我,感觉莫名的温暖,被你们暖到啦(两个爱心的表情)。”可见,闲聊往往能够增进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
小组中还有众多成员坚持分享日常生活的记录,使社区成为一种网络化的记事本。有成员发帖:“从1月24日起,记录每天生活上令我觉得温暖或者快乐的事情,尽量让自己的病情慢慢好起来。加油。”也有成员发帖“好的坏的每天有空就记录一下吧”。一些成员偶尔也会记录自己的烦恼,例如“好难过,没有收到二面的短信”。有些成员还以文字加图片的方式进行记录,将日常生活直观呈现于他人面前。这样的集体记事,将成员的日常生活链接在一起,提供了一种线上的共在感。
抑郁症群体通过豆瓣小组聚集起来,更有“抱团取暖”之意,就像有成员说得那样:“在豆瓣上看到很多和我一样的思考,想到什么诚实记录下来,就不再感到孤单。”“大家一起来,人多了力量就大,所以要感谢有这样的小组把大家聚起来。”
疾病通常会带来一种孤立感。知道其他人正在处理类似的问题,学习他们如何处理困难的问题,可以减少这种孤立感,带来对群体的归属感,并让人确信自己的经历和反应是正常的(Harvey et al., 2007)。通过小组中的日常交流和连接,成员之间能够形成陪伴,这也是一种化解孤立的有效方式,一些受访者特别强调了陪伴的意义:
这个小组对我来说多的是陪伴感,原来那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受访者H)
看病友们的近况,会让我觉得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扛抑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需要的是群体,不是文章……主要是陪伴,会觉得不只是自己有抑郁,还有那么多人,也在每天坚持着,所以自己会从里面获得力量。(受访者M)
(二)数字压力的来源
按照既有的数字压力构成研究,“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中成员的数字压力主要有三种:关怀成本、错失恐惧和认可焦虑,但这些数字压力的来源对应的是社区使用的具体情形,其中关怀成本是由于成员的疾病书写造成了痛苦的传染,错失恐惧源于社区边界设置带来的社会排斥,认可焦虑则是由交流中的分歧和延迟所导致的。
1.疾病书写与关怀成本
数字媒体提高了人们对亲密和更远的熟人生活中的网络生活事件(network life events)的认识,意识到他人生活中不受欢迎的重大生活事件可能是心理压力的一个来源,即关怀成本(Hampton et al., 2016)。各种类型的数字媒体使传播负面网络生活事件和了解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Hall, 2020:169)。显然,数字媒体的广泛连接,增加了他人社会压力环境信息的可见度。
关怀成本是基于对亲密朋友和家人生活中的意外生活事件的意识提出的,但“数字媒体也可能增强个人社区的结构,使更广泛而不是特别密切的联系网络变得更持久,并施加额外的社会压力”(Hampton et al., 2016)。在“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中,成员之间并非强关系,关于疾病的普遍书写却增加了成员对他人病痛的感知和意识,由此形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疾病书写的网络化已成为一种趋势,基于弱关系网络带来的关怀成本越来越成为在线抑郁症社区中的一个数字压力来源。
通过对小组发帖内容的观察发现,大量的帖子都是关于病痛的讲述,难免会带有一些负面情绪。如有成员发帖时说:“我看到我自己打出来的字,就好像已经和自己诉说了一遍,身体里的我能听见我说话,这导致我和外界愈发割裂。割裂也会造成痛苦。所有都没结束,痛苦没结束。”还有成员说道:“我现在在阳光下,心里却和外面的雾霾天一样。家里人总说,我是整个家庭的纽带,可我觉得这个角色好累,要平衡各种关系。忽然对未来的生活厌倦,绝望了。”这种情形也印证了既有研究所指出的,负面情绪的表达在心理健康社区中非常普遍,比积极情绪更普遍,特别是在在线抑郁症社区中(Gkotsis et al., 2016)。
小组中这种负面情绪的表达,虽然可以让发帖者在一定程度上释放情绪,但是这种表达也会给他人带来一定的困扰,尤其是痛苦的传染。既有研究发现,了解其他有相同健康问题的人的负面经历和结果尤其令人痛苦(Benetoli et al., 2019)。另一项研究也指出,如果病人发现他们的同龄人过得很糟糕,他们对自己状况的绝望感可能会变得更严重(Hinton et al., 2010)。在小组中,这种带有负面情绪的帖子在某些方面的确会加剧抑郁症患者的无能为力感,很多受访者都表达了看了这些帖子之后自己的无助:
其实我看到那么多抑郁患者那么痛苦会感觉有一点难过,而我也没什么办法帮助他们走出来。(受访者H)
很多人有的痛苦我都已经走出来了,我看了会很难受,想帮也帮不了。(受访者E)
看到很多人的实例吧,外界的压力,学校的不作为,能让我很清晰地感受到整个社会大环境对抑郁还是不那么宽容,甚至连最神圣的教育都只是从老师的个人角度出发,有些时候真的蛮无力的。(受访者G)
在线抑郁症社区基于弱关系网络而形成,它本身并不要求小组成员有更强的义务承担感和责任感,但是社交媒体平台赋予的永久性和公开性意味着对他人压力环境信息的持久接触,这也是一种由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关怀成本。
2.边界设置与错失恐惧
Steele等人(2020)将错失恐惧定义为“因他人从事有益的经历而产生真实的、可感知的或可预期的社会后果,自己却缺席其中所引发的压力”。他人所从事的有益经历,既指发生在网上的交流,也指数字媒体中其他人发布的积极体验(Steele et al., 2020)。错失恐惧并不是真正的恐惧,主要是指伴随着被忽视或被排除的焦虑或不安感(Hall,2020:166)。在“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中,他人所从事的有益经历的缺席主要是和社区的边界设置联系在一起的。
“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有较明确的主题设置:“本小组只讨论抑郁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典型心理病症的哲学治疗,而不讨论抑郁导致的身体症状和它的医学治疗或宗教救济。”在此背景下,小组中多有哲学和心理学层面的讨论和分享,一些帖子甚至引入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和思想家来进行书写,极力体现一种思考的深度。但囿于知识背景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小组成员都能获得参与其中的积极体验,有成员在评论里就说道:“感觉这些离我很遥远,也许对于看得懂的人来说在里面理解一句话就像理解‘我刚刚吃饭了’、‘这朵花是红色的’这样简单,但是对于我来说就好像只是在认字。”可见,对于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帖子,很多时候也会给其他成员带来被排除在外的边缘人境遇。
此外,小组的边界设置还包括许多明确的组规,比如发帖内容的限制和删帖的管理方式,这些设置也使小组成员的参与被排斥或中断,在观察和比较他人的网上交流时,就会产生孤立感或不受欢迎感。
小组有“组内不是倾倒绝望情绪的场所,请先有思考”、“与小组主旨无关的帖子将会被删除,从而保证重要的声音能够被充分倾听”等规定。针对这些组规,成员在评论里表示:“没有人喜欢这些苦水,包括吐出来的这些人,包括我。可这就是抑郁症……当然,也可以不看。我崩溃的时候也不看。可要允许它们存在。”更有甚者认为:“共情当然不足以治愈发帖者,但是谁指望在这里接受治疗?”一些抑郁症患者加入小组更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树洞”来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组里的这种边界设置对他们来说,实际上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压力,有成员就表示:“我都不知道怎么排解负能量。我知道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不愿意听,但是在网上也没有人愿意听。”在访谈过程中,有受访者也认为这些规定使成员错失了参与一些网上交流的机会:
我不太希望有这样子的组规,因为这里本身是这个群体表达的一个地方。如果限制了,就已经违背了这个小组的意义。我其实挺高兴那些发负面情绪的人可以在这里发,只是我自己尽量不看很负面的而已……这个小组的存在可以让需要它的人在这里抒发情绪是它最基础的意义,在此之上,它才能去增加别的意义,例如好的方法的推荐、总结、抒发等等。因为抑郁这群人就是有这样子的情绪,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你不能限制他们。而且作为抑郁患者,我们是真的很能理解他们表达的负面情绪……真的有很大负面情绪的,基本上已经不会发帖子了。能发,说明他还在争取。(受访者M)
这是个关于抑郁症的哲学小组,虽然是个专注理性思考的小组。但我不认为抑郁症患者到情绪汹涌的状态可以真的用哲学角度思考。或许他们只是搜到了这个小组,急需一个出口。(受访者L)
3.分歧、延迟与认可焦虑
在数字压力中,认可焦虑是关于他人对自己的帖子、照片或信息以及数字足迹的组合(即数据档案)的反应的不确定性和焦虑程度(Steele et al., 2020)。在“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中,成员之间在交互过程中的分歧和延迟是认可焦虑的主要来源,这两种情形都给参与者带来了负向的反馈。
一项研究发现,负面的论坛体验来自于与其他论坛成员的互动不佳或与论坛版主的分歧(Griffiths et al., 2015)。即便是在成员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在线抑郁症社区中,交往互动过程也难免存在分歧与误解,由此也造成了一种压力。在“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中,有成员在被误解后就表示:“虽然有失语但我是专业的,不过打错了也不高兴改,解释了半天太累了,不回了,随便。”也有许多成员就帖子的内容产生了分歧,最终形成了彼此之间的对立,如有成员说道:“我最后也说了,不想看到非建设性意见,怼你我也无意冒犯,但踩我雷点就是这样,请相互拉黑,你的言论让(我)觉得不值得交流。”以至于有楼主主动出来“劝架”:“我发帖的初衷是让大家了解自己,坚持下去,找到希望。不是让你们在这吵架……大家都是来这寻找出口的,弄得不开心反而把自己堵住了,就南辕北辙了。”
小组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带有恶意的评论,诸如“我不理解学历高、家境好、家庭完整的人为什么得抑郁症”,以及“抑郁症是否是在为自己的无能和逃避找理由”之类,而这样的一些言论必然也会伤害到组内的一些抑郁症患者。有成员就提到:“简直就像没有得抑郁症的人对病者说‘你怎么会得抑郁症啊’,没想到在病者之中,也有这样想法的人。”Weinstein与Selman(2016)提到数字化敌意关系是一种数字压力来源。在小组中,轻率、粗鲁甚至攻击性的评论类似于敌意关系中的“恶意和骚扰性的人身攻击”,可以看作一种极端的分歧形态。
在小组中,并不是所有的帖子都能够得到大家及时的回复。一些在线健康社区研究也提到了交互延迟的情形及其后果,如许多寻求支持的请求甚至没有得到任何回复(Coulson & Greenwood, 2012),异步性质意味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任何反馈,这种延迟会导致低感知情绪支持(Malloch & Hether, 2019),而未被回答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发布者感到被拒绝,此外,回复可能来得太晚了,以至于它们变得毫无意义(Turner, 2017)。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E就认为自己发的帖子没有得到大家的回复会让她产生压力:
我有时发一些帖子其实是为组里负能量量身定制的,但似乎他们并没有解药在这里的感觉,依然沉浸在宣泄痛苦中,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真心被错付,就会删帖,觉得不值得。毕竟在组里想帮人花的精力远比收获多,但有时候真的觉得带不动,会有些沮丧……发的是一些针对他们走不出来的思维定势和死循环,告诉他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想。但似乎收效甚微,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这个问题,或者说已经没有精力思考了,痛苦占据了大部分心力。我还发过心理咨询的一些注意事项,明明很多人问,但发出来之后无人问津,我就干脆删了。
五、结语
本文旨在探讨在线抑郁症社区中的参与对于成员的影响,不仅关注社区所提供的社会支持类型,还试图以数字压力为概念化工具,讨论社区中的参与会给成员带来什么样的不安与困扰,以揭示在线抑郁症社区对于成员的复杂意涵。
通过非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本文发现豆瓣“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所提供的社会支持类型主要分为信息支持、情感支持和陪伴支持。由于小组突出强调“哲学治疗”,重视哲学思辨在抑郁救治上的运用,小组所提供的信息支持大多都是基于精神层面的思考和分享。作为一个知识性而非实用性社区,小组更偏向于提供疾病认知和理解方面的反思性知识,而不是关于临床治疗方面的建议、参考和教授。此外,即便是一个知识性社区,情感支持与陪伴支持在社区中也是明显的社会支持类型,情感和归属是在线健康社区得以建构的重要基础。由于成员大多都是抑郁症患者,他们在情感上能够体会到彼此的痛苦,容易产生共鸣与获得安慰。社区中的日常互动和个人生活记事的网络化,某种意义上也给成员提供了一种陪伴感,他们倾向于在社区中互通声息和抱团取暖。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线社会支持与社区类型、互动情形以及网络关系等情境因素有较大的相关性。
本文同时也注意到,在线抑郁症社区中的参与也会给成员带来一些数字压力。这种数字压力并不是单纯地由社交媒体本身所引起的,它更多来源于线上的人际互动,是一种主观的负面体验。在本文所考察的个案中,在线抑郁症社区中的数字压力及其来源主要包括疾病书写带来的关怀成本,边界设置带来的错失恐惧,以及在线交互中的分歧与延迟带来的认可焦虑。既有数字压力研究中所描述的连接过载和可用性压力对于在线抑郁症社区的成员并不显著,前者是由于抑郁症患者缺少社会关怀,反而更希望从在线社区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分享和互动,后者则由于成员个体之间并非熟人关系,往往并不需要对特定的人作出及时回应。
本文从经验出发进一步强调,关怀成本的产生并不局限于强关系网络中的熟人,陌生人网络生活事件中的变故也能引发对此的意识和压力,在线抑郁症社区中,通过网络化连接的成员基于共同遭际而能够感知他人的痛苦,基于弱关系网络的关怀成本成为在线抑郁症社区乃至在线健康社区用户一个显著的数字压力来源。本文还从社区的边界建构方面,发现主题与规则约束对于用户使用带来的疏离感,个人参与的外部限制导致的缺席也可能成为错失恐惧的来源,归根结底,错失恐惧体现了渴望与他人保持联系和归属感的需要。
数字压力作为一种主观体验,可以从寻求联系的基本倾向与一个平台或设备的功能所支持或鼓励的与个人媒体使用模式之间的交集中理解(Hall,2020:157)。本文同时确认了数字压力来自于数字媒体和用户的交互作用,它与平台的可供性有关,也是在成员的实践中产生的,数字压力的研究因而需要不断纳入新的经验化事实。
由于有社交焦虑、抑郁症状和/或孤独感的青少年和年轻人更有可能使用社交媒体寻求支持或缓解症状,因此努力减少数字压力的主观体验或减轻潜在症状可能比通过减少社交媒体使用本身来减轻心理症状的努力更有效(Steele et al.,2020)。探明数字压力来源,也有助于在线抑郁症社区相应的改进与完善。以“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为例,对于小组中负面经历披露可能带来的关怀成本,该小组就设立了专门的“刀锋独语”分区,以减少压力环境信息的暴露,同时也满足了倾诉者的心理需求,但这也对社区的维护和沟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个体来说,当成员意识到分歧和敌意会带来认可焦虑时,他们可以选择“切断”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的功能(例如删帖、禁止回复)避免再次让自身陷入这种压力,成员自身对数字压力来源的认知也是一种必要的社交媒体素养。■
参考文献:
常李艳,华薇娜,刘婧,王雪芬,潘雪莲(2019)。社交网站(SNS)中在线社会支持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现代情报》,(5),166-176。
刘璇,汪林威,李嘉,张朋柱(2017)。在线健康社区中用户回帖行为影响机理研究。《管理科学》,(1),62-72。
倪赤丹(2013)。社会支持理论:社会工作研究的新“范式”。《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58-65+93。
潘文静,胡敬凡(2020)。网络社区中的社会支持: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分析。《新闻春秋》,(2),72-82。
潘文静,刘迪一(2021)。在线互助论坛中如何获得社会支持:结构化社会资本与礼貌原则的影响。《国际新闻界》,(4),51-73。
施建锋,马剑虹(2003)。社会支持研究有关问题探讨。《人类工效学》,(1),58-61。
涂炯,周惠容(2019)。移动传播时代社会支持的重构:以抖音平台癌症青年为例。《中国青年研究》,(11),76-84。
张惠蓉,何玫桦,黄倩茹(2008)。线上社会支持类型探讨:以PPT精神疾病版及整形美容版为例。《新闻学研究》,(94),61-105。
Armstrong, N.& Powell, J. (2009). Patient perspectives on health advice posted on Internet discussion boards: a qualitative study. Health Expectations, 12(3)313-320.
Bambina, A. (2007). Online Social Support: The Interplay of Social Networks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ambria press.
BenetoliA.Chen, T. F.& Aslani, P. (2019).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using social media for health purposes: Benefits and drawbacks. Health Informatics Journal25(4)1661-1674.
BrodC. (1984). Technostress: The Human Cost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ReadingMass. : Addison-Wesley.
CobbS. (1976).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38(5)300-314.
Coulson, N. S.& GreenwoodN. (2012). Families affected by childhood cancer: An analysis of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support within online support groups.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38(6)870-877.
Demiris, G. (2006). The diffusion of virtual communities in health care: concepts and challenges.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62(2)178-188.
Gkotsis, G.et al. (2016). The language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social media. In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Workshop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pp. 63-73).
Griffiths, K. M.Reynolds, J.& Vassallo, S. (2015). An Online, Moderated Peer-to-Peer Support Bulletin Board for Depression: User-Perceive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JMIR mental health, 2(2)e14.
HallJ. A. (2020). Relating through technology: Everyday social inter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mpton, K. N.Lu, W.& Shin, I. (2016). Digital media and stress: the cost of caring 2. 0.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9(9)1267-1286.
HarveyK. J.et al. (2007). ‘Am I normal?’Teenagers, sexual health and the internet.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5(4)771-781.
HefnerD.& Vorderer, P. (2016). Digital stress: Permanent connectedness and multitasking.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edia Use and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ory and Research on Positive Media Effects (pp. 255-267). Routledge.
HintonL.KurinczukJ. J.& Ziebland, S. (2010). Infertility; isolation and the Internet: a qualitative interview study.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81(3)436-441.
JoinerT. E.et al. (2009). Main predictions of the interpersonal-psychological theory of suicidal behavior: empirical tests in two samples of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8(3)634-646.
Lachmar, E. M.et al. (2017). #MyDepressionLooksLike: Examining Public Discourse About Depression on Twitter. JMIR mental health, 4(4)e43.
Leahy Warren, P. (2005). First-time mothers: social support and confidence in infant car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50(5)479-488.
LoweP.et al. (2009). “Making it All Normal”: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Problematic Pregnanc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10)1476-1484.
Maier, C.et al. (2015). The effects of technostress and switching stress on discontinued use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a study of Facebook use.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25(3)275-308.
Malloch, Y. Z.& Hether, H. J. (2019). The dark side of addiction support forums: Impacts of poor quality and insufficient emotional support on perceived support availability and health efficacy.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24(4)432-441.
Maloney-KrichmarD.& Preece, J. (2005).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sociabilityusabilityand community dynamics in an online health community. 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TOCHI)12(2), 201-232.
PrescottJ.Hanley, T.& Ujhelyi GomezK. (2019). Why do young people use online forums for mental health and emotional support?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47(3)317-327.
ReineckeL.et al. (2017). Digital Stress over the Life Span: 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Load and Internet Multitasking on Perceived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mpairments in a German Probability Sample. Media Psychology, 20(1)90-115.
SteeleR. G.Hall, J. A.& Christofferson, J. L. (2020). Conceptualizing Digital Stress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n Empirically Based Model.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3(1)15-26.
Tanis, M. (2008). Health-Related On-Line Forums: What’s the Big Attractio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13(7)698-714.
TarafdarM.et al. (2007). The Impact of Technostress on Role Stress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24(1)301-328.
Thomée, S.Dellve, L.HarenstamA.& HagbergM. (2010). Perceived connections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se and mental symptoms among young adults-a qualitative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1066.
TurnerJ. A. (2017). Online Support Groups: The Good, the Badand the Motivated. Journal of Consumer Health on the Internet, 21(1)11-25.
WalkerM. E.WassermanS.& WellmanB. (1993). Statistical Models for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2(1)71-98.
Weinstein, E.C.& Selman, R. L. (2016). Digital stress: Adolescents’ personal accounts. New Media & Society18(3)391-409.
WilsonC.& StockJ. (2021). ‘Social media comes with good and bad sidesdoesn’t it?’ A balancing act of 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social media use by young adults with long-term conditions. Health , 25(5)515-534.
ZieblandS.& Wyke, S. (2012). Health and Illness in a Connected World: How Might Sharing Experiences on the Internet Affect People’s Health? The Milbank Quarterly90(2)219-249.
佘文斌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倩倩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