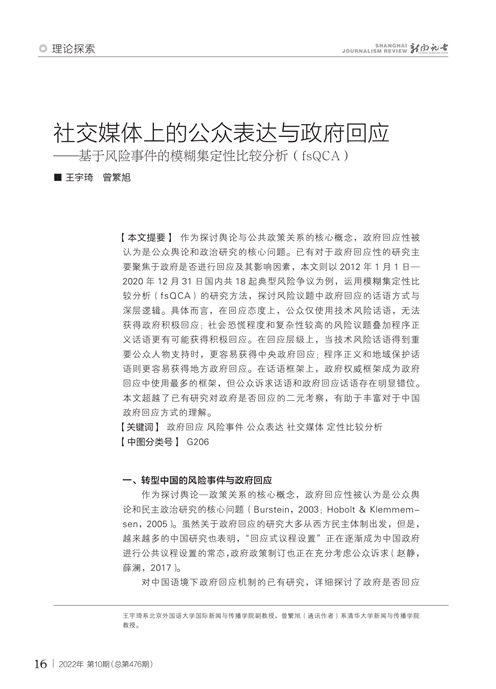社交媒体上的公众表达与政府回应
——基于风险事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王宇琦 曾繁旭
【本文提要】作为探讨舆论与公共政策关系的核心概念,政府回应性被认为是公众舆论和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已有对于政府回应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是否进行回应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则以2012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国内共18起典型风险争议为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研究方法,探讨风险议题中政府回应的话语方式与深层逻辑。具体而言,在回应态度上,公众仅使用技术风险话语,无法获得政府积极回应;社会恐慌程度和复杂性较高的风险议题叠加程序正义话语更有可能获得积极回应。在回应层级上,当技术风险话语得到重要公众人物支持时,更容易获得中央政府回应;程序正义和地域保护话语则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回应。在话语框架上,政府权威框架成为政府回应中使用最多的框架,但公众诉求话语和政府回应话语存在明显错位。本文超越了已有研究对政府是否回应的二元考察,有助于丰富对于中国政府回应方式的理解。
【关键词】政府回应 风险事件 公众表达 社交媒体 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
一、转型中国的风险事件与政府回应
作为探讨舆论—政策关系的核心概念,政府回应性被认为是公众舆论和民主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Burstein, 2003;Hobolt & Klemmemsen, 2005)。虽然关于政府回应的研究大多从西方民主体制出发,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也表明,“回应式议程设置”正在逐渐成为中国政府进行公共议程设置的常态,政府政策制订也正在充分考虑公众诉求(赵静,薛澜,2017)。
对中国语境下政府回应机制的已有研究,详细探讨了政府是否回应公众诉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具备较高社会地位或拥有较多社会资源的诉求主体,以及解决难度较低的议题,均能获得较为积极的政府回应(孟天广,李锋,2015)。此外,议题本身较高的社会关注度(Tang, Chen & Wu, 2018)、涉及群体利益或有较高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Hassid & Brass, 2011;Su & Meng, 2016;Chen, Pan & Xu, 2016),均与更为积极的政府回应相关。
然而,除了是否回应以外,中国语境下风险议题中的政府回应往往体现出更为复杂的逻辑,并蕴含着更为多元的理论困惑。从政府回应的态度而言,一些风险事件中的公众诉求能顺利引发政府关注,并被政府所接受,比如“黄金大米”事件、江门市民反对核燃料项目建设事件等;而在另一些风险事件中,公众诉求则遭到政府反驳,原有风险项目依然继续推进,比如公众反对中国化工集团并购先正达事件等。从政府回应的层级而言,一些风险事件仅在地方层面得到政府回应,也有一些议题则上升到中央,引发中央政府的重视和回应。从政府回应的话语而言,不同风险议题中,政府使用的话语框架也存在差异,比如江门市民反对核燃料项目建设为代表的风险事件中,政府更多采用基于对风险议题进行专业解释的话语方式,而在昆明PX等风险事件中,政府采取的话语框架则更侧重与公众的情感交流。
为此,本研究将超越已有研究对政府是否回应的二元考察,对政府回应态度、话语和层级的具体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细致分析。在样本选择上,本文选择2012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国内共18起典型风险事件,对社交媒体平台上公众讨论以及政府回应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
第一,风险议题中,政府主要采用了怎样的回应态度?公众诉求表达中的哪些因素会对政府回应态度产生影响?
第二,风险议题中,政府回应主要使用了怎样的话语框架?公众诉求表达中的哪些因素会对政府回应话语框架产生影响?
第三,风险议题中,通常是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进行回应?公众诉求表达中的哪些因素会对政府回应层级产生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政府回应
政府回应性(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是指政府政策制定与公众政策偏好契合的程度(Roberts & Kim, 2011)。在西方语境下,研究者普遍认为民主体制中政府对公众意见具备相当程度的回应性(Stimson, MacKuen & Erikson, 1995)。其中,选举竞争与压力成为推动政府回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政治候选人而言,由于选民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政治命运,因而他们不得不顺应公众意愿来制订政策,以争取多数选民支持,赢得选举胜利(Hobolt & Klemmensen, 2008)。
除此以外,其他宏观和微观影响变量的存在,进一步增加了西方语境下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根据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路径,制度会形塑并制约政治行动者的行为;即使同为民主体制,不同的制度特征,包括选举系统、制度结构、决策流程等方面的差异,都可能影响政府的执行模式以及对公众诉求的回应程度(Hobolt & Klemmemsen, 2005)。此外,利益团体的存在,可能推动公众表达并对政府产生压力,倒逼政府做出政策回应(Lax & Phillips, 2009)。而媒介体系的特征也可能对政府回应性产生影响,具备更大规模报纸发行量的国家,往往呈现出更高程度的政府回应性(Besley & Burgess, 2001)。
(二)中国语境下的政府回应与风险抗争
相比于西方研究对选举压力在促成政府回应中关键作用的强调,中国经验表明,选举竞争和压力并不是引发政府回应的主要来源(Su & Meng, 2016)。具体而言,影响中国政府回应的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参与主体差异。已有研究表明,诉求主体的身份差异和人口统计学特征,都可能对政府回应产生影响。Su和Meng (2016)发现,在地方层面,本地居民的诉求将更有可能引发政府关注和回应。而从社会身份的角度来看,对于政府官员,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而言,媒体工作者要比其他社会身份的公众更具影响力;对媒体工作者诉求相对迅速的回应,往往是出于官员的升迁压力和个人政绩考量(Distelhorst & Hou, 2017)。此外,政策企业家的存在,将有助于连接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推动民间舆论和诉求上升为政府关注的议题,进而促成政府回应和政策变迁(赵静,薛澜,2017)。
第二,议题领域差异。从议题所属的领域而言,复杂性低的议题,如城市建设、社会治安等议题较容易获得政府回应;而涉及政府部门多、利益主体复杂、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成本和协调工作的议题,则较少获得回应(Su & Meng, 2016)。特别是在环境保护议题中,议题往往涉及不同政府职能部门和诸多社会主体而呈现出比其他政策议题更为错综复杂的特征,加之处理周期长、难以短期见效,因而一直以来就呈现出较低程度的政府回应性(孟天广,李锋,2015)。除了复杂性以外,议题可见度也是影响政府回应性的因素之一。在环境议题中,由于空气污染议题的可见度相对高于水污染,因而政府会更为积极回应公众与空气污染相关的政策诉求(Tang, Chen & Wu, 2018)。
第三,公众表达的话语框架和策略。已有研究表明,集体行动中的公众诉求表达通常会采用情感化策略和法理化策略两种方式(郭小安,2017;管兵,2013;郑雯,黄荣贵,桂勇,2015)。其中,情感化策略往往以情绪动员为主要特征,这在社会抗争中常常体现为诉诸悲情的情感动员框架(杨国斌,2009),如通过运用“弱者框架”凸显自身利益受损的处境等(黄荣贵,郑雯,桂勇,2015)。有时,一些行动者也会采取“表演式抗争”这种更为戏剧化的形态,通过蕴含愤怒和焦虑情绪的表演行为来传递诉求(刘涛,2016)。事实上,政府也已经认识到情感因素对线上行为的重要影响,并对互联网上较为负面和激进的情绪进行管理,而对爱国等较为正面的情绪进行倡导(Yang, 2017)。而法理策略则更多体现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O’Brien & Li, 2007:1-9)的特征,由行动者们利用相关法律和可能的政治机会开展抗争行动(管兵,2013)。
而从话语框架的使用而言,公众在诉求表达中采用的话语框架与表达方式,会影响表达的效果和政府回应的方式(孟天广,李锋,2015)。研究者(Huang & Sun, 2016)通过对中国一起反核运动中公众线上话语的分析,发现公众倾向采用个人化的反对框架,而非以行动动员和协作为核心的话语框架。已有研究表明,出于社会稳定和政绩考虑,诉诸集体行动的话语框架,将会推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产生更高程度的回应性(Chen, Pan & Xu, 2016)。这与中国政府一贯以来的舆情治理策略紧密相关,政府对公众线上言论的关注中,相比于批评政府的言论,与集体行动相关的话语更有可能引发紧张的反应(King, Pan & Roberts, 2013)。此外,公众如果使用与工作、居住地等相关的集体认同表述,而非个体化话语框架,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府回应性(李锋,孟天广,2016)。
总体而言,探讨中国语境下政府回应的研究仍较匮乏。已有研究将政府回应性的概念引入中国语境,并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影响中国政府回应性的因素。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首先,已有研究对于政府回应性缺乏严格的操作化定义。由于概念测量上的困难,对中国政府回应性的研究,并未根据政府回应的经典定义,严格测量政府政策与公众意愿的契合程度;而是通过测量政府是否对公众诉求进行回复(如Su & Meng, 2016),或政府是否愿意对公众诉求进行回应(如Meng, Pan & Yang, 2017),来间接衡量政府回应性。
其次,在对作为因变量的政府回应进行测量和分析时,已有研究大多将政府回应分为回应和不回应两种形式,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自变量与政府回应的关联。对政府回应的二元划分方法,固然能回答政府是否回应的问题,但对于政府如何回应的问题,特别是哪些变量将影响政府回应的方式这一问题,已有研究缺乏充分的解释力。
再次,对于中国政府回应性的实证研究,大多聚焦于地方层面,探讨地方政府的回应性,而对中央政府回应性则缺乏相应的研究。本文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回应性都纳入研究中,探讨不同层级政府回应的运作逻辑。
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择
本研究选择2012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国内18起风险事件进行分析。对风险事件的选择,参考以上时间段内《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每年发布的《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分析报告》,人民网、腾讯网、《民主与法制》等媒体每年盘点的十大社会事件/十大环保事件,以及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定期发布的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从中选择与风险议题紧密相关的事件进行分析(表1 表1见本期第19页)。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是基于布尔代数和集合论思想,整合传统量化和质化研究方法,试图解释复杂社会现象发生“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所以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法,主要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方面,该方法适用于解释成因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发生规律(Ragin, 2014:13-16),因而它也适合用于分析政府回应这一社会现象,因为政府、公众、专家、NGO在内的多个社会主体,以及政治体制、社会信任、国家—社会关系等多重社会制度因素都会对这一社会现象产生影响(Meng,Pan & Yang,2017)。另一方面,本研究选取了18个案例作为研究样本,也较为契合QCA对样本量的要求。因为一般认为QCA更适用于样本量为10—60的小样本研究(Katz,Vom Hau & Mahoney,2005)。
具体而言,定性比较分析包括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其中,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并不十分常用(Pappas & Woodside,2021),而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只能将变量处理为0和1,更适用于能清晰进行二元划分的研究对象,因而本研究主要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该方法能将变量赋值为介于0和1之间的多个数值,适合没有明确的二元对立类目的变量,如本研究中的诉求主体、诉求框架等,也能更好地避免赋值过程中的信息损失(Ragin, 2009)。
本文的数据分析借助软件fs / QCA 3.0完成。
(三)研究变量与分析类目
总体而言,本研究对所有变量的赋值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的六值赋值方案,即变量赋值可涵盖1, 0.8, 0.6, 0.4, 0.2, 0这六个数值。数值设定采用直接校准法,即研究者参考现有理论或基于样本数据频率分布,为每个变量分配基于0和1之间的数值(Douglas et al., 2020)。其中,1代表对应条件发生,0代表对应条件不发生,其他情况则取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数值。当然,部分变量由于细分类目有限,编码取值不完全涵盖这六种数值。
本研究的因变量(结果变量)为政府回应。根据政府回应的经典定义,我们将该变量操作化为:政府以发布公告或出台政策的形式,对公众诉求作出答复的行为。
为了测量因变量,即政府回应,我们对特定风险事件发生后政府出台的政策、公告和新闻发布会文本进行内容分析,以充分了解政府对该事件的态度和决策。这些相关政策文本,主要来自风险事件发生地的政府官方网站、官方微博账号,以及媒体对政府就相应事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文字、视频报道或现场实录。对政府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政府的话语框架及其政策偏好,因而被已有研究证明是能有效呈现政府回应性的方法(Hofferbert & Budge, 1992)。
具体而言,我们将从以下几个维度考察政府回应:
(1)政府回应的态度,包括接受、反驳和协商三种,编码为1(接受)、0(反驳)和0.6(协商)。其中,接受/反驳是指政府完全采纳/完全拒绝公众诉求,协商是指政府面临公众质疑后对原有政策进行了一定调整,但也并未全盘接受公众诉求。
(2)政府回应的框架。已有研究将中国语境下政府回应公众诉求时所采用的话语方式分为描述话语、共情话语、规则话语和混合话语四种(常多粉,孟天广,2021)。其中,描述话语侧重对公众诉求进行事实层面、程式化的回应,共情话语主要表达对公众的理解、信任和重视,规则话语主要基于具体法律法规或政策文件进行回应。本文在该划分方式的基础上,通过对本文所分析案例中政府回应文本的预览和总结,并结合风险事件的特殊性,最终得出三种政府回应框架,包括:“科学解释”框架,即政府运用专业知识和科学原理对公众诉求进行答复;“政治权威”框架,即政府表达运用自身权威捍卫公众利益的决心,以及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对公众诉求进行积极落实、干预或解决;“情感互动”框架,即政府对于公众诉求中传递的情感表达充分的理解与共情。这三类框架的划分,主要来源于我们对18个案例中政府回应文本的预览和总结。由于fsQCA方法可以根据样本频率分布对变量赋值进行直接校准(Douglas et al., 2020),因此本研究根据各个话语框架的占比,将占比最大的政治权威话语编码为1,将占比第二的科学解释框架编码为0.6,将占比第三的情感互动框架编码为0。
(3)政府回应的层级,包括中央和地方两种,编码为1(中央)和0(地方)。在编码中,本研究根据每个案例中回应公众诉求的最高政府层级进行编码。换言之,如果某案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回应了公众诉求,则仅编码为1。
为了测量自变量,即公众的政策诉求表达,我们对社会化媒体上的公众政策讨论进行内容分析。相比于大规模的受众调查,对特定政策议题中公众舆论的直接测量,将会提供更为准确的方式,来评估公众舆论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联(Norrander, 2000)。具体而言,我们以每个风险事件名称为关键词,选取该事件发生高峰期前后共计一个月的时间,在新浪微博上进行搜索。在所得结果中,我们选择转发数量前100的微博进行内容分析。以转发量为标准进行样本选择,主要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量较高的文本获得了更多的公众注意力,也较能代表大多数公众在讨论特定议题时的关注点和聚焦点;此外,由于微博内容本身的质量是影响用户是否转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Yan & Huang, 2014),因此转发量较高的微博内容也能较为清晰、准确地呈现与特定议题相关的诉求或态度。本研究最终分析样本数总计1800条。
本研究的自变量(解释条件)包括:
(1)诉求表达的话语主体。主要是指在公众进行政策诉求表达的过程中是否有关键社会主体的介入,包括专家/科技工作者、NGO、媒体人和网络博主等。其中,根据参与者的专业化程度由高到低,公众诉求表达中有专家/科技工作者介入被编码为1,有NGO介入被编码为0.6,获得媒体工作者或网络博主支持被编码为0.4,如果除了普通公众没有以上这些关键社会主体介入,就编码为0。之所以按照参与者专业化程度由高到低进行编码,主要因为本文所研究的议题多为具备高度专业性和科学性的风险议题。与一般社会性议题不同的是,在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在内的“知识复杂性”程度更高的政策问题中,政府对专业观点的依赖程度更强,更具专业性的话语主体影响政策变迁的可能性也会更大(朱旭峰,2011)。
(2)议题类别。Slovic等(转引自Winterfeldt & Edwards, 1984)分别以公众对风险的恐慌程度和公众对风险的陌生程度为横纵坐标,将风险议题分为四类:1.Ⅰ类风险,公众高度陌生、高度恐慌类风险议题。这类议题往往存在较大的技术争议,可能造成灾难性和毁灭性后果,也可能面临价值伦理方面的质疑(Winterfeldt & Edwards, 1984),代表议题为核电、转基因、化工(如PX)等。这类风险议题也是最容易引发公众争议和风险事件的领域。2.Ⅱ类风险,公众陌生程度高、恐慌程度低的风险议题。这类风险议题以公共健康领域的风险议题最为典型(Winterfeldt & Edwards, 1984),包括抗生素、阿司匹林、疫苗等议题。3.Ⅲ类风险,公众陌生程度低、恐慌程度低,典型议题包括以“煤改气”为代表的能源利用类议题。4.Ⅳ类风险,公众恐慌程度较高,但对风险事实较为了解。与Ⅰ类风险类似的是,这类风险议题也具备相对较高的危害性和破坏性,但是其在技术上基本不存在争议。其中的典型议题包括各类工业污染、空气污染或垃圾焚烧议题。风险议题的分类如图1所示。
本研究根据这四类风险在18个案例中的占比,根据样本频率分布对变量赋值进行直接校准,将占比最大(55.56%)的Ⅰ类风险编码为1,将占比第二(27.78%)的Ⅳ类风险编码为0.6,将占比第三(11.11%)的Ⅱ类风险编码为0.2,将占比最小的Ⅲ类风险(5.56%)编码为0。
(3)诉求框架与抗争策略。已有研究将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抗争策略分为情感和理性两大类诉求方式(郭小安,2017;管兵,2013)。本文以该分类方式为基础,结合风险事件自身的特殊性,将风险事件的抗争策略分为法理策略和情绪动员策略两种形式。其中,法理策略是指公众主要采用理性抗辩或论争的形式进行自身诉求表达,其依据通常为与特定风险议题相关的国家法律政策或技术性材料,具体包括“技术风险”框架和“程序正义”框架;情绪动员策略是指公众主要通过诉诸愤怒、悲情等情感进行诉求表达,对应的话语框架包括“道德伦理”框架和“地域保护”框架。在每个风险议题被抽样的100条微博中,如果有超过25%的微博使用了特定框架,则视为使用特定框架,并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每个议题中的公众诉求框架可以包括不止一种。每个框架的具体含义见(表2 表2见本期第22页)所示。
四、政府回应的机制
本研究首先通过计算一致性来考察单个解释变量是否能构成因变量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如果必要一致性指标取值大于0.9,则可被视为必要条件(Skaaning, 2011;Ragin, 2009:44-68)。
结果表明,对于政府回应态度、回应层级和回应话语框架这三个因变量而言,话语主体、议题类别、技术风险、程序正义、道德伦理、地域保护等六个解释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这表明,单一变量不足以成为解释因变量的必要条件,因而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解释变量的组合是否有助于解释因变量。
(一)政府回应态度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揭示了六个因果路径,用于呈现哪些解释条件的组合能够影响政府回应态度(表3 表3见本期第23页)。这六个因果路径的总覆盖率为0.7121,表明有71.21%的案例能够被这六条因果路径共同解释。
首先,最重要的因果路径为F1-1,该路径的原生覆盖率为0.3333,唯一覆盖率为0.2121,表明该路径能够解释33.33%的案例,且有21.21%的案例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F1-1表明,对于Ⅰ类风险而言,采用程序正义框架,且不采用道德伦理和地域保护框架,更有可能获得更为积极的政府回应态度。
事实上,对于包括核电、垃圾焚烧等议题在内的Ⅰ类风险项目而言,审批、建造和运行等环节均需要进行较为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涉及选址、环境影响、事故预防等,并在各个环节进行公众参与机制设计,以保障公众知情权。①但在一些议题中,风险审批、信息公开、环境影响评价等程序中常常存在漏洞,这成为公众表达政策诉求的突破口。公众往往聚焦于地方政府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的诸多漏洞,借助“程序正义”话语框架来表达他们希望取消特定项目的政策诉求。比如,在2012年江西彭泽核电项目建设中,项目在环评、民意调研、前期审批程序中的诸多问题,被公众在政策诉求中表达出来。面对公众对项目建设程序的质疑,加之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影响,地方政府宣布彭泽核电项目暂停建设。迄今为止,彭泽核电项目在环境评估等方面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该项目目前依然处于停滞状态。
其次,因果路径F1-2表明,对于Ⅱ类风险、Ⅲ类风险而言,使用技术风险和道德伦理框架,不使用程序正义和地域保护框架,将更有可能引发政府较为积极的回应态度。Ⅱ类风险、Ⅲ类风险均为公众恐慌程度较低的议题,如公众健康、能源利用等,风险危害程度相比于核电等Ⅰ类风险议题较低,在环评、审批等环节上的复杂性程度也相对较低。因此,公众只有在诉诸议题的风险危害的基础上,叠加伦理话语,才有可能引发较为有力的政府回应。
再次,在几乎所有因果路径中,技术风险话语作用均不明显。这表明,对于宽泛意义上的风险议题而言,如果仅使用技术风险话语,不利于公众获取政府较为积极的回应态度。在以“公众反对中国化工集团并购先正达”为代表的议题中,政府往往在信息公开、风险决策等环节不存在严重的过失或漏洞,公众仅仅将诉求点置于风险议题本身对公众健康和社会环境造成的危害,并不容易引发政府对原有决策的改变。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风险议题本身就面临很大的社会争议和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对于一些议题而言,即使是专家内部也存在争议,因而政府不会仅仅基于公众对特定风险议题危害性的表述就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另一方面,与专家基于风险发生概率进行风险评估不同,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则更多基于风险的灾难性后果(贝克,2004:30),所以公众对风险议题的表达更多体现出情绪化的特征,也极易对风险议题的实际危害性产生误解和偏见。因而政府一般不会针对仅使用技术风险话语的公众诉求进行积极回应。
(二)政府回应层级
针对政府回应层级,fs/QCA 3.0 共揭示了四种因果路径(表4 表4见本期第24页)。这四种因果路径的总覆盖率为0.5333,表明有53.33%的案例能被这四种因果路径所解释。
其中,F2-1和F2-2可以概括为:techrisk*~projustice*~region*(Idendity*issue+ ~Idendity*~issue*ethics),这意味着对于Ⅰ类风险而言,有重要公众人物参与、采用技术风险话语、不采用程序正义和地域保护框架,更有可能获得中央政府的回应。
首先,中央政府相对更倾向于回应技术风险话语,特别是在Ⅰ类风险中,当这种技术风险话语得到重要公众人物(特别是专家或专业领域NGO)的支持时,更容易获得中央政府的重视。
一方面,对专家角色的重视一定程度上与中国语境下风险议题的政府决策机制有关。在以核电议题为代表的风险议题中,政策制定过程的核心参与者为政治家、技术官僚和专家委员会,具备技术理性和专业判断的专家在决策过程中具有投票权(陈玲,薛澜,2011)。因此,在Ⅰ类风险等本身具备较强不确定性和技术争议的风险议题中,专家意见在相当程度上受到高层政府部门的重视和积极回应。
另一方面,NGO也呈现出在推动Ⅰ类风险中政府回应的重要作用。比如,“黄金大米”事件最早就是由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揭露,推动政府对该研究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批并回应公众诉求。而在昆明安宁石化项目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也是在“自然之友”、昆明“绿色流域”等环保组织的倡导下最终公布。②
其次,程序正义和地域保护话语很大程度上不会获得中央政府回应。在风险议题中,以程序正义和地域保护为核心话语策略的公众诉求,恰恰最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回应和重视。使用程序正义框架的公众诉求话语,大多聚焦于地方政府在推动风险项目过程中存在的程序问题,包括项目审批、环境风险评估、信息公开等环节。为此,公众往往会主张自身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并以此为出发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诉求表达,甚至发起集体行动。为了防止可能的社会稳定风险,并防止地方政府程序审批等方面的问题被举报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往往会暂停已有的风险项目,在事态平息后从长计议。这与早先(Chen, Pan & Xu, 2016) 关于中国政府回应动因的研究较为一致,即集体行动的威胁和诉诸上级政府的压力,会对地方政府的回应行为产生影响。
(三)政府回应的话语框架
fs/QCA 3.0 共揭示了五种因果路径(表5 表5见本期第25页),用于解释哪些条件组合能够影响政府回应的话语框架。这五种因果路径的总覆盖率为0.666667,即有66.67%的案例能被这些因果路径所解释。总体而言,这些因果路径表明,公众使用特定话语,并不会导致政府使用类似话语框架进行回应。
首先,对于Ⅰ类风险而言,如果公众诉求话语使用技术风险话语,会导致政府使用政府权威话语而非科学解释话语进行回应。这一因果路径,凸显了公众诉求话语与政府回应话语的错位,也体现了政府在回应公众诉求时的核心逻辑。在政府回应中,政治权威框架主要强调政府自身的责任感和对公众诉求的重视,并强调政府会运用相关制度、整合相关机构对公众诉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回应。
其次,对于Ⅱ类风险、Ⅲ类风险而言,公众诉求话语必须将技术风险话语与道德伦理话语同时使用,才会导致政府使用政府权威话语进行回应。比如,在以煤改气事件为代表的能源利用议题中,由于该类事件基本不涉及技术争议,公众政策诉求主要集中在冬季正常取暖、保证基本的温饱权利。因而政府对公众诉求的回应也相对多地使用了“政治权威”框架,强调政府对公众基本权利的保护与尊重,提出“以确保温暖过冬为第一原则”。③
再次,如果公众使用程序正义话语,不使用技术风险、道德伦理和地域保护话语,将会导致政府使用政府权威话语进行回应。即对于任何类型的风险议题而言,只要公众以程序正义为主要诉求框架,均会引发政府较为有力的回应态度。
以上因果路径表明,政府权威框架成为政府回应中使用最多的框架,即使公众在诉求表达中并未采用明确诉诸政府权威的话语策略。特别是当公众表达对特定风险议题危害性的担忧,或是特定风险议题存在程序问题时,政府更有可能采用该框架进行回应。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2012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国内共18起典型风险争议为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研究方法,探讨风险议题中影响政府回应的关键因素和具体机制。研究发现,在回应态度上,公众仅使用技术风险话语,无法获得政府积极回应;社会恐慌程度和复杂性较高的风险议题叠加程序正义话语更有可能获得积极回应。在回应层级上,当技术风险话语得到重要公众人物支持时,更容易获得中央政府回应;程序正义和地域保护话语则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回应。在话语框架上,政府权威框架成为政府回应中使用最多的框架,但公众诉求话语和政府回应话语存在明显错位。
已有关于政府回应的相关研究,大多将政府回应行为分为回应/不回应两种形式进行考察(孟天广,李锋,2015;Tang, Chen & Wu, 2018)。而本文则从政府回应框架、回应态度、回应层级三个角度考察政府回应行为,试图超越政府是否回应这一二元划分方式,呈现政府回应行为的复杂性,挖掘影响政府回应态度和话语方式的机制。
除了探讨政府回应的条件和具体机制,本研究更希望呈现政府回应机制的制度和政策意涵,特别是政府回应机制对现有政治系统韧性的强化。这具体体现在:
首先,政府回应中对公众程序正义话语框架的重视,呈现出国家政治运作的自我调适。在政府回应的逻辑上,Ⅰ类风险中使用程序正义话语进行表述的公众诉求给予更为积极的回应态度,并对所有议题中采用程序正义话语框架的诉求均采用政府权威框架进行有力回应。一般而言,诉诸程序正义的公众诉求会揭露地方政府项目建设、环评、审批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希望借此获得中央政府的干预。政府选择对这些议题进行回应,一方面是出于地方政府官员对自身政绩的担忧和社会稳定考量,因为集体行动的压力和诉诸上级政府的担忧,会推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更具回应性(Chen, Pan & Xu, 2016),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央政府在处理程序失当的风险项目时体现的自我调适机制。
其次,政府对生存伦理话语的及时回应,体现出政府通过选择性回应的方式实现对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消解。本研究发现,在Ⅱ类风险、Ⅲ类风险等较低风险危害的议题中,公众使用技术风险叠加道德伦理话语,将会获得政府更为积极的回应态度。正如Giddens (1991:209-220)所言,在后传统社会,生活政治已经逐渐取代解放政治的主流地位,成为一种新型政治。解放政治更多致力于消除剥削和不平等,而生活政治关乎生活方式的选择,并具有伦理或价值尺度(Giddens,2003:117-125)。在生活政治成为主流的当下,一旦公众以此为由头组织集体行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并动摇政府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以煤改气为代表的Ⅱ类风险、Ⅲ类风险中,公众希望表达的正是对自身生活方式选择以及对包括正常取暖在内的温饱权利的呼吁。
再次,政府回应中对专家所表述的技术观点的吸纳,体现出政府决策中借助专业力量对决策水平的提升。在风险议题中,虽然公众所表达的技术观点并未获得政府过多回应,但是专家观点获得了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重视。
此外,本研究发现,在公众诉求框架的选择上,风险议题与传统民生议题呈现出明显差异。关于中国集体行动的已有研究指出,行动者通常会采用“情绪动员策略”和“法理策略”两种方式(管兵,2013)。然而在风险事件中,公众诉求中采用的话语框架更多具备法理策略的特征,通过诉诸议题的技术风险、项目审批过程中的程序正义问题,或是公众知情权和选择权等问题,从技术和法理层面进行政策诉求表达。这也呈现出风险议题与拆迁、征地等传统民生议题的差异。在后者的政策诉求表达中,情感性的话语表达则更为常见。
但即使是在技术元素和理性色彩如此浓重的风险议题中,我国政府回应仍以政治权威为主要话语策略。本研究表明,在风险议题中,科学解释话语并未成为政府回应所采用的主流话语,且仅以技术风险为主要诉求话语的公众诉求也难以获得政府回应。这一方面表明,现有政治运作中政府的权威性仍然在风险议题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公众风险感知和表达往往更多基于经验判断而非概率事实,且常常带有情绪化的倾向,仅通过技术理性的话语难以与公众实现有效沟通(贝克,2004:30),因而政府也相对较少使用科学解释话语进行回应。■
注释:
①相关文件如《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参见http://jjjcz.mee.gov.cn/djfg/gjflfg/fl/200210/t20021001_444291.htmlhttp://www.mee.gov.cn/gkml/hbb/bgsh/200910/W020210318530106352703.pdf。
②参见:吴珊:《PX中的NGO 博弈“公众参与”》,凯迪社区,2013年7月31日,https://club.kdnet.net/dispbbs.asp?id=93963
50&boardid=89。
③摘自国家发改委2017年12月18日所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部分内容,参见:壹条能:《发改委:居民供暖宜电则电、宜煤则煤、宜气则气、宜油则油》,搜狐财经,2017年12月18日,http://www.sohu.com/a/211312371_678455。
参考文献:
常多粉,孟天广(2021)。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环境治理中网络问政的政府回应话语模式。《社会发展研究》,8(03)44-62+243。
陈玲,薛澜(2011)。“执行软约束”是如何产生的?——揭开中国核电谜局背后的政策博弈。《国际经济评论》,(2),147-160+6。
管兵(2013)。愤怒与理性:模式切换与维权结果。《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63-170。
郭小安(2017)。社会抗争中理性与情感的选择方式及动员效果——基于十年120起事件的统计分析(2007-2016)。《国际新闻界》,39(11)107-125。
黄荣贵,郑雯,桂勇(2015)。多渠道强干预、框架与抗争结果——对40个拆迁抗争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社会学研究》,30(05)90-114+244。
李锋,孟天广(2016)。策略性政治互动:网民政治话语运用与政府回应模式。《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69(05)119-129。
刘涛(2016)。情感抗争:表演式抗争的情感框架与道德语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69(05)102-113。
孟天广,李锋(2015)。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性。《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0(03),17-29。
乌尔里希·贝克(2004)。《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杨国斌(2009)。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9),39-66。
赵静,薛澜(2017)。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转型一类案例的分析。《政治学研究》,(3),42-51+126。
郑雯、黄荣贵、桂勇(2015)。中国抗争行动的“文化框架”——基于拆迁抗争案例的类型学分析(2003-2012)。《新闻与传播研究》,22(02),5026+126。
朱旭峰(2011)。中国社会政策变迁中的专家参与模式研究。《社会学研究》,(2),1-27+243。
BesleyT.& BurgessR. (2001). Political agency,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nd the role of the media.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4-6)629-640.
BursteinP. (2003).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public policy: A review and an agenda.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56(1)29-40.
ChenJ.PanJ.& Xu, Y. (2016).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60(2)383-400.
Distelhorst, G.& HouY. (2017). Constituency service under nondemocratic rule: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9(3)1024-1040.
Douglas, E. J.Shepherd, D. A.& Prentice, C. (2020). Us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 a finer-grained understanding of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35(1)105970.
HassidJ.& BrassJ. N. (2011). Scandals, Mediaand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in China and Kenya. In APSA 2011 Annual Meeting Paper.
HoboltS. B.& Klemmemsen, R. (2005). Responsive government? Public opinion and government policy preferences in Britain and Denmark. Political Studies53(2)379-402.
HoboltS. B.& Klemmensen, R. (2008).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41(3)309-337.
HofferbertR. I.& BudgeI. (1992). The party mandate and the Westminster model: Election programmes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in Britain1948-85.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2(2)151-182.
Huang, R.& SunX. (2016). Dynamic preference revelation and expression of personal frames: how Weibo is used in an anti-nuclear protest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9(4)385-402.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 (2003).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Taylor & Francis.
KatzA.Vom HauM.& MahoneyJ. (2005). Explaining the great reversal in Spanish America: Fuzzy-set analysis versus regression analysi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33(4)539-573.
KingG.PanJ.& RobertsM. E.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326-343.
Lax, J. R.& Phillips, J. H. (2009). Gay rights in the states: 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 responsiven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3(3)367-386.
MengT.PanJ.& Yang, P. (2017). Conditional receptivity 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50(4)399-433.
Norrander, B. (2000). The multi-layered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capital punishment implementation in the American stat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53(4)771-793.
O’Brien, K. J. & Li, L. J. (2007).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ppasI. O.& Woodside, A. G. (2021).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practice in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marke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58102310.
Ragin, C. C. (2014).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Ragin, C. C. (2009).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Social Forces, 88(4)1936-1938.
Roberts, A.& KimB. Y. (2011). Policy responsivenes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Public preferences and economic reform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41(4)819-839.
SkaaningS. E. (2011). Assessing the robustness of crisp-set and fuzzy-set QCA result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40(2)391-408.
Stimson, J. A.MacKuenM. B.& EriksonR. S. (1995). Dynamic represent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3)543-565.
SuZ.& Meng, T. (2016). Selective responsiveness: Online public demands and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in authoritaria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952-67.
TangX.Chen, W.& Wu, T. (2018). Do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respond to public opinion on the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5(2)266.
Winterfeldt, D. V.& EdwardsW. (1984). Patterns of conflict about risky technologies. Risk Analysis, 4(1)55-68.
Yan, W.& HuangJ. (2014). Microblogging reposting mechanism: an information adoption perspective. Tsinghu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5)531-542.
YangG. (2017). Demobilizing the Emotions of Online Activism in China: A Civilizing Proc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11945-1965.
王宇琦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曾繁旭(通讯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