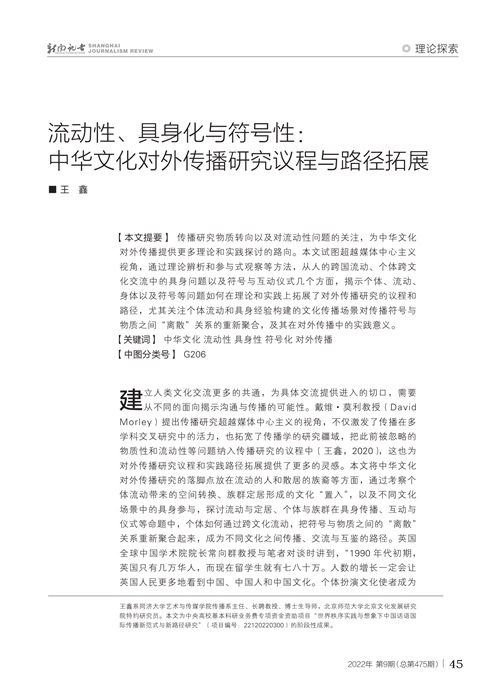流动性、具身化与符号性: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议程与路径拓展
■王鑫
【本文提要】传播研究物质转向以及对流动性问题的关注,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更多理论和实践探讨的路向。本文试图超越媒体中心主义视角,通过理论辨析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从人的跨国流动、个体跨文化交流中的具身问题以及符号与互动仪式几个方面,揭示个体、流动、身体以及符号等问题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拓展了对外传播研究的议程和路径,尤其关注个体流动和具身经验构建的文化传播场景对传播符号与物质之间“离散”关系的重新聚合,及其在对外传播中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华文化 流动性 具身性 符号化 对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建立人类文化交流更多的共通,为具体交流提供进入的切口,需要从不同的面向揭示沟通与传播的可能性。戴维·莫利教授(David Morley)提出传播研究超越媒体中心主义的视角,不仅激发了传播在多学科交叉研究中的活力,也拓宽了传播学的研究疆域,把此前被忽略的物质性和流动性等问题纳入传播研究的议程中(王鑫,2020),这也为对外传播研究议程和实践路径拓展提供了更多的灵感。本文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研究的落脚点放在流动的人和散居的族裔等方面,通过考察个体流动带来的空间转换、族群定居形成的文化“置入”,以及不同文化场景中的具身参与,探讨流动与定居、个体与族群在具身传播、互动与仪式等命题中,个体如何通过跨文化流动,把符号与物质之间的“离散”关系重新聚合起来,成为不同文化之间传播、交流与互鉴的路径。英国全球中国学术院院长常向群教授与笔者对谈时讲到,“1990年代初期,英国只有几万华人,而现在留学生就有七八十万。人数的增长一定会让英国人民更多地看到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个体扮演文化使者成为‘行走的文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尽管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不过在较长的时间里,尤其是在大众媒体和新媒体成为主导的媒体语境之下,媒体以及文本研究成为关注的重点,而人的流动成为被忽略的“低音”。相关议题的文章也只零星可见,其中《超越表征: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视野》(李鲤,2020)侧重具身传播对于跨文化传播的新视野和理论意义,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但是并没有将流动与具身问题进行对照考察;研究流动与传播的文章不少,但是从跨国个体流动与族裔散居视角关注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议题并未有文章清晰涉及。传播研究的物质转向、以媒体为中心的对外传播的现实以及在对外传播中对“流动的人”的忽略,包括作者在参与式观察中对诸多问题的发现,成为本研究的缘起。本文也希望能从流动性和物质性(具身)出发,超越媒体中心主义的视角,通过参与式观察和理论辨析,考察个体在跨国流动中如何通过身体在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交流,以及个体与族群在他者文化中的交互,拓展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议程、范式和实践路径,增进了对外传播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并彰显了民间个体流动对文化传播的意义。此外,“中华文化”是一个宏大命题和叙事,但其本身也并非一个空洞的能指,中华文化既可以通过经典的文本和器物显现,也附着在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上。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一趣一味中,个体的生命感和生活经验与中华文化以及中国的国家修辞关联在一起。从人的流动中携带着文化基因的“入乡”,可弥补宏大传播叙事的不足,并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文化的交流、碰撞、融通和共在。
一、流动与定居: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主体的空间转换与在地性体验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悠久历史与人的流动、货物的流动和金钱的流动分不开。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是经由西安(古代长安)、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丝绸之路”,无论是出于当时军事、外交、贸易的需要,还是个人的商业往来,都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早期的通路。“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最庞大的商贸网络,它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与中亚的诸多贸易重镇联系在一起,还间接连通了东亚和西南亚的帝国中心。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井然有序的贸易活动,还有军事要塞和政府税收机构,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汉代(前206—200年)”(罗伯特·N.斯宾格勒三世,2021:11)。古代中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以及承载这些物质的技术和审美,被西方世界认知甚至视为时尚追逐,大量货币也因此流入古老的东方。当然,古代文化传播之路也并非都是这么温和与友好,武力屠戮、血腥征伐交织在不同文明的碰撞和联系之中。在前现代阶段,人类文明的交流与文化传播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强大的国家意志、军事行动和对财富渴望衍生的各种冒险。但是历史的大叙事总是遮蔽个体生命在这条路上扮演的角色以及遭受的磨难,无数充满冒险精神的个体,无论是基于财富还是个人抱负,或者帝国雄心,都将各自的文化向世界不同文化区域传播和扩散,棉花、茶叶、咖啡豆、葡萄酒、辣椒和火药,甚至是病毒,将人类的块状文明,通过流动的路径和线索,逐渐连为一体。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流动性相伴,文化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伴随着人类生生不息的流动,这也是人类文明不断扩散的历史。《大流动》的作者纳扬·昌达认为,大流动历史中这四类人,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武士,不仅将“产品、思想和技术传播到域外,而且拉近了不同地域间的关系,并借此建构和深化了‘全球一体化意识’”。他还认为,“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激进的社会活动家、移民和游客一直持续推动着数千年前就开始的一体化进程”(纳扬·昌达,2021:V-VI)。
被技术改变的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方式,使文化的传播呈现新的状貌。特别是随着航空等交通设施的发达,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流动作为一个古老的问题,在新的技术媒介和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流动现实中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理论命题。本世纪初,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提出的“新流动范式”推动了流动性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当今世界有许多不同的社会实践,每一种都涉及特定的人、物体、技术和创作的流动组合,比如一些学生探险旅行、互惠生和其他年轻人的“海外经历”,或者在特定散居地内一些重要地方的旅行和迁移,例如海外华人等(Urry, J.& M.Grieco, 2012:5)。这对本文关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流动性议题以及物质与符号之间接合关系的研究有较大启发。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受到交通技术的推动,流动成为个人、机构和国家三者交织在一起的行为,跨国流动者以及在地华人,携带自身文化的基因进入他者文化中,并在日常生活中经历“转文化”(transculture)的过程,正是跨文化传播要关注的部分。
文明和文化的传播涉及人、物和思想等多个方面。关涉到人,本文认为可分为“中心传播者”和“边缘传播者”两个部分,前者以国家精英或者在全球不同领域的功勋卓著者为主,具有“典范”意义;而“边缘传播者”,是指普通人在跨文化流动中,通过自身携带的文化信息所产生的交流与传播实践。这些边缘传播者,通常是以私人和个体方式进入另一种文化中,是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生命与生命的相互感受和认知,因此,更易建立文化连接上的“共通感”;相反,“中心传播者”往往带有宏大叙事的色彩,形成“国”与“人”、“高”和“低”、“上”与“下”的层级关系以及无形的权力宰制,这使文化的流动和文明的沟通产生了某种不平等感。因此,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问题上,“中心传播者”往往少了“边缘传播者”的日常性和生活化,边缘传播者更易被接纳。2019年,中国留学生数量达到70.35万,成为全球留学生数量第一的国家,根据Frost和Sullivan的报告分析,2022年留学人数预计将达到83.05万人。留学生群体成为跨国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无意间成为文化传播的巨大的“普通传播者”。如何在庞大的留学生群体从中国走向世界的空间转换中释放其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和潜力,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连接,这一点尤为重要。厄里就非常看重学生以及其他年轻人的海外学习和探索性的流动,认为这是重要的“成人礼”,也是他描述流动性的五个重要面向之一。尽管留学生出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承担的是个人的未来期许和价值实现,并无对中华文化传播的明确任务,也未必有主观上的自觉,但是作为“行走的符号”或者“流动的文化载体”,客观上已成为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连接者与沟通者。笔者在观察中发现,青年学生在本土普遍接受过较好的教育,对民族文化符号和样态也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在交流和互动中,也能有较好的展示和传递。作为“普通传播者”,留学生也会在文化碰撞中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身份感和文化的主体性,提高对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的认知。因此,在考察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问题上,要特别重视“普通传播者”的空间转换,挖掘“普通传播者”文化携带性的特质,充分利用“普通传播者”做好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这些留学生,往返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带着中华文化的烙印——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从人际交往到审美偏好等,也带着文明塑造的认知和判断。当个体进入他者文化时,一方面遭遇“文化震惊”,另一方面也把民族文化中的某些精神旨趣带到其他文化中。当然,跨国流动的个体,不仅包括留学生,还包括大量的跨国旅行者。由于交通的便利以及中国家庭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往被视为遥不可及的“出国”,现已成为很多人的日常生活。这些跨国流动,无意间建立了个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修辞连接,个体形象成为民族国家形象的关联表述,个人与家国的关联性往往在他者文化中体现得更为鲜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如果能超越“媒体中心主义”的局限,将视角转向流动的人(留学生、跨国工作者、游客、移民等)和其他流动的物(汽车、服装、食物等),不仅能从理论上拓展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议程,也能在实践上拓宽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和载体。
流动的个体成为文化“行走的符号”,海外华人作为异国“定居者”,都是他者文化对本土文化的直接嵌入的表现,这也是研究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不能忽略的部分。海外华人族群基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相似,大多居住在相近或者相邻的街区,比如唐人街或中国城。这些中国风格的商铺、食品以及日常生活习惯,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部落格”。海外华人并没有被赋予中华文化传播的职责,但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印刻在个体的生命经验中,被携带、呈现与传播。笔者曾访谈多位定居英国的华人,其中包括学者、医生、作家、公司职员、中餐馆老板等,他们普遍表达出在他者文化中更在意保护和传承自己文化的内容,对中国传统节日、语言、习俗等格外看重。比如华商在伦敦举行的春节文化大游行,作为伦敦最著名的游行之一,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伦敦市民观看,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他者文化中的一次展演。一些中餐馆或者中国超市中大量的中国美食、手工制品以及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的小商品,形成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汇入和接合。此外,华人社群通过商会、读书会以及各种运动集会,通过文化的方式聚合和加强“想象的共同体”的建设,客观上也将民族传统文化在异国他乡进行展示和传播。这些华人社群正是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散居的族裔,虽然他们与本民族主群构成空间疏离,但疏离使散居的族裔具有对民族文化的独特感情,既担心遗忘也恐惧文化上的“失联”,因此会形成更深层次的连接,也借此应对当地民族主群对散居族裔的歧视和偏见。海外华人面对不同的文化,其自身也需要不断地学习、接纳和调整,找到连接人类相处中共通的部分,才能在文化碰撞与适应中更好地“入乡”:既要了解规则和程序,也要懂得风俗和人情,并能找到自我与他者文化中有效连接的部分。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海外华人的语言优势和在地经验,以及对属地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帮助中华文化找到更好的“入乡策略”,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具身传播与场景构建:对外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感性实践
流动,特别是跨国流动,不仅是文化传播的基础,也创设了跨文化传播生动的现场和语境。身体在场的感受和体验与文字、书籍、影像制造的想象空间不同,并且难以被替代。新闻报道框架以及各种“把关人”对信息进行的过滤,容易形成文化理解和认知上的“偏见”,也不断制造交流和沟通上的藩篱,而流动以及人际之间的沟通可以即时发生,在某种程度上祛除了文化传播和交流之“魅”。互联网和手机真的能够代替身体在场的交流和仪式吗?兰德尔·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在《互动仪式链》中曾这样提问。身体作为重要的媒介之一,参与到日常交流和跨文化传播中,这也拓宽了跨文化交流的新视野。身体和场景等概念也被应用到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尤其是在考察传播效果方面,更倾向于场景搭建中参与者的体验和感受,注重跨文化沟通的语境和情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对外传播中出现的困惑和困境。
对外传播中的身体问题,离不开前面对流动性的讨论。没有流动作为前提,对外传播中的具身研究也只有理论层面的意义,难以落实到实际的交往中。随着全球大规模的人群流动,特别是留学生、国际游客以及华人移民的增加,使对外传播中的具身问题研究,成为值得关注的重点。流动使人不断被“抛入”陌生的文化中,需要不断去建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单波认为,这三种表述重点呈现了文化互动的“我”、文化交叉的“我”和文化融合的“我”,回应全球化时代“我”的生存图景:全球流动不断使人们体验普遍交往,遇见陌生人,经受文化差异与文化压力,进入文化适应,感受文化连接与分割的心理考验(单波,2020)。可见,个体在文化互动、交叉和融合中,“身体”被卷入到巨大的跨文化交往中,个体不再通过媒介信息构建的想象场景交流,而是进入具体的场景之中通过体验、思考、反馈和互动实现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强调身体在场是传播物质转向的一个研究维度。以往的传播研究是以媒体为中心的范式,“专注于信息传播的符号、制度和技术维度的中介形式,把传播等同于象征性或修辞性的交流”(王鑫,2020),这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传播研究的范围和议程。关注传播中的感性实践与身体交流,以及交流场景的建构,关注传播中的人的生命性和情感能量,是对传播原初之意的复返和再现,“communication的原始意义在中文里就是‘沟通’,在拉丁文与community同个字源,都是communis,即是要建立‘共同性’(make common)——也就是透过社区内人们面对面的沟通,彼此分享‘信息’和‘情感’,以建立深刻的‘了解’”(李金铨,2019:70)。以媒体为中心传播,传受主体分别居于信息的两端,遵循传播主体—信道(信息载体)—接收主体的这一线性传播模式,两者之间并不一定以身体在场的方式交流,因此也难以提供柯林斯所言的情感能量以及情感连带。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 2001)描述路过某地时如何要求各种感官,如“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动感,即所谓的本体感受”,甚至“味觉”参与其中。声音包含“从鸟鸣到交通和喇叭的声音”,触摸的感觉则可能“包括蒿草刷过身体时的触感,过往车辆的湿滑路面溅起了浪花和在拥挤的地方陌生人之间互相推搡”(转引自彼得·阿迪,2020:160),这种充分调动生命各种感官获取并传递的信息,建立了与场景之间的深度关联,并与他人之间建立情感共通与连接,也会形成“瞬间共有的实在”,特别是身体在场提供了“高度的互为主体性,跟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同时也为每个参加者带来了情感能量,使他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做出他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事情”(林聚任,2012:V)。这显示出身体在场赋予传播的情感性以及强大的身份感,情感能量促进主体间沟通意愿以及沟通信息的清晰和准确。面对面的交谈中,交谈的双方因为身处同一场所,因此能通过身体在场相互影响,并且能够分享共同的情绪和体验,这对于跨文化传播而言尤其重要,补足了大众媒体或者新媒体传播隐去的身体感受和现场能量会聚。此外,身体作为信源传递同样的信息,比文字和其他媒介载体要更丰富和全面,巴恩伦德(Barnlund)认为:
人类交往中的许多甚至绝大多数关键的意义是由触摸、眼神、声音的细微差别、手势、说话或无言时的面部表情传达出来的。从认出对方的那一刻起到相互告别,人们利用所有的感官观察对方:注意话语的停顿、语调的变化,留意着装、仪表,观察眼神、面部表情,乃至注意其遣词造句、话语背景等。每一个信号的协调与否关系到能否理解对方转瞬即逝的心情或其持久不变的品性。通过对动作、声音和语言等信号的理解,人们做出不同的决定:是争论还是同意,是报之以微笑还是面红耳赤,是放松还是抵触,是继续还是中断谈话(转引自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埃德温·R·麦克丹尼尔,2015:183)。
身体在场所传递的信息,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而且是仪式的建立,并且非语言交流“是人从出生到生命结束这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信号系统”。若要想填满意义空白之处,不仅需要了解身体语言与文化的相应性,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文化确定了非语言行为在何时进行、如何进行和产生什么后果的表现规则”(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埃德温·R·麦克丹尼尔,2015:183)。马塞尼斯(Marseilles)认为:
全世界的人们都拥有同样的基本情感。但是什么事情会引起某一情感,人们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表达这种情感,以及人们如何界定情感等都因文化而异。因此,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日常生活千差万别不仅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行为方面,而且体现在人们如何用情感来充实生活方面(转引自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埃德温·R·麦克丹尼尔,2015:187)。
身体在场对于情感的传递以及情感能量的流动,是人和人基于共通感建立沟通的前提,并且要将身体在场与文化语境充分结合起来,才能使非自然语言的表达具备超越民族、种族、肤色以及语言等诸多障碍的条件,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不仅是交流情境的构建,也是感性实践。欧文·戈夫曼也认为,个体的主动表达,指语言符号或者双方皆知的传达信息的语言替代物,这是传统意义上和狭义上的交流;个体留给别人印象涉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行动,别人认为这些行动就是发出者(交流者)的象征,这种行动理应发出有因,而不是为了以这种方式发出信息。这说明身体在场至少完成两种功能:第一是传统意义上的交流;第二是更广泛意义的行动。由于全球化带来人口的大量流动,文化传播不只是依赖少数的个体或者媒体,身体在场的跨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带去了感性的交流实践,同时也使非自然语言交流的优势得以显现,也恢复了传播中身体在场带来的经验的回归与张扬。
身体在场建立交流的仪式感和场景。身体在场是典型的文化之间的互动,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碰撞、表达、交流。跨文化交流是人与人的相遇、人与事的相遇以及人与物的相遇。不同文化中的主体的相遇就是激发、唤起、激活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也会产生冲突、矛盾和困境,但是人与人之间仍旧存在着共情的部分,这里的共情,指的是“一种能力,它使我们理解别人的想法或感受,并用恰当的情绪来回应这些想法和感受”(西蒙·巴伦-科恩,2018:14),并且存在“共情回路”的生理基础与感官的共通。此外,情绪的表达与情感能量传递“液态”的方式可以自由地流动和蔓延,因此会超越非身体在场带来的固化和想象,在情境中将个体意义凸显出来,而不是洗刷个体的过程。“一个人只能通过交流治疗交流的问题,只有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才能把陌生的变为熟悉的,进而把自己从自我异化中解救出来。在与他人的互动之中,个体可以体悟到巴赫金所说的‘视野剩余’,即每个自我在观察自己时都会存在一个盲区,就如同我们不可能看见自己的脸和后背一样,所谓独特的个体视野即每个个体都拥有的‘视野剩余’”(单波,2020)。可见,身体在场的交流,提供了超越于文本和影像的丰富信息,特别是在情感与情绪的流动中,释放更多的交流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于“视野剩余”带来的局限。虽然数字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即时视频,使在场交流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必要,但是具身交往仍旧是重要的。对外传播与交流,身体在场的重要性体现在:第一,情感能量的传递使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更容易得到理解和尊重;第二,超越自然语言表达的局限,从而实现更加丰富的信息传递;第三,构建跨文化交流的仪式感,体现对他者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尊重;第四,纠正对外传播中认知偏向,形成对于跨文化交流的正向理解。对外传播的基本理论问题只有转入人的日常交往实践之中,才有可能找到可行的路径(单波,2011)。跨文化交流从以媒体为中心的范式转向“具身传播”物质维度,意在发掘对外传播中身体在场的重要意义。身体在场实现了跨文化交流中的时空合一,交流是一个线性过程,体现为时间性;身体在场,又体现为空间性,因此,身体在场实现了对外传播的时空合一。无论这个场景是两个人或者多人的,都提供了情感流动的空间,比如人们会通过握手、拥抱、微笑去感知和体验与对方的交流,实现了沟通者双方在自然语言以及身体语言的多维交流,以及场景对沟通效果实现的有效性。笔者曾与伦敦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交流,得知她的小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并且会突然发病而住院进行各种治疗。这种共情,使笔者在交流的时候,会通过握手和拥抱表示鼓励和安慰。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多维信息体,包含仪容仪表、服饰着装以及举止言谈等,这不仅是个体文化修养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彰显。比如,身着汉服走在伦敦街头的女生,通过服装来表明身份以及审美,阿拉伯民族的长袍和头巾、拉美和非洲的脏辫等,都是各自民族文化的体现。因此,身体在场仿佛一个民族国家“行走的文化”的现场演示,并实现与其他民族的对话和交流。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流动的个体或者行走的“文化”,并不是以文化传播为目的,而是作为文化的载体,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入另一种文化中,在文化震惊、适应、融合中,通过对话、杂音,甚至默音的方式实现了跨文化的交流。
三、个体与族群:对外传播中的互动仪式与族裔象征符号
全球时代人类的流动促进了文化之间的交流,身体在场释放了跨文化交流的情感能量。人类被更加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因为“人类的生存要依赖于人们考虑形形色色的共同行动的能力”(转引自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埃德温·R·麦克丹尼尔,2015:293)。前面提到的流动与定居,实际上主要体现为个体的流动与族群的定居。个体多表现为频繁与短期的流动,族群则体现为稳定与长期的定居。在全球流动中,不同文化中的个体不断相遇和交流,这种交流可能是瞬时的、偶然的,也可能是阶段性的和必要的。旅行者在途中遇到的其他文化中的个体,这种交流通常就是偶然的;但是对于留学生或者长期驻外工作者,这种交流在时间上可能是中短期的,在实践层面也是必要的。在对外传播中,涉及两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一个是互动仪式,另一个是族裔散居的象征
符号。
关于对外传播中的互动仪式,实际上是自我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与他者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之间在情境中发生的交流与互动。这个互动仪式,既包含了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也包含了柯林斯的互动仪式中的情境与情感能量的传递。戈夫曼认为,“我使用‘仪式’这个术语,因为这类活动,尽管是非正式和世俗的,代表了一种个体必须守卫和设计的其行动的符号意义的方式,同时直接呈现对其有特别价值的对象”(柯林斯,2012:38)。戈夫曼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仪式类型,其实并不是神圣物的敬畏,而是各种较小的体现各种各样私人关系的小型会话。这些对话中的热情、友好、平淡、熟悉、陌生等都在“打招呼”这种仪式中体现出来,“他们暗示了一个人对待他人的态度,即有不同程度的友谊(即团结)、亲密性或尊敬。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明白,它们在细微之处表现了,在完全的陌生人、暂时功利性联系的人、担当某些组织角色的人之间、彼此知道名字并互相作为个体而不是作为角色认识的人……他们之间的差别”(柯林斯,2012:39)。这是基于个体交往的微语境,戈夫曼与柯林斯一样,都强调了仪式发生的共同在场性,并从身体在场转向对于共同际遇的关注。柯林斯甚至认为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互动仪式链,并且认为“互动仪式最富激情的瞬间不仅是群体的高峰,也是个人生活的高峰。对这些事件我们刻骨铭心,它们赋予我们个人生命的意义”(柯林斯,2012:73),个体随着情境的变化,行为、感受和想法也会发生转变。个体从本土文化向其他文化流动,必然会带来情境的变化,这会使其根据自身的经验、认知和情境进行有效的沟通以确保自身在他者文化中的安全和确定性。同时,会对他者文化进行充分学习和了解,寻求能够建立互动仪式的行为和方式。笔者在曼城学习期间,为欧洲大陆以及英国的朋友带去“中国风”的各种小礼物,并根据音译,将他们的名字写在书签上,这些异国友人惊异自己的名字以不同文字符号呈现的样子。礼物与心意、友善与惊异让来自不同文化之间的人迅速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并在后续过程中,友好、善意、真诚的情感能量在互动双方之间流动,使交流的双方体会、感受并做出反馈,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认识到仪式操作的简单以及意义的不简单。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看起来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行动,实际上,却在个体与他者文化的互动中悄然实现,“实事求是、生动、客观地呈现我们的语言、文化和生活,坦诚相见会更容易打开自身,找到与外界沟通的契合点。不同文化地域中的人,都有自己对于真善美的理解,虽然有些微的差异,但是仍旧具有普遍的共通点,找到双方共通的‘理、事、情’至关重要”(王鑫,李锷,2021)。以个体为代表的跨文化流动,必然与对外传播进行关联。在互动仪式中,身体在场聚集了大量的情感能量,并且交流双方“乐意捕捉共享的关注点和情感连带”,会形成较为顺畅的交流,甚至可以弥补言语上的欠缺。个体之间的相互交流,弱化了民族与国家的宏大叙事,在一个微小的情境里,以生活的方式实现了跨文化的交流。在互动中,个人的喜好和偏爱,包括对于他者文化的熟悉和了解,进行日常化的交流或者学术讨论,避免与国家的宏大叙事构成更多的关联。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个体意识是集体意识的一部分。个体具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情感特征是社会化因素内在化的过程,中国人习惯在“关系”和“归属”中安放自身的位置,在跨文化交流中呈现出含蓄、宽容、内敛、温和、真诚甚至是隐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对人伦理想和人际关系的形塑。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交流和互动仪式,提供了对外传播的重要场景,其中“尊重”成为互动仪式必须具备的心态。受制于具体环境、刻板印象以及社会心态等因素,个体往往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歧视、偏见、冷漠以及不尊重。不过,放松、诚恳、开放和友好交流的心态,能够给予互动的双方鼓励、肯定,并向对方构成积极的反馈和回应,这些是需要个体不断学习和实践的。身体不在场,很难在情境中通过情感流动提升交流的品质和效果。提出对外传播中互动仪式的问题,着眼于流动的个体客观上必然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通过建立良好的沟通情境,个体在跨文化交流中容易获得在他者文化中的良好存在感和认可度。虽然个体在跨国流动过程中,会遭遇不同程度的文化震惊,但是身体的在场又会形成情感和能量聚集,通过分享、关注和体验,保持对他人和情境的关注,准确地捕捉他人的情绪状态,在交流中做到移情,接受差异,在必要的妥协中寻求通融与合作等。如何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宏大叙事消弭于个体间日常交流的微叙事,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与互动仪式相关的,就是族裔象征符号。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华文化对于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构成了重要的影响。随着人类航海事业以及其他交通工具的发展,大量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远到马六甲海峡,或是到非洲和北美地区淘金和拓荒,成为早期输出的海外移民。比如新西兰学者宫宏宇在《意想不到的使者》一文中(2013),专门讨论了早期的广东淘金客在新西兰的音乐传播,并认为相比于早期的传教士、商人和旅行者,广东淘金客从社会底层开始的音乐传播,是重要的传播途径之一。第一代移民往往伴随着艰辛的求生历程以及社会底层的生活。后来的移民或者是高学历、具有专业技术的移民,或者是投资移民,当然也包括跨国婚姻的移民等,相对第一代移民来讲,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等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欧美一些相对较大的城市都有华人商业和生活居住区——唐人街或者中国城。这些散居的族裔,通过日常生活、族群内部沟通以及中华文化传统习俗的展示,一方面对于散居族裔有情感和文化的连接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不同文化中渗入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和气质。前面提到的英国华埠商会在伦敦举办的春节庆典活动,它以特拉法加广场和唐人街以及伦敦西区为主要活动地点,每年有几万人参加和观看,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故事、人物、图腾符号以及传统艺术活动得到展示。不仅华人参与其中,来自不同肤色、人种和文化的人们也参与其中。除了游行,期间还有手工摊位、中国美食展览以及传统的中国舞蹈、音乐和武术表演等。这种大型的“流动的文化”展演,文化的物质形态、图腾符号以及族群身份等,都得以显现。海外华人族裔进行的文化展演活动,是出于对“文化之根”的记忆和留存,在文化对比和参照中,体会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分野,如何在他者文化中保留、呈现、发扬自我文化,也是海外族裔寻求文化身份和自我认同的路径。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西方人通过宗教连接彼此,中国人通过世俗的生活伦常建构个体与族群的关系,个体的价值需要在集体和族群中确立,因此,海外族裔的文化聚力和发散性相对较强。海外族裔与留学生及驻外工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早期移民与故乡之间构成一种“遥远的亲切”,甚至存在一种“分离的焦虑”。散居的族裔定居在异国他乡,由于本土文化的同化,移民的二代,甚至三代对祖辈文化的保留越来越少,出于对自我“根”文化的衰落和消逝担忧的朴素情感,他们聘请中文教师给移民的二代、三代讲授中文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并不对中华文化传播的宏大叙事负责,而是出自一种自我文化认同与保存,或是对自我过往的珍视。文化像一条河,流淌在人类的土地之上,形态各异,也会受到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导致阻塞,但是人类的大地是共通的,河流总有交汇的可能。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不是单一的“对外输出”,“输出”的话语总是让他者文化存有“入侵”的警惕,“文化和价值观的交流,可以提出概念和口号,但是对于实际操作的人来讲,要把宣传的概念和口号弱化到无,踏踏实实地做事情,用‘事实’来体现‘理念’”(王鑫,李锷,2021)。通过不断流动的跨国者以及散居的族裔在不同文化空间传播互观,通过物的形式和互动仪式与他者建立关系,更容易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鉴。
结语
当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在文本和媒介研究方面成果颇多,也是研究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高音”之处。随着传播研究对流动性、物质性、具身性等问题的关注,对外传播的研究也需要传播议程的拓展和扩散,超越以媒体为中心的对外传播的单一思路,形成更立体和多向度的传播路径和方法。笔者通过自身的海外生活经历,以及参与式观察和访谈,认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有几个问题是必须要关注的:第一,关注流动性,并将其作为考察传播主体的重要维度,有利于扩充“谁”在传播的问题;第二,考察对外传播的具身问题,关注身体构成的信息场域和情境,有利于观察对外传播沟通效果;第三,对外传播的仪式和符号问题,通过对个体互动与族裔呈现的研究,有利于激发传播主体的活力,也使中华文化的多样性面向能够被更好地展现。以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是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进一步实践的可能性和路径,沿着这个思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会有更加务实和丰富的拓展。■
参考文献:
彼得·阿迪(2020)。《移动性》(戴特奇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宫宏宇(2013)。意想不到的使者——广东淘金客与中国音乐在新西兰的早期传播。《星海音乐学院学报》,(04),17-21。
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埃德温·R·麦克丹尼尔(2015)。《跨文化传播》(闵惠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兰德尔·柯林斯(2012)。《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金铨(2019)。《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林聚任(2012)。《互动仪式链:译者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罗伯特·N. 斯宾格勒三世(2021)。《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起源》(陈阳译,唐莉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纳扬·昌达(2021)。《大流动》(顾捷昕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单波(2020)。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域。《跨文化传播研究》,(01),1-30。
单波(2011)。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1),103-113。
宋美杰(2020)。非表征理论与媒介研究:新视域与新想象。《新闻与传播研究》,(3),86-97。
王鑫(2020)。物质性与流动性:对戴维·莫利传播研究议程扩展与范式转换的考察。《国际新闻界》。(09),159-176。
王鑫,李锷(2021)。孔子学院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五重意象”——与德国纽伦堡 - 埃尔兰根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锷的对谈。《辽宁大学学报》,(03),112-117。
西蒙·巴伦 - 科恩(2018)。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高天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许倬云(2018)。《中国文化的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
GriecoM.Urry, J. (2011). Mobilities: 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port and societ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UrryJ. (2012). Mobilities: 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port and Society (M. Grieco, Ed.). London Routledge.
王鑫系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系主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世界秩序实践与想象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新范式与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12022030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