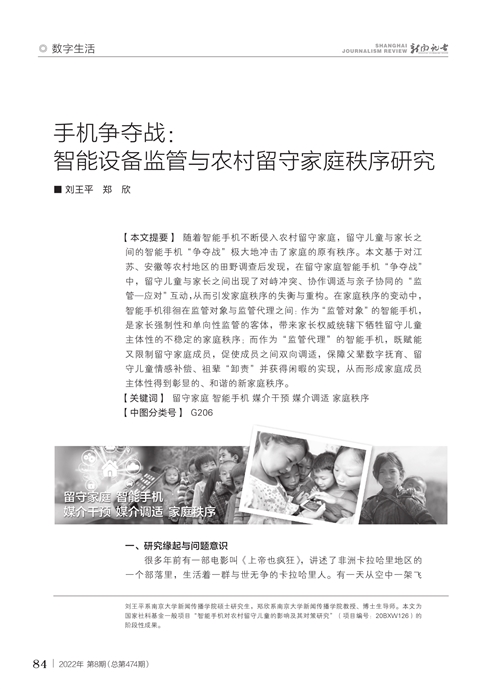手机争夺战:智能设备监管与农村留守家庭秩序研究
■刘王平 郑欣
【本文提要】随着智能手机不断侵入农村留守家庭,留守儿童与家长之间的智能手机“争夺战”极大地冲击了家庭的原有秩序。本文基于对江苏、安徽等农村地区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在留守家庭智能手机“争夺战”中,留守儿童与家长之间出现了对峙冲突、协作调适与亲子协同的“监管—应对”互动,从而引发家庭秩序的失衡与重构。在家庭秩序的变动中,智能手机徘徊在监管对象与监管代理之间:作为“监管对象”的智能手机,是家长强制性和单向性监管的客体,带来家长权威统辖下牺牲留守儿童主体性的不稳定的家庭秩序;而作为“监管代理”的智能手机,既赋能又限制留守家庭成员,促使成员之间双向调适,保障父辈数字抚育、留守儿童情感补偿、祖辈“卸责”并获得闲暇的实现,从而形成家庭成员主体性得到彰显的、和谐的新家庭秩序。
【关键词】留守家庭 智能手机 媒介干预 媒介调适 家庭秩序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上帝也疯狂》,讲述了非洲卡拉哈里地区的一个部落里,生活着一群与世无争的卡拉哈里人。有一天从空中一架飞机上坠落的一个可乐瓶打乱了他们一成不变的日子。人们惊叹可乐瓶子的独特造型和诸多用途,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他们的礼物。可瓶子只有一个,稀缺的资源引起部落里的诸多冲突。一个本来知足而快乐的部落因为一个来自现代文明的可乐瓶发生了改变。
尽管智能手机如今已经谈不上是什么稀缺资源,但自从其进入乡村社会特别是留守家庭,它就成为娱乐、亲情沟通、教育以及社会交往的工具,帮助留守儿童实现数字隔离的弥合与边缘重生(王佑美,2013),并且提供数字情感补偿(王清华,郑欣,2021),减缓亲代缺位的孤独感(向敏,毕重曾,2017),更为外出打工的农村妇女实现母职提供“遥控”的可能(曹晋,2009),进而促进亲子沟通,巩固家庭稳定(胡春阳,毛迪秋,2019)。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智能手机更是成为留守家庭为配合学校、社会开展线上教学不得不为孩子配备的必要学习工具。可见智能手机进入留守家庭所带来的便利与美好,与上述同为现代文明的可乐瓶当初坠落在卡拉哈里人部落里并无二致。
然而,进入留守家庭的手机并非只带来媒介技术发展的最大红利与积极功能,如《上帝也疯狂》中的可乐瓶一样,也给留守家庭带来各种麻烦和冲突。如同一般家庭对于孩子使用智能设备的担忧,缺乏父母监管的留守儿童,更是容易迷失在网络漩涡中(谢安琪,2019),引发较为突出的个体问题,诸如成绩下降、性格发育不全、社会化困境等。同时,智能手机也导致留守儿童的人际交往面临另类封闭的可能,出现“社交茧房”的问题(郑欣,高倩,2021)。对此,很多家长都会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孩子使用智能设备。但笔者在江苏、安徽等地调研时发现,留守儿童面对家长监管,不会简单顺从,往往会消极抗拒,甚至采取反制举措进行“报复”。智能手机“抢夺战”经常在留守家庭中上演,而“折戟”的大多是家长一方。留守家庭出现“外出爸妈管不到,爷爷奶奶管不了”的双重焦虑景象。
田野调查中暴露出的手机监管失落与留守家庭乱序的问题,促使笔者思考:(1)家长如何监管留守儿童的手机使用?留守儿童如何应对家长的监管?家长与留守儿童之间关于手机的监管与应对出现了怎样的争夺战?(2)伴随手机争夺战的发展,农村留守家庭关系及其稳定性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家庭秩序是否会受到影响?(3)最后,留守家庭如何更好地实现媒介监管抑或媒介干预,从而维持家庭秩序?
对此,国内外不少学者曾经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讨论“父母媒介干预”问题,他们认为父母应该落实媒体督导的角色,对媒介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伴随着技术变迁,干预举措有所改进与突破。Bybee等人(1982)在关于电视使用研究中提出了父母媒介干预(parental mediation)的三个面向,即限制型干预(包括限制收看内容和时间)、积极型干预(对电视内容的互动与谈论)和共同使用(共同接触电视)。在网络与手机出现以后,Livingstone和Helsper(2008)、Snock等人(2013)将限制型干预扩展为安装过滤或监控软件的技术型限制,以及关注社交的互动型限制。而Nikken和Jansz(2006)更是提出监督(supervision)这一新的维度,即父母在场才被允许使用媒介。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越来越依赖ICT(信息通信技术)进行社交、工作和生活,这也引发家长较过去更为频繁地使用前述方式干预孩子的媒介使用(Beatrice et al., 2022)。
上述父母媒介干预因自身的积极/消极两面性带来正负效用并存的局面。从儿童个体层面的认知、态度和行动实践来看,积极干预促使孩子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家长督导的角色,采取配合家长的媒介使用,从而能够解决孩子“数字成瘾”、“网络风险”等问题;另一方面,父母媒介干预能有效抑制孩子遭受网络欺凌的风险和影响(Lin & Steven, 2021;朱秀凌,2021),有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与成长发展。但以限制为主的干预模式则会使孩子对父母产生不满、怀疑乃至抗拒的心理。反映在行动层面,监控型父母媒介干预不能降低部分孩子的手机游戏成瘾程度(黎藜等,2021)。而过度限制的举措引起孩子“出招抵制”(陈青文,2019),甚至出现脱离亲职控制的“媒介叛逆行为”(赖泽栋,2018)。同时,亲子关系也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积极干预与共同使用能促进亲子深度沟通,提高家庭联系水平,增强家庭关系亲密度(Padilla et al., 2012)。但父母严格的举措未能收到监管成效,反而将孩子越推越远,出现了较为消极的“家庭凝聚”(张煜麟,2015)。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前述研究更多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考察媒介干预及其效果,对家庭干预互动和家庭关系的讨论只是做了显微镜下某个切面的观察,而且如“蜻蜓点水”般“浅尝辄止”。众所周知,深度嵌入家庭中的手机,引发的干预互动并不会发生一次就即刻结束,而是循环往复,乃至深入发展。静态观察的方法无法更好地阐释网络治理和媒介干预中家长与儿童之间的动态传播互动,缺乏对变动的家庭关系、家庭秩序的全面关照。再者,Bazalgette和Buckingham(1995:3)认为许多研究“看上去低估了儿童理解媒介、将媒介内容与自己经验相连接的方式的多样性”。这或许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积极干预/限制干预并非对儿童产生“皮下注射论”所认为的一成不变乃至强制性的影响。如若不注重分析儿童主体的具体应对,在某种程度上容易遮蔽儿童作为社会主体的能动性,限制媒介干预研究的客观性与丰富性。
进一步而言,绝大多数农村儿童由祖辈隔代抚育,现有父母媒介干预研究却未能关涉农村家庭抚养模式的现状。留守家庭的特殊结构、关系形态,容易导致家庭成员对手机需求的有增无减与留守儿童手机使用失范之间的张力,从而导致留守家庭中家长干预—留守儿童应对的“手机争夺战”。这场微型战争可能是长期、动态、多元、复杂的,也是亟需被解释与解决的。发端、盛行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媒介干预研究,为配合核心家庭的情境突出强调父母角色。而在重视血缘关系的中国乡村,“祖孙三代”组成的主干家庭仍是农村家庭结构的主体。与核心家庭的父母媒介干预相比,主干家庭的亲代与祖代家长不仅采取差异化的干预举措,两者之间还会出现复杂的协调互动。故在中国农村特殊情境下,“父母媒介干预”概念应当扩展至(外)祖父母—父母联结的“媒介使用干预”,即父辈与祖辈联结的家长共同体相互协调,为规范、监控、控制儿童使用媒体采用的各种干预策略。
因此,本文将“媒介使用干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希望从农村留守家庭关系和互动入手,分析家长干预留守儿童媒介使用所处的重要关系场域和传播场景,进而考察留守家庭的智能手机使用与干预互动产生的手机争夺战,揭示智能手机在媒介使用干预中的具体角色,剖析干预—应对中家庭秩序的演变,从而理解农村留守儿童智能手机沉迷动因及家庭监管的痛点,更为重要的是为解决互联网时代农村留守儿童危机提供思路。
本文分析的调研资料主要依托南京大学“心相连·云相伴”留守儿童主题公益支教团队于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期间进行的田野调查。出于不干扰学校正常教学工作和留守儿童学习生活的目的,团队成员分别在江苏南京某民族小学、安徽杨山初中、花桥初中教授新媒体教育与学习方法等课程。通过公益支教,团队获取了学生、家长以及学校校长、教师的信任。8位三年级、9位四年级、10位五年级、10位六年级以及8位初一年级,共计45位农村留守儿童接受了团队的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座谈。团队成员细致访问了留守儿童的手机使用情况、面对媒介使用干预时产生的态度与应对举措;并通过实地家访与线上访问并举的形式,同受访留守儿童的祖辈和外出父母进行了不低于一小时的深度访谈,了解家长干预媒介使用的动机、举措和对干预结果的态度。①在这些案例中,农村父母均外出务工在半年以上,孩子全部被交由祖辈抚育。被访谈的留守儿童均使用智能设备在一年以上(其中仅一位留守儿童智能设备为平板电脑,后文讨论的设备均为智能手机),用于实现其自身亲情维系、娱乐、学习以及同侪社交的需求。绝大多数受访留守儿童每日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长超过一小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手机依赖。为保护受访者,文中出现的地名、人名均为化名。
二、代际协同:留守家庭媒介使用干预类型分析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大多数外出父母为方便与留守老人、孩子取得联系,并配合疫情防控期间的线上教学的需要,纷纷给家庭和孩子配备了智能手机。众所周知,在手机进入城市家庭以后,不少家长产生了孩子新媒体成瘾的忧虑。留守儿童滥用或泛用智能手机,免不了会对其身体、心理、社交产生一定的危害,这同样也引起了在外务工家长的忧虑。
家长对留守儿童的手机使用出现了担忧与焦虑交织的复杂局面。担忧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成绩下降、身体损害以及社交危害。同时由于父母外出、祖辈文化素质的局限,家长产生了“管不到、难管”与“看不懂、不好管”的监管焦虑。具体而言:
首先,大多数家长最为突出的担忧是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下降。从学校的记录来看,南京某民族小学和安徽花桥初中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在疫情爆发以后大幅下滑。成绩下降的原因主要包括:留守儿童在疫情期间养成的坏习惯,例如上课开小差、玩手机等,以及不动脑思考题目,使用“猿辅导”答题App抄答案。另外,部分家长担心手机损害身体。“熬夜玩手机,周末躺一天”是留守儿童的智能手机使用常态,这样不良的使用习惯不仅给儿童视力,也给身体造成严重损害。最后,高年级学生的家长对网络社交风险的担忧较多。在调研中,很多六年级以上尤其是初中的留守儿童十分喜爱使用社交软件,例如安徽花桥初中的娜娜,加入了很多陌生QQ群。外出务工父亲看到后说,群里“语言不堪入目,什么情情爱爱的,都不是她这个年龄的”。而类似的案例在不少高年级的留守儿童身上经常发生,引起了家长的重视和担心。而在调研中,低年级留守儿童并不擅长也不专注于使用社交软件进行交友。
家长不仅担忧手机危害,也产生了监管焦虑。祖辈不高的文化素质和家庭权威导致其产生“看不懂、不好管”的焦虑。调研中只有两个家庭的老人读过高中,但对手机仍“摸不着头脑”。此外,农村留守家庭中祖辈的家庭权威逐渐过渡至父辈,大多数情况下祖辈无法通过权威来迫使孙辈“就范”,也更达不成较佳的媒介使用干预成效。父辈大多外出务工以支持家庭需要,出现了“管不到、难管”的焦虑。一方面距离造成父辈很难知晓孩子的生活细节,出现代际信息的不对称。另一方面距离也容易冲散家庭权威和情感联结,导致父辈监管的失效。例如南京某民族小学六年级的紫萱与父母存在相当程度的疏离,外出的紫萱爸爸直言,“搞不清她心里想什么?”紫萱也对爸爸的管教并不信服,“总是听了就忘”。
与城市不同,留守家庭中家长的担忧则更多从现实考虑出发,如成绩下降、社交危害等,并没有关注到城市家庭担忧的“暴力等不当内容造成的危害”(陈青文,2019)。这与不同家庭的利益关注点和媒介素养程度相关。农村家庭可能始终有一种“阶层跃迁”观念,但在现有城乡二元区隔背景下,实现阶层跃迁的有效途径是“高考”,故农村家庭在培养下一代上格外注重孩子学习成绩。
第三,农村家长的媒介素养普遍不高,较少能察觉出媒介内容中的暴力危害。一方面,外出父母无法在场监控留守儿童的社交动态;另一方面,祖辈又通过新闻、街巷闲话等渠道强化网络社交风险的感知,于是两代家长产生了不同于城市家庭的媒介干预偏向。总之,留守家庭的家长容易产生种种忧虑,这些忧虑会随着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演绎出不同的代际干预类型,从而出现了不同于其他家庭的“手机争夺战”。
由于个人禀赋的不同,家长在干预智能手机时出现了不同的策略和效果。本文尝试对留守家庭的父辈和祖辈的禀赋进行划分,梳理出多种类型的代际干预。按照父辈外出距离、责任心、媒介素养、人生遭遇等标准分为亲代积极型干预、消极型干预;按照祖辈身体素质、媒介素养、责任心、娱乐闲暇、家庭权威等标准分为祖代积极型干预、消极型干预。
在田野调查中,本文发现祖辈与父辈不同行动者的干预举措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种代际协同干预类型:专制协作型、有心无力型以及爱而不得型,如图1所示。由于在实际调研中并没有出现祖辈与父辈双双消极干预留守儿童的手机使用,故本文暂不讨论疏忽型代际干预(孤儿等困境儿童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一)专制协作型代际协同干预
“专制协作”是指代际积极行动者采取了有效的团结专制干预,从而实现家庭权威的稳固和媒介使用干预成效的达成。祖辈深知其媒介素养较低,给干预手机带来不小难度,因此在监管中总会寻求父辈的帮助。父辈对孩子进行远程操纵与网络把关,也需要祖辈通信人和代理人的协调和执行。因此,积极的祖父辈的完美配合完成了对孩子使用手机的有效干预。
前文中的紫萱家庭是非常典型的专制协作型代际协同干预案例。线下上学期间,紫萱熬夜上网课补习数学,与奶奶发生争吵。祖辈作为媒介使用干预实施者,出于对网络风险和身体危害的担忧,想阻止紫萱的线上学习行为。但奶奶无法判断在线学习是否合时宜,也不能有效控制孩子上网,于是积极寻求父辈紫庆的帮助,说“你打电话给老师看看网上是什么课,不主要的课就不需要上,搞得晚了耽误休息”。紫庆立即联系班主任后得知学校没有安排网课,于是提出限制紫萱上网行为的严厉要求。奶奶也严格执行紫庆的“指示”,限制孩子的网络学习。就这样,紫萱的主动学习尝试,被祖辈与父辈的协同管制扼杀。类似的专制协作型代际协同干预也发生在南京某民族小学六年级的丹丹的家庭中。
需要说明的是,不少家长常常控制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和内容,甚至如紫萱家长“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抵制媒介使用,也如期末期间家长剥夺丹丹的手机使用权,均是未合理善用媒介的正向功用。家长很少采取积极介入,解读媒介内容以及共同使用等,因而媒介使用干预带有强制性。但强制举措不只会引发家庭争端和亲子嫌隙,也会影响家庭的和谐稳定,我们将在后文中详细讨论。
这里更想揭示协同机制达成的原因:代际家长出于家庭利益一致的考虑,均对孩子有着非常高的期待,于是积极履行养育后代和监管手机的家庭责任。祖辈希望全身心照顾有好的结果,父辈则因为没能给孩子必要的陪伴而感到愧疚,认为自己应该要履行好责任,避免其“学坏”。
此外,祖辈充足的闲暇时间、较好的身体素质、能够肩负起监管留守儿童的重担等因素也影响积极协同的达成。59岁的紫萱奶奶身体很健康,并全职在家;而丹丹奶奶身体也很强健,一丝不苟地照顾孩子的起居与学习。她们都有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耐心,足以成为监管手机的积极行动者。
总之,父辈在匡正和支持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上倾注相当心力,但是由于外出务工没法对孩子生活有着全面和持续监管,只能依靠留守祖辈把关孩子的一切。而祖辈也的确细致地履行好监管责任,扮演好媒介使用干预的代理与通讯角色。祖辈与父辈均在媒介使用干预中扮演积极的行动者,专制控制着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
(二)有心无力型代际协同干预
有心无力型代际协同干预是指在留守家庭中,父母长期在外,缺少对孩子的日常照顾。祖辈则取代父辈,被迫成为“育儿总管”,践行“具身父母”的干预责任(肖索未,2014)。尽管祖辈有心干预媒介使用、培育孩子,但因为缺乏权威且监管艰辛,不仅容易与留守儿童产生冲突,也常常对父辈产生失望与微词。
南京某民族小学五年级的小君与三年级的阿鑫的家庭均属于典型的有心无力型代际协同干预案例。小君父母一年回家一两次,平时也只偶尔打电话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而阿鑫父母离婚后,父亲离家出走,母亲则回湖北老家治疗精神分裂症,两人与阿鑫的联系甚少。于是,祖辈无奈接下养育留守儿童的责任,成为育儿总管。
祖辈凭借对媒介危害的经验认知,采取严格的媒介使用干预。例如小君爷爷要求孩子“周一到周五每天最多玩两个小时”。而阿鑫爷爷在孩子成绩下降以后,便没收了手机。但祖辈的干预很难收到成效,甚至会引发家庭小争端。“小君平时是个听话的孩子,就是挨不得骂”。爷爷不给玩手机,小君便会用吵闹的方式抗议。而阿鑫在手机被收掉以后,虽不至于争吵,但还是会偷摸玩手机。
于是祖辈在“手机争夺战”中将限制干预调整为奖励、姑息的策略。譬如小君爷爷把“玩手机”作为孩子做作业的奖励,阿鑫爷爷则是适当延长孩子的手机使用时间。在祖辈的退让下,大多数留守儿童不仅遵从手机使用的新规范,而且也较好地实现家长对其学习方面的期待。如此便重新树立起祖辈的权威,减少祖孙之间的冲突与对立。
但退让举措还是会带来“数字成瘾”与家庭矛盾的潜在风险。周末沉迷手机的小君,星期一大清早却爬起来补作业。爷爷了解到小君谎称写完作业偷玩手机的小心思后,便在心里留下了孩子不做作业的坏印象。在往后的监管中,爷爷在无法判断孩子是否完成作业时,便限制孩子使用手机。小君对此争辩但得不到爷爷的信任,吵闹也于事无补,便“觉得爷爷不好”。由此,祖孙间的信任危机与矛盾冲突频发。
此外,日常抚育的艰辛以及媒介使用干预的复杂,令祖辈背负较为沉重的负担。父辈的缺席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不尽孝”,比如家庭日常开销仍由祖辈支付,这令不少祖辈失望与抱怨,祖辈与父辈之间的亲密关系产生缝隙。
总之,父辈多外出务工缺乏对孩子的监管照顾,祖辈承担起主要的抚育功能,被迫成为监管手机的积极行动者,父辈则退居补充性地位(魏冬芹,2013)。起初,祖辈囿于文化素质与媒介素养较低的限制,监管举措多以限制为主,遭致儿童的反对与抗争。于是,权威并不高的积极行动者——祖辈面对任性孩子,无奈采用退让策略,虽能收到成效,但反过来也蕴含着媒介使用失范与家庭危机的风险。
(三)爱而不得型代际协同干预
前文所述积极的祖辈行动者并不占多数,不少祖辈因无法承担监管留守儿童的责任,外出父母不得不远程操控,采取广泛多样的限制型干预。但父辈缺乏祖辈的配合,媒介使用干预收效甚微,可能引发父辈对祖辈的抱怨。此种媒介监管被称为爱而不得型代际协同干预。
南京某民族小学六年级的李子非常沉迷手机,其家庭媒介监管是比较典型的爱而不得型代际协同干预。外出的李爸爸十分担心手机对孩子的危害,不仅采取社交干预的策略,如李爸爸提前设定李子社交媒体联系人为熟人,还限制手机游戏数量与内容。但是外出父辈无法随时监督孩子,于是李爸爸将监督与没收手机的任务交给奶奶。结果李子的智能手机“下满游戏”,限制措施运行地非常不顺畅。李爸爸认为奶奶如果认真监管可以达成效果,但“我家母亲好玩,喜欢打麻将,晚上跳广场舞、散步,基本上不在家陪她”。对此,李爸爸计划在孩子上初中后,就接到身边来照顾。
李爸爸属于手机干预的积极行动者,在认识到手机的危害后便采取互动与内容限制的举措。而李奶奶有更多的主体闲暇与娱乐选择,在监管手机时缺乏必要的陪护,未能完成外出父辈委托的任务。这样一方面未能实现媒介使用干预效果,另一方面使得父辈丧失对祖辈的信任,造成家庭亲密关系的裂隙。于是,对于父辈来说,媒介使用干预成了“爱而不得”的举措。
调研中多数家庭均呈现出这种爱而不得型代际协同干预,例如南京某民族小学六年级的露露,其奶奶已经80多岁高龄,无法倾注心力干预媒介;南京某民族小学五年级的小轩,其爷爷生活自理能力差,还爱打麻将,小轩的日常起居全得独立完成。安徽杨山初中的阿琦,其爷爷奶奶每天忙于工作无暇照顾。祖辈因为忙于工作补贴家用、身体素质差或有其他的主体选择,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留守儿童,成为消极行动者,未能与父辈达成亲密一致的媒介使用干预,造成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失范问题。
总之,在农村留守家庭中,因为不同的个人禀赋,代际协同干预的家庭类型有所差异。但生计是“保卫家庭”的首要目标(邢成举,2020),留守儿童的抚育工作常常次之。所以,“爱而不得”或者“有心无力”的监管模式才是农村留守家庭的常态。此外,前述三种类型的代际协同干预都或多或少暴露出强制监管的问题,容易遭致孩子反感,导致手机争夺战“一触即发”,十分影响家庭稳定。当然我们也了解到留守家庭会出现譬如姑息、共同使用等非限制性媒介使用干预,这些干预举措在同留守儿童互动中,形制出各色各样的家庭关系与家庭秩序。
三、失序、重构与平衡:手机争夺中的留守家庭秩序
如今深深嵌入留守家庭的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最为常见的生活媒介。但手机的危害无孔不入,架构了留守家庭成员间监管与应对的复杂互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前述三种家庭在干预与应对的对峙中均面临失序的风险,但家庭成员和手机的持续互动,却又能制造出和谐新秩序。此外,部分案例还展现了理想的平衡秩序,即突出留守家庭手机监管的积极一面。
(一)对峙冲突与家庭失序
前述三种协同干预类型的家庭普遍会采用较为强制的时间限制举措,不少留守家庭还会使用互动限制和监控来检视留守儿童的举动,实现不在场的监管。留守儿童的应对也较为激烈,容易出现比较严重的叛逆行为。由此,家庭中常常上演对峙与冲突的争夺战,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失序的风险。
首先是时间限制型。绝大多数家长直接没收智能手机,或者采取拔网线、断网、藏卡等各种形式限制手机使用时间。其次是针对高年级留守儿童,部分家长会采取互动限制型举措。前述李子爸爸会提前设置孩子社交账号的联系人,紫萱爸爸会查看并分辨孩子的交友情况,防止网络风险。最后是监视。监视是配合着其他设备进行的一种限制举措。南京某民族小学六年级的雨涵的妈妈通过给家里安装摄像头来随时监控孩子的日常作业与生活行动,从而缓解祖辈监管的压力以及弥补祖辈监管的不足。
面对家长的严格限制,不少留守儿童会采取一定的抵抗行为,例如耍赖或发脾气。前述案例中紫萱不喜欢奶奶的监管,与奶奶发生过多次争吵与“冷战”。留守老人粗暴的监管未能有效控制孩子使用智能手机,外出家长的限制措施也会适得其反。当手机使用受到限制时,南京某民族小学三年级的小娄会采用反制措施报复家长,“妈妈不让我玩游戏,我就给手机加密,他们就删不了我的游戏”,留守儿童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媒介叛逆与生活叛逆行为。而高年级学生家长的互动型限制几乎起不到效用,留守儿童仍旧会进行网络交友,不过大都局限于班级同学及熟人,较少接触陌生网友。
可见家长对孩子采取多重的限制措施,必然引起不少留守儿童的反对与抵制,导致手机争夺战的发生。在前述手机争夺战的第一回合中,家长看似占据上风,赢得了手机的控制权,但家长的强制监管造成了家庭秩序的失衡,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亲子矛盾突出。无论是前文提到的专制协作型家庭还是爱而不得型家庭,家长监管大都与学习生活相关,较少涉及孩子的情感支持,亲子间未能形成良性互动。面对父母的严厉管制,留守儿童往往采取抵抗的方式来应对。此外,年纪相对较大、独立性较高的留守儿童,更希望独立安排生活,抵制程度便更高。留守儿童与父母在两不相让的情况下,容易引发家庭冲突,矛盾和争吵时常发生。
其二,祖孙隔阂放大。祖辈因较低的媒介素养与家庭权威等困境,在严厉监管时更容易与孩子发生冲突和矛盾,这在专制协作型、有心无力型家庭中尤其明显。祖辈作为媒介使用干预的直接执行者,与留守儿童的互动最为频繁。但是祖辈与孩子代沟较大,双方难以达成相互理解和信任。因此,祖辈越是严厉监管,与孩子之间的隔阂便越大,随之而来的便是家庭内部无休止的矛盾。同亲子矛盾一致,孙辈年龄越大,祖孙之间的矛盾越激烈。
其三,祖辈与父辈的嫌隙。在爱而不得型家庭中,父辈将监管责任委托给祖辈,但祖辈未能履行好监管责任,导致监管受挫。由此,父辈产生对祖辈的不满与责怪。另一边,在有心无力型家庭中,祖辈“含辛茹苦”却换不来父辈的情感与经济支持,满是“伤心”。因此在爱而不得与有心无力型家庭中,祖辈与父辈之间均存在程度不一的抱怨与嫌隙。
虽然强制干预在很多留守家庭中埋下了家庭失序的隐患,但是对手机的控制,也存在缝隙。拥有自主性的留守儿童在与家长的互动中逐渐摸索出应对之策,获取边缘性手机实践。随着留守家庭中干预—应对的互动发展,手机的使用愈来愈合法,使用规则日益明晰且趋向制度化,留守家庭秩序也趋向有序。
(二)协作调适与家庭秩序
留守儿童被约束以后,因无法抑制对智能手机的欲望,便尝试各种方式获取手机的使用权。而家长在经历第一回合的争夺后对此并不强烈抵制,反而采取姑息、开放的态度。于是,手机争夺战的发展趋向平和,家庭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稳定平衡的留守家庭秩序。
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生存于“留守孤岛”中,缺少户外社交,没有典型意义的线下交往与游戏活动。而手机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娱乐、联系的功用,使留守儿童能够排解孤独、进行朋辈交往、达成亲情依恋。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大多数受访的留守儿童使用手机的频率非常高,几乎每天都玩网络游戏、进行网络社交。每到放学以后,笔者加入的紫萱班级私密QQ群,时不时就有99+消息,她与同学聊得火热。不少受访对象放学回家便打开了“王者荣耀”或“和平精英”,和同学匹配或独自单打。此外,留守儿童也会通过手机积极向家长分享学校、家庭事务,更会向父母寻求生活与情感帮助。紫萱会和妈妈吐槽离异父亲对自己的管教,以及寻求为人处世的建议。
孤独的境遇、无聊的家庭与网络社交、有趣的网络形成鲜明对比,留守儿童无法抑制对手机的渴望。面对监管,留守儿童逐渐“暗度陈仓”,实施未经授权的边缘性手机实践,该实践被戈夫曼称作“次级调适”(戈夫曼,2012:195)。笔者发现大多数留守儿童均采取“偷用”、“耍赖”举措,不同年龄阶段的留守儿童未表现出较大差异。例如前文中五年级小君的“耍小机灵”,三年级阿鑫以及花桥初中的小华偷玩手机等。而小娄的做法更具创造力,他为了防止手机发烫被奶奶发现,将手机放进冰箱或者冰块里,进行物理降温。小娄还会删掉外出父母安装在手机上的追踪软件,以躲避家长的线上监管。通过访谈发现,具备创造性的“次级调适”举措与留守儿童个体经验和学习能力相关。小娄告诉调研人员,物理降温是看抖音学的,删除追踪软件是自己发现的。
留守儿童想出多种多样的“次级调适”之策,来谋取手机使用,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家长的严厉限制,满足了手机使用的需求,也在另一层面上内化了媒介使用干预规范,维护了家长的监管权威。随着手机日益嵌入留守家庭生活,留守儿童的“次级调适”也实现了家长对留守儿童手机使用的期待,从而利于家庭冲突的缓解。
手机因满足在线教育的要求、亲情维系的需要,其搭载的“数字抚育”功能日益嵌入留守家庭,成为留守家庭不可或缺的存在,使得家长逐渐妥协,同意孩子使用手机。一方面,在线教育要求智能手机在场。前述三种类型的留守家庭,均在疫情期间配备智能手机用于留守儿童的线上学习,以完成学校安排的每日学习和健康打卡任务。另一方面,智能手机是亲情连接的必需品。在专制协作型、爱而不得型家庭中,手机变成亲子联系的必要工具。外出父辈依靠手机和祖辈的中介,维持亲情“在场”。因此,在日常监管中,外出父母无奈承认手机合法性,并对留守儿童的手机使用采取更为宽容开放的态度。
当然,在有心无力型的隔代监管中,作为直接抚养人的祖辈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容忍。如前述小君爷爷知晓孩子有偷玩手机的行为,并没有直接戳穿他,而是通过容忍来化解爷孙之间的矛盾,还利用使用时长的奖励赢得孩子的支持,建立起良好的祖孙关系。
因此,留守儿童采取次级调适获取手机使用权,以躲过家长的全程监管。而家长对此并非全然不知,但为维持家庭稳定采取了容忍和默许的态度。在留守儿童与家长的调适—平衡的持续互动中,留守儿童的边缘实践,满足了其使用智能手机的需求。与此同时,制度约束下的留守儿童的手机使用也满足了家长的期望,这使得家庭监管规则得到进一步深化,最终制造并维系了稳固和谐的留守家庭秩序。
具体来看,在亲子关系层面,外出家长借助手机开拓情感连接的通路,来谋求同孩子更多的联系与理解,从而缓和亲子关系,修缮亲子依恋秩序;在祖孙关系层面,祖辈采取容忍与奖励措施,通过出让手机使用权与留守儿童交换监管权力,从而树立监管权威,减缓祖孙冲突,维护祖孙和谐秩序;最后,监管成效的凸显,有可能消解祖辈与父辈之间的嫌隙,达成代际关系的团结秩序。因此,留守儿童与家长之间的手机争夺战,以孩子的边缘性实践和家长的妥协告终,带来了留守家庭三层秩序的团结和谐。
(三)亲子协同与家庭维序
在一些家庭中,留守儿童面对家长的监管并没有产生对抗姿态,反而保有认同与配合的态度。家长干预在某种程度上还促进了亲子关系的发展,维持家庭秩序的平衡。尽管现实生活中“维序”趋于少数,但作为积极典型需被重视和学习。
在调研的大多数留守家庭中,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留守儿童的手机使用并非完全被禁止。当然,在超过约定的使用时间后,家长会采取前文中较为激进的策略。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留守儿童并没有归还手机的自觉性,所以需要家长的介入。但是一些学习成绩优异、听话懂事的留守儿童,能够积极配合家长,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争端。
例如前述生活在专制协同型家庭的丹丹,她的手机在小升初考试期间被奶奶没收后,并未与奶奶有过争吵。而平时在奶奶眼里,丹丹很自觉,学习具有主动性。奶奶很放心丹丹使用手机。于是丹丹的懂事与优异的学习表现反过来为自己使用手机提供了合法性,从而使得家庭更为和谐。
因此,在留守家庭中,手机监管并不一定带来家庭秩序的“土崩瓦解”。平衡的家庭秩序的维持,源于祖孙两代之间的信任与配合。而信任则是建基于祖辈对孩子“乖巧”的评判与学习成绩的肯定。
除此之外,“共同使用”是家长在场并与孩子一起进行的游戏互动(Nikken & Jansz, 2006),这属于媒介干预中较为积极的策略。Padilla等人(2012)认为“共同使用”的监管策略具有互动性,亲子合作感知到的现实是共享的,这样能够提升家庭联系的水平,提高家庭亲密度。可以看到家长干预手机除了带来家庭秩序的维持以外,还有促进亲子关系良性发展的可能性。
南京某民族小学六年级的然然处于有心无力型家庭中,在外婆和老师眼里,然然父亲是不称职的,因为他从未过问然然的任何事情,也不跟学校老师沟通。但然然特别喜欢父亲,“爸爸的游戏段位很高,技术很好”。每次玩游戏,父亲都能带他上MVP,这令他十分崇拜。游戏过程中的亲子沟通,带来了父子相处的平等地位,也让孩子加深对父亲的情感依恋,从而构建出了亲子的亚平等状态(郑希付,1998)。由此看来,共同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弥合并促进亲子关系的良性发展,手机成为父子沟通、父爱修复与父亲权威树立的媒介。
但调研中并未发现留守家庭中出现较为突出的积极性媒介使用干预,譬如谈论、阐释媒体及其内容、规避网络风险,促进新媒介的正向使用等。实际上这类积极意义的媒介使用干预举措能够在维持家庭秩序方面发生重要作用,更应当成为留守家庭媒介使用干预的学习模板。
四、结语:媒介调适与留守家庭秩序重建
比起城市里的家长,农村留守家庭的家长在面对孩子使用智能手机时,产生了不同的媒介担忧偏向,如担忧低年级留守儿童的学习与身体的危害,担忧高年级留守儿童的社交风险,以及产生了“管不到”、“不好管”的多重监管焦虑。由于留守家庭的具体情况不同,代际协同的媒介使用干预又出现了三种类型,专制协同型、有心无力型以及爱而不得型。这三种代际协同的媒介使用干预或过于紧张的控制,或缺乏有效的干预配合,遭致留守儿童的抵制,点燃了手机争夺战,带来家庭矛盾与摩擦,其中包括亲子冲突、祖孙隔阂与祖父辈的嫌隙,造成留守家庭失序问题。
然而随着留守家庭干预媒介的深入,留守儿童的手机使用却只增不减,手机争夺战也没有酿成更为持久的家庭争端,家庭秩序反而逐渐向平衡和谐的趋势发展。这显然说明在留守家庭中媒介使用干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具体情境不断调适并变化。那么,如何理解手机争夺战中家庭秩序的变化?又如何在现有的媒介使用干预研究基础上,理解干预策略及其成效的变迁?
显而易见,应当放弃将媒介干预视为单向控制手段的认识,毕竟留守家庭中以限制为主的媒介使用干预导致的是家庭危机而非转机。可供性理论强调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形塑,为媒介使用干预研究与媒介角色反思提供新的参照。可供性揭示技术物不仅作为互动的客体,更是作为社会结构的行动者,在与人类互动中既展示某种功能,又带来某种限制(孙凝翔,韩松,2020),这一视角对考察媒介使用干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即是,干预的对象——媒介并非被动的客体,而是作为主体发挥着干预“可供性”,对实施干预的主体——家长以及干预影响的对象——留守儿童发挥“使能”与“限制”效用。
媒介的可供性使得“媒介使用干预”这一概念转向“媒介调适”抑或“调适媒介”。媒介调适即是:媒介在家长和留守儿童的合谋下,由被监管的对象调适/转义为沟通与监管、抚育和控制的协调行动者——监管代理。家长干预的举措由“限制”调整为“平衡”,留守儿童的反馈由积极抗争调整为次级调适,从而形成合法的家庭手机使用规范,实现父辈数字抚育、留守儿童情感补偿、祖辈“卸责”的和谐家庭秩序。
具体而言,最初作为留守家庭“监管对象”的手机,在家庭成员对其物质特征与用途的认知,以及社会文化、家庭互动乃至情感关系的实质影响中,其科技设计、物理特征和使用用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转义,成为了“监管代理”。将网络成瘾的“帮凶”调适为数字抚育、秩序修复的助手,家庭冲突的协调者。手机赋予家长追踪留守儿童使用新媒体的行为脉络、描绘孩子生活轨迹的可供性(王绍蓉,2020),使外出父辈得以实现“数字抚育在场”,但同时也要求家长赋予孩子更多的手机使用权,满足孩子的主体性需求;手机为处于“孤岛”的留守儿童提供次级调适、获取边缘实践的开放渠道,从而满足留守儿童解决情感饥饿、谋求娱乐的需要(刘文学,2019),但同时手机也在某种程度上要求留守儿童遵从家长形制的手机使用规范;最后,手机支持父辈的数字抚育,为留守祖辈减少家庭抚育责任、开辟生活空间提供了机遇,但也要求祖辈承担更多数字抚育的通讯、代理责任。因此,智能手机在使得家庭成员相互沟通,协调留守家庭成员利益的同时,形制出一套广泛认同的使用规范和家庭责任。在各方利益得以满足的情况下,起初因为争夺手机导致的失序逐渐向有序协调发展。
可以说,媒介调适是在留守家庭的特殊环境中由媒介使用干预日益优化和家庭成员之间动态互动形成的,因此媒介调适比起媒介使用干预更能形成和谐的家庭秩序。媒介使用干预,本质上是将手机当作家长干预的客体,受到家长权威的宰制。在农村留守家庭语境中,家长干预孩子使用手机是具有强迫性和单向性的行动,由此形成的家庭秩序实质是在家庭权威统辖下,牺牲留守儿童的平衡代际关系,存在实际或潜在失序的可能。而媒介调适是具备协调性与双向性的“家长—手机—留守儿童”三者构筑的家庭行动,由此形成的家庭秩序实质是家庭内部主体性不同程度得到彰显的团结与和谐的代际关系。
媒介调适与其他家庭媒介干预还存在一些不同。相较于普通家庭的干预,留守家庭中家长干预举措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与前者并无二致,但在“制造”家庭秩序中,媒介调适更偏向于“居间调停”,不仅满足留守儿童的精神和教育需求,还实现外出父母的“数字抚育”,也安置留守祖辈的晚年生活。此外,相较于普通家庭的干预成效,因为留守家庭权威离场和家庭功能的失衡,媒介调适的效果有限。并且家庭关系随着手机参与的广泛程度和地位的上升,也容易出现裂痕。
最后,相较于祖辈不在场的核心家庭的媒介干预,留守家庭的媒介调适构建出家庭互动的新图景。一方面亲子互动呈现出限制、共同使用与默许的监管行动——抵抗与次级调适的应对举措,另一方面留守祖辈代替外出父辈承担监管执行的责任。家庭互动维系的代际亲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有序与无序之间摇摆的不稳定性。
媒介调适维持的留守家庭秩序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平衡。相较于城市家庭中智能手机作为娱乐与兴趣的补充,留守家庭中智能手机则占据生活的核心,导致留守儿童手机沉迷和家庭干预失落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外出父辈与留守祖辈用手机来干预留守儿童使用手机,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家长越依赖手机监管留守儿童,越加深留守儿童对手机的依赖。
手机作为媒介维系了祖辈、父辈和留守儿童三者的妥协与调适,却始终没能解决父母陪伴与教育的缺失同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之间的张力,也没能解决父辈离场与年迈祖辈无力承担监管责任的张力,潜在的家庭失序仍不可预期。例如下一次考试失利,又或者是熬夜玩游戏,都会引发新一轮的手机争夺战,手机又将成为干预对象。在媒介使用干预与媒介调适的往复中,家庭失序与“制序”同样循环更迭,由此始终无法根治手机沉迷与监管失落的问题。
因此试图维系留守家庭秩序,完全依赖媒介调适并非万全之策,而是应当从监管策略与留守儿童困境着手。从家庭结构和功能来看,农村留守家庭核心角色的缺失导致家庭结构残缺不全,家庭抚养、赡养、情感满足、保护的功能受损(杨静慧,2008)。智能手机作为监管代理侵入了农村留守家庭,并在恢复家庭结构和功能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一媒介技术隐含着不稳定因素与各种风险,容易形成畸形的农村留守家庭结构。譬如留守家庭成员日常沟通、协调与情感互动过度依赖智能手机,造成家庭失序。因此,家庭作为恒久的爱的空间,我们应当呼吁家庭成员主体地位的再现,让媒介技术退出家庭生活的重心。倡导父辈回归家庭监管中心,扮演好“育儿总管”的角色,增加积极陪伴时间,提高情感沟通质量,树立正确榜样,维持和加强留守儿童心理的亲代在位(吴重涵,戚务念,2020),而非过于依赖祖辈和媒介技术,真正做到“缺场”并不“缺位”。
从个体层面来看,家长拒绝或完全放纵留守儿童使用智能手机均不现实,应不断提升媒介素养,学习积极性媒介使用干预的措施。尤其要借助父辈或学校教师的传播渠道,努力提升隔代祖辈的媒介素养,更好地帮助留守儿童培养智能手机使用习惯,制定出更为合理的手机使用的家庭规范。此外,农村社区、学校要帮助留守儿童营造健康向上的学习生活环境,传播或组织各类文艺体育活动,帮助留守儿童更好地充实和提升自己。譬如调研的南京某民族小学在平日里便组织学生参加科学实验、音乐舞蹈等课程,并在假期组织教师进驻农村社区,为留守儿童免费补习。总而言之,诉求不同的祖孙三代应当共同努力,通过互动调适,实现家庭秩序的稳定与团结,来维系为孙辈提供抚育与社会化、为祖辈提供养老支持、为父辈提供安全保障的和谐亲密的“家”。■
注释:
①对45个留守家庭的田野调查均由南京大学“心相连·云相伴”留守儿童主题公益支教团队成员王梦彤、王清华、匡卉、高倩、邵沛、刘颂雯、曹玥、付思涵、赵呈晨等于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完成,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曹晋(2009)。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1),71-77+109。
陈清文(2019)。新媒体儿童与忧虑的父母——上海儿童的新媒体使用与家长介入访谈报告。《新闻记者》,(8),15-25。
厄文·戈夫曼(2012)。《精神病院:论精神病患与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处境》(群学翻译工作室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胡春阳,毛迪秋(2019)。看不见的父母与理想化的亲情:农村留守儿童亲子沟通与关系维护研究。《新闻大学》,(6),57-70+123。
赖泽栋(2018)。青少年微媒介叛逆与亲职督导。《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6),163-168。
黎藜,赵美荻,李孟(2021)。“行之有效”还是“徒劳无功”——父母干预会降低孩子手机游戏成瘾吗?。《新闻记者》,(10),67-76。
刘文学(2019)。留守儿童:“情感饥饿”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国人大》,(10),18-19。
孙凝翔,韩松(2020)。“可供性”:译名之辩与范式/概念之变。《国际新闻界》,(9),122-141。
王清华,郑欣(2021)。数字代偿:智能手机与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研究。《新闻界》,(10),219-230。
王绍蓉(2020)。监视液态性、手机可供性:行动社群族之隐私与窥视。《传播与社会学刊》,(54),127-159。
王佑镁(2013)。数字融合与边缘重生:新时期侨乡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与满足。《远程教育杂志》,(1),86-92。
魏冬芹(2013)。《农村隔代抚养模式下代际互动问题研究——以菏泽市A村为例》。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硕士论文。吉林。
吴重涵,戚务念(2020)。留守儿童家庭结构中的亲代在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6),86-101。
向敏,毕重曾(2017)。手机使用对留守儿童的“补偿”效应: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中国会议》,1484-1485。
肖索未(2014)。“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社会学研究》,(6),148-171+244-245。
谢安琪(2019)。《走近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世界——对一个安徽省自然村的考察》。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硕士论文。浙江。
邢成举(2020)。“保卫家庭”:家庭策略视角下留守现象的再思考。《江汉学术》,(4),5-13。
杨静慧(2008)。解析留守家庭缺损现状:从结构到功能。《西北人口》,(4),121-124。
郑希付(1998)。良性亲子关系创立模式。《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72-76。
郑欣,高倩(2021)。社交茧房:智能手机与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4(6),75-86。
张煜麟(2015)。社交媒体时代的亲职监督与家庭凝聚。《青年研究》,(3),48-57+95。
朱秀凌(2021)。家庭沟通模式、父母介入对青春期网络霸凌的风险控制研究。《新闻大学》,(11),75-91+124。
BazalgetteC. & Buckingham. M. (1995). In front of the children: Screen entertainment and young audiences. London: BFI Publishing.
Beatrice SciaccaDerek A. Laffan, James O’Higgins Norman, & Tijana Milosevic. (2022). Parental mediation in pandemic: Predictors and relationship with children’s digital skills and time spent online in Ireland.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271-12.
Carl R. BybeeDanny Robinson & Joseph Turow. (1982). Determinants of parental guidance of children’s television viewing for a special subgroup: Mass media scholar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26(3)697-710
Laura M. Padilla-WalkerSarah M. Coyne& Ashley M. Fraser. (2012). Getting a high-speed family connection: Associations between family media use and family connection. Family Relations61(3)426-440.
Lin Wang, & Steven Sek-yum Ngai. (2021).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personal factors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for adolescent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The roles of internal states and parental mediation. Journal of Adolescence8928-40.
Nathalie Sonck , Peter Nikken & Jos de Haan. (2013). Determinants of Internet Media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reports by Dutch parents and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7(1)96-113.
Peter Nikken & Jeroen Jansz. (2006). Parental mediation of children’s videogame playing: a comparison of the reports by parents and children. Learn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31(2)181-202.
Sonia Livingstone Ph. D. & Ellen J. Helsper Ph. D. (2008). Parental mediation of children’s internet us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52(4)581-599.
刘王平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郑欣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智能手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BXW12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