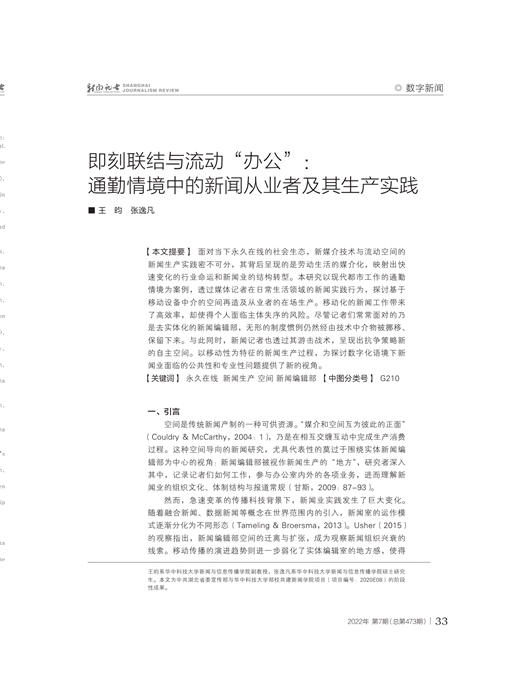即刻联结与流动“办公”:通勤情境中的新闻从业者及其生产实践
■王昀 张逸凡
【本文提要】面对当下永久在线的社会生态,新媒介技术与流动空间的新闻生产实践密不可分,其背后呈现的是劳动生活的媒介化,映射出快速变化的行业命运和新闻业的结构转型。本研究以现代都市工作的通勤情境为案例,透过媒体记者在日常生活领域的新闻实践行为,探讨基于移动设备中介的空间再造及从业者的在场生产。移动化的新闻工作带来了高效率,却使得个人面临主体失序的风险。尽管记者们常常面对的乃是去实体化的新闻编辑部,无形的制度惯例仍然经由技术中介物被挪移、保留下来。与此同时,新闻记者也透过其游击战术,呈现出抗争策略新的自主空间。以移动性为特征的新闻生产过程,为探讨数字化语境下新闻业面临的公共性和专业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永久在线 新闻生产 空间 新闻编辑部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
空间是传统新闻产制的一种可供资源。“媒介和空间互为彼此的正面”(Couldry & McCarthy, 2004:1),乃是在相互交缠互动中完成生产消费过程。这种空间导向的新闻研究,尤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围绕实体新闻编辑部为中心的视角:新闻编辑部被视作新闻生产的“地方”,研究者深入其中,记录记者们如何工作,参与办公室内外的各项业务,进而理解新闻业的组织文化、体制结构与报道常规(甘斯,2009:87-93)。
然而,急速变革的传播科技背景下,新闻业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融合新闻、数据新闻等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引入,新闻室的运作模式逐渐分化为不同形态(Tameling & Broersma, 2013)。Usher(2015)的观察指出,新闻编辑部空间的迁离与扩张,成为观察新闻组织兴衰的线索。移动传播的演进趋势则进一步弱化了实体编辑室的地方感,使得作为绝对空间的采编场所转变为保持时刻联结的相对空间——虚拟新闻编辑部(帕夫利克,1990/2005:116-117)。新闻生产空间的结构转型,映射出快速变化的行业命运,通过重新塑造接近新闻机构、参与新闻工作的方式,再定义了媒体制度化运作的文化意义。因此,面对新闻业与新媒介技术、与外部社会不断发展的紧密关系,研究者有必要检视从业者进行新闻劳动的独特日常体验,立足更广阔的视域理解新闻业经由一系列社会实践被不断概念化的过程(Deuze & Witschge, 2018)。
本研究注意到以移动智能终端为支持的流动空间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依据Meyrowitz(1986:6)的观点,现代历史的去地方化趋势使得人们注意到,理解新兴媒介的意义并非在于内容,而是社会生活“情境地理”的改变:无论身在何处,人们都可以保持联结状态。在遭遇信息技术革命过程中,新闻业形成媒介渠道和平台广泛互联互通的局面(Kramp & Loosen, 2018)。新闻实践由此迈向在线化,迈向“云端”,迈向移动场景(Perreault & Stanfiled, 2019),逐渐与从业者个性化的媒介使用和生活方式相融合。本研究试图将视角从实体新闻室延展出去,考察媒体记者进入日常生活领域的新闻实践行为。我们以现代都市工作的通勤情境作为案例,检视通勤作为社会职场“上下班”与打卡途中的过渡状态,如何被纳入日益扩大的专业劳动范畴,从而塑造一种暂时性移动生产空间,呈现记者以其能动性完成新闻报道以及想象职业身份的方式。这种围绕通勤情境推进的新闻活动外延化,为探讨数字时代新闻生产实践的流动性创造了窗口。研究的具体问题在于:移动通勤情境下新闻从业者如何完成新闻生产?他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呈现出何种面貌,反映出何种职业意愿和个人自主性?这一实践模式背后表现出新闻产制的何种变化?
二、数字联结与流动空间的新闻生产
(一)永久在线视野的媒介实践
媒介决定了人类活动对空间、环境的体验方式(Verbeek, 2005: 40)。随着即时性技术对社会生活的深层介入,传统互联网使用中的“启动”和“登录”状态正在终结,“随时、随地在线”成为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Vorderer和Kohring(2013)将“永久在线”(permanently online)视作媒介用户的基本境况,用以形容人们如何透过数字网络不受时空约束地完成交流和互动。无时无处不在的数字联结消解了空间恒定性,强化了时空秩序的移动感,这使得研究者逐渐借由流动空间的加剧来探寻社会变革踪迹,关注技术物质性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当代在线生活的自我持存与真实感(Caporael & Xie, 2017;卞冬磊,2019a)。
可以说,大众生活领域与移动设备之间的即刻联结使得媒介研究重返身体实践(孙玮,2018),据此探讨个体运用灵活媒介实践建构不同程度的在场方式,再现日常公共领域的社会体验(Bork-Hüffer, 2016)。譬如,有研究即关注到手机用户策略性的打卡行动,指出“科技漫游者”构筑自我空间之同时,形成了“流转”的居所感(吴筱玫,2016)。Thompson(2018)以行业临时工的移动设备使用为案例,也发现互联网环境围绕物理移动和信息移动展开的生产性行为赋予了暂时、特定的地方感,这强化了以实践为中心的社会空间导向。随着电子产品成为个人化的基础设施和行动载体,在个体经验不间断接入移动技术网络的过程中,媒介不再限于实现群体联结的通讯工具,同时更广泛地影响着资源分配、劳动过程以及社会关系缔结(胡杨涓,叶韦明,2019)。
(二)新闻生产的流动网络
新传播技术悄然影响着新闻生态系统的职业边界和专业规范(张志安,束开荣,2015)。如ornebring 与Weiss(2021)谈及,新闻业本就是一项流动实践,当代数字与移动媒介景观则令这种流动性变得更为显著可见,改变了记者行动的节奏。其中最具代表之一的影响无疑在于新闻生产时间性结构的变化,加速成为主导新闻业生态的基本原则(王海燕,2019)。传统的新闻制作难以满足新闻信息的即时性需求,新闻行业须“争分夺秒”。大型商业化的新闻机构和媒体平台于是开始建立多平台服务模式,用以快速发布新闻资讯。全天候的新闻室工作模式产生,由此出现“24小时营业”的编辑部样态、“每日10推”采编模式等(陈阳,2019)。
面对社会大量的信息需求,瞬时更新、反复循环成为新闻业常态。仅仅利用时间资源不足以达成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目标,空间资源的转换运用也成为新闻组织的重要策略(陈百龄,2016)。新闻记者因而不可避免地在采编流程使用移动设备摆脱物理空间限制,用以提高生产效率。在此过程中,即时通讯软件实现了记者与新闻事件主体的远程互动,减少了实地外出采访的时间消耗和物理位移,乃至于形成Paulussen(2012)所言的“久坐新闻学”:人们可以便利地使用线上材料完成内容“炮制”,只需在办公室通过联网就可以完成新闻生产流程(Lewis et al., 2018)。然而,吊诡的是,在线新闻活动虽降低了记者的行动成本,却强化了其本身的劳动作业。随着移动媒介的发展,新闻室这一物理地点借助媒介技术,隐蔽地成为“流动”办公场所,令记者工作时空不断延展,与生活休闲的区隔更为模糊。例如,以Slack为代表的新闻社交工具既实现了跨地理区域的信息共享和生产实践,使得在地新闻室转变为结构扁平化的“关系性空间”,但同时也被发现作为一种组织监控形式和同辈压力来源,正在消除工作者的私人领域(Bunce,Wright & Scott, 2018)。换言之,在商业主义持续占据支配性框架的背景下,新闻报道经由移动技术转化为不受物理时空约束的生产活动。传统观念中,关于有形地点以及在该地点应当上演何种行为自有其一套预设,然而,数字网络削弱了两者的密切关联,人们对于什么是“恰当行为”的观念由此发生转变(周鹏,2017)。投射于新闻业当中,则意味着原本在个人闲暇时空生产新闻的“不当行为”逐渐被合理化,进而加强了从业者的劳动压力。
(三)通勤与媒介化劳动生活
脱离时空限制的在线新闻生产背后指向的是劳动生活的媒介化。如Manzerolle(2010)指出,信息通讯技术在不知不觉中增强了劳动领域的工作强度。Lefebvre(1991:30)认为,日常生活领域淘汰生产工厂成为社会核心,极大扩大了当代经济活动的边界。将工作之意涵纳入围绕以技术中介为底色的生活实践之中,无所不在地对劳动者做出提醒。为了达成信息社会的“网络速度”,新闻记者也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即便是休憩与娱乐,亦成为劳动生活的附属(王淑美,2018)。这种专业实践的日常化“瓦解了工作场所与否、工作时间与否,以及工作与空闲之间的区别”(Caporael & Xie, 2017)。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来临由是推动移动性生产成为一项显著研究主题。新近研究者也普遍关注到较为新兴的职业群体,包括网约车司机(胡杨涓,叶韦明,2019)、外卖骑手(张玉璞,2019)、平台新闻工作者(蔡雯,朱雅云,2018)等等,探讨移动时代劳动者主动或被动融入数字化进程的方式,如何呈现新媒介文化与社会劳动分工之间的张力。
面对移动生产实践对空间意义的再造,通勤成为一种极富意味的情境。作为场所与场所之间的联结方式,通勤承载着物理移动,以此维持人们平时生活的正常运转。加速物理位移本该是通勤行为的主要目的,但城市空间分配和生产秩序却导致通勤耗时正在不断增加。2020年《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检测报告》称,36个全国重点城市超过1000万人正在承受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赵一新等,2020)。大量的城市工作者每日在通勤上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而时间的消磨大多依赖于移动设备活动,实际上使得通勤情境中存在着丰富的在线心理和媒介行为,催生出以上下班为主要日常实践的“移动空间”(卞冬磊,2019b);相较于将交通途中视作乏味的“中间时空”(Stokols & Novaco, 1981),透过移动设备使用,劳动者仍能保持与工作以及组织之间的有效联系,从而令这一原本“不重要的”的“暂时性地点”转化为现代劳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劳动的媒介化及其在线化为新闻业带来的现实在于,“现在的新闻并不只在新闻编辑部中被生产出来,还有可能在家、在提供免费Wi-Fi的咖啡厅中,甚至在路途中被生产出来”(常江,田浩,2020)。通勤发生的物理移动与在线生产活动相融合,重新定义了劳动者的工作节奏和工作方式,使得通勤空间衍生为劳动场所,移动设备的介入则挪移了特定作业实践的地方感(Thompson, 2018),新闻生产流程在其中被不断再组织、协商与建构。结合前述,鉴于研究者已广泛承认随时在线工作正成为现代生活之常态(Forlano, 2008; Wajcman, 2015:87-110),本研究试图讨论劳动空间的日常化线索对新闻业态带来的影响。以通勤情境作为考察案例,我们将审视记者在途新闻生产及其媒介设备使用的方式,并探讨移动时代新闻职业的劳动方式变化如何影响从业者关于专业理念的想象。
三、研究方法与经验材料收集
本研究经验材料收集分为两个阶段展开。首先,我们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访问新闻从业者通勤时空的工作生活方式与个体感受,初步把握基本情况。调查采用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方法,结合线上线下形式发放问卷。发放时间为2020年12月—2021年3月,共计发放350份,回收314份。题项设计主要包括人口统计特征、从业信息以及通勤中的移动设备使用等方面。鉴于大型新闻媒体机构地域分布上呈现的聚集性,受访者主要工作于北京(33.8%)、上海(16.9%)、武汉(12.9%)等城市。
过往调查指出,“工作时间超长是记者最大的苦衷”,乃至于其休闲生活也与新闻职业特征紧密相关(刘昶,陈文沁,2018:29-51)。尤其在移动媒介不断延展劳动实践的背景之下,“对于一些‘老黄牛’式的记者”,“每天24小时开着手机待命”已是常态(王维佳,2011:260)。为了维系持续的内容产出,在上下班途中处理工作,可谓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职业习惯。本研究数据结果显示,受访者最为常见的通勤时间主要分布在30—60分钟,约占全体的半数,另外有18.2%存在逾1小时的极端通勤时长。从业者普遍以在线方式保持着时刻准备的工作状态。除却骑行和开车出行,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通勤时段一直在线并保持着与他人联系:譬如,乘坐地铁时浏览在线内容或进行网上交流的比例达到98.1%、96.2%,步行时比例为75.8%和92.7%,乘坐公交则为95.5%和97.5%,排队和上下扶梯时也均逾80%。同时,这种永久联结情形已经形成深刻的心理状态:61.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产生对移动设备使用的警觉心理,令自身保持恒常在线。另外,我们划分了一些移动设备使用方式,请受访者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打分(0=从不,5=经常)。数据显示,上下班途中,表示会“使用即时通讯工具工作”、“查看工作相关内容”、“因工作呼叫某人/接听电话”、“收发工作相关邮件”等回答的整体评分均值分别为3.6、3.4、2.4和1.9。这表明受访者虽普遍会将通勤时间予以运用,具体的工作内容却有其倾向性。总的来说,经常在线处理简单事项的受访者占79.6%,从事深度复杂工作占25.5%,也即,诸如回复消息等行为较为频繁,而与人沟通采访这类工作则相对较少。由此观之,通勤情境中的新闻从业者主要完成的是如聊天沟通、查阅资料等一些“可以分心”的在线工作。
在问卷调查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开展质性访谈工作。针对调查对象回答情况获取可能合适的访谈者,有目的地选择访谈对象,并设计采访提纲,最终确认10位不同类型的新闻从业者。他们工作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是从事采访、撰稿、编辑及发布的新闻机构员工。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时间为2021年4月至6月,每次持续约1—3小时。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基本工作状况、通勤工作具体内容、工作压力、职业理念、工作自主性认知等展开。本研究试图通过质性访谈材料“重返生产的隐秘之处,将被遮蔽了的生产场景和劳动过程暴露在研究者的视野之下”(闻翔,周潇,2007),以此展现通勤时空中新闻实践的灵活性。
四、新闻编辑部“在云端”:通勤情境的新闻工作
(一)移动化的新闻编辑部
过去以来,不乏提醒新闻学的“空间转向”的声音,呼吁关注空间对新闻实践思维模式的影响,尤其移动技术如何推动人们所处位置与新闻生产消费相互整合的文化过程(Weiss, 2018)。显然,对空间叙事的引入,扩展了人们对新闻生产流程的理解。Usher(2019)也指出,思考记者工作方式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新闻编辑部内外正迎来基于地方的调整。传统意义上,新闻编辑部指向有形、可感知的实体建筑(Usher, 2018)。而社交媒介的介入塑造了关系性流动网络,新闻报道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亦被挪移到日常闲暇时空,最终建构起移动化的办公场景。本研究中,通勤路途为这种移动空间实践提供了一个有趣注解。新的沟通方式应运而生,重新塑造了新闻组织的内部协作惯例。例如,部门聊天群组补充了传统编辑部会议的功能。众多报道环节需要不断进行即时沟通来完成协调,这使得记者在通勤途中经常性地保持与新闻室的通讯软件联系。受访者F3提到,“看到一个新闻热点,编辑或者同事就会立刻转发到部门群,我的通勤时间很长,一看到这种消息就会马上点进去看,大家就在群里讨论”。分享新闻线索能够完成对事件变化的快速响应,在此之中,群聊信息是即时可达的,共享消息动态本身也塑造记者的主体在场,提升了内容生产的协作网络。这种借由移动技术建立的内部沟通关系,有助于新闻组织有效地协调行动。
在线环境对于传播速度的要求,普遍造成新闻报道产出的压力。为了更好地完成生产,新闻记者也依据移动作业条件进行着适应性调整。M2谈道:“今天值班的记者要监控一下昨天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整理成文档,发到我们组的大群里,大家就可以从里面找选题。所以我常常在路上看各类新闻App找新闻选题。”在本研究受访者看来,运用通勤时间铺垫前期报道工作已是职业常态。社交媒体不仅是了解各类信息的窗口,也是同行之间实现沟通核查的纽带。受访者F4即表示:“下班之后在路上,有其他记者发微信给我的稿件或写作方向提意见,我会秒回”。稿件写作与审核从编辑部转移到了外部场所,一些时候,甚至是透过在途社交的闲聊中完成的。这种报道模式的延展有助于组织与个人互相校正,并加强两者之间的沟通,投射出新闻机构在向“网络式企业”(常江,田浩,2020)衍变中的灵活实践,从而推动组织制度脱离被限定的固定场域,以更为高效的姿态完成运转。
(二)在线坐班的记者:可暂停的路途与移动工作
新闻报道虽被视作高度机动性的社会实践,新闻组织仍然强调坐班制度在其管理文化中的作用。Paulussen(2012)甚至发现,由于网络新闻时代带来更为繁重的桌面工作,这使得越来越多的采编人员被办公桌或办公室束缚。与之不同的是,本研究经验材料呈现了坐班制度新的在线形态:从业者面向办公桌的身体邻近被弱化,但与组织的劳动关系仍一如既往地得以保留下来。受访者表示,他们有的需要到单位按时打卡,一些则无需每天前往上下班,仅开会要求到场。不过,“不打卡”并不意味着远离了上班状态。在运用手机等可供性技术过程中,记者私人空间与公共交通环境相融合,塑造了持续性的移动工作。M3便坦言,自己已将通勤直接转变为新闻劳动的一部分:“当我坐上地铁,我就已经把自己转换到一个工作的场合。”作为联结“前往”与“到达”的过渡时空,通勤常常是工作与居家环境的中间地带。但随着记者将手头工作植入其中,通勤途中“前往到达之所”的目标感被“当下存在”的内容产出要求取而代之,新闻工作临时性地实现了其空间占有,渗透到个体生活细节中来。
借由移动设备为中介,新闻从业者反复进出于私人通勤情境和在线新闻室所规范的制度环境,处于持续分心状态。由于具体的新闻采写行为是“可暂停”的,从业者往往能够运用时间碎片来重新组织工作。通勤途中,记者们的自我安排方式也形成固定风格。受访者尤其表示,他们大多倾向处理一些简单、机械,无须过于耗费精力的内容,如“基本都是在看新闻文章或者转录音”(M1),“只做简短的research,比如找联系方式,或者有时在备忘录里列提纲”(F6)。此外,M2还提及一些附加的新媒体排版工作:“我做的最多就是做推送的文字梳理,去格式复制报道内容,粘贴到手机的记事本里面”。在他的表述中,数字新闻转型同步提高了对传统采编人员的专业要求,工作职位开始出现相对去技能化的“超额”内容,导致记者常常一人承担多种任务。将部分“小工作”挪移到通勤时空反映出从业者面对的工作负荷,也呈现当工作任务相互形成时间排挤效应时,人们所进行的自我协商。
不论如何,在某些时刻,记者仍然不可避免地需要集中精力进行写稿或其他复杂任务。研究者发现,一旦需要更为专注地完成原创信息生产,受访者往往立刻终止物理移动,甚至直接在站台上工作。F7如是描述:“我会干脆中断行程,地铁坐到哪一站算哪站,在地铁口的台阶上、等车的座位上,甚至在垃圾桶上放着电脑就开始干活,调低电脑亮度防止写完之前没电,只有这样我才可以保持思维的集中。”由此来看,即使处于移动的可分心世界,新闻从业者仍会设法创造必要条件,用以克服通勤环境对专业报道造成的扰动。某种程度上,永久在线的新闻工作不仅意味着个体在行动轨迹中时刻保持被联结状态,与之紧密相随的是,一整套包含客观准确、独立思考等在内的职业观念也卷入其中,影响着人们做出符合自我要求的行动策略。从业者有意或无意识中坚守的职业实践准则,构成一种隐形生产文本,融入高度日常化的内容作业机制。
(三)架构工作空间:移动情境的物质中介
通勤情境的新闻生产乃是围绕相应的移动技术中介作为物质基础。以手机、便携式计算机为代表的新媒介设备不仅关乎私人使用需求,并且嫁接了通勤者与新闻编辑部的关系,透过承载群际分享和事务性交流,完成组织期望的工作责任目标。经验材料揭示,新闻机构也广泛意识到移动作业在当下新闻生产中的位置,提供移动设备已成为采编人员入职的标准配置。例如受访者F4提到:“在平台媒体工作时,工作者所在新闻机构会派发工作专用的笔记本电脑以供内部交流沟通使用。在职时个人可自由使用笔记本电脑,进入公司内部工作社交软件,免费使用付费应用”。如Kitchin与Dodge(2011:71-73)所言,“空间是程式码和物构成的结合体”,媒介物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在与通勤情境的互动中维系着移动工作状态,搭建了流动的空间架构。
在媒介设备与新闻实践形成深刻关联的背景下,媒介本身也成为新闻室的延伸。鉴于此,工作情境被异常顺利地移植到通勤空间,媒介化劳动得以隐蔽嵌入。完成新闻产品设计、制造和发布的各个环节,常常是在受访者提及的“某App聊天”、“在线文档协作”、“对话框私戳”等过程中完成的。不同媒介及其软件工具的使用贯穿于通勤路途,成为工作方式的一部分。媒介本身的状态也影响着正常工作的运转,比如电量不足、功能缺失、屏幕过小的手机。为了更好地适应移动性工作,从业者甚至必须调整其媒介使用习惯,并反过来加强了通勤负荷。例如,受访者M1表示,作为摄影记者,手机处理照片较难,为方便处理较急稿件,基本每天背着电脑出门。设备应用背后展现的是有关劳动的深层修辞,随身携带、即刻使用的技术工具强化了新闻报道本身的厚度和密度,将内容生产活动经历的各项环节落实为更加细微的日常行为,从而扩大了新闻业的劳动时空。
五、一直在路上:日常化新闻生产的行动写照
通勤介于办公场所与私人生活之间,对人们生活幸福感有着巨大影响。然而,对知识型劳动者来说,通勤时段却常常用于多任务工作,进行相关生产性活动(Teodorovicz et al., 2022)。尤其伴随传媒经济日益将内容制作标准与社交媒体逻辑“联姻”(Broersma & Graham, 2012),新闻业不得不对报道时效性提出更高要求,从而适应数字时代的信息消费节奏。手机作为联结工具“改变了记者的工作方式”(Knight, 2003),智能设备在保障从业者一直在线的同时,也进一步将新闻报道导向移动化空间的生产逻辑。新闻劳动面向从业者个人闲暇时空的挤压,乃是新闻产制一系列复杂变化所引发之结果,期间既牵涉媒介组织对信息时代转型变革要求的内在响应,又源于外部市场化制度所造成的“媒介产品和劳动样态的相互规训”(夏倩芳,2013)。本研究所发现的通勤新闻作业虽以简单事项为主,其内容却涵括广泛。从业者平日经历的选题交流、资料查询、线人采访、图像处理和界面排版等任务,几乎都成为在途工作的一部分。伴随现代社会工作生活扩大的一体化范畴,通勤情境呈现的潜在劳动趋向投射出数字环境下新闻从业者的行动样态,为检视新闻生产活动的日常化线索提供了可窥之径。
首先,移动化的新闻工作无疑提升了新闻机构生产效率,并塑造了新的组织关系网络。在追求全时段内容产出过程中,新闻业透过虚拟编辑室,进一步推动了“聚合新闻线索—记者原创写作—编辑在线发布”的类型化模式。对于记者而言,将文字稿或新闻组图发给编辑并离开单位后,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受访者们描述,一旦收到编辑私信反馈,即便在下班途中,也会立即进行修改,以便稿件及时发出。伴随着记者和编辑在途生产中的协作,稿件审核和校正的应答效率得以提高,并加快了内容生产周期和流通的节奏。此种移动性实践驱动的不仅是新闻生产方式的转变,同时意味着组织结构和文化的重塑。通过替代物理建筑的功能,虚拟编辑室一方面缓解了新闻机构承担的经济成本(Bunce, Wright & Scott, 2018),另一方面更强化针对采编人员的管理控制。“不坐班”的记者远离了办公室空间,但身体的永久在线却带来了持续性任务。受访者F7如是提及:“因为是在线工作,很难界定上下班时间,工作群的消息我都会秒回,晚回只会被领导骂得很惨”。即时响应、快速应答的数字网络秩序和新闻组织追求效率的目标不谋而合,新闻记者身处其中,无法避免地接受着劳动时间的延长,有时不得不同时承担多项职责。面对移动化的编辑室趋势,某种意义上,记者既失去了面对面建立同侪情谊或感受共同体情感的氛围,又受制于无时无处不在的压力网络,这种关系生产的“松散联结”实际上牢牢约束着个体从业者,形成个体面对职业场所的空间疏离以及不可化约任务量的难解矛盾。
其次,即刻联结的日常生活状态带来了新闻记者主体性的失序风险。移动传播固然有其便利性优势,然而,“随时在线”的预设反而加深了新闻从业者工作时段的变形。譬如,受访者出于时间考虑,更多采访被频繁安排在记者的吃饭时刻、中午休息或者下班闲暇时段。蒯光武与罗琦文(2013)认为,数字新闻生产模式中编辑的主导角色,减弱了突出“执行”的新闻记者能动性。在移动媒介的深层介入下,内容生产进度得以被“全景监控”,这带来了组织和个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界限模糊的工作与休息领域相互扰动下,一些记者难以借用休闲来排解职业压力,面临着交通失序风险和现实生活的自主性危机。受访者F5表示,“眼睛在看手机,脑子在想稿子怎么写,完全在靠下意识走路,直到被别人提醒,‘朋友,你撞到我了’”。有受访对象甚至经历自己称之为连续两次坐反地铁方向的“魔幻事件”。紊乱通勤节奏的背后,进一步指向的是新闻从业者日常时空秩序的中断。受访者F1指出,在职业惯性驱使下,即便朋友聚会也会带上电脑,感到失去丰富自身价值的时间和精力。新闻记者本寄望通过弹性工作制掌握时间主权,充分实现自我能动性,然而在具体实践中,“新闻从业者们都过着即时发稿、随时使用通讯软件、即时在社群媒体发布”的生活(刘蕙苓,2018)。
“弹性”消解了人们身处的日常生活。并且,由于从业者对新闻机构的专业性或行业规范有着一套约定俗成的想象,这种个体精神追求的热爱和激情驱动了对于劳动的自洽认同(刘芳儒,2019)。受访者们提到,自己对于“所工作的媒体调性和专业度有自己的期待和要求标准”,即便闲暇时间被占用,仍然“还是会接受”。在Hochschild(1983:9-12)看来,现代管理文化乃是透过深层情感体验的扩展实现其“控制”。在与新闻组织打交道过程中,从业者持有的情感认同内化为新闻室扩大其生产规模的制度化准则。全时段、碎片化的工作节奏在日复一日的数字对话中演化为无意识的群体惯习,隐蔽地维护某些压迫性结构(常江,2020)。移动本身就是工作,这种流动办公意识强化了新闻产制内部的劳动强度,加深了市场逻辑的宰制。譬如,M1讲述了一段经历:“有次我因为热点新闻事件出差,当晚就必须发稿,所以下午采访完之后编辑就跟我说,你回去在车上这一个小时,要是速度快,就能把稿子写完。突发热点新闻文本组织是很复杂的,车上又很晃,我在车上非常痛苦地写,也写了一点开头,最后稿子发出去还是晚了,但我也只能做到这样。”私人路途不再游离于工作空间以外,而是被嵌入组织规范要求的秩序当中。以出外勤为代表的工作任务,和以在途生产为代表的通勤时空相互缠绕在一起,映射着当下专业实践默认的劳动期望,令从业者卷入持续不断无边界的在线工作之中。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日常化新闻劳动施加的影响,从业者同样以其策略抗争,带来了内容生产实践一些新的自主空间。如蔡惠钧(2009)指出,记者常常能够借助线上空间的遮蔽效应以及移动设备的灵活使用实现对劳动的短暂规避。举例而言,“已读消息”是在线互动中的一项重要隐喻。聊天框显示的消息读取意味着信息有效传达,接收方则需要做出与之相对的回应。然而,与现实场所中身体的物理“出席”不同,社交媒体更需通过捕捉一些在线踪迹来验证主体在场性。记者常常巧妙运用“游击”方式掩饰自身行踪,或延迟线上应答,以此建立针对技术控制的抗争实践。受访者F5提到,“飞书(注:某即时通讯软件)能够看到你是否已读消息,你要是已读不回,就很尴尬。下班之后,我就通过弹窗去看消息,这样不会显示已读,又能看到消息内容。如果我不想做,我就会晚点回复他,因为不回他也是不可能的”。凭借“读取”但不“点击”信息这一手段,个体绕过软件本身的机械判断,实现在线“隐身”,以此暂时规避自己不情愿的工作任务。有人甚至强制采用网络离线方式,更为彻底地中断了即刻联结状态。F6描述称:“那时候我记得交稿时间很紧,整个部门都等我交稿,我就在地铁上打字。当时文字稿打了一半,我手机只剩最后1%的电,我就在部门群里说我半个小时之后再去做。手机关机的时间里我真的是觉得难得忙里偷闲,太棒了,我就在地铁上享受了半个小时。”运用关机、离线乃至切断设备“电源”等方式,移动通勤退回到闲暇“真空”,从新闻生产的关系网络中抽离出来。这一策略背后的意涵在于从业者对市场化逻辑的自主逃离以及面向生活意义的回归。与此同时,个体亦可编造或“伪饰”在线时长,展现符合组织所期望的工作态度,M2即表示:“我有时会特意在下班坐地铁的时候登上石墨文档,希望展示给合作的同组同事或领导一种我在工作的勤奋印象。”某些时刻,身处采编流程中的记者甚至可借由移动技术自行抉择是否前往新闻事发地,以此减少城市空间移动耗时。对于一些受访者所表述的“简单选题”,寻找一个安静之所拨打电话相比实地采访更能够快速完成报道写作。可见,新闻记者有意识地管理自己在线联结关系和情感劳动,做出微小、零碎的反击,呈现出充满战术实践的替代性手段。个体制定能动策略,努力寻求空间解放,激活了具有群体特征的行动秩序和报道样态,并建立起新闻记者审视职业规范新的自我主张。
六、讨论:移动化时代的新闻生产
如Jenkins(2021)指出,相较于围绕劳动工作不公正问题的讨论,专门针对通勤的关注却少了许多,事实上,“通勤即是人们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诚然,新闻工作向来注重时效,对于记者而言,上下班途中适当处理辅助工作,可谓一种习以为常的职业习惯。不过,随着现代都市通勤时间的延长以及永久联结环境下日趋移动化的生产实践,这种生活世界和职业环境的叠合仍然赋予了新闻采编业务鲜明的数字时代特征。新媒介对新闻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具有融合属性的技术革新,并且透过将生产作业面向移动时空挪移,塑造了从业群体日常化的持续劳动状态。Krippendorf(2011:XIII)谈道,自工业社会以来,人们总是怀揣着一种迫切的“移动”愿景:抓住每一次离开日常工作惯例的机会。然而,透过呈现通勤情境的新闻从业者实践,本研究探讨了新闻生产惯例如何经由技术中介物被植入无处不在的移动场景,从而检视其中个体身份认同、新闻组织规范和社会工作生活的复杂联结。一定意义而言,虚拟工作场所的出现带来了对劳动的遮蔽,造成对日常休息空间的非合理性叠加,从而模糊了职业劳作与日常生活的边界。新闻人时常身处局促狭窄的工作处境中,面临主体性失序的风险。在卷入媒介化劳动的过程中,从业者不得不借助不同程度的游击方式和积极的策略抗争,去获取具有灵活性的自主空间。
可以说,移动设备的嵌入改写了人与组织网络、与坐班制度,乃至与媒介物的关系。新闻业的转型话语带来的是从业者劳动生态的转变,深度媒介化的组织工作与寻求解放的主体难解难分,漂泊感和不安感的话语始终围绕着从业者群体。新闻生态系统面临着多元信息形态的冲击,以帮助公民实现自由和自治为主要目的,以现代民主为神圣使命的新闻业正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矛盾和挑战(Kovach & Rosenstiel, 2007)。数字环境新闻转型业态的高度日常化过程,提供了进一步检视新闻业在技术变迁环境所面对的张力:
其一,新传播科技的使用过程如何扩大现代社会工作生活的一体化范畴。新时代,传统以办公室、工厂为核心的工作模式卷入到一系列包罗生产、消费和休闲的社会活动当中(Lefebvre, 1991:29-42),新闻劳动与日常生活世界亦形成紧密脉络。围绕这一转变,新闻组织的劳动强度不再意味着延长内部成员的工作日时间,而更多转向对个体休闲时空的支配。工作和休闲之间的传统平衡被日常化作业模式打破。一方面,新闻活动呈现更具网络性、中介性和碎片化特征,另一方面,移动时空构成新闻实践方式的有机部分,化约为开展工作的常规地方,并逐渐让位于商业主义的系统重组。研究者有必要注意新闻生产实践的边界变化,探讨从业者劳动方式的时空延展及其背后延宕的政治经济意涵。
其二,新闻编辑部权力如何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塑造新闻实践新的报道常规。数字环境透过增加对新闻内容时长、节奏、更新频次等方面的要求,影响着从业者的时间感知,并加深了“24小时不打烊”的焦虑文化(王海燕,2019)。弹性工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新闻记者自主采访的个人空间,但也推动编辑部如影随形地交织于生活休闲场域。在个体远离办公单位的移动场景当中,新闻组织透过即时核查机制以及非正式化的群聊手段等新形态沟通方式,仍然将一套层级化的内在控制逻辑保留下来。永久在线状态下个体与新闻室之间的联结关系,不仅有助于对劳动作业本身的控制,也便于建立对新近事件的即时监控,面对竞争激烈的内容市场,完成对新闻故事的模仿与追逐(Boczkowski, 2009)。新闻组织接纳新技术的过程,因而伴随着制度规范面向从业者群体行为的渗入,强化着新闻业的市场导向。
其三,流动的生产空间如何再造新闻记者对新闻事业的想象,从而影响其关于专业理念的理解。生产主体往往倚靠专业话语及实践行动来构筑正当性(李东晓,2019)。专业新闻存续的首要之义是时间主权,记者因而产生了即刻响应就地生产的意识自洽。个体默许闲暇时空片段被扰乱的这一事实,也包含着对专业身份以及行业规范既定想象背后的情感劳动,专业理念以及采访报道技能最终成为践行日常生产的隐性行动文本。借助实践主体、流动空间、互联互通技术与价值观念组成的串联网络,有助于探讨关于“职业”这一话语体系形成的丰富性(巴泽利尔,王茜,2019)。随着通勤工作成为新闻从业者习以为常的模式,新闻记者在移动社会对专业身份的认知重构,投射出职业正当性的复杂构建问题。尽管本研究资料呈现,个体从业者寻求自主解放的策略抗争仍在微观层面不断丰富,但其关涉的主要是劳动任务的规避,日常化新闻生产所影响的行业规范与主体性之间的平衡,是否影响从业者对专业价值的社群认同,则是另一项有待继续考察的话题。
以通勤为代表的新闻生产场景呈现了新技术时代新闻业运作的多重矛盾。正如Alexander(2015)所说,专业新闻业视为神圣的行为准则既关涉公共生活的道德,又渗透到日常生产实践的每个角落。当下,虚拟编辑室的广泛兴起不仅指向移动智能媒介推动的技术变革,同时也带来新闻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刻画围绕于新闻室外在环境,组织权力规范、个人专业认同与行业价值导向之间的互动性提供了新的经验关照。面对数字网络推进的新闻生产方式变化,如何在应对媒介市场竞争过程中,维系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地位与工作权利;以及从业者在日常劳动压力下所建立的类型化和常规化实践,如何影响新闻业面向公共领域的对话,无疑都构成未来研究可供继续讨论的方向。研究者亦可结合时空日记、影像民族志、移动定位系统(Büscher, Urry, Witchger, 2011)等多元方式追踪特定情境中人员、技术、资源和策略的组合,基于更为详尽的方法数据,讨论虚拟新闻室与新闻生产新业态背后的政治经济效应。■
参考文献:
巴泽利尔·帕翠丝,王茜(2019)。职业,差异与复原力:关于组织传播学发展新路径的对话。《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48),1-22。
卞冬磊(2019a)。线上社会世界的兴起——以“自我”概念探究“社交”媒体。《新闻记者》,(10),31-40。
卞冬磊(2019b)。路上无风景:城市“移动空间”中的交流。《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47),29-54。
蔡惠钧(2009)。劳动过程之研究:新闻记者的劳动控制和展现主体。《台湾劳动评论》(台湾),(1),89-113。
蔡雯,朱雅云。(2018)。从新闻聚合平台看新闻编辑业务的变化。《国际新闻界》,(10),101-112。
常江(2020)。互联网、情感连续体与情感劳动。《青年记者》,(19),93。
常江,田浩(2020)。马克·杜兹:新闻学研究应当“超越新闻”——后工业新闻的转型、动态与理论化。《新闻界》,(7),4-11。
陈百龄(2016)。追分赶秒:新闻组织的时间结构化策略——以报社图表产制为例。《新闻学研究》(台湾),(127),75-117。
陈阳(2019)。每日推送10次意味着什么?关于微信公众号生产过程中的新闻节奏的田野观察与思考。《新闻记者》,(9),23-31。
赫伯特·甘斯(2009)。《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杨涓,叶韦明(2019)。移动社会中的网约车—深圳市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时间、空间与社会关系。《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47),135-165。
李东晓(2019)。界外之地:线上新闻“作坊”的职业社会学分析。《新闻记者》,(4),15-27。
刘昶,陈文沁(2018)。《当代中国记者群体:基于社会学的某种观照》。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刘芳儒(2019)。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理论来源及国外研究进展。《新闻界》,(12),72-89。
刘蕙苓(2018)。台湾记者的3L人生:数位时代的工作状况与赶工仪式。《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43),39-71。
蒯光武,罗琦文(2013)。难以言喻的写照:以隐喻抽取技术探索报社摄影记者的心理范式与价值共识。《新闻学研究》(台湾),(115),187-236。
孙玮(2018)。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国际新闻界》,(12),83-103。
王海燕(2019)。加速的新闻:数字化环境下新闻工作的时间性变化及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10),36-54。
王淑美(2018)。网络速度与新闻——转变中的记者时间实践及价值反思。《中华传播学刊》(香港),(33),65-98。
王维佳(2011)。《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闻翔,周潇(2007)。西方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批判性的述评。《中国社会科学》,(3),29-39。
吴筱玫(2016)。网上行走:Facebook用户之打卡战术与地标实践。《新闻学研究》(台湾),(126),93-131。
夏倩芳(2013)。“挣工分”的政治:绩效制度下的产品、劳动与新闻人。《现代传播》,(9),28-36。
约翰·V.帕夫利克(2005)。《新闻业与新媒介》(张军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张志安,束开荣(2015)。新媒体与新闻生产研究:语境,范式与问题。《新闻记者》,(12),29-37。
张玉璞(2019)。流动中的社会关系:上海外卖骑手移动媒体使用与社会资本。《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47),167-198。
赵一新等(2020)。《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检索于:http//www.chinautc.com/templates/H_subject/content.aspx?nodeid=247&page=ContentPage&contentid=96685。
周鹏(2017)。《是劳动,还是社交?》。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武汉。
Alexander, J. C. (2015).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Cultural cower.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8(1)9-31.
BoczkowskiP. J. (2009). Technology, monitoring, and imitation in contemporary news work. CommunicationCulture & Critique, 239-59.
Bork-HüfferT. (2016). Mediated sense of place: Effects of mediation and mobility on the place perception of German professionals in Singapore. New Media & Society18(10)2155-2170.
BroersmaM. & Graham, T. (2012). Social media as beat: Tweets as a news source during the 2010 British and Dutch elections. Journalism Practice, 6(3)403-419.
Bunce, M.Wright, K.& ScottM. (2018). “Our newsroom in the cloud”: Slackvirtual newsrooms and journalistic practice. New Media & Society20(9)3381-3399.
Büscher, M.Urry, J.& Witchger, K. (2011). Introduction: Mobile methods. In M. Büscher, J. Urry & K. Witchger (eds. )Mobile Methods (pp. 1-19). New York, NY: Routledge.
CaporaelL. R. & XieB. (2017). Breaking time and place: Mobile technologies and reconstituted identities. In J. E. Katz (ed. )Machines that become us: the social context of person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p. 219-232). New York, NY: Routledge.
Couldry, N.& McCarthy, A. (2004). Orientations: Mapping MediaSpace. In N. Couldry & A. McCarthy (eds. ). MediaSpace: Place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pp. 1-18). New York, NY: Routledge.
Deuze, M.& Witschge, T. (2018). Beyond journalism: Theor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19(2)165-181.
Forlano, L. (2008). Working on the move: the social and digital ecologies of mobile work places. In D. Hislop (Ed. ). Mobility and technology in the workplace (pp. 28-42). Abingdon, UK: Routledge.
Hochschild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enkins, D. (2021). Work, rest, play...and the commute.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080/13698230.2021.1926134.
Kitchin, R.& DodgeM. (2011). Code/space: Software and everyday life. CambridgeMA: MIT Press.
KnightM. (2003). Can a cellphone do it for a journalist? Rhodes Journalism Review, 2349.
KovachB. & Rosenstiel, T. (2007). What is journalism for? In Bill K. & T. Rosenstiel (Eds).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pp. 89-216).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Kramp, L.& Loosen, W. (2018).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From changing newsroom cultures to a new communicative orientation? In A. Hepp, A. Breiter & U. Hasebrink (Eds. ).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ransforming communications in times of deep mediatization (pp. 205-240). Cham, CH: Palgrave Macmillan.
Krippendorf, J. (2011). The Holiday makers: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leisure and travel. Trans. by V. Andrassy, New York, NY: Routledge.
LefebvreH. (1991).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Ⅰ: Introduction). Trans. by J. MooreLondon, UK: Verso.
Lewis, N. P.Bu ZhongFan Yang & Yong Zhou (2018). How U. S. and Chinese journalists think about plagiarism.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8(5)490-507.
ManzerolleV. (2010). 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 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 world. Ephemera: 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10(4)455-468.
Meyrowitz, J. (1986).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nebring, H. & WeissA. S. (2021).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mobility. Journalism Studies22(14)1894-1910.
Paulussen, S. (2012). Technolo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s work: Are labor conditions in (online) journalism changing? In E. Siapera & A. Veglis (Eds. )The handbook of global online journalism (pp. 192-208).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Perreault, G.& StanfiledK. (2019). Mobile journalism as lifestyle journalism? Field theory in the integration of mobile in the newsroom and mobile journalist role conception. Journalism Practice, 13(3)331-348.
Stokols, D.& Novaco, R. W. (1981). Transportation and well-being. In I. Altman, J. F. Wohlwill & P. B. Everett (eds. )Transportation and behavior (pp. 85-130). New York, NY: Plenum Press.
TamelingK.& Broersma, M. (2013). De-converging the newsroom: Strategies for newsroom change and their influence on journalism practic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75(1)19-34.
Teodorovicz, T.KunA. L.SadunR.& ShaerO. (2022). Multitasking while driving: A time use study of commuting knowledge workers to assess current and future u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162102789.
ThompsonT. L. (2018). The making of mobilities in online work-learning practices. New Media & Society20(3)1031-1046.
Usher, N. (2015). Newsroom moves and the newspaper crisis evaluated: spaceplaceand cultural meaning. MediaCulture & Society37(7)1005-1021.
Usher, N. (2018). Re-thinking trust in the news: A material approach through “Objects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19(4)564-578.
Usher, N. (2019). Putting “place” in the center of journalism research: A way forward to understand challenges to trust and knowledge in new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1(2)84-146.
Verbeek, P. (2005). What things do: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gency, and design.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VordererP.& KohringM. (2013). Permanently online: A challenge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7(1)188-196.
Wajcman, J. (2015). 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eiss, A. S. (2018). Location-based news in mobile news apps: Broadcast leads in geolocated news contentnewspapers lag behind.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39 (1)42-54.
王昀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张逸凡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与华中科技大学部校共建新闻学院项目(项目编号:2020E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