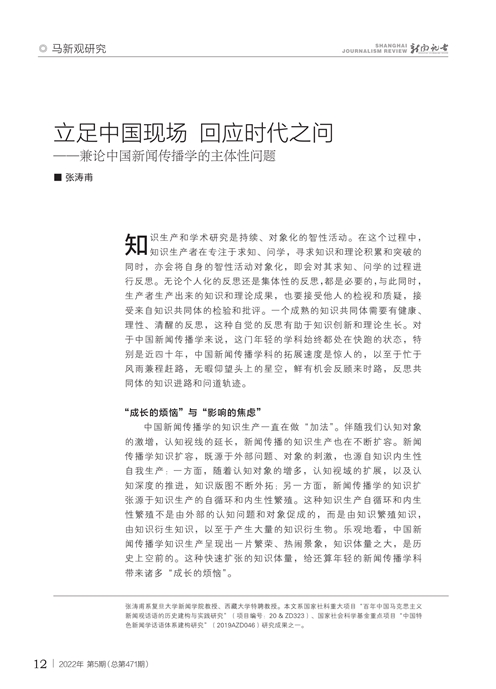立足中国现场 回应时代之问
——兼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主体性问题
■张涛甫
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是持续、对象化的智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生产者在专注于求知、问学,寻求知识和理论积累和突破的同时,亦会将自身的智性活动对象化,即会对其求知、问学的过程进行反思。无论个人化的反思还是集体性的反思,都是必要的,与此同时,生产者生产出来的知识和理论成果,也要接受他人的检视和质疑,接受来自知识共同体的检验和批评。一个成熟的知识共同体需要有健康、理性、清醒的反思,这种自觉的反思有助于知识创新和理论生长。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来说,这门年轻的学科始终都处在快跑的状态,特别是近四十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拓展速度是惊人的,以至于忙于风雨兼程赶路,无暇仰望头上的星空,鲜有机会反顾来时路,反思共同体的知识进路和问道轨迹。
“成长的烦恼”与“影响的焦虑”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一直在做“加法”。伴随我们认知对象的激增,认知视线的延长,新闻传播的知识生产也在不断扩容。新闻传播学知识扩容,既源于外部问题、对象的刺激,也源自知识内生性自我生产:一方面,随着认知对象的增多,认知视域的扩展,以及认知深度的推进,知识版图不断外拓;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的知识扩张源于知识生产的自循环和内生性繁殖。这种知识生产自循环和内生性繁殖不是由外部的认知问题和对象促成的,而是由知识繁殖知识,由知识衍生知识,以至于产生大量的知识衍生物。乐观地看,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呈现出一片繁荣、热闹景象,知识体量之大,是历史上空前的。这种快速扩张的知识体量,给还算年轻的新闻传播学科带来诸多“成长的烦恼”。
仔细盘点家底,不难发现,新闻传播学知识体态其实是“虚胖”的。多年来,我们生产出一大堆“散装”的知识。表面看上去,我们的知识规模相当可观,但现今的新闻传播知识存在这样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新闻传播实践中的很多问题得不到知识和理论的有效供给,“硬知识”供给相对不足;另一方面,低浓度、粗放型的知识产能过剩。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长是外力驱动型,甚至可以说是强迫型的,诸多知识生产不是内生性、本源性的。这主要表现为,诸多知识话语和概念表述,脱离我们本土语境或问题场景,被直接挪用、移植到中国语境之下。这种知识漂流物悬浮在学科表面,难接地气。
究其原因,作为后发型的知识生产领域,中国新闻传播学一直存在挥之不去的“影响的焦虑”。“影响的焦虑”这个概念是美国著名文学家哈罗德·布鲁姆(2006)在其名著《影响的焦虑》中提出的理论概念。布鲁姆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后来的诗人、作家多是活在前辈作家的阴影中,诗歌的历史乃是一代又一代诗人误读前驱、冒犯前驱的结果。一些卓有影响的作家诗人,会对后来者构成强大的影响,后来者处在前驱的阴影之下,并在影响的焦虑中做出超越的尝试。诗歌的历史即是影响的历史,诗歌的历史就是在前人对于后人的影响中绵延推进的。其实,“影响的焦虑”不仅在文学诗歌领域存在,几乎在所有的知识生产领域皆存在这种现象。当一种知识理论成为“显学”、具有强势知识话语权的时候,就会对其周边或后来者构成影响和压力,而这种影响并不仅仅表现为归顺和盲从,被影响者还会在“影响的焦虑”中产生超越或叛逆的冲动(张涛甫,2018)。反观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也存在这种源于西方的知识输入带来的“影响的焦虑”。数十年来,这种焦虑更多表现为归顺和盲从,鲜有超越或叛逆。
近四十年来,我们引入的概念、理论、话语以及方法论不可谓不多,甚至出现了过度移植的倾向。对西方理论话语的过度移植,造成了中国新闻传播学主体性的弱化。2007年,韩国著名传播学者姜明求教授与笔者交流时,谈及韩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他反思道:韩国传播学研究陷入西方中心主义陷阱,失去了自身的理论主体性。如今,反观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不难发现:今天的我们同样也在重复着韩国传播学界的故事,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西方新闻传播学话语陷阱,甚至到了离开西方新闻传播学话语,似乎我们在理论上就不会说话的地步。这种对西方学术话语的重度依赖,已经将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引入了偏离中国现实语境的路径上。
不可否认,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建设不能离开外援,就像我们当年主流新闻传播理论话语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这一强大外援一样。问题是他山之石,未必能攻玉。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一直存在自主性不足问题,这固然与这个学科还比较年轻有关,关键在于理论创新不足,很多理论框架靠其他学科以及国外“接济”。新闻传播学领域不是一个理论自足的专业领域,新闻传播理论自身缺乏一个结构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地盘并不牢固。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理论资源很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真正由中国自己原创的理论资源更为稀少。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大量引入促进了国内新闻传播理论的话语转型,但这种外来理论资源如何实现“在地化”、“本土化”,业已成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一大焦虑。毕竟,根植于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是一种“他者”知识,其内生于西方问题语境,将其挪用到中国语境,成就其理论效度的前提条件以及约束变量均发生了变化,若不假思索地直接套用,反而会遭到“他者”理论的反制。其实,在理论上有力解决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的重大命题,其贡献就不只是“地方性知识”,而是世界性的,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责任和理论自信,也有能力做到。仅靠这些外来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无法有效解释中国场域的实践命题。理论创新不是闭门造车,满足于理论自转乃至空转,而要有力回应时代命题。外来理论资源须转化为内生资源,与中国语境对接,内化为中国理论话语的自身逻辑,方能体现理论的活性。否则,外来理论瓷砖贴在中国问题的外墙面上,看上去很美,但不能解决实践问题,更谈不上回应时代的重大命题。
溯源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进路,不难发现:我们所依附的“他者”知识理论,其自身就存在学科主体性不足和创新能力不济的问题。就以我们新闻传播学中“外援”最多的传播学领域而言,其知识体系、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主体来自于西方,而对美国传播学的依赖尤甚。在中国历经四十年历程,传播学已经部分地融入或整合到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知识系统中。这里面包括传播学的很多理论模式以及研究方法,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面貌和知识架构(吴予敏,2018)。其实,这种“依附之路”是狭窄的,且路基松软。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西方传播学本身也存在身份的尴尬和主体性不足问题,以美国的传播学问题尤为显见。传播学身处多学科交汇处,受到多学科话语的影响,受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多重影响。克雷格把西方传播学理论分为七种传统:(1)修辞学传统,(2)符号学传统,(3)现象学传统,(4)控制论传统,(5)社会心理传统,(6)社会文化传统,(7)批判传统(Craige,1999)。在这种情境之下,传播学如何自处?这成了传播学与生俱来的艰难选择。传播研究不但没有成为统摄性的中心理论,而且边缘如故,只能继续拼命争取中心的承认。主体性缺位,致使传播学常常处在“他者”中左冲右突,难以自处,更难自立。李金铨(2014)曾对美国传播学作出“内卷化”的诊断。他指出,早在1970年代,美国传播学界密集出现以下的“理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知识鸿沟(knowledge gap)、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认知共同适应(co-orientation)、第三者效果(third-person effect)、涵化(cultivation)、框架和铺垫(framing, priming)、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等等。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不等,有的一开始就有气无力,有的刚提出时颇有新意,但因为长期孤立使用,过劳而透支,很快呈现疲态。何况连这类“内部理论”也长久不见有人提出,而整个学科生态又满足于划地自限,不作兴跨学科互动,其理论贫瘠的尴尬境况可想而知。传播学“内卷化”(involution)问题表现为:学者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佛躲进自筑的一道围墙,得到心理安全,拒绝与外界来往的压力,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李金铨(2017)先生提醒,向西方学习,须趁早提醒自己:一方面追求专业的严谨规范,一方面谨防落入过度专业化而划地自限的陷阱,以致异化为技术化、碎片化、孤岛化的窠臼。
西方传播学主要有三种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这三种研究范式正是依照方法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区分彼此的(丁方舟,韦路,2017)。研究范式背景下的传播学知识生产意味着:传播学的知识谱系本身充满了张力,不同学科背景和知识规范之间充满了话语权力的竞争和碰撞。如果把传播学的这种张力带到中国新闻传播学场域中,其张力就更大了,难以用统一的知识共识和范式标准,对各自为政的知识“孤岛”进行整合。
回归中国现场,回应时代之问
新闻传播学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性学科,现有的学科实力、学术贡献度以及话语能力与这场深广的社会变革所提出的吁求比起来,还有不小的距离。虽说其他学科同样存在这样的差距,但新闻传播学的紧迫性更强,这是因为新闻传播学已深处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影响当中。新闻传播学面临的问题场域被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革命打开了全新的疆域,新闻传播学从来没有遭遇过现今这么深刻且广泛的冲击和挑战。这些冲击和挑战使得原先那些确定的理论命题需要修正、升级和完善,甚至会给原有的理论话语存量带来颠覆性的冲击。面对新的媒体现实和高度媒介化的世界,如何从中穿越而过,进而把握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性?在资讯严重过剩,社会现实与虚拟世界交叉渗透,在“无社交,不新闻”的“后真相”时代,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揭示真相,满足人民全面客观正确地理解中国和世界的需求?如何对关联变量发生了几何级数增长的复杂媒介系统进行理论提炼和概括,增强理论的硬度,让理论变得有解释力和预见性?如何让理论更好地指导媒介实践,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回答这些问题,都离不开新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创新。
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抽象,它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一个理论若不能回应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理论的合法性就会踩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创新乏力,首先表现在:理论研究对生生不息的新闻传播实践缺乏有力的回应,尤其是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鲜有正面、有力的回应。当下中国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而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变化更为深广。中国社会转型正面遭遇以新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传播革命。这双重变革叠加在一起,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对当下中国构成重大影响。传播系统作为连接社会系统各个器官的传感系统,其功能不限于局部,而在全局。如今,中国传播系统的内涵、结构、功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要求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能够跟进新闻传播实践的深刻变革,有力回应来自实践的挑战,回应时代之问。
但是,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在这方面恰恰与发生剧烈变革的实践存在极大的落差。造成这种落差不能简单归咎于新闻传播学界自身,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第一时间关注着实践的潮汐涨落,那些批量生产的研究成果,皆是我们新闻传播研究者在海边捡拾的知识贝壳,其中有不少亮点之作。问题是,新闻传播实践变革太快,影响太深广,这些都远远超出我们现有的理论能力极限,现有的理论存量难以承载超重的实践问题。在巨变下的新闻传播实践面前,现有的理论支点已经支撑不起。一些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分析逻辑远远透支,不能系统、有力地解释实践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结果是,我们多在理论上“打补丁”,在原有理论“孤岛”上守望,未能建构一个相对强固、完整的理论“岛链”,以回应来自实践的空前挑战。来自实践层面的困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来自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理论研究去探讨,而我们的新闻传播理论并没有在这个理论期待甚为迫切的时段展示出应有的理论光芒和锋芒。
几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理论资源上做“增量”,努力把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移植到中国来,造成了中国新闻传播理论资源的快速繁殖,但这种去语境化的理论移植,与中国问题缺乏根本性的关联,理论缺乏“在场”感。表面上看,似乎我们不缺少理论,别人有的,我们这里也会有,问题是,这些理论“浮标”不是内生于中国语境,与中国问题缺乏结结实实的关联,致使一些在西方颇具理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到了中国语境就沦为空洞的学术修辞。这种游离于实践之外的理论生产,被有些学者认为是“言语的学说”,是一种“炫耀性的理论工作”。不少新闻传播理论仍在“内河”中兜圈子,没有产生与中国社会大转型、新传播革命相匹配的大理论来。新闻传播理论话语多是由若干学科话语板块拼合而成的,不同板块之间的接榫不够严实、周到,导致话语割据现象甚为突出,这不仅导致话语体系的难产,也难以形成大逻辑上的有机建构,更谈不上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了。
构建基于中国语境的话语体系
习近平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从新闻传播学研究来看,如今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面临空前的挑战,现有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供给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理论创新的质量上——凭借现有的理论供给,无法回应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系列挑战。新闻传播学研究必须回应时代的呼唤,从大的理论逻辑层面着眼,重构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我们的理论不能满足于在微观层面修修补补,应以结构性、系统性的理论创新,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建构开启理论大格局。
时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到了“关键时刻”。在这“关键时刻”,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需要着力解决“不充分”、“不平衡”问题:
一方面,要做“加法”。在新闻传播实践领域,面对问题的井喷和传播系统的非线性扩张,认知不确定性的集聚,关联变量的激增,新媒体技术的快速迭代刺激了知识的激增和信息的无序扩张,知识界对于未知领域的探求任务愈加繁重。面对不断延展的未知领域,我们必须做增量,尤其是要在硬知识上做“加法”。在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存在甚多“灵感式”的“临场发挥”,尤其是那些“老运动员”,对这种中国情境下的“实践感”并不陌生。中国当下新闻传播学研究,需要调动这些能动性知识,发掘每一个精彩场域背后的“小逻辑”,建构我们自己的“主体性知识”,在此基础上,最终构建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话语体系。这套理论话语体系应内生于中国情境,可以有效回答来自实践的重大命题,与中国新闻传播实践无缝对接,它来自于实践,也能引领实践。
另一方面,需要做“减法”,挤水分。面对大量的“散装”知识,一方面要去“库存”,去“低端知识产能”,提升知识浓度和硬度,同时需要强化知识的“语法”提炼。从知识生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变知识“弱连接”为“强连接”,提炼新闻传播知识语法,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
建构中国新闻传播话语体系,须立足中国语境和文化传统。有学者在反思中国传播学时,提出了十分到位的见解。李彬(2015)认为,反思中国传播学也好,重构中国传播学也罢,归根结底无不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逻辑,正如美国传播学无不基于自身历史传统与文化逻辑而繁衍生息。因此,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中国,才能明白传播何为,学问所在。吴予敏(2018)指出,重构中国传播学,需要中国学人深入具体的历史时空和动态过程,去发现、辨析、阐释和建构知识系统;必须牢牢把握本土文化情境和脉络,通过感知和实践投入中国本土的生活世界的创造过程,在和历史与现实的交互经验中进行理解和诠释,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观念的层面讨论。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更应基于中国问题语境,不能迷信去意识形态化的客观知识和普世价值。新闻传播学知识作为社会性的科学研究,按照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三个范式去归类,其中每一个范式下的知识生产都不是在零度价值下操作的,只要是社会性的知识,都不可能是去意识形态化的,难以脱离社会语境去提纯知识。诚如布迪厄(2004)在反思社会学时指出的:社会学是具有显著政治性的科学。原因在于它极为关注符号支配的各种策略和机制,并融汇于中,环环相扣。社会科学不可能保持中立的、超脱的和无政治意义的立场,它永远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所具有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地位。社会学越是科学,它就越是与政治相关。中国新闻传播学不可能与意识形态性绝缘,正如西方新闻传播学不可能与意识形态性绝缘。吉登斯(2013)认为,意识形态必须与它嵌入其中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且还必须考虑在特定的社会中,是何种因素决定了哪种观念能够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观念并不会因为其自身的缘故而演化,只是在当它们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意识中的要素时,它们才会发生演变,而且遵循着特定的实践路径。事实上,正因西方新闻传播学带有精致的价值滤镜和隐蔽的意识形态底色,这要求我们在搬运他山之石时,须多些心眼,不能误把他乡作故乡。当然,我们强调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不能迷信西方知识理论,超越西方霸权并不意味着“义和团”式的反叛和“返祖”。李金铨(2017)教授有言:不反对建构“非西方”模式,但前提是理论必须开放,愿意和西方平等对话,断不能像原教旨派似的,假设“非西方”天然占据道德高地,因而走向批判对象的反面。此言是及时的提醒。
当下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佳时期。在这个时期,需要各个学科超越学科域限,回应时代呼唤,回归对“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立体观照,实现整体性理论创新的整体性“爬坡”。新闻传播学研究者身处新传播革命语境下的中国现场,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话语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今后的理论大突破做了很好的准备,接下来需要整体发力,把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话语体系提升到与时代匹配的高度。■
参考文献:
安东尼·吉登斯(2013)。《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丁方舟,韦路(2017)。《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及其演化》。《南京社会科学》,(3)。
哈罗德·布鲁姆(2006)。《影响的焦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彬(2015)。重思中国传播学。《当代传播》,(4)。
李金铨(2014)。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书城》,(2)。
李金铨(2017)。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开放时代》,(3)。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2004)。《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吴予敏(2018)。“重构中国传播学”的时代场景和学术取向。《国际新闻界》,(2)。
张涛甫(2018)。影响的焦虑——关于中国传播学主体性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
Craig, R. T. (1999).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 Communication theory, 9(2)119-161.
张涛甫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西藏大学特聘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的历史建构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 & ZD3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19AZD046)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