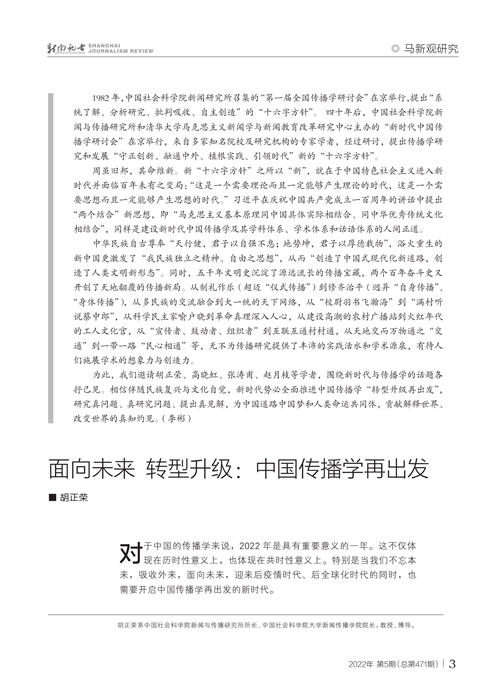面向未来 转型升级:中国传播学再出发
■胡正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集的“第一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京举行,提出“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 四十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办的“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多家知名院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经过研讨,提出传播学研究和发展“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植根实践、引领时代”新的“十六字方针”。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十六字方针”之所以“新”,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两个结合”新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样是建设新时代中国传播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人间正道。
中华民族自古尊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浴火重生的新中国更激发了“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而“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五千年文明史沉淀了源远流长的传播宝藏,两个百年奋斗史又开创了天地翻覆的传播新局。从制礼作乐(超迈“仪式传播”)到修齐治平(迥异“自身传播”、“身体传播”),从多民族的交流融合到大一统的天下网络,从“校尉羽书飞瀚海”到“满村听说蔡中郎”,从科学民主家喻户晓到革命真理深入人心,从建设高潮的农村广播站到火红年代的工人文化宫,从“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到互联互通村村通,从天地交而万物通之“交通”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等,无不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丰沛的实践活水和学术源泉,有待人们施展学术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为此,我们邀请胡正荣、高晓虹、张涛甫、赵月枝等学者,围绕新时代与传播学的话题各抒己见。相信伴随民族复兴与文化自觉,新时代势必全面推进中国传播学“转型升级再出发”,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提出真见解,为中国道路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真知灼见。(李彬)
对于中国的传播学来说,2022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不仅体现在历时性意义上,也体现在共时性意义上。特别是当我们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迎来后疫情时代、后全球化时代的同时,也需要开启中国传播学再出发的新时代。
一、中国传播学出发的历史意义
我国大陆新闻学界第一次跟西方传播学者进行正式的交流,并且进行直接的对话是在1982年4月至5月。在这期间,美国传播学代表人物之一施拉姆在他的学生余也鲁陪同下访华,并在人民日报社主楼顶层的大礼堂,做了一个传播学的学术报告,参加报告会的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当时称新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部分高校教师,还有媒体从业人员等数百人。报告后还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虽然,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学者译介海外新闻学与传播学新思潮、新研究,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也陆续在一些内部刊物发表译介文章或者以内部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译著,但是多是自发的、零星的介绍。因此,这次西方传播学者的正式报告和交流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学界第一次正式而直接地与西方传播学者进行的学术对话。
上世纪80年代初,也是改革开放之初,大家对海外各种学术或者新闻传播实践都非常好奇,也非常感兴趣。因此,此次交流激发了中国新闻学界的学术热情。随后,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这次会议后来被学界称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也正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者讨论并确立了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既表达了改革开放,兼容并包的胸怀,更表达了希望推进传播学本土化的强烈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主。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将这次会议上发表的十三篇介绍性文章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成书,名为《传播学简介》,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传播学的著作。1984年,我国大陆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传播学译著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即施拉姆与波特合著的《传播学概论》。随后,一批我国学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相继出现,运用传播学范式进行的学术研究也逐步大量出现,产出了不少有影响的研究与成果。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早期的传播学引介更多还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为主的传播学的研究,而且基本上都是美国经验研究的流派。我们也不能忽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有国内学者介绍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与成果,更有上个世纪70年代,批判学派代表性人物之一达拉斯·斯迈思来华访问,并广泛实地调研,还写出了基于中国调研的学术作品。
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大陆确立合法性地位是在1997年。这一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中将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将新闻学、传播学列为下设的二级学科。之后,传播学硕士、博士,乃至本科专业都开始设立并招生,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科研站等也陆续建立。
过去四十年中,中国传播学界做了大量的工作,卓有成效。一个方面是不忘本来。在系统介绍海外传播学的同时,中国学者就已经开始对本国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中的传播现象与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对华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的研究,这些年来蔚然成风。另外一个方面是吸收外来。四十年来一直就没间断对海外优秀研究成果的系统而批判性吸收。系统译介、海外学者交流合作、中国学者海外传播等各方面都做得扎实而有效。现在,国际舞台上主要的几个传播学学术组织及每年的学术交流活动中,都能够看到中国学者的身影,他们越来越成为参与传播学国际学术平台交流的主力军之一。在ICA、IAMCR以及区域性的国际大会上,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在讨论议题的基础性和前沿性,研究的广度、深度方面不断提高,在学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已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股重要的学术力量。再一个方面是面向未来。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我国新闻传播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如此丰富而具有开拓性的实践,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滋养。特别是在互联网及其应用方面,中国快速发展的庞大市场提供了众多的实践话题与问题,这些都促使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立足本土,对前沿性、基础性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面向未来的研究无论在紧迫性和必要性,还是在适用性和创新性方面都是当务之急。简要来说,过去四十年,我们走的这条道路还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而且形成了高质量的研究和实践。
二、中国传播学再出发的时代意义
近些年世界格局的变化,让人们深切体会到,人类社会正在开启一个后疫情时代,正在进入一个后全球化时代。两个时代交织,我们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或者说是力量叠加、力量转换的时代。所以,我们如何面向未来,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是非常关键的。这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再选择和再出发,而且是对中国传播学界提出的一个命题——中国的传播学面向未来需要做哪些转型和升级,成为摆在学界业界面前共同的话题。
面向下一个四十年,当下中国传播学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升级迭代时期。之所以这样认识,主要有以下两个考量:
一个是历史考量,即历史范式在转型。就全球格局看,我们习以为常的工业化带来的全球化体系,及其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工业社会全球化框架之内的理论、法则、定律都正在被改变着。基于竞争和自我利益驱动的贸易与交流的全球化模式日益难以适应正在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复杂世界和复杂社会。百多年来的工业社会全球化产生的众多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日益凸显,协作、协同、合作、共治才能创新全球化新模式,这恰恰与基于互联网的、网络社会的后全球化或称新全球化的底层逻辑相符。三年来的疫情治理就是这种历史范式转型的典型案例,也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人类社会需要回答的新问题和面对的新挑战。疫情特殊时期终将过去,人类一定要重启社会,进入后疫情时代,那么,众多问题都有哪些,解决问题的答案或者方案都有哪些,这些问题导向的解决方案所导向的后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需要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各学科学者给予全新的发现、认识、解释、驱动和引导。就国内格局看,我们进入发展的新时代,踏上新的征程。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正在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要求,“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对于中国的传播学者来说,更亟需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三大体系,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坚持的思路。
另一个是历史背后的逻辑考量,即理论与实践范式转型。透过上面说的历史范式在转型,我们深入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支撑这种历史重构的逻辑、理念、方式、方法以及制度安排与操作,都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支撑这个历史范式转型的必然,特别是在过去疫情发生的年代,理论和实践范式的转型在全球范围内都正在发生,而且转型的领域与层级也逐渐清晰。比如,就全球发展模式而言,有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也有逆全球化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操作。从这种差异可以看出两种国际观的不同,即全球主义与新全球主义。原有秩序与规则、运行与实践都正在被打破。比如,极化的社会现实使得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实践日盛的同时,国家主义也在寻找着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现实实现。与此同时,民主的实践形式也出现多样的选择,从工业时代的代议制、协商制,进入网络时代更为可能也更为必需的直接参与制。再如,就经济发展阶段而言,工业革命4.0或类似理念与做法正在成为各国经济进步的核心动力,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全球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较为普遍的认识是这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信息的聚合、传播、使用和分享,出发点是人脑的解放与深入了解人类的自身行为,终极目标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改变并重塑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价值。人类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可能都要改变。比如,就互联网带来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言,由平台经济驱动着平台社会的形成。正在到来的互联网3.0,不少理论和实践都认为这将去中心化。不过,网络与平台社会的去中心化与中心化,或者再中心化是并存的;扁平化与再层级化也可能是共生的;共同体与族群或者圈层分化也是同在的。诸如此类的现实与理论范式的转型升级与更迭其实意味着一种力量在转化,同时代表着一种价值在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可能就需要政治秩序、经济模式、社会建构与文化形态的重塑与重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时,指出要看到“西强我弱”中“东升西降”。这种认识放在中国传播学发展中也是适用的。上述理论和实践范式的转型升级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从底层逻辑来讲已经不是工业时代,急迫需要学界将我们丰富的新闻传播现象、经验与实践进行概念化、范畴化,然后把它架构化,最终普遍化,这样传播学可能就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全球普遍性。虽然西强我弱的大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当前的概念体系、范畴体系和研究方法,包括表述的方式仍然不少是“西强我弱”的,但是要看到东升西降趋势非常明显,学术界、业界都要避免自话自说、自娱自乐。
中国传播学的确到了再出发的时候了。基于过去四十年的引进、吸收、消化以及自主研究的开发、深入与拓展,我们的传播学研究需要突破模仿的、复制的、对已有理论的中国实践的重新证明,以及自发的、零散的、表象的、经验的、先验的研究,需要立足我们的实践,放在全球传播生态的格局变化中,基于迭代升级的基础逻辑转化,进行我们的研究。我们知道,美国的传播学是基于美国现实需要和目的,形成了经验研究传统;而欧洲的传播学则是基于欧洲不同国家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生长出了批判研究的学术大树。因此,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植根中国实践,中国传播学也需要关注真现象,研究真问题,解释真原理,发现真规律,提出真方案,厘清真方向,构建真格局,创新真体系,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学术贡献。
四十年前,中国传播学刚刚出发的时候,曾经提出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历经四十年发展的中国传播学在新时代肩负重要职责使命,基于学界的对未来的期待,我建议需要提出新的“十六字方针”,对未来中国传播学予以导引,这就是“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期待新“十六字方针”成为面向未来的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一个指向,或者是一种价值取向。期待中国传播学面向下一个四十年再出发,以中国传播学的创新发展迎接全新的面貌和全新的时代。■
胡正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