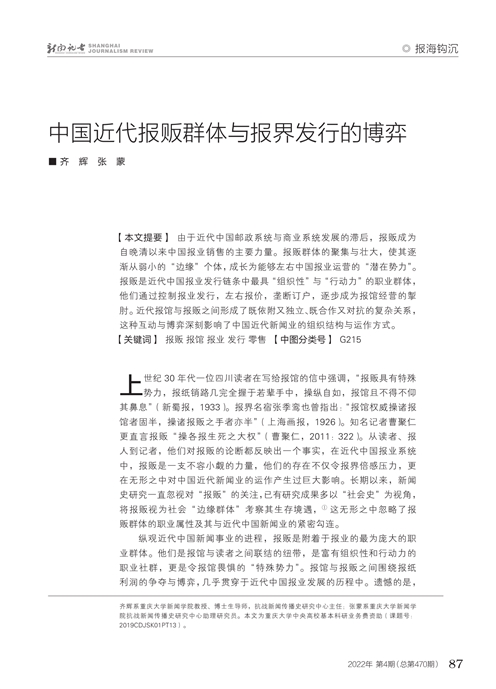中国近代报贩群体与报界发行的博弈
■齐辉 张蒙
【本文提要】由于近代中国邮政系统与商业系统发展的滞后,报贩成为自晚清以来中国报业销售的主要力量。报贩群体的聚集与壮大,使其逐渐从弱小的“边缘”个体,成长为能够左右中国报业运营的“潜在势力”。报贩是近代中国报业发行链条中最具“组织性”与“行动力”的职业群体,他们通过控制报业发行,左右报价,垄断订户,逐步成为报馆经营的掣肘。近代报馆与报贩之间形成了既依附又独立、既合作又对抗的复杂关系,这种互动与博弈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新闻业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
【关键词】报贩 报馆 报业 发行 零售
【中图分类号】G215
上世纪30年代一位四川读者在写给报馆的信中强调,“报贩具有特殊势力,报纸销路几完全握于若辈手中,操纵自如,报馆且不得不仰其鼻息”(新蜀报,1933)。报界名宿张季鸾也曾指出:“报馆权威操诸报馆者固半,操诸报贩之手者亦半”(上海画报,1926)。知名记者曹聚仁更直言报贩“操各报生死之大权”(曹聚仁,2011:322)。从读者、报人到记者,他们对报贩的论断都反映出一个事实,在近代中国报业系统中,报贩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他们的存在不仅令报界倍感压力,更在无形之中对中国近代新闻业的运作产生过巨大影响。长期以来,新闻史研究一直忽视对“报贩”的关注,已有研究成果多以“社会史”为视角,将报贩视为社会“边缘群体”考察其生存境遇,①这无形之中忽略了报贩群体的职业属性及其与近代中国新闻业的紧密勾连。
纵观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进程,报贩是附着于报业的最为庞大的职业群体。他们是报馆与读者之间联结的纽带,是富有组织性和行动力的职业社群,更是令报馆畏惧的“特殊势力”。报馆与报贩之间围绕报纸利润的争夺与博弈,几乎贯穿于近代中国报业发展的历程中。遗憾的是,对于报贩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纠葛,已有研究成果尚缺乏系统的梳理和讨论。有鉴于报贩在近代中国报业发行销售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尝试以史料为基础,梳理该群体的职业成长及其与报业的博弈,从一个侧面呈现中国近代报业发行所面临的复杂境遇与生存状态。
一、从“派报”到“贩报”:近代报贩群体的聚集及其组织化
近代报贩群体是“持卖报为生活者”(陈荣广,1919:113),他们是专以贩卖报纸为生的社会职业群体。中国近代报业发轫之初,报馆多不负责发行业务,商业报馆除“直接定户”外,报纸发售主要仰赖于报贩。这种形式是“报贩按照批发价钱向报馆批购”,随后按照一定的区域路线,或街头叫卖或摆摊零售,从中赚取差价。除街头零售外,报贩还承揽“家庭订报”业务并负责“每日递送”,“月底自己收账”,盈亏“与报馆全不相干”(詹文浒,1946:123)。报贩承揽报纸发行是自晚清以来中国报纸发行的主要模式,报贩也因此成为近代商业报馆与读者之间难以逾越的中间环节。
关于报贩形成的渊源,有学者认为始于明清交替时的“报夫”或“报差”。明末清初北京曾出现以“送邸报为业”的报夫(洪煜,2008)。据清代《报局规例》记载,清末时期《京报》编印之后皆由“报房”指派专人发送,“发结送报之人,分路送往各看报之处”(内藤乾吉原校,1987:1)。据戈公振考证,清代《京报》在外地的贩运有“专人”负责,“时有山东登属之人,负贩于西北各省,携之而往,销行颇易”(戈公振,2018:33-34)。另据报人钱伯涵记载,晚清“同光之季”“只有报馆专雇的人,把每日所出的报纸挨户分送”,由于报纸“多系赠送”,故报馆“收取报费至为困难”。当时国人多视报纸为“一种无聊的东西”,报贩群体的规模亦有限(钱伯涵,孙恩霖,1940:101)。
洋务运动时期,随着上海商业报纸的繁荣,报贩遂突破单纯的“送报”范畴,开始涉足报纸零售业务。这一时期报纸“发行份数逐渐增加”,“报馆始指定承包的人,分给报贩去兜卖分送”(钱伯涵,孙恩霖,1940:101)。1872年《申报》在差人送报之外,另雇他人沿街进行售卖(申报,1947),销售模式的创新引发了上海同业的仿效。有学者推测,自1895年前后报贩已对上海报纸零售市场“渐成霸占的局面”,其规模约有“数百人”,他们控制了固定的销售地段与订户资源,上海各报若想打开销售局面,已不得不求诸报贩。据史料所载,上海知名报纸《新闻报》发行之初曾请求报贩组织“代为推广”,报贩提出“要比销《申报》、《字林沪报》高一点的批发折扣”,遭到拒绝。《新闻报》另雇“贫人之失业者报童若干人……沿街零售”,但他们无法进入被老报贩盘踞的“茶楼烟馆”,报纸销售惨淡。迫于竞争压力,《新闻报》老板斐礼思不得不“急为转圜”,通融报贩头子,方才化解危机(马光仁,1996:92)。该事例表明,19世纪末上海报业内部激烈的价格竞争,加速了报馆对成本控制和报纸销量的依赖,促使其将报纸销售业务外包给“报贩头子”负责。清末民初之际,报贩职业已被社会各界广泛承认,“缘今日各日报,其发行本埠之报纸,均由贩报者先时订定,或由一人呈报,已为今日沪上一种专业”(姚公鹤,1989:127)。
早期贩报人数少,其街头售报多以生存为动机。随着报贩从业者益众,报贩内部的倾轧与分化亦逐渐加剧,一批拥有和控制众多报贩的“报贩头子”(简称“报头”)开始出现。报人詹文浒曾这样描述“报头”:“中国社会的一种剥削风气,在报贩群体中亦非常盛行。几个老奸巨猾的报贩头子,手下率领一批小报贩,每天替他派报和赚钱,而他自己则坐享其成,他唯一工作即为依赖地方恶势力,对报贩剥削,对报馆敲诈,这是正义的报馆和记者最不能容忍的事”(詹文浒,1946:124)。“报贩头子”借助控制和剥削底层报贩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派报网络,具备了与报馆分庭抗礼的实力。
清末在“报头”带领下,报贩垄断报纸发行的同时日渐“组织化”。在上海的“财源楼”茶馆原为“信局诸客汇集之地”,报贩每日代报馆送报于此,借此垄断了本埠报纸的外销业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固定的“贩报茶会”。1911年在“报贩元勋”陆行逊的率领下,报贩茶会进一步统合为“捷音公所”,重新制订“行规”。公所内部,通过协调大报贩利益矛盾,保护小报贩权益等措施树立了威信,此后又拥有了合法社团的身份,报贩的组织化极大地提升了其与报界抗衡的话语权(申报,1927)。
事实上,出于成本控制和增加销量的考量,早期报界曾是报贩组织化的推手。考察上海及北京等地报贩组织的形成,均有报界助力的身影。民国初年,上海报贩筹建“捷音公所”之际,《新闻报》主笔孙玉声曾解囊襄助,甚至被报贩推举为“公所”负责人之一(上海市政协文史委,1996:260)。此时的报界尚未意识到报贩组织壮大对日后报业发展形成的反噬。到20世纪上半期,上海“每一个派报人,无论你是送一份报,或是在马路上卖出一份报”,都必须是捷音公所的成员,否则“休想踏入这个(卖报)生意的门槛”(华文大阪每日,1940)。对外,捷音公所以社会组织示人,实则是各种“势力”相互盘踞的封建行会。在旧上海,各种政治及社会势力都与捷音公所过从甚密,相互之间的利益纠葛与权力渗透可谓盘根错节(洪煜,2019)。捷音公所的首脑是具有雄厚资本的大报贩,他们把持公所业务称霸一方。民国初年,在上海报业中心“望平街”逐步形成了以王春山、蒋润卿、陆开廷、张阿毛为首的报贩“四大金刚”。他们利用排他性的垄断经营,相互倾轧,巧取豪夺,逐步瓜分了各大报馆的客户资源,形成了对报业市场的牢固控制,从中赚取巨额利润。
与上海不同,北京报贩群体的聚集则脱胎于传统报房的报夫。晚清时期,北京形成了“聚兴”、“聚恒”等六家老字号“报房”。这些报房共用一支400余人的报夫队伍(北平实报社,1936:892)。他们身着“蓝衫”,划区送报,互不相扰。庚子之变后,随着北京商业报馆日盛,传统民间报房乃顺势转变为“各报之推销所”,专门负责报纸派送,“报房有谙练之报夫,固有之定户,各城各路分配差役,各有专职,俗称‘报道’,无论新、旧报馆皆利赖之”(池择汇,1935:621-622)。然而,这六家报房结成的送报联盟,不仅对北京各报馆收取高额送报费,还经常使用“砂片钱”(即赊账白条)拖欠报款,在京各报馆“皆感于不便使用之苦”。据梁漱溟回忆,北京知名报人彭翼仲的《京话日报》就曾“托报房代为发行”,后因“备受旧报房之欺”,遂改为自办发行。
到民国初年,“新民社”于北京南柳巷永兴寺内创立“报市”,此后将各报发行皆集于此地,彻底打破了报房送报的“专利”。通过批发,零售报纸的新型报贩成为在京各报销售的主力(申报,1947)。“无论风雨寒暑,清晨五六时”,北京各地报贩即聚集于南柳巷一带,“各按所需之报分别配购(报纸)”,至上午9时报纸即可遍布京城(池择汇,1935:623)。在天津的南市广兴大街一带亦形成了所谓的“新闻市场”,津门各报馆指定的“派报社”每日七八点钟将报纸批发给报贩,经其分拣之后,随即沿街叫卖(刘炎臣,1943:82)。在杭州,1917年已经成立了由全市37家报馆组成的派报公所,每报雇佣专职报贩1至2人,每月工资7到10元,负责每日“晨报”的派发,至上午9时前,杭州当天的报纸已经可以“遍布全市”(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课,1932:79)。毋庸讳言,民国初年报贩售报作为一种高效且成本低廉的销售方式,已普遍被各地报馆所接受。在此过程中,报贩也从分散的个体经营向群体化和组织化积聚转变,形成了具有封建“把头”性质的垄断组织,逐步成长为与报馆分庭抗礼,争夺报业资源的重要力量。
二、从“共生”到“博弈”:近代报贩与报纸发行的互动
(一)共生与合作:报贩与报馆互为依存
报贩以贩报为业,报馆盈亏与报章质量都会直接影响报纸销售,进而关乎报贩的利润与收入。与此同时,报贩的销售技巧、叫卖水平,亦与报纸的发行销量密切相关,从而左右报馆生存,共同的利益促使报贩与报馆之间形成了一种休戚与共的合作关系。
民国时期,报贩销售报纸主要有批发、设摊和叫卖三种形式。批发多由大报贩指派专人从报馆批来报纸再分售给其他中小报贩。20世纪30年代,北京专职批发报纸者,日收入“五六角钱,一月亦不过十六七元,能赚到二十几元收入的,就算是出类拔萃了”(大同报,1936);零售报摊多设立在电杆或店铺前,摊位各有地段,“不得随意占据”。做报摊生意也需要一定本金,个别地方的报摊租金之高有时令人咋舌。上世纪20年代“上海三洋经桥一报摊”,因地处黄金地段,摊位费高达每月60余元,同时“还需要缴纳三四元站岗巡捕月规”(远东饭店日刊,1926),这在当时堪称天价。这类报摊除了售报外,还会“兼卖口罩、耳挖、居住证夹、鞋垫等”(刘炎臣,1943:82),因而收入颇为可观。沿街叫卖则是最为常见的贩报形式。报贩多从大报贩手中赊购报纸,无需多少本金投入便可进行销售,因其入职门槛低,无资金压力,而颇受底层民众择业的青睐。这类报贩人数众多,终日走街串巷,收入微薄,每日得资不过仅能“糊口”(新天津,1933)。
对于贫寒的底层报贩而言,依附报馆售报往往是其“唯一的生路”,如果报馆关张,底层报贩可能陷入衣食无着的境遇,因此在报馆有难之时报贩偶尔也会与之共同进退。1931年一家名为《新天津》的报纸,因言获罪被勒令停刊。该报在当地影响甚众,销量可观,报纸停刊直接影响到天津近七千名报贩的生计。有报贩称,其平日两餐费用来源即靠卖《新天津》早晚两报来维持。报纸的停刊不仅令报贩“叫苦连天”,更有不少人“改营他业”(新天津,1931)。为生计所困,天津报贩为该报复刊奔走请愿,天津当局遂被迫恢复了《新天津》的发行。此后,报贩“集腋成裘”,特制作两方匾额送与报馆,以示庆贺。由此可见,报贩与报馆有着唇亡齿寒的依存关系。
在报贩组织形成之初,报馆报纸的销量多仰赖于报贩保障。民国时期,报贩按照批发价钱向报馆批购报纸,随即按照固定路线,沿街叫卖。倘有家庭订报,报贩亦按照零售价出订,以后按日递送;到了月底,报贩自己收账,整个销售过程“与报馆全不相干”,报馆因此可以专心于报纸的内容生产,不必为报纸发行和销售增加投入。报贩则“自己是老板”,身份独立于报社,其收入直接与报纸销量和订户多寡挂钩。为了获取更多收益,报贩往往用尽浑身解数兜销报纸,千方百计保留并增加订户资源。经营中报贩对各类客户都“特别客气”,“服务亦特别周到”(詹文浒,1946:123-124)。在资金结算上,报馆与报贩多为现金结算,即使“偶有拖欠亦必月底结清,极少周折”,从而降低了报馆的经营风险与资金压力。报贩组织借助成熟的销售渠道与人脉网络,增加了报纸的发行数量和发行效率,“大为减省”了“报馆的用人与开支”(詹文浒,1946:124),这些便利都使得报贩组织的存在曾颇受报界的认可。
报界在扶植报贩组织壮大的同时,亦形成了对该组织的依赖。在上海,新报发行若想拓展市场,唯有仰赖报贩组织的帮助方有机会。据报人回忆,“每当新报出版之始,必先邀宴报贩头目,藉资联络,而求推销,日销若干份(最少亦一两千份),商议既定报纸始能见于市面,并先约日。报纸涨价须看风色,且俟通知,倘报馆当局见销路甚佳,自行增价,则报纸销路,立即惨落,每每跌至一两百份”(微闻,1933)。利用报馆弱点,报贩在与报馆合作过程中,逐渐掌握了销售发行的主动权。民国时期,报馆经营和生存越来越依赖于报贩的资源,合作天平的倾斜,导致双方矛盾激化,缠斗不息。
(二)冲突与对抗:报贩群体与报馆之间的利益博弈
近代报馆与报贩围绕着报纸发行利润与读者资源的争夺,曾是中国近代报业史上十分常见的一幕。报贩群体凭借对订户资源和销售行为的掌控,经常干预和操纵报馆的经营,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1.垄断发行
报人詹文浒指出,民国报业的发行和销售,其制度设计之初即是以报贩为主导建立的。“报馆的发行基础,完全建筑在报贩身上”,报馆缺乏对报纸发行和定价的主导权。不仅“报纸要涨价,须得征取报贩的意见”,甚至报纸“减少篇幅或酌减印数”,“事前亦须征取报贩的意见”(詹文浒,1946:124)。民国时期,上海报馆的发行被陆行逊及“四大金刚”长期挟制。凡在上海经营的报纸,“必然要与他们合作”,否则报纸的“销路便没有把握”(申报,1937)。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望平街之“四大金刚”便垄断了上海报业的销售业务,报纸若想获得“大宗销数”,“必赖望平街之报贩”,“托一有势力之大报贩包揽代发”,报馆不能自行发行(常识报馆,1928:37)。报纸发行中,报馆一旦选择某一报贩代理业务即“不能换别人”再行代理,进而形成对报纸销售的“垄断”。对此,有报馆曾哀叹,“只要你的报纸到了他的手里以后,他便可以随便指挥。他要欠钱,你也奈他不得。你如果想换了一个人,那么别的报贩也决计不接受的”(常识报馆,1928:37)。
报贩对报纸发行的垄断掐住了上海报业的“命门”,报馆一但与报贩发生矛盾或“措辞不慎”,即有“报纸销数俱毁”之灾(詹文浒,1946:124)。在报贩垄断报纸经营的“行规”中报贩的“权力颇大”。行规约定,报馆“每出一报,必须预先知照,否则不销”。在北京报贩约定,“发结送报之人,分路送往各看报之处”,“其报亦各有地段之家,不得擅越”,违者重罚(内藤乾吉原校,1987:1)。上海捷音公所的行规则强调:“定户不得争夺”,“各有一定之范围”。若有报馆胆敢破坏报贩行规自办发行,找人替换原有报贩“包批”报纸,“那么必(招)致一场大格斗”。报馆轻则遭受恐吓威胁,重则遭到报贩组织的集体封杀。上海《新闻报》在创办之初,因不满报贩“批价”,另雇他人售报,结果刚上街头即遭到威胁和殴打,报纸被撕毁数千份。《新闻报》被迫聘请上海“报头”陆行逊担任发行,报纸销售才得以恢复正轨(马光仁,1996:91)。
《新闻报》是具有洋商背景的大报,其经营尚且仰人鼻息,其他地方小报摆脱报贩组织控制则更难。据史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上海“数十家小报的发行权,全为报贩所垄断”(王定九,1934:542)。这些报纸的售卖由报贩组织代理,报馆的发行活动受到极大掣肘。1927年,上海报贩因与报馆在发行价格上未能达成一致,大报贩遂下令“今日各报皆不发行,日报不可专利”,于是当日印好的上海数十种报纸皆无法发售。报界被迫与报贩紧急协商,各报才在9点半后被允许上市发行(小日报,1927)。由此可见,在早期报业市场,报贩组织对于报纸发行的垄断和控制已驾轻就熟。自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内地报业已被“报贩掌握着发行全权”(快活林,1946),只有“很少的都市报纸的发行不是被报贩子把持着,由报贩子来支配报社的”(著者不详,1948:17)。
在报贩组织内部,不接手他人经办的报纸,是整个报贩行业必须“绝对遵守”的规矩。面对来自报贩组织的统一行动,各地报馆的反应却迟钝无力,这令报贩更加有恃无恐。双方一旦产生纠纷,报界多自认倒霉,唯有提醒后来办报者,“初办报纸的时候,应该郑重选人,免得后悔不已”(常识报馆,1928:38)。垄断使得报贩对报纸销售具备了“专利”性,报贩头子即凭此坐享其成,大发横财。他们“每日仅需在早上七八点钟忙碌一下”,“即可写意终日,进款颇巨”(远东饭店日刊,1926)。反观“报社编辑部全体人员不眠不休的劳作所得,尚还不及一个报贩头子的收入”(文化函授学院,出版时间不详:98)。
2.拒卖报纸
报贩对报馆的威胁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大规模拒卖停售报纸来直接实现的。这种针对报馆的攻击,方式虽然简单粗暴,但对报馆的遏制可谓立竿见影。民国时期,即使报馆拥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若得罪了报贩,就有可能被整体封杀,报纸在“市面竟可不见一张”(燕京大学新闻学系,1932:25)。在北京,尽管报馆对报房的送报服务有诸多不满,却都不敢公然得罪报房,因为“一有不和”,“报房便不代送(报纸),报纸即无形停刊”(申报,1947)。此种矛盾使得北京报界与报房的矛盾积怨日深。在上海,收买报贩已是商业报业恶意竞争的惯常手段。上海《商报》发行期间,曾遭受《新闻报》的故意打压。在《新闻报》授意下,报贩组织表面与《商报》合作,实则背地将报纸尽数送到废纸店卖掉,上海市面上见不到该报,使得商业信誉大损,受此挫折,《商报》此后销售惨淡一蹶不振(现代上海市文化馆,1986:67-68)。
民国时期,报贩组织对报纸的态度甚至成为后者能否生存的基本条件。报贩对报业的控制能力使之成为政治斗争的利器,他们时而参与反帝爱国运动,时而又成为政党钳制言论的帮凶,其政治属性复杂且多变。1928年日本在华的《顺天时报》因对华报道歪曲事实、造谣惑众,引发国内反日运动高涨。北京报贩积极参与其中,宣布不再销售《顺天时报》(民国日报,1928)。报贩的抵制导致《顺天时报》月销量从高峰时的1万份跌至不足千份。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强迫望平街报贩在销售报纸时夹送日伪报纸销售,此举亦遭到爱国报贩的集体抵制。1939年汪精卫降日后,引发粤港两地民情大愤,香港报贩遂联合起来,宣言拒售汉奸报纸。当年“八月十一晚(粤港)各区报贩,召集全体大会一致通过,签名不售汉奸报,十二日晨,并推派代表分头向所有报贩接洽通知”(扫荡报—桂林,1939)。到8月13日起,与汪伪派系相关的众多汉奸报纸在报贩的抵制下绝迹于香港市面,此举沉重打击了汪伪报纸在华南地区的扩张。
3.与报馆争利
报贩与报馆博弈的核心是争夺报纸销售利润。报馆经营追求赢利,报纸销售以薄利多销为主。自从报纸销售被报贩垄断后,报馆盈余即有相当部分被报贩从中“分肥”。在报价长期固定难涨、读者群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报馆与报贩之间围绕报纸批发价格的争夺势必愈演愈烈,利润之争成为报贩与报馆矛盾的根源所在。
在近代中国报业市场,新报纸若想打开市场销路,首先要免费赠报委托报贩代销,通过给报贩组织的让利换取市场的拓展。报人萨空了回忆,新报发行之初,很多报馆“完全白送给报贩令其售卖一周或三天”(萨空了,1944:159),以此激励报贩售报。这种报馆让利于报贩组织的情况,在全国报纸销售中是普遍存在的。在南京,即使“门槛最精的报馆”,也会按照和报贩“讲妥的最优待条件”,于销售之初“送报三天”,此后再“对折三天”(香海书报,1946)。这种优待报贩的让利促销,令报贩在与报馆的价格博弈中时常占据相对有利的位置。更有甚者,让利过后报馆若想恢复正常报价,还需孝敬报贩一笔“小费”(王定九,1934:542)。在上海,对于报馆的赠报和让利,大小报贩甚至形成了独特的牟利手段。民国时期,上海报馆竞争激烈,更迭频繁,报馆为争取报贩支持赠报情况甚多。小报贩在获得赠报后,多以销售价格卖给读者从中谋利。大报贩则虚报销量,欺骗报馆增加赠报份额。例如某报贩,日销报纸仅有2000张,却要求报馆赠送2—3万张报纸,如果报纸销售不掉就将多余报纸以“每斤不过十几个铜板”的低价按“废纸”卖掉,由于赠报数量庞大,仅卖废纸大报贩依然可以获利颇丰(常识报馆,1928:38)。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有人曾计算过报馆和报贩之间的利益博弈。资料显示,当时报纸批发给大报贩价格低廉到“每张对开报纸只批二个铜板(即20文钱)”,“普通的四开报每一张只批十二文”。大报贩只要“经一经手”即加价几文钱批发给小报贩从中取利。“大报贩专做报馆和小报贩的居中介绍人”,盘剥之后报纸最后经“小报贩”之手卖给读者。“一张小报”读者购买价格为二个铜板(两个铜板面值20文钱),而报馆实际仅收十二文钱。另外的八文利润,大报贩从中经手抽取三文,小报贩沿街叫卖分得五文。据此推算,一个小报报馆如果按照“每期实销五千份”计算,实际收入仅为“六十千铜板”,而“大的报贩”,“却一人要独拿十五千铜板”。报馆因经营支出较报贩为多,因此时常抱怨“报贩赚钱太易,但是这是没有法子的”(常识报馆,1928:37)。
忌惮于报贩的势力,报馆若想通过提价来增加利润,就必须征得报贩的同意。若报馆擅自改价,报贩便会“强词夺理,作种种不近情理的要求,要求不达更会集体拒销”(詹文浒,1946:124)。1931年,徐州销售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欲将报纸提价,消息一出即遭到了当地报贩的集体抵制。报贩罢工导致《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外埠报纸无法在徐州市面销售,最终迫使当地报业公会暂缓加价(大公报,1931)。1938年广州越华、国华两报馆想提高报价,遭到报贩200余人的抵制,最终迫使报馆让步(劳动周报,1938)。1948年9月,北京《世界日报》也曾因提高报价遭到报贩抵制,当日报纸被一众报贩堵在报馆内不让派送,迫使该报发行受阻,冲突结果以报馆暂缓提价妥协收场。
在实际售报中,报馆很难监管报贩个体的销售行为,有些时候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报贩也会根据供需情况随意定价,损害报馆利益。上海《生活》周刊创刊后十分热销,报贩就加价销售,极大损害了该刊的市场信誉(生活,1929)。在天津,报贩售报时常“因人而异”,如是“熟人”“可以白看”,但若购报者“眼生”,那就“随意要钱”。这种任意定价售报的现象,在天津报贩中“恐怕十个有八个都是这样的”(三六九画报,1943)。报纸明码标价销售本应是正常的市场规范,报贩任意改价售报,不仅增加了购报者的负担,更严重损害了报馆的商业信誉。
除了改变报纸销售价格外,报贩还会采用“租报”方式来赚取利润。民国时期,租报在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十分普遍。南京报贩曾自述,他每日傍晚时将当日贩卖剩下的报纸送到夫子庙各茶坊,给吃茶的人阅看,每份收铜元二枚不等(申报,1921)。该报贩每月卖报收入加起来净赚二十五元五角,其中租报收入便占了八元,足见“租报”利润在报贩收入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租报主要是满足无力购报或者对报纸价格敏感的底层民众。通常报贩在茶馆中将报纸以低廉价格租给多人传阅,第二天再将未能卖出的旧报纸悉数返还给报馆,不仅无需增加本金的投入,还能从中赚得一笔“额外”收入(快活林,1946)。租报过程中,读者的租报价格远低于其购报价格,租报可以多人传阅不受次数限制。租报的结果是读者降低了阅报成本,报贩获得了额外收益,唯有报馆颗粒无收蒙受损失,报纸销量亦因此大受影响,尤其是销量不高的中小报馆,更是因租报的存在而难以为继。他们为此哀求报贩和读者,“周报除了少数营业稳定外,没有一家不是亏折的,都打算要停办了”,“向租报的读者讨饶”(海光〔上海1945〕,1946)。
三、余论
报贩组织与报界的复杂互动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幅特殊的图景。在近代中国报业经营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发行量小、资金少等问题,这使其难以建立起以报馆为主导的发行组织与销售网络。销量不振与经营困顿,使得中国报界大多无力承担自办发行需要的人力成本与资金消耗,将报纸发行和销售外包给“报贩”组织负责,即成为近代中国报界一种既无奈又现实的普遍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报业形态复杂,报贩组织对不同类别报纸的态度与影响,亦有所差别。相对于民营商业报纸,报贩对党派报纸发行的影响相对有限。例如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主要依托其政治组织和党员订阅来维持销量,从而压缩了报贩辗转腾挪的空间(方汉奇,宁树藩,1996:456-257)。1927年国民党控制上海后,通过拉拢和渗透,加强了对报贩组织的控制和行政干预,使其逐步沦为国民党政权的帮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日盛,曾招致国民党政府的嫉恨。迫于抗战形势,国民党并不敢明目张胆地禁售该报,只能暗地指使重庆报贩工会头目邓发清拒卖《新华日报》。为摆脱报贩的讹诈,《新华日报》克服各种阻力,自建了一支以少年儿童为主的“报童”销售队伍,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持发行斗争,成功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张帆,2017:200)。1944年,邓发清因“挟制报社,操纵批价”,被送交法院受审(重庆档案馆,1944a)。然而,反动组织三青团及国民党报纸却以此人“以前牵制《新华日报》多出其力”,未来“打到《新华日报》尚须赖其力量”为由干预司法,最终使其逍遥法外,案件亦不了了之(重庆档案馆,1944b)。可见,在政治权力的渗透下,民国的报贩组织与国民党报业有着紧密的合作,沦为其控制言论和报界的工具。
报纸发行是报纸经营的命脉,纵观中国近代报业的发行和销售,长期被报贩组织所垄断和控制。报贩对上敲诈报馆,对下肆意剥削底层报贩,成为横亘在报馆与读者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黄天鹏认为,中国报纸发行较之欧美来说,“读者之负担重,而报馆所得又较微,此中获利者乃居中之报贩,此应设法改善也”(黄天鹏,1930:84-85)。燕京大学新闻系则在调查报馆经营后得出结论,“报纸之营业,完全攥入报夫之手”(燕京大学新闻学系,1932:25)。民国时期,报馆收入被报贩组织侵蚀和盘剥,压缩了报业投资与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报贩组织不对读者负责、不受报馆约束,在二者之中蚕食发行利润的行为,是中国近代报业长期存在的顽疾。在报贩组织内部,行规遍布,等级森严,其运营充满了封建行会的垄断性质与世袭色彩。报贩之间层层剥削,相互倾轧,实际的厚利“为少数头目分子所独得”(申时电讯社,1934:162),而广大底层报贩却操劳终日,“每日所得,不足糊口”(远东饭店日刊,1926)。
面对大报贩的控制,近代报人曾大声呼吁打破报贩销售垄断权,汲汲渴求建立一支以报馆为主导的报纸发行系统。燕大新闻系程其恒指出,“发行的生路,必在打破报贩操纵而变成直接送达阅户”(程其恒,容又铭,时间不详:58)。余润棠则提出,“一个进步的报社,负责任的社长、经理都应该有一个建树新的发行网的决心”(余润棠,1947:32)。报人马星野更是大声呼吁:“发行问题,为办报者最感棘手者”,当彻底“取缔报贩制度,使报纸收入,不致为‘报阀’所中饱”(马星野,1944)。在行动上,《申报》、《新闻报》都曾尝试自办发行,但终因受迫于报贩组织的压制而无果而终(王英,2000)。近代报贩组织其内部组织依附性强、行动高度统一,能够合力应对报馆的挑战。反观报界则往往单打独斗,缺乏团结,最终难以摆脱被报贩盘剥的命运。像《新华日报》这种招募报童自办发行摆脱报贩控制的成功案例,在民国报业史上可谓凤毛麟角。
历史证明,中国近代报业运作经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化工程,它既包括技术物质方面的“硬件”积累,也需要经营观念和产业组织的“软件”配套。近代中国报界常以“独立”为期许,他们多视报贩头子为“报阀”,对之嗤之以鼻,不屑与其为伍。但在现实中,报界又不得不与之曲意迎合,通过周旋与让步来换取利益,这种矛盾折射出中国近代报业经营的困难与孱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报业实行“邮发合一”制度,旧中国的报贩组织被彻底改造,中国报业至此才得以挣脱报贩的束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注释:
①相关成果包括:洪煜(2008)。《近代上海报贩职业群体研究》。《史学月刊》,(12),67-72;洪煜,付晓琳(2019)。《权力文化视阈下的近代上海报贩组织研究》。《史学月刊》,(11),87-94。这些研究着重关注了报贩的群体组织与生活状况,但对报贩对于新闻业的影响鲜有涉及。目前以新闻史为视野涉及报贩的成果仅有王润泽(2007)。《民国前期中国现代报纸的发行途径及其潜规则》。《国际新闻界》,(7),75-80。其中一节“报贩及其对报纸发行的牵制和制约”有过初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微闻(1933)。上海之报贩。《新蜀报》1933年11月21日。
炯炯(1926)。望平街上四大金刚。《上海画报》1926年9月18日。
曹聚仁(2011)。《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回忆录(修订版)浮过了生命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洪煜(2008)。近代上海报贩职业群体研究。《史学月刊》,(12),67-72。
洪煜,付晓琳(2019)。权力文化视域下的近代上海报贩组织研究。《史学月刊》。2019,(11),87-94。
王润泽(2007)。民国前期中国现代报纸的发行途径及其潜规则。《国际新闻界》,(7),75-80。
陈荣广(1919)。《老上海(上册)》。上海:泰东书局。
詹文浒(1946)。《报业经营与管理》。南京:正中书局。
内藤乾吉原校(1987)。《六部成语注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戈公振(2018)。《中国报学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钱伯涵,孙恩霖(1940)。《报馆管理与组织》。上海:申报新闻函授学校。
申报(1947)。申报七十五周年二万五千号纪念·七十五年来:本报的广告发行及其他。《申报》1947年9月20日。
马光仁(1996)。《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姚公鹤(1989)。《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申报(1927)。报贩陆行逊君逝世。《申报》1927年9月2日。
上海市政协文史委(1996)。《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上海:上海人民社。
陶然(1945)。上海报贩的特殊势力。《华文大阪每日》,(10),16-17。
著者不详(出版时间不详)。《新闻学》。上海:文化函授学院。
北平实报社(1936)。《实报半月刊》。北京:北平实报社。
池择汇(1932)。《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北京:北平市社会局。
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课(1932)。《杭州市经济调查(上下编合订本)》。杭州: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
大同报(1936)。南京报贩,老少共有五百余人,竞争甚烈生活艰苦。《大同报》1936年3月15日。
远东饭店日刊(1929)。谈谈报贩。《远东饭店日刊》1926年11月22日。
刘炎臣(1943)。《津门杂谈》。天津:三友美术社。
新天津(1933)。报贩争销路,持刀刺同行。《新天津》,1933年10月23日。
新天津(1931)。天津报贩劳教数千工人赠送本报匾额两方。《新天津》1931年11月2日。
申报(1937)。望平街的报市(1937)。《申报》1937年5月9日。
常识报馆(1928)。《常识大全(第1辑)》。上海:常识报馆。
王定九(1934)。《上海顾问》。上海:中央书店。
珑玲(1927)。昨日望平街观察记。《小日报》1927年2月22日。
快活林(1946)。苏州报贩与明报馆。《快活林》,(6),10。
著者不详(1948)。《报学杂志》。南京:中央日报社。
燕京大学新闻学系(1932)。《新闻学研究》。北京:燕京大学新闻学系。
现代上海市文化馆(1986)。《上海地方史资料(五)》。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张帆(2017)。《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新华日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民国日报(1928)。北平报夫爱国宣言不送顺天时报。《民国日报》1928年9月9日。
荒冠(1939)。排字工人制裁汉奸经过。《扫荡报—桂林》1939年8月24日。
萨空了(1944)。《科学的新闻学概论》。桂林:文化供应社。
香海书报(1946)。首都报贩之享。《香海书报》,(14),2。
大公报(1931)。徐州报贩反对沪报加价。《大公报》1931年8月1日。
劳动周报(1938)。报贩工人抗增报价。《劳动周报》第2卷第4期。
生活(1929)。关于报贩抬价的声明。《生活周刊》,(14),216。
三六九画报(1943)。天津的报贩。《三六九画报》,(6),16。
申报(1921)。报贩谈卖报的利益。《申报》1921年1月15日。
海光〔上海1945〕(1946)。向租报的读者讨饶出版人已濒绝境。《海光〔上海1945〕》,(21),5。
方汉奇,宁树藩(1996)。《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重庆档案馆(1944a)。《关于办理报业职业工会利用组织挟制报社案的呈函训令》。重庆档案馆藏。
重庆档案馆(1944b)。《整饬渝市派报业问题》。重庆档案馆藏。
黄天鹏(1930)。《中国新闻事业》。上海:上海联合书店。
申时电讯社(1934)。《十年:申时电讯社创立十周年纪念特刊》。上海:申时电讯社。
程其恒,容又铭(时间不详)。《记者经验谈》。出版者不详。
余润棠(1947)。《新闻学手册》。上海:纵横文化事业公司。
马星野(1944)。《言论与诽谤》。重庆《中央日报》1944年2月6日。
王英(2000)。张竹平广告理念初探。《新闻大学》,(1),65-67。
齐辉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抗战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心主任;张蒙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抗战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本文为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课题号:2019CDJSK01PT13)。